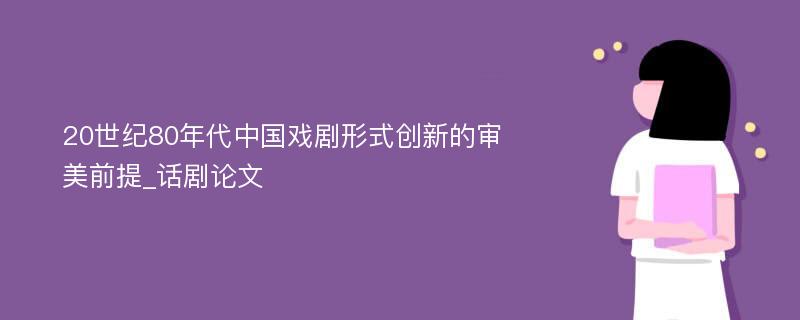
八十年代中国话剧形式创新的美学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前提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七十年代末,处于政治批判热潮中的中国话剧,因其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热点的剧种优势而在整个戏剧界独领风骚,万众瞩目。然而,话剧舞台仍然是写实剧的天下,而且在话剧创作思维上也体现出历时的、共时的惊人一致,那就是社会问题剧的模式。难怪一位罗马尼亚戏剧家在观看了当时的话剧演出后,说中国的话剧仿佛都出之一个导演之手。可见,中国话剧仍然没有钻出历史的怪圈,仍然在顺着过度强调政治宣传功能而忽视艺术独创性的思维惯性滑行。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范围的拓展,话剧创新求变的想法首先在一些青年戏剧创作者中间悄然萌动,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当代话剧形式创新思潮。
构成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话剧形式创新的美学前提,是背离写实剧传统的形式突破。当时许多形式创新的话剧,往往以突破传统写实剧的束缚来支撑其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著名导演胡伟民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创新观念:“我想突破什么,想突破七十多年来中国话剧奉为正宗的传统戏剧观念,想突破我们擅长运用的写实手法,诸如古典主义剧作法的‘三一律’,以及种种深受‘三一律’影响的剧作结构;演剧方法上的‘第四堵墙’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当众孤独’;表导演理论上独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家垄断性局面。简言之,想突破主要依赖写实手法,力图在舞台上创造生活幻觉的束缚,倚重写意手法,到达非幻觉主义艺术的彼岸。 ”(注:胡伟民《话剧艺术革新浪潮的实质》,《戏剧报》1982 年第7期)显然,胡伟民对如何突破传统写实手法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而对创造什么样的新的戏剧形式,则较为笼统。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国话剧界热衷于形式创新实验的戏剧家,基本上还无法提出与自己的形式创新实验相匹配的戏剧美学纲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屋外有暖流》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形式创新的剧目,该剧在话剧时空的自由转换、非幻觉的表演、人物深层心理的直接表现以及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给习惯于欣赏传统写实话剧的观众带来很大的震撼。可是,正如该剧作者所说:“这个戏在形式上属于哪个类型?我们没有认真想过,自己还有探索。然而,形式必须有新的探索,这一点我们是有意识加以追求的。我们吸取了我国传统的写意手法,对外国意识流小说和荒诞派剧作等表现手法,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注:贾鸿源 马中骏《写〈屋外有热流〉的探索与思考》,《剧本》1980年第6期)同样,《血, 总是热的》在话剧形式上的创新也颇引人注目,该剧演出后,有人问该剧的作者宗福先:这个戏的写法,属于哪一种流派。宗福先则回答说:“我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流派观念。当然,我有许多想法,但这些想法未能贯彻到底。”(注:转引之陈恭每《戏剧观念问题》,《剧本》1981年第5期)可见, 八十年代初期的戏剧家对新的戏剧形式的理解,还缺乏自觉而深入的美学思考,单纯的背离传统的形式突破,构成他们形式创新的基本动机和美学前提。同时,当时的戏剧评论界和观众对话剧形式创新的评判,也基本上从背离传统的角度出发,而背离传统的程度大小,往往成为评判戏剧形式创新的审美价值的主要美学尺度。
八十年代初期的戏剧家既然以突破传统写实剧的束缚为基本审美价值取向,那么,传统写实剧的美学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也规范了这一时期话剧形式创新的走向。依照当时戏剧家对传统写实剧审美特征的理解,其主要为话剧舞台时空上的封闭式结构、易卜生的情节剧模式和表导演方面的幻觉型模式。因此,话剧创新也主要从这几个方面作逆向延伸和发散,形成了与传统写实剧相对应的美学特征:
(一)开放式的舞台时空自由转换。封闭式的传统写实剧在舞台时空上强调与现实生活形态的严格一致,尤其象易卜生的《挪拉》、曹禺的《雷雨》这样的经典作品,更是恪守“三一律”的规范,全剧往往只有一个场景,最多也不过两三个场景,在时间上则基本对应于物理时间,称得上是封闭式舞台时空处理的极致。为了突破传统写实剧的封闭式舞台时空,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就致力于舞台时空的自由转换的实验。其一,通过多场次的方法来实现舞台时空的自由转换。王正的《迟开的花朵》,共有十一场,每一场更换一个场景,舞台空间转换就达十一次。陈白尘的新编历史剧《大风歌》,舞台上直接铺叙的时间达十五年,而场景变换更是多到二十三次,时空转换非常自由,而且频率极快,这样既能推进情节发展的速度,又能大大增加话剧表现生活的广度。其二,通过多演区的方法营造舞台现实时空和人物心理时空的自由而快速的切换。都郁的《哦,大森林》在第一幕里,将舞台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演区,当人物处于回忆中时,一个演区为现实时空,另一个演区则是人物内心的时空,其中的人物活动都只是心理活动的映象。类似这种舞台时空处理的还有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宗福先的《血,总是热的》等。马中骏、贾鸿源的《路》对多演区作了更为复杂的运用。除了上述两个演区,一为现实时空一为心理时空外,即使同一时空,也能随时从现实时空切换到心理时空。该剧为主人公周大楚提供了一个由演员扮演的“自我”形象,当这个“自我”形象出现时,现实的场景随即转入心理时空,因为周大楚与“自我”形象的争论自然属于人物心理活动。毫无疑问,这种多场次多演区的话剧时空处理,与传统写实剧封闭的时空模式相比,在舞台时空的自由转换以及表现生活的广阔程度方面,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二)非情节化的散文式戏剧结构。传统写实剧在情节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故事的完整性,剧中人物为情节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并基本贯穿始终,幕与幕之间、场面与场面之间的前后相依、层层推进等。八十年代初期的话剧形式创新,也表现在非情节化的散文式结构的广泛采用。沙叶新的《陈毅市长》就是较早出现的运用非情节化散文式结构的剧目。该剧摒弃了传统写实话剧的封闭式戏剧情节结构,将陈毅市长在上海一年间的经历分为十个片段,每个片段在情节上也呈散文化的态势,各个片段之间更没有情节上的联系,除了陈毅市长外,其余人物基本上不连贯。这种以情节上相对独立的片段连缀式的结构,被当时的评论称之为“冰糖葫芦式结构”。由于其片段组合的随意性和在戏剧时空组接上的较大自由,更接近散文的特点,因而,这类话剧也可以称为组合式话剧。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在全剧结构上也采用了片段组合的非情节化的结构形式,舞台的现实时空是一次审查主人公罗心刚的会议,而罗心刚始终缺席。因此,全剧一个个片段实质是会议参与者有关罗心刚的发言,罗心刚当凤凰厂厂长的改革历程正是由这些带有发言者个人情绪的片段组接而成。刘树刚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则通过路野萍为写有关离婚案的论文而到法院采访调查为由,将十五桩离婚案串联成一个整体,显示了话剧已经能象散文似伸缩自如,形散而神不散,在宏观表现现实生活整体面貌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另外,漠雁、肖玉泽的《宋指导员日记》和沈虹光的《五二班日志》,以日记的方式来串联全剧各个在情节上相对独立的片段,结构的散文化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总之,情节的淡化、散文化,作为对传统写实剧严密而紧凑的情节结构特征的背离,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非幻觉式的表演形式。以“四堵墙”为主要特征的写实剧幻觉式表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国写实剧传统的精髓之一。八十年代初期我国话剧在表导演形式上的创新,主要从突破“四堵墙”的幻觉式表演开始的。为了打破舞台“四堵墙”的限制,有的导演采用了小剧场形式。如胡伟民导演的《母亲的歌》采用了全方位中心舞台的形式,舞台设在剧场中间,观众围坐四周。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则是三面围坐观念。这两个话剧演出过程中,剧中人物的上下场就从观众中间经过,有时,演员就在观念身旁表演,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另外,话剧场面的频繁转换,往往需要舞台场景能随之迅速变换,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几何形状的中性道具,以随时代替规定的场景道具。苏乐慈导演的《路》,就采用了中性几何体道具,而且空间的划分和转换也往往通过灯光切割变换来实现,其虚拟的色采是很明显的。因此,演员表演时也不得不结合虚拟的方法,而不是纯粹写实的幻觉化表演。还有如《双人浪漫曲》、《放鸽子的少女》等话剧,出现了歌舞场面,以此探索非幻觉的表演形式。
如前所述,八十年代初期的话剧形式创新,在美学上虽然只是以突破传统写实剧的审美形式为前提,在创造新的戏剧形式时也往往缺乏新颖系统的戏剧观念的指导,然而,强烈的反传统思维,促使戏剧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勇气去借鉴传统戏曲和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表现手段,大大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语汇,以致在短短几年内,就基本打破了传统写实剧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示了话剧创新的勃勃生机。
二
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在突破写实剧传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单纯的反传统思维,也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因素。比如,对我国写实话剧传统定位方面的偏颇,也多少影响了话剧形式创新在美学上的整体突破。当时许多戏剧家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写实话剧传统一味归结为易卜生式的封闭型社会问题模式和幻觉式的斯坦尼表导演体系,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早在三十年代,曹禺、夏衍、于伶等剧作家就对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产生了疑议,《日出》、《上海屋檐下》、《夜上海》等剧作的出现,便体现了一种淡化情节的散文化戏剧的尝试,五十年代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则在散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话剧的史诗风格。田汉和欧阳予倩的非幻觉式写实剧的创作演出经验,也是不应忽略的。欧阳予倩早在三十年代就对幻觉式的写实表演提出批评:“写实主义简单的解释,就是镜中看影般的如实描写。不过这也不限于存形,何尝不可以存神?尤以形神并存方为上乘。灵的写实当然不能忽略,所以不妨拿写实两个字广义地解释一下。譬如三一律第四堵墙之类,本来无遵守的必要。”(注:欧阳予倩《戏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欧阳予倩研究资料》第231页)欧阳予倩的《桃花扇》和田汉的《丽人行》,都采用了多场次戏剧形式,而且两剧都摈弃了自然主义布景以适应场景的频繁转换,在表演上也充分发挥了虚拟手法的作用,强化了非幻觉色彩。可见,在戏剧美学上,写实与非写实的区别并非仅反取决于多场次多时空和非幻觉的特征,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除了象《车站》等话剧外,大多数话剧的形式创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背离写实剧审美形式的范围。另外,因为话剧形式创新思潮尚不具备相应的美学积淀,而仅仅以背离写实剧传统作为前导,这就必然会形成许多创新话剧在审美形式上的不平衡,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无法成为戏剧家深刻把握现实的利器,新的戏剧形式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观念的陈旧肤浅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和谐的倾向。所以,只有在话剧形式创新的同时融入编导对人类命运,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切关注和独特思考,话剧形式创新才会获得整体的飞跃。
不过,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思潮的出现,为话剧美学观念的更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1983年前后,话剧理论界从戏剧观念的更新入手,形成了一场南北呼应的全国性戏剧观大讨论。在中国话剧史上,“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对易卜生写实主义戏剧的倡导,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到中国传授斯坦尼体系,理论观念的更新走在了戏剧创作的前列,并对创作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指导性。另外,1962年著名导演黄佐临发表了《漫谈“戏剧观”》一文,这是当代话剧发展中罕见的公开阐述自己独特戏剧美学观念的纲领性文献,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在当时的戏剧创作中产生应有的影响。在更多的时间内,我国戏剧理论在美学观念更新上往往滞后于戏剧创作的实践。八十年代初期,戏剧理论界对话剧形式创新的反应较为迟缓,事实上,有关话剧形式创新的文章,大都只是从中外话剧史中寻找例证为话剧形式创新的合理性辨护,而缺乏在戏剧美学层面上的开创性的观点。随着话剧形式创新的发展,话剧观念的讨论也逐渐趋于深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从美学角度对戏剧本体的强调。一切戏剧形式在其本质意义上都可以还原为观众、演员和剧场这三个基本元素,而戏剧本体就是这三个基本元素的统一。正是这种建立在美学观念上对戏剧本体的重新确认,从根本上推翻了独尊写实的传统话剧观念,同时也为一切戏剧形式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实现了戏剧观念的彻底解放。所谓戏剧观的彻底解放,并非只意味着对非写实话剧形式创新的肯定,也是对写实话剧的审美价值的承认,写实话剧形式的审美变革同样是当代话剧形式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戏剧观念更新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当代戏剧家已经不再简单地从写实与非写实的角度来衡量话剧形式的创新与否,而是将形式的创新作为张扬各自主体性的审美实践,努力去寻找一种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个性化方式。
85年初《魔方》的创作演出,既是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的顶点,也是话剧形式创新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魔方》无论在话剧形式和观念上都是对传统写实剧的彻底反叛。其一,表层形态杂乱到极点。《魔方》取玩具魔方的寓意,共分九个片段,犹如魔方的九个方块颜色都不同,九个片段各自独立成章,不仅情节上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风格上也相异其趣。主持人作为唯一贯穿全剧的人物,却与全剧九个片段的规定戏剧情境无关。然而,主持人又每每进入戏中,忽而发表评说,忽而与剧中人调侃,忽而又跑到观念席里即兴采访观众。《魔方》可以说全面推翻了传统意义上的编剧法,同样,如果仅就非幻觉式表演形式的创新而论,《魔方》也走到了极点。其二,杂乱的组合却隐含着完整的哲理性结构。九个片段,九九八十一个主题,还可以进行九的二十次方的变化组合,但万变不离其宗,魔方每个层面上始终保持九个片段(色块),所以,《魔方》既象征了现实社会纷繁多变的内在结构,也暗示了宏观把握现实社会本质的辨证思维方式。其三,模糊。《魔方》不要求观众作简单社会学的、伦理的判断,而是上下左右飘忽不定,诱惑观众自己去思考。其四,舞台界限、观众和演员界限的打破。主持人可以随意邀请观众谈观感,演员也可以从角色中游离出来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表真实的见解。剧场气氛活跃、效果强烈。因此,《魔方》可说是集八十年代初期话剧形式创新之大成,对传统写实剧传统的背叛也更彻底,然而,与前期创新话剧相比,《魔方》又显示了一些新的创作倾向。比如,戏剧家主体意识的加强,即不仅力求形式的更新,而且巧妙地将新的形式作为把握现实生活的独特方式,与内容构成统一的艺术整体,这样,新的形式则意味着内容的深化。另外,《魔方》的作者将全剧的结构归结为马戏晚会似的组合,也说明了一种立足戏剧本体的自觉而明确的美学追求已经开始融入戏剧家形式创新的全部过程。
三
从85年的《魔方》开始,我国话剧形式创新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当代戏剧家在戏剧观念更新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单纯的突破传统戏剧形式的思维方式,确立了新的戏剧形式创新的美学前提:立足戏剧本体的自由创造。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话剧创新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立足戏剧本体基础上,戏剧家纷纷开始努力营建和丰富各自美学风格,形成了多元并存、各显神通的创作格局。
(一)哲理化的组合式话剧日趋成熟。这一时期散文化的组合式话剧表现出浓郁的哲理化倾向,如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赵耀民的《天才与疯子》、刘树刚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从容的《爱的构思》、宗福先的《传呼电话》等,在片段的组合上不循旧章,标新立异,然而,这些片段经过精心而独特的组合,既取得表现社会现实的宏观视界,最大限度地展示社会面的宽度,容纳尽可能多的社会信息;同时,又能暗合哲理性的象征性框架,传达出创作者主体的独特思考,具有浓郁的哲理思辨性。
(二)话剧综合元素的全面呈现。剧作家高行健和导演林兆华一直致力于多种艺术元素综合表现的戏剧实验,歌、舞、声、光等均在他的戏剧中占据独立的地位,具有戏剧语汇的功能,创造了一种多声部的戏剧。《野人》可视为这种多声部戏剧的代表作。原始的舞蹈、原始的号子、原始的歌谣、现代人复杂多变的意识流动,以及寻找野人,滥砍森林等事件的铺陈、分别从感觉的层面、现实的层面和意识难以渗透的神秘的层面扑向观众,刺激观众从不同的层面与戏剧演出形成反馈。王培公的《MW我们》写一群知识青年插队以及回城后的人生经历,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章节。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员扮演角色各异,但衣服却都是一种颜色。形体、色块成为重要的舞台语汇,既可以组合成具体的场景,又能演绎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在高行健等戏剧家看来,话剧不应该姓“话”,在他们的戏剧实验中,对话确实失去了主导地位,而成为戏剧综合元素中的一般成分。高行健的《彼岸》,干脆取消了对话,演出全靠形体和其他艺术元素的综合。
(三)写意话剧的斐然成就。黄佐临早在1962年《漫谈“戏剧观”》一文中就阐明了自己对写意戏剧的钟情。八十年代,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念也趋于成熟,其基本美学原则是以写意传神为内核,强调舞台的自由叙事功能,注重表演真实感与美感的结合。1987年,黄佐临所导演的《中国梦》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写意戏剧的美学特征。全剧的人物有六、七个,但演员只有两个。男演员要同时扮演年龄、身份差异极大的多个角色。黄佐临卓有成效地从传统戏曲中借鉴了虚拟手法和形体动作的造型美,在叙事传情方面显得游刃有余,可以在舞台上任意表现他想表现的意境。如该剧著名的“放排”一场,湍急的河流上一男一女正在放排,没有排,也没有竹篙,更没有河水,但在演员传神的虚拟表演中又似尽在眼前,并且姿态优美,既是剧中戏的推进,又象在表演舞蹈,可谓美伦美奂。最后一场,竟然在舞台上模拟起美国海滨划水的场面,也照样潇洒自如,让观念惊叹不已。罗剑凡的《黑骏马》、徐频莉的《芸香》,在表演上也充分显示了写意戏剧形式的独特魅力,在剧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写实话剧的重新崛起。这一时期的写实话剧显然度过了美学上的彷徨期,通过对写实话剧的审美形式的大胆创新,走向了创作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称得上是八十年代话剧的优秀之作。如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朱晓平等人的《桑树坪记事》、马中骏、秦培春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沈虹光的《寻找山泉》、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古塔街》、郝国忱的《榆树屯风情》、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等。这些话剧在审美形式上基本呈现三种面貌:一、艺术方法上仍然保持整体的写实风格,但在全剧意蕴的开掘上却融入新的文化观念,赋予全剧浓郁的哲理性和象征性色彩,以强化写实场面的抽象因素。如《天下第一楼》,全剧的演出严格按照幻觉式的写实方法,然而,编导在人物塑造和剧情发展中,着重强化“窝里斗”现象的文化历史内涵,使剧中福聚德烤鸭店的盛衰命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某种象征性的联系,具有深厚的思想力度。《田野又是青纱帐》在全剧风格上也是写实的,而且剧情时间限定在一天之内,场景也基本集中在村口。但剧作家李杰却有自己新的美学追求:“我不是要写文化的物质表层,而是想表现青纱帐后面的恒定的生存,我想挣脱以往人云亦云的制造戏剧的观念。”(注:李杰《李杰剧作选》第1页)他在剧中展示的所谓“青纱帐文化”,是由长期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狭隘、封闭、停滞、愚味的恒定的心理特征,在改革的浪潮中如何变化、调整、抵抗和歪曲的过程所组成的一幅幅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性的人生图画。二、将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活动也纳入写实的审美范畴,创造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心理剧。既然人物深层心理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而人物深层心理也是应该是写实话剧表现的题材。当然,人物深层心理活动有其特殊的逻辑构成,不同于外部的、日常生活的逻辑构成,因此,表现人物日常活动与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活动之间必须作出艺术手法上的不同选择。比如,《狗儿爷涅槃》的整体风格是写实的,全剧在人物的行为和台词的运用上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真实感,但又运用了表现主义的方法将狗儿爷深层的心灵搏斗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但是,这种深层心灵搏斗的展示,并不妨碍整个戏剧行动仍然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方式推进。在结构上,该剧采用戏剧似的多场次结构,有戏则长,无戏则短,以适应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的随时转换。该剧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上述的形式上的变革,主要的是这些新的形式因素被剧作家用来深化人物性格的刻画,取得极好的效果。狗儿爷是个地道的农民,曾受尽地主的压迫,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地主一样强烈,而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发家致富,当地主。当现实粉碎了他发家致富的可能性,可这种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他不时在灵魂深处与地主祁永年的较量,就是这种欲望的披露。由于剧中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与外部现实的行为始终处于比较的状态,使狗儿爷这个农民形象拥有了极为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如果运用传统写实剧的方法是很难达到这种人物刻画的深度和现场的震撼感。三、写实主义与传统戏曲以及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兼容,而整体上则以写实主义为主。这方面徐晓钟是功不可没的,徐晓钟在戏剧实验中逐渐形成自己明确而成熟的美学主张:“兼有叙述体戏剧和戏剧性戏剧的特征。表现和再现两种美学原则的结合,情与理的结合,在破除生活幻觉的同时创造诗化的意象。”(注:徐晓钟《在兼容与综合中嬗变》,《戏剧学习》1988年第2期)他导演的《桑树坪记事》就是这种风格的写实话剧的经典之作。他对该剧的导演阐述是:“以再现原则为主,糅进表现原则的美学特征。”(注:徐晓钟《在兼容与综合中嬗变》,《戏剧学习》1988年第2期)一方面是极为真实的写实表演,李金斗等人物形象也塑造得神情毕肖、栩栩如生,另一方面则用表现主义等艺术手段通过歌队、舞蹈等以现实层面上的人物命运和事件进程予以抽象的概括,强化了编导对这些发人深省的现象的理性思考。在青女被犯有羊疯子病的丈夫扒下裤子的一场戏里,整场戏的表演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当青女被羞辱的时刻,表演随即转换为表现主义的形式。青女化作了一尊残缺的维纳斯石雕,村民们化作了歌队,生活的事件被抽象为对落后封闭的文化的理性批判。胡伟民导演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从极端的写实逐渐走向象征,最后,所有的实物都还原为几何体的色块,人物的服饰也成为单色调的色块,色块的流动和不断的重新组合拼凑成对全剧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象征性的符号结构。
(五)象征主义戏剧挟形式创新之雄风,也悄然亮相。自话剧在中国诞生以来,象征主义话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49年以后,象征主义戏剧那种扑朔迷离、隐约其词的审美特征在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环境中是很难生存的。然而,当代话剧立足戏剧本体的多元化戏剧创新格局的形成,终于使这颗深埋在地下多年的话剧种子破土而出。余云、唐颖的《二十岁的夏天》在87年初由导演胡伟民搬上舞台,这是中国当代象征主义话剧一次完整的演出。《二十岁的夏天》选取了一个青春浪漫的剧名,而它所展示的却是荒岛上无端掀起的一场极其压抑、极其变态、极其残暴的普查麻风病的骚动。编导无意强调这场非人性骚动的时间和地域特征,而是简化、抽象化、符号化,这就大大扩展了演出所包容的象征性外延。它既可以被看作是对“十年文革”的象征,而同时又能被当作是对人类面临非人性化威胁的象征性符号,或者还有更多的联想和意会,这主要归因于全剧整体内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另外,贺子状等的《山祭》、《火祭》、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时装街》、徐萍莉的《芸香》、《老林》等象征主义话剧的相继演出,也在当代剧坛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象征主义话剧的主要特征是:一、题材的寓言化。上述剧作都不同程度采用了寓言的方式,企图用一种极为单纯而又浓烈的故事去印证或暗示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隐含的内在结构,以换取某种本质上的理性沟通。二、表演的风格化、形式化。由于全剧故事单纯,情感强烈,因而导演就有充分的余地强调形式本身的符号化的视觉象征。比如,人物的形体除了演绎故事的内容,还有传达象征形式所内蕴的独特含义,这就使演出充满了具有现代美感的舞台造型。三、多义性。演出有意留下大量的叙事空白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填充,而不愿作任何直接的解释和提示。这就造成了剧作读解或演出欣赏时的多义性、模糊性。
总之,随着《魔方》将悬挂在当代戏剧家面前的种种传统的清规戒律统统扯倒后,戏剧的天地不仅没有崩塌,而且还更加辽阔和诱人。从立足戏剧本体的美学前提出发,85年以后的戏剧创新更多的表现在新的戏剧风格的开创,以及戏剧家主体性的张扬。诚如美国著名戏剧理论家盖斯纳所指出的:“现代剧作家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到自我的派别,这对任何熟悉戏剧的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任何一位剧作家如果他的货色煌煌然引人瞩目并且成为批判界如此难得的众矢之的,就不外乎是这种意识到自我的人。”(注:转引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第73页)正是由于当代中国戏剧家在创新中强调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创造,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入自我风格的完善和戏剧美学的思考。这一时期在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以外,还出现了徐晓钟再现与表现兼容的美学观念,高行健回归戏剧本体的多声部戏剧的美学原则,胡伟民营建符号化的诗意空间的导演美学思想等等,在这些美学观念指导下创作演出的《中国梦》、《桑树坪记事》、《野人》、《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都渗透着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具有独特的戏剧审美价值,在艺术成就上也称得上当代话剧的精品杰作。另外,许多戏剧家虽然没有发表有关的戏剧美学观点,但他们往往通过具有形式连续性的戏剧创作来发展自己的戏剧美学思想。如锦云的《狗儿爷涅槃》和《背碑人》,李杰的《田野有是青纱帐》和《古塔街》,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和《时装街》,徐萍莉的《芸香》和《老林》,沙叶新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耶酥、孔子和披头士列侬》,刘树刚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和《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些作品不仅在戏剧形式上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且在美学风格上也呈现着一种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这一时期的庆剧形式创新实验,不仅在创作演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由于戏剧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在美学观念的更新创造方面也显得更加自由、自觉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话剧形式创新才真正实现了对七十多年中国话剧传统的整体突破,书写了中国话剧史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