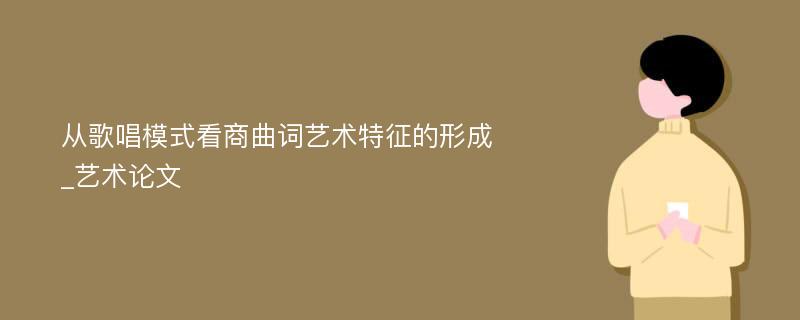
从演唱方式看清商曲辞艺术特点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艺术论文,商曲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晋南朝时期,清商旧乐逐渐衰亡,代之而起的是源于江南民间的清商新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清商新声分为六大类:吴声歌曲、神弦歌、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雅歌。其中吴声歌曲和西曲是构成清商新声的主体部分,神弦歌为吴声歌曲中自成一体的特例,是南方祭祀神灵鬼怪的祭歌。这三类大约产生于东晋、宋、齐三代,其歌词与曲调也多源自民间。而后三类产生于梁代,是文人们对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的仿作。因此,探讨清商新声的发生源头、形式体制及语言特色等问题,首先应该从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入手。现存吴声歌曲326首,西曲142首,其内容几乎全是情歌,而五言四句的形式体制约占近80%。这些特点的形成,固然与贵族阶层的爱好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作为民歌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它们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早期的实用功能,对它们的艺术形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无疑更大,而这些情歌在“被诸管弦”时又要受到音乐体制和表演方式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未作深究,本文则想从这一视角对吴声和西曲做重新审视。
一
现存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为什么几乎都是情歌?对这个问题,以往的解释是“六朝贵族阶级采录了江南民歌,制成美妙的吴声和西曲,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工具。他们当然不会中意于……讽刺本阶级的充满战斗气味的歌词,因此,在吴声和西曲中间,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哀感顽艳的情歌”①。这种解释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因为除了这些“充满战斗气味的歌词”外,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其他歌诗也不见于现存南朝民间歌诗。如果把这一点与汉代乐府及北朝乐府相比,就更为明显。因此,如果现存情歌的确是经过采录者选择的结果,那就意味着南方民歌中实际存在的情歌要远远多于被采录的情歌,否则采录者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可以肯定南方民歌中情歌的数量与其他题材的民歌相比也同样是占绝对多数的。
那么,南方民歌中情歌发达的原因何在呢?据考证,吴声歌曲大约产生于东晋、刘宋两代,是以扬州治所建业为中心的吴地一带的民歌;西曲歌大约产生于宋、齐、梁三代,又以宋、齐两代为多,是以荆州治所江陵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民歌。②一个地方的情歌往往与该地的婚姻习俗是密切相关的,婚姻习俗的基本状况,总会在情歌中得到反映。台湾学者洪顺隆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以大量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了荆、扬二州自上古以来即为夏民族的活动地区,在商汤灭夏以后,活动于此的主要是由夏民族和殷商民族相互混化而成的百越族。直至东汉时期,百越族还保留着其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而现代西南地区的布朗族和纳西族本是荆、扬一带越人的后裔,因此可以肯定,至今流行的布朗族的实验婚和纳西族的阿注婚,均与荆、扬越人的婚姻习俗有渊源关系,亦即与吴声、西曲中所反映的婚俗有关③。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粤歌”条中说:“粤(越)俗好歌,凡有吉庆,必歌唱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又说:“东西两粤(越)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洪顺隆则在吴声、西曲中找到了反映阿注婚遗迹的20余首歌诗,这些歌诗中明显地反映出男到女家访宿的风俗和对歌的痕迹。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些民歌“有可能是在流行着‘阿注婚’的社会风俗地区居住的、尚保留着原始百越族的风俗习惯的越人后裔的作品”④。洪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是以现存风俗与六朝民歌互证的方法,由于民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虽有变化,但其本质性的内容却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故越人后裔纳西族的阿注婚与六朝吴声和西曲的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而这也正是荆、扬一带情歌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
学者们认为,清商新声的歌词“大抵采撷或摹拟江南的民歌”,“几乎纯是创新的部分”⑤。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清商新声的早期形态实际上就是荆、扬一带越人的情歌。东晋以来乐官的采录、加工当然会对清商曲辞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清商曲辞艺术特征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恐怕不是采录者,而应当是被采录之前江南民歌的本来特征。所以源于江南越人婚俗的荆、扬民间情歌,既是认识清商曲辞早期形态的一个基点,也是探讨清商曲辞后来特征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关键。
二
以情歌为主的南方民歌,其实用功能主要是用来实现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这其实也是人类特殊的交际方式之一,它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就曾普遍地存在并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对诗歌最早的理论解说是“诗言志”,虽然从文献中来考察,这一概念的出现比较晚,就是“言志”的说法,在文献中也只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说文》将“诗”解释为“志也”,闻一多先生从卜辞字形出发,对此作过详细的考辨。他认为卜辞中的“志”字,其上半部从“止”,而甲骨文“止”字“像一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训停止”,“‘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于心上。停止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故《荀子·解蔽》曰:‘志也者,臧(藏)也’,注曰:‘在心为志’,正谓藏在心里。《诗序》疏曰:‘蕴藏在心谓之志’,最是确诂。”又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⑥因此,我们认为“诗言志”的起源同样是非常久远的。“至少在歌、乐、舞综合艺术形态中,它已经存在,尽管当时的诗还很不成熟,但它所表达的也仍然是‘藏在心里’的‘志’,而且,其时用以‘言志’的又不仅仅是诗,而更主要的恐怕倒是舞、乐与歌。至于日后的‘诗言志’自然是由此发展而来。在根本的意义上,前者构成了‘诗言志’观念产生的文化前提,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日后的特征。”⑦对此朱自清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可以见出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传统的一贯,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时结恩情,做恋爱用乐歌,这种情形现在还常常看见;那时有所讽颂,有所祈求,总之有所表示,也多用乐歌。人们生活在乐歌中。乐歌就是“乐语”;日常的语言是太平凡了,不够郑重,不够强调的。明白了这种“乐语”,才能明白献诗和赋诗。这时代人们都还能歌,乐歌还是生活里的重要节目。献诗和赋诗正从生活的必要和自然的需求而来,说它只是周代重文的表现,不免是隔靴搔痒的解释。⑧(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如果立足于上述观点,来重新考察吴声、西曲中那些情歌,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古代曾生活于荆、扬一带的越人较多地保留了古代文化的原貌,或者说较多地保留了“以乐歌相语”的传统,只不过他们不是将乐语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是主要在情爱生活的范围中使用。而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初民社会就已经普遍“以乐歌相语”,汉魏六朝时代的越人则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而在越人的后裔纳西族人那里,乐歌至今还是他们“生活里的重要节目”,由此可见,“以乐歌相语”的传统是怎样顽强地、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结恩情,做恋爱”既是南方民歌产生的基本前提和背景,也是其目的,并决定了情爱主题在这些民歌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而由这些南方情歌发展而来的吴声、西曲,其形式短小、语言通俗等特点也无疑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现存的吴声、西曲中,还十分明显地保留了南方儿女“以乐歌相语”的演唱特点。他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通过对歌的方式,用含蓄的双关语试探对方的心思,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情感,这种对歌的即兴创作模式在吴声和西曲中都有所表现,如:
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四十二首》三十一)
炭炉却夜寒,重抱坐叠褥。与郎对华榻,弦歌秉兰烛。(《子夜四时歌·冬歌十七首》其八)
侬本是萧草,持作兰桂名。芬芳顿交盛,感郎为《上声》。(《上声歌八首》其一)
郎作《上声曲》,柱促使弦哀。譬如秋风急,触遇伤侬怀。(《上声歌八首》其二)
初歌《子夜》曲,改调促呜筝。四座暂寂静,听我歌《上声》。(《上声歌八首》其三)
阿那曜姿舞,逶迤唱新歌。翠衣发华洛,回情一见过。(《子夜四时歌·春歌二十首》其十六)
上引第一、第二首中的“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与郎对华榻,弦歌秉兰烛”几句,正是男女对歌的真实写照。第三至第五首本是《上声歌》八首的一、二、三首,我们虽不敢肯定就是一次男女对歌的记录,但从上引第三首“感郎为《上声》”及第四首“郎作《上声曲》”的诗句可知,当时男女青年确曾有以《上声歌》互诉衷肠的习惯。由“柱促使弦哀”、“改调促鸣筝”、“阿那曜姿舞,逶迤唱新歌”等诗句可知,这些对歌除有特定的音乐伴奏外,有时还伴有舞蹈,实际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
由于一赠一答是现实中的男女对歌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因此,多数的情歌应当是以两首为一个基本单元。虽然在乐官采录、后来流传,以及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歌诗都将赠歌与答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很多歌诗原来的次序已被打乱,还有的歌诗只有赠答的其中一首流传下来,甚至有些歌诗今天已经很难确切地指认它是不是以赠答的方式即兴创作出来。但是,现存东晋南朝民间歌诗中,依然明显地保留了赠答特点的歌诗还是可以举出不少。其中又以吴声歌曲中的赠答之作较多,如《子夜歌四十二首》其一曰:“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其二曰:“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是男女一见钟情,互表倾慕的赠答。其六曰:“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其七曰:“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是男女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情不谐,爱情无望的赠答。类似的赠答之歌,《读曲歌八十九首》保留最多,典型的如:
执手与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六十二)
百忆却欲噫,两眼常不燥。蕃师五鼓行,离侬何太早!(六十三)
欢相怜,今去何时来?裲裆别去年,不忍见分题。(六十五)
欢相怜,题心共饮血。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六十六)
上引两组歌诗都具有明显的男女赠答的痕迹,而且这些赠答之歌在现存《乐府诗集》中还被置于相邻的位置,这说明当时的采录者以及后来的编辑者也注意到了赠歌与答歌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民间情歌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大约由于西曲的产生比吴声晚⑨,这种男女赠答的特点在西曲中远不如吴声中那么普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如《那呵滩六首》的四、五两首即是明显的例证:“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弯。原得篙橹折,交(教)郎到头还。”(其四)“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其五)。另外,受民歌的影响,文人拟作的歌诗也往往采取了男女赠答的模式。如《桃叶歌》共有四首,《乐府诗集》称前三首为《桃叶歌三首》,后一首单列: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明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
这四首歌诗,《玉台新咏》选了后二首,以为是王献之作,《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也以为是王献之作,但《诗纪》卷四十一注引《彤管新编》,认为除第三首外,其余三首为桃叶所作。从歌诗原作来看,第一首是以女性口吻写成,即使是王献之所作,也当是代桃叶立言的。故这一组歌诗基本上也是采取了男女赠答的方式。
此外,还有一些歌诗从其内容推测,应当也是赠答体,如《前溪歌七首》其一:“忧思出门倚,逢郎前溪度。莫作流水心,引新都作故。”《阿子歌三首》其一:“阿子复阿子,念汝好颜容。风流世希有,窈窕无人双。”这些歌诗在即兴创作时都是青年男女中的一方唱给另一方的,按实际情形,对方都应该有所回应,但现存歌诗中却只留下了两首或多首赠答歌诗中的一首。
《宋书》卷十九《乐志一》曰:“吴哥(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又在列叙吴声、西曲之后说:“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歌),既而被之弦管。”可见,南方民间情歌与吴声、西曲有着共同的产生背景。因此,吴声、西曲以表现爱情为主的原因自不必多说,而以即兴创作、演唱来实现求爱活动中的互相表白和互相试探,从根本上决定了吴声、西曲不可能长篇大论、典雅古奥,而只能是通俗易懂的短歌。这是吴声、西曲中五言四句的形式体制占到近80%及语言接近口语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
就汉代歌诗表演的总体情况来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汉乐府的演唱有比较复杂的乐调相配,歌舞音乐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歌词在演唱中是从属于音乐的。这使得汉乐府歌词不可能无限止地扩展。汉乐府歌诗的长度是有限的”,“从汉人的欣赏习惯来看,他们看重的并不是乐府歌诗中所表现的故事内容,而是对歌舞音乐的欣赏和情感的抒发,叙事在这里只占次要地位。”⑩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汉末、曹魏及西晋时期,故事性在歌诗表演中却越来越受到重视,产生于汉末的长篇叙事歌曲《焦仲卿妻》、西晋时期的故事体和代言体歌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虽然这些歌曲在当时究竟是怎样演唱的,目前还难以确切地考知,但可以肯定,这种强调故事性的歌诗表演艺术在这一历史时期已经非常兴盛(11)。依此,东晋南朝时期的歌诗表演艺术应当在此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事实上,演述故事的长篇叙事歌曲在这一时期却似乎突然销声匿迹了。在清商新声中,最基本的歌诗形式是源于南方民歌的五言四句格式,这与《焦仲卿妻》等长篇歌诗,甚至与西晋时期的故事体歌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清商三调曲和吴声、西曲的这种差异,王运熙是从清商曲辞与相和歌辞在音乐上的继承关系来加以解释的:
我们既知道相和古辞以四句为一解是普遍格式,而且承认汉魏古辞的“解”与吴声、西曲的“曲”在音乐上的地位相等,那末就无庸否认相和旧曲与清商新声中间的承递关系。而短小的吴歌,能直接代替篇幅较大的古辞(《相和歌》);吴歌的五言四句格,最盛行于清商新声中间;六朝清商新声每调曲词,多者达数十首,少亦绝不至一曲(合若干曲歌唱,等于《相和》旧曲的一曲)等等现象,其缘由均可由此迎刃而解了。(12)
这对于说明短小的吴歌何以能直接代替篇幅较大的相和古辞,并盛行于东晋南朝,的确是卓论。但是,却不能说明在汉魏西晋时期已经比较成熟的故事性歌诗,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清商新声每调曲词多者虽有数十首,然而各首之间的连贯性却并不是很强,尤其从演述故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各自独立、以抒情为主的吴声、西曲歌辞,不仅与汉代的《陌上桑》、《焦仲卿妻》等长篇叙事歌曲难以相提并论,就是同西晋时期的故事体和代言体歌诗也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歌诗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表演艺术,而故事性歌诗受故事情节和主人公情感变化的制约,所配音乐也自然要比单纯的短篇抒情诗更为复杂,因此,东晋南朝时期故事性歌诗的萎缩,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商新声在继承发展相和旧曲的同时,其音乐体制的变化已不再适合故事性歌诗的表演了。其主要原因恐怕与永嘉之乱对中原音乐的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对清商新声的声调,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或以为它“接受了不少相和旧曲的规模,承袭的部分也较多”,(13)或以为“在《清商乐》中间,虽然也包含着一部分旧有的北方民间音乐,但其主要组成部分则已是大量的南方民间音乐了”(14)。但确切的情形,学者们多语焉不详。从《乐府诗集》解题中可以知道,相和旧曲与清商新声在乐器及演奏方式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引《古今乐录》曰:“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其中,平、清、瑟、楚四调所用乐器稍有出入,但笙、笛、琴、瑟、琵琶、筝六种却是四调共同的(15),而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古今乐录》曰:“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案《古今乐录》为陈释智匠所撰,所谓“今”即指陈代。西曲又分为舞曲和倚歌两大类,舞曲所用乐器和演奏方式不可考,《乐府诗集》卷四十九《青阳度》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可见,吴声、西曲所使用的乐器均比相和旧曲少。
由于乐器较少,在演奏方式上,吴声、西曲也比相和旧曲要简单。《乐府诗集》解题引张永《技录》对相和旧曲各调的演奏方式均有简要的说明。杨荫浏据此作过细致的分析。依照杨先生的说法,相和旧曲的演奏方式前有器乐合奏,其中的笛和笙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合奏后有尾声,然后才是正式的歌唱。而歌舞大曲,在每次歌唱之后有“解”,在一曲的开始或中间有“艳”,结尾有“趋”与“乱”(16)。而吴声、西曲的演奏方式则相对简略,只有“和”与“送”。据王运熙的研究,“送声与大曲的趋、乱确很相像,而和声与艳辞就可说毫无共同之处了。”“送声的位置,应在全篇末尾,自不成问题;至于前面的和声,却并不如《大曲》的‘艳辞’一般往往在全篇的开端,它的位置,应在每句之末尾。”王先生还认为《古今乐录》论平调曲所谓“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其中的“送歌弦”当即送声(案:此处似当在“送”字后断句,以“歌弦”属下句,如此,王先生的观点就更为可信),故“清商新声的和送声其体制盖亦渊源于《相和》旧曲”(17)。这一点,从《古今乐录》所谓吴声歌曲之“半折、六变、八解,汉世已来有之”的记载也可得到印证。但由乐器合奏以及笛、笙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吴声、西曲中却被省略了。因此,吴声、西曲的乐调虽由相和旧曲而来,但其演奏方式却比相和旧曲要简单。这一方面与吴声、西曲使用乐器少完全一致。从上引《古今乐录》对吴声歌乐器的说明可知,吴声歌所使用的乐器也是有变化的,但直到陈代,仍没有相和旧曲使用的乐器多,这种情况一直要等到隋统一全国后,才能有根本的变化(18)。另一方面,东晋南渡后乐工凋零,乐器残缺,雅乐的建设直到太元八年(383)杨蜀等第二批邺下乐工到来之后,才初具规模,但郊祀所奏乐曲还是无法解决。(19)这也就决定了早期的清商新声,并不是在相和旧曲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而是在部分的继承中有变化,也有明显的倒退。严格地说,清商新声实际上是残缺不全的相和旧曲与南方民间音乐相融合,又配以南方情歌而产生的一种新歌曲。情歌先天的特点使得清商新声大大地偏离了汉代歌诗的叙事传统,而走上了以抒情为主的艺术表现之路;而音乐发展的倒退也使清商新声难以满足篇幅较长的叙事性和故事性歌诗的表演需求,而更适合于配合短小的情歌的演唱。受此影响,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少数有一定情节、演述故事的歌诗,也基本上采取了短篇联缀的结构方式。如梁武帝萧衍有《上云乐》七首,陈代谢燮有《上云乐》唱辞——《方诸曲》一首,任半塘即将萧衍《上云乐》七首重排次序,理解为一出有完整情节的戏剧,认为“全剧有发简、赴会、容耇、感洛、传丹、六博、遨游、降羽、惜别诸情节”,又说“此八曲演故事,有情节,多数带和声,乐别分明,并且来有因,去有果,显然继承于汉代之‘总会仙倡’,又发展出元代之‘神仙道化’”(20)。但这八首歌诗均为短篇,以萧衍《上云乐》第二首《桐柏曲》为例,其辞曰:“桐柏真,升帝宾。戏伊谷,游洛滨。参差列凤管,容与起梁尘。望不可至,徘徊谢时人。”乃是一首短篇杂言诗,且萧、谢八首《上云乐》,格式基本相同,可以初步肯定是依调填词。如果把这一组《上云乐》置于汉代的《陌上桑》、《焦仲卿妻》等长篇叙事歌曲,以及西晋时期的故事体和代言体歌诗与后代的词、曲之中,可以肯定地说,处于这两者之中间地带的《上云乐》,更近于宋词和元杂剧,而与汉代及西晋的故事体歌诗不类。这说明,在清商新声的影响下,经过东晋南朝数百年的发展,抒情性终于成了中国歌诗乃至诗歌艺术的主流。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南方民间情歌的产生背景、方式及其交际功能,决定了清商曲辞通俗短小、男女赠答等基本艺术特点,而清商新声以短歌或将若干短歌“连接起来歌唱”,并以合唱的和、送声为主要声调的演唱方式,则更加强化了这些艺术特点,并进而影响到文人的创作,甚至成为唐代绝句的滥觞。此外,清商曲辞的创作和演唱方式,又共同造成了南朝歌诗重抒情、轻叙事的审美品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诗歌和戏曲以后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文学整体的审美品格。
收稿日期 2007-10-29
注释
①②⑤⑨(12)(13)(17)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第1-29页,第38页,第11页,第36页,第37页,第94、104页。
③④洪顺隆:《从六朝民歌看原始阿注婚残迹》,《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⑥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84页。
⑦刘怀荣:《中国诗学论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⑧朱自清:《诗言志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9页。
⑩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
(11)刘怀荣:《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2期。
(14)(1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第144-145页。
(15)平调曲有“筑”而无“节歌”,清调中多出“篪”,除平调外,其他三调“节歌”皆作“节”。
(18)《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曰:“清乐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
(19)刘怀荣:《魏晋乐府官署演变与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
(20)任半塘:《唐戏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59、1263-1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