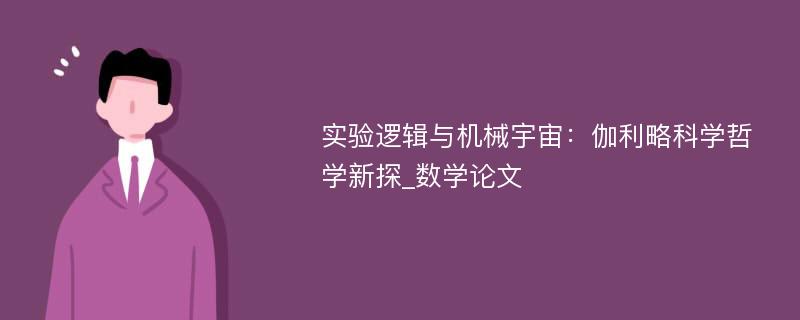
实验逻辑与力学宇宙——伽利略科学哲学思想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伽利略论文,哲学思想论文,力学论文,逻辑论文,宇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4 [文章编号]1000-0763(2008)06-0032-06
在传统的科学史语境中,伽利略的辉煌与伟大不仅在于他发现了摆的等时性、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抛物体运动规律,以及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四颗卫星和月球上的环形山等,他的传奇一生,他与教会的“关系”亦令史家所浓墨重彩,而且其作业重心和运思逻辑作为一种科学正道,开通了此后的牛顿路途。然而,他的科学贡献何以可能,其科学劳作背后的形上理念和方法论架构是什么,却很少为人们所探寻。笔者以为,就现代性科学历史建构的进程而言,这些才是真正具有奠基性功效和根本性意义的事件。此外,科学的当下进展并非存有某种特定的未来预设,英雄的美名往往总是事后他者的认同,而英雄本人未必都会始终清醒地在场。故此,本文基于相关的文本解读与史实考量,以再现出伽氏的当下思绪及其解惑过程,进而提炼出其形上理念、方法论架构及其历史意义。
一、数:科学语言的范式转换
一般认为,伽利略的出场缘自中世纪的“冲力”余荫和哥白尼的“运动困惑”,这一点并不错。但我以为,伽氏的真正意义还在于他在解决这两大难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整套形上理念和方法论准则。这就是说,在其科学劳作的背后所昭示给后人的科学之哲学基础与思想方法同古代和中世纪人们的运思有着质的差别,此后科学之所以能阔步前进,纵横驰骋,所沿袭的正是他创建的这套全新的理路构架。
先说科学语言。索绪尔说,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1] 既然是“社会性规约”,就要求语言本身的严密和准确。历史地看,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智者派时便已经注意到了语言的功能与规范对知识确定性的意义,[2] 为了解释各种物理现象,亚氏除传承前人有益的语词指称外,还自创了一套语言解释系统,如自然运动和受迫运动、本体与实体等。中世纪的人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沿袭亚氏的这套解释系统,当然也有创造(如冲力),而到伽氏这里则更是自觉地把语言与语义问题作为科学建构的首要前提了。他曾说过,“哲学被写在那本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伟大之书上——我指的是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会语言和把握符号,我们就无法理解它。这本书是以数学语言来写的,符号就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符号的帮助就不可能理解它的片言只语”([3],p.62)。所以,在伽氏的思绪中,数学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工具,而且是理论建构及其规范化的象征,以几何形式和代数法则表述的自然知识才真正具有现实价值。
当然,有关“数”之意义的认识伽氏并非第一人。历史上,毕达哥拉斯曾把数视为世界之本原;在柏拉图的“可知世界”中,数的必然性似成某种定则和机杼,从而构成了宇宙图谱的实在根据;开普勒因对几何学的执着与偏爱,便重新“安排”了天体结构及其运动的真实过程。所有这些对擅长实验与求精的伽利略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震撼力。据记载,他17岁时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又发明了一种把复杂图形化简为简单图形的几何仪,还写了一篇关于连续量的文章。25岁时因其将数学应用于流体静力平衡和固体重心的研究被任命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由于数学上的造诣以及将数学用于物体运动规律的研究所获得的初步成功,使他坚信数学语言的科学意义,由此更为自觉地把严格的数学方法广泛应用于机械力学的探索之中。他说,“自然界能通过少数东西起作用时,就不会通过许许多多的东西来起作用”([4],p.153)。这里的“少数东西”不是别的,指的就是数学的定则,因而如何把物体的运动还原为严密的数学,便成了他一生的工作焦点与思想重心,当然也是其形上理念的具体体现:“我们没有从逻辑手册中学会论证,而是从充满证明的书中学会论证,但这些书是数学的,不是逻辑的”([3],p.62)。将伽氏的运动定律与亚氏的运动观做一对比便不难看出,这里再也没有了自然运动与被迫运动、质料与形式、目的与内聚力等哲学语言与逻辑分析,而是完全以数学语言和数学方程将运动的因果关系予以精确表达。亚氏虽然也提出过动力与速度间的正比关系,但这仍然是模糊含混的,而任何关于运动规律的表达都必须精确与真实。诚如伽利略自己所说,“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讨论时就得小心不要使自己为错误辩护”([4],p.67)。不仅如此,自然科学的这种正确与必然恰恰表现为“数学的原理和单位”。因为“一个人想要解决物理学的问题,没有几何学是行不通的”([4],p.262),自然的奥秘如同一个个不可解惑的密码,这些陌生的语言不是别的,正是数学的术语。如任何物体总是可以用一定的几何图形表达,运动过程中的因果联系与变化过程也可以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来说明。尽管自然呈现给我们感觉的各种信息是零散无序的,但人类理性的功效恰恰就是要将这些无序的信息进行有序化处理(数学证明),以说明自然秩序的和谐与合理。克莱因对此曾有过恰当的评价:“科学已被Galileo指导去使用量的公理和数学的演绎,所以由科学直接激发的数学的活力就变得占支配地位了。……Galileo指令去寻求数学的描述而不是去探索因果关系的解释”。[5]
再譬如他对冲力问题的研究。“冲力”概念原本是为解释亚氏的运动问题而由中世纪的布里丹(J.Buridan)所提出。亚氏曾以媒介作用来解释抛物体的运动原因,因为他深信“受动者皆为他者所动”。布里丹则把冲力设想为“一种自然呈现的性质,它具有一种使受到它作用的物体产生运动的倾向”,[6] 同时又以该运动物体的速度与质量的乘积定量地加以描述其强度。此后的奥雷斯姆(N.Oresme)则更进一步,以几何方式严格证明出一个从静止开始作匀加速运动的物体所通过的距离等于在同一时间间隔中点的速度作匀速运动的物体所运行的距离。伽利略则试图把阿基米得静力学中的物体密度与冲力相联系,以便寻找一种利用流体静力学方式去描述冲力的方法。在他看来,研究物体运动(包括上升与下落)的速度“不仅需要考虑运动物体的轻重,而且要考虑该物体运动过程所通过的介质的轻重”。[7] 就是说,物体的运动速度既应统一归因于其重力,且又取决于它本身的密度与介质密度的差异。这样,通过实验测量不同介质条件下物体的实际运动状况,便可以大致知晓其运动路径和速度的变化了。与此同时,他还沿袭了布里丹的几何法对此加以严格辅证。虽然后来他放弃了冲力概念,而且其结论也都错了,但我以为,伽氏对冲力所做的详尽分析以及数学化描述本身已为他后来从事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研究准备了语言学基础,从而规整了此后现代性科学建构的大方向。顺便说一句,他对同时代的吉尔伯特的不满,也就在于吉氏所使用的语言不规范。
虽然由于数学本身的严谨性、严密性而作为描述自然过程的一种最有效方法在伽利略那里是自觉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他认为,数学还是一种“物理实在”。因为自然之联系与秩序不是偶然的。开普勒说自然秩序遵循简单性原则,伽利略则更进一步:上帝如同一位几何学家,他用数学创制了世界,因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辛勤的分析和论证来重新发现这种数学和必然性。自然虽然没像亚氏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目的性,但自然却是一个不变的数学系统,其中蕴含着简单、和谐和严密。他说,世界上存有两类性质的东西:一个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这是神和人的知识王国,亦即客观的自然界之本体,该王国的实在性是几何的,其唯一的根本特性可为数学知识的表达提供可能。因此,我们能用数量图形、位置和运动来描述它。另一个则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觉得到的,它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意见王国之所以虚假(如同人们看到太阳东升西落而确定地球不动那样),就源自感觉经验的狭隘性与片面性,该王国往往是理性的弱者、科学的大敌。也正因为此,数学方法和实验工具就成了我们探索自然奥秘的两大武器,舍此再无别的机巧了。诚如伯特评价的那样:“正是他奠定了近代最惊人的理智征服的基础,即关于物理自然的数学科学的基础;……他充分地领悟到他的公设和方法的重大含义,而且为力学知识和进展提供了决定性的辩护”([3],p.90)。格兰特也说,伽氏的“创造才智表现在从中世纪冗长繁复的性质张弛理论中提炼出与运动的数学和运动学描述直接相关的内容。”[8]
二、力:物理实在的机械本性
与数学语言紧密关联的是伽利略关于物理实在的力学解释系统。如前所述,伽氏的真正降临源自哥白尼的运动困惑。哥氏出于信奉自然遵循简单和谐原理而提出日心说,但他无法解释地球绕日运动的持久性,特别是重物落地时何以不会因地球运动而落向垂直点的偏西处。倘若沿袭亚氏有关“自然运动”与“受迫运动”的解释,势必存在三个悖论:一是人们无法精确求解这两种运动的具体变化过程,因为它们在保证了宇宙万物以某种高度确定的方式分布排列的同时,又会因被迫运动必然回到自然运动而造成这种安静秩序的混乱。二是地球位于世界中心既然完全是自然的过程,那么人们就无必要去对这种本就处在安静状态下的地球做出解释,因为性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这样也就等于否定了地球运动。至于我们所见的月下区物体的运动,这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是一种受力作用后的表征。三是运动物体脱离动因后之所以仍能维持运动,亚氏的解释是由于“介质的推动”,因而真空就不存在,可事实上在伽氏时代,人们已经用技术确认了真空的近似存在。正是上述悖论,促使伽氏另辟蹊径,通过抛物体运动、落体分析和斜面实验,引出重力和惯性力以对物理实在的机械本性予以说明。
就落体分析而言,伽氏在《对话》中借萨尔维阿蒂之口对哥白尼的困惑有过清晰而通俗的描绘([4],pp.242-244)。如他以苍蝇、蝴蝶的飞行及人的双脚起跳却不会因船的行驶或停止而发生质与量的变化这一事实来证实地球运动。有人认为伽氏这里实际地提出了相对性原理,[9] 但我以为,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不该被忘却,即从微观上看,他通过各种现象的归纳类比,统一地以物体自身固有的某种力源来条分缕析地破译运动的原因,进而定量地来描述力与其他物理现象之间的数学关系,以谋求一种一与多、质与量、形与体、时与空、内与外以及因与果的同一性关系。从宏观上看,他总是把一物一己之一运动置放到地球甚至整个宇宙运动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4],pp.149-150),这样的眼界与襟怀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的牛顿。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抛物体运动和斜面实验。伽氏在《对话》中曾不厌其烦地反复分析抛物体的运动,特别是其过程中的各种可能的受力状况。如在讨论从航船的桅杆上抛射的石子运动轨迹时,除最初的抛射动力和石子自身的重力这两种基本的作用力外,还有空气阻力、船桨冲力等;为了否定亚氏的介质推动说,他又通过不同方向射出的箭、在塔上水平方向射出的炮弹、在奔驰的马背上扔下的小球等现象仔细分析其运动路径中的受力过程和可能结果;在讨论摆的运动和落体过程时,又分析了空气阻力、绳索拉力、地球引力、物体冲力的影响过程,并以严格的数学形式证明出其运动轨迹。有关落体定律,柯瓦雷认为,伽氏虽然得出了结论,但“他只是把此定律看作为客观事实,而并不知其所以然”。同时他还提醒人们对此“有必要解释和去理解的不是下落本身这个事实;也不是去发现物体下落的原因。他所寻找的是落体运动的本质”。[10] 申先甲说,伽氏为了实验上的便捷(减缓下落运动),通过斜面实验验证了落体定律。[11] 我们的分析是:从现象上看,斜面实验的确是为了论证落体定律,进而求解落体运动的本质。但倘若再进一步追问,在伽利略的思绪中,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我判断,从方法论的视域看,伽氏实际是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阿基米得的力学概念、柏拉图主义的几何证明和自己的实验设计高度糅合的产物。其中,又以逻辑和力学最为关键。
众所周知,虽然《对话》和《两门新科学》都是以亚氏为批评对象的,但诚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对的多数是亚氏的结论,尤其“只是责备那些使自己完全沦为亚氏奴隶的人,变得不管他讲的什么都盲目地赞成,并把他的话一律当作丝毫不能违抗的神旨一样,而不深究其他任何依据”([4],p.149)。而对于亚氏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对其追究事物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谋求知识的确定可靠性这一毕生的理论主旨,他不但没有批评非难,而且倍加传承光大。至于有关原因问题的求解,则秉承了阿基米得的力学理路,详尽穷究其各种单个或合成的力的影响。何谓运动的本质?要回答它,解释原因就不可或缺。而力则是这种原因的最恰当的表达。因为力既形象生动,又精致准确,较好地反映了机械运动物体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与关系。同时,力作为一种物理实在的解释系统,既直观又通俗地反映了作用的方向性和数量级,以便人们从实验上测量和分析力在施行过程中的种种外在效应,进而从数学上加以精确求解和严密论证。此外,力的线型性特征和直接性功效,以自然本身的固有禀赋还把哲学的、宗教的、心理的、文学的等一切附于自然的种种神秘符咒统统打倒了。力犹如一把利剑把自然的一切都劈开了,曝光了,剩下的只是力的作用、力的受动和力的世界。由力还可以生发出各种链锁的组合词,如机械力、摩擦力、阻力、重力、应力、剪力、力矩等,这些概念与亚氏的本体、形式、质料、质、量、实体等描述运动物体及其变化的机理概念相比,显然要规范与精确多了。由此,他实际上已经与开普勒、哈维以及后来的笛卡儿一道,联手开创了整个现代科学的一大研究系统:以力的作用来求索与领略物理实在的机械本性。
三、实验:工具理性的隐性逻辑
作为科学实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伽利略也不能算是第一人。因为毕达哥拉斯就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希腊的医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等都曾从事过科学实验,[12] 培根对实验的倡导力度并不亚于伽氏及其后来者。但是把所有科学结论都奠基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并对这一工具理性本身进行哲学反思,以此创造出一种理想化方法而成为日后科学研究中的一条基本定则的则应归功于伽利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伽氏才应当是“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3] 伽利略一生中做过很多著名实验。如斜面实验、摆的振动实验、抛物体实验、落体运动实验等。[14] 这里,我们同样不准备就上述实验的过程做出描画,而是想彰明隐渗在这种工具理性背后的亚意图式的方法论架构。
科学实验这一工具理性背后之隐性逻辑的首要构件是寻求感性事实。与后来的几乎所有现代科学家一样,伽氏把科学理论都奠基于感觉经验上,强调自然本身对于科学的绝对优先权。无经验就无理论,无实据就无科学。他说,“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确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依据”([4],p.161)。“自然并不是先制造出头脑,然后才按照它们的知性能力来构造事物的,而是它首先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出事物,然后再构造人的知性”([3],p.65)。坦率地说,科学研究当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这一点本无什么可圈点的,因为这几乎是所有科学家的本能反应。但他们在实际的科研活动中,特别是建构理论解释系统、寻求为自己辩护依据时就未必始终清醒了。因而伽氏一再申言,“我们的争论是关于感觉世界的争论,不是纸上之争。”科学理论正确与否,不是单凭逻辑推论,而必须“回到特定的论证、观察和实验之中”,只有通过真实可靠的实验事实与过程的检验,才能最终为新兴的科学理论寻求辩护。所以,伽氏在批驳辛普利邱不是崇奉试验而是崇奉古人时再次强调:“可能这些权威们没有做过试验就得出了结论;你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你没有做过试验就肯定了它,并且对权威的教条深信不疑。……他们总是相信前人,并且一直相信下去而永远找不到一个做过试验的人。因为任何人只要做一次,就会发现试验的结果同书上的恰恰相反”([4],p.190)。呜呼!望着伽氏的上述这段文字,笔者忍不住在此要放言一句:最简单的真理在奴性者的眼里往往总是深不可测的!
科学实验工具理性背后之隐性逻辑的第二个构件是通过周密的实验设计以纯化对象,剔除假象。如前所述,在伽氏看来,科学理论的建构不是依凭逻辑或权威,而是诉诸经验事实。然而经验从何而来呢?诉诸人的感官之感觉?这一点对向来就重视经验的他来说当然不会受到怀疑。然而感觉的局限性往往会使人很难准确与精确地把握自然的真实联系。因此要获取可靠而真实的经验事实就必须通过周密的实验设计以纯化对象,剔除假象。他曾举例说,历史上好多人对于运动都有论述,但运动的性质与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仅仅靠感官观察是不够的,就像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错了,并非在于其逻辑论证不严谨,而恰恰在于他囿于经验所造成的假象。后来,伽氏不无骄傲地说,一些人已经观察到一个下落物体的运动是加速运动,但就没有宣告这种加速运动是在什么程度上产生的;一些人注意到一个抛物体的运动轨迹是一曲线,但就是没能证明这条曲线必定是一条抛物线,而这一切他却做到了。亚氏“首先是通过感觉、实验和观察所得的结果,尽可能地弄清自己的那些结论无误;以后他才设法加以证明。在实验科学里,……当结论是真实时,人们就可以使用分析方法探索出一些已经证实的命题,或者找到某种自明的公理;但如果结论是错误时,人们就可以永远探索下去而找不到任何已知的真理”([4],p.63)。显然,这段话并不是要否定亚氏的观察与实验,而恰恰表明的是由于观察(包括粗陋的实验)本身的局限有可能使结论引向谬误(尽管在推论上正确)。正因为此,伽氏特别注重精确实验的设计与实践,以谋求实验结果的尽可能准确。
科学实验工具理性背后之隐性逻辑的第三个构件(亦为实验的最高级别)是理性重建下的“思想实验”。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常听人说,伽利略之所以为近代科学之父,是由于他以经验的、实验的方法来代替思辨的、演绎的方法。但我认为,这种理解是经不住严格审查的。……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的思想”。[15] 伽氏自己也说,“表象如果没有理智插进来,很显然是会使感觉受到蒙蔽的”([4],p.332)。的确,人们在实验中将自然现象数量化描述或将自然过程延缓与加速,还只是实验的功效之一种,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过程,可以把一些在天然状态下的自然问题以较为理想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例如,他在“惯性问题”研究时就曾把斜面设计成像镜子般光滑,把滑动的小球制成既硬又重的青铜圆球,这显然是一个理想化实验装置,虽与理论要求还有距离,但较之完全的自然景况来说,毕竟有了质性变化。再如,他通过对“落体佯谬”的思想实验以否定了亚氏“落体运动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定论;通过炮弹发射过程之受力分析的思想实验,论证了其路径实为一条抛物线;通过在航船的桅杆上抛射石子之受力分析的思想实验,确证了其路径是一条螺线,等等。正如韦斯特福尔所评论的那样,“伽利略抓住了操纵杆的另一端。就在亚里士多德从经验出发的始端,伽利略从理想化的情况出发,而实际情况只是理想化的情况的一个不完美的体现。在定义理想条件之后,他便能理解无疑包括摩擦在内的所需物质条件所带来的限制。”[16] 我以为,思想实验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克服在自然状态下无法消除的各种限制因素,便于观察和记录准确的信息;二是可以在理想条件下排除其他的干扰信息,甚至创造出自然状况下不具有的物理情景,以便人们较为清晰地抓住自然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方面;三是通过这种思想性的条件设计,便于人们直接借助几何逻辑进行跨时空的抽象思维,在纯粹的几何王国中去领略对象的核心关联与可能规律。也正因为此,此后的科学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更为精密巧制的实验装置的设计和采用,归功于此种思想实验的推延与扩张(如爱因斯坦建构相对论),而伽氏无疑是这方面的先师与引航者。
四、原子:宇宙自然的终极构件
伽利略还有一项重要贡献一直未能引起史学界的关注,那就是他在“主客二分”基础上所提出的“原子化宇宙自然终极构件”的思想。如前所述,在伽氏的视域中,宇宙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因而宇宙的实在性就在于其几何性,现象世界的背后遵循着力学原理,所有可感知的世界只不过是带有依附性的“意见王国”。我判断,伽氏在这里实际上是把世界的特性一分为二了:一是自然本身的特性(绝对的、客观的和数学的),一是人类的认识特性(相对的、主观的、感觉的),这也就预示了科学现代性视域中的一种新的本体论,即自然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外在性。伯特对此也曾有过类似的指认:该思想“在近代思想中的影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正是把人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流放出来,把他处理为自然演化之产物的这一根本进步,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一个相当坚定的特点,成为一种大大简化了的科学领域”([3],pp.75-76)。这也是后来笛卡儿提出二元论的思想嚆矢。伽氏虽然还不像笛卡儿那样自觉,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却蕴含了一种自然图景在人类认识域中的格式塔转换:自然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因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就在于与这种实在的无限接近,科学知识也就成了无关乎人的价值的中立实体了。
那么,自然本身特性的构成状况究竟如何?伽利略对此又是如何设想的呢?首先他联想到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原子论在德谟克利特那里是关于世界本原的一种哲学臆造,但伽氏却在这里赋予了其科学内涵。在《两门新科学》中他认为,假设物质可分解成为无限小的不可分的原子,那就很方便理解世界的基本构成,而有了原子论解释,则勿须求助于“固体中存在空旷空间”或“物质具有可渗透性”假设就能较好地说明固体如何转变为液体和气体的原因,以及合理地理解凝聚、膨胀和收缩问题。因为正是这些具有数学特性的原子本身的运动变化,引起了主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同时也制造了种种假象[17]。为了进一步对这种原子构成理论寻求辩护,他以白或红、苦或甜、有声或无声、香或臭等性质与人的感觉之关系加以说明,以确证客体本身的性质如何外在于人的感觉。在他看来,上述性质“仅仅存在于有感觉的物体中”,如果不考虑感官的作用,它们也就消除了。但是像尺寸、形状、数目、缓慢或快速运动等特性,即使没有感官的感觉,它们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物质可分解成原子,而原子的碰撞、结合、渗透和重组自身就能直接表现为形状、数量、运动、速度乃至收缩与膨胀等特性,因此,人的感觉只是对原子的这些特性在经验中的重组与再现。至于主体及其行为则无法用定量方法来处理,人的快乐与悲伤、情感与欲望、奋斗与野心,以及感官引起的色、声、味等不遵循数学法则,因而这种主观世界只是通过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相对性去猜度和表达对象自然的绝对性和客观性,由此势必会导致各种假象。科学的任务不应被这类假象所干扰,必须以数学的精确性去表达那个世界。
当然,仅仅确认世界由原子构成还不够,还需回答这个世界之运动变化的机理。由于伽利略把自然只看成是外在于人的任何活动印迹的纯粹的原子世界,因而对终极因问题的追问便幻化成对事物过程的具体分析,真实的世界不过是处于数学连续性中的一系列的原子运动。谈到运动,伽氏当然会本能地想到力。开普勒由于坚信匀速运动,因而有关力的作用的思考不会成为其思考重心。伽氏则相反,他更关心加速运动,而加速运动就必然有力的作用。所以,解释这个由原子构成的世界之变化机制就必然促使他将焦点聚集到力的思考上。在他看来,同一事件有且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基本的原因,在这种基本原因和它的各种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恒常的联系,该联系的纽带就是力,结果也就是力的作用。虽然这种力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如重力、冲力、推力、阻力等,但人们在用数学方法定量地处理这些力的作用时,并不会因其对象的差异而不同。也就是说,只要是力的作用及其机制,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均匀的、不变的。
于是,世界如同一架巨大的机器,其部件为原子,原子间的运动依据力的作用原理维系着,世界运动变化的机制就是力学原理。后来惠更斯抓住了这一点,并以功代替了力,依据功,原因在数学上便等价于结果。再后来又有了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失,只能以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由此,作为完美机器的世界就这样呈现在人的面前了,而具有目的和情感的人本身,要么是一位并不重要的旁观者,要么就凌驾于这部机器之上,操纵它、主宰它,为人所用。这是一幅迷人的图画,因为人可以依据其目的,以工具理性去征服与享用自然。但这又是一幅恐怖的图画,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将不复存在,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必将在新的时代以另一种方式报复人类。当然这只是后话了,毕竟在伽利略时代,人们还未真正品尝到征服他者的甜头!
[收稿日期]2006年12月31日
标签:数学论文; 伽利略·伽利雷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力学论文; 科学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对话论文; 原子论文; 逻辑与论文; 物理论文; 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