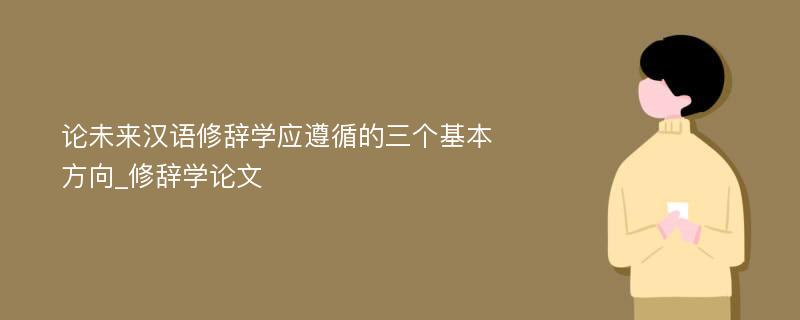
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三个基本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中国论文,所应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由于《修辞学发凡》的影响,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前进。其间,虽有“文革”十年的沉寂停顿,但却孕育了七十年代末以后更大规模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八十年代中期那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谓令人鼓舞。然而,无庸讳言,尽管七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在修辞学新体系新理论的建构方面,在辞格研究的深化方面,在词句段落篇章修辞方面,在语体风格研究方面,在修辞学史研究方面,在修辞学新领域的拓殖方面以及作家作品修辞研究、口语修辞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多方面填补了《修辞学发凡》所未涉的空白,或将《修辞学发凡》所论述的内容进一步深化了,但至今仍未出现一部像《修辞学发凡》那样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为什么呢?这里就可看出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修辞学发展所存在的严重缺陷。通过对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反省与对相邻其他学科发展的经验以及未来世界学术发展的普遍趋势的省察、思考,我们认为在中国修辞学未来的发展历程中,要想出现诸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这样的里程碑性质的巨著,使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有一个大的飞跃,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依循如下三个基本方向。
首先,必须强化修辞学的多边性学科性质的认识,充分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及其菁华精髓成果。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出版的修辞学著作亦数以百计,特别是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可谓是修辞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到目前为止,许多修辞学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卓有成就,但在学科体系与思想理论建设上严重不足,很多人的研究还仅满足于在《修辞学发凡》的框架中修修补补。虽然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旨在建构或公开声言要建构一个与《修辞学发凡》不同的新的修辞学体系的“力作”,但结果是,有的如孙悟空一般翻了七十二个筋斗而终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似地没能脱出《修辞学发凡》两大分野的体系;有的虽一个筋斗就跳脱了,但却一头栽进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的泥潭,再也动弹不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旨在建构修辞学新体系的学者们终究没有人能够做到象陈望道先生所说的那样:“坐在中国的今天,一手向古人要东西,一手向洋人要东西,”[1]也就是学贯中西,建立一个镕铸古今中外学术精华于一炉的独立的科学的修辞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立一个独立而行之有效的修辞学研究方法。事实上,陈望道先生所著的《修辞学发凡》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它有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和修辞学研究方法。而这一切又是依托于作者的学贯中西,对古今中外的有关文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学科知识的渊博占有,所以才有博大精深的《修辞学发凡》问世。
众所周知,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运用艺术与规律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边缘性很强的学科。研究它,必须要有坚实的语言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等一系列学科知识修养。这样,才能识见广,思虑精,最终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博大精深的修辞学体系。而在陈望道先生之后的许多修辞学家与研究者,虽然绝大多数出身于语言学专业,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坚实或深厚的学养,但不少学者或谙熟于现代汉语而对古汉语缺乏研究,或是对语言学理论有很深的修养而疏于文学、哲学或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汲取与研究,因此从整体上看,总有知识不合理与欠缺之憾。这样,就必然产生不出诸如《修辞学发凡》这样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巨著。因为没有学贯中西、高瞻远瞩的学识与识见,是建构不出博大精深的修辞学体系的。由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与《修辞学发凡》的成就影响,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中国修辞学在今后要想求得一个新的发展、飞跃,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更新学术研究的知识结构,更换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这样,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出现诸如陈望道这样的学术大师与《修辞学发凡》这样的修辞学巨著,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现在世界学术呈现出强烈的学科互相渗透、交叉的特点,任何一门科学要想获得新的发展,都必须吸纳新的邻近学科的新思想、新成果,更新本学科的知识结构,拓展本学科的研究思路,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使本学科有新的飞跃与大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修辞学发展,无疑是应遵循这个方向前进的。
其次,必须切切实实地将演绎法与实验法贯彻到今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之中。尽人皆知,与其他学科一样,研究方法的问题,对于修辞学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修辞学家们曾运用了观察和记述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抽象和具体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的方法、比较法、统计法、实验法等多种方法。[2]其中,多数学者对归纳法、分析法、比较法等几种方法运用得最多,也最习惯而娴熟,而且结出了不少丰硕的成果。但是,对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尤其是演绎法、实验法这两种现代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却鲜少运用,真是令人扼腕痛惜。虽然八十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演绎法与实验法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撰文专门从理论上阐述这一问题,强调要重视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以期促进中国修辞学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但是,放眼看去,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界却始终没有出现以演绎法与实验法来实践的学者与论著,真可谓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
诚然,归纳法、分析法、比较法等方法都是对科学研究十分有用的方法,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些方法对科学研究是行之有效而有贡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研究要深入,要探求未知的科学奥秘与规律,是离不开演绎法与实验法的。因为演绎法和实验法可以在归纳法、分析法、比较法等方法所得出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出我们所未知的科学奥秘与规律,可以促进科学发展有更大的跃进。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运用归纳法、分析法、比较法等,目的就在于从现有的事实概括出一些公理、公式、定律或规律,然后再以此为基点推演下去,找到客观事物发展更深层的内在规律。其实,中国现代的许多修辞学者是深知演绎法、实验法的重要性的,只是目前很多学者还不够思想解放,不敢大胆运用这两种方法而已。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学者还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习惯于归纳法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并不了解国外学术研究的趋势与方法。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当美国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与转换生成语法学说风靡全球时,就有很多西方与日本的语言学家或在国外的中国学者运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说用演绎法推演出一些新的语法规则,并根据他们自己推演出来的规则造出一些汉语句子,寄给中国的一些学者并请他们在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的实验,请中国学者与学生们判定他们所造句子的正确与否。当时,我并不十分理解这种作法。现在想来却幡然有悟,认为这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果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我们也采用这种方法,即通过现有的规律而推演出新的修辞规律,然后再以实验法去印证,很快就会确知自己所推演出的修辞规律是否“合法”或“有效”。若此,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不就更具科学性了吗?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不就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了吗?比方说,陈望道先生运用演绎法曾推演出藏词格除藏头、藏尾以外,还应有藏腰一类存在。最后,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例,印证了他的推演,从而将这一演绎法推演的成果写入了1976年修订版的《修辞学发凡》之中,由此在修辞学界成就了一段佳话。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假设,要是陈望道先生当时“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寻寻觅觅而没找出那所要找的例证,那么我们今日也就听不到陈望道先生的这段佳话了,则汉语修辞的“藏词”格中势必要少掉“藏腰”一类。其实,假设陈望道先生当初真的找不到那个例证来印证他的推演而在理论上存在的“藏腰”手法,还是有办法来弥补的,这就是用实验法。即根据理论上推演出来的“藏腰”模型,自己造一些带有“藏腰”修辞手法的句子,将这些句子写入文章中,看读者反应如何。若能接受,且有很好的表达效果,则“藏腰”法可定矣;或者更直接些,创造一些“藏腰”的修辞“文本”(text),直接以问卷调查的方法来实验。若是在被实验的各知识层级的人中皆获通过,则也可据此而立“藏腰”一类。因为这在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合法”的,西方学术界早已运用了这一方法。即以修辞学研究来说,这种方法在现今的西方修辞学界就很流行,且非常有效果。如关于隐喻的研究,卡麦克和鲁克思博格很想知道构成隐喻的两个词语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他们就设计了两组“词对”,其中一组中的“词对”可以构成隐喻(如外科医生——屠夫、办公室——牢房),而另一组中虽为同样的词,但顺序被打乱,因而每个“词对”均不构成隐喻(如外科医生—牢房、屠夫——办公室)。实验要求受试者对两组中每一“词对”中的两个词之间的相关性作出判断。一般来讲,人们总是认为构成隐喻的两个词语由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相似性而包含有内在的联系,因而认为受试者会对构成隐喻的“词对”的相关性做出较快的判断,但实验结果却都表明受试者对两组“词对”的反应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由此,实验者得出了结论:两个词并置,不论它们先前是否关联,都会产生新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构成隐喻的两个词语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3]如果不采用实验法,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不清楚。光凭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那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可见,实验法确是科学研究包括修辞学研究中的一种直捷而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在往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中重视采用此一方法,配合演绎法而进行汉语修辞学的一系列规律的探讨,一定会事半功倍,卓有成就的。
再次,必须重视对修辞原则的研究与总结。说到《修辞学发凡》,可能人人都会知晓其中的一句名言:“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其实,这句名言之所以成为名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修辞的总原则,概括性极强,周遍性极大,因而其所适用的范围也极广,无论是书面修辞还是口语修辞,无论是字句修辞还是篇章修辞,无论是汉语修辞还是其他语修辞,统统适用。这里,我们便可见出《修辞学发凡》的博大精深来,便可知其所以成为不朽的巨著之缘由。然而,到目前为止,数以百计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却罕见有提出诸如《修辞学发凡》这种具有科学性、周遍性大的修辞原则来的,令人遗憾!其实,修辞原则的研究与总结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一条修辞原则的提出,实际上也就是一条修辞规律的总结,它能很有效地指导人们如何修辞,使学习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执简驭繁,功效大矣。即以传统的辞格研究来说,很多著作都习惯于找一些新、老辞格的例证,分析一下,评点一下其修辞效果如何如何。就是很少有人想到从中总结出几条创造某一修辞手法或使用某一辞格的原则,使学习者可以依循修辞学家所归纳的原则或者说是规律来游刃有余地进行富有创造性的修辞“文本”的创作,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立竿见影的效果。众所周知,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运用艺术与规律的科学。毫无疑问,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如果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不能对人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表达效果的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不能提供给学习者以周遍性较强的原则或规律作语言实践的指南,则我们的修辞学就不成为修辞学。因为科学是不能没有指导人们实践的使用价值的。如果我们在今后的修辞学研究中加强对修辞原则与规律的研究、总结,使学习者有原则可依,学习效果立竿见影,那么21世纪修辞学在中国一定广受社会欢迎,成为带动其他学科的领先学科、热门学科,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注释:
[1] 参见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2] 参见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3] 参见安都尔卡亚·毕斑《隐喻与认知》,转引自杨君《论隐喻的认知作用》,《修辞学习》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