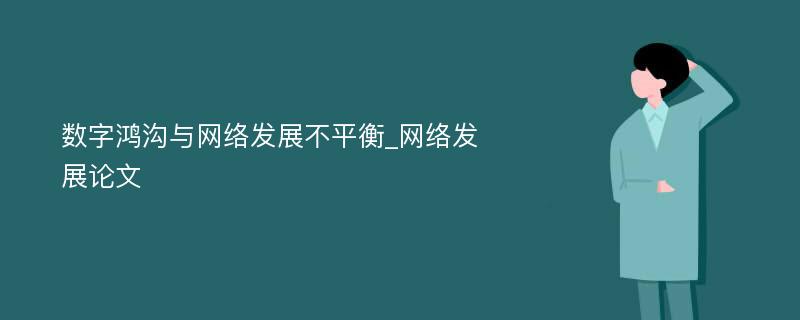
数字鸿沟与网络不平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不平衡论文,数字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早就置身于“媒体社会”中了,无论是认识还是感知这个世界都必须以“媒体”为中介,甚至可以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已经充分“媒体化”了。当然,这里所谓的“媒体”不仅仅指的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渠道和方式,而是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 “媒体”一词结合了意义相关但又有区别的三种含义:一是艺术模式或美学生产的特殊形式;二是以重要的装置或机器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特殊技术手段,三是一种社会建制。詹明信特别强调,这三方面的含义虽然没有给“媒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提醒人们如果要完成或建构一个关于“媒体”的定义,那么就必须关注它的物质、社会和美学的不同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文化成了一件关乎媒体的事情”[1](PP67—68)。
很显然,詹明信之所以突出“今天”文化和媒体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因为他发现了“电子媒介”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形式”和“感觉结构”的巨大影响力。就像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的那样:“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电子媒介与历史中出现的其他媒介相比,它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量建立在对传播形式和结构也即沟通“语法”的极大改变上。“语法”一词也来源于麦克卢汉,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传播方式都拥有自己的“语法”规则,这些规则既来源于人类各种感觉的混合交织,同时又和人们平时对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虽然人们会有意识地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媒体传递信息的内容上,但是就个人对信息的理解而言,媒体所使用的“语法”是一个更关键的因素。离开了对“语法”的把握,信息的“内容”常常变得无法索解。所以,“媒介即信息”:“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释放出来一样”。[2] 而电子媒介在这方面的潜力特别巨大,它在技术上的不断更新、它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紧密互动,它对社会形态的深刻影响……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自我、历史和世界的方式。事实上,媒介创造或制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化”。
网络作为电子媒介的最新形式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同样甚至是更疯狂地发挥着“塑造”社会的作用。“全球化”现象尽管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真正使之具有实体感和可操作性,却是20世纪晚期网络社会的兴起:“只有到了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讯科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国际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协助下,世界经济才真正变成全球性的”[3](P119)。一般认为,网络空间的发展正在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封闭性控制力量。信息和知识的加速商品化,使网络空间演化成一种整体市场。这正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未来之路》中憧憬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free capitalism)”:“信息高速公路将扩大电子市场,并且使之成为最终媒介,一个无所不包的中介场所。……任何一个连入信息高速公路的计算机都能获得有关卖者和他们的产品以及服务的信息。……这将把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花少量交易费用就能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这是购物者的天堂。……它将使那些产品生产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效地看到消费者究竟需要什么,也使得那些未来的消费者更有效地购买产品,亚当·斯密将会对此感到高兴。”[4] 这种憧憬实质上是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向往,即通过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的整体营销工具获得较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这会更进一步促使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和销售过剩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对知识和信息的新需求。譬如微软公司曾以“你今天想要到哪里去”(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oday?)作为广告语,在这句广告语中,微软似乎是在强调无限制的自由,个人意志和不受拘束的选择自由好像真的因为科技力量而“美梦成真”了,但是在商家的承诺中,个人究竟是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还是仅仅拥有了消费的自由,对此微软首席科技主管纳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 )作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表示:微软想要在任何一笔钱的交易中分一杯羹。他的意思是说微软的终极目标不是在于成为一家软件公司、一个内容服务提供者,“或者”电子商务的来源者,而是成为一个超级商务中间人。在网际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微软不再局限在电子商务中,它希望每个人都阅读它所提供的内容,观看它的程序设计成果,并且在微软的线上商店购买商品。[5](P153) 微软不只掌握网络使用者的中间代理,它也期待成为网络使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那句广告语的潜台词其实是:在微软所建立的世界里,今天你想要到哪里去?
但问题在于,当网络空间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整合力量时,是否还有产生新的政治和文化效果的可能?比尔·盖茨从“理想市场”的立场出发,明确表示“信息高速公路带给人们的美妙事物之一是在于,与物理世界相比,在数字化的世界里人们更容易获得真正的公平”。基于这种看来有点令人困惑的论断,他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都在为平等而努力,我们也可用这种平等来帮助我们认清一些社会学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物理世界中并未得到解决。网络并不能推倒歧视和不平等这些障碍,但却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6](P49) 正因为相信高科技可以带来“人间天堂”,所以“乐观论者”提出了“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的乌托邦构想:“新兴科技在此不是敌人,它们带来的希望远多于危险。事实上,从共和国的观点看,它们带来伟大的希望,特别是它们能让一般人轻易知道无数的主题,并且可以去寻找无止境的不同看法。”[7]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悲观论者则指出不能无视“数字不平等”背后的“现实不平等”,即使比尔·盖茨的设想真的可以带来建立在网络世界上的虚拟平等和数字自由,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拥有高级终端工作站、宽带网和种类复杂的软件资源。而且在市场化的网络空间中,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将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和思想等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逐渐被商品化所侵蚀甚至封杀。就如詹明信所描绘的:“当前的文化到用巨大无比的传通网络和电脑所达到的不尽忠实的再现,我以为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一个更深刻、更富寓意的误读和夸张。此中被歪曲、被借喻的,正是雄霸今日跨国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系统。因此,尽管当前社会的科学技术有惊人的发展,尽管尖端技术是充满魔力的,但事实上技术本身并无稀奇之处,其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为人所接受的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一个我们的脑系统、想像系统皆无法捕捉的网络,使我们更能掌握‘资本’发展到第三个历史阶段所带来的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整个现象几乎可以称为一种‘高科技能’,大都瞩意于一种公认为跨越全球、网罗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这个整体性网络的线路和系统更透过叙述作巧妙和繁复的安排而进一步跟一些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勾连、互相斗争的讯息媒介机构挂上关系。”[8](P488) 如此巧妙和繁复的网络系统究竟会发挥怎样的作用,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借用福柯“作为话语的全景监狱”的说法,把网络社会视之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全景监狱并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徒、把他或她构成为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全景监狱时代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即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或她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之中……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上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9](PP119—120)。
网络“乌托邦”和“恶托邦”之争可以说是就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展开的一场极有价值的辩论。尽管本文的论题是以此为背景的,但并不直接介入到这一辩论中,而是期望通过对中国大陆经验的检讨,在一个“非西方”的不同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中考察网络成为“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二
2004年7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 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比2003年同期增长27.9%。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依然保持了很高的速度,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一些指标明显增长。中国网络国际出口带宽增长飞速,总数达到53.9G,比去年同期增长190.3%。中国CN域名下注册的WWW网站数量达到62.7万,比去年同期增长32.2%。同时, 中国宽带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到3110万,比去年年底增加1370万,半年增长率高达78.7%。[10] 从这一连串数字可以看出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网络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样,这又是一种极不平衡的发展。尽管中国网民人数为8700万,绝对数字居世界第二位,但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约7.86亿人,平均普及率为12.2%,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更是超过70%,而中国只有6.7%,与世界水平差距仍然巨大。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数字时代”还只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想。
一般认为,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应该有以下几个部分构成:首先是网络的线路组成,包括电线、电话线、光导纤维电缆以及地对地或借助于卫星的电磁传输装置;其次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系统;第三是信息处理器,一方面保持网络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提供各种特殊需要的服务;第四是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个人信息终端,譬如电话机、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等;最后是有能力购买必要的设备并懂得使用这些设备的个人。很显然,这个网络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超社会语境的信息工具,而是非常深刻地“镶嵌”在国家、市场和个人的历史性关系中。根据哈拉瓦依斯的研究,他调查了四千个网站的链接情况,发现国家边界仍然嵌入到链接网络中。网站最可能与同一国家的主机相链接,而不是与越过国家边界的站点链接。因此他认为,国家地理边界对于辨认网络世界的地形依然重要,因为这些分界实际上是文化、政治、经济和习俗的分野。[11](PP7—28) 具体到国家内部,譬如在中国,电信业是由国家垄断的,它的发展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建基在电信业之上的网络自然也受到了以发展为主导方向的政策面强有力的制约;同时网络服务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必须计算成本、风险和回报,很自然会把投资和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发达地区,因为只有这些地区既提供了现代化的电信设施,也具备了消费网络服务的广大市场;由此引出了“网络消费者”的概念,一个人必须具有“硬件”和“软件”——姑且借用电脑术语——两方面的条件,才可能成为合格“网民”:“硬件”指的是他要有购买个人电脑和相关上网设备以及支付上网费用的经济实力;“软件”则要求他懂得使用这些设备并且会充分利用各种网络资源。无论从经济水平还是从知识水平来看,“网络消费者”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低的门槛。三方面的合力使得中国的网络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报告也承认,截至2004年6月30日,中国WWW网站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占到84%,东北、西南和西北网站比例只是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互联网整体上虽然呈较快增长态势,但地区之间互联网发展水平、普及水平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并呈现东部快、西部慢,城市快、乡村慢的特点,这和各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相一致。
就地域分布而言,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较充分地显示出来,同时“调查报告”也开始注意到网民的性别差异、代际差异和收入差异等。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互联网的网民在结构上呈现低龄化的态势。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 中国上网用户中以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6.8%,35岁及以下的网民占82.0%。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最多,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单身网民占60.1%,未婚网民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已婚网民。在性别比例上,男性是主要的网络使用者,占59.3%。[12]
调查报告一个最令人迷惑的地方是,它宣称“低收入”网民是中国上网人群的主体。只有21.9%的上网者月收入超过2000元;个人月收入在500 元以下(包括无收入)的网民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9.0%。而网民每月实际花费的上网费用(仅限于上网费及上网电话费,不包括使用网络服务的费用)多控制在百元以内,以月花费51—100元的网民最多,达到38.9%。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4.2天、12.3个小时。[12] 很显然, 这种“低收入”者成为上网主体的现象与国际互联网研究中所谓“数字鸿沟”的状况严重不符,因为按照“数字鸿沟”的说法,它把“有者”和“无者”,即拥有电脑和互联网的人与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区隔开来,而低收入者是当然的“无者”,被排斥在网络之外。一些最明显的数据是:1999年全世界2.4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只有500万即2%的人来自低收入国家;[13](P107) 而2000年在非洲,100万拨号上网者中,有65万来自富裕的南非。[14](P184)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网络发展创造了什么人间奇迹,使得“低收入”者成为了网民的主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符。仔细研究一下调查报告,可以发现问题原来出在调查方式上。既然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最多,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人数,占据绝对优势。那么在这些18—24岁的年轻人中,中学生和大学生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学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固定收入的,所以把这些没有固定收入的学生纳入统计数据中来计算网民的收入情况,很容易得出“低收入”网民是中国上网人群的主体的结论。而按照国际惯例,应该调查的是网民的家庭收入,因为许多家庭中电脑以及相关上网设备的购买和上网费用的支付,常常是由不上网的父母替孩子支出的。所以统计家庭收入,就可以避免没有收入的学生带来的统计误差;也不会在调查报告中出现如此不合常理的现象:一方面称个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无收入)的网民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9.0%;另一方面又说如此低收入的网民每月实际花费的上网费用百元以内,至少要占总收入的1/5;更不会得出“低收入”者成为网民的主体这样错误的结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于种族、家庭和收入的差异导致“数字鸿沟”现象的调查显示,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的可能性(40.8%)比黑人家庭(19.3%)或西班牙裔家庭(19.4%)高出两倍多。而且这种各种族间的数字差异普遍出现在所有收入层次的人群之中。在高于7.5万美元的收入水平上,白人拥有个人电脑的可能性(76.3%)还是高于黑人(64.1%)。[14](PP187—188) 可以在中美之间形成对比的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但近两年的电脑销量一直在1000多万台徘徊,而总人口数仅为中国1/6的美国,每年的电脑销量却有4000多万台。[15]
问题在于,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完全忽略了“网络不平衡发展”背后更严重的隐患,那就是网络发展有可能“加深”而不是“弥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也许永远都被隔绝在网络之外。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他的巨著《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讨论了网络技术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新形态:这个世界有许多地区和相当部分的人群被网络技术体系所抛弃,不同人群、地区和国家接触到新技术力量的不同时间,可以说构成了当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对那些被信息化资本主义视为无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财富和信息的流通往往绕道而行,整个国家、区域、城市和邻里的人口都被“网络社会”所隔绝,甚至连人们必备的生产、消费、沟通乃至生活的基本科技设施也被剥夺,更不用说经由信息技术的全球网络积累财富和资讯的权利了。这种不平等不单是加剧了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通过信息技术,所有资本、财富和资源都联合在一起了——这种联合不分“发达”和“发展中”——同时却有大片地区和大批人民被隔离于“网络”之外,同样,这种隔离也不论“发达”与否。卡斯特把这些被隔离的地区称之为“断了线的区域”(switchoff areas), 它们在文化与空间上都是断裂的:“这种地方位于非洲的破落城镇,或是中国及印度贫困的农村,但也包括美国内地的城镇或法国的‘城郊’”。[3](P38) 而在中国,由国家政策、市场导向和消费环境共同决定的“网络发展”也可能如卡斯特描述的那样“绕道而行”,为“不平等的发展”推波助澜。
三
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国网络发展的不平等,是为了避免单纯地把网络当作一种中性的高新技术,并且依据“技术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逻辑,认为它可以游离于社会语境而带来“抽象”的进步。相反,不平等发展的事实可以提醒人们注意网络深深地纠缠于国家、市场和个人的历史性关系中,它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现,正如詹明信对“媒体”一词的分析那样,在物质、社会和美学的不同层面既受制于原有的权力和市场结构,同时又通过创造新的表达空间改造了这一结构。也就是说,在“真实世界”中所常见的传播障碍,如国籍、语言、种族、性别、社会阶级、政治倾向和经济地位等,在“虚拟世界”中仍然存在。互联网的“全球性”本质上也是以“地方性”和“社区性”的方式牢牢地控制着。一项关于台湾网民行为的研究表明:平均84.3%的线上时间用于浏览当地站点:“……用户继续生活在‘本地’,也就是与他/她相联系的地方,他/她的需要和愿望产生的地方,他/她有归属感的地方。”[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催生出了各类边缘的、处于模糊地带的新文化空间,譬如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制片人负责制的电视节目,譬如“以书代刊”的出版形式,譬如“二渠道图书”的发行与营销……这类既具市场因素,又与权力周旋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正越来越有力地作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甚至是形塑了文化思想的新形态,同时其自身也极其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它们与既成体制的利用、改造、收编和吸纳关系,显示出了文化思想生产的某些新特点。这种特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市场化的过程带来了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但变化不是在“权力”与“市场”二元对立中完成的,而是导致了权力与市场交织在一起的新的统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功能。所以当人们试图使用来自西方的“公共空间”的理论来说明这些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予以定位,显示了当代中国媒体空间、文化生产与“公共性诉求”之间复杂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以其“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双重威力改写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面貌。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它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空间。而且伴随着这种新空间的浮现以及它日益深刻地介入到传统媒体和社会之中,则必然会产生出新型的媒体社群。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一新的媒体空间的可能性,因为它的生产同样受制于市场与权力交互运作的特殊语境。
可以把网络媒体兴起至今的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网络兴起的初期,一方面由于权力对新技术蕴含的解放性力量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新经济”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大肆“烧钱”,免费为个人或团体提供了大量的网络空间。实际上,按照网络发展的所谓“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 网络经济的扩张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② 通俗地讲,就是网络在使用人数众多的情形下才会展现其价值,而且一旦使用者超过某个特定临界量后,它的价值就会以几何级数成长。其原理是越多人使用网络,其价值就越高,也越能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因此,系统开发者在运营之初往往以低价甚至是免费来吸引使用者,他们寄希望于当使用者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几何级数地发挥网络效用。所以,政府和市场最初在不断扩大网络的使用上利益是相当一致的。而“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即WWW)的出现,使得机构、公司、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网址”,然后每一个能够联上网址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文本和图像来制作自己的“主页(Home Page)”,或者开设相关的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即“电子公告栏系统”)。特别是BBS这种形式, 用户只要连接到Internet上,直接利用浏览器就可以使用BBS。而进入到BBS,用户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讨论组,周期性地检查是否有新的消息出现在一个讨论话题中,向讨论组发送一个消息以便其他组员阅读,向发送一个消息的某个组员做回复。这种个人化、互动式的交流新形式用卡斯特的话来说,“比较接近源自蓬勃都市文化的商店街历史经验,而非单调无聊的匿名郊区里蔓延的购物中心”[3](P438), 它可以让公众广泛地接触到各种信息并展开讨论,同时由于技术上的开放性,也使得政府和市场难以有效地限制和控制这种接触和讨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传统媒体依然受到权力强有力控制的情况下,网络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不仅构制了文化生产、发表、阅读和交流的新空间,进而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秩序,而且由于网络具有强烈的“交互性”,与其他传统媒体相比,它更容易使得参加者具有“参与感”和“认同感”,这也是网络社群产生和繁荣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则随着网络的逐渐成熟和广泛扩散,权力也强化了对这一新型媒体的管制,譬如对国际互联网在信息通道上设置“防火墙”,散布大量的“伪代理服务器”;对国内的网络媒体则加强网络内容的审查,强制性地关闭某些经常“犯规”的论坛、网页和网站,对有“出轨”言论的网络实体处以高额的经济处罚,以经济手段控制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向……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管理互联网的法令、法规和条例,比较重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国务院,1998年3月6日颁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2000年9月25日颁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产业部,2000年11月7日颁行);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2002年11月15日生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2003年11月7日颁行)。由此不难看出, 任何一项技术的选择首先是政治的选择,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监督和控制。譬如2002年9月,著名搜索引擎“google”突然在中国大陆被关闭一周。重新开放以后,不仅网页快照功能受到了限制,而且当用户在“google”的搜索栏中输入某些词语时,就可能导致网站无法登录。由于网络源于军事科学,人们在热衷于谈论它的开放性时,却或多或少遗忘了其技术本性中具有的强大控制性。而且更关键的是权力的功能不止于监督和控制信息,它同时也是信息的制造者和生产者。网络个人化、去中心和互动性的“弹性”形态有可能催生出更加灵活多变的统治方式。③ 另一方面则由于网络经济泡沫的出现,“新经济”不再以“烧钱”为目的,转而要求降低成本,追求利润。一般认为,由于对新技术发展的迷信,1996年至1999年可谓是网络经济最兴盛也最狂热的阶段。但如果仅以技术的因素作为推动网络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未能掌握如何运用网络来加强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则过于乐观的期望难免流于泡沫化。自1999年至今,这股热潮已逐渐由狂热转归为对现实经营环境的考量。所以各大网站大量取消免费的个人空间,使得不少已经办得有声有色的个人网页和论坛被迫关闭;而且出于赢利的目的,资本也加强了对“网络”形象的塑造,这不仅表现在为了规避处罚的风险,强化了自我检查的机制,同时也以电子媒体和纸质媒体相互生产的方式放大了“选择”和“过滤”的功能,这在所谓“网络文学”形象的建构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文学”最终演变成“纸质媒体”对“网络空间”想像性的生产。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技术”和“新经济”因素的介入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有着显著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检讨的是,“技术”与“资本”和“权力”诸因素的交构如何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思想的表达形式,同时这种形式又怎样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的生产条件;而新的“文化”和“思想”形态又是如何借助这一新的媒体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突破它的限制,而不被资本和权力的逻辑所宰制。
收稿日期:2005—10—24
注释: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从1997年开始实施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调查工作,从1998年起每半年公布一次统计报告,目前已完成了十四次调查。
② 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为3Com公司的创办人,以太网络(Ethernet)的设计者,他提出网络产生的效用与使用者人数的平方成正比的网络发展定律。这个定律故名“梅特卡夫定律”。
③ 已有论者将网络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过渡的论述结合起来考虑。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中第五章《作为话语的数据库或电子化的质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的相关论述。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网络如何导致了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