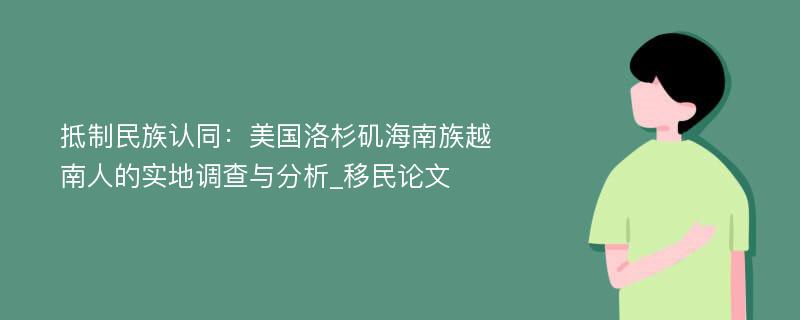
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裔论文,越南论文,海南论文,田野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尤其是国际难民的族裔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y)处于一个不断选择和再选择、塑造和重塑的动态过程之中。①在西方族裔理论中,族裔群体(ethnic groups)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泛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群体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定的情境(circumstance)中建构与协商自身的身份认同,现存理论对此做出了颇多解释与论述。其中,以格尔茨(Geertz)为代表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族裔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植根于族裔文化并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根基性情感联系和认同,强调“原生情感”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在因素。②这种视族裔特性(ethnicity)为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就遭到了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m)的质疑和批判。情境论也称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裔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族裔身份认同是族裔以个体或群体的文化标准对特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和理性选择。③以韦伯(Weber)和巴斯(Barth)为代表的建构论(constructionlism)则在情境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制约,认为族裔身份认同是在同一社会结构中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④在这样的互动中,族裔成员根据文化“异质性”(difference)来划分“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这种划分,不完全是族裔成员主观的理性选择,还有赖于社会或其他族群的认定,是一种“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y)的划分。此与族群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族群而言更是如此。由于族裔成员的身份认同由“社会边界”所维持,因此区分族裔的主要依据是它的“社会边界”而不仅仅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原生”因素,文化可能只是表达族裔边界的一种符号与工具而已。⑤
在上述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将族裔身份认同细分为不同类型与表现形式。其中,社会学家甘斯(Gans)在情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象征性”族裔身份(symbolic ethnicity)的概念,指出族裔身份认同确实具有工具性和理性选择的成分,但随着少数族裔群体向主流社会的融入,族裔文化和族裔社区的实用功能也随之逐渐弱化,族裔身份也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象征性的族裔特性在人们的生活中就不再具有工具性的功能而仅仅是一种表意的功能,越来越像一种可有可无的、可选择的“业余活动”。⑥燕西(Yancey)与泰勒(Taylor)等学者则在建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动中”的族裔身份(emergent ethnicity)的概念,认为在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制约下,族裔成员会根据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及与其他族裔的互动来不断修正族裔群体的边界与标准。族裔身份认同会随着个体定居模式、教育、职业、收入状况及当地的社会制度而改变。⑦受到上述研究的启发,周敏等学者从情境与结构互动的视角提出了“混合性”族裔身份(hybrid ethnicity)的概念,既强调族裔成员在不同情境及与不同人群互动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族裔身份的理性选择(情境论的解释),又强调社会结构对其理性选择的限制(建构论的解释)。周敏在对美国亚裔第二代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这群人,虽然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美国白人不分上下,但其族裔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族裔身份认同受到美国的种族制度(结构因素)的制约,即便他们在某种情境下可以自由地表述和展演不同的族群身份(如华裔、唐人、中国人等),但他们却无法自我建构成为真正的“美国人”或“白人”,⑧不管他们的内心和行为如何的美国化,还是被先入为主地视为“外国人”。
情境论和建构论多强调族裔身份的弹性,注重影响身份认同的外部因素;而后的“象征性”、“变动中”与“混合性”族裔身份的概念,同样强调族裔身份的弹性与多变性,但更注重考虑内在因素及不同人群的互动过程。这些理论,在解释定居型移民及其土生土长的后裔的身份认同中是比较适用的。
对于一些有着多重跨境与迁徙经历的群体而言,则需要用新的理论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族裔身份认同中出现了凝固和相对不变的状况。如果说社会结构和特定情境会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那么如何解释某些群体在宏观社会结构与中层社会情境发生了巨大变动后依然有意识地保留原有的族裔身份认同呢?实际上,不少族裔群体(通常发生在第一代移民身上)在移居地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及与当地社会的其他族群互动时,由于被当地主流社会或其他族群所排斥,往往会通过使用传统的文化符号,依靠延续与强化原有族裔身份认同来应对社会地位的变动和社会排斥,即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抵御性”族裔身份(defensive ethnicity)。⑨而有着多重跨境迁徙经历的政治难民最有可能发展出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由于突然而来的社会变迁,他们比一般移民更有可能强化公认的族裔文化传统和原来的族裔身份认同,通过此类族裔建构,对一些不利情况作出回应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近年来,来自越南、柬埔寨、老挝(简称印支)的华人难民的族裔身份认同已引起学界关注。⑩笔者在对华人难民中的一个分支——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调查中发现,这群原籍海南、出生越南并辗转美国的移民群体,为了抵御来自越南及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不断强化自己原有的“中国人”和“海南人”的双重族裔身份,形成了上述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尽管他们从未回流到祖籍国中国,也从未在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中有过长时段的生活经历,但是他们却将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在辗转迁徙过程中凝固下来,并通过某些特殊形式加以强化。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在不同社会结构和情境中凝固、表述和展演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先后发生、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且跨越时空的。2011年暑期及2012年寒假,笔者对美国海南籍越南华人的聚集地之一——美国洛杉矶唐人街以及新华人移民聚居郊区(Chinese ethnoburbs)(11)进行了田野调查。笔者的研究对象基本上介于40-60岁之间,祖籍海南,出生越南,在20世纪70-80年代因越南排华而被迫逃难,几经辗转迁移至美国。他们在越南时大多为有产阶级,后受越南排华的冲击,一贫如洗地以难民身份逃难到美国。(12)来美后大部分人投身于华人族裔经济,包括从事餐饮业、美容业及这些行业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少数人抵达美国时年纪尚轻,他们一般通过教育的途径跻身于专业技术人员行列。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具有共同迁徙经历的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13)
二、跨境流徙中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凝固
首先分析海南籍越南华人在流徙与侨居过程中如何受到来自传统“侨”文化、个体的跨境迁移经历及在异地的社会境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出抵御性身份认同,并逐渐凝固下来。
(一)侨居越南:认同的初步形成
越南曾经受到过中国封建王朝上千年的统治,即便后来自主独立,也一度是中国的“藩属”。1858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随后把越南变为其保护国,并建立了一整套殖民政治、经贸与管理体系,实行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在此之前和此时到来的华人移民大多是贸易商贩,他们在当地的较为强势的经济地位和特殊的职业身份很快使其成为介于殖民者与土著多数族群(majority group)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社会夹缝中继续发展华人族裔经济,成为典型的“中间人少数族裔”(middleman minority)。(14)越南华人主要分为广府、潮州、客家、闽南和海南五大族群。海南籍越南华人大多聚集在越南中南部,从事商业、手工业和贸易活动。根据1952年的相关统计,全越南的华侨为1,254,481人,其中琼侨人口大约为12.5万。(15)
尽管这些海南籍越南华人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他们多数人仍抱有“落叶归根”的侨民心态,另立族裔社区,不主动在政治和文化上同化于越南主流社会。(16)他们基于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观念、家乡情怀,以及悠久辉煌的中华文化而建立起一种“历史认同”。这种认同,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孙中山民族观念影响而发展出基于中国国家的“民族主义认同”,并由于日本侵华而在二战后达到了高峰。(17)20世纪70年代越南排华前,海南籍华人在越南一直保留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具体表现为对祖籍地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多重认同,不仅包含着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cultural identity),也包含着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认同(national identity),同时还保留了作为族裔分支的“海南人”认同。这种身份认同集中体现了“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Once Chinese,always Chinese)的传统“侨”文化观念。
事实上,大部分海南籍越南华人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侨民”寄居者(sojourner)心态。尽管他们大部分出生于越南并拥有越南国籍,但却自称为“出生在越南的海南人”,并强调自己“不是越南人”。韩女士的父母都是海南文昌人,她本人出生在越南并在越南长大。当问到她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时,韩女士不假思索地回答:
嗯,我肯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从小就听到父亲不断地说我们是从文昌来的,所以我们是海南人。我是在越南出生,但是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上华文学校的,家里也都是讲华语,我父母之间讲海南话,我会听海南话不会讲。我们从小都没有这个意识说自己是越南人,我们只是在越南出生并长大。
对于这群海南籍越南华人来说,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入了越南国籍,且很多人也认为越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但他们乐于表明与“越南人”的区别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自身族裔优越感。语言尽管是族裔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记之一,但却不是影响海南籍越南华人认同的决定因素。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不会说海南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海南人”认同,祖籍国、乃至祖籍地的认同凝聚着这群人的共同情感。
李先生的父亲是海南文昌人,在日本侵华时期逃到越南,与一位越南女子结婚后生下他。由于母亲是越南人,李先生在家里都是讲越南话。李先生只能听懂一点海南话,但不会讲,可他却宣称自己是“海南人”: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读华文学校的,在越南的时候,我会讲华语和粤语,但是我就不会说海南话,会听一点点。所以我们是中国人,不是越南人。我的家乡也在越南,因为我是在越南出生的,越南是第二故乡。文昌是我爸爸的家乡,也是我的老家。我是在越南的中部,我们海南人主要是集中在越南的中南部。那里很多海南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医院和学校,我们是不会到越南人开的医院和学校去的。
海南籍越南华人在侨居地越南具有经济强势地位,他们会将自身的族裔身份凌驾于侨居地的社会结构之上,并通过族裔隔离(ethnic segregation)的社会适应模式较为完整地保留传统的“侨”文化,与当地人相区隔,从而初步形成强调本族裔优势地位的“抵御性”身份认同。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不仅强化其族裔优越感,还使他们对越南和越南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强化现有的族群边界。同时,这种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和社会隔离又使他们处于政治边缘化的际遇,为之后受到排斥和驱赶留下了伏笔。
(二)流徙逃难:对原侨居国疏离感的强化
1954年至1975年期间,南越政权先后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强迫华侨归化运动。1975年越南南北方统一后,越南当局开始逐步有规划地推行排华政策。1978年以后,越南公开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越南当局变本加厉地公开驱逐华侨华人。(18)许多越南华侨华人由于害怕遭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害,开始从海路、陆路外逃。(19)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统计,至1985年9月,逃出的印支难民共151万人,其中越南难民为96万人。(20)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大多数也是在这个时期被迫通过各种方式离开越南的。
1979年韩先生只身从越南偷渡到美国。讲起偷渡经历,他不免有点感慨:
我是怎么说呢,我当时是偷渡过来的,1979年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先逃出来,然后我父母第二年的时候也是自己偷渡出来的。当时我偷渡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先到香港,我们坐木船逃到了香港。然后呢,我从香港坐船,那艘船非常小,挤满了逃出越南的难民,很多人在途中生病或死亡。我们坐到大洋中央,美国有军舰来接我们到美国。当时确实是很危险的。
李先生一家也是在1979年的时候离开越南的。他讲起当时的情境依然心有余悸:
当时越南当局对我们中国人很不好,把我们华人开的商店没收了,我们都没有办法生活了,感觉都走投无路了。越南人其实很妒忌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我们都不到他们的医院和学校的。但是排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得走,跑到美国来了。我在越南已经是没有什么亲戚,全部都走光了,也没有回去过。
李先生在表述中用了“我们中国人”这个词,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在排华期间更为显著。越南当局以“非国民”的强硬方式来迫害和驱赶拥有越南国籍的华裔国民和长久居留的华裔侨民,使得这批华人难民的受害感愈加强烈。在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中,不但强化了他们对于越南——他们口头上说的“第二故乡”——的疏离感,还无形中延续了传统的“侨”文化和强化了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
(三)辗转美国:族裔分支和“亚”华裔凝聚感的强化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印支三国政局动荡,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成千上万的印支难民,其中美国为最大的接收国。(21)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据,1978年到1982年是越南难民和印支华人难民大量涌入美国的高峰期。为了安置印支难民,美国政府当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衣食住行、学习就业等方面给予援助。(22)美国对于越南难民采取了疏散(dispersion)的安置方式,便于其尽快融入美国社会。(23)但是,被分散安置到美国各地的很多难民,通常在几年内又再次迁移,加州是他们的首选。(24)位于洛杉矶南部的橙县(Orange County),有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越南人聚居区。加州的大多数越南华人,集中居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老唐人街和新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笔者所访谈到的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也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流徙到美国并大部分最终在洛杉矶定居下来的。(25)
史先生的父母祖籍海南文昌,他本人在越南出生并长大,后在70年代末越南排华期间以难民身份举家迁入美国。史先生全家在洛杉矶柔似蜜市安顿下来并一直居住至今。史先生在解释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与越南人聚居时说到:
我们一来就住在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有很多华人居住嘛,越南人有越南人聚居的地方,而我们是跟中国人住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越南人嘛,虽然我会说越南话,但是我们是碰到他们越南人时才跟他们说越南话的。我觉得我是中国人,不是越南人,我只是在越南出生的而已,我父母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当然我的国籍是越南的,但我是中国人。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的话,我还是海南人呢。我是出生在越南的华侨,越南只是我们的侨居地。
与史先生一样,大部分海南籍越南华人选择在老唐人街或者是新华人移民聚居郊区落脚。这种居住模式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选择,也以结构化的方式进一步将这种身份选择凝固于其中。在老唐人街或是新华人移民聚居郊区里,这个“亚”华裔(sub-ethnic Chinese)群体往往被从其他地方来的华人视作越南人,也因他们的越南难民背景而受到来自华人社会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为了能够保持自身主体性,他们往往更强烈地保留了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并以此与越南人保持距离。而其后的社会适应模式更是促进了其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形塑。史先生到美后,由于缺乏相应的美国专业文凭,在一家美国银行作最低级的职员,从柜台做起,然后一步步升职做银行经理。由于受到“天花板效应”(26)的影响,他辞掉了银行工作,于上世纪90年代转行自己做生意,从事营养品销售行业。在问及是否为“美国人”时,史先生显得很诧异。在他看来,美国相比越南更无法称得上是“家乡”。他还将这种“不是美国人”的抵御性身份认同传达给子女。
美国这里?这里只能算是侨居地,无论是越南还是美国。我们都很珍惜同乡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排华),所以才懂得珍惜。我的孩子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我就跟他说,你是黄皮肤的,你是黄种人,你到外面跟老美说你是美国人,没有人会信你的喔,哪怕你是本地出生的,他也会觉得你是中国人,也会歧视你,你去到大公司工作,他也会歧视你的。小时候,当然说他自己是美国人,他大了就慢慢明白了。
史先生的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在美国生活的海南籍越南华人的想法。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青少年或是成年时期移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排华的集体记忆使得他们的抵御性身份认同被延续和强化了。尽管当地政府对于这批难民采取了颇多保护性、扶助性的政策,但由于受到族裔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加入了移居国国籍的移民也仍被当地主流社会视作“永远的外国人”(forever foreigner),饱受“他者”身份的困扰。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压力下,传统的“侨”文化观念被海南籍越南华人重新延续,以此来建构其在“强势客文化区域”(27)中的自我身份。如果说在越南的抵御性身份认同更多是强调族裔在当地主流社会的优势地位,那么在美国重新强化的抵御性身份认同更多是表达他们对于自身弱势地位的不满。
由上可以发现,洛杉矶的海南籍越南华人基于侨居越南、流徙逃难而后辗转到美的共同的跨境经历及相似的社会境遇与适应模式,将抵御性身份认同——也即“中国人”和“海南人”的双重身份凝固于跨国流动的过程之中,同时也使得“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传统“侨”文化观念得到巩固和延续。
三、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表述
下面分析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之表述,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传统“侨”文化及移居地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互动之影响,发展出“离散”(28)文化的。这种身份表述,同样以“中国人”和“海南人”为叙述框架。
(一)“正宗海南人”
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但他们的“海南人”与“中国人”身份并不矛盾。“海南人”与“中国人”是一种双重的身份认同表述。他们执着地认为自己是“正宗”的“海南人”,由此引申出他们也是“正宗”的“中国人”。这种表述,不仅受到他们在越南所延续下来的传统“侨”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当前美国的社会境遇与社会适应模式的制约。
大部分在洛杉矶的海南籍越南华人始终认为,自己难以摆脱“难民”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身份。而保持传统的“侨”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劣势地位,应对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斥,防范不良后果。陈先生今年六十多岁,他在越南时拥有着一份足以过上小康生活的生意,1980年,以难民身份、一无所有地与太太一起从越南来到美国。来美国后由于缺乏英文及美国所认可的文凭,难以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就业。目前其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所给予的救济。当问到其身份认同时,陈先生略显激动:
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在越南所受到的华文教育比你们还要多,我们都是很传统的,保留了很多中国人的传统,反而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很多传统都已经没有了。我不是歧视他们哈,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这个大陆的社会变化太快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还保留得很完整的。我们其实比海南人还要海南人。那些海南儋州的兄弟过来,我和他们说儋州话,他们都很惊讶、很惊奇,他们说为什么你在越南可以保留得这么好的儋州话。还有的时候我们回海南、回大陆,当地人都很惊奇我们怎么还有这么多传统是在外面保留下来的,我们竟然在越南保留了这些传统。我以前在越南时是念华校的,我以前小时候被父母逼着去读古文。现在很多人在大陆都未必受到这种传统的教育。我们说的话也是很标准的,他们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说的话是像我爷爷辈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没有怎么变过,但他们那里受到了很多语言因素的影响,反而变了。
陈先生对于“我们保留了传统”、“我们比海南人还要海南人”的身份表述,实际上是对作为中华文化及其分支的海南文化的合法继承人地位的强调。他之所以要如此表述,无非是向想象中的参照群体(在祖乡的海南人)证明他们依然保有家乡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保留得比家乡还要“完整”和“纯正”。这种看似有炫耀与自豪的身份表述,实际上反映出历经越南排华并以难民身份辗转到美国的这个“离散华裔”群体想要与祖乡建立密切情感联系的强烈意愿。
我对海南人是很有感情的,如果说有海南乡亲,特别是从内地过来的话,我们是很欢迎的,就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都会很热情的接待。像海南侨办啊,还有市政府的人来的话,我们都会觉得特别亲切,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的。还有如果是从中国来的,我们也是有着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陈先生的“海南人”身份表述,在直接从海南迁移至美国的移民身上是很少见的。对于后者来说,族裔身份往往不需要额外强调。但对流徙于祖乡、越南、美国三地的海南籍越南华人来说,他们作为“海南人”、“中国人”的身份必须通过不断地略显夸张的宣称与表述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夸张的身份表述,在美国华人社区的特定情境中尤为重要。
(二)“在哪里都是中国人”
笔者从田野观察中发现,几乎所有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都频繁使用“中国人”而不是“华人”或“华裔”的表述。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是他们能够从“侨”的传统文化中所寻求到的最直接的表述。这种表述,由于“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日益表现出离散的文化形态。
在美国,通过聚居区族裔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29)而获得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资源,是大多数海南籍越南华人所选择的社会适应模式。韩女士也不例外。她在1979年随家人离开越南时才16岁。她来到美国之后读高中并完成了大学学业。目前在华人移民聚居郊区从事房地产经纪生意,收入颇为不错,她全家也在附近买了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算是安居乐业。这种依赖族裔资源的社会适应模式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我们觉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不太会困扰我们的问题,父母从小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也觉得很proud(自豪)。我们在越南是这样觉得,来到这边(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也很proud。我觉得(做)我们中国人挺好的。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
“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的表述,实际上反映出大部分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离散华裔”的倾向,他们对于中国有着一种接近本质主义的原真(true)情感。其中所展示出的抵御性身份认同,既是其传统“侨”文化的延续,也受到美国社会适应模式的影响;既可暂时逃离越南排华的惨痛历史记忆,也能够为其在移居地社会的生活提供新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他们还将这种身份认同传达给在美出生的第二代。韩女士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在美国出生的广东籍华人。说到自己孩子的认同,她颇为坚定地说:
我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Chinese,所以还是Chinese。我是在越南出生的Chinese,所以我也是Chinese。
尽管韩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也是中国人,但她可能忽视的一点是,她的孩子可能更倾向于“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的认同而不是“中国人”(Chinese)的认同。另外,对于自身认同而言,韩女士对于表述中所提及的“中国人”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的理解也是比较含糊的。
大多数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强调使用“华人”或“华裔”,但有时也接受具有族裔特性而非国籍意义的“中国人”这个名称。(30)本研究所涉及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难以从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直接判断他们口头上说的“中国人”是不是只表达了族裔特性而不含有民族国家国籍的指涉。作为“中国人”的抵御性身份认同的表述,为这个群体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展演(performative identity)(31)奠定了基础。
四、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展演
如果说抵御性身份认同的表述多是一种言辞上的表达,那么抵御性身份认同的展演则是一种更为主动的行动上的体现。
(一)建立海南会馆
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位于洛杉矶东部,原名“南加州海南同乡会”,主要由上世纪70-80年代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洛杉矶的海南籍华人组成,其中有95%的成员是从越南过来的。现任海南会馆会长韩济元先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提到会馆的宗旨:“我们成立这个会主要是为了‘心的安置’,为我们这群无家可归的乡亲能够在这边重建一个新家园,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互相照应,互相帮助。”
海南会馆成立之始就成为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赖以生存的“新家园”。原来的海南会馆坐落在洛杉矶的唐人街内。大部分会馆成员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多迁居洛杉矶的新华人移民聚居郊区——柔似蜜市和圣盖博市,海南会馆新址也搬到了柔似蜜市。会员出资买地,购置了永久会址。会址于2010年10月份落成。会馆为了实现“为生者有聚会之所,终者有长眠之地”的目标,不仅设立耆老相济金、学生奖学金用以资助上了年纪的长者及年轻学生,而且还购置坟地,希望乡亲们在去世后能够有一席长眠之地。除此之外,为了丰富成员的日常生活,海南会馆还聘请了老师(多数也是海南籍越南华人)来教授中国武术、中国传统歌曲及民族舞蹈。每天晚上六点钟,海南会馆会开设供成员选择的各种学习班。会馆每隔几年就会组织会员回中国及海南观光探亲,让许多从未回过海南的乡亲重新认识自己的祖乡。
海南籍越南华人的传统“侨”文化与华人离散文化,在海南会馆里,即在离散华裔的组织结构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下面是其社团组织的介绍:
溯自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世局色变之后,时至危殆,吾旅印支三邦乡亲,秉冒险犯难之精神,桴海逃秦,流徙四方,转移来美,庆得收容定居,数年间络绎不绝,逾万之众,多聚居加州地区,深知既得其安居而乐业,然欲图长治久安,万全之计,唯须乡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始克达到安和利乐之境界,此请示之所趋,急不容缓,乃发起筹备组织同乡会,群策群力,促成其事,终于一九八二年元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命名为“美国南加州海南同乡会”。本会之宗旨以“联络感情”、“促成团结”、“发挥互助”、“服务同乡”为会务活动之准则,推动有益于乡亲之福利事业……
海南乡亲侨居海外,遍布世界各国,将近三百万众,虽身在海外,心系家国,片片乡心契机缘。固有世界海南同乡会之组织,加强各地区同乡间之联系,敦睦乡谊,缔造基业,进而策励将来以作。为吾人今后努力之准成,是厚望焉!
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始终视自己为“侨居海外”的“流徙者”,“侨”与“离散”的意味无不尽显其中。一位被访者史先生在谈到海南会馆时说道:
……其实只有是经过了排华,就是被排斥了,你才能够更珍惜这种乡情,我们会馆里面成员之间的这种情谊是很浓厚的。还有就是珍惜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国家是很重要的。
史先生上文提及的“国家”既非指他们的出生地越南,也非他们现在的移居地美国,而是明确指向他们从未真正生活过的“想象的祖籍国”——中国。这些“离散者”积极地利用海南会馆这个“亚”华裔平台,将自身的抵御性身份认同以仪式化形式充分展示出来。
(二)开展祭祀仪式
下面以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新会址落成一周年庆典中的祭祀仪式为例,分析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如何从“文化工具箱”(32)中寻找到适合于自身族裔身份展演的资源。
祭祀活动在位于洛杉矶东部的海南会馆内举行。海南会馆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天后宫,后面设立有可容纳百人的活动大厅。在活动大厅里,22张圆桌有序排列,每张桌子上摆放了一些饼干之类的小点心和餐具。天后宫殿内供奉着七位神像。天后圣母娘娘(也即妈祖)居中,一百零八先烈昭应祠居右,关帝圣君居左,矗立在天后宫的正殿位置,其他四位神明(福德正神、月老神君、文昌帝君、值星太步)分居正殿两侧。七尊神像前面设立了供案台,供案台上面摆放着烧乳猪、鲜果、香花、烛台、香炉、西式蛋糕、纸钱、茶水、酒、筷子、净手水及手巾等类物品。正式的祭祀仪式于上午11点开始。
程序一:舞狮开场。海南会馆会长韩济元与其他理事、监事陆续来到天后宫的正门口,顺着阶梯有序排成五行。他们都穿着祭祖的袍子,其中主祭与陪祭身着深红色袍子,其他工作人员身着蓝色袍子。前面第一排中间是韩济元,他的右边是监事长符志建,左边是第一副会长陈嘉展。在主祭与陪祭人前面摆放着生菜和橘子。接下来青少年舞狮团入场,在海南会馆正门口的广场进行表演。接着舞狮头的人上前把生菜和橘子咬碎,将掰开的生菜和橘子送到主祭人与陪祭人手里,并把剩余的生菜和橘子抛向人群,人们会把接到的生菜和橘子吃掉。
程序二:祭祀天后宫大殿外地基主。(33)祭祀程序的主持人是海南会馆陈秘书长。他身着鲜红色袍子,宣布此项仪式开始。他说:“传香”,身着蓝色袍子的工作人员便将供案台上的香点燃,并把香火传给在阶梯上一列排开的各位祭祀人。首先,主祭韩会长一人上前,净手并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黄纸,做宣读状,旁边的主持人陈秘书长拿着麦克风宣读祭祀文。祭祀文主要大意为:我们希望地基主能够保佑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我们的乡亲能够在新的家园里安居乐业。接着主持人说:“献花”,这时工作人员把插在金猪上面的红花递给韩会长,韩会长拿着花向空中扬了一下,接着工作人员将花放回金猪身上。陈先生说:“献果”,工作人员把放在供案台上的鲜果递给韩会长,韩会长又扬了扬。其次是献酒、献糕点。等到献牲品时,韩会长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红色筷子,双手举过头顶,以示献金猪。接着主祭高举纸钱“献财帛”,之后交给工作人员烧掉。最后,主持人宣布礼成。
程序三:祭祀天后宫大殿外皇天后土。基本程序跟祭地基主类似,只是在上香献礼后,全体祭祀人员要行三跪九叩之礼。
程序四:祭拜观音神像。观音神像位于天后宫门口的右外侧,属于殿外神明。其基本程序跟祭地基主的仪式相同,但只需上香献礼。
程序五:祭祀天后宫大殿内诸神明。殿内七个神明前面分别站着一位主祭和两位陪祭。大殿中央还另设供案一张,在供案前面站着一位正献主祭,两位陪祭,正献主祭为韩会长,陪祭分别是监事长与第一副会长。主持人陈秘书长宣布:“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会馆新址、天后宫落成一周年酬神祭典开始。”此时,殿内钟鼓齐鸣。主持人接着说:“请全体肃立,请各执事就位,请各位神明陪祭就位,请各位主祭净手。”然后他宣布:“传香”,身着蓝色袍子的工作人员将摆放在供案台上的香递给正献主祭。接着主持人宣布:“上香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在场除了祭祀人员祭拜外,围观的群众人手拿着一支香,虔诚地对着诸位神明三鞠躬。接着,正献主祭韩会长做献祝祷文状,主持人陈先生宣读祭文内容,大意与在殿外的祭文内容差不多。此后,主祭、陪祭分别向神明献香花、献鲜果、献茶、献酒、献牲品、献财帛元宝。接着,主祭、陪祭行三跪九叩礼。最后,主持人宣布礼成。
实际上,并非在场的所有人都了解这个祭祀仪式的程序及内涵。在此之前,这群海南人在越南及来到美国之后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祭祀仪式。海南会馆秘书长陈先生在建立天后宫暨海南会馆新址之初,曾遍访台湾、香港等地,通过对这些地方的祭祀仪式进行模仿才制定出这样一整套仪式。因此,直接从海南移民到美国的少数会员会觉得这个程序与海南的祭祀仪式存在着差异。但是,执行此仪式的会员坚信这个程序是传统的华人祭祀仪式,以此来彰显他们的中国特性。制定这套祭祀程序的陈先生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可以展演一套甚至在遥远的“祖乡”都难以实现的传统祭祀仪式。“去年海南省侨办那边来人,他们都很感叹,他们说在海南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这么完整,但竟然在这里可以做得好”。祭祀是中国华南汉族地区的重要文化传统,某种程度上成为华人认同的重要表征。这群海外的“离散者”,将祭祀这种可复制的传统文化“发明”出来,成为其抵御性身份认同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祭祀仪式,不仅反映出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族裔认同,也表现出对于海南的地域性认同。在祭祀仪式之后,这个移民群体随后在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举行了午宴,以下是当时午宴的情景。
午宴于十二点正式开始。首先,海南会馆韩会长上台致答谢词,并与全体理事、监事合影留念。接着,主持人上台,请海南会馆歌唱团会员就位。经过了几分钟的组合,歌唱团的会员陆续上台。前面是身着蓝色靓丽唐装的女士,后面是打着领带的男士。他们分别演唱了《站在高岗上》、《根在海南》及《海南之家》等歌曲。海南会馆陈先生在台上指挥。台上的演员唱得很动情,台下的观众也深受感染。尤其是《根在海南》一曲,似乎把在场所有的人从美国拉回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祖乡海南。演唱结束后,台上台下高喊“海南万岁”,呼声此起彼伏,把会场气氛带到了高潮。中间还穿插了一些中国传统武术、舞蹈表演,以及会馆成员自娱自乐的卡拉OK,唱的也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族歌曲。最后,全场还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群情激昂,并高喊“海南万岁”。据有些会员讲,他们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在会馆里面联系唱歌等事宜。在洛杉矶聚居的美国海南籍越南华人经常举行类似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歌曲、舞蹈等文艺表演,来显示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强调跨境海南人“根在海南”。而聚会的尾声,即“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再次重申了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展现出的宏大力量。
当然,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展演,是移居国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对于完整公民身份及完全社会认可的一种诉求。无可否认,他们对于中国保留着某种政治认同与情感,但这些都并不意味着这个离散华裔群体仍然保留着对于中国的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事实上,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想象的祖籍国”,他们从未在那里居住过也不愿意去那里住,也无需履行任何国民义务和遵从中国法律。尽管众多族裔成员表现出对祖籍国的支持和依恋,但通常并不愿意放弃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与身份。(34)这种身份展演,可以说是当他们在面临美国社会结构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五、结语
本文以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为个案,提出了族裔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类型——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笔者认为,这个移民群体的族裔身份认同不仅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还与其迁移的跨境经历及其在迁移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境遇,即个体的社会适应或融入(social adaptation or integration)和群体在移居国社会被接受的程度(social acceptance),以及族裔群体在移居地社会的地位等社会结构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受到传统的“侨”文化观念、共同的跨境经历及相似社会境遇的影响,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作为“中国人”和“海南人”的双重身份并没有由于迁徙、移居地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而是以此展示出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并在流徙辗转的过程中凝固下来。由此,又使得“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传统“侨”文化观念得到巩固和延续,充实和丰富了离散文化的内涵。与很多东南亚华人不同的是,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并不倾向使用“华人”或“华裔”的表述而是使用“中国人”的表述。这种表述方式,为其进一步的身份认同展演奠定了基础。
对于有明显族裔特征且被社会排斥的美国的海南籍越南华人来说,他们的抵御性身份认同不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象征符号,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其“二次少数族裔”(twice-minorities)(35)的不利地位,使得这个群体要面临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社会压力及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境遇。当这个群体与美国的当地居民在就业机会、住房和社会服务及教育资源上展开竞争与争夺时,族裔身份是他们获得社会与文化支持、免于成为“孤单个体”的重要资源。(36)出于自我保护及谋求发展的动机,族裔成员往往夸大且强化这种“侨”与“离散”的文化价值观念。(37)因此,其“中国人”与“海南人”的双重身份认同,可以理解成既是一种族裔自立和团结的保障机制,也是一种应对移居国主流社会种族主义及排斥华人的防御机制。
尽管他们在迁徙过程中一直维持关于故乡(ancestral home)的记忆与想象,但所谓的祖国或故乡部分是被创造出来的,存在于这个群体的想象之中。(38)虽然自我幻想为“中国人”、“海南人”能使自己与分散的、非领土化的,仅在理念上由抽象的“族裔认同感”和同样抽象的文化自豪感所凝聚成的想象的跨国离散族群共同体(imagined transnational diasporic community)(39)相互联结在一起,并且弥补了由于“去疆界化”所造成的意义缺失(meaning loss),但这种虚幻的归属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家园”问题。
注释:
①参见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曾少聪:《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王苍柏:《重塑香港华人的族群地图——华人移民认同和族群建构的再认识》,《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②参见Clifford Geertz,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New York:Free Press,1963。
③参见Jonathan Y.Okamura,"Situational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4:No.4,1981。
④参见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9; M.Weber,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9-38。
⑤参见Sandra Wallman,"Ethnicity and the Boundary Process in Context," in John Rex and David Mason,eds.,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6-245。
⑥参见Herbert J.Gans,"Symbolic Ethnicity: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No.1,1979。
⑦参见William Yancey,Eugene Eriksen,and Richard Juliani,"Emergent Ethnicity: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1:No.3,1976; Ronald L.Taylor,"Black Ethnic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thnogen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4:No.6,1979。
⑧参见Min Zhou,"Are Asian Americans Becoming White?" Contexts,Vol.3:No.1,2004。
⑨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个体基于对社会资源竞争的需求会以族群为单位来建构边界来抵抗资源流失,出现“抵抗性”身份认同。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艾伯特·勃杰森指出,优势的社会群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会以族群为单位重建边界,展示一种“防御性”政治反抗(Defensive Political Protest)。参见Albert James Bergesen,"Neo-Ethnicity as Defensive Political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2:No.5,1977。但抵抗性身份认同和防御性政治反抗更具竞争性和抗争性,与上文所提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不尽一致。当然,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有时也会发生在拥有优势地位的族群当中。为了保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他们会在社会互动中刻意突出群体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并以此来强化或重建社会边界,使之区别于其他群体。
⑩参见Nazli Kibria,Family Tightrope:The Changing Live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Monica Mong Trieu,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Chinese-Vietnamese Americans:Being,Becoming,and Belonging,El Paso,Texas:LFB Scholarly Publishing,2009;郭玉聪:《越、柬、老华人再移民的民族认同》,《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翟振孝:《迁移、文化与认同:缅华移民的社群建构与跨国网络》,2006年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11)除了唐人街外,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洛杉矶东部的圣盖博市(san Gabriel)与柔似蜜市(Rosemead)。
(12)目前,这批移民约有4万人左右,主要聚居在美国洛杉矶。参见寒冬:《海南华侨华人史》,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
(13)据2000年美国普查数据,美国的越南华人多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只有20%左右的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其比例普遍低于其他亚裔美国人。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唐人街及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的海南籍越南华人,从业情况大体与普查数据相同。参见http://www.census.gov/。
(14)参见Jeremy Hein,"State Incorporation of Migrant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a Middleman Minority among Indochinese Refugee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29:No.3,1988。
(15)参见寒冬:《海南华侨华人史》,第114、128页。
(16)参见Jacqueline Desbarats,"Ethnic Differences in Adaptation:Sino-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20:No.2,1986。
(17)参见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18)参见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
(19)参见Pao-min Chang,"The Sino Vietnamese Dispute over the Ethnic Chinese," The China Quarterly,No.90,1982。
(20)参见香港《大公报》1986年3月23日。
(21)参见Min Zhou and Carl L.Bankston,Growing up American: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1998,pp.24-40。
(22)参见钱皓:《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3)参见Min Zhou,"Straddling Different Worlds:The Acculturation of Vietnamese Refugee Children," in Ruben G.Rumbaut and Alejandro Portes,eds.,Ethnicities: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America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pp.190-191。
(24)参见http://www.factfinder.census.gov/。
(25)据笔者的调查,很多海南籍越南华人一开始并不住在加州,但由于加州华人众多、气候宜人舒适,于是他们陆续搬到加州并在此永久定居。
(26)“天花板效应”即指设置一种无形的、人为的障碍,以阻碍少数族裔、女性中间有能力的人的职位升迁。
(27)参见李亦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海外华人研究研讨会”祝贺词——兼谈海外华人研究的若干理论范式》,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8)“离散”(diaspora)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多方争论。有学者批评主流的“离散”概念的基本假设(即离散族群有紧密的社区边界、有共同的文化与民族的参照)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离散”是一种对现状的过往虚构,会不断地生成和赋予新的意义以符合现状。离散族群其实没有紧密的社区边界,他们的社群想象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参见Rogers Brubaker,"The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8:No.1,2005。
(29)参见Kenneth Wilson and Alejandro Portes,"Immigrant Enclaves: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6:No.2,1980。
(30)陈志明曾指出“中国人”有两个意思,既指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也指具有华人族裔特性而非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参见陈志明:《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1)参见Catherine Nash,"Performativity in Practice:Some Recent Work in Cult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4:No.4,2000。
(32)参见Ann Swidler,"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No.2,1986。
(33)地基主,是住宅、房舍的守护灵,为台湾人信仰的神灵。台湾人常会在春节、清明节、中元节时,或者旧历每月初二、十六作牙时,以简单菜肴为祭品,加以祭拜。这是海南会馆的陈秘书长从台湾借鉴而来的祭祀习俗。另外,他还把祭祀皇天后土添加到仪式中来。但在海南的祭祀仪式中,大多并不包括祭祀地基主和皇天后土。
(34)参见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思想战线》2012第1期。
(35)有学者指出,“二次少数族裔”是指那些在移民输出国属于少数族裔的移民群体,而“一次少数族裔”(first-time minorities)指的是那些在移民输出国就属于多数族裔的移民群体。参见M.Bozorgmehr,"Internal Ethnicity:Iranians in Los Angel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1997,40。
(36)参见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37)参见William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Vol.1:No.1,1991。
(38)参见Arjun Appadurai,"Ethnoscapes: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ichard G.Fox,eds.,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Santa Fe,New Mexico: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1,pp.191-121。
(39)参见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
标签:移民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越南华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海南房地产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洛杉矶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田野调查论文; 难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