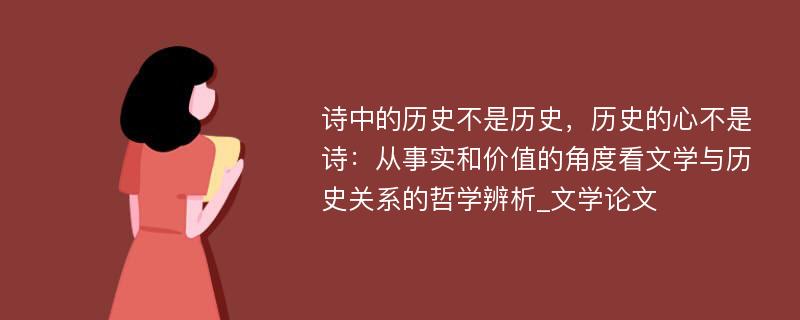
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系的哲学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文史论文,诗中论文,事实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3-09-01
引用格式:李伟.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607-614.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5-0607-08
在那个“给老师送礼”的年代,史学领域曾风传过一首讽刺陈寅恪等老辈史学家的打油诗,中云:“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援庵公。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1]4
这里所谓的“理论”专指马列主义,公、老等敬称是代拟的讽刺,表示用此称呼的人太落后,被此称呼的人则根本不配。更具历史意味的是,“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一语,竟夺了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三边互动”)的先声,成为1980年代以来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绝妙写照。以马列主义一统新时代之学术的大势和威力,终使自那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辗转到了“史料考证”这一不太需要“理论”时时莅临的纯粹领域,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味”日益淡减,几成了史学的道场。①
这正好应了畅行久矣的“跨学科研究”的景。“跨学科”本身值得提倡,关键在于“从哪里跨”、“跨到哪里”、“什么时候跨”以及“怎么跨”。康德曾告诫,在我们对本门学科固有之本性无知或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贸然“让各门科学互相跨越其界限时,这些科学并没有获得增进,而是变得面目全非了”[2]11。不论是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还是重又借陈寅恪所倡“诗文证史”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即史”的史学化理路,都把文史关系逼进了乱境之中,不免都有“面目已非”之虞。如此,对“史学理解的文学化”和“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这两种极端倾向,进行哲学反思并给它们以“正位”就显得尤有必要了。
诗中有史:陈寅恪的诗学实用观
逻辑上看,诗史间的关涉有二:诗中有史和史中有诗。“诗中有史”是个非常古老的诗学观念,除孔子“诗可以观”和杜甫“诗史”美称外,《本事诗》《唐诗纪事》和各种索引派算是最典型代表,后者亦可称为“以史解诗”。细按之,“诗中有史”和“以史解诗”尚有取径之别:前者由“诗”及“史”,目的在“史”,欲从“诗”中寻得“史”的素材;后者由“史”及“诗”,旨在从“史”的角度析解诗文。但二者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根据则相同:诗文和史作都来自特定的历史境遇,借歌德之言,它们都是“世界的奴隶”,要受“世界”(nature)的规约。“世界”成全了的,复又限制之,限制则又激起超越,诗与史就在这种限制和超越的张力中被创生。
孟棨《本事诗·序》交代作文动机:“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触事”二字实为序眼,正透露出其理论机栝所在。孟棨的方法论实属“以史解诗”一路。“触事”即是物感,“以史解诗”的理论根基正是中国古文论的“物感说”(事感说);《本事诗》和各种“红学索引派”——远如蔡元培、近如刘心武——则是这种理论不无精彩的批评实践。
由“诗中有史”,既可向后追溯其理论基础为“诗可以观”和“物感说”,又能向前延展于文学实践而得出“以史(事、古典、今典)解(证)诗”“诗具史笔”的欣赏和批评策略以及“以史入诗”的创作方法。“向前”所得之欣赏、批评和创作等启示都还以“诗”为中心展开,若以“史”为中心,就会得出陈寅恪所倡于诗可谓实用的结论即“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和“以诗证史”虽皆从“诗中有史”即“诗人写诗,必定和时代息息相关”[3]13这一认识论前提和“物感说”这一理论基础得来,但一个诗家立场、一个史家眼光,却也泾渭分明。
文学研究当是多元的,史学的与诗学的(艺术的)是其中重要的两种,正如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然就文学之为文学而言,艺术研究则是基本且根本的,史学的研究自可按其认定的理路深掘下去,但如把这种史学理路推广至极且认其为圭臬,致使文学研究见“史”不见“文”,那就名不副实了。陈寅恪晚年极尽“诗文证史”之能事,其意在“史”不在“诗”亦确然无疑,实与文学研究无涉,只重开“用诗”一途罢了。这种“实用”的初衷,使得陈寅恪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元白诗”这类纪实性较强的诗作(客观诗人),而无法对李白、李商隐、李贺这类诗人的诗作(主观诗人)也作如是挪用,是为“以诗证史”之所短。就元白诗而言,陈寅恪之“以史释诗”所关切的,主要还在诗之“什么”即内容和“为何”即动机上,而鲜及“如何”即“诗艺”“史才”[3]17-18也因之被他列为诗人必具之品质。②故他对《桃花源记》之“纪实”一面的研究,就需与“寓意”一途划清界限,这对文学研究而言实在只能说是“旁证”——此非谦词而乃实情。[4]188“诗文证史”的方法于文学止于“旁证”,陈氏对之亦早自知③,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方法穷尽了诗学的真谛。《元白诗证史》课程中,他开门便说:“此课属历史学范围,不多涉及文学,不过有时也要提到文学方面的内容。”[3]13《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的1944年8月,他曾致信陈槃:“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5]231晚年陈氏在《柳如是别传》中亦自谓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6]3,缘起。陈氏一生与文学有关的研究,究其实,探其衷,多是外部研究,这是无疑的,也是自认的;故于陈寅恪那里,并没有多少在其后继者那里才表现出来的“诗即史”及“诗学即史学”的极端倾向必须予以斥驳。
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文学研究的史学化理路,使他对叙事诗文和客观诗人尤为看重,终至偏爱④。如论元白“新乐府”,颇为推重其历陈时事以寓讽谏之旨,竟许以“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的极高评价,不惜与其曾谓“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相悖。此类推定过当的言论固不能掩他史家巨子的异彩,但亦不免招人非议,后世踵武而极端者更等而下之。然细按之,陈氏誉于少陵者,亦不在其艺术性方面,在与摩诘之诗相较后,他说:“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8]64陈氏笺诗的这一特点即“轻于艺而独深于意”⑤,萧公权1956年就已指斥:“陈君于洋洋十万言之长篇未尝一论技巧品质,而仅详考新乐府某篇依据某某史实……遂断然欲令元白夺少陵之席。如此评论文学,吾人实不敢阿好苟同矣。”[9]在《元白诗证史》的听课笔记中,随处可见陈氏对具体诗句“真、假、对、错”的史家断语[3]。
陈氏取史学理路以用诗,除上述理论和文本方面的依据外,尚有:(1)史学家重实证与求客观的学术圭臬,“雅不愿作主观的论述,而从严格的论证求答案”[10]7,增订版自序,弟子许世英曾概括乃师治学态度与方法为“科学的、逻辑的、公正的、缜密的、谨严的”[11]47;(2)诗人陈寅恪的创作体验和家传使然:义宁之诗,多“有为而发”,寄托遥深,至有“暗码系统”之说,推己及人,故总爱于诗中求纪实和本事;(3)诗史互证之法确曾在文史领域都取得过重大斩获,实践上的巨大成功无疑增加了推而广之的砝码;(4)“目盲”或许是陈氏晚年大倡“以诗证史”法门的重要外部因素,“引申诗韵中的‘微言大义’,实为一个双目失明学者无奈的选择”[12]521。
陈寅恪对古典诗文普遍采取了工具主义的态度,而如何把这种研究理路与文学本体研究对接并以之深化后者,则是他本人连同承继此法者所未尝措意的。更有甚者,这种史学理路一旦在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便会产生这样一种不良倾向,即对所谓原意或本意的迷恋甚至迷信。这种倾向之不良,于研究实效上看,所得之结论虽不乏卓见,然“多语焉不详,证焉不确……势难许为定论”[13]270;于理论上看,无视艺术创作的超越性、创造性及作品本身客观存在的多义性;于实践上看,不仅无益且有害于文学审美功能的现实发挥,并有可能禁锢后人对作品所可能做出的多元而独特的解读。王夫之曾就此讥讪道:
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姜斋诗话》卷二·三四条)
这则材料曾被汪荣祖引述于他与余英时就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所作的商榷文章中[10]257,以证余氏对“陈诗”释证“过于深曲”之弊。于此,我们依然可见当年陈寅恪与钱锺书两位学界巨擘就如何解诗所做的或明或暗的较劲。与钱氏一样,汪氏奉行中国古典诗的比兴传统和“诗家语”特性,强调诗之别于历史的本体特征;与陈氏一样,余氏关注的焦点亦在史证不在诗艺,其意在“用”不在“体”。事实证明,余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法,实属得间之举,故得许“作者知我”四字[14]32;据近年来披露史料看,余氏早年全靠作品“内证”所做的释读有着令人惊叹的准确性。⑥于诗文而言,陈寅恪与钱锺书、余英时与汪荣祖,双方立场、眼光迥乎不同,一体一用,故只可“互补”不可“对观”。
综之,诗与史毕竟有本性上的差异,即便它们可以“同构”,那也得以“异质”为根本前提。老杜的伟大、元白的流行,若非出之以“诗”的面目,断不可能。比兴意象、含蓄蕴藉的诗性思维是基础,直陈时事、述情切景的史家笔法是基于前者的深化或升华;前者成就的是诗与诗人,后者成就的则是它们的伟大。向“诗”中求“史”,探骊得珠时有之,缘木求鱼者更多。诗之能补史阙,并非“诗性思维”的本质功能,“诗史更重要的是一种心史。因此,所谓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学术方法,尽管有其沟通文史不同学科,因而显得独到和坚实之处;但是若不从本质意义上考虑到其间存在着富有审美敏感和创造性的心灵的介入,则有可能失其趣味,产生某种程度的刻舟求剑之弊。”[15]536、478
兹举广为学界传颂的陈寅恪关于老杜《哀江头》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之“北”的考释为例示之。陈氏断言“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故有“望城北”之语,“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究其实,陈氏此解若成立,则必具一事实前提:“黄昏胡骑尘满城”为老杜所亲历——而这实无可能。
据考,唐至德元年(756)六月底长安陷落,七月十二日太子于灵州(灵武)继大统,八月杜甫得悉,“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新唐书·杜甫传》),解至长安。因此,长安沦陷时杜甫并不在那里⑦,胡骑进城时“尘满城”的场景,老杜根本无缘得见。第二年春季某天,杜甫偷偷溜到昔日皇家贵族士绅游猎的曲江边,水边宫殿千门紧锁,今昔对比,百感交集,于是乎写下这首《哀江头》。据考,老杜此时所居之所,亦在曲江西面一带,距离并不算远,返程中不可能有什么“黄昏胡骑尘满城”;况且,“细柳新蒲……绿”实与“尘满城”无以共处一坊。更为紧要的是,老杜所游之曲江,在唐之长安城东南,且是最南,即便他目睹了“尘满城”,那他也是自城南往城西走,何来“欲往城南”之说?“欲往城西”才对。老杜此时尚能自由走动,看来并未为贼所扣,即便他按规定还必须在某一时刻回到城中被拘之所,那也同样是从城南往城北,本就在“望城北”,何需曲意如此。业有十年居于长安的杜甫想来也不会由曲江迷路至城中而后“欲往城南”。故而,“黄昏胡骑尘满城”只是诗人想象中的慌乱不知所措的城中平民奔逃的场景,如同杜甫站在高空,看着那些逃难的市民,急忙忙向南面奔走,突然又停下来,回望北方,显然是转了向,算是纪实之笔,谈不上“眷恋迟回不忘君国”。
史中有诗:钱锺书的文史异质论
如果说“诗中有史”是创作实践先天决定了的,那么“史中有诗”则来自对“诗”与“史”共同特征的分析,即双方的主体、对象和媒介皆相通,这是确乎存在的客观事实,所透露的正是“诗”之刻意追求和“史”之竭力避免的“主体性”。
史家天生与俱的主体性,使得历史著述先天具有了主观性、情感性和因“前理解”必生的倾向性;加之人命定的有限性又逼使其在撰史叙事时,不得不运用从学科本性和追求上必须尽力摆脱的想象和推理能力,通过“虚构”“代拟”去填补过去留下的大量空白和断裂。这种想象、虚构、代言和推理的过程,在本性上,同文学艺术创作中参与其中的主体心意机能并无根本不同。因此,钱锺书由此提出与陈寅恪“诗史互证”相对的“史蕴诗心”就显得那么地顺理成章,同样显出大师的卓识。陈寅恪由此以诗证史,甚至可以以诗补史,自有其理论依据和研究成效;钱锺书当然也可以由此大谈“史蕴诗心”,甚至“古史即诗”[16]104、103,从文学角度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揣想生象”“想当然耳”,称其史作“堪入小说、院本”[16]106,“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7]273。然而,理论上的清晰明澈并没有带来实践上的相互理解。其实,陈寅恪对此也早有理论上的自觉(1931),认为史家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可以真了解”,但亦深知“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8]279稍可申说的是,陈氏晚年作史,大都用此法而少有此“穿凿附会”,这是他毕生寝馈古籍以至“旧学遂密”且“新知深沉”的结果,可这是承继者几无可能获致的。这样看来,“穿凿附会”在承续者那里不时显露就显得事有必然了。更何况,即便陈寅恪也不能完全摆脱“穿凿附会”之嫌,真所谓“先生之学说有时而可商”。
钱锺书之有“史蕴诗心”的卓识约在1948年(虽然详解多在其后的“修订”中),20多年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中,建构了有分析哲学性质的新历史主义即“历史叙述主义”,旨在揭示一切史学著述中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并断言它是“诗性的”(poetic),尤其是“语言性的”(linguistic)[18]序言,1。这似乎是一个西方学者冥冥中在阐释一个中国学者早先的理论慧见。怀特对这一理论创见甚为自负,然其于学术研究之实际价值,多在其被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之后。真正的史学界并未对之抱以兴趣,在他们看来,怀特顶多算是用一大套耸人听闻的言词揭示了一个史学界人人熟知的常识而已[19]140-141。严格说来,这一揭示逻辑上并不严密,其最大失误就在于把一切历史著述划归为“文本”和“叙事”之后,便武断地置“文学叙事”于“历史”之上。其实,“叙事”不止“文学叙事”一种,尚有他类,比如“历史叙事”。相对于“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并不拥有怀特赋予它的那种优先性和典范性。正如柯林武德特意解释的那样:“叙事一词并非指的是虚构性叙事,而是指真实的叙事;或者不如说,不是指一种倾向成为虚构的叙事,而是指意在成为真实的叙事。”[20]338怀特自己在1966年的《历史的重负》中也坦承“科学叙述”和“艺术叙述”的区别[21]。
看来,怀特所揭示的仅仅是历史著述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他蓄意抛弃的则是史学的价值理想,连同史学作为学科存在的根据。“元史学”之于文学研究可谓“喜客”,之于史学则是“瘟神”,照之而行则有“绝后”之虞,史学界对之冷眼以待,可谓大大的明智之举。正如英国史名家斯东(L.Stone)指出的,我们至今还未读到一本重要的史学作品,是彻底根据后现代史学观念并使用后现代语言和词汇写出的历史著述[22],这个判断至今依然有效[23]29、47-48、154-155。
在对钱锺书诗史关系论的勾稽中,学界多顺路而下,得意而去,很少注意到钱氏所论皆置于一个明确的前提下:“古代史与诗混”。对这个前提,钱氏解释说:“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藉以寓己。”[16]102-103他虽并未明言,在史学意识觉醒和史学观念确立之后,这种“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的情形还会不会出现以及还能否如此看待,但他就“诗”所下论语固可适用于“史”:“必有诗,方可究诗之本质;诗且未有,性德无丽,何来本质。”[16]101钱氏所论史、诗关系,也从未直称“史即诗”,而都是“古史即诗”。钱氏此论所最为倚重者即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所谓“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周秦之际,子即集也”之论。据“古史”这一限定语,显然暗指此后的历史决不能再如此视之,否则,“古史”二字便无着落了。深而言之,与怀特郑重其事完全不同,钱锺书对“史蕴诗心”等事实的揭示,实为矫不念诗史本体差异的“以诗为史”之枉而过正之举。
再者,古史中虽有“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者,但若从效果史角度看,所述之事的真假,实在无关紧要——即使它们全为“虚构”然亦决非全是“无稽之谈”,而常常是远古历史现实的记忆积淀;紧要的是,记述之人连带时人和后人均对之“信以为真”,所述之事实际上既已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并具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价值,这是另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信史”,史学的价值理想依然得以护卫。这就是为什么从维柯、克罗齐至柯林武德,皆强调对历史材料(一切历史遗留物和历史著述)首先追问的不是“真假”而是其“意味着什么”的根本缘故。[20]256、271陈寅恪曾力排众议而把这种睿见概括为“史论即史料”、“史论即政论”[8]280-281。
对诗与史的本体差异,钱锺书有着非常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宋诗选注·序》云:诗歌表现时代背景和生活现实有不同方式,有一种可称为印证式,即“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但是,“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24]3-4
正如我们不能用“空谈史释”来指责陈寅恪式的“史料考据”,面对钱锺书,同样也不能斥以“窠臼”而了之。“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均不可偏废。面对“现实”这个先天的立足点,“诗”与“史”的心境完全不同:“诗”之于“现实”,既是其“奴隶”又必须成为它的“主宰”,“诗”之本性和追求正在后者,而前者正是其虽无法完全脱离但却竭力要超越的;“现实”之于“史”,则完全是其鹄的和依归,意在无限逼近或力图还原到后者,即中西史学共举之“如实直书”,这种心境几乎成了史家必备的德性,谓为“史德”。就“主体性”而言,它正是诗的生命和祈向,“诗”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表情达意,即使这种情感是最普遍的,那也得表之以不同于前人的个性化极强的方法、手段和艺境。“主体性”则是“史”亟须尽力摆脱的,艰难地在主体性中探寻客观性,这是史家的律令,一如独创性是诗家之圭臬。文史如上的本体差异,就是哲学意义上“事实”与“价值”的分野。
事实与价值:文史的哲学分野
如果说“主体性”是“诗”无法回避亦无须回避且极力追求的因素,同样,“现实性”则是“史”无法回避亦无须回避且极力追求的因素;那么,“现实性”则是“诗”事实上无法避免而本性上欲竭力超越的因素,同样,“主体性”也是“史”事实上无法避免而本性上又须竭力摆脱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事实上”和“本性上”的差异对应于哲学所谓“事实”与“价值”的著名区分——我把这种区分名为“二向度思维”[24],那就会对问题有更深层的理解。
“现实性”之于“诗”“主体性”之于“史”皆是“事实”层面的问题;同样,“主体性”之于“诗”“现实性”之于“史”则都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正如我们不能用“事实”否定“价值”一样,我们亦不能因“诗”之有“现实性”而无视甚至否定其“创造性”与“超越性”、因“史”之“主体性”而遗弃甚至拒绝承认它对“真实性”与“客观性”正当且不懈的追求。这正如人的肉体和精神、物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人之有肉体、物性这些“事实性”的现实而否认人之为人的精神需要和人性诉求,更不能因精神和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时缺失而否弃我们对它的追求和向往。诗之为诗、史之为史、人之为人,均不在其必定立于其上的“事实”一端,而恰恰在于它们超越于“事实”因素之上的价值和理想。实践中之不可能决不是我们放弃追求的理由。这层意思本不难领会,正如史家余英时所说:
事实上,即使没有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我们也早就知道历史世界一去不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学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史学家诚然不可能重建客观的历史世界,但理论上的不可能并不能阻止他(她)们在实践中去作重建的尝试。
只是此种尝试须以如下这个清醒认识为前提:
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26]5-6,自序二
真正的历史哲学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柯林武德曾以“伟大的兰克”的名言“如实直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当历史学家说“我将只会如实直书”时,“他只是许下了一个他永远也无法兑现的诺言”,或者“一种无法实现的观念”、“历史被看作是有关过去事实的知识,它是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明了,“按照事实实际发生的情况叙述事实”是根本“无法做到的”,那历史学家该何去何从呢?的确,此前人们是可以相信有真正的“如实直书”,但现在,历史学家要么放弃自己的工作,就像海登·怀特后来宣称的那样,要么坚守自己的工作,但必须解除这里提到的这个二难选择。它其实涉及的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事实”(“是”)与“价值”(“应当”)的区分问题。柯林武德说:“如果你说由于那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它事实上无法像一种理想那样运转,那么,你就消除了进步被称为进步所依据的唯一标准。”[20]385-388因此,“如实直书”作为史学的“乌托邦”并非无用,而是史学取得进展的必要前提和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有意思的是,若以“应当”之意言,历史最求“客观”,文学最要“独创”;然于“事实”一面,历史著述恰恰最多分歧故被不断重写,文学往往辗转相袭而每每最少独创。由此可见,“客观”与“独创”两端,嘎嘎呼其难哉!然而,史学最少认同并不代表可以放弃应有之追求,文学独创维艰也不意味着从此就该批量生产。顺便说一句,以事实证否价值的恶习正是“起源决定本质”的流毒所致。
这种在“事实”和“价值”间保持应有的张力和清醒而执著的意识,也体现在柯林武德对“历史倾向性”的论析中。他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有倾向性的历史,而且,如果历史没有倾向性,没有人会去写历史”,但是,“历史根深蒂固的那种倾向性,无论它出现在哪里,都是一种瑕疵。屈从于它就意味着不再做历史学家而是要做律师了”;历史学家既不是某个人的律师,也不是某个时代、民族、阶级的律师,历史学家应当竭力克服这种倾向性,“竭力将自己带进一种不偏不倚、不悲不喜而只为真理的心灵境界。”[20]390当然,在实际的工作中,历史学家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尤其“当我们看到像塔西佗、李维、吉本和蒙森这样的人都没有完全做到时,我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这些都是“事实”,柯林武德无意要否定它们。“事实上做不到”既非“可以不做”的理由,也不是“不需要做”的口实,更不是“随心所欲”的依据。任何伟大的历史著述都有倾向性,但也决不止于倾向性,真正支撑伟大史学家的,不是历史固有的“倾向性”,而是“只为真理的心灵境界”和“对历史的真正热爱”,我们要做“清醒的理想者”和“不懈的追求者”。“一种由仇恨激发的历史”,“一种由阴谋策动的历史”,都是“偏执狂”的历史,都是“历史中的低级罪犯”[20]390-391,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史学堕落。
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已经成了一个绰号,专用来指那些好作空想的思想家头脑中的想法……然而,我们最好还是竭力去弄懂它,亲自搞清它的真实含义,而不要借口说它是不可实现的将其视为无用,弃若敝屣,这种借口是卑下而极有害的……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有害最无价值的事情莫过于庸俗地诉诸所谓(与理想)相反的经验了……即使这种情况(指理想)永远不会实现,然而这一理念毕竟是完全正确的,它把这一极限提出来作为蓝本,以便按照这一蓝本使人类……日益接近于可能的最大完善性。”[27]94,[2]271-272在《人论》(1944)中,卡西尔对之亦有清醒的意识:“一个乌托邦,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nowhere)。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了考验并且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它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27]95、96。照康德哲学的术语说,“如实直书”之于史学著述只是一个“范导性”理念或原理,并不具有现实的“建构性”功能;“倾向性”之于史学只是“事实”和“因素”,追求“如实真书”才是其价值理想。总之,文史关系论,必须以文、史本体上差异为前提,正所谓“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这个本体的不同,伏根于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所追求的价值理想,不管是“审美”、“向善”还是“求真”,均对应于文化主体多样的生命需求。正如卡西尔所言,包括文学和历史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都并非仅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诸器官(organs)”,通过它们或以它们为媒介,我们才能感受和体验种种生活世界,“尽管这些形式在建构精神实在的过程中共同地有机地发挥着作用,但每一个器官都各有其独特的功能”[28]36。因而,不能用“事实”或“是”去否定“价值”或“应当”:既不能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就把文学的一切都归之于现实,无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也不能因历史固有的主体性或倾向性,就把历史归结为诗意的遐想,无视史乘和史学家应有的职责和追求,甚至去否认文学与历史的本性差异及功能分工。不惟如此,还得用后者来提升前者,引领前者,这万万不能被遗弃。因此,文史研究中,作为“诗中有史”和“史中有诗”极端化表现的“诗即史”和“史即诗”,于今都是本末倒置、逐末忘本的误人之说。这里所做的只是正本清源的“理论去污”工作。
注释:
①比如罗宗强就认为:“(傅)璇琮先生以其精深与博通从事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承接文史不分的传统。”(罗宗强《〈唐诗论学丛稿〉序》,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5页)罗氏此文,对1980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策略有清醒的学术反思,意义重大。而傅氏之所以选择“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策略,实与他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认知密不可分(参阅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第75-83页)。这一点亦在周勋初的一项研究报告(1991)中得到证实:“前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重观点轻材料”,破坏和阻碍了中国文史不分的传统学风;“近十年来”(1976-1990),“学界力反蹈空之弊,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治学方法重新得到确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得了继承和发扬”(周勋初《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这种古典文学研究的“陈寅恪范式”至今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参阅陈文忠《三千年文学史,百年人生情怀咏叹史——关于文学生命本质的新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00-702页。
②当然,关于诗之“什么”“为何”与“如何”均有所谓的“史”。前二者之史,是陈氏关注的焦点,“如何”则涉及“诗艺”之史,即诗艺的历史渊源和承继关系,自有其内在理路和历史脉络,但与一般所谓的社会史、文化史相去较远。这是钱锺书甚为关切也用力最勤的领域。由此亦可见出陈、钱二位对于诗的不同兴趣和学术取向。
③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陈寅恪曾“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证诗,随之就说:“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参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9年,第134页。
④据俞大维回忆,陈氏“最推崇白香山”(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页)。
⑤这在他评价被他分别誉为“六朝长篇骈文第一”和“赵宋四六文第一”的庾信(子山)《哀江南赋》和汪藻(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时表现得最为显明:“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9年,第73页)。
⑥参阅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东方早报》2009年5月24日第B08版)、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E23版)和《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2010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B14版)、刘广定《陈寅恪先生一九四九年的选择》(《传记文学》[台湾],2012年3月,第100卷第3期,第99-108页)和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台湾],2012年3月,第100卷第3期,第109-115页)等文。
⑦杜甫是年四月赴奉先,后携家至白水,六月携家避乱于鄜州羌村,八月闻肃宗即位于灵武,便只身赴之。参阅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