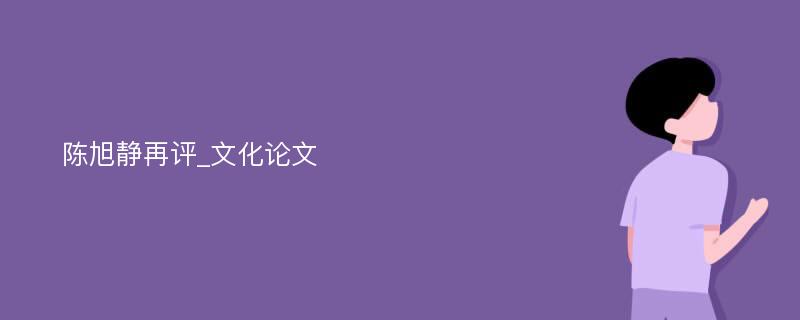
重评陈序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评陈序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我们的理论宣传里,总是有着这样一种逻辑:凡是爱国的,就必定是传统文化的护持者。所以年复一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均不外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赞颂。相应的,那些钦羡西方文化的人,总是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被当作民族文化的不肖子孙。
然而我们在陈序经身上,却看不到这样的逻辑。他是全盘西化论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甚至还可以说,他对民族的爱,比起那些口喊爱国实则为民族蠹虫的人来,不知要真诚多少倍。
陈序经出身于一个南洋华侨家庭。其父陈继美当过船员,经营过橡胶园,是一个靠劳动致富同时又对祖国有着万般温情的厚道人。1903年,陈序经出生于祖籍海南文昌县,10岁随父侨居新加坡,就读于当地的育英小学和华侨中学。由于不愿接受殖民教育,16岁回国,就读于广州岭南中学。1922学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一年后由于不愿信仰基督教而转学复旦大学,由生物学改读社会科学。1925年大学毕业,并于同年八月留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秋回国,执教于岭南大学。1929年夏又远赴欧洲,入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1931年回国,时年28岁。凭其学历和所学专业,陈序经完全有可能跻身政界和实业界。然而他遵照父亲的遗愿,一不做官,二不经商,而是为祖国的振兴献身教育事业。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终年64岁。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陈序经原不过是一名学者,远没有西化论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那样风光和体面。如果说做官,顶多也只是当过大学校长,何况这种头衔还算不得是个官衔。一个纯粹的学者关心民族的命运,是很少私心杂念的,其所思所想完全是出于学理,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或者说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一份真挚的情感。
陈序经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并在那里生活了六年时间。这是他的青少年时代,也是逐渐懂事的时代。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他原本是十分反感的。中学时代因厌恶西方人的殖民教育而离开南洋,大学时代又因不愿信仰基督教而转学,均说明在他的心底里,祖国和民族这样的概念有着很重的分量。但是,南洋生活的六年,又使他亲身经历了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受到的歧视和鄙辱,并从中悟到这样一层道理:民族之落后,根本原因乃是文化的落后。当时的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即西方殖民者、华工和当地土人。三者的关系是:西方人为统治者,高高在上;华工备受西方人的歧视,但地位又高于土人;土人的生活最为悲惨,不仅受西方人的剥夺,而且客观上还受到华工的排斥。因为西方人宁愿雇佣华工,而不愿给当地土人以谋生的机会。陈序经正是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等级及其同文化的关系,才深感文化问题之重要。
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大都有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为了不被西方人看不起,格外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和宣扬,并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同样为了不被西方人看不起,他们希望民族富强起来,因而又很想向西方人学习,用西方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陈序经的青年时代就陷入这样的矛盾心理。但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明智的办法只能是二者择其一。
陈序经摆脱此种矛盾心理,大概得益于留学美国。他在美国的三年,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经济繁荣时期。这块新大陆,决非新加坡可以比拟。繁华的城市,发达的交通,先进的科技,自由的学术,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无不使年轻的陈序经大开眼界,亦使他真正地认识到中国之前途就在于全面向西方人学习,即全盘西化。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也才可能彻底解除被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陈序经写道:
我以为仲甫先生既没有积极的提倡个人主义,适之先生的介绍,也不外是一方面和断片的介绍。然这样的轻轻一试,已有这种成绩,要是中国人能尽力从这条路上做工夫,则将来的效益,当无限量。可惜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已深入脑髓,结果是轻轻的一针注射的个人主义,敌不住什么堂皇的思想统一的注射,结果我们仍是照旧的只会游手好闲的享受西洋的汽车和洋楼,没有自己有所振作的决心。(《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凡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在《东西文化观》一书中,陈序经又写道:
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于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意义,却又不外是变印度菲列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的祖宗在历史上所做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为他日之重视我们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祖宗与其文化。(第196页)
这里所表述的,是陈序经提倡全盘西化的由衷所在。读了这两段文字,我们实在难以在全盘西化与崇洋媚外之间划上等号,难以对陈序经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有半点怀疑。
二
鸦片战争之后,有感于民族危难而主张接受西方文化,并不始于陈序经。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有过这样的文化主张。特别是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更是推波逐浪,将这一文化主张推到更高更深的层次。然而,这些思想家的西化主张,都未能做到全面和彻底,不是带有旧文化的考虑,就是停留于文化的表层,作枝枝叶叶的工作。尽管也有十分激进的(如钱玄同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厕,有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拼音文字),但其主张大多只是激愤之词,很少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思考。陈序经则不同,他留学西洋,做过系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能够从文化哲学的高度考察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并将其放在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来思考。而这些,都是他的思想先贤们所不及的。
陈序经全盘西化主张的系统性,首先得自于他对“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一切文化皆出于人类的创造。但是,文化一经创造,就能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也可以说,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以创造和模仿两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这两种形式,得难说孰轻孰重。因为没有创造行为,也就没有文化之可言;同样,如果没有模仿,非但文化传承与传播不可能,就连文化创造的意义也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就整个人类而言,文化创造毕竟是极少数人的事情,绝大多数人不过只是文化的模仿者和受益者。用陈序经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自生长到老死,差不多处处都是在文化里过他们的日子和生活。举凡一切衣食住动作等,都受了文化的影响。人类自生长到老死,对于这些动作的方法、模型或样式,用不着件件事事由自己去发明,或创造,以便自己的应用;因为这些日常需要,差不多通通已有了准备,有了方法、模样。人类自己所需要者,不外是去学习已有的方法、模样。”(第65页)
陈序经所说的文化“模仿”,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传播方式。为了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借用了当时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将文化研究对象之单位称为“文化圈围”。按照他的理解,“文化圈围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她也可以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她像政治学上的政府,经济学上的财产,生物学上的生命,天文学上的天体。”(第68页)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形态学说是德国学者施宾格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出来的。施氏认为,没有所谓的“世界历史”,有的只是各种自成体系自成生命的“文化”。各个文化之间很难彼此沟通,因而也是不可能相互交流的。显然,如果按照此种文化理论,中国人是不可能向西方人学习的。陈序经也正是看到了其欠缺所在,因而在借用此种文化理论的同时,又对文化作了历时性的理解。这就是他的“文化的层累”说。
所谓“文化的层累”,即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或者说是人类为着自身的利益将文化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推进。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陈序经援引西方学者多种文化分期理论,以说明人类历史无非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文化本身不断优化的过程。在他看来,文化既然是层累而成,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那么也就有优劣高下之分和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进一步说,先进与落后之存在,也就是文化传播的根据,亦可充分说明文化的模仿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陈序经的“文化圈围”和“文化的层累”两种说法,如果简约地看,实则文化的时间问题。前者谈的是文化的空间关系,后者谈的是文化的时间关系。他之所以将二者同时放在他的文化理论中,就在于前者可以帮助他说明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后者可以帮助他说明文化传播的必然性。正因为这样,他的“文化圈围”并非像施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彼此之间完全是自足的封闭的,没有模仿与被模仿的可能。他认为,文化于时空两方面是“一致与和谐”的。作为空间意义上的“文化圈围”,同时也是时间性的。因为它不是被一硬壳所包裹,而是逐渐向外扩散的,由点到面,由小面积到大面积。而这,既是文化空间的扩大,又是文化的时间性流延。反过来说,作为时间意义上的“文化的层累”,同时也是空间性的。因为,文化的流延决非仅限于其原被创造的地方,它必然地要向外扩散,从而使时间性与空间性达到“一致与和谐”。
陈序经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且不曾借用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其文化主张的理论根据。但读其文字窥其思想,则不难发现,他的全盘西化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非相距太远。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人类历史同样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重意义上的进步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交往不多,各民族文化可以自行发展,自成形貌,但世界历史一经联为一体,便势必打破各民族原有的封闭格局并改变其原有的文明体系和生活方式。而且在他看来,文化是有高下之分的。就近代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着人类文化创造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它必然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三
社会发展即文化的传承,后人的创造必赖于前人的已有成果,因之,任何为了开创未来而全然否定传统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正因为这样,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提出来后,马上招来学者们的非议,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
不妨看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
大而言之,陈序经基本上是照着胡适的调子看中国文化的,即中国人“百事不如人”。不同的只是他不是空泛地议论,而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比较。在他看来,(1)中国人虽然也强调民以食为天,重视饮食,但不如西方人的卫生,而且也不充足。(2)中国看重穿,但布料和制作工艺却比不上西方人的考究,就连丝绸也没西方人的精美。(3)中国人的住宅简陋,与西方人的居住条件更是不可比拟。(4)中国人日常的娱乐活动,只会打麻将,而西方人却要丰富很多,像跳舞、体育乃至日常的公园散步之类的活动,中国人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5)中国的交通至今仍是以骡车、牛车、马车为主,甚至还有最没人道的人力车,而人家西方人早就有了火车、汽车、电车。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公路和铁路,但同西方人相比,也是相当落后的。(6)中国政治至今还是既混乱,又黑暗,比起印度人来也相差一大截,更不用说同西方世界相比了。(7)中国以人治代法治,有法等于无法,远不如西方人那样有健全的法制。(8)中国素来号称道德第一,其实都是些吃人的道德,“公共道德,固不如人,个人私德,家庭美德,也不如人”。(9)中国人无思辨传统,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到清代人顾黄戴王,思想见解大多“乱七八糟”,无体系可言。(10)中国文学质和量两方面都不如西方文学。中国人的文学作品大多诘屈聱牙,言不达意,是一种死的文学,而不是活的文学。(11)中国科学更无成就可言,“比起欧美各国,简直是惭愧得很。”(12)中国教育之落后,恰与西方人的教育成反比,人家百分之九十几是受过教育的,而我们则是百分之八十几是没有受过教育的。(13)中国的工业和矿业才刚刚起步,而西方人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14)中国人自以为很会经商,“但一遇着西洋人,就要相形见绌”。(15)中国的医学、美术、音乐以至文字,如果拿来同西方人的相比,也是“相形而见绌”。总之,在陈序经看来,“过去和今日的中国还是事事太落后,样样不如人”。(第194页)陈序经的上述看法,不能不说过于偏激了些,而且有些看法亦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比如中国的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文字,中西双方就很难说孰优孰劣。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仅这一点就可充分说明它的文化自有可取之处。如果一切都是糟糕的,又怎能汇成如此宽阔的文化长河?然而另一个事实是,中西两方的文化一经接触,中国的一方又确实处于劣势,被动挨打就是此种劣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点,又正是拥护西方文化的学者们立论之根据。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数落和贬
抑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妄言妄语,很大程度上是有事实依据的。
但是,就我们今天看来,西化论者对中国文化之态度,不管怎么说,都有些过分,给人的印象是公允不足而偏激有余。问题是,西化论者并非对中国文化没有了解,他们为何会失去公允之心,对传统文化几乎采取一切骂倒的做法呢?对此,胡适曾有一段解释: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
胡适的这段话,可说是道出了西化论者的苦衷。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出于某种私心,对国家和民族,谁人没有拳拳赤子之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血脉里流淌着中华文化之血,对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何能没有几分感情,几分眷恋!其所以批判传统,甚或说出不中听的激愤之词,也只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前景,所体现的是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其品格或许比那些一味为传统日夜唱着颂歌的人更为高尚,其内心也更为痛苦。他们不是不知道传统里藏有宝物,有可发扬光大的基础,但同时又要违心地批判传统,把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此种违心本身就是痛苦的,何况还要招来骂名。这样的事情,老于世故的“聪明人”是不会做的,只有像胡适、陈序经这种为了民族利益而不计个人毁誉的人才可能为之。
不过,陈序经并没有像胡适那样,对自己的全盘西化主张作过有关“矫枉过正”的说明,更没有像鲁迅那样,作过类似于“开窗户”和“拆屋顶”的比喻,而是从理论上论证他自己否定传统之必要。在他看来,第一,我们承认样样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缺点和错误,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有改正缺点和避免错误的努力,民族也才会有进步之可言。第二,各民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差别,落后文化受到批判与否定,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不正是在于夷狄事事不如华夏吗?今日世界,西方文明独领风骚,我们同其关系,不也正像古代中国夷狄同华夏之关系?既然古代中国人可以有夷夏之辨的传统,我们今日又为何不可以将自己摆在夷狄的地位,从而丢掉原有的文化中心主义优越感呢?第三,中国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文化命脉,但这并不能说它就能应用于现代社会,为解决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有所贡献。相反,对传统的依赖性越大,对未来的创造力就愈小。第四,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检讨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开放的心胸迎接西方文化,有朝一日,国家和民族一旦灭亡,何以可能再言保存民族文化?即是说,如果对传统文化有一份真正的爱心,对民族和国家有一份真正的责任感,就应该勇于面对传统文化之短处,并在对其批判的前提下,为民族创造出新的文化。
陈序经的上述分析,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另需指出的是,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观点,并从理论上为之辩解,但另一方面,他有时又承认传统文化里也有值得称赞的东西。请看他自己所说一段话:“一种文化之能够继续存在到四千余年之久,未必就没有半点的好处。……从文化的各方面来比较,中国的确是不及西洋,所以的确是没有半点的好处。假使她有了半点或不少的好处,这不过是历史上的好处,而非现在的优点。”(第200页)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陈序经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即正如前文所说的,西化论者既要批判传统,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传统的优秀所在。所以他们的理论表述也就难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陈序经是这样,胡适也是这样。
四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各种文化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传统派、西化派和折衷派。三派中以折衷派人数最多,亦最为国人所认同。因为该派主张,既采纳西方文化,又不丢弃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最经典的表述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使今日,此种文化主张依然还很有市场。所谓“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和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均可看作张之洞的观点的延伸。
陈序经是坚决反对折衷派的文化主张的。在他看来,首先,折衷派对“西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西学不仅仅局限于“西政”和“西艺”,除了学校、医院、交通、航海、工商、科学、法律、武备等器物和政制层面的东西之外,西方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即人生观和社会观,而折衷派“不但不注意,简直不知道其存在”。其次,折衷派对“中学”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在他们眼里,“中学”不外是四书五经,圣贤格训,加之历代读书人所不断增益与精练的内圣外王之学,即如何修身如何平天下,却看不到“中学”尚有许多方面是“内圣外王”四字所不能囊括的。复次,陈序经认为折衷派没有看到学问有新旧之分,所强调的只是中外之分和东西之分。实际上,“学固有时间上差异,而没有空间的不同”,因之不能以民族性或国界来强调其体用之关系。再次,陈序经认为,文化之体和用不能分割开来看,不是你想怎么采纳就可以怎么采纳的。下面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十分中肯:
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依其体。中学有中学的体,西学有西学的体。中学有中学之用,西学也有西学之用。唯有中学的体,才生出中学的用,唯有西学体,才有西学之用。反过来说,就是中学的用,是完全建立在中学的体上。西学的用,完全建立在西学的体上。西学的用之所以异于中学的用,是因为西学的体异于中学的体。比方:听是用,耳是体;看是用,目是体;耳的用所以异于目的用,就是因为耳的体异于目的体;今因为了耳聋,而欲以目的视的功用去配到耳的体上,怎能配得?同样,既承认了中西学的不同处,则中西学的体用,也必有不同之处;今欲存中学之体,而取西学之用;去中学之用,而舍西学之体,其愚昧之甚,和欲以目之用,而配于耳之体,相去几何?其实体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要是中学只有了体,而没有用,那么中学已成了废的。至多只能把它来作古董来玩玩,至多只能当作为学而研究的学吧。(第95页)
这段文字主要是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除此之外,陈序经还对本世纪各种折衷派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如梁启超认为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号召国人说:“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陈序经认为,“文化”二字本身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二者混然一体,密不可分。“文化的物质方面,不外是精神方面的表现,又必赖物质以为工具”。所以一切的物质文化的进步,必赖于精神文化的进步;或者反过来说,一种文化,它的物质方面如何,是由它的精神方面决定的。近代欧洲日新月异,就在于它拥有使其日新月异的精神文明;中国物质文明落后,也只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是有问题的,确切说是其落后的根源。
又如杜亚泉、李大钊以及来华宣传东方文化主义的泰戈尔把西方文化看作“动的文化”,把东方文化看作“静的文化”,认为文化的过静易被自然征服,过动则又易于在精神上受无限的刺激和痛苦;最好的办法是,以西方动文化调和东方静的文化,同时以东方静的文化弥补西方动的文化。陈序经认为,世界上没有静的文化,一切文化都是动的。“动”是文化的特性,亦是其存在方式。正由于文化是“动”的,所以才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中国人所要做的,并不是以什么“静的文化”去弥补西方人的不足,而是要迅速地“动”起来,去追赶西方文化,摆脱落后的现状。
再如许仕廉、孙本文认为,对中西文化的取舍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具体作法是:“(一)分析吾国固有的文化,而了解其种种特性;(二)了解我国固有文化的特长,及其缺陷,以为改造文化的张本;(三)根据现代世界趋势,对于这种种特性的价值,加以严密的评估。”陈序经认为,此种所谓“科学的分析方法”,其对文化问题“没有充分的了解”。文化是整全性的,并非你可以挑三拣四的,“它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第104页)
再如三十年代成立的亚洲文化协会的文化观。该派人士认为,西方文化为物的文化,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为人的文化,王道的文化,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可取道路应该是,“以西洋的霸道来救中国之弱,同时保存中国之王道以济西洋霸道之穷。”陈序经认为,用王道和霸道作为东西文化的差异,本身就是不妥的。西方文化不只是霸道的文化,而东方的文化也不只是王道的文化。如其不然,我们既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黄帝征蚩尤、春秋王霸、秦皇汉武等历史现象,也不能解释西方世界诸多爱好和平的主张和行动,如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威尔逊的十四条款,国际联盟等等。
在陈序经看来,折衷派不但认识上错误,而且还会生出“最大的危险”,甚至比复古派的主张更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请看他下面这段话:
是真的复古、复孔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是“食无求饮,居无求安”,衣不求适,也许会减少半点西洋货物经济的压迫,而免权利之外溢。然而折衷派的人,则不然,他们一方面享受了西洋的物质文化以饱私欲,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旧道德思想以欺骗人民。他们购买枪炮就说是物质的西化,他们杀戳无辜,就说是攻乎异端。你叫他们去留学,他们就只学了人家的跳舞,你叫他们要随着中国习俗,他们就沉醉于麻将。这样的东西合璧,简直是坏上加坏了。我们放开眼睛一看,今日所谓乘汽车,住高楼,食西菜的卫道先生,以至瞒洋人欺同胞的中国人,无一不是挂起折衷办法之名,而行其因利乘便营私自饱之实。骨子里仍无半点西化,这是时代的投机者,这是文化过渡时代里的蠹虫,这是人类的公敌。(第201页)
现代中国文化的悲剧就在于,折衷派的主张是最具欺骗性,最能够在广大国民乃至很在一部分糊涂的知识分子中间得到认同。同时,此种主张又最容易被少数人所利用,作为他们中饱私囊的工具。一方面,他们主张向西方人学些皮毛的东西,并在其学习(用今日的话说叫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尽情地享受西方文明所带给他们的奢侈生活,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以图自己的特权地位不至于受到威胁,他们又口口声声鼓吹传统文化之优秀,用文化相对主义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辩护。实际上,传统文化早已被他们所践踏,传统美德早已被他们丢弃得干干净净。他们所爱的只是自己以及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现代物质文明,而不是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更不是传统的文化。如果要在孔孟之道与高级轿车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只不过,当他们已经选择了后者或者说一头钻进小汽车之后,才探出头来对老百姓说,要如何尊重孔孟尊重传统。
五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在今日读来,犹如昨日说过一般。这里的原因是,这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定向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即是说,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我们究竟应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作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国人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虽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但其深入的程度远不如陈序经等人发表讨论的三十年代。正因为问题未能解决,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仍然接着这个话题来讨论。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在现代社会,一个半世纪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照道理,这个话题本在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初就应该结束,然而由于民族历史的曲折与多难,导致二十一世纪的前夜,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这不能不说是民族之不幸,是中国学术之不幸。
问题是,这样一个算不得深奥且直接关系着民族能否正常发展的话题,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竟然打了一个多世纪的笔墨官司?这里面本身就是有文章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乃至三十年代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难成定断,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之而反映的西方文明弊端一时模糊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线,使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于断定西方文明的前景的话,那么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几十年来,西方人并没有靠东方文明的超拔,而是凭着其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断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一个新的起点走向另一个新的起点。相反,固执于传统文化的东方民族,却没有凭着自己的传统资源发展起来。更可注意的是,作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由于与其他的东方民族不是走在一条道上,而是敞开心胸学习西方,竟能够日新月异,发展迅猛。回忆这百余年的东方历史,想想我们今日的社会状况,难道我们还应该将西化论者摆在批判对象的位置?难道不应该给陈序经等人一个恰当的评价?
诚然,世纪末的今天,相对于本世纪的上半期,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主领今日世界文化大潮的虽然仍是西方文化,但又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经过长时期的接触与交流,各民族文化早已联为一体。也就是说,代表今天人类文化先进水平的,已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文化,而是经过长期融汇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尽管其中西方文化依然唱着主角。这种新的文化,是不能以“西方文化”这一概念而框定的。因之,我们今日敞开国门,接纳域外先进文化,也就不是什么西化的问题了,而是世界化,人类化,全球化。如果说当年胡适“现代化就是充分的世界化”的提法只是西化的另一种表述,而没有多少实际差别的话,那么今天,“现代化即世界化”也就有了真正有别于“现代化即西化”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