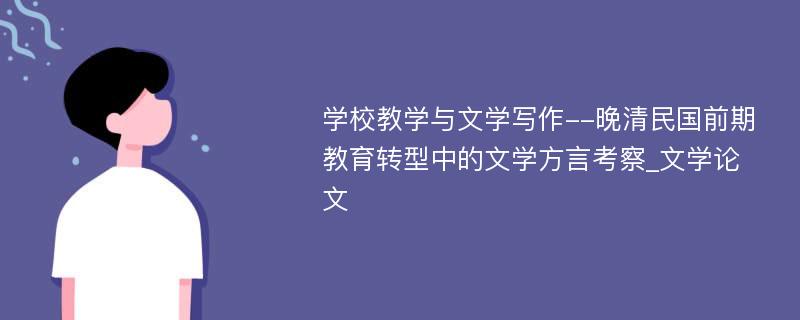
学堂讲授与文话书写——晚清民初教育转型之际的文话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晚清论文,学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40-06
晚清民初时期教育经历了一大变革,即新式学堂的兴起和传统书院的式微。在学堂讲授中,教科书与讲义的作用开始凸显,它们成为衡定教学内容、性质与效果的核心材料。从晚清民初开始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意味着讲授内容具有了一定的规范与程式;而政府颁布的学制章程则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的编写体制与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众多文话被列为各类学校文学科目的教科书,还有不少文话在体制与内容上与这些被列为教科书的文话有类同趋势。以《历代文话》所收的此期30种文话著作而言,可以确定为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就多达17种,这种传播方式的改变为观察文话乃至文章学在转型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从经学传统到文学话语
经学在封建文化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科举时代的文章衍变带有明显的经学传统影响印迹,原道、征圣、宗经成为文章依傍经学而取得独立地位的常见手段,文章的本体特征被经学叙述遮蔽。晚清民初,经学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受到空前挑战,经学传统开始动摇。科举的废除从根本上影响了士人对经学的关注热情,经学的地位由原来的必考科目与主流话语变为普通学说,推动经学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因由此消失;西学的涌入则从学理方面提供了异域之眼,加速了经学式微的进程。处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学堂,成为这一转向的见证:“今学堂之兴,辄本东西文为教育,甚乃请罢六经四子,专事东西。嗜古之儒,又或别启一堂,毅然取昔时训诂、性命、词章,尊为国粹。新旧殊绝,靡所折中。”[1](P6804)在书院向学堂的演变过程中,因政体的更迭,学制颇有反复,但其近代化进程没有改变;而经学的命运与学制变化紧密相连。在晚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与奏定学堂章程中,读经都占据重要的地位。为了避免经荒学废,奏定大学堂章程还特别设立经学科大学,列为八科之首,并将理学列为经学之一门。但自从新学被纳入教育范围以来,其吸引力远迈传统中学,读经有流于形式的趋势,难以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即作出决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校科目中经学也不再列入,大学堂也废除了经学科大学而分为七科。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度有所反复。袁垮台后,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与施行,教育近代化近于完成,经学从此完全失去了在教育制度方面的话语特权。经学传统在新式学堂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新学影响日益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经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归于泯灭,文化意义得到凸显。作为学堂教科书的文话,在这当中所表现出的观念变化,也就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必本经的观念正悄然发生改变。此前很少有从“文”方面谈论经典的,所谓“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2]这一叙述隐含的价值判断就是,与文章相比,六经的地位无疑要崇高得多。因而历代文章选集很少选入六经,这既是尊经的需要,也体现了区别经部与集部范围的意图。《经史百家杂钞》却打破了这一惯例,“乃选及经、子,凡各体文,皆推原于经某篇,甚允当也”。[3](P6675)陈衍《石遗室论文》对此表示认同,似乎未脱经学牢笼,但他的着眼点已转移到文学:“《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自唐虞下逮周末,《尚书》外文学分两大宗,曰《左氏传》,曰《小戴记》,皆各极文章之变化”。[3]P6675-6676)经学被纳入文学范畴,成为文学的论述对象。他指出:“《礼记》开后世史书中各志文法与各种笔记文法,实则子书体裁也。”[3](P6685)经学典籍被归入子书一类,这在科举时代几乎不可想象,而在学堂讲授中,却成为体认古代文章流别的普通知识。当经学失去神圣性之后,依附经典以自占地步的追溯本源做法亦趋消歇,沿波讨源的标准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
能注意到文章的本体规范,将之与经学适当疏离,这在观念上已属难得的进步。徐昂说:“观文学家之文,当寻其道之所在;观道学家之文,不必以文辞绳之。就造诣言之,道难而文易,然心远乎道,道求诸心而即得;而言远乎文,文则求诸言而不易即成也。故论其既则道易而文难,道有大小,文有厚薄,能见乎道而不失为文,斯亦可矣。”[4](P8909)徐昂的观点表明文与道皆有独立价值,不必依附;而对为文之难的充分认识,则解构了此前由道入文易的观念,对文学的阐释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尝试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姚永朴指出,“文学家之别出于诸家者有四”,第一就是“异于性理家”。因为“性理家所讲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显之在伦常日用,其学以德行为主,而不甚措意于词章”。由于各自追求的目标不同,自然不能以一方之准则衡量另一方的高下,“无如宗旨与文学家异,而流风渐被,其文既域于语录之中而不能振,诗亦但以《击壤集》为宗。夫邵子雍之诗,非无佳者也,然而无意为诗,即偶与风雅之旨合,不过出于性灵,故妙者极妙,而俗者极俗。奉为圭臬,流弊实多,而况语录之俚乎?”[5](P6849-6850)文章成就的高低不能以是否阐释性理来评判,故而儒家的语录与理学诗均因境界未至而受到排斥。在这里突出的是文学自身的标准,内容方面的经学叙述未能掩盖其表达方式上的缺失,经学传统已经让位于文学话语。
以文学为本位必然导致对文章表达中的经学论述的重新思考,传统经学文论“文以载道”的内涵开始发生位移。林纾认为,科举时代的“载道”之文,“其述政事,则不离官文书气;辨道学,则不离语录气;著经说,则不离高头讲章气”,这种文章只能说聊充插架,无裨艺林。而实际上,“道理”二字,“实纯备于为文之先,断不关系于临文之下。若秉笔为文,即思某者合理,某者中道,拘挛桎梏,不期趋入于陈腐矣”。经学传统影响下的文章写作容易沾染伪托门面的习气,其实这也是表达的惰性使然,此种文章“不必穿穴古今,但采取先儒口头所常言,后生小子耳中所熟闻者,补辑成文,以为得诸天然,出以清简。故理学家言,最为退老乡宦著书之蓝本,以不必用心,又据绝高地位也。究竟汗牛充栋,徒资覆瓿,可以不作”。合乎文章创作规律的方法则是,“吾人平日熟读经史及儒先之书,须镕化为液,储之胸中。临文以简语制断之,务协于事理,此便是道”。[6](P6402-6403)在林纾的解读之下,“道”的经学意义已经消退,文章所表达的内容合于日常生活规律就可以说是“载道”,也就是说,“文以载道”命题中的经学限制已被取消,文章的目的在于再现生活内容,而这正是文学观念的要义之一。刘咸炘也同样说:“‘文以载道’,此语实是名言,特为解者所狭。明乎道之无不在,则此语之不可非,明矣。”“盖道者,一切事、理、情之总名也。文能道一切事、理、情,即是载道矣。”[7](P9721)当我们回首体会这段话时,就不难了解,在时势变迁之后,经学传统在文学话语中是如何被淡化的,也不难体会,作为学堂教科书的文话在传达这一趋势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要之,在新旧学制递嬗过程中,学堂作为新知识的授受空间真切地感受了教育主导思想的变化。当经学被作为传统文化中保守与顽固的部分抛弃时,它对文化导向的控制作用也一同消亡。在学堂讲授中的文话,初步显示出摆脱经学影响的迹象。这既是近代教育的必然要求,也反过来促进了主体性文学观念的流通。文话的表述已由经学传统转向文学话语,从而也具有了面向现代文论的转型特征。
二、学堂章程与文话书写
学堂章程的制定与施行,是教育系统化的重要体现。晚清至民初所颁布的一系列学堂章程,为各级教育的开展与管理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文件。而教科书的编定,表明一门功课已有较完备的面貌,内容相对确定,性质趋向统一,具有稳定性与可重复操作性。这既有利于教育职能部门对课目进行考核监督,也可促进学科本身的规范化,是教育近代化的必然要求。晚清时期学堂教科书实行审定制,即不强行统一教材,但有纲领性条目规定其内容与性质,讲授者可以自行编订讲义,但需上报审定。这一制度使得讲授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避免了千篇一律的程式泛滥之作。
作为教科书的文话,映射出当时对中国文学科目设置、内容安排、教材选择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其书写策略成为观察学堂章程影响下的国文教学的重要资源。
文话被用作新式学堂的教科书,自然是以国文科为主。传统文章在学制中的地位一直为时人所关注。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的主要科目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文学研究法与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两种功课。民初的大学课程规划对此有一定的沿用,其文学门国文学类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等。从关涉文章之学的主要科目来看,两者有相当程度的叠合。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词章学、中国文学史都与文话具有性质方面的关联。《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还对高等学堂中的国文讲授作出了规定,所区分的三类学科当中,都安排有中国文学一门。第一、二年,主要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年则要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民初的各类专门学校亦将国文纳入通习科目。这些设置都为文话的讲授提供了空间。从现实情形看,晚清中学堂的中国文学教学,除了讲解文义、文法与作文外,“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8](中学堂章程)而这正是此一时期文话的关注焦点。民国初年,中学校“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9]也初具大学堂国文课的规模。正是这样,文话的讲授场合得以延伸至中学堂。
作为学堂教科书之用的文话,其编订的统领性指导意见来自于各类章程。由于章程详略不同,有的对于讲授内容与方法有详细的意见,而有些则十分简单,因此文话的面貌颇有个性纷呈的趋势。同样,审定制也为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些因素导致文话在具备个性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整体面貌,这一共性书写特点的出现即是章程影响的结果,虽然其程度有疏密之别。
章程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定文话的论述方式,直接影响文话相关观点的表述,甚至为之确立基调。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一卷二专为“解蔽篇”,以“剽窃前言,句摹字仿”、“堕迂腐理障,或杂陈庸陋俗谈以为工”等14种弊病为古文创作的禁约。而这一论述架构其实即依照章程展开。“《奏定大学堂章程》之《中国文学研究法》称:‘词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须辨其与古文不同之处。’以上所辨正诸弊即辨明诸体与古文不同者也。”[10](P7134)可见此书开端的辨体明义与章程有密切关联,不啻为章程的具体化。王葆心以述情、记事、说理为三种统系,并以此分析文章。这一统系为其评述文章的得意之处,实际上也与章程中的纵区、横区观点相近。在论述外国文与中国文的关联时,王葆心指出:“又至今日,有以西政西艺说经一派,遂因而发生以他邦语文与我华文并治一派。”他不忘说明“定章大学研究经学有以外国科学哲学证《易》之法”,[10](P7740)清楚地交代了理论来源。当然这样明确提示章程影响的文话并不多。但这一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在学科发轫时期,章程对于教科书书写的意义。在缺乏范本的情况下,章程规定的细则成为课堂讲授的原则,为教员提供了照章敷衍的便利。同时,作为纲领性指导文件,章程又是编订教科书需要遵循的准则,不允许有过多的偏离。这又导致文话中某种集体性话语的出现。例如,文话中对于东瀛文体、新译语名曾出现较一致的排异倾向,这固然与因应西学的策略有关,但实际上也反映了章程的意见。鉴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章程明确限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甚至强调指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8](学务纲要)字里行间渗透出对国学沦亡的忧虑。文话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趋同现象,应该说是对章程步趋的直接结果,在章程的禁止性言辞之下,作为教科书的文话,其表达主体性见解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章程对文话的结构也具有提示作用。姚永朴有《文学研究法》四卷,这一颇具现代气息的文话名称其实就来自于章程所规定的科目。早在1909年,姚氏即讲学于京师法政学堂,遴选历代文论名作20篇,加以评述疏讲,成《国文学》一书,性质上近于“古人论文要言”的讲义。章程规定此科目“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而《国文学》之体例一如章程所言。在此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研究法》体系更见严整,虽发凡起例有模仿《文心雕龙》之意,但其编纂结构实有章程影响的痕迹在。章程研究文学之要义前三条言字体、音韵、名义训诂之变迁,皆属小学范畴;《文学研究法》则论“起原”,首重小学,以文字为根本。章程言“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实即不同时期“文”之内涵;此书则述“范围”,指出今日文学的界限。章程言“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此书则挈纲领,以“义法”综括有物、有序诸说。章程举列群经文体、诸子文体及汉魏文体、唐宋至今文体等文章体类;此书则辨“门类”,逐一分析,并专设“著述”、“告语”、“记载”等以统细目。章程论“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主张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此书则设“运会”,以析文之盛衰。章程分文为“有德与无德”、“有实与无实”、“有学与无学”;此书则重“工夫”,授人以读文、看文、作文之下手方法。章程自“文章险怪者”以下皆言为文之诸种弊病,此书则有《瑕疵》以为文戒。两相比照,《文学研究法》章节设置方面,依托章程以展开论述的策略颇为明晰。
章程甚至会决定文话的核心观念。编书处章程将文章分为理胜、词胜两派,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则一衷其言,论文主旨“以理胜、词胜判为两途,其意尤独重理胜”。[11](P8149)此书为陈康黼讲授师范学校之讲义,从贯彻章程角度来说,可谓范本;但代言之作的嫌疑太过明显,其叙述方式近于以历代文章纳入章程设定的框架之中,以致自身观点完全湮没其中,不能不说是章程影响下的负面效果。
章程对文话书写的深层影响在于学术意识方面。传统文评中不乏文章史性质的文字,对文章流别亦有涉及,近于“时序”之作,但以之作为全书策略,关注文章流衍轨迹的并不多见。因而晚清民初文话中集中出现的历史意识就更值得注意。无论是大学堂还是中学,章程中都规定讲授文学流别、文风盛衰,甚至文学史。这就正式从观念上提示,对文章的把握必须具有学术总结意识,以历史眼光来衡论古今,使历时叙述成为讲授规范,在教科书中不断得到强化。章程对历史意识的重视成为文话书写的内在理路,促使文话具备了文学史的某些质素。《石遗室论文》以上古至周秦、两汉、三国六朝、唐四阶段展开论述;《文章学》上篇历论文章源流;《文谈》由近代上溯周秦,其卷二专论各代文;《读汉文记》近乎汉文小史;《历代文章论略》历述各代文章变迁;《桐城文学渊源考》探索派别传承轨迹,初具文章派别史规模;《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类似断代文学史;《文学述林》则以文变论、文体演化论辨正、辞派图、宋元文派略述、明文派概说等章目述此意旨,历史线索宛然。课程讲授围绕文章源流展开,由文评而趋近文学史,显示了学术的进路,学术史意识渐成共识。不能排除会有单独的文话著述与章程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受其熏染或所见略同亦显自然。
三、学堂讲授与技法重提
晚清民初,由于泰西科学观念的传入,加上传统学问自身统系的渐趋严密,使得文话呈现出学理性的提升,以往丛残琐语类的论述形式渐为体系严整的学术著作替代。《文学研究法》、《古文辞通义》、《文学述林》等文话都具有近代著述的特征。然而在学理性加强的同时,文话中对于技法的关注亦渐增多,似有向写作指南回归的倾向。技法重提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在这一文化思潮激荡的年代,当文言的生存境况日渐窘迫时,技法成了文章得以承续的关键。“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12](P8745)技法领悟则文章通达,文章通达则文化传承。由于时势的差异,对技法的重视程度及紧迫性都与以往不同。即使是从最切合实际的角度考虑,技法亦不得不讲,“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因而新式学堂中,“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8](学务纲要)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技法通过章程规定成为学堂的讲授内容。《春觉斋论文》明论文十六忌、讲用笔、用字;《晦堂文钥》重炼局炼意;《文学研究法》倡格、律、声、色;《古文辞通义》述文之读法、讲法、作法,将之归为“识途”;《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则详列四十四法,选文定篇,以期读者披文见法;《汉文典,文章典》由字句而篇章,逐一析论;《文谈》更结合制作,逐体明辨作法。这些集中的文话论述毫无例外,全都属于学堂教科书。无论是讲解文章以领悟大义,还是分析文题以敷衍成章,对技法的讲求都属于学堂讲授的份内任务。
然而不仅仅如此。技法虽然属于形下之迹,但法的规范在着意于技巧层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伦理特征。法意味着范式,只有形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才有可能被认可为法。因此对文章技法的择定,必然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肯定的是一种合乎规范的表达方式,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表达内容的认同。“谨修其法而审行之”(《礼记·曲礼》)规定的是礼法,传统文章的技法亦与此相通,社会规范借此而渗入技法,成为技法的隐性内涵。
因此当技法肩负了传承文化的重任时,这不过是放大了它的隐性质素。师法自然及与古为徒是技法的企慕之境,近乎无迹的技法成就只能是远景目标,对文章典范的研习却仍然要从技法切入。“古人文字最不可攀处,只是文法高妙而已”,“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13](P4)要达到高妙的文章境地,就必须重视技法,“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13](P6)晚清民初文话中的技法重提除了学堂讲授的促进,内在的理路亦甚显明。来裕恂指出重视技法与文章传统有关;“中国自上古至三代,语言文字不甚相离,故能以词见法。魏晋以来,骈文盛行,于是尚造句配章之法。逮唐宋古文家又专重篇章格调,而文法益密。故汉以前之文,因文生法;唐以后之文,由法成文。因文生法者,文成而法立;由法成文者,法立而文成”,因此技法成为衡鉴文章的必然要求,“舍法而求之,不得也”。[14](P8505)在《汉文典》中他详细分析了文章之法,以语助法、形容法、分析法、增改法、锻炼法、类用法析字法;以格调、节次、性质、声情、优劣论句法;以起法、承法、转法、结法述章法;以完全、偏阙分篇法。其所罗列,细密异常,四大类中各为析分,区分为17章138节,确乎满足了文典的条分缕析要求。以上区分多为单篇文章技法,王葆心则将文章区划为告语文、记载文与议论文,类聚大量古人相关作文技法,并互相比照,将交错法、对待法、接续法等比较观之,在翔实的资料排比中别出己见,调和折中。
技法不仅有正面的范式作用,还会给出反面的禁约。文话中屡见的文忌从为文应极力规避的诸多情况着眼,使技法论具有了双向维度。林纾揭举了16种文章弊病:直率、剽袭、庸絮、虚枵、险怪、凡猥、肤博、轻儇、偏执、狂谬、陈腐、涂饰、繁碎、糅杂、牵拘与熟烂,以戒律的形式对技法作出了反向规定。姚永朴则从文章援引故实、名称、立言得体与否论及文章的“瑕疵”,以求涤而去之。《文章典》更总结了庸、佻、弱、艰等40种文中之病,希望文家能够有所诫勉。
学堂讲授在特定的情境下使技法重提成为文话发展的一种趋势,而课堂氛围又限定了文话中的技法表述必然要向深细开掘。当然技法入手则易,脱化则难,因而守法而知变尤其成为技法说的核心。马其昶所标榜的“后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虽然,此先生之所自得也,人不能以先生之得为己之得,则仍诵读如先生焉,久之而悠然有会,乃取先生之言证之”,[14](P6440)正是对技法入而能出的态度。因此“欲工兹学,非有真悟不可”,[5](P7027)技法说的最终归宿正在于对自身的消解。以此,技法说又具有了超越品性。借以领悟前贤往哲文章之高妙的,无过于技法,“于是,我之精神与古人之精神,合而无间。乃借古人之精神,发挥我之精神”。[15](P8240)以技法为中介,在把握文章文本层次的同时,达到对精神内蕴的体悟。这样技法重提在学堂中的盛行就不仅仅是教学形式的需要,同时也暗含了某种文化期待:“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又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气,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阅世考情,所以广其实也。至于化而裁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由是而成经成史,成子成集,成训诂家,成性理家,成政治家,成大文学家,岂非通乎经纬之道而然哉?”[15](P8241)在这个意义上,技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晚清民初是一个变化急遽、动荡频仍的时代,文话中所表现出的新动向因新式学堂的兴起而展开。在思想倾向、著述体式与内容偏尚方面的变化,无一不与教育近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在这个文章生存空间日益压缩的时段里,文话的调适突出地彰显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种种貌似守成的文化现象之后,潜伏的是传统自新的趋势。对接续文章传统的期待,将文话书写与学堂授受绾结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