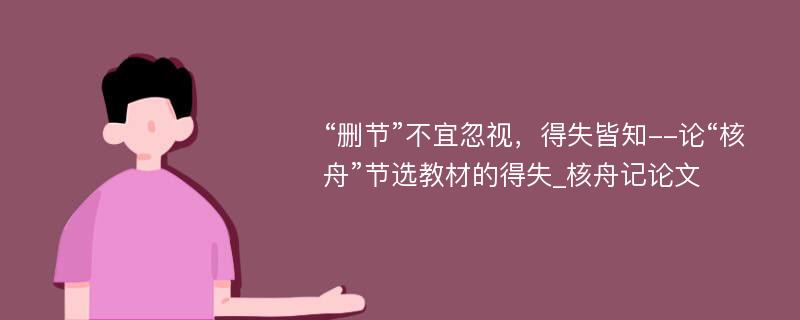
“删节”不宜忽,得失寸心知——由《核舟记》一文的删节看教材编选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一文论文,心知论文,教材论文,核舟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一篇出色的状物杂记,全文观察细致,描写具体,行文畅达,层次清楚,生动地记述了核舟巧夺天工的状貌,赞美了雕刻艺人的高超技艺,很为后人推崇。大凡读过《核舟记》的人,无不为中国古代精美绝伦的工艺所折服,无不为作者富有情趣、充满想象的语言所感染。但长期以来,人教版教材在选编此文时,一直省略“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和“嘻,技亦灵怪矣哉”中间的一段内容: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 技亦灵怪矣哉! 庄列所载,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糜了然者。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繇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
译文:我仔细地端详核舟完毕后,惊奇地说:啊!技艺也真是灵巧奇妙了!庄周、列子(在他们的著作里)所记载的,称得上惊奇如同鬼斧神工的器物也有很多,然而又有谁在长不到一寸的材质上运用他的刻刀(削刻出形象),而极小的细节也能刻得清楚明了的呢。假如有一个人,拿我以上所说的(即整篇核舟记)来回答我(即关于“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麋了然者”的疑问,而我又没有亲眼看见过的话),我肯定怀疑他在说假话。到今天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样精巧的东西(所以我终于相信有这种精巧的技艺存在)。由此看来,荆棘的末端的尖刺,未必不可以刻一个母猴啊。
据说编者如此删节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核舟工艺绝技已经失传,桃核艺术精品早已湮没,教材无法向学生展示核舟实物图片,为避免自相矛盾,故将此段删去。如是说法,恐很难站得住脚,因为现在桃核舟早已重现人间(按:新华社1994年3月16日北京电《镇海发现罕见的明微雕桃核舟》,载《宁波日报》1994.3.17①),到底是何原因删节,在此不作讨论。但这样删节的效果,笔者认为不好。
首先,删节部分篇幅不长,即使人选也不会给学生增加多大的阅读负担。相反,倒可以使课文文气畅达,前后连贯,让学生真正感悟核舟艺人的高超技艺。以笔者的教学实践为例,笔者在讲到最后一句“嘻,技亦灵怪矣哉”时说,古人称鬼神曰“灵”,称妖物曰“怪”,文章用“灵怪”二字赞扬王叔远的奇技,意思是说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技,简直不是世人所能具有的,只有鬼神妖物才能办得到。对这样的解说,大部分学生感到突兀,不能真正理解作者为什么忽然来这一句抒情和议论。因为在学生看来,王叔远的技艺固然“奇巧”,但还不至于与“鬼神妖物”相媲美,更不能领会核舟雕刻艺术已至“鬼斧神工”之境界。鉴于此,笔者及时补充了删节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删节部分的含义,最终明确作者在抒情议论中运用对比手法(将王叔远的核雕艺术与庄子、列子笔下的奇人奇技相对比),称赞王叔远雕刻核舟手法熟练,技术神妙,前无古人,就算《庄子·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匠石也望尘莫及;通过现身说法,强调如无实物佐证,连本人也难以置信的真实心理,以此说明核舟工艺成就惊人;最后一句运用先秦典故,典故的大意是说有一个狡猾的工匠欺骗齐王,说他技艺极好,可以在荆棘刺上刻一个母猴。后来有人告诉齐王这一定是假的,因为工匠的刻刀比荆棘刺还大,一定没法刻。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强调了王叔远雕刻技艺之高明。在此基础上,作者深情感叹:“嘻!技亦灵怪矣哉!”至此,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浑然一体,水到渠成。如此行文,文气畅达,反复咏叹,毫无矫情,实是作者由衷赞叹之心声,易于学生理解感悟。
其次,这样删节忽视了“记”的文体特征。“记”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它主要是记载事物,并通过记事、记物、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由此可见,抒发情感或发表见解应是“记”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以“记”为题的文言文为数不少。这类文章中,大多数是游记,还有些叙事性散文或者“杂记”。但不管是“游记”还是“杂记”,它们都有一共同点,就是以记叙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以叙事、写景、状物的成分为主,而以抒发作者的情操和抱负,或阐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为目的,多采用“卒章显志”的表现方式。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章先略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一事,交代作记缘起,然后着力描写“迁客骚人”登楼时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最后表达作者有如“古仁人”的阔大情怀和政治抱负。而另一些则是寓情理于事、景、物之中,主要用的是“融情于景”“融情于物”的写法。《核舟记》中核舟这一“奇巧”的工艺品所塑造的每个形象,得益于作者能依托核舟这一事物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再结合合于情理的逻辑思维,使核舟上的事理逻辑与作者的语言逻辑完美统一,如实生动地再现了苏、黄、佛印及舟子共五人各不相同的身份、志趣爱好、各为所事及细微动作,使他们各自的形象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读者面前,如写鲁直“若有所语”,佛印的神情“与苏黄不属”,舟子中的“居右者”“若啸呼状”,“居左者”“若听茶声然”,所刻之字“细若纹足,钩画了了”。这些语句不仅使核舟上的人物在读者面前形象鲜明,而且使核舟上的事物在读者面前具体生动,核舟上苏东坡《赤壁赋》的主题和意境也自然领会在读者心中。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对核舟人、事的说明,不如说是饱含作者深情的生动描写。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结尾发出由衷的赞叹,即物抒情,寄托了特定时代士人的独特心态和生活情趣,抒发对创作者精巧的构思和大胆创新的由衷赞美,写作技艺实在奇妙高超。假如作者仅是作些客观的描绘,而不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文章至多只能是一篇呆板平实的说明词,而决不会像现在所写的那么感人,启人想象。
那么,编者为什么要删节作者的“抒情议论”的文字呢?我们可以从教参中发现一点信息:本文原作在介绍完核舟之后,还有一段议论,课文删去它的绝大部分,只保留了最后一句,即“嘻,技亦灵怪矣哉”。因此,现在看来,它跟我们常见的说明文可算是很相似了。(人教版教参八年级上册《核舟记》课文研讨)由此可知,编者是想把文本删节成一篇“说明文”让老师进行教学。但笔者认为,这恰是严重忽视了“记”这一古代文体的特征。作为教学资源的存在,文本的文体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如何确定文章的教学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是诸多问题中最需要明辨的。从教学实践看,笔者一直对核舟记作为说明文体编排“耿耿于怀”,因为纵观本单元文言篇目不难发现,有的反映了我国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桃花源记》《大道之行也》),有的谈到知识分子处世立身的态度(《陋室铭》和《爱莲说》),有的表达了志存高远、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杜甫诗三首》),可见本单元的文言作品,均侧重于抒情或议论,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作为其中的一篇传统篇日《核舟记》如果定位成说明文,则显得不伦不类,难以“合群”。
作为状物杂记的名篇《核舟记》,它既表现出一个时代民间雕刻艺术的精妙绝伦,同时借助描绘核舟上一代文豪的闲情逸趣、古代船工的生活习性和纯朴的热情,表现出作者作为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核舟记》从对核舟这一“奇巧”雕刻的事物解说上说是一篇小品说明文;从对人物进行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描绘来说,它因极强的文学性又不失为一篇精美的“杂记”散文。
最后,作为教材的编写者,对入选文章进行必要的删节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文本的删节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得破坏原著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不得损害原著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更不得浅化原著丰富蕴藉的思想内涵。
笔者认为,这种删节是对张潮所编《虞初新志》意蕴的破坏。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不仅通过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选材要求、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而且借助篇末批语,随时宣讲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小说观念,即所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馀”(《虞初新志自序》)。通过序跋凡例和篇末批语的阐发揄扬,使出自众手的各篇在风采各异的同时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书有很强的整体感,显示出编选者的总体构思、内容取舍和美学好恶。
《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并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核舟记》中作者凭借与雕刻艺人有交往,“尝贻余核舟一”,来增强所记之事的真实性。作者凭借雕品的艺术魅力和结尾的抒情议论下了断言:核舟将流芳百世,并一直为后人所叹绝——“技亦灵怪矣哉”。我们因此认定作者在叹赏艺人水平高超的同时,也获知了作者自道不无得意的内心话,这是全文首段与末段合作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因此,结尾的抒情议论恰是文本深厚意蕴之所在,也是解读文本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删之,实是对原著编辑意图、文化意蕴的漠视和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