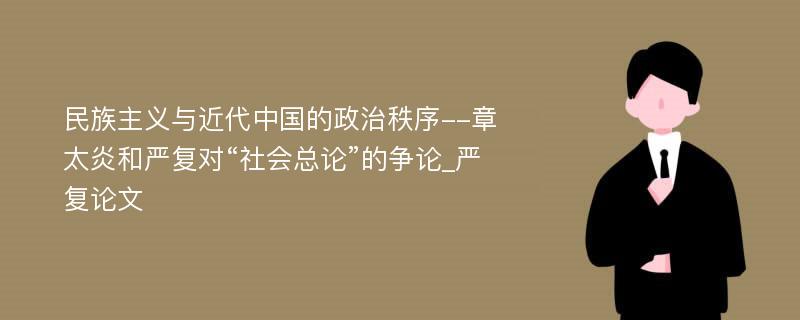
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通诠》一书,系严复根据英国思想家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之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翻译而成。一部通俗性读物缘何会成为严复所选定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为何会在晚清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前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严复最为直接的刺激来自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排外风潮。因为在严复看来,排外无异于是对于文明的拒绝。①总体而言,严复寄望于这本通俗著作以明快的方式建构起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他借助甄克思的图腾、宗法、军国民三阶段论,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确定为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中国走向文明的道路,即宪政民主政治框架。这个动机在严复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1904年4月20日起在《大公报》连载四期,总第651号至654号)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这篇介绍性文字中,严复强调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将排外思想的源头归之于民族主义,而排外既无法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也难以真正与列国竞逐。“总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②换句话说,严复希望中国人接受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他对“民族主义”特别要加以批评的原因。因为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形态,“偏离”了这个普遍性的路径,因而需要“校正”,即接受西方已经成功的社会新形态。 对于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因由,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旧译为“史华兹”)的分析也值得注意。他说,严复虽然试图从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中西方不同的制度根源,但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导向中国可以产生自己的制度体系的结论,而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中国制度的落后,并且儒家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社会通诠》的按语最集中地体现了严复的逐渐进化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他坚定不移地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儒教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本身是错误的;它们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的反映,是一个早该退出而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不合而引起的错误反映。”③ 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中,通过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进而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视为文明的代表。尽管严复也意识到这种文明的制度并不能简单地移植,还需要知识、道德和身体等因素的配合。但是在严复看来,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民智、民德和民力并不能真正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获得。所以,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严复所呈现的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民权的压制:“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④ 严复对中国民众接受文明的能力表示担忧,并把这种能力的“低下”归咎于政治传统:“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⑤ 也许是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也许是基于晚清国家积弱的现实感受,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严复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力量,因而对于逐渐兴起的、以排满为口号的革命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立场怀有深深的忧虑。在我看来,严复倾向于赞成以增加国家能力的方式来使国家迈向文明,而认为革命的方式和革命派的主张,都会阻碍国家的富强。 对于严复的态度,革命派也洞若观火。因此,当《社会通诠》出版之后,新创刊的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报》所设定的论战对象除了梁启超之外,就是严复。汪精卫、胡汉民等纷纷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其中最为充分的则是章太炎所著之《〈社会通诠〉商兑》。可见,正是因为严复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导致本书成为革命派竞相讨论的文本,进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本文将围绕章太炎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宪政、议会等制度的质疑,来剖析晚清思想界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路。 一、汪精卫和胡汉民对《社会通诠》按语中“民族主义”的评析 在严复所著之《社会通诠》的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⑥这段话引发了汪精卫、胡汉民和章太炎的共同兴趣,如果说胡汉民通过曲折的辩解,试图建立起严复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正相关联系的话,那么,汪精卫和章太炎则是要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误解”。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以排满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潮流。在经历了《辛丑条约》等事件之后,新近形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质疑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派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 革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改良路径的绝望。而异族统治则恰好可以被利用为改变权力结构的理由。所以,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派的武器。这样,是选择基于原有统治格局进行变革,还是推翻现存的满族统治阶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思考新的中国的不同立足点。“1903年前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场辩论,他们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上出现分歧。直至20世纪的最初几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在1905年前的二三年里,这一倾向开始发生变化,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转而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信条。”⑦的确,深受伯伦知理(Johann Bluntchli)等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等人,由于担心反满的情绪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目标的确定,因而提倡一种“大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而严复所翻译的《社会通诠》及其按语,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和了梁启超等对革命派所主张的、以反满为口号的“小民族主义”的批评,因此势必成为革命派与立宪派争论的主题。 新创办的《民报》成为革命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而其于1905年的创刊号中刊出的汪精卫的长文《民族的国民》,就是要系统地回应梁启超和严复的问题。他也通过引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中的“民族”(nation)和“国民”(volk)来回应严复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落后”观念的做法;同时指出康梁“满汉一体”的主张也并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唯一途径。 基于伯伦知理等人的观念,汪精卫说,民族是由血缘与风俗等因素凝聚而成的团体,是人种学上的名词,而国民一词则是法律意义上的名词。“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⑧ 既有基于“民族”和“国民”的区分,那么国家的构成就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单一民族可构成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也可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等等。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既有互相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同化,也有通过征服等手段达成不同地位民族之间的同化方式。在汪精卫看来,满族就是通过征服手段对汉族进行压制,这样,汉族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同时也具有追求民族独立自主的道德正义。 在汪精卫看来,严复只是看到了社会进化的大趋势,而不能看到由种族发展为国民的复杂性。因此,严复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实属错失了准星。汪精卫说,从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安排而言,满汉之间并没有融合,满族人擅用各种专属特权来奴役汉人。虽然,满族皇帝也试图用“君臣大义”来涵摄种族差异,但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汉族人顺从地接受统治。据此,汪精卫进一步批评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满汉一体”论,认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目标,即民族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政治革命则是要建立一立宪国家。⑨革命党并非只有民族革命一个目标,而是将民族革命视为实现政治革命的必要前提,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以“立宪”为形式的现代国家。汪精卫说:“深观乎国民之所以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辗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尅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⑩建立同族政府和实现立宪政治便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如此,民族主义便成为实现宪政的前提。 革命党另一舆论娇子胡汉民亦有《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一文发表于《民报》与《大公报》等报刊。在该文中,他结合严复的其他译作和观点,对严复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清理。在胡汉民看来,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目的是要矫正因《天演论》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严氏乃惧其仅为种族思想不足以求胜于竞争激烈之场也。故进于军国主义而有《社会通诠》之译也。”(11)将进化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关联起来,是胡汉民精审的观察所得。严复之提倡进化,是要说明历史大势,而中国人在接受进化观念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反而从观念上拒斥普遍趋势,进而寻求中国的独特性。因此,如何将民族主义与“历史趋势”相结合则是胡文的关键。 基于对严复翻译《社会通诠》的出发点的认识,胡汉民首先要破除的是民族主义与军国民主义之间的排斥关系。胡汉民认为,严复从斯宾塞的有机国家论出发,论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实际上,有机国家论作为与社会契约论的对勘之作,二者或注重国家的整体,或注重个人的权利,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因此,要分析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能以某种学说为定论,最合理的方式是将国家的整体和个人的权利进行有机的结合。 胡汉民认为,严复所反对的是只知排满、排外而不知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胡汉民更是根据严复在《法意》等书中的按语认定,严复自己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首先,严复批评明代之后以君臣之义取代种族思想,使亡国而不以为耻。其次,严复认识到殖民国家是不会给那些被征服国家制定“仁法”的,而这样的说法则足以激起亡国之民的悲痛情感。所以胡汉民认为,不能从严复表面的言辞来判定严复的思想,而是要从其内在的理路中发现严复思想之实质。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其对民族主义所进行辩护的要点之一在于民族革命并非与某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相结合,而是民族主义并非革命的唯一目标,革命的目标还在于发展民权和宪政。 相比于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基本赞同甄克思理论的立场来为在民族主义指导下的种族革命进行辩护,章太炎的批评可以说是入室操戈,他对于宗法社会、军国民社会和民族主义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从而呈现出带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和哲学色彩的思想面貌。 二、“总相”与“别相”:章太炎对《社会通诠》中宗法社会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评论 章太炎对于严复的总体评价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这句话出自他与吴承仕谈话所录的《菿汉微言》:“严复既译《名学》,道出上海,敷坐讲演,好以《论》、《孟》诸书,证成其说。沈曾植笑之曰,严复所言四书题镜之流,何以往听者之不知类邪?严复又译《社会通诠》,虽名通诠,实乃远西一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是故知别相而不知总相者,沈曾植也;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者,严复也。”(12)的确,作为一个在英国留学并立志改变中国的人而言,严复所致力的是以西方之长来补中国之短。所以,他总是在试图进行中西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比较。此类比较一般而言会着眼于中西之别,因而有许多总体性的概括难以照应到所有的情况,导致产生许多“知总相而不知别相”的判断。(13)而章太炎对于《社会通诠》所作的“商兑”,虽然从总体上是要为民族主义辩护,然其方式上则是抽丝剥茧式的层层推进,以甄克思的结论和严复的按语为依据,对其文从推论方式到具体的观点做了递进式的批驳。 严复等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确立起一种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路径,认为这是由社会进化的公理所决定的,因此,严复的社会进化路径总体而言是单线式的,虽然在国权和民权的优先性上,严复有过很多的纠结,但是他依然坚持,中国要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的价值体系、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体系加以接受和模仿。严复的翻译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向的,如果我们阅读《原强》等文章,可以看出严复的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富强策略的理论支持。 这个时期的章太炎,思想极其复杂,与严复或康梁接受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并将之视为社会发展的“公理”的看法不同,章太炎糅合了佛教与庄子“齐物”的思想方法,对于“公理”(14)本身,以及由此依附于这个“公理”的自由、国家、议会等概念,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因此,就社会发展层面而言,章太炎所提供的可能是中国发展的另外一种方案。 章太炎对于与公理的建构相关的现代科学方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他首先质疑的是《社会通诠》的结论所依据的方法,即归纳法和社会学的方法。章太炎认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质学)之不同在于,“心能流行,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15)即很难以一种计量的方法,对变化万端的人类活动做出精确的分析。因而由此所建立的所谓社会规律,就很难真正令人信服。章太炎不满严复和杨度以此为据来分析中国社会。章太炎提出: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存在不过百年,而专业的学者,也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方法。 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夫尽往事以测来者,犹未能得什之五也,而况其未尽耶?(16) 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严复十分推崇归纳逻辑,然章太炎正是看到了归纳法所必然会面临的经验事实难以穷尽的困境,据此这样的方法所推论的结论自然是有限的。从方法的局限出发,章太炎进一步所要质疑的就是甄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有效性。 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书中,把社会演化的进程划分为太古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对原作所描述的社会类型及相应的时空系统进行了改造”,甄克思并不断定人类社会必须经历此三种社会形态,而且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涉及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并未涉及中国。而“严译《社会通诠》对甄克思原作中这种并不十分明确的时空序列进行了重新排列,认定人类社会‘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并把原作中所不涉及的中国社会纳入这一发展序列中。(17)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要强调的恰好是章太炎着力要批评的。当然需要说明的也在此,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的词汇选择和倾向强调,所以导致译作和原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并不一定为章太炎或同样引以为据的杨度等人所了解,这就意味着,章太炎对于甄克思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严复立场的批评。 甄克思在描述宗法社会和军国民社会的时候,提出了四条基本的差别。其一为“重民而不地著”。即认为宗法社会没有明确的国民意识,只有种族观念;而军国民社会的人则以其所居地为准,住在哪个国家就成该国的国民。其二是“排外而锄非种”。宗法社会或仇视或奴役国内别的种族,而军国民社会则主动吸收移民以增强竞争力。其三是“统于所尊”。认为发展程度高的社会以个人为本位,所以平等;而宗法社会以一族一家为本位,则有依附关系。其四是“不为物竞”。即宗法社会,一切以祖法和习俗为规则,所以人的竞争能力并不能获得展现;而文明社会,则可以“各竭心思耳目之力、各从其意之所善而为之”,从而个人有充分的决断力。(18)这四条差别其实也就是严复所要强调的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意图是要让中国摆脱宗法社会而进入军国民社会。 这样的一些思想,在严复为《社会通诠》所写的按语中得到强调。严复在讨论“宗法社会”时的按语是:“作者举似社会,常置支那,盖未悉也。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9)从这个按语中,严复已经点明了甄克思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对此,严复的判断是甄克思可能并未具备关于中国的知识。然而这个说明并不意味着严复试图将中国视为例外,他依然认为这个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存有解释力。根据甄克思的模式,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处于由宗法社会向军国民社会发展的阶段,即所谓七分宗法,三分军国民。尽管与惯常一样,严复会强调这个判断的个人化特性,不过严复依然自信地认为,基于其所掌握的“先进知识”,对于当时的国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过,在章太炎看来,甄克思对于宗法社会的四个特征的描述,或完全、或部分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能简单以“宗法社会”概括。章太炎根据史实指出,传统中国,有宗法之秩序者,唯在社会上层,而礼不下庶人,民间并无宗法可守。继之,章太炎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人口流动的状况,认为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动十分频繁,并不以其出生地为限。同样中国古代也并不排外,不但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安居乐业,甚至外来宗教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至于所谓的人身依附关系,章太炎认为战国以前或存在过,但战国之后,国家和宗族对于人民并不具备绝对的控制力,所以“有合于古,不合于今也”。关于第四条,章太炎提出,中国古代虽然有子承父业的说法,但是职业的变动并没有限制,所以“甄氏以其所观察者而著之书,其说自不误耳。而世人以此附合于吾土,则其咎不在甄氏而在他人。若就此四条以与中国成事相稽,惟一事为合古,而其余皆无当于古”。(20) 章太炎之所以要对甄克思的社会模型进行批评,关键是要反对甄克思所提出的“宗法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合群者也”(21)的结论。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时候所使用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大多是在“宗法”、“宗族”和“家族”意义上使用,与后世的“nationalism”有很大的不同。(22)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则可以认为严复是有意将甄克思所批评的家族、宗族主义思想转化为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批评,其手法则是将民族主义视为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因而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这有点类似于“设靶自射”的做法。 严复在《社会通诠》中对“宗法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合群”一段话的按语中,对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 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3) 在这段话中,严复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各种政治力量在民族主义方面取得了共识,而这种主义所导致的是排外的思想,所以不能“强吾种”。在他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则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民族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勾连。(24) 由此,章太炎对《社会通诠》的批评转入对于严复所“有意”引入的“民族主义”的讨论。 章太炎并不像前文所提到的胡汉民那样,试图将严复本人的思想与民族主义挂钩而证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批驳严复的观点。他说严复对民族主义的判断“污谬之甚”。“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然就严氏所译甄说,则民族主义,或为普遍之广名,如是则外延甚巨,而足以虚受三种形式”。(25)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这样的观念,在图腾社会,则以图腾作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宗法社会,则以谱牒等为收族之道,其功能都在于凝聚民众。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而是在所有的政治形态中均可以产生的思想形态,故而民族主义本身并不一定附着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在军国民社会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只是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在军国民阶段,国家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形态,因此,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国家的主权和富强,而不仅仅是种族的利益。 对于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概括说:“且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则求合,一国异民族则求分。”(26)在以民族建构国家的指向下,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德国就完成了建构起一个大国家的使命。而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民族则希望独立,例如爱尔兰则希望脱离英国。 作为多民族融合典范的美国和以超越民族国家为指向的社会主义思潮,其民族主义思想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章太炎也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美国因其国家新建,所以广泛吸纳各种族的人口,但是其中白人和黑人及其他种族之间在权利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所以,存在着事实上的民族主义。而以阶级划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看上去是一种超越种族主义的思潮,但章太炎引用不具名的欧洲学者的言论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得利者,只在于少数白人,这样,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并非背道而驰。由此,章太炎所试图证明的是,即使在甄克思所认定的军国民社会,民族主义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而不是如严复所谓民族主义是一种宗法社会特有的思想。 我们难以断定章太炎是否阅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不过章太炎在论述中是可以看出种族与国民之间的分辨的。这一点与汪精卫等当时的革命派类似,即中国的民族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通过排满恢复汉族的统治,二是建立现代国家,确立国民意识。所以,章太炎指出,革命党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其任务有二,一是恢复国家主权,二是逐渐“化合”各民族。 吾党之言民族主义……惟曰以异民族而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则吾欲与之分,既分以往,其附于职方者,蒙古之为国仇,则已解于半千岁上,准回、青海,故无怨也。西藏则历世内属,而又于宗教得中国之尊封者也。浸借言语,风俗渐能通变,而以其族醇化于我,吾之视之,必非美国之视黑民。若纵令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举敦煌以西之地,以断俄人之右臂者,则虽与为神圣同盟可也。若是,而曰此民族主义者,即是宗法社会,则何异见人之国旗商标,而曰有此徽章者,犹未离于图腾社会也。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27) 章太炎何以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促进宗法社会的“镕解”呢?对此,他从“历史民族”(28)的观念出发,认为历史上蒙、藏、回各民族一直在不断融合,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建构民族意识。因此,新的民族之间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异族歧视。 从现实的活动组织方式而言,章太炎也认为革命党的活动目的是要建立起国族和国家。他借助晚明会党活动的例子来说明,革命党其活动的方式,延续了会党的传统,即以国家利益为上,超越于家族与地方利益的局限。而革命的成功,还将“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坏宗法社会”。(29)最终建立起与这个新的主权国家相符合的“国族”观念,“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30)所以,章太炎说,革民党的民族主义,不仅不是宗法主义,反而是宗法主义的解放者。 严复反对民族主义之原因,是认为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排外特性会阻碍国家的富强。对此,章太炎认为,是否能让种族强盛,并非基于某种主义,关键是在具体的“术”,即达成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诸如此类主义的方法。章太炎认为,只以有用无用来断定一种思想的方法,是“功利主义”思维习性的产物,并非严复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儒人之天性”。章太炎所要批评的则是关于“成败之策”,即促使一种主义得以实现的方式方法。 关于达成民族主义的方法,章太炎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武力实现,另一种是舆论鼓动。他说,“今日固决死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此民族主义所任用,而于宗法社会无忽微之相系也”。(31)也就是说,以民族主义来激发革命的热情,推翻旧的王朝,这跟宗法社会并无瓜葛。他甚至认为,如果再出现一个洪秀全、杨秀清,就不会再有曾国藩和胡林翼这样维护清王朝的汉族官吏了。 对于舆论上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承认舆论鼓动强于军事活动,是革命党的软肋,然其作用依然不可小觑。“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32)的确,革命党因其财力限制,并没有相应的武装力量来支持其政治诉求的达成。然而革命党所进行的革命宣传,使革命和改良成为晚清政治发展的一个选项,而一些体制内的力量,比如地方督抚、新军、地方绅士集团,在辛亥革命的前后,成为革命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拜革命舆论宣传之效。 接下来,章太炎开始对反对民族主义革命的群体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政客之所以不认同民族主义的路径,而热衷于以“立宪”来解决政治问题,其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热中干禄,而以立宪望之满洲政府者”;第二类是“欲以国民自竞……以倡国会于下,使政府震怖”,他认为这种方式其实与革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没必要“局促于立宪之辕下”。(33) 最后,章太炎认为,如果固执地认定军国民社会高于宗法社会,并将之视为进化之铁律,而不知在历史上成败并不一定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环环相扣,就会转而相信不如直接迎立西方元首来统治中国,这样比中国人自己努力还要强百倍。章太炎认为,这样的做法虽然为所有中国人所唾弃,却被严复等人视为合理之举,这不啻为卖国之举了。 史华慈有一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严复和章太炎等人争论的总结。史华慈认为,严复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由皇帝推动的现代化的努力之上,因此,他反对革命派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去鼓吹革命,因为这样的革命会造成社会混乱。“在严复眼里,由孙中山、汪精卫、章炳麟和其他革命者培育起来的反满情绪代表着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任意毁灭改革的希望,而这种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进化阶段里只能导致毫无希望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满情绪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最具宗法性的反动特征即集团的或宗族的排外主义的复活。”(34)而章太炎等人则认为,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不能再依赖毫无作为的清王朝,唯有将其推翻才有实现国家富强的可能,而要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则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立宪政治与追求富强:严复和章太炎对于国家与社会秩序建构的歧见 行文至此,本来章太炎对于严译《社会通诠》之批驳似可告一段落,然而由《社会通诠》引发的相关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向纵深发展。 这个发展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章太炎针对杨度根据《社会通诠》而作的《金铁主义论》所展开的未来国家形态所进行的争辩,其核心的思想体现在章太炎1907年所作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主张以文化认同而非种族认同来建构未来的中国。其二则是针对严复在《社会通诠》、《法意》等译作所提出的立宪政治作为军国民国家的主要政治体制而进行的争论,其主要的代表作品包括《代议然否论》、《四惑论》等。因本文主要关涉章太炎与严复之间的争论,所以章太炎与杨度之争论当另文讨论,而这里集中于章太炎与严复关于立宪和议会制度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的困境所进行的争论。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胜利被视为中国走向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因为国人将日本的胜利看作是明治维新的胜利。而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则进一步被“描述”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严复认定传统中国的政治是一种专制政治,而中国想要获得富强,则唯有立宪一途,这乃“天演大进之世局”。(35) 严复自从在《原强》中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之后,便一直强调西方的富强自有其价值与制度为依托,此为体用合一。这样的观念可以说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别在于不同的时期其落实西政之方式各有不同。翻译《社会通诠》提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论,其目的也是要强调中国要从宗法社会上升至军国民社会,关键在于“政理程度”的差别。而“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36)因此,中西富强和积弱之根源在于政体之文明与野蛮之别。 严复有时会将制度的差异归结为文化。在严复看来,中国并无民权观念,自古以来的圣贤,从不认为其赋税等行政手段需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甚至韩愈在《原道》中直接说,民若不出租赋就可以对其直接诛杀。而相比之下,欧洲各国即便是处于最黑暗的历史时代中,当时之政府虽然也将“养兵为民”作为征税之借口,但仍需要获得民众的允诺才可进行实质征税。这就是西方民权之所以形成、议院制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制度决定论的思想。与《社会通诠》建构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相应,如果与宗法社会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皇权的话,那么军国民社会的理想制度则是立宪、议会政治。 根据严复对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中对西方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介绍的翻译,及严复自己所作的按语,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的政治体制,有如下一些基本要素:第一,采行英国式的准共和制或美国式的共和制,中央政府“其权不止于诘戎议制,乃并刑法行政二大权而有之”;第二,中央政府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相应地采行代表制和政党制;第三,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实行地方自治。而要实现这一蓝图,必须始终处理好国家与小己之间的关系,打破二者之间的任何环节特别是宗法性的家族与宗族组织,使国家与小己之间发生直接联系。同时国家应适当限制自己的权力(或更确切地说,适当限制国家的权力),凡与“诘戎”、“议制”、“刑法”、“行政”诸大权无关而制关系到民生事业者,应放手任民众自为,以培养国民的自立能力,培养小己的国家思想,以此为基础,建设强大的近代国家。(37) 在经过了短暂的迷信公法可以保护中国的阶段之后,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民族国家体制必然带来以本国利益至上的游戏规则,即杨度所精确概括的“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国际格局。因此,在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之间必然需要一种次序上的分辨。严复在稍后的《法意》按语中说,“虽有至仁之国,必不能为所胜亡国之民立仁制也。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其民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不心蕲之而不可得也”。(38)所以,国家的主权独立对于仁义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前提。在这样的认识下,严复尤其心仪斯宾塞的国家有机体的思想,认为个人在一个有机的国家中要担负其各自的责任。“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39)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义务感的民众之间的协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民智民德民力未臻完善之际,遽开议院、强调权力制衡徒害无益,要先从培养国民的责任感开始。因此,最现实的让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使为之得其术,民气不必缘此而遂嚣,而于国家纲举目张之治,岂曰小补?上无曰民愚不足任此事也。今之为此,正以瘉愚。但使人人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且各知尊主隆民,为人人之义务,则加赋保邦之事,必皆乐于自将。”(40) 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时候,在其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四点好处的第一点中,特意“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地方自治‘使国民人人有国家之思想’这一重要内容,在第四个优点中增加了中央政府‘可专意会神于纪纲之大者’这一内容,使得地方自治制度看起来不仅有利于地方,而且更有利中央政府”。(41)这依然是试图在培育民权素质的同时,关照国家的整体性利益。严复在《社会通诠》有关地方自治的按语中比较了现代政治秩序下的地方自治和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制度的区别: 地方自治之制,为中国从古之所无。三代封建,拂特之制耳,非自治也。秦汉以还,郡县之制日密,虽微末如薄尉,澹泊如学官,皆总之于吏部。其用人也,以年格而非以才。其行政也,守成例而非应变。此吾国之治,所以久辄腐败,乃至新朝更始,亦未见其内治之盛也。总之,中西政想,有绝不同者。夫谓治人之人,即治于人者之所推举,此即求之于古圣之胸中,前贤之脑海,吾敢决其无此议也。……考为上而为其下所推立者,于中国历史,惟唐代之藩镇。顾彼所推立者,为武人,非文吏也,故其事为乱制。往顾亭林尝有以郡县封建之议,其说甚健,然以较欧洲地方自治之制,则去之犹甚远也。(42) 严复认为,封建制度并不能等同于地方自治。在郡县制之后,官吏由吏部任命,地方官员并非由当地民众推举,即使是晚明大儒顾炎武所主张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提高地方官员的地位,扩大地方经济的空间的设想,与欧洲的地方自治也不一样。因此,严复主张的地方自治的关键是地方治理者由被治理者推举,而逐渐进行现代政治观念的落实。 地方自治这个主张为许多革命党人所支持,因为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朝廷权力的分解。但是,这个主张却为章太炎所反对,(43)其理由同样是基于国家的建立应从秩序和语言、价值的趋同入手,而地方自治则可能造成地区特别是民族之间的疏离,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立。 提到国家认同,章太炎思想的复杂性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章太炎与其他革命党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以鼓吹民族主义而著称的他,对于以民族建立一个国家,以获取爱国之心,以及以国家为单位而造成对别的民族和国家进行侵略和欺压的格局有深深的怀疑。 然而,在找到更为合理的生存形态之前,如果将国家作为一个暂时必须建立的机构的话,那么地方自治可能是危险的,尤其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更为有害。章太炎说: 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阴阳二极,毗阴故更互鄙夷,毗阳故争求和会。在昔魏氏代汉,梁氏代唐,以合为分,以博为俴,则讴歌者有怨志。三国分而晋混一之,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亦有文思憔杀之人,未闻以灭宗为怨,何者?幸同气之和合为一家,不至以弋矛相见也。故当伏其阴极,轩其阳极,令民族亲如昆弟,宁可以联州促其骚离哉?(44) 章太炎虽然在民族观念上与康有为多有不合,但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立场及其理由方面,他们却多有一致,即忧虑地方势力的发展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竞争力。 章太炎最为引起人们疑惑的是他对于立宪制度的否定,虽然有人指出,章太炎之所以反对立宪,其所针对的是晚清满族王朝“仿行宪政”政策的虚伪性,然细考其相关讨论,我们可以了解章太炎所关注的是议会和立宪等制度是否真正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达成国家富强的目的。而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严复所主张的政体进化必臻至议会立宪的一种质疑。在《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一文中,章太炎特意指出,他之反对立宪,与排满等革命活动之间并无关系,而完全是就宪政制度能否在中国推行所提出的独特思考。他说: 原吾辈所以遮拨立宪者,非特为满、汉相争,不欲拥戴异族以为共主;纵今日御宇者,犹是天水、凤阳之裔,而立宪固不适于中国矣。是何也?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耳。其用在于纤悉备知,民隐上达,然非仍封建之习惯者,弗能为欧洲诸国之立宪也。其去封建时代,率不过二三百岁,日本犹近。观其上、下二院所以并设,岂故为钤制哉,藩侯贵族渐替,而为地主握赋役之枢纽者,惟是为重,异于中国所置名号,王侯空无凭藉,故二院不得不同时并立。观其二院并立,而因仍封建可知也。(45) 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欧洲、日本实行立宪致国家富强而认定中国必须推行宪政,现时中国应该推行的政体或许是唐代专制。 综观中外之历史,则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中国欲立宪,惟两汉之世差可,今则时已去矣。诚欲求治,非不在综核名实也。然观贞观、开元之政,综核之严,止于廉问官吏,于民则不为繁苛。夫惩创贪墨,纠治奸欺,宁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于有司者,一丝一粟,有司悉以归之左藏,而监守自盗者必诛,挪移假借者必戮,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至于民间之有容隐,虽时时检括,终于无可奈何。夫如是则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46) 对于立宪制度的解构,更为严密的理论推理来自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一文。在文中,他对于共和政体表示了怀疑,认为原先的主张未考虑到国家的规模,以及选举总统和选举一般议员的差别,而其关键在于民权与民生二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所以,章太炎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第一,选举总统,限制总统的权力;第二,司法和教育独立,总统及行政系统不得干涉司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轻谋反,重谋叛,提倡对国家的忠诚高于对权力的服从;第四,新闻出版自由;第五,实行实物货币制;第六,确定继承法,反对官员子弟经商和商人子弟从政,以防止利益输送。(47) 在章太炎看来,作为宪政之关键的代议制,只是封建制度之变相,并不能真正保障人的权利。“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48)而下院的设计,则与古代问计于民的做法接近,因此,这样的制度对于去封建不远的欧洲、日本而言,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而对于已经取消等级制久远的中国而言,“欲闿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49) 章太炎借用管子“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的话,来说明在超大面积和超多人口的国度,实行代议制所可能带来的困难。在他看来,如果以人口的比例来选举的话,议员数量过多,便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而议员人数过少,又难以真正表达其所代表的人的意愿。如果以纳税的多寡来选举的话,则议员的来源将集中于富庶之地,并使议院成为地主和豪强的俱乐部。因此,革命党虽然主张民权,但民权并不能通过代议制来得到伸张,“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50) 章太炎的这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思想方式,导致他对于国家、社会、政党以及公理等近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本身都产生了一种跨越时代使命的思考,从而使自己由一个革命者,成为了一个具有解构一切政治目标的批评性思想者,甚至对于他所坚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他都有所保留,他在《五无论》中说,“五无”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是人类虽有无涯之智,但其现实的限制颇多,就好像是骑着一头跛足的驴前行,必然受无穷之限制。因此,切近可行的依旧是民族主义。 从某种角度来看,近代重要思想家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无论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公政府”,还是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都期待形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秩序。但这样的理想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所以康有为作《大同书》秘而不宣,孙中山一定要把民族和民权、民生进行平衡。章太炎将国家、群体甚至民族都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存在,因而必然会把社会活动的价值置身于“个体”之上,虽然“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51)这样一个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虚实关系,也体现了章太炎对于国家取向的社会思潮有可能对个体权利造成压制的担心,而国家的建立又是一个不得不然的“恶”,所以,民族主义,甚至复仇主义都被章太炎所坚持,这也构成了章太炎思想的内在矛盾。按汪晖的概括,个体既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的道德资源,也是反现代的。个体一方面构成否定一切普遍性的集体认同的理由,但同时又是章太炎建立民族认同、建构国家的要素。(52)章太炎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双重解构,使他的思想超越了革命者眼前的使命,从而比孙中山和黄兴他们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理念。然而,这样的否定也使其时常脱离中国现实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而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产生思想和策略上的分歧。 在我看来,章太炎对于共相的怀疑,导致他从根本上怀疑西方式的国家和政治模式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这就与严复力图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目标,将中国纳入西方模式有根本的差异。而章太炎对于中国特殊性的坚持,与他作为革命家推翻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目标产生了奇异的矛盾。而在政治组织模式上,章太炎反对议会和自治等新的主张,甚至认为唐代的政治模式最适合推翻清朝之后的新的国家。 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怀疑作为革命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进化”思想。对于进化,章太炎也将之看作人类之“惑”,在《四惑论》中,他先借助质量守恒定律认为,物质之某方面的增进必以另一方面的减损为前提。人类的一切现象也是如此,人类竭尽一切力量追寻的事物首先并非是人类的天性所乐从,即使基于天性,其追求所付出的,往往要超过得到的。更为关键的是,明日是否存在是一个不能确证的问题,因此,明天胜于今天之论当为“戏言”而已。(53)如果明天并不一定胜于今天,那么革命乃至改良其合法性何在呢?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章太炎,作为严复和康有为的论敌,在解构了严复和康有为的方案之后,章太炎自己的方案也日渐哲学化而远离实际,日渐面目模糊。 ①关于严复缘何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翻译《社会通诠》,学界有诸多的研究,相关的综述可参看王宪明先生的描述,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0页。 ②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载《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 ③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④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严复集》第4册,第931页。 ⑤同上,第933~934页。 ⑥同上,第926页。 ⑦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⑧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⑨汪精卫和严复的争论,有一个巨大的背景,即《新民丛报》和《民报》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梁启超等人认为排满可能将建国的事业窄化为“复仇主义”。而在革命派看来,梁启超他们所要建立的国家,即是满清政府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如果参考这样的背景,章太炎对于严复《社会通诠》的讨论会有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比如,在章太炎等革命派那里,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是革命的双重目标。参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部(公理与反公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57~1059页。 ⑩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11)《民报》报馆(编):《民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1页。 (12)章太炎:《菿汉微言》四十九,载《章氏丛书》下册,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949页。 (13)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罗列了中西因自由观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如中国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等等。说到知识方面,认为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虽然严复说只是罗列不同,并无优绌之分,但是其中西文野之分的意味是很明显的,见《严复集》第1册,第3页。 (14)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指出,所谓的公理,是以自己的学说为公,并非所有人所公认。“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陵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同样,章太炎还否认了进化与进步的对等。 (15)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23页。 (16)同上。 (17)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231页。 (18)同注(15),324~325页。 (19)同注④,第923页。 (20)同注(15),第330页。 (21)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转引自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129页。 (22)王宪明教授通过对严复所翻译《社会通诠》的文字的比对,发现“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家长’、‘群体’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严复在《社会通诠》正文中所加出的与原文没有对应关系的‘民族’以及按语中所提到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基本都是在‘宗法’、‘宗族’、‘家族’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而与后来流行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完全不同”。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121页。 (23)同注④,第925~926页。 (24)“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中国自与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载《严复集》第1册,第148页。 (25)同注(15),第331页。 (26)同上,第332页。 (27)同上,第333页。 (28)章太炎在《訄书·序种姓上》中认为当下欧美区分人民,或以国民,或以族民,其有不同的旨归。国民是就国家而言,而族民则是以种族而言的。对于种族,章太炎主张一种“历史民族”的观点,认为民族并不完全依赖于血缘,而是因为战争、游牧等原因,不断融合,“各失其本”。“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载梁涛:《〈訄书〉评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29)同注(15),第334页。 (30)同上。 (31)同上,第336页。 (32)同上。 (33)同上。 (34)同注③,第169页。 (35)严复在《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一文中说:“夫中国自三古洎兹,所以治其国者,虽道揆法守,运有污隆,固无一朝非为专制,而专制之治,又非泰西之所未行也。国小民谗,行之不胜其弊,以千余年之蜕化,乃悉出于立宪之规,而国以大治,称富强焉。夫政治之界,既专制先有,立宪后有,则可知立宪乃天演大进之世局。列邦异种,林立地球,优者以顺天而独昌,劣者为自然所淘汰,此非甚可惧者耶!由此言之,将无论中国民智幼稚如何,国家旧制严立何若,一言求存,则变法立宪不可以已。”此文最初发表于1905年9月20日至10月4日之《中外日报》,载《〈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页。 (36)同注②,第147页。 (37)同注④,第933页。 (38)严复:《〈法意〉按语》,载《严复集》第4册,第972页。 (39)同上,第981~982页。 (40)同上,第982页 (41)同注(17),第161~162页。 (42)同注④,第932~933页。 (43)章太炎固然反对地方自治,但认为其要好于立宪。“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在章太炎看来,唯一可以使中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则是民族精神,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 (44)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05页。 (45)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76页。 (46)同上,第378页。 (47)同注(44),第306页。 (48)同上,第300页。 (49)同上,第301页。当然,严复和章太炎对于中国人是否“平等”有不同的看法,在严复看来,“盎格鲁以最自由而平等。泰东以无自由而亦平等”。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严复集》第4册,第935页。 (50)同注(44),第306页。 (51)章太炎:《国家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7~458页。 (5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12~1013页。 (53)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1~454页。标签:严复论文; 章太炎论文; 胡汉民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汪精卫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民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