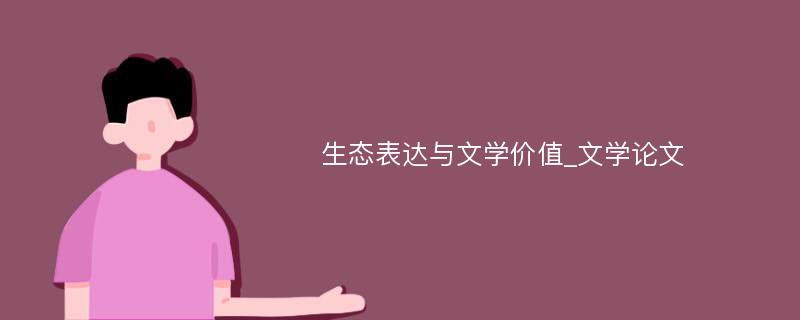
生态表达与文学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人们认识到应该是人类重新走进自然的世纪。实际上,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产物,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生存环境,工业文明把人类逐渐装置在阁楼中无疑是人类自身的悲哀。与此相适应,人类的文化也渐次步入工业化的轨道,文化的内容被工业化的浪潮充斥,越来越缺乏自然生态的宁静、和谐与深刻内涵。于是,人们面对拥挤的空间、滚滚的浓烟和铺天盖地的糟杂而焦虑,面对被工业化炉火烤焦的文化而困惑。它使我们认识到,文化要重新获得活力和丰富内涵有必要对工业化进行反叛,回归自然。
一、文学的视野
文学自产生以来,人们对文学的思考、界说可谓汗牛充栋。文学是什么?权威的概括是,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应该是生动的、深刻的。问题在于,文学究竟应该反映哪些社会生活?长期以来,我们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属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学对自然的深刻关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表述没有问题,但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全景式的,作为整体的文学概念,文学反映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而不是残缺的生活。
自从有了人类,自然与社会既是矛盾体,又是关系体。并且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类生存的环境有社会环境,还有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改变可以随时改变社会环境。因此,虽然我们不否认社会环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不能否认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动性,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还是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说到底,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在社会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归之于在自然界的生存。其实,人类在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早期对自然的崇拜看,各民族都曾经把自然作为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因而高度关注自然界的变化,以各种方式祭祀、祈祷、许愿,希望自然界能遂人们的意愿,带给人们安康和幸福。中华民族更是高度重视自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除了对自然物象的崇拜之外,追求“天人合一”,人的生存状态和自然的存在状态的和谐。当然,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期待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和科学技术还没有起步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科学的、理性的高度,但是,重视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把自然作为人类生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在今天仍然是正确无误的。
近代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科学技术的进步撩开了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自然的重要性不再是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仅仅把它当作工业发展的资源和构筑现代化的材料,因而不需要再崇拜、护佑,只需要掠夺和索取。于是乎,自然的主体性在人类的视野中已经完全丧失,人与自然的关系俨然成为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基础和价值倾向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而且,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率先发展,使得这种意识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严重阻碍了人类通往自然的思维之路。以现代科技支撑的工业革命可以改变一切、造就一切,甚至可以造就第二自然。在现代科技面前,自然是苍白的、软弱无力的,人们需要它时,它便是资源,不需要它时便无关紧要,自然的灵性完全被泯灭。现代工业造就的景观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切,人们在对它津津乐道的同时,思维的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为其所左右。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学中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工业中的文学,文学在现代工业的熏染中原有的清纯的自然美越来越难以看到,充斥其中的是越来越多的浓烟、糟杂和人们心头永远抹不去的无休止的焦虑。
当然,文学为现代工业的这种献身似乎也是出于无奈,一则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如左,文学就不能如右;二则就如现代工业为社会创造金钱一样,现代工业也同样为文学奉献金钱,因而文学就不能离开现代工业。不过,文学如果一味这样被动地依附于现代社会,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就无从谈起。就如我们一贯强调的那样,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人类全部的生活,而不应该是某一部分社会生活,文学关注的应该是人类所有的生存状态,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发展环境。同时,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能动地反映,不是被动地反映,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思维空间。文学犹如社会的一面镜子,既能映照辉煌和美好,又要透视悲惨和丑恶,既要看到历史的可能,又要看到历史的不可能。因此,文学作为人类人文理想的结晶,既要充满强烈的热情,又要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甚至应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巨大的穿透力。一句话,文学应该拨开、穿透社会生活中的污泥浊水,展示人类纯美、洁净的生存空间。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畸形发展中对人类和人文精神的漠视,文学的任务应该是透过工业社会的纷繁,始终关注人性和人文精神,追寻人类真正的诗意生存空间,满足人类的生态期待,为人类提供绿色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意境。这才是文学应有的视野。
二、文学的生态表达
实际上,文学对于生态的表达即是对人自身的表达。从生态学的角度讲,我们生存的地球是所有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的地球,人类不能独占,而只能与其他生物共享;同时,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共同组成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多元生存、相辅相成的系统,既不是惟其他生物需要人,而人不需要其他生物,也不是惟人需要其他生物,而其他生物不需要人,任何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是这个系统平衡的砝码,失去任何一个砝码就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因此,人类作为一个存在的种类是地球上自然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物种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生态要素。人类早期虽然不能站在这样的高度这么理性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在人们朦胧意识里,对待自然却比现在的人们看得更重,以至于达到神秘膜拜的程度。自然就是天,自然就是地,人类须臾不能离开。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一切,没有自然就没有了人类的生存。
因此,人类启蒙之后就虔诚地崇拜、祭祀自然,热情地讴歌、礼赞自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情感的花朵,是人类讴歌、礼赞自然的主要形式。譬如中国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西方的亚当、夏娃等神话故事,应该是文学对自然生态最早的关注和表达。其后,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人们在实践中对自然的行为感受和心理感受的丰富,文学对自然的面貌、情态、智性、灵性的表达逐步深入、细腻、拟人化、审美化。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诗经》就不仅有对政事、世风、民情的记录,更有对自然风光的生动描绘和深情赞美。如《蒹葭》,诗中以物喻人,以人应物,物美情长,人物情景交融,具有深邃隽永的审美境界。
屈原的《离骚》虽然在反映现实的黑暗的同时表达作者的爱国之情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作品整篇铺采,以香花喻美人,以物象喻情志,人性与物理、人品与物品合一,可谓开人与物互喻之先河。自此以后,对自然生态和自然神韵的表达便如初日之朝霞,蔚为大观。曹植的《洛神赋》借神话传说,极尽描摹、张扬,把洛水迷人的自然情态人化、神化,使客观的自然状态生发出灵性。陶渊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作家中少有的对大自然最为钟情、且对自然生态表现得最为深入、最为完美的作家,他的《桃花源诗并记》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没有被任何尘世侵染的、近乎完美的、完全自然生态化的理想世界。他在《归园田居》中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达了永“返自然”的心志。而其《饮酒》(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表明作者彻底回归自然之后,自己已完全融入天籁,作者深悟到,大自然不仅充满美景、天趣,而且充满真情真意,真在自然,善在自然,美在自然。
到了唐宋,对于自然美的表达更是异彩纷呈。孟浩然的《春晓》,王维的《山居秋暝》和《鹿柴》,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柳宗元的《江雪》,白居易的《赋得古原送别》,杜牧的《山行》,这些所谓的山水诗、田园诗借鉴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写意手法,对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做了简要勾勒,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悠美深远的自然图景,妙理横生,反映了当时人居生态的那种令人惬意的状态。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运用更加细腻的手法把自然的情态和灵性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人是景之性,景是人之容,人融景中,景为人生,人与景达到高度的和谐。由此可见,唐宋时期文学对于生态的表达达到很高的境界,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生态表达的传统,为后来的文学家们效法、追寻。
当然,随着宋明以后市井文学的兴起,文学的生态表达并没有像唐宋时期那样形成壮观的气势,但仍然有不少上乘的作品熠熠生辉。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谓绘景写生的经典。到了现代,新诗和现代小说的诞生,文学的生态表达的空间应该说更为广阔。在现当代文学中,主事生态表达的文学作品很多,其中也不乏佳作。如朱自清的《绿》对梅雨潭的绿的描写,俞平伯、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对于秦淮河风景情态的抒写,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对于湘西迷人自然风光的描绘,张承志的《黑骏马》对于大西北少数民族区域自然风光、文化内涵的表现,等等。不仅续继了中国文学生态表达的传统,还体现了现代人的生态意识。
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由于所受影响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以及语言体系的不同,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西方文学也有非常成功、非常精彩的生态表达。我们仅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作品表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人生。但我们读了作品之后会分明地感受到,克利斯朵夫伟大不朽的音乐创作既是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的积淀,又是他所处的生态环境哺育的结果。当他匍匐或静卧在莱茵河畔聆听着波浪的翻涌、体味着大自然的静谧与神奇、感悟着内力和外力的冲动,美妙与神圣的音乐分明在天籁和他的心灵升腾。小说运用3段文字描写了克利斯朵夫儿童、青年、成年时期对于大自然的感受,也是自然在他心中酝酿、升华为音乐的过程。在这里,自然、生命、艺术、美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作品体现了作家严肃的批判精神,作者不仅对战争、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而且对西方日益泛滥的工业社会生态观表明了鲜明的态度。作者借助克利斯朵夫的思维反思道,即使儿童对于自然的破坏甚至对虫豸的摧残都是“犯了凶杀的罪”,这不仅使作品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了深刻的生态认识意义。
三、文学生态表达的价值
通过以上中外文学作品的回溯考察,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感受到生态表达对于文学的意义和审美价值。那么,为什么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专注于生态表达?生态表达究竟如何让文学产生了如此大的魅力和审美价值?我们仍然需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起。
人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追问,但实际上却值得重新审视。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但就人的本源而言,人是自然的人,除了具有思维能力以外,与其他动物、甚至与虫豸等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人既存在社会属性,而归根结底又归类于物类的自然属性。人既然最终归类于自然属性,就必然从属于自然的法则,并与自然界其他物种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序列组合和内在结构规律。自然界存在和生成美,人类社会发生和形成审美。而审美从根本上说是人思维活动和智性的产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然的原因。因为人的思维、人的活动、人的价值判断总是体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我们知道,美是客观与主观、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概念。应该说,美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自然美更是如此。我们不否认人类能够创造美,如人们身上体现的懿德、善行,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等。但在人类的视野中,许多美的形式甚至美的内容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原因在于这种美的形式和内容合乎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规律性,因此,人类并不能随意否认它们美的属性。
审美,体现了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与和谐。它根植于人与自然的相通性和人体自身的生理结构。人们赞美女性体型的曲线美,古希腊的雕塑多呈S型,画家荷加斯认为一切线条中波状线最美,何以会有这种共同的对“曲”的钟爱呢?原来,作为生命基础物质的DNA分子就是一种卷曲的螺旋或双螺旋结构。音乐美的内在秩序也与生理密切相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数列结构,其鬼斧神工之妙当是表达了生命的节奏。另据介绍,有的科学家把DNA分子四种碱基T、G、A、U按照配对原则构成的螺旋结构进行处理,以每个碱基代表一个音符,结果发现竟是一首极为优美的乐曲。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儿,人体的生理结构源于宇宙的普遍秩序。“曲”可能是万物形成和变化中的一种普遍状态,我国古代的“太极图”非常精妙地表示出生生不息的宇宙图景。现代科学的相对论证明,时空是弯曲的或卷曲的;弦理论揭示,基本粒子不是点状而是弯曲或卷曲的小弦。宇宙大化也许是无声的乐曲,毕达哥拉斯早就推测宇宙存在一种音乐和谐,中国古代的哲人也曾意识到“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大大推进了“日心说”的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坚信宇宙存在着“数的神秘性”,据传他甚至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而谱写了一首乐曲。因此,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并不是无稽之谈[1]。
由此可见,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讲,自然的美是现实存在的,虽然由美到审美需要人类的感知,但由于人的生理结构与自然的普遍秩序的相通性,这种感知是容易产生的。文学是人类创造的艺术美。艺术美与自然美某些内在的一致性,拉近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对于自然生态的表达,实质上是为艺术寻求美,也反映了艺术美与自然美走向内在和谐一致的趋势。自然审美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形态,人类在自然审美活动中产生了形式感,实现了由耳目快感到心理快感的飞跃,培养起对现实对象超物质功利的精神性审美。自然审美也是人类最高的审美境界,它可以拓展和提高整个审美活动的精神品格。自然审美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审美不仅仅是逸致闲情,首先是更直观的生存状态——生态美问题。生态美是自然审美的当代现实形式,它既是人类起码的自然生存条件,又是人类生活美之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们高尚的精神生活,发扬自然审美精神符合当代人类文化主题[2]。
因此,生态表达是文学的本质需要。其一是文学的主体对象——人的需要。文学是人学,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属性,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文学对社会的表达是人回归社会属性,对自然的表达则是人回归自然属性。其实,无论从人的社会需要还是从人的物类生理需要,人类都离不开自然生态,因为人是自然中的人,社会也是自然生态中的社会。严格地讲,人只有恢复原本生存状态,回归自然的原生态,才是完整的人。其二是文学自身的需要。文学要创造艺术美,而艺术美的产生并不仅仅来源于人类自身。人类所处的自然界存在着取之不竭的美,而自然的美又是最原始、最本质的美,因此文学向自然寻求美,从自然中选择审美对象,是文学创造艺术美的必须。其三,是现代人文精神的内在要求。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有太多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在人类今后的前进过程中需要更自觉地遵循人文的理念:既要关照人,又要关照自然,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承载着重要的人文使命,在传达人类的人文精神方面具有极大的丰富性。文学承载的这种人文使命和自身的特性要求文学不仅对人而且对自然充满自觉的关怀。否则,文学将会丧失应有的人文情怀。因此,文学需要以更丰富的自然大化的内涵充实自己。这就难怪文学还在萌芽时期便以自然表达为开始,此后荦荦大端;更难怪人们对于文学的生态表达那么钟情,每每手捧或咏读着那些自然美的篇章爱不释手,回味无穷。原因在于人类从中找到了最伟大、最深邃的美,找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这便是文学生态表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