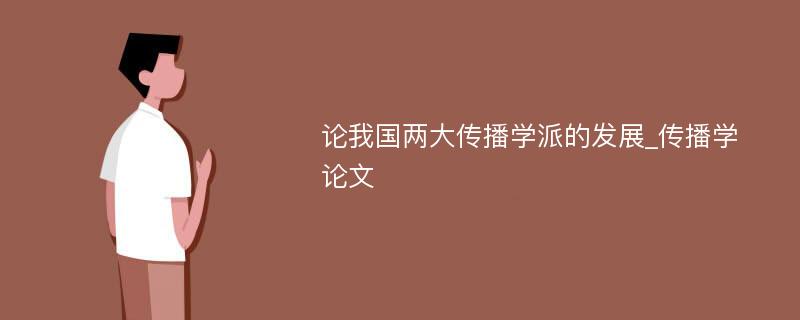
论“两个传播学派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中国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2(2011)07-0006-07
2011年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入学考试中有一道题,要求论两个传播学派在中国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应该从中国是否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派别这一前提谈起,毕竟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学派在中国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是否有传播学派
(一)何为学派?
《学派的天空——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群落》一书在开篇界定了“学派”的特征:
其一是有核心的代表人物,以及围绕着这些核心人物所形成的特定时空的学术思想群体。
其二是共同拥有近似的学术精神,其学术信仰与倾向也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特殊的学术风气。
其三是由学术精神衍生而出相应的学术方法,这种学术方法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切入对事物进行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观照世界的新的视野和新的认知可能。
其四是由上诉三点所产生的经典理论文献,每个学派既有代表性的中心任务,也有体现其核心主张的著作,它们都是一个学派所必需的构成因素。
此外,学派一般有一定的依托空间,它们或者是某个地域,或者是像大学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甚至也可以是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家族等。
可以说,以上五个方面,大致上可当作学派存在的验证标识,它们也因此构成了我们界定“学派”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①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学生罗尔夫·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导言中也对“学派”典型特征作了总结:
1.一个研究机构。
2.一个思想上的超凡人物,对新理论范式抱有信心,能够,也愿意和够格的学者合作。
3.一份宣言。
4.一份新范式。
5.学派研究工作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②
综上,中西关于学派特征的看法几乎一致:学术集体,既包括有领军人物,也包括依托于某个研究机构的学术群;有以宣言或其他方式阐释学术精神、学术信仰与倾向;有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方法;以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方式汇集的理论文献和学术成果。
所谓学派,应该有“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这些思想成果和所依托的一定的空间相结合,是学派存在的必需,因此也成为直接验证是否构成学派的充要条件。
(二)西方传播学派的特征对应
西方传播学派派别众多,上述学派特征可以从各派别一一找到印证。
在学术集体上,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梯队明晰,虽然期间不乏内部分歧,但至少在“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③之前,由诸多学者共同构建和发展的批判理论将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汇集在一起,构成一个学派。而理查德·霍加特与雷蒙·威廉斯以及后来的霍尔成为伯明翰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从初期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到美国时期提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回到德国时期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④以建立社会批判理论为目标的学术信仰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伯明翰学派严守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⑤以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宗旨,为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寻找到一个立足点。⑥
法兰克福学派遵从共同的学术范式:“作同样的理论假设,提出类似的问题,都受到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辩证哲学的影响。”⑦而伯明翰文化学派采用一种文本阐释和社会语境阐释混合的文学阐释的方法,一种深层的文学研究,即人类学的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依托社会研究所,伯明翰文化学派依托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皆著述丰富。
拉扎斯菲尔德无疑是美国经验学派领军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吸引了大批学者。经验学派作为学派在结构上更松散,但更具一致性:坚持将社会视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和平衡的有机生物体,以定量和统计为主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范式上坚持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以及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范式。
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虽然也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提法,但“正如莫斯可所指出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所具有的明显特征就是它不像文化研究、行政学派等传播研究领域一样形成了标志其作为一个研究流派的研究场所,也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许多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取向研究的学者,从未声称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因此,如果按照通常的标准,似乎很难称之为一个学派”,虽然“这些散见的研究所具有的鲜明的研究起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取向”。⑧
(三)中国传播学领域:学派与学者的差异
面对西方传播学派明晰的学派特征,很难将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学者的活动界定到学派的层面,两者间存在学派与学者的差异,即学术团体与个体的差异。
行政力量是大学研究机构运转的必需,无论西方还是我国,传播学者大多隶属于大学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都是核心人物借助行政力量将具有一致学术精神、信仰与倾向的学者招募在一起。这是构成学派的重要基础,也由此促成群体与个体的差异,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批判理论是多么不统一,它都很特殊地汇集在社会研究所这个外在形式之下,汇集在一种植根于反资产阶级情绪和承担批判社会之使命感的发展欲望之下。”⑨
我国大学内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徒有类似外在形式,无类似统一学术精神。即使有诸多学者名列其中,在学术层面,群体是形式的,个体才是实质性的,彼此间并无以共同旨趣凝聚成群的意愿,更无意于以管理型学者的意识和身份确定某一研究任务,那种如同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社会研究所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的任务要求,以振臂一呼的方式招募并培养杰出学者的学派意识和行为在我国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都尚不明晰。这种个体性导致没有所谓的领军式人物,更没有围绕其周围的同行者以及梯队式接班人,所谓研究机构,至少在学派意义上毫无作为。
这种学派与学者的差异也同样体现在学术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无论批判学派还是经验学派,有稳定一致的研究对象、倾向与方法,而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在方法和范式的特征也是个人化的,甚至在个人化中尚缺乏稳定和一致性,因为极少方法和范式是与所谓学术精神相关,甚至从后者中衍生出来的。
学术团体与个体差异之下还暗含着条件与现状的差距。这将是本文第二和第三部分将论述的方向。
传播学派的之所以存在与不存在
从学派的特征仅能做出存在与否的判断,本小节将从历史与现阶段的条件差距说明存在与不存在的必然性,即“之所以”。
(一)学派的出现往往暗合了一定时代的历史语境及其要求,传播学派的出现也是如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纳粹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霸权。60年代末欧洲学生运动失败之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一统天下,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法西斯主义成为20年代开始研究所主要关注的问题,1933年美国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化的强烈社会反差以及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引发的对消费资本主义和异化物化的批判也成为那一历史语境下的学术要求。⑩
伯明翰学派的出现与英国战后的社会与思想状况息息相关。从社会与文化上看,文化研究的出现可看作与当时英国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的直接应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 Bhattacharyya曾在访谈中谈到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包括1968年革命、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11)
批判学派建构的批判理论“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继续彻底评判。他们反复探讨、苦苦追寻的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12)其目的是希望它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制定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但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延续学派的中心任务似乎不太可能,当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自身内部的时候,我们缺乏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对等批判对象,且不说忽略了研究的时间差。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完全以商品形式提供消遣手段,从而引导消费者同现存社会整体保持一致的观点,与我们学者恰好维护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社会体制的出发点之间看似找到了交集点,但是面对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批判什么呢?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将意识形态看作是被广泛视为正确的错误信仰、一种功能性的错误信仰,因为它能使实际上属于社会的、人为的,因而原则上具有可变性的机制显得恒定而自然,或者它能使实际上服务于一小部分阶层利益的机制看起来是为每一个人谋福利的。(13)仅仅在意识形态这一批评对象上我们就可以预见到批判挪用的不现实。即使文化工业这一最容易被看作促成理论挪用与研究对接的批判对象,其提法的成立与否也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因为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首先不是“文化评判”,“它是对商品形式的最新社会性呈现方式的批判,要根据社会文化现象的表面情况来把握自我变化的社会的结构性变迁”。(14)
法兰克福学派“植根于反资产阶级情绪和承担批判社会之使命感的发展欲望之下”的批判理论纵然不统一,至少还能汇集在一起,而我们在延续批判学派的脉络逻辑下,找不到自我批判的根基,更无法形成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著述正是因为其符合历史语境的现实性而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我们的现实性也应该与我们所在的历史语境相吻合,如果挪用西方理论,那首先必须是在同一语境下。当哈贝马斯在追求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的同时兼顾现实感,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对于其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从而有发展余地的可能性进行有限度肯定的时候,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延续西方批判学派的中心任务更不现实。
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最强有力的批判学派,“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学派的内部分化甚至衰落将不可避免,尽管其思想遗产的影响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15)
(二)学派的产生有其内在理路。
“我们说某一学派的形成,其思想主张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的。”(16)
欧洲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孕育了我们在狭隘意义理解上的西方传播学派,也成就了它们作为西方重要社会哲学流派的存在,构成了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因为立足于传播学角度,我们可能轻易将这些学派看作是属于且仅属于传播学领域,忽略其社会哲学流派的身份,而后一身份恰恰比传播学派的标签更具内在性。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补充并改造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在其中注入了精神分析这一相对新生的学科,以及来自德国社会学、人类学与非主流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的敏锐洞见。(17)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源自对弗洛伊德以及拉康、齐泽克精神分析学的援引与整合,像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南湜说的,正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援引与整合,法兰克福学派才形成了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核心——意识形态批判。因此,要探析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就不能离开它的意识形态批判,而要探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就不能绕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8)“弗洛姆经过精神分析的社会化修正对工业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的揭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运用精神分析对同一性思维逻辑强制性的批判,还是马尔库塞透过精神分析对工业社会一体化统治的解蔽,哈贝马斯通过精神分析的重建对扭曲的交往的探察与修复。”(19)
法兰克福学派在科学伦理思想中对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韦伯的经济合理性伦理观、卢卡奇物化伦理观与科学伦理观以及海德格尔哲学追问的吸纳,构成了其思想谱系的重要来源。比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思想中,在方法论上运用了类似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回溯式的追问,虽然“海德格尔的回溯式的追问主要是语义学意蕴上的,而马尔库塞的回溯式的追问则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蕴。”(20)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的阐释主要是在对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和马尔库塞的科技——社会伦理观评析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21)
西方传播学派本就是哲学流派,哲学不仅是构成思考理论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本身的构成部分。这正是我们缺失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吸纳欧洲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学术的思想基础,但要将它内化到学派的内在理路层面,并不容易,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传播学这个领域。阿多诺在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思想辩证地扎根于德国哲学传统,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连贯性”。这种精神的连贯性对于学派尤为重要,中国哲学自成一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却是走的西学东渐的路数,虽然在追寻本土化的过程中间或有对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照,但离学派构成必需的内在理路相距甚远。
经验学派同样是各种学科杂糅的产物,对于经验学派来说,最重要的范式包括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以及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范式,也就是说,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搭建的理论视野成为经验学派构成自己理论体系和学科价值的基础。而我们惯于将其简化成一种方法即定量方法,切断方法与范式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取其表而弃其源,用一种比西方经验学派更加功利的手法来使用方法,而作为学派必需的理论体系荡然无存。
(三)学派的出现需要外部条件。
“强调内在理路,并不意味着对学派出现的外部条件的重要性的否定。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外部条件有时对于学派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简而言之,政治的开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达、移民的汇聚等,都是促成学派产生的重要因素。”(22)
对于学派的出现,这些外部条件既是一种催化剂,也是一种保障。法兰克福学派在30年代出现与当时德国较之二战时较为宽松的环境不无关系,之后迁到美国不仅有比在德国更多的自由环境,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批判对象。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出现也与英国战后的社会与思想状况息息相关。而2002年伯明翰大学以“末位淘汰”为由关闭文化与社会学系,导致伯明翰学派退出江湖,正是一反例。
我们没有传播学派主要不在于缺乏外部条件,而是与学派产生所需要的内部条件缺乏有更直接关系。与历史语境、内在理路等引起的不同学术界难题的争论和抗衡及其所形成的思想张力对学派形成的作用相比,外部条件是决定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远不是其出现的决定性因素。
学派标签之下的研究差距
无论是局外人贴上还是自居,学派只是一个标签,但这个标签蕴含丰富,甚至像罗尔夫·魏格豪斯评价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标签时说的,“标签本身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了它所标示的思想的影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个影响史已经超出了我们在严格意义上讨论一个‘学派’的范围。”(23)因此当我们讨论“两个传播学派在中国的发展”这一问题的前提即“是否存在两个学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涉及到有无标签之下学术思想、学术态度及其影响上的巨大差距。
(一)建构理论与使用理论之异
理论建构与学派形成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虽然理论建构不一定就构成学派,但学派必然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1937年发表“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开始,理论一直是霍克海默热情关注的问题,(24)也是霍克海默圈子致力的目标、用来描述自己的主要标签。关于理论的目标,“应该具有实践性,而不能是纯理论的;也就是说理论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正确的理解,还应该是创造出比现有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繁荣的局面。”(25)
尽管从4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逐渐对其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没有放弃这个根本目标。他和阿多诺的合作被认为最终产生了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尽管这一合作在“哲学断片”这个暂时形态之后就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这种“理论”还是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招牌。不管怎么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二战之后还都同样相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拜物教特性的批判传统中,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同时也必须给出正确的词语,来打破那种使一切事物——人类、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听命的咒语。(26)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分崩离析,也是建立在理论的分歧之下,所有的研究都从未偏离过理论。
西方传播学派理论在80年代后陆续为我们认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启蒙”与“反思”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这是理论的使用层面,与理论的建构还有距离。可惜的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理论的使用甚至还不及启蒙与反思运动对理论的使用那么具有思辨性和长远性。
使用是为了建构,而且是批判地使用,思辨地使用。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用“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不是其教条形式作为他们的原则——那种教条形式执著于从经济基础、从依赖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27)纵然是像张旭东所说的“据为己有”式的使用,也“必须建立在对西学内在纹理和意识形态含义的全面、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就像要理解本雅明的思路和行文,“只有在社会史和‘形式史’(更不用说两者内部的众多潮流)的错综复杂的交汇点上,并作为这一个特定局势的结晶才能被理解。……在他自己的著作和大量书信里,本雅明对几乎所有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重大问题和潮流都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回应。而他的写作,也正应该放在这个还原的历史语境里来审视。”(28)
理论建构与使用既构成了学派与非学派的差异点(虽然如前所说,非学派也同样可能建构理论,但是建构却是学派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学术思想和理想的差异。
(二)专家的灵魂与有灵魂的专家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过一种“没有灵魂的专家”,这种人作为学者从来不去尝试超越自己狭仄的专业领域。
徐友渔评价哈贝马斯说,“哈贝马斯恰恰与这类人相反。他的研究冲破了学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学者那样螺丝壳里做道场。”因为他的思想体系庞大复杂,涉及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的各个方面。徐友渔甚至认为他的思想可以放到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马克思这个序列中来理解和评价。(29)
像哈贝马斯那样将多个学科的知识精心编织在一起来对重大问题作答的方式在西方传播学派乃至个体学者的著述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将多视角、多学科的方法同时运用于道德、宗教、科学、理性和合理性研究,认为不同学科视角的交叉能够产生新的洞见,这样的见识在一个视阈狭隘、日趋专业化的学术领域内则无法获得。(30)他们对20世纪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的吸纳一点不迟钝于他们对更久远哲学思想的吸纳。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理论活动。
本雅明有四个核心研究领域,即语言理论、审美反思、媒介理论以及历史理论,他深受新康德主义哲学影响;如果没有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先锋派电影等现代主义流派特别是布莱希特的戏剧实验及其理论的贴切领悟和相当程度上的参与,就会低估本雅明艺术、美学理论上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即在形式和政治两方面的激进性。阿多诺作为音乐家致力于一种有关社会整体过程的、跨学科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31)“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雷蒙·威廉斯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32)霍加特采用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运用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的多重视角,把通俗报纸、杂志、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象当作一个个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批评。
经验学派采用的定量和统计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可以追溯到来自19世纪的实证哲学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说的影响。
撇开这些繁复的思想源头和庞杂的著述领域,有无灵魂的鉴定从专家自身的标签上就可窥知一二:哈贝马斯是当代政治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等是闻名遐迩的社会思想家,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新左派思想倡导者。雷蒙·威廉斯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最言行一致、自由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英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33)拉扎斯菲尔德是社会学家、实验心理学家,曾获哲学、人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政治学权力学派的代表拉斯韦尔是政治学家,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美国经验学派的耶鲁学派代表霍夫兰是实验心理学家……即使从这些简单抽象的标签来判断,这些学者应该就是韦伯所说的能够超越自己狭仄的专业领域的“有灵魂的专家”了。而且这种超越不是从传播学内部,也不绝囿于传播学领域。
没有哪一个西方传播学派能比我们更紧贴新闻传播,对象、目标与过程的高度吻合。因为这与我们的知识结构相吻合。除了本雅明曾在媒体(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电台)工作,甚至找不到第二个媒体实践家。即使是本雅明,媒介理论也只是他的研究领域之一,并且他为媒介理论建立起一个反思的立场,为每一个问题建构起错位复杂的联系,“令个别现象呈现为这一力场中的某种星丛的变体”。(34)如果说我们有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常常迷失在所谓的专业领域里。虽然我们深知传播学本就是一门学科交叉渗透的学科,但我们为自己圈定了一个传播学的圈圈,跳进去,就不走出来,仿佛刻意要与传播学接轨、贴上传播学的标签,结果将这条设定的道路越走越窄。
相反西方学者似乎是在学科间游走时漫不经心地对传播回眸一瞥,却留下深远的影响。即使我们经历哈贝马斯生平所经历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我们也难以有足够的思想积淀让它们引发我们深邃的思考。我们对多学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其他学科中拿来东西,尤其是现成的理论,然后回到我们的专业领域里,依然在做原有的东西。如果说“真正的传播学派其实无法从做且仅做传播学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中形成”这一论断有些狂妄无知,至少我们对多学科的理解是偏狭的。我们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窄化为传播学派,将庞杂的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简化为传播学,忽略掉诸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我们传播学者少有深厚知识与思想根基甚至少有涉猎的部分,在“扬长避短”的过程中丢了韦伯所说的专家的灵魂。
(三)“特有的不对应”现象
2008年歌德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办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上,歌德大学哲学系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Axel Honneth)在开幕辞中惊讶于中国同事不关注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而是关注批判理论在社会研究所成立和流亡时期的一些代表,如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唯一例外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这些关注讨论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思想在亚洲地区的被接受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以及他们在今天的亚洲又具有哪些发生影响的可能。”他用“特有的不对应”来形容这种现象:“一方面我们这里恰好在渐渐看到了批判理论在文化指向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目前亚洲则尤其关注着批判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方面。”(35)
一方面,西方学派在不断反省(批判理论本身即具有反思的特征,一种内在的自我意识特征),反思其自身产生的社会背景、自身在社会中的作用、其实践者的意图和利益等。批判理论同这样的反思密不可分。(36)就像霍克海默在晚年对资本主义表示无限的歉意。(37)就像法兰克福学派后来者意识到批判理论“确切地说是灌注着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的体系……整个世界历史往往被用欧洲历史的那一小部分来得到权衡”,因此“即便批判理论继续遵循它本来的目标,即在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极端理性化和社会病理时,它也应该看到,这些将理性推向极致的做法和出现的社会病症也是与不同文化条件、政治体系和经济形式息息相关的。”(38)
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些西方自我反省忽略不计,对其特定局势也忽略不计。
这种不对应其实早就存在,也早就被我们的学者所警觉。徐友渔在为英国学者James Gordon Finlayson的《哈贝马斯》作的序中写道,“由于作者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精髓有深入准确的把握,所以本书的根本特点是论说精到,这个优点对于与诞生哈贝马斯思想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距甚远,对于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而有特定期待并容易产生特定偏见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异常重要。”(39)这段话的“特定期待”与“特定偏见”是对中国学者的含蓄的批评。
张旭东在汉娜·阿伦特的《启迪:本雅明文选》中译本代序“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中关于中国学术的批评却尖刻得多:“那种从不加反思的个人体验和集体欲望出发,将西方理论话语的一鳞半爪拿来当作表达或形式的权宜之计的做法,无论其意象和术语多么新奇险怪,在90年代已难激起读者的兴趣,甚至无法赢得他们的尊重。那种不顾学术、理论问题的内在关联,只用‘激进、自由、保守’划界的陋习,同无视学术的社会政治内涵和意识形态倾向,一味讲求‘纯学术’和形而上‘哲理’的怪癖,一样误人子弟。在严肃的学术探讨内部,这只会造成空疏、混乱和简单化的弊病。最终离开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理论创造,任何方式的搬弄西方‘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潮’都会沦为一种不关痛痒的‘私人话语’,或是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或市场上流通的新的文化资本(或不如说是资本的新的文化符号)。”(40)
虽然他的批评是针对80、90年代的“这一空间和表象体系本身内部的知识汲取、循环、积累和在生产机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背景的,但放在21世纪头十年的当下,这个批评意见并未完全过时,如今一代的心理状态早已不是当时的兴奋、震惊、焦虑与急迫,却依然在跨越西学不同理论传统和意识形态立场为我所用地选择和组合,这些不同的话语也依然可以摆脱其具体语境中的理论和政治切关性,诉诸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人文背景和思想旨趣。我们自己的问题史框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为新的知识话语和文化表述方式找到其现实历史中的坐标和成熟的意识形态立场。
霍耐特为这种“特有的不对应”找到三种彼此互启的解释选择:一是中国学者先接受法兰克福学派老一代的思想,而这些早期代表所披露的由现代化而来的特定倒退和社会病症对不同路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二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被看作是欧洲文化遗产,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披露或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题旨,而是因为他们思想的丰富文化内涵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三是中国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关注或许体现了中国学术知识分子一个不良的自我误读,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被认为是具有澄明问题的威力而被接受,但在事实上却并不真正掌握这样的力量。如果是这样,当今中国对阿多诺、霍克海默或本雅明的关注不经意地与那里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在当今中国强力推行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情况下出现的。(41)
虽然霍耐特并没有对这三种解释做出定论,但对于我们来说,答案比较明朗。而对于他在开幕致辞中的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同事们能告诉我们,批判理论在今天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专研西方哲学的哲学界学者都难以回答,那么对我们传播学学者来说,应该是更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不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诸多理论上我们与西方学者都存在着“特有的不对应”。比如解构主义,我们近20年内对解构主义的追捧不亚于雅克·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的名声在法国开始迅速衰退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对其的热捧,当之后解构主义在北美也遭受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依然如获至宝。理查德·沃琳将解构主义看作是“一种自我标榜为‘批判的’方法论,一个政治和文本批判的榜样,已经迅速腐化为一套普通的学术把戏”,(42)这是我们在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下难以看到的解构主义的终极自相矛盾的论题事实。
有没有学派固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创建我们自己好的社会理论,抑或好的传播理论。所谓好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何种程度上该理论能够与先驱理论和竞争理论相衔接,既阐明、保留它们的成功之处,又能补救它们的缺陷。(43)对于我们的传播学来说,衡量学派是否出现,至少产生这样一个好的社会理论是必需的判断标准,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
注释:
①艺衡(主编):《学派的天空——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群落》,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Yi,Heng(ed.),The Sky of Schools:the Thoughts Communities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History,Nanning,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9,pp.5-6.(in Chinese)]
②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Wiggershaus,R.,Die Frankfurter Schule:Geschichte,Theoretische Entwicklung,Politische Bedeutu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p.5.(in Chinese)]
③同①,第243页。[See 1,p.243.]
④同①,第242-243页。[See 1,pp.242-243.]
⑤张华(主编):《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2-273页。[Zhang,Hua(ed.),Review about the Leading Persons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Jinan,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2-273.]
⑥同①,第274页。[See 1,p.274]
⑦詹姆斯·戈登·芬利森:《哈贝马斯》,邵志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页。[Finlayson,J.G.,Habermas,Nanjing,Yilin Publishing Press,2010,p.1.(in Chinese)]
⑧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1页。[Liu,Xiaohong,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Shanghai,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2007,p31.(in Chinese)]
⑨同②,第856页。[See 2,p.856.]
⑩同①,第244页。[See 1,p.244.]
(11)同⑤,第273页。[See 5,p.273.]
(12)同①,第244页。[See 1,p.244.]
(13)同⑦,第11页。[See 7,p.11.]
(14)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鲁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Schweppenhauser,G.,Adorno,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p.93.(in Chinese)]
(15)同①,第6页。[See 1,p.6.]
(16)同①,第7页。[See 1,p.7.]
(17)同⑦,第2页。[See 7,p.2.]
(18)王睿欣:《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北京,红旗出版社,2008年,序。[Wang,Ruixin,Psychoanalysis and Frankfurt School's Ideological Criticism,Beijing,Hongqi Press,2008,Preface.(in Chinese)]
(19)同(18),第231页。[See 18,p.231.]
(20)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Chen,Aihua,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cientific Ethical Thoughts of Frankfurt School,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07,p.333.(in Chinese)]
(21)同(20),第346页。[See 20,p.346.]
(22)同①,第7页。[See 1,p.7.]
(23)同②,导言第4页。[See 2,Preface p.4.]
(24)同②,第9页。[See 2,p.9.]
(25)同⑦,第3页。[See 7,p.3.]
(26)同②,第9-10页。[See 2,pp.9-10.]
(27)同②,第9页。[See 2,p.9.]
(28)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页。[Arendt,H.(ed.),Illuminations:A Selected Collection of Benjamin,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8,p.4.(in Chinese)]
(29)同⑦,前言。[See 7,preface.]
(30)同⑦,第2页。[See 7,p.2.]
(31)同(14),第5页。[See 14,p.5.]
(32)同⑤,第269页。[See 5,p.269.]
(33)同⑤,第24页。[See 5,p.24.]
(34)斯文·克拉默:《本雅明》,鲁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Kramer,S.,Benjami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p.111.(in Chinese)]
(35)霍耐特:《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王才勇译,《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第21页。[Honneth,A.,"Frankfurt School and China:the Opening Speech for 'Frankfurt School in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Modern Philosophy,2009,No.1,p.21.(in Chinese)]
(36)同⑦,第3页。[See 7,p.3.]
(37)同⑦,序言。[See 7,preface.]
(38)同(35),第20页。[See 35,p.20.]
(39)同⑦,序言。[See 7,preface.]
(40)同(28),第5页。[See 28,p.5.]
(41)同(35),第21页。[See 35,p.21.]
(42)理查德·沃琳:《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页。[Wolin,R.,Heidegger's Disciples:Hannah Arendt,Karl Lowith,Hans Jonas,and Herbert Marcuse,Nanjing,Jiangsu Education Press,2005,p.16.(in Chinese)]
(43)同⑦,第18页。[See7,p.18.]
标签:传播学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霍克海默论文; 阿多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