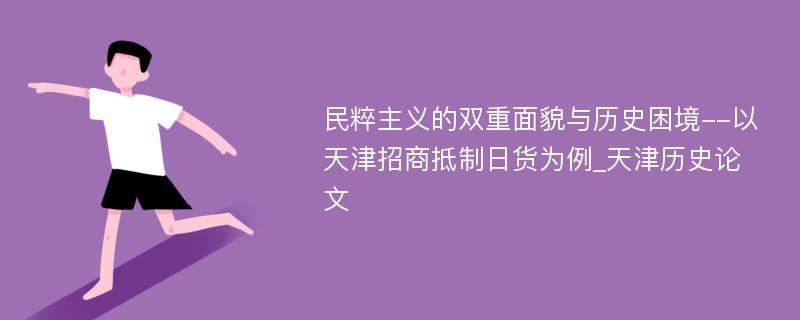
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与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天津论文,为例论文,抵制日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之后,各界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经济绝交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雷麦在1933年即对“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之经济效果进行了极富成效的研究①,稍后,国人亦开始关注其经济效果②。相对晚近,日本学者也涉及此一主题③。国内学者则大多以“反帝爱国运动”的架构来言说书写这一历史事件,往往聚焦于学生和工人两大群体,相对忽视经济绝交运动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商人,而即便有所着力者,也多以上海商人为考察的个案④。本文选取学界较为忽视的天津商人为考察对象,以天津《大公报》和天津商会档案资料为中心史料,对商人的言论作为作一必要的梳理,并尝试作出移情式理解,从而为把握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取向以及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提供个案支撑。
一、民族主义诉求:自动对日经济绝交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战争诉求几乎成为各界民众的集体意识,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责难甚厉,但津商则较为保守稳健。1931年9月23日,天津市商会召开会议,认为“自日军占据东北要隘后,本市谣言甚炽,人心恐慌,倘不急为设法维持,难免宵小扰害地方”,故推举银行公会会长卞白眉等5人于次日赴市府谒见市长,“陈述一切,并请市府对于本市治安方策,妥为筹划,布告民众,以安人心”⑤。卞等谒见市长之后即转告各商:“必须力持镇静,勿得轻信谣言,自相惊忧,是为至要。”⑥可见如何稳定地方秩序,乃是事变之初津市商人关注的焦点所在。
10月2日,裕元纺织公司投函天津《大公报》,宣称自定于9日起停购日货,所需一切原料亦尽量采用国货,并谓“此举自顾于事实方面无甚裨益,即对于日方亦无关痛痒。惟全国各界苟能一心一德,杜绝购买,亦定能收效,希全国同胞一致猛醒”⑦。此为事变后天津商界对日经济绝交的最早表态。4日,天津市救国会召集钱商开会,议决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各商均不与日本银行及各商往来⑧。稍后,钱业公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的简略方案:“有与日商直接往来者,自本日起,一律找清;有与日商买办往来者,自本日起,一律找清;对于经营日货各商号,自本日起,绝不垫款;凡日本各银行钞票,一律拒绝收受;不受日货押款。”⑨党政力量于10月中旬介入经济绝交活动。16日,天津市政府奉南京行政院命令,转饬天津财政、公安、社会等局,要求他们与市商会组织粮运稽核委员会,俾免奸商任意操纵市价及私运出境。市商会即定18日召集粮商会议,讨论防止私运粮食和抑平米价等问题。市党部亦组织经济绝交宣誓活动⑩。
市商会的经济绝交行动似乎是遵命而行(11),但“商人自动经济绝交委员会”显然更加活跃。该组织成立于万宝山事件之后,其自主色彩要浓于市商会。万宝山案之后天津的经济绝交运动,基本上由商人自动经济绝交委员会组织进行。“九·一八”事变之后,经济绝交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抵制日货制度也基本上是承继先前的日货通行证制度。我们可对其颁行的日货登记条例与惩罚条例稍作考察。日货登记条例共14条,适用范围是10月18日前天津各商店已进未售之日货。对于此类日货,该条例将其分为绝对禁止与相对禁止两大类别。所谓绝对禁止者,即除了相对禁止者之外的一切日货。对于10月18日以前已购而未到的绝对禁止之日货,要求各商必须设法退还,若万一无法退货,即须在11月1日至15日之间到会登记。倘经调查核实,即颁发证明书,各商持证至反日会缴纳货值10%到90%不等的救国基金,领取通销证则可销售。所谓相对禁止之日货,包括日本文化、交通、医药类物品,以及中国工业制造与日常生活必不可少,而一时又无同类国货可资替代的日本所产各种原料。条例规定,对于相对禁止之已进未售之日货,给予半个月的登记期,缴纳5%的救国基金之后则可销售于市。
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则按惩罚条例进行惩罚。惩罚条例共17条,其中主要规定了4种处罚标准。在日货登记期间,尚未发给通行证而私自偷运者,原货充公,并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截止期限以后再私自批购日货者,按货价科以20%以上、50%以下之罚金;日货登记截止以后,如查有隐匿不报、私运私售或其自报实不相符者,或将原货充公,或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对伪造通行证或偷售者,亦按货价科以10%以上、50%以下之罚金(12)。此一日货登记制度显系济南惨案之后所实行的“寓禁于征”制度之翻版。实际上,此前的多次抵制日货的历史业已证明,即便该制度严格执行,亦无法禁止日货的人口与销售。但天津救国会成立伊始,即对经济绝交委员会的存在提出严峻挑战。由此,商人自动对日经济委员会连同通行证制度的废止便注定无法避免。
二、商利自维:封存日货
日货登记尚未进行,经济绝交会即已遭遇“合法性危机”。10月21日,天津市抗日救国会抨击经济绝交会“黑幕重重”,指责自该会成立以来,“市面不见日货减少,反见日货入口增加”,并呈请市党部下令停止该会工作(13)。27日,救国会又指责该会“成绩毫无”:“东北事变爆发以来,反日高潮激荡,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日团体,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我津市商人虽有商人自动对日经济绝交会之组织,而该会一味敷衍延宕,以致成绩毫无,爱国人士啧有烦言。”(14)在救国会的严厉指责声中,经济绝交委员会于23日召开执委会,议决自次日起全市日货一律停止运售(15)。针对救国会对其此前工作的攻击责难,该会公开辩驳:“本会自成立以来,各项工作,无不加紧进行。对于登记检查,并截止日货来津,尤为积极办理。”同时表示:“兹以外患日迫,国难方殷,各地日货,俱已禁止运售,所有本市日货,亦自力求彻底而资抵制,议决自24日起一律停止运售,望本市各商一体遵行,幸勿存心偷运,致遭重罚。”(16)
对其逼迫解散,经济绝交会显然心怀不满,但又不得不屈服于市党部的压力。因为尽管解散要求虽为救国会提出,但直接命令却来自市党部。经济绝交会颇为无奈地表示:奉天津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来电,“令本会即日停止工作,暂交商会接受,自应遵照办理”(17)。“党部令行移交市商会办理,商会乃商人领袖机关,移交自无不可”,但却表白:“商人此种举动,纯为爱国表现。自开始对日工作以来,个人精神之损伤与夫金钱之牺牲,毫不顾惜”,同时意味深长地说道,“救国会要求查办,不无其他用意”(18)。
经济绝交会停止工作后,其制订的有关抵制日货条例亦由救国会所订新条例所取代。10月27日,抗日救国会公布封存日货条例10条,其中主要内容涉及“津市所有日货,一概禁绝出入境;所有国产土货,一概禁绝输往日本;倘为世界各国及中国所无,又为绝对必需之物,或者系中国绝无用途,而又无大益于日本者,可向该会请准酌量通融;天津各商店如果私向日商购货,或将国货售予日商,按其惩戒条例严惩之”(19)。次日,市商会与救国会又议定7条抵制日货办法,对日货封存、检查办法等作出细致规定:“对于货栈所存整件货物,自28日至30日,由商家自行封存,并造具清册呈报市商会,31日由市商会会同救国会派员开始检查,并加盖印记封存;而门市零星日货经救国会检查许可,并用文字标明,暂准销售,销毕之后即不许再销日货。”(20)救国会所订规则显然远比经济绝交会的相关规定严厉激进。对此,救国会自身亦坦承:“此种办法诚为我国民重大牺牲”,不过“当此国难领头,亦不能不忍痛须臾”(21)。诚然,抵制日货对一般国民日常生活均有影响,但商人无疑损失更大,同时封存日货势必牵动整个市面。救国会的抵制日货条例甫一出台,“市面情形,立见紧张,商界尤为不安”。市商会接到救国会封存日货的通知之当日,即召开执委会委员及全市贩售日货之17行商联席会议,讨论应对之法,咸谓“救国会此举,难免发生误会,未来纠纷,恐将不免,但商人亦是中国人,自同俱爱国热忱,与其被动,不与自动,较为妥当”。最终议决由商会主席张品题等访问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要求由商会代为封存。张公开表示:“以天津情形观察,日货实居七八,华界方面实行封存,租界方面毫无办法。商人爱国,不敢后人。倘如此办理,可谓革人生命财产,……本人忝居商界领袖,自必竭尽全力,设法维护,总期爱国运动,与商人无损。”(22)此番谈话,凸显经济绝交运动中存在“国权”与“私利”之间难以两全的紧张关系。
市商会的努力抗争最终有了回报,救国会并未按规定于28日封存日货。商会与党部商得一变通办法,即30日以前封存日货由商家自动进行,自31日起则由商会与救国会检查和封存。门市零售货物于31日呈报商会候查(23)。11月4日,全市日货封存完毕。
封存日货延期数日,且门市日货仍可销售,无疑兼顾了市民生活与商家私利。但年关将至,被封日货的启封问题又被推到了台前。1932年1月初,17行商提出:“际兹旧历年关,为各行齐帐之期,被封货物既多,金融流通,当然停滞”,多数商人恳请市府准予启封,以便拍卖还债。少数日货商更拟假借日人势力,“强行起货”(24)。而救国会则认为“日本侵略益急,抵货运动自宜坚持”,除派员彻查市区日货之外,又公布“处罚扣留日货办法”及“私运日货惩罚条例”,规定:“商人如有私运日货出入天津境内;由日本及中国各商埠购运日货入口;由天津运送日货私售各埠;以国货及国产原料私售日商情形之一者,则处罚从价的50-80%之罚金。倘以日货饰充国货;同一商品私运三次以上;私代日商偷运或私藉日商名义等情形之一,则加倍处罚,处罚完毕,由原商号领回封存,但不得私售。”(25)
实际上,救国会亦曾考虑将日货启封销售,同时征收一定的启封费用。对此传闻,“各商对之多怀观望,……若再收费,则宁愿永久封存,以免受过巨损失”(26)。1月中旬,商人态度更趋强硬,17行商宣称:“如不启封,宁愿焚毁。”(27)月底,市府认为“旧历年关将届,各商困苦已达极点”,准予日货启封销售。2月1日,封存日货全部启封,而反日救国会这一组织亦不复存在(28)。
三、封存日货:言而未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时,天津反日救国会已遵命取消,封存之日货业已启封,经济绝交运动实际上已经中止。事变之初,天津商界的应对之道主要是筹款支援沪战。但日本肆虐上海,而天津日货畅销,此种强烈反差显然不合时宜。战争未及一月,经沪商大力呼吁与津市党部切实指导,天津市商会开始考虑继续抵制日货。一度中止的经济绝交运动又持续但并不激烈的进行起来。
1932年2月19日,天津《大公报》以“淞沪战争中,天津商界畅销日货”为标题,披露天津日货商人进口大量日货的现象。一记者亲至近海仓库及大阪码头调查,发现日本船只载入日货竟达20000余件,进口日货多系华商托日商洋行代办,甚至有改用日商牌号者。文章沉痛指出:“日寇炮击淞沪,凡我国人,莫不发指,誓与偕亡,乃全国视线,方全集中于沪滨,而天津商界乃在此时期,批订大批日货。”(29)次日,天津市商会致函日货商各同业公会:“暴日入寇辽吉,祸我天津,进窥长江,淞沪喋血,今已成不宣而战之局,国家存亡,系于俄顷,吾人苟有一丝国家观念,岂仅经济绝交所能自已”,指责部分商人大批私购日货到津,“实属不顾大局”,呼吁“速勒悬崖之马,赶图结束,万勿再铸大错,致贻后悔,而妨大局”(30)。
23日,天津市党部开始介入抵制日货运动,训令市商会检举贩卖日货之奸商。市党部指责乘机订购与销售日货的津市商人,“既堕民族人格,尤为商界之羞”(31),必须坚决取缔。而市商会亦再次呼吁贩运日货各行商“速勒悬崖之马,免铸大错”(32)。天津其他民众团体以及全国各地的诸多团体甚至国民党党部,亦纷纷谴责天津商界的贩售日货行为,要求坚决对日进行经济绝交。天津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要求对“本市奸商私进仇货,破坏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行为严予惩处(33)。市长周龙光也公开发表看法,认为制裁奸商之法在于国人根本不用日货,从而使商人感觉“滞销之苦”,故而主张“抵货先从本身作起,自然商人受良心制裁”。他虽然认为“官厅因立场关系,未便严厉干预”奸商行为,但对于民众制裁奸商之举,“官厅决不再干预”(34)。显然,周默许甚至可以说鼓励民众对奸商进行制裁。北平民众救国会指责销售日货行为“令人发指”,呼吁天津市商会严厉阻止,“以绝来源而资抵制仇货”。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从媒体得知天津奸商私购巨额仇货之后,斥其“罪同资敌”(35)。上海市商会知悉华北商人贩卖日货的行径之后,分别致电青岛、济南、天津各商会及银钱公会,责难华北商人破坏抵货运动。上海市商会致天津商会与银钱公会的电文中,对天津“日货畅销,且有著名商家,专实营运”之现象“痛愤欲绝”,指出“日人占地三省,炮击沪市,战地平民,伏尸盈万,此情此景,惨烈奚如”,“贵地商界不念同胞水深火热之痛,转为觐颜事仇,分我杯羹之计,讵有良知”,“日人难以暴力禁我抵制,岂能挨户派兵勒索”,希冀天津商界诸公“好自为之”(36)。江苏铜山县卷烟公会要求“对奸商严惩以儆效尤,以谢国人”(37)。
面对天津市商会的频频警示与市党部的严词训斥,津市诸多同业公会似无反应,而绸布棉纱呢绒同业公会认为市商会作为“众商之领袖”,应该早日对全市各业日货商“作一总调查,俾便检举而免分歧”,而市商会常委会议决“所有此项检举工作,仍请各有关系同业公会,各就本业自行认真办理”(38)。市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显然有相互推诿之嫌。
诚然,即便没有抵货规则制约,经各有关组织督责,亦不乏幡然醒悟者。据报载消息,天津日货商批购日货,“不顾国家信义,致颇引起一般人士之反感,全国各处亦纷纷电津责难,市商会亦警告各行商”,部分日货商人公开表示从此“收市”,如在津经营洋广货多年的宫北源丰和商号,与日本贸易关系最为密切,“近国难日迫”,业经市商会多次劝告,“现已毅然收市,从此不再从事日货生涯”,媒体誉其“爱国表现,诚足称道”(39)。但天津的日货大量进口亦为既存之事实。总体来看,“一·二八”事变之后的两三个月之内,沪战正烈,而天津抵货运动却并无进展。面对各界的巨大压力,天津商界开始酝酿具体的抵货办法。
4月25日,市商会如期召集各日货行商讨论抵制仇货的有效办法。商会主席张品题宣称:“各省对于抵制非常严厉,华北情形,亦颇泄沓。倘我津市商界再不积极主张,不惟辱遭各省唾骂,且扪心自问,亦难对良心。本市商民同为国民份子,良能独落人后。”而各业代表虽亦承认“抵货事关救国,凡属国民无不赞成”,但又提出“事关重要,须返本会召集大会,研究有效办法”(40)。此次讨论无果而终。
5月2日,救国会要求市商会“晓喻商家即日与日断绝贸易,现存仇货5月15日前售罄,余者查封”。10日,救国会决定于次日派代表赴商会研究日货封存一事,而市商会则呈请市党部、政府、社会局有关政府机关,请示对救国联合会所提要求的应对之法。18日,部分与日本经济联系极为密切的同业公会,各自表明对封存日货一事的有关主张。海货业公会希望“停缓检查与封存仇货而恤商艰”,杂货糖业公会则提出,日货充斥华北的原因在于东北及沿海各县奸商偷运私售,因此“若将东北偷税仇货断绝来源,则天津仇货不封自绝”。换言之,在杂货糖业同业公会看来,现存日货之封存纯属徒劳之举,当然也就毫无必要。而自行车公会则宣称,对日货早已停止批购,同时提出“上年本市遭两次事变,经济上受无量打击,本业元气大伤,端午节在即,请缓查封”,实则要求至少在端午节这一商业良机之前,不能封存日货。绸布面纱呢绒业公会更加直接了当:“本会对封存日货赞成,惟须将上年批定未退各货售完再行办理,庶于爱国保商两益”。稍后,市商会致函救国会,请求俟端午节之后再行办理登记日货。此处暗示我们,尽量销售现存日货以便减少损失,当属商人之共识。他们并未忘记,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同时也是消费狂欢节。实际上,市政府否定了救国会前此所提方案,宣称此事“关系法律威严、地方治安、商民经济,中央迭令查禁以防滋扰”(41)。因此,救国会检查日货的决定徒具一纸空文。但日货封存一事并未就此了结,中止了两个多月的封存日货问题,随着华北危局的出现,至是年8月又重新提上议程。此一问题,俟另文探讨。
四、“移情”式理解:津商之难境
日货重新启封,标志着“九·一八”事变之后天津商人经济绝交运动之曲终人散。但如果以此而挞伐商人爱国情感之缺失,似乎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不如转而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从而明了众商此举背后的复杂心态。
首先,东北事变给天津商人带来巨大损失。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初期的1个月之内,天津北宁路的商业损失即超过500万元。事变发生之前,北宁路商业颇为繁盛,最旺时期的日营业额达20余万元,而事变发生之后,每日多则3、4万元,少则1万元。据此推测,仅北宁路一地的月损失则超过500万元(42)。东马路各商号直接间接损失也达到40余万元(43)。对于东北事变给津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时人早已洞察:东北变起,“商业大小无间,俱受影响”,仅提花一项,放出未收之货款即达100万元之巨。而石友三之变,日入东北,两次津变等一连串变故,不仅阻滞交通,货源、销售亦多受阻碍。原本依赖秋季新货上市,但“九·一八”发生,“抵制日货风浪渐高,凡行销内地各品,胥有关联”,“百变突起,金融无形紧缩”(44)。
其次,对日经济绝交,进一步加剧津商的经济损失。津商曾经宣称,若不启封日货,则日货商店势将倒闭,此言并不夸张。抗日救国会、检查日货委员会进行日货登记,商家缴纳登记费70000元,当不至于令其有破产之虞,不过封存日货总值达3500万元(45),此则血本攸关。可以说,经济绝交对商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天津匹头业为例,据《大公报》报道,1931年春季的匹头市场平稳,而秋季较春季“胜强数倍”,而因抵制日货,日货销路几乎停顿,国货产品供不应求。因为“国货虽蒙良好影响,实际亦尚未显出成绩”,国货产品种类少,不足以适应社会各方面之需求,此种困境导致各商难以转营国货。在既往抵制日货运动中,因为一经抵制而造成日货供不应求,天津日货转口反而大旺。但是此次不同,“各批发商定货,反行减少十分之六”。缘由在于此次抵制,“系属各商自动原因,半由于爱国热潮,半由于以往各次抵制,假手他人,挫折不堪,不如自动之为愈,开始间召回大阪分庄,停止买进”。加上内地重要乡镇亦有抗日会成立,即使有商人敢从天津购买,亦无法在当地销售。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日商定货难以退还。天津与上海的市场交易规则有异,津地所定日货,如届期不能履行者,日商则即按月利4至5厘收取利息,按照货价逐日计算,尚需负担“栈租火险”。而上海并无此种规例,因而退还所定日货之交涉,远较津市为易。天津匹头“尤为日货之巨销市场”,西洋货已成日货附属品,专营西洋货者,可谓绝无(46),抵制日货之艰难可窥一斑。
再次,日本骚扰天津,酿成两次津变,商人损失尤为巨大,处境更加艰难。据河北省政府秘书张芾棠记载,天津便衣队的暴动导致“一个繁华的天津,一夕顿成死城,即如平日最热闹的旭街,也行人绝迹”,“尤其是日本指使便衣队奸淫抢劫,随处而施,造成天津市面处在恐怖和静止的状态之中”,“整个天津皆为恐怖可怕的空气所笼罩。商店闭门,交通断绝”(47)。从1931年11月8日至30日,事变牵延将近1月,营业完全停顿,收入毫无,开支仍旧,“华界两万商号莫不亏蚀”,平均每号损失5000元,共计损失达到1亿余元,“元气大伤”。诚如《大公报》评论所指出的那样:“矧天津乃商埠所在,社会生活,纯恃贸易周转,事变既作,商业停滞,动脉阻塞,机构失灵,一发所牵,中外同病。地属商场,民鲜蓄积,市况既陷呆滞,物价势必升腾,且又戒严已久,出入艰难,商贾歇业,购买无力,生产消费,两濒绝境。”(48)12月初,天津市商会、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对此“仍觉揣揣不安”:“双方猜疑,是否尽泯,暴徒潜伏,是否不再蠢动,商民惊惧之余仍觉揣揣不安。现在金融濡滞,百业未复,兼之时迫年关,更行紧急,似非亟谋比较的切实保障办法,且长此人心浮动,前途危惧,正难臆测。”(49)翌年春,国联调查团赴华调查“九·一八”事件,天津市政府向各界民众征集意见,市商会特别请求市府向国联强调津变于中国商业及各国商业所造成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之损害”(50),这一事实也从侧面证明事变给商界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巨大。
1932年元旦,《大公报》记者观察到,天津“巨创之后市况异常萧条”,两次津变,不时戒严,导致人心不安,一般市民“如非绝对必需品,均绝对不轻易购置”,而“年关将至,照例年终结账,清算一切。批购货物,又须如期起货,遵约付款”。因此,记者感叹:“虽值兹年关,反增无限烦恼”,“市面景况,大为凄凉,实津市数十年来所未有之景象也”(51)。由此观之,我们便不难理解广大商人为何迫切而强硬地要求启封日货了。时人曾经批评华北商界:“抗日的根本方法,是对日经济绝交,对日经济绝交,是抗日救国的根本武器。”“华北密迩辽宁,闻东北受害之情形,当更为亲切。然9月18日以前,尚有所谓检查日货者,为一时之点缀品,今则反寂然无闻,岂为日人之炮声惊死乎?抑甘心为亡国奴,思为见好于仇,亦表示欢迎乎?不然何以若是之死气沉沉也!”(52)如果能够移情式理解天津商人的特殊处境,此番指责则显系偏颇之论。
近代愤激青年往往谴责“商人无祖国”(53),而在部分学者的解释框架中,所有商人都幻化成了简单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商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只不过是权宜之策的“变态”罢了(54)。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尚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55)。商人亦莫能外。因此,与其试图以某种单一模式来概括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商人性格,毋宁将商人视为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换言之,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经济绝交运动这一近代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核心表达,注定交织纠缠着商人“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在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遭到侵凌之时,商人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无法祛除的历史实在。
注释:
①〔美〕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g press,1933.本文参见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Taiwan,1966年,pp155-231.
②陈正谟:《“九·一八”后中国排斥日货之检讨》,《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1期,〔北京〕中国经济学社出版社1935年版,第71页。
③[日]菊池贵晴:《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对外ボィコット運動の研究》,〔东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第361-424页。
④温济泽主编的《“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对经济绝交运动中商人的言论作为叙述甚简。
⑤⑥⑦⑧⑨⑩(13)(16)(18)(22)(23)(24)(25)(26)(27)(28)(29)(31)(32)(34)(39)(40)(42)(43)(44)(45)(46)(51)〔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4日,9月6日,10月3日,10月5日,10月9日,10月16日、10月19日,10月22日,10月24,10月25日,10月28日,10月29日,1932年1月7日,1月11日,1月11日,1月15日,1月30日、31日,2月19日,2月24日,2月27日,3月6日,3月23日,4月26日,10月22日,1月15日,12月26日,1月15日,1月1日,1月1日。
(11)从1928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为配合其威权主义模式,对天津商会进行了三次改组。1931年2月,在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代表的监督下,天津总商会改组为天津市商会。新成立的市商会,“尽管凭借其在工商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国民党政权多次对商会组织的整顿与干预,一切都被国民党政府统管起来。”可参见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8页。
(12)(14)(15)(17)(19)(20)(21)(30)(33)(35)(37)(38)(41)(49)(50)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0-2403页,第2396页,第2399页,第2403页,第2396-2397页,第2398页,第2396页,第2420-2421页,第2425页,第2426页,第2427页,第2421页,第2425页,第2369页,第2370-2371页。
(36)《申报》,1932年2月27日。
(47)(48)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便衣队暴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第126页。
(52)陈际云:《从对日经济绝交说到中国的商人》,〔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1月5日。
(53)早在济南惨案后国人抵制日货的进程之中,时人分析国货不振的原因时指出:“足以阻碍国货振兴的,就是中国人道德的堕落。……自私自利与偷懒浮夸。……商人们只要自己赚钱,替洋货推广销路也好,做外国银行买办盘剥中国人也好,反正在商言商,什么国家社会的福利,民族的生命,都是迂阔之谈,所以现在一般愤激的青年,甚至高呼‘商人无祖国’。”(参见《提倡国货的理论与方法》,第11-12页,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丛书之九,1928年,浙江省图书馆藏。)但青年学生恰恰是洋货的主要追逐者:“最近教育部曾派员视察上海六所大学之报告,中有各校学生服饰,大同比较朴素,其余大多数习于奢侈繁华,衣履则竟尚新奇,……甚至出入娱乐场所,感受时下习气极深,……至于女生服饰,犹多繁华新奇,……吾早说过,目下社会中最繁华奢侈的,无过于学生,无过于大学生,更无过于大学生中子女学生。所以有人说受教育程度愈高,需用奢侈品愈多,便是推销洋货愈力,……故而有人说,和大学中的女生谈服用国货,等于是与虎谋皮。”(参见天然:《大学生与女学生之服饰》,《申报》1934年1月1日,第7版。)
(54)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55)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