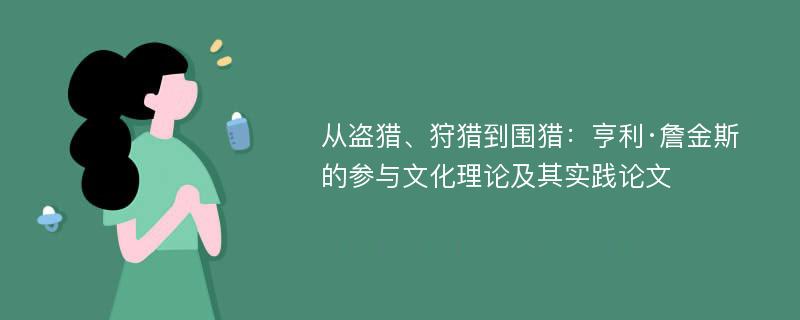
从盗猎、狩猎到围猎:亨利·詹金斯的参与文化理论及其实践
黄家圣 赵丽芳
作为约翰•菲斯克的学生,亨利•詹金斯从起初的粉丝文化研究到当前网络时代的青少年文化研究,始终对来自消费端的集体智慧以及公众参与文化的赋权持乐观态度。
1988年,亨利•詹金斯在美国《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期刊上发表了《〈星际迷航〉的重播、重读与重写: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写作》,可以视作其参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起点,文中也第一次提出了“参与文化”这一概念。[1]1992年,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一书中,亨利•詹金斯较为充分地阐述了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参与文化。之后20年间,他独著或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多本相关著作,持续地推进参与文化的讨论及由电子互联技术和移动技术带来的新的发展可能性,以多样化的案例说明媒介进化过程中个体被激活所释放出的微力量、微价值以及参与文化对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与变革。参与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奠定了亨利•詹金斯在媒介研究领域、受众研究领域以及大众文化批判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也使其成为粉丝圈层研究的知名学者。
一、电视媒介时代:盗猎式参与文化
亨利•詹金斯自称“学者粉丝”,自述进入媒介研究领域基于自身对大众流行文化的痴迷,作为一名通俗文化粉丝所获得的知识和体验让詹金斯在写作中非常重视普通消费者和粉丝的体验、文化实践。[2]他早期研究聚焦于电视迷,特别是科幻题材影视剧迷的研究。作为科幻题材影视剧《星际迷航》的忠实观众,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一书中,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了电视媒介时期作为文化工业话语边缘的粉丝群体如何通过对大众文化资源的拼贴重组(盗猎)进行话语抵抗和主体性身份建构。基于自身以及其他电视迷的行为观察,詹金斯批判了当时学术框架下以及大众媒体对电视观众“头脑简单且痴迷成性”等污名化以及刻板印象标签,借助米歇尔•德赛都的“盗猎”理论,聚焦粉丝作为文化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不同于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至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表现出粉丝圈作为亚文化社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詹金斯的观察案例里,不是所有电视受众都是“沙发上的土豆”般被动、消极,也有积极的电视受众,热情而投入地参与到大众文化商品的内容讨论与“同人小说”“同人视频”等二次创作中,开创了非牟利求共享的“同人艺术”形式,虽然这种私底下的“混剪和二次创作”有法律诉讼危险。[3]借助同人志、同人视频、同人音乐、同人MTV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粉丝群体构建了一个既隐秘又与主流文化并行的同人文化世界。原文本成为他们创作的原材料,也是他们社会互动的基础,“更多粉丝将单部影剧系列作为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粉丝社群起点,并把各种节目、电影、书籍、漫画和其他通俗材料连成了一个互文性的网络”[4]。
共检出病原菌109株,均为需氧菌且为单一细菌感染,其中革兰阴性杆菌75株(68.8%),革兰阳性球菌32株(29.4%),白假丝酵母菌2株(1.8%)。革兰阴性杆菌中以大肠埃希菌(39.4%)和肺炎克雷伯菌(16.5%)为主,革兰阳性球菌中以肠球菌(11.9%)和金黄色葡萄球菌(8.4%)为主。其余36例为表皮葡萄球菌和棒杆菌,均为皮肤表面正常菌群。见表1。
在电视时代,囿于技术与媒介生产特性,参与文化体现出粉丝圈层特性与反馈式、滞后式的间接生产特征,同时又是一种较为隐蔽、带有知识产权风险的后台生产。有组织、半结构的粉丝圈通过挪用、盗猎电视文本或影视文本,通过元文本实现了文化再生产,并通过邮政系统进行分享与交流;对流行叙事的不满或不满足,让粉丝通过文艺批评和持续跟进向制作方表达原作中未能实现的可能性。粉丝对文本材料的重新写作,让他们成为未来情节的积极批评者与建构者,从而间接、滞后地参与到了电视机构的生产;若制作方对粉丝建言视若无睹,挑战侵犯粉丝对电视剧的理解和粉丝圈层的批评共识,粉丝们针对制作方的大规模信件抗议运动也会成为参与文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影响到公司决策层或者节目制作方。
影响世界的《数字化生存》所言的“互动性新媒体”,确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平台开放、用户分享、信息聚合特征日益凸显,用户主导生成内容互联网产品成新的模式。网络的互联性构筑了一个开放性、互动性的社区空间。詹金斯用大量案例集中阐释了“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这一概念。詹金斯认为,融合是一种范式转换,原本媒体独享的内容因为技术介入得以实现跨媒体多渠道流动,各种传播体系相互依赖形成了新的媒介生态圈,在互联网的协助下,电视制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通道从单向趋向双向。
2) 商铺媒介广告发布。商圈APP提供商铺个性化的宣传和发布功能,弥补因场地问题引起广告位不足的缺陷。对商铺的宣传广告进行定时发布、定时撤销,同时允许商家自行根据模板设计广告,通过审核之后完成商铺产品的推广。
二、新旧媒介冲突、融合时代:狩猎式参与文化
2006年,亨利•詹金斯出版了《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关注到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化的生产与流动,描述了通俗文化世界主义的景观。技术融合、技术赋权所随之产生的文化新范式成为詹金斯媒介研究新视角。
在亨利•詹金斯看来,德塞都的“盗猎”比喻,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5],电视时期的粉丝盗猎争夺的是挪用电视剧的权力与元文本的再创造权力,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与电视剧紧密联系开展批评与解读实践,这种解读模式远远超越电视文本本身,并创造出比原影视文本更丰富更复杂更有趣的元文本。“他们多次观看电视文本,利用录像机仔细检视有意义的细节……创造意义的过程包含分享、表达和争论意义。对粉丝来说,观看电视剧是媒体消费过程的起点,而不是终点。”[6]
在融合媒介业态下,曾被质疑的参与文化呈现出新的生命力,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三者的创造性思维融合,让文化工业呈现出双向互通的道路。以大型媒体、大型传媒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力量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推动文化产品的跨媒体流动,同时,自下而上的消费者更全面地参与到融合过程中,或更紧密地与媒体制作人建立关系,或更坚决地进行文化权力争斗。伴随着新旧媒体的冲突与融合,在旧媒体时代总体上被动的、可预测的、孤立的、沉默的消费者在融合时代变得积极、流动与喧嚣起来。[7]
亨利•詹金斯乐于分享融合文化中集体智慧的创造性以及参与文化带来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影响。詹金斯引用法国数字文化理论家皮埃尔•莱维创造的“集体智慧”这一概念,对参与文化进行了进一步解读。皮埃尔•莱维说,在互联网上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专长达到共同的目标:“没有人无所不知,但是每个人又都各有所长,所有知识都寓居于人。”詹金斯认为,融合实质上是在鼓励参与和集体智慧,他分享了《幸存者》节目与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集体智慧”所扮演的角色,[8]并乐见“粉丝社群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来实施政治影响(对喜欢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通过利用新的社会结构(集体智慧)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参与文化)来实施政治影响”[9]。
的确,如詹金斯所言,在新旧媒体冲突、融合时期,技术赋权使得参与文化呈现出互动性、开放性和对话性的特征,信息流动更为多向性;媒体消费者与制作者之间界限趋于消弭,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化,知识分子、草根群体和大众文化粉丝圈层在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变得更加积极。传统上垄断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媒体生产权遇到挑战被打破,呈现开放态势。网络作家与独立制作人呈现了文化生产的多面向,粉丝数字电影制作者开始进入业内主流行列,德拉吉报道、超女粉丝利用新媒介技术形成的粉丝文化、“山寨网络春晚”代表了一种更活跃、更自主、更富参与性的大众文化生产。“狩猎”一词对应“盗猎”,彰显的是人们参与文化的权利与生产文化的主体性。
小学数学教材中专业术语极多,不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大幅度的文字描述都让教材显得晦涩难懂,所以,教师除了拥有传达知识,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知识的作用外,还要注意调整语言,以保证能将数学教材中难以理解的知识点转换成直白简单的口语,通过简化专业术语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所讲解的知识点最好结合生活实例,让学生能从生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提升思维能力的目的。
三、可拓展媒介时代:围猎式参与文化
2013年以来,詹金斯与他人合作的论著主要包括2013年与萨姆•福特、约书亚•格林合作出版的《可延展媒介:在网络文化下创造价值与意义》(Spreadable Media: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2015年与日本文化人类学者伊藤瑞子、美国社会化网络研究专家丹娜•博伊德一起合作完成对谈集《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2016年与其他四位作者合作出版的《连接一切媒体:新青年行动主义》(By Any Media Necessary: The New Youth Activism)。
但另一方面,融合、参与消解了权威、距离感和稀缺性。在新闻传播领域,博客记者、参与式新闻、众筹新闻改变了新闻传播业态,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后,读者和观众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媒体工业洞察了粉丝经济的巨大可能性,自觉地取悦粉丝并利用参与文化在大众文化生产领域制造被物化的世界观和趋于异化的日常生活,文化现象层出不群,但大多被娱乐化绑架。正如彭兰所说,文化生态变得“江湖式”,海纳百川,既包容、又藏污纳垢。
这一阶段,詹金斯对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依然持积极、乐观态度,一以贯之地投身于参与文化实践,对参与文化的讨论与论述跳出了参与本身,更多转向从意义层面讨论参与何为,从社会与权力的批判视角反思数字世界的参与文化及其与政治、商业、资本的关系,并寄望数字原住民青年一代能成为行动主义者。
可延展媒介基于移动互联互通,实时、移动和智能技术赋予互联网更多的可能性,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互嵌成为可能,连接达到空前的广度与深度,渠道变平台、受众变用户,人与媒介深度融合,信息生产与传播形成普通个体遍在的围猎态势,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互联网正在形成。[10]以内容为中心的网络让位于关系网络和服务网络。[11]音乐评论人李皖感慨刚刚过去的台湾金曲奖颁奖过去得无声无息,究其原因,归结到整个人类被互联网载乘,艺术的权威体系败给艺术的草野体系。[12]这是可延展媒介时代参与的胜利,是个体赋权后的围猎景观,消费、审美、价值观的分化与分层几乎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可延展媒介时代,中心已死。
詹金斯等人关注到用户利用数字设备进行分享与传播,在社交平台上建立学习社区,通过分享与连接创造价值的文化现象。在参与、融合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可延展媒介”(Spreadable Media)概念,合作者们着力探讨了何为有意义的参与,并认为在可延展媒介阶段,参与文化的形态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为验证自适应调整变异算子的可行性,实现标准遗传算法,先取算法定网格密度,初始种群规模为30个个体,迭代次数为110代,交叉概率为0.9,变异概率为0.2,适应度函数中各变量分别取m=140, L=56, n=20, θ=35,k=0.75,即适应度函数为
推荐理由:本书以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为切入点,以上海历史演进和发展为脉络,突出体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本书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利用并活化地方志资源,穿插大量具象的故事、鲜活的细节讲述上海故事、彰显上海精神,是反映上海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开展乡史乡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著作。
《数字化生存》出版20年后,“技术乌托邦主义”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坦言“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未成现实,[13]互联网祛魅,去精英化,一方面成为草根文化表达的重要展示性空间,另一方面在文化学者陶东风、李皖看来,又导致了文化活动“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14]越来越多的隐藏文本、后台话语走上前台成为日常景观,导致“创作的高贵性崩散、艺术品的神圣性崩散、珍贵感的消散、卓越的人、物及其关注度的削弱、离散”,大众越来越疏离于传统的庙堂文化、“阳春白雪”,有“格调、品味”的文化也必须学会对话,学习借势新的媒介手段、新的传播观念连接用户。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播出反应平平,但在B站(Bilibili网站)上走红,引发了“故宫网红”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甚至和电商合作,找到了与商业对接直接变现赢利的入口。
可以说,粉丝群体在电视媒介时期仍处在大众文化边缘和社会弱势地位,粉丝文化是一种“边缘书写”。但其积极意义在于,这些处在主流话语边缘地位的文化消费者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力构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文化空间。而这些文化共同体通过地下活动实现了粉丝群体文化的活性,在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彼此的情感认知,并促使生产端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与认知。
何为有意义的参与?这是詹金斯等人反思的关键所在。个体参与与数字资本主义收编、个体狂欢与政治虚无、更公平的环境还是新壁垒的兴起?网络时代的个人主义有无聚合的可能?数字世界诸如此类的病症在上述提及的著作中成为论述焦点。
不过,詹金斯始终是“参与文化的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公众(不仅仅是粉丝)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文本,彼此建立联系、调解社会关系,并对他们周围的世界赋予意义。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他们都在可扩散模型中发挥作用,参与到有意义的对话中确定共同的利益、表达共同的愿望。在可延展媒介环境中,最具价值的是公众在媒介文本分享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公众可以利用社交网络通过集体沟通表达主张诉求与价值观,并利用线上平台发起社会变革运动。公众可挪用媒体文本推动推动网络社群讨论与辩论,进而推动网络社群运动或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对话。此外,在可延展媒介时代,公众掌握媒介支配权的企业要想吸引网络社区参与,不得不容忍那些曾经被视为具有抵抗力或越界性质的行为,并学习倾听民意。[15]
结语
从最初对粉丝群体的身份建构到当下关注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运动,亨利•詹金斯的文化研究随着媒体的变迁而向社会层面不断深入。他本人始终秉持积极受众观,是粉丝文化、参与文化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倡导者。詹金斯将参与文化视为一种公民权利,他假设一切公民都拥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权利,拥有发言和向他人表达观点的权利,在集体或个人层面上拥有左右那些影响他们生活机制的权利。
粉丝文化为曾经“污名化”的粉丝群体提供了重塑集体群像的途径。在20世纪关于粉丝的刻板印象还多围绕在“狂热”“缺乏理性”这些负面评价之上,但随着社会对“粉丝”(fan)在态度由“过度无节制的宗教信仰狂热”转化为“过度且不合适的热情”,粉丝文化、粉丝圈层通过自我赋权、技术赋权由边缘走向对话,继而成为多个小众的主体,在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同时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文化阵地。
粉丝文化在消费时代体现出的创造力和经济效益,迫使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生产者向消费主义低头,主动顺应粉丝的文化诉求。这种话语转向实际上也呈现出了从精英话语向草根话语转变的过程,大众参与不断深入,通过建立粉丝社群,利用集体智慧共同协作,并延展粉丝文化的内核,粉丝正在创造文化融合的文化景观。
易非跟妈摊了牌,她以为妈会推辞一下,因为房子毕竟是她买的、她装的,——开口的时候,她只是想提醒一下妈,这婚也结了,该给向南一家找个住处了。可没想到,妈一口答应了,她说:
参考文献:
[1]Henry Jenkins.Star Trek rerun,reread,rewritten: Fan writing as textual poaching[J].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8,2(5): 85-107.
[2][6][7][8][9](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279,61,63-65,357.
[3][4][5](美)亨利·詹金斯.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23,68,66.
[10]胡泳,王俊秀,段永朝.后工业时代:意义互联网的兴起[J].文化纵横,2013(6):19-26.
[11]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3(12):17-18.
[12]李晥.流行音乐为什么不流行了?[N].文汇报,2018-7-26.
[13]胡泳.尼葛洛庞帝之叹——打造“互联网公地”的探索[J].新闻爱好者,2017(1):56.
[14]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J].学术月刊,2009(5):23.
[15]Henry Jenkins,Sam Ford,Joshua Green. Spreadable Media: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3:167-173.
【作者简介】 黄家圣,男,广西崇左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赵丽芳,女,山西运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最终被确诊为子宫内膜癌,幸运的是癌细胞并未向邻近器官及组织扩散。考虑英的年龄太大,不宜手术,医生建议她马上接受放疗治疗。英当然不懂这些,她只记得外甥说自己的病有得治。英舒了一口长气,她的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内心按捺不住高兴。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媒介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詹金斯论文; 文化理论论文; 亨利论文; 盗猎论文; 实践论文; 狩猎论文; 文化研究论文; 参与文化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