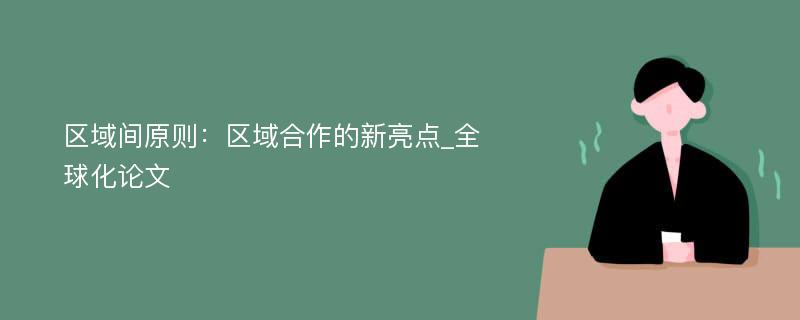
地区间主义——地区合作的新亮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间论文,新亮点论文,主义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国际性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大多数地区组织都在扩大地区间关系,出现了许多地区间合作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欧盟—拉美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等。虽然一些地区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定期联系,但从90年代开始,地区间关系的数量才有了快速增长,地区间合作的深度得到了显著加强。国际关系由此增加了一个新的层次,即地区间或跨地区层次,它是在新地区主义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地区之间互动的日益增长,成为冷战后地区合作的一大亮点。地区间关系遂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内容,并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即“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对地区间主义的研究虽起步不久,但已取得一定成果①。
一、地区间主义的发展及形式
地区间主义源自地区主义,但又与地区主义不同,后者主要是考虑地区自身,而前者除了关注本地区外,还重视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这使地区积极促进地区间安排和协议的达成与实施,进而影响全球层面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兴起的第一波地区主义的目标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贸易或安全方面,尽管不乏在其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图。因此,当时地区间主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彼此关系松散,合作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合作形式多为非正式性,如为人熟知的欧共体与非加太集团(ACP)的伙伴关系。同时,当时的地区间主义由欧共体主导,对两极格局下的国际体系影响有限。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地区主义的目标更加复杂和全面,政治性也更强,表现为多层面的立体形式,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强调地区的认同和凝聚力。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新地区主义是外向型的,因此,又被称为“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使各个地区向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地区开始在世界及本地区以外的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地区间的安排和协议更是对全球层面的关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增进了建立和加强国际制度的需求,以应对世界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配置了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了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合作。地区间主义由此获得了新发展,具体表现为由松散型趋向紧密型,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合作形式较为正式,因而常被视为新地区主义的衍生物②。地区间主义和地区主义因而构成了互补的进程,共同推动地区合作向前迈进。此外,冷战结束以来地区间关系网络的迅速发展以及几乎所有国家都程度不等地整合入这一网络,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鲜明的特色,虽然欧盟仍扮演主要角色,但许多地区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当前的地区间主义对国际体系以及整个世界的地区合作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地区间主义的定义,迄今众说纷纭,未达一致:最简单的说法指地区间主义是“地区对地区的关系(region-to-region relations)”③;更进一步的说法是“地区之间制度化的关系”④;意义最为普遍的说法则认为“地区间主义是指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互动”⑤,或者说“两个地区由此作为地区进行互动的状况或进程”⑥,以及“国际性地区之间扩大和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进程”⑦;还有人将其定义为“两个特定地区在地区间框架内或正式关系中的合作”⑧。
地区间主义在现实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分别是:1.地区组织或地区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通常建立在部长级或高官级定期会议,以及开展联合项目和规划的基础上,并且往往集中于信息的交换与特定问题领域的合作,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投资。东盟与欧盟的长期对话伙伴关系属于这类关系。2.双地区(biregional)和跨地区(transregional)关系⑨。这类关系的特点是参与者来自两个及两个以上地区,各自以独立身份加入,地区组织不能完全代表它们,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地区协调。亚欧会议、欧洲—拉美峰会、非洲—欧洲峰会就是双地区关系,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则是跨地区关系。它们多半建立在高层定期会议(峰会和部长级会议)以及许多联合项目和规划的基础上,共同点是其议程主要集中于经济问题。3.混合型(hybrid)关系。这类关系通常指一方为地区组织,另一方为一组没有建立地区组织或组织松散的国家⑩。但还有人认为,地区组织或集团和单一大国的关系也属于混合的地区间关系,并且是双地区或跨地区关系中的重要成分,如欧盟分别与美国、中国、日本等的关系(11)。
与此相对应的是地区间主义的三种变体,即:“纯粹的地区间主义”(pure interregionalism)、双地区和跨地区主义(12)、混合型地区间主义(13)。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跨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概念,包含的行为体关系比单纯的国家间关系更加广泛。任何跨地区的联系,包括公司产品的或非政府组织的跨国网络,也就是说涉及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行为体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可以在理论上被归为跨地区主义”(14)。在跨地区主义中,国家固然是重要的行为体,但来自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行为体在内也参与了这一进程,因此,跨地区主义有时又被认为是凝聚型或扩散型的地区间主义。跨地区主义建立的是更加广泛深入的整合性联系,以形成跨地区的基础,其中包含这样一些共同的“空间”:经济空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统一商业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和其他类似的整合性措施;实业空间——与经济空间紧密联系,但更多地来自于跨国企业跨地区经营的活动,这些活动与生产和配置的跨国体系的发展有持久联系;政治空间——涉及政府间甚至超国家机制管理共同的跨地区空间的活动;社会—文化空间——在跨地区进程中形成社会性社区、共同的文化认同等(15)。因此如果“地区间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并分开的地区之间的关系,跨地区主义则指地区间和跨地区共同‘空间’的建立,构成这一空间的行为体(如个人、社区、组织)在其中活动,并且彼此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16)。
二、地区间主义的研究方式及内容
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对地区间主义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式,即由外到内、由内到外,以及体系理论(17),它们彼此互为补充,直接或间接地解答了以下问题:民族国家为什么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建立和加强地区间合作机构?地区间主义如何影响地区一体化及合作进程?
由外到内的方式聚焦于外部因素,认为地区间主义的发展是民族国家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外部双重挑战所做的回应,其运作由复合型相互依存(18)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互补来推动,只注重一方将会导致对地区间主义的错误解读。在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复合型相互依存发展迅速,建立起了国际和跨国关系的密集网络,各国试图以加强地区合作来改善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地区合作则导致了全球化世界的区域化,各国通过平衡地区力量的不对称来回应区域化的趋势。扩大或深化地区合作增加了国家的竞争优势,这就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地区合作协议急剧增加的原因(19)。由于保护主义的或者说封闭的地区主义不足以回应复合型相互依存的增长,而新建立的地区性相互依存并不像传统的关税同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经济上有益处,因此,地区合作结构要求是开放的,这就是“开放”的地区主义。通过力量的地区性平衡来管理相互依存和两极分化,导致了灵活的地区间合作机构的建立,跨国行为体的加入则平衡了从国家转移到市场的力量。地区于是开始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其本身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由内到外的方式专注于内部因素和文化的整合,典型的是K·W·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概念和A·埃茨奥尼的一体化理论。前者认为文化的整合能使地区最终形成安全共同体(20),后者通过研究共同文化的“隐蔽变量”来解释地区和地区制度性合作的存在(21)。与由外到内的方式相比,由内到外的方式更关注地区间主义对地区体系和新地区主义的影响,认为地区间的互动将会直接影响到参与的各方,每个地区的特性通过互动而变得更加突出,这又有助于其进一步的发展及各自身份的建立,因而成为经由地区间主义培育地区主义的一种方式,东亚合作就是典型例子。
体系理论则是把国际、地区间、地区和国内四个层次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并在研究中运用了多种国际关系理论:用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地区间主义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用制度主义理论来阐释地区间制度建设对正在成长中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诠释地区间主义对复合型相互依存管理的影响,用建构主义理论来解释地区间主义对地区和地区间共同体建设或认同的影响。因为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地区间主义源自民族国家为回应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而推动的进程,有助于力量的平衡;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地区间主义是管理多极世界中更为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一个部分,是增强全球治理的一种工具,有助于管理相互依存中固有的机会和风险或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地区间的联系建立在地区认同形成的基础之上,地区间的互动形成了“我”/“他”意识,因此,地区间主义是建立和巩固地区集体认同的一种方式。
体系理论关于地区间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全球化和区域化是重塑国际体系结构的过程,因而对地区间合作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全球化形成了国际关系的多层结构,国际政治逐渐接近于全球治理体系,后者的特点是在地区、地区间、双边和多边的不同层次上进行务实和灵活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全球化也促进了区域化的发展,开放的地区集团的建立则导致了国际政治中多极结构的出现,因而要求地区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如果协调和平衡失败,地区间关系就会出现对抗。因此,地区间主义的定位就是地区间的协调,力量的平衡作为地区间协调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地区间的对抗,而是合作性的竞争。总之,全球化和区域化导致了国际政治多极和多层结构的产生,这样一种灵活的秩序要求民族国家以建立地区间合作机构去适应复合型相互依存和力量平衡的必然存在。体系理论研究地区间主义的重要性在于解释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及推动区域化和地区间主义的国际因素,不足之处是没有充分解释外部因素对地区间制度的挑战及地区间合作如何影响国际体系。
地区间主义研究的内容目前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
一是地区间关系的形式(22)。
二是地区间关系的制度化。新地区主义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具有相对开放的合作机制,其特点是灵活和非正式的结构、软制度化、政府间主义,以及坚持不干涉成员国事务的原则等。新地区主义的这些制度化特点被转到了地区间关系上,导致了地区间普遍建立协商性的论坛,以避免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及产生与缜密的组织构造相联系的巨额治理成本。
三是地区认同的建设。地区间的互动通过互相承认、彼此参照和重申各自的主张,促进了地区认同的建构。每个地区的特殊性通过互动而凸显,这又有助于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及认同建设,地区间主义以这种方式促进和强化了地区主义。
四是地区间和跨地区关系的功能。地区间主义有5个方面的功能(23):一是平衡,其表现形式有两种,即力量和制度的平衡(24),除前述的地区力量的平衡外,主要大国也利用地区间和跨地区论坛作为制度性工具来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二是制度建设,大量的区间和跨地区论坛的建立使国际体系新增了一个层次,促进了它的多样化。地区间互动在为地区内协调创造更大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地区组织的制度性凝聚力,因为地区组织的成员必须更紧密地合作,才能更有效地与地区间对话伙伴打交道;三是地区认同的建设,如上所述,地区间和跨地区互动的活力,以及接之而来对地区凝聚力更大的需求,促进了地区认同的建设,因为在地区间层面上与外部的“他”互动的进程,将会加强地区层面上的认同;四是减轻全球多边论坛的负担,由于全球性论坛讨论的内容日趋复杂,代表不同利益的行为体参与的数量与日俱增,导致其效率低下。地区间和跨地区论坛分担和分解了全球多边论坛的决策过程,使全球性问题的谈判和解决成为由下而上的进程。地区间关系因而精简了全球性论坛负荷过重的议程,防止在国际体系最上端出现“瓶颈”而使全球性机制瘫痪的情况出现。五是议程设立,与为全球多边论坛“减负”的功能紧密相连,地区间和跨地区论坛为将新议题引进全球性论坛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并建立了具有广泛基础的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或阻止其发生。六是对策研究。主要评估现有的地区间合作机制的成果,推测其对国际关系和地区合作的影响,为进一步的政治行动提供建议,讨论克服因地区间不同文化而产生的分歧的方式,以及增进彼此了解的战略等。
三、地区间主义的作用及贡献
地区间主义作为地区合作的新领域,其作用还在显现之中,但目前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化了地区作为行为体的作用。全球经济的变化以及跨界活动的规模表明了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问题难以由单个国家独自解决,需要地区内部及地区之间的合作来应对。地区间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使地区能够作为行为体互相讨论和交流彼此关注的事情。第二,有助于巩固地区主义。地区间主义并不仅指两个独立地区的联合,还指通过彼此互动的进程,影响各自地区内部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促使参与地区间合作的各方进一步增强地区内部的团结和力量,从而提高了地区处理经济、社会、安全等问题的能力。第三,推动了地区认同的建设。地区间主义具有建立地区形象的潜在可能性,这一形象超越地区自身范围,并影响地区认同的发展。通过将两个地区置于平等地位,互相承认对方的不同身份,地区间主义以扮演在地区内部起动员作用的角色这样一种方式提供了互动的“我”/“他”关系。第四,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参与的新空间。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地区间主义重要和决定性的行为体,但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进程,而且由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往往聚集在复合的多行为体网络和联盟中,很难将它们视为两个分离和独立的行为体范围。因此,地区间主义不能被简单地被认为是由国家领导的或政府间的进程,而是超越了国家的范围,将工商部门、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包括了进来。第五,影响了多边主义的发展。传统的多边主义是建立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基础之上,建基于地区的多边主义则意味着所有相关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以地区间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模式,尽管目前这一模式还不是非常清楚。第六,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功能性作用。地区间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回应,以及应对跨地区威胁和挑战的手段。
另外,一个地区在其内部变得团结和强大时,就会积极向外拓展关系,并发现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会增加自己的角色性(actorness)。所谓的角色性是指地区及地区组织具有“形成存在、发展认同、聚集利益、阐述目标和政策、制定和实施决定的能力”(25)。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执行某些功能的能力,这些能力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属性。在地区具备了角色性后,必然导致地区间需要更多有组织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地区间主义的发展。这也再次证明了地区间主义是地区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但超越了后者,成为国际体系中又一个互动的层面。
地区间主义对国际体系和地区合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多边效用”(multilateral utility)上,即“通过具有多边制度的积极伙伴关系来促进全球体系的稳定、和平、繁荣与平等”(26)。地区间合作机制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公共政策问题,其方式是通过实质性地推进讨论和建立新的机构来有效地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区间合作机制能够帮助实现甚至形成“不可分割的”目标(如全球自由贸易、减贫等),同样反过来也可以此检验地区间合作机制对全球体系的有用性。多边效用与全球体系紧密联系,并且集中关注地区间合作机制对全球合作的推进,由此使参与地区间合作机制的成员按照多边合作的准则行事,从而加强了它们的责任感,后者正是国际体系的基础。
总之,地区间主义提供了机会,将有关全球化和区域化、地区主义,以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建等问题集中到了一起。地区间主义的出现,使地区合作增加了新的内容,地区合作与地区间合作、次地区合作互相重叠、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网络中,地区正在建立由其构成的世界。
地区间主义创造了一个新的地区合作形式,即建立了地区间关系,并在地区的形成中发挥了建构性作用,成为方兴未艾的全球地区合作进程的一部分。虽然地区间合作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其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但毫无疑问,它已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支新兴力量。
注释:
①瑞士学者海纳·汉吉(Heiner Hanggi)和德国学者拉尔夫·罗洛夫(Ralf Roloff)、于尔根·吕兰(Jürgen Rüland)在2001年发起了名为“国际政治中的地区间主义”的研究项目,邀请世界各地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参与,并于2002年1月31日~2月1日在德国的弗赖堡举行会议,研讨其研究成果,会上提交的论文经修订后于2006年结集出版: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utledge,2006.紧随其后,由瑞典欧洲政策研究所资助的研究项目“欧洲在世界的作用”启动,该项目研究为期2年,欧盟的地区间合作是研究的重点,相关成果先是发表在2005年第3期的《欧洲一体化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27,no.3(2005),entitled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上,2006年又结集出版: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Routledge,2006.这是目前所知国外对“地区间主义”的集中探讨。国内相关研究迄今所见:陈志敏和杨小舟的“地区间主义与全球秩序:北约、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载潘忠歧主编:《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主要分析了地区间主义的形式、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与全球秩序的关系;卢光盛在阐述亚欧会议绩效时附带地提到了“地区间主义”(卢光盛:《亚欧会议:机制和绩效》,载《国际政治》第7卷第2期(2005年3月),第1~6页;郑先武在《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61~68页)和《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第44~50页)中则分别介绍了地区间主义的理论与实证问题以及东盟的地区间主义。
②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在地区主义的框架内简单理解地区间主义,它是行为体互动的新层次和不同的现象,需要根据其自身情况来研究。见Fredrik So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Introduction: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p.9.
③Fredrik So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Introduction: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p.2.
④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
⑤Julie Gilson,"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p.61.
⑥Fredrik So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Introduction: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2006,p.9.
⑦Ralf Roloff,"Inter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ate of the art",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8.
⑧Fredrik So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Introduction: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p.10.
⑨双地区和跨地区在地缘上的区别是:前者的成员来自两个地区,后者的成员来自两个以上地区。
⑩Fredrik So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Introduction: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eds.),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The Politics of Interregionalism,p.10.
(11)Heiner Hanggi,"Interregionalism: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p.7,paper delivered to the workshop "Dollars,Democracy and Trade: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Los Angeles,CA,May 18,2000),sponsored by The Pacific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Policy,Los Angeles and The Center for Applied Policy Research,Munich.另一种意见认为,地区组织或集团和单一大国的关系应在地区组织的对外关系之列,不属地区间关系。见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n unfinished agenda",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98.
(12)双地区和跨地区主义所代表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还被冠之以其他名称,如“大地区主义”(mega-regionalism)、“跨大陆主义”(transcontinentalism)、“大陆间主义”(inter-continentalism),“泛地区主义”(pan-regionalism)等,见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
(13)也有人将地区组织或集团和单一大国之间的关系称之为“准地区间主义”(quasi-interregionalism),见Heiner Hanggi,"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In search of a typology",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42.
(14)V.K.Aggarwal & Fogarty E.A.(eds.),EU Trade Strategies:Betwee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Palgrave Macmillan,2004,p.5.
(15)Christopher M.Dent,"From Inter-regionalism to Transregionalism? Future Challenges for ASEM",Asia Europe Journal,No.1(2003),p.232.
(16)ibid.,p.224.
(17)地区间主义研究方式的有关内容参考和借鉴了Ralf Roloff,"Inter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ate of the art",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7~30.
(18)“复合型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创,指相互依存体系中各行为体运用不同传播渠道行动的复杂性,见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Little Brown,1977,p.23.
(19)20世纪90年代,地区主义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各种地区合作安排大量增加,以贸易合作协议为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48-1994年,向关贸总协定通报的地区贸易协定(有关货物贸易)是124个,但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至2007年9月25日,向其通报的地区贸易协定(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超过240个。"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Facts and Figures".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fac_e.htm.
(20)K.W.Deutsch,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 Lantic Are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1)A.Etzioni,Political Unifi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ders and Forces,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5.
(22)见正文第一部分中相关内容。
(23)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 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1~12.
(24)Jürgen Rüland,"Interregionalism:An unfinished agenda",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00.
(25)J.Rüland,"Inter-and Transregionalism: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No.35,p.6.Paper delivered to the Workshop on Asia-Pacific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Europe: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Future,sponsored b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5~6 July,2002.
(26)Christopher M.Dent,"The Asia-Europe Meeting(ASEM)process:Beyond the triadic political economy?" in Heiner Hanggi,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eds.),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