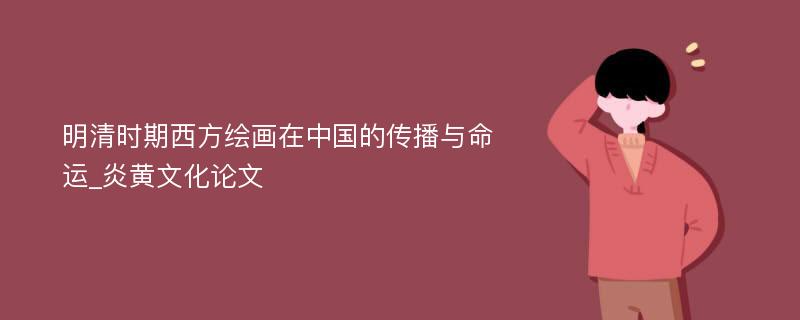
明清时期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际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画论文,际遇论文,明清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75(2007)02-0124-03
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尤为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莫过于明清之际的西画东渐及其带来的本土文化效应。西洋画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以后,随着传教士在内地活动并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触,迅速得到传播与蔓延开来。据史料记载,最先在本土传播西洋美术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发明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教’形式,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进呈给中国上层官儒和帝皇,”[1] 从而开始在了西洋画在宫廷传播的历程。在宫廷之外,传教士也与中国文人画家有着广泛交游,“1597年,中国的山水画家、绘画理论家李日华写了略带夸张的颂辞送给了利玛窦。10年以后在北京与利玛窦往来的众多的中国文人当中,便有著名的画家张瑞图。利玛窦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友谊》的谈论友情的文章并且翻译成中文送给了他。”[2] 在民间,传教士们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途径向广大民众和社会各个阶层传播西洋画,并由教会兴办学校、画坊和工厂,培养西画人才,以扩大了西画在民间各个阶层的影响。然而在西画东渐的历史过程中,西洋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现象,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画的认识反应不一,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水准和价值判断,反映出社会变迁时期中国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复杂变化,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洋画在中国传播和生存发展的轨迹。
在明清社会中,西画东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学东渐为背景的,这种现象体现在宫廷统治阶层中尤为明显。西洋画大规模传入中国时,正值明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衰落时期,内忧外患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寻求新的治国良方,而其时西方国家依靠科技实力的强大,使统治者深受启发,并表现出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关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都具有精深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自然能够赢得皇帝向往“西学”的欢心,从而在宫廷中取得了立足之地,为西洋画在宫廷得以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就西洋画这种外来画种本身而言,其写实性表现技法(如明暗法、透视法)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法则,已经暗合了“西学”中的某些因素,而生动的写实风格和异国情调更能唤起了皇室和贵族们的好奇和追求。在这种文化情境下,明清皇帝都对西洋画怀有极大的兴趣。据记载,利玛窦曾向万历皇帝进献一幅绘有欧洲王公贵族、天使和教皇的宗教铜版画,由于其细节十分精美,得到皇帝的赞叹,于是便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用色彩放大复制了这幅画。清初康熙皇帝也对西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对西洋画这样评价到:“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之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3] 焦秉贞《耕织图》深得康熙嘉许,不仅亲自作序,还为画幅题诗,并指示将该图镂版流传。乾隆帝对西洋画的兴趣超过康熙,他曾下令将自己的养老的居所全部饰以西洋风画,由此大量传教士油画家应召入宫并奉旨作画。事实上,传教士画家御用宫廷阶段,也是西洋绘画在宫廷内影响的鼎盛时期。
“西洋画在明清之际所产生的最煊赫的影响恐怕还是在宫廷绘画,这是聪明的传教士甚至欲倾毕生心血奋力冲开的一条重要的文化通道;那么帝王的趣好规范也就密切地关系着西画在中国的命运。”[4] 尽管西洋绘画得到皇帝的喜爱和认可,传教士画家由此也获得极高的待遇和地位,但西洋画在宫内的传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要来自皇帝和上层官僚的评判和兴趣所好,可以说,是皇帝和上层官僚左右着西洋画在多大程度上在宫内的传播。乾隆帝“不喜油画,盖悉涂饰,阴色过重,则视同污染,由是宁取淡描,而使阴色轻淡。”[5] 这里已透露出,皇帝对明暗对比过于强烈的西画不是十分喜好,而其真正的审美趣味仍然是中国画笔墨轻淡的艺术效果。为了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和宫廷的需要,这些传教士画家不得不放下纯西画式的创作方法,而转向学习中国画的表现技巧,并将中西不同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加以综合,创造出一种折衷主义画风。其中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的艺术实践尤具代表性,他把西方的写实主义和中国的意象概括,西洋的焦点透视深度和中国长卷式的连续透视,隐现的色调明暗对比和线条勾勒等手法掺和运用,逐步形成了自己综合性风格。例如他的《百骏图》运用了中国长卷样式,透视是散点式的构成,却又有静态瞬间的焦点透视深度;山、树、草的勾勒大体是中国式的笔法和线条,但体积晕染和阴影的处理无处不在,使中国画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写实作风所融化,意象具有西洋式的实感。这种巧妙的综合,正好迎合了当时满清朝廷上层人物的审美水平和好奇心。除此之外,他还与宫内许多中国画家一道创作了一些“合笔画”作品。如《弘历雪景行乐图》轴是描绘乾隆皇帝和子女共度新春佳节的风俗画,是由郎世宁来完成图稿的起草和图像的主要部位,其余则由唐岱、陈枚、沈源及丁观鹏共同完成。
这种折衷主义之举,带来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那就是不同风格手法的拼凑所造成的不统一性,其结果是削弱了东西方传统各自的优长,这对清廷内的西画家而言,无疑是陷入了一种困境。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说:“是余抛弃平生所学而易为新体,以曲阿皇上之意旨矣。然吾等所绘之画,皆出自皇帝之命,当其初吾辈亦偿依吾国画体,本正确之理法,而绘之矣,乃呈阅时不如其意,辄命退还修改,至其修改之当否,非吾等所敢言,惟有屈从其意旨而已”[6] 这样一来无形中限制和左右了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擅长油画的传教士画家的创作自由,使他们无法遵循油画自身创作的规律进行实践。而对于中国画家而言,他们尽管在创作中对“海西法”有过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比如蒋廷锡以“戏学海西烘染法”而著称,并且还参与郎世宁新体绘画创作,但这一切并非是他们所情愿,致使西洋画在宫内的命运举步维艰。“清康乾间,虽为中国画西洋化之极盛时期,然自乾隆末叶此种糅合中西之新画派,一因西籍教士被禁,钦天监中西教士复渐绝迹,一因当时士夫对此种画派,渐生厌弃之观,当相鄙斥,于是此种画派逐渐然中断。”[7] 由此可见,到了乾隆年间,随着中国同西方的政治局势日渐紧张,耶稣会被教皇格列门十四解散,传教士停止了来华活动,西洋风画便在中国宫廷趋于沉寂了。
自利玛窦到郎世宁,耶稣会艺术家献身中国艺术达200年,然而,他们的艺术影响仅仅限于中国上层社会和宫廷画师,对于中国文人所主宰的画坛,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使中国人在18世纪拒绝接受西方的艺术,这就是中国画自身存在的固有特征。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反映了士大夫的文化,然而确是这个处于中国社会顶峰的小集团决定了中国艺术的主旋律。是这些学者们建立了艺术标准,而不是朝廷。”“西方风格的绘画,和掺用西方写实主义作的画,即使达到让人惊叹的水平,它也不适合士大夫去实践的。在那个社会里,文人学士即是审美情趣的最终审判者,他们的判断就是一切。”[8] 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所列“西洋画”条,曾经这样写道:“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与阴阳远近不差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墙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以其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9] 邹氏的这种西洋画评说,鲜明地体现了传统文人士大夫“重神轻形”的价值观念,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持同样观点的在清代学者、画家中还时有反映。张庚《国朝画征录》曾经就焦秉贞的参用西法的有关实践,评价到:“焦氏得其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10] 晚清葛元煦《沪游杂记》对西画盛行于上海这一现象,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而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11]
明清以来,西画东渐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人物画和肖像画方面,而对代表文人画主流的山水画的影响,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对曾经生活于南京一带,主要是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画家,如吴彬、樊圻、龚贤等。这些画家的作品之所以可能被视为受西画影响,“在有关的学者看来,主要是指他们的山水画在透视和光影处理等方面与西画有某些近似之处。”[12] 如吴彬在画中描绘房舍在水中的倒影,除了早期佛教绘画外在传统中国绘画中很少见到的落日余晖映红天空和水面的景象,还有农舍的烟囱冒出的屡屡轻烟。樊圻在画中描绘地平线上的远景,画上一道直线,线上有点点岛屿来表示水面。这些新的表现技法,如采用透视法表现远小近大、阴影画法和在向远方延伸的地面消失在同一焦点上等写实的画法,苏立文先生解释为:“曾经在北宋晚期的杰出作品、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出现。500年之后,这些写实的画法又伴随着其它新的技法再次出现,只能解释为西方美术影响的结果。”[13] 而有些学者对此提出疑义:“如果真是在这些山水艺术中存在‘写实’的因素。那么其是否体现了‘17世纪卷轴中出现西方写实主义确实是西方绘画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清代初期,来自西方写真画风的影响仅限于南京的一批被称为‘金陵八家’的画家当中,那么,我们又如何剖析‘一般说来文人画家对此并不注意’的思想倾向。”[12] 显然,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洋画对文人山水画的影响不如宫廷画和人物画明显,即使存在某种“感应”的话,也需要十分仔细的辨别和探究。
相比较这些金陵派这些山水大家,明末清初的吴历的山水画受到西画的影响是较为公认的。这是因为吴历有长期与西方传教士接触的经历,并于康熙年间入天主教,晚年又献身于传教事业,可谓是受到西方文化的长期熏陶,这样他的画风受到西画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叶廷《欧波渔话》记“道人入彼教久,当再至欧罗巴,故晚年作画,好用西法。”作于1675年的《湖天春色图》,运用了西洋色彩和透视法表现出空蒙飘渺的中国画意境,是其参用西法风格的写照。可是当我们再看看他曾在一则《墨井志跋》中所说的话:“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即款识我之题上彼之识下。用笔也不相同。”[14] 表面看来虽谈的是中西绘画的差别,可再深究一下,会发现画家的审美取向依然归于文人画的空间意识、用笔观念和“神逸”的审美标准。再看有关学者对他的评价:“渔山作画,特主意趣,不重形似。又从现存渔山之画观之,不见所谓云气绵渺凌虚者,唯湖天春色一帧远近大小,似存西法,树石描绘与郎世宁诸作微近;然其他诸帧,一仍旧贯。”[15]“严如吴渔山诸人作画,仍喜参西法然皆成分甚少,仅存其意耳。此为中国画受西洋画影响之一斑。”[7] 所以,即使像吴历这样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深重的文人画家,还是无法丢弃骨子里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由此更能看出西洋绘画在文人阶层中的生存可能性微乎其微。
明清时期的中西美术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宫廷之外的“民间”进行的。当西方传教士远涉重洋踏上中国的国土时,他们除了北上京城进呈贡品或供奉宫廷之外,还活动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特别是在广州、南京、上海、北京一线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所到之处,他们在教堂中陈列摆放宗教题材绘画,以吸引更多的民间信徒。正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所记载:“拥有学问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圣坛上图画中的圣母像敬礼……他们始终对这幅画的精美称羡不止,那色彩,那极为自然的轮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16] 教堂中的宗教画确实起到了吸引民众的效果,那么西洋绘画的最初印象也一定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传教士们除了从本国带来宗教画在教堂摆放之外,他们还带来大量的印有宗教题材插图的书籍。书籍中的宗教画起着在没有传教士讲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为民众解释教义的作用,而且书籍传播的影响面比教堂的范围要广得多。所以,这些印有西画的书籍在当时非常受欢迎,清代方殿华在《像记》中记载:“崇祯八年(1635),艾司铎儒略传教中邦,撰《主像经解》,仿拿君原本,画五十六像,为时人所推许,无何,不胫而走,架上已空。”[17] 从这些书籍在民间需求数量之大和受欢迎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对西洋画在民间的传播一定起到不小的作用。随着西洋画在内地的进一步传播,传教士还在其创办的教会学校内开设绘画课,培养绘制宗教绘画的专门人才。如意大利耶稣会士乔瓦尼·尼科洛在澳门创办的一所绘画学校内,培养出一批影响比较大的如游文辉、石宏基、冯玛窦等绘制宗教画的中国画家。此外,教会还在南方设立工厂、画坊,雇佣中国工人为其生产艺术品。被雇佣的工人在工厂和画坊里通常要按雇主的要求学习西画技法,他们必须熟练的掌握西画技术才能满足雇主的需要,而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民间,他们在学成之后,又回到民间中去,对西洋画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西方绘画在民间传播与影响不仅范围广、路径多,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当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西洋风画由于政治原因在宫廷迅速衰落的情况下,却依然在民间长时间地流布,而且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如果说明清时期传教士们种种艰辛努力,只是西洋画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可和传播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民间的积极“回应”无疑是西洋画在民间真正生根发芽的内在因素。与文人士大夫和上层贵族不同,民间阶层的世俗性审美趣味使其对西画的态度非常开放,民间阶层因为没有上层集团的显赫地位,也没有文人士大夫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他们能够在传统思想主导的文化背景中,不受任何正统审美标准和条条框框限制,比较容易接受反映西洋风格的精巧工细的绘画。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明清西画东渐之际,正值中国江南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城市与工商业兴起,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的细致化,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在民间迅速崛起。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非常活跃、开放和进步,他们对外来艺术和民间新艺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他们中的富裕阶层有的还热衷收藏,充当着民间艺术赞助的角色,所以他们的艺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民间审美风尚,在其倡导下,西洋风绘画得以在广大市民阶层和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使其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土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民间阶层出身的民间画工,又深受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熏陶,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对西画的主动择取与创造性融合的倾向,使民间绘画呈现出一派新的风貌。例如苏州地区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在明末清初之际曾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旺盛之时,桃花坞年产年画数万张,远销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省,甚至还出口日本与东南亚。”[18] 在这批版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仿泰西笔意”(《全本西厢记图》)、“仿泰西笔法”(《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图》)等题跋,表明了民间画工对于西画具有某种主动接受的意象。在绘画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具体地看到对明暗法与透视法等西画技法的多种吸收痕迹。《姑苏万年桥》就其画面构成来看,主要是在画面中设定不同的固定视点,相应运用焦点透视原理里,将参差复杂的房屋、桥梁以及大大小小各种景致和人物,安排得井然有序且富有变化,显然有吸收西画中透视法的痕迹。而在明暗法吸收方面,主要体现在房屋、桥梁等建筑物的造型上大都进行光源及其投影的处理。《渔樵耕读图》以排列细密的线条刻画了近景池塘中的水纹、倒影和中景人物衣纹的明暗,与传统版画对物体的刻画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带有明显的西方铜版画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民间版画对西画技法的借鉴是比较全面的。民间画工的艺术实践与创造,是西洋绘画在民间长久立足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西洋画传入中国以后,通过多种路径方式在宫廷和民间广为传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基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对西洋画这一外来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地审视和观照,并作出不同的反应和评判,这就决定了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并非是单线性的,而是在不同阶层中且呈现多线性的发展轨迹,且遭遇到的各自命运也不尽相同。在宫廷中,由于皇帝主导着审美趣味,西洋风画不能在宫廷中自由传播和生长,它必须以折衷方式与中国画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才能迎合上层集团的趣味。而一旦随着政治风云变幻,朝廷对“西学”热情消减和中断对西方交流,西洋画在宫廷中的传播也就终止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由于固守传统文化观念,他们对西洋画的态度“采其逼真而讥其匠气”。尽管他们对西洋绘画的写真与写实性效果表现出赞叹,但却认为缺乏意境韵味,无法与中国绘画相抗衡,基本上是持排斥的态度。而且明清时期写意文人画主导画坛,写实、写真根本不是文人画家兴趣之所在,所以,西洋画在文人阶层影响甚微。与西洋画在宫廷阶层和文人士大夫阶层所经历的遭遇大为不同,民间阶层对西洋画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民间艺人对西画技法积极吸收和创造性融合,使西洋画能在民间长时间的流布和生根发芽,同时也铸就了明清时期民间绘画的新辉煌,对近现代西画东渐的延续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西洋论文; 明清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美术论文; 国画论文; 传教士论文; 郎世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