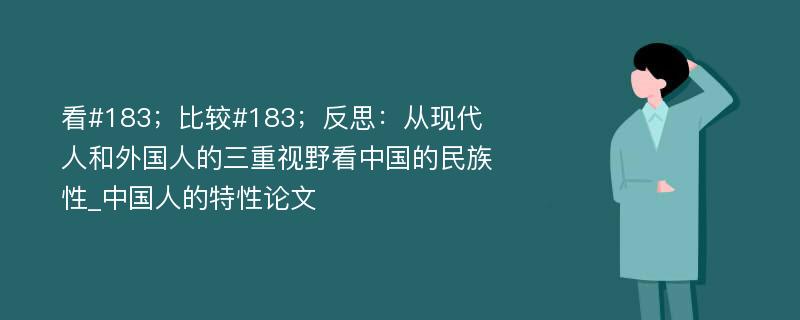
旁观#183;比较#183;自省:近代中外人士三重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视野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6)02-0212-06
国民性批判是近代民族反省思潮的焦点与核心,但在近代中国,热衷于国民性话语,关注与评说中国国民性的并不限于致力于民族反省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中外人士。他们对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一类是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向来的灵魂”,着力针砭国民劣根性,我们所说的民族反省主要是这类话语;一类是来华传教士、商人、政客等外国观察家或说“中国通”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一类是有中外经历、中外两种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以西方民族性、日本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与对中国国民性的照察。
一、西方人与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
最早以现代的国民性观念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民族性格与比较中外民族特性的并不是中国的思想家,而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外交家与旅行家等外籍人士,可以说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是在西方与日本的国民性话语的启发下,在外籍人士有关中国国民性之言说的影响下展开的。近世以来,曾经有不少外国观察家在试图说明中国民族性格方面作过努力和尝试。
中国人在西方视野里的形象像“变色龙”一样,总在变化着。自16至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倾慕有加,如利玛窦(Mattew Ricci)在《中国札记》里称赞了中国人温文有礼、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1]188。殖民主义者将中国人说成天生要受他们支配的低劣民族。某些西方观察家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中国,比较公正地评论中国民族性格。他们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如:坚韧,称赞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能克服任何困难的民族,罗斯(E·A·Rose)将这种性格归因于中国人经历的“优胜劣汰的程度更严格”,艰苦环境使只有20%的婴儿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幸存者“带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基因”[2]44;和平,中国人贵和、宽厚的特性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和谐是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基本的和主导的思想”,“西方人总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和平安宁的国家”[3]94,103;适应性强,他们对中国人所体现出的能应付种种意外、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极强的生存能力有同感,并表示推崇、赞许;等等。近代来华西人也指出了中国国民的一些劣根性,如:保守,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凝结在孔、孟等少数圣人的经典中,称中国人相信“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句格言;封闭,他们对中国人以“天朝上国”或“中央王国”自居而鄙视他邦为蛮夷之邦不以为然,批评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指出中国人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世界,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变得“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现代技术和科技”[4]50;迷信,指出迷信弥漫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心态,有祖宗崇拜、宗教迷信、风水迷信、鬼神迷信、日期时辰迷信等,“还有其他形形色色超自然的神力威慑着人们,使人们战战兢兢,勉力相从”,好在“中国人还具有冷静的头脑、善良的天性和务实的眼光”,否则,“帝国之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迷信,也许早就把这个民族变成了神经错乱的疯子”[5]113;矫饰,指出中国人死要面子,至于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人很讲究礼节,但欧洲人“通常却对这种礼节的真诚性产生疑问”[3]198;等等。
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第一个对中国国民性作出系统分析的外国观察家,他的《中国人的特性》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作。该书分27章评介了中国人的特性,有褒有贬,但总体色调是灰暗的,谈及了中国人好面子、保守、排外等特性。该书的第一章是“面子”,认为“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打开中国人特性中许多“暗锁”的金钥匙。他指出,中国人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旧时地方官被杀头时还要穿戴官服,为的就是保住面子。为了“脸面”,“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6]8,行动时摆出演戏的姿势,思维采用戏剧化的语言。在一切复杂的生活中,完全依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有人捧场就会“有面子”,喝倒彩就是“丢面子”。该书所论及的其他特性多与“面子”有关。第四章“客气”讲到,中国人已经把客套的艺术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礼节过于繁琐,是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表现。第十二章“蔑视外国人”说中国人盲目自大,对外国人抱有毫无道理的优越感。第二十五章“缺少信用”,认为“虚伪、欺骗、不守信用,趋炎附势才是中国人最为突出、明显的特性”[6]239,中国人为了“讲面子”尽管心里不愿意,但还得有虚伪的客套。第二十六章“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中的一句话道破了“面子”问题的思想根源:“与其他民族依靠物质上的力量不同的是,中国人是依靠精神上的力量方才获得生存与发展的。”[6]260中国人需要以道德荣誉感、精神“优胜”感来安慰自己,满足自己,这是好“面子”的根源。该书谈及的其他弱点主要有: (1)缺乏时间观念。西方人的问候语是:“干得如何?”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中国人的问候语是:“吃过没有?”“吃”的时间长得没完没了。中国人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如“中午”、“半夜”等。(2)缺乏精确习惯。如在数字的运用上,离城1里到6里不等的村子都可叫“三里屯”;才满70和80好几的,都是“七八十岁”;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3)因循保守。中国人确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对现状不满不是使中国人向前看,而是使他们向后看,他们相信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其他如“有私无公”、“知足常乐”、“相互猜疑”等。
近代日本人评说中国国民性,从思想倾向上看可区分为“左、中、右”三种视角: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鲁迅称其“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7]267,可代表“左”的观察视角。他通过对中国人生活的长期观察,发现中国人性格、气质中确有令人叹服的宝贵品质,有着独特不凡的生活智慧与美德,如他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从内心深处同情穷人,嫉恨富人等。渡边秀方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大体透出做学问的严谨和静观之态,体现了大体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书中对于中国人有好的就说好,乃至心悦诚服地夸赞;有不好则说不好,乃至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军国主义分子原物兵卫在《中国民族性之解剖》一书中极力诋毁中国,列举了中华民族的种种缺点,代表了“右”的视角。近代日本人眼中的国民性,比较集中的特点有:(1)天命思想。渡边秀方指出:“考察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果忽视了天命思想,那是难以讨论下去的。天命思想是中国人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一切都受天命支配。[8]121(2)家族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人尊祖先、重孝道,指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没有像中国人那样重视血缘关系,那样重视家族生活的,并批评中国人不能由家族的集合导出国家观念,因而常缺乏国家观念。(3)守旧尚古。渡边秀方指出,中国人的保守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开口尧舜,闭口周公孔子,“不放眼未来,而置于过去,这可以是证明他们先天保守的资料之一。”[8]178(4)重形式,顾面子。他们指出,中国人的重形式表现在方方面面,如礼仪的仪式繁杂得惊人;再如文章,尤其是八股文,作者为了形式的完全,而戏弄自己的思想;还有如社交,照例的虚礼和客套话很多;还有,中国人自古就非常重视体面,如在对外政策上“实利可捐,面子必争”,古代王朝可以给夷狄送岁币,“只要名义上的能以哥哥辈自居,呼敌国为弟弟辈,那就算心满意足了”,近代也是如此,“只要体面不坏,租借地等等似乎是没有问题的”[8]186-189。(5)功利实际。内山完造通过很多具体事例说明中国人功利心重,过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实际生活”,认为“福禄寿在支那,实在是最大的宗教”。中国人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色欲、食欲、生欲之满足,也就不可能把非功利、超世俗的宗教和爱情当作生命的归宿,也就不可能出现有很高精神境界的殉教者和情死者,中国人只追逐“彻底的实际生活”中的福禄寿[8]102。(6)文弱和平。渡边秀方认为,汉人是世间少有的和平的民族,他们对敌对和入侵的异族总是耐心地以自己的文明去感化、同化,“就是对‘武’字,也以‘止戈为武’相解释”[8]250。近代日本人还指出了中国国民的矛盾特性等。
二、局外“旁观”对先驱者“自省”中国国民性的影响
近代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对中国近代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外国人的眼光打量中国人自己,以达到民族的自省、自警、自励,是近代民族反省思潮的重要特点。近代国民性批判思潮受启发于“旁观”者的视角,是晚清以来启蒙话语接纳西方话语影响的典型例子。
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对民族反省思潮影响最大的要首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即深受其书启发。外国人论及中国文化与国民性,有赞扬的,有批评的,前者总遭到启蒙论者的反感,他们更多地借取、吸纳了西方“旁观”者灰暗的中国观。鲁迅曾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外国人享用中国奉献于征服者的盛宴,自然欣然色喜,免不了要赞颂中国固有文明。倘有具备“赴宴”资格的“外国的谁”批评中国,表明他“是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9]214-215。对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冷峻地批评中国民族性格的缺陷,鲁迅就颇为赞赏,他一生中多次介绍并力主翻译该书。在1926年7月2日的《马上支日记》中,他谈到日本安岗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他似乎很相信Smith《Chi 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10]3261933年10月27日他在致陶亢德信中说,日本的“支那通”攻击中国弱点,“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11]2461936年10月15日,即鲁迅逝世前14天的《“立此存照”(三)》一文,还这样嘱托:“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意怎样的是中国人。”[7]626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认为“面子”是理解中国国民性的关键,即与该书篇首对中国人“好面子”特性的剖析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曾说:“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作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10]326好“面子”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重形式,为面子而“做戏”,而“欺瞒”。对此,史密斯有所揭露,鲁迅也进行了针砭,从中可寻出鲁迅借鉴史密斯思想的轨迹。1925年7月,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批评中国人没有正视人生与社会的勇气,“万事闭眼看,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9]238-240,呼吁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觉醒。 1934年在《说“面子”》一文中提到外国研究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7]126鲁迅塑造的阿Q备受欺凌,丢尽“面子”,但仍要以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史密斯批评中国人“蔑视外国人”,鲁迅对中国民族自大狂的认识,应该是受其影响的。在提及史密斯说“面子”的《马上支日记》中,鲁迅提到一些留心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的外国人,不但对此早有心得,且已加以应用。他们在取得外交实利的同时,颇顾及“支那人”的“体面”,如连“支那人”三字也不说而代以“华人”。《说“面子”》一文谈到,外国人研究透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相传洋人到总理衙门要利益,一通威吓,中国官员满口答应,但取得实利后却从边门出去,没走正门而走边门,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外国人有意识地专要实利,专将“面子”留给我们,可叹的是,中国有些人偏偏要“面子必得,实利可捐”,甚至不惜为保住“面子”而自欺欺人。史密斯等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言说是深深影响了鲁迅,但有的学者强调鲁迅国民性话语不过是西方传教士话语的复述,尤其是史密斯的书“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12]81,则是欠妥当的,明显低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原创性。
史密斯的国民性话语不仅深深影响着鲁迅,也影响着其他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如在20世纪 30年代中期,潘光旦将该书首次译成了中文,并将其中的15章重新排序,作为其专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部分发表。
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对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批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曾经两次提到日本人市村赞次郎有关中国国民有五种矛盾性的说法,并表示了某种认同。这五种矛盾性是:一是保守而不厌变;二是从顺而有时反抗;三是一般文弱而个人有所反抗;四是极好主我而又能雷同;五是贵实行而泥于形式[13]174,253。1926年7月2日,鲁迅买到日本人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他在《马上支日记》中多处议论此书,希望中国人都读读此书,因为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几乎同时,周作人因安冈秀夫的这本书写了《支那民族性》,主张将这本书译出来,发给人手一编,让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劣点。鲁迅还于1935年3月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作序,表示:“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尚以此自足,却有害。”[14]683可见,鲁迅等先驱者在反思与针砭国民性时从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吸取了营养。
三、近代中外人士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
近代中外人士还以异域文化的背景透视中国民族特性,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国民性,形成了民族反省的又一思路。
近代中国哲人对中西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比较。早在甲午战争前,多位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的倡导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中国之智虑运于虚,以义理为本,重道轻器;而西洋之聪明寄于实,西人穷研万物之质,重艺轻道。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变革,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这就推动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民族特性、中西文化心理的同异进行比较与认识。严复在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政论《论世变之亟》中,列举了中西方由于不自由与自由这一根本区别而导致的“丛然以生”的“群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5]3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则以西方资产阶级国民的标准,抨击中国人的缺点,评论中华民族的不足。他认为,当时世界各色人种中以白色人为最优,原因在于“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能传播文明”[16]10。他列举了西方民族所以强而中国民族所以衰的种种表现,包括: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中国“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一私人之事也”,而泰西“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以对于一团体之事也”[16]12。“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日每况愈下也[16]29,“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16]23;中国人缺乏权利思想,而西方人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我国民仰治于人”,无力自治,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富于自治精神,“世界中最富于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若者也”[16]51;中国人力主复古,而西方人则推崇进步,“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之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16]51;等等。维新派强调民智未开,不能遽用民权,故每言中国国民性不及西人。革命派虽有人如邹容等以共和国民的标准抨击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但认为不应以国民素质为借口抵制共和革命;或强调国民愈需要启蒙就愈需要革命,因为专制政权是造成国民愚弱的根本原因,革命本身就是开民智的基本手段;或强调中国国民程度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戊戌时期开始酝酿的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重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中西民族文化心理的比较,到了五四时期成了启蒙思潮的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均关注中西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比较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基本取向是扬西贬中,主张取法欧美。陈独秀以西洋民族独立、自由、进取、向上的民族性衬托出东洋民族“卑劣无耻之根性”。他对中西国民性作了广泛的对比,1915年底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即对东西洋民族之差异作了系统的比较,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17]97-100。李大钊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之根本异点》一文中,罗列了中西文化心理的种种差异。他说:中西两大民族的根本差异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其他差异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通过对比,他认为与西方民族相比,中国国民性有以下弱点,“(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 (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 (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盛行”[13]557-560。鲁迅在抨击中国国民劣根性时,也以西方的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为参照,指出了中国人较之西洋民族的欠缺。他称西方的卢梭、尼采等为“轨道破坏者”,“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9]192;中国人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即“党同伐异”、“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而没有西方人那种“个人的自大”,没有那种“独异”、“对庸众宣战”[9]311。胡适指出,“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是:“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换句话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西方民族在无穷的进境上不断探索,不断奋斗,创立了工业文明、科学世界与自由政体。相对于西方,“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8]6-12。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上述言论,在批判摧残人性、人格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的背景下,主要显现了其合理与深刻的一面。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中西民族心理比较上的基本取向则是褒中贬西。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具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西方各民族不是缺此,就是少彼,都不像中国一应俱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法国人灵敏却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人生“三路向”说:西方人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奋力改造局面;中国人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在既成境遇上求自我的满足;印度人是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既不想改造局面,也不想变更自己的意思。中国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积极进取,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消极禁欲,而是随遇知足,不论境遇如何,都可以满足安受。
近代哲人对中日民族性格也作了深入比较。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士大夫认真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注意、发现与吸取日本民族的优点与长处。维新派主要领袖康有为认识到日中两大民族“以不更化则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则强弱之效如彼”[19]152,更化和不更化,其结果如此截然相反,所以中国“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以开创治天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守旧不变,居风雨飘摇之室犹然酣嬉鼾卧,终使国家弱亡,而日本“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遂使国家强盛起来,他说:“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20]152。革命派孙中山等人也注意到了中日两大东方民族一个昧不知变,一个乘势变法,造成一弱一强局面的情势,指出日本善于吸取外来文明,“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中国文明曾领先于世,“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落伍了[21]278。其他差异还有如中国文弱与日本尚武,中国人依赖服从与日本人自尊独立,等等。新文化阵营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在中日比较方面,都发表了重要见解。陈独秀指出,在东洋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征服者“好勇斗狠,不为势屈”,被征服者“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中国“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大多数国民缺乏政治觉悟,日本有国民运动,“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17]102-104。李大钊认为,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明,而中国民族由于固有文明深厚,导致新旧文明冲突激烈,形成矛盾之国民性。他指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况在吾国,以其固有之文明与外来之文明相遇,离心力强,向心力弱,即同化之机不易得,即归一之径不易达。故曰‘矛盾之生活,亦不统一之生活也’。”[13]254胡适批评中国全国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称赞“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认为“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22]385-387。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贬中扬日的态度,与其在启蒙思潮中猛烈抨击国民劣根性,倡导学习西方民族(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长处的整体取向是一致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对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伍于日本的原因作了分析:一是中国的文弱、颓丧与日本的尚武,进取。二是中国的“排外”和日本的“开国”。三是中国失却了自信力而日本具有自信力。四是日本人信仰的真实性与中国人信仰的功利性。五是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
近代来华西方人与日本人也对中西、中日国民性作了比较。来华西人对中西国民性所作的比较如:“他们是和平主义者,而我们则崇尚武力;他们强调清静无为,而我们则提倡奋斗的生活;他们放任自流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而我们则认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们则快要沦为只注重物质享受的实利主义者;他们是不可知论者,而我们相比较而言则是较为虔诚地信仰宗教;他们崇尚文学才能,而我们则崇尚科学;如此等等差别,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列举下去”[23]1-2。日人对中日国民的比较集中体现在内山完造在《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它对日、中、英三个民族的不同根性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是孤岛根性,很认真,养成了直线生活的习惯,而中国人是大陆根性,是曲线生活,富于融通性;等等。
[收稿日期]2005-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