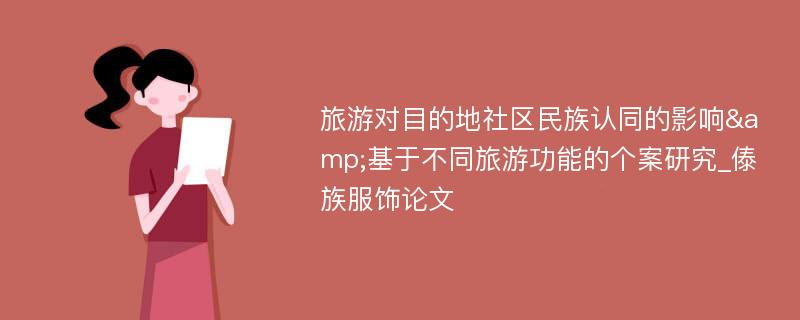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族群论文,案例分析论文,目的地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促使地域之间、族群之间的障碍被逐渐打破,到遥远的地方去旅游,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族群也成为当代旅游者的普遍追求,主客之间的互动也因之成为族际交往的常态。而随着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交流和接触的增加,他们也会发现彼此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种种不同,尤其当两者是来自两个迥异文化的族群时,这种情形下的交往就会产生对各自族群的认同问题。
由于游客来自五湖四海,地位身份各异,且一般而言在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较短,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又会回到原先熟悉的环境,相对而言,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就不如目的地居民那样持久而剧烈(彭兆荣,2004)。在族群认同意识方面,“由于游客在进行旅游之前,一般就已经建构了自身的族群认同”(Hitchcock,1999),因而他们对自身族群的所属就不会那么敏感。相反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在与大量异质文化的游客交流之后,其本身的文化必然会发生变化,即发生所谓的“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庄孔韶,2006)。而外在文化形式的变迁又必然会对族群认同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族群的认同意识是依附在这些文化形式之上的(周大鸣,2001),但在某些族群中,认同并不一定随着文化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孙九霞,2003)。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特定的族群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出发点。
目前,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外学者进行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并归结出了所研究案例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所发生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特征。艾德马斯(Adams,1984)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托六甲人(Toraja)为迎合西方游客的需要,将一些在本地已较为少见的文化元素如传统的船形屋、水牛祭礼等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强化了托六甲人对即将消失的族群文化的认同,但也有人开始认同游客的文化而成为基督徒。此案例揭示了较强程度接触下对族群认同的分化作用;伊斯曼(Esman,1984)在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Cajun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原本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法裔卡津人(Cajun),因受到一股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法语地区游客对卡津文化强烈兴趣的影响,重又建立了自身对本地文化和族群的认同。这说明对当地人文资源感兴趣的游客与主人深度接触下强化本地族群认同;佩奇福德(Pitchford,1995)在对威尔士的旅游业的研究中则发现,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要求地方自治的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普通威尔士民众的族群认同意识得到了重新建构和加强。这是对高度参与、深度接触下加强族群认同的分析;盖姆坡(Gamper,1981)对南奥地利两个族群界限明晰、文化截然不同的族群的研究发现,在开展山地旅游业之后,出于合作开发的需要,两大族群开始逐渐融合,这是对于两个目的地族群旅游合作发展而强化族群认同的解释。除了案例研究,也有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波哥黑和凯斯(Berghe & Keyes,1984)认为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性旅游一方面使得当地居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马康奈尔(MacCannell,1984)则提出旅游发展既给目的地带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又因为游客的需要而终止了当地社区的文化发展,即造成了所谓的“博物馆化(museumized)”现象;希契科克(Hitchcock,1999)从情境论(工具论)(Situational Perspective)的角度出发,认为旅游促进了新生国家中认同形成的进程。
同样,国内学者在进行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时也关注到了其对族群认同变迁的作用。旅游开发初期,学者们更多关注旅游对民族、对社区的消极影响,积极倡导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刘晖,2001;黄芳,2002),但在旅游对族群认同的作用方面则乐观得多。有的学者认为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徐新建,2001),后者揭示了族群本身对旅游开发的积极认同。大多数研究认为旅游强化了族群认同。“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的不断展现,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杨慧,2003)。有的研究更具实用性,将旅游看作实现族群认同和文化要素复兴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族群的精神重建(白杨,2006)。
虽然此前这些学者就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对单一旅游作用下的族群认同进行了分析,对主客关系的探讨也上升到了理论层面。但这些研究往往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视作不分场域、不分对象、不分类型的普遍现象,而忽略了对旅游影响进行不同强度、不同参与程度的细致区分,不考虑旅游者的类型和主客交往的程度,也忽略了目的地社区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由于在旅游过程中,相对于以个人身份参与的旅游者,目的地社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并且受到旅游接触的持续性影响,因此,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族群认同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作者在近八年的旅游研究中,调研了许多旅游社区,深刻感受到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多次调研①过的云南迪庆雨崩村、西双版纳傣族园、深圳民俗村可以作为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代表。下面将逐一讨论和分析这三个案例地,解读在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中,族群认同是如何变化的。
一、低强度、深接触下的旅游作用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
低强度、深接触下的旅游作用是指:游客的数量较少、类型为追求深度旅游的自助型和生态型的散客、主客之间的互动较为深入的旅游目的地影响。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属于这种旅游作用类型。
(一)备受散客青睐的迪庆雨崩村
雨崩村坐落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以西,距德钦县城约63公里。由上、下两个自然村落构成,称为雨崩上村和雨崩下村,隶属于云岭乡西当行政村管辖。雨崩村因拥有雪山冰川、神瀑冰河、高山湖泊、牧场草甸、原始森林等丰富的雪域高原景观,而被海内外游客称为真正的“香格里拉”和“世外桃源”。
雨崩村目前有33户人家②,共计182人。村民以藏族为主体,在2008年5月调查时村中还有四位汉族人和一位纳西族人,一般在旅游旺季时还会有外地其他民族的人进入雨崩打工,如维西县的傈僳族等。汉族中有一位是来自四川的上门女婿,其他三人均是从大理来的打工者。那位纳西族人也是因通婚而来到雨崩。大部分村民只能使用简单的汉语与游客打招呼,能够熟练使用汉语交谈的人并不多。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很大比例。
在旅游未开发之前,全村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畜牧业和农业。牧业收入(包括肉、奶、酥油等)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而每年六七月到雪山下的草甸采挖冬虫夏草、藏红花和松茸等山珍,也一直是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作为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社区,宗教信仰在雨崩社区影响力很大,村中的藏族男女都笃信藏传佛教。在对两位因通婚而来的异族村民访谈时,他们也坦然承认自己信仰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文化、藏民族文化是雨崩社区文化的主体。该村作为前往“内转山”活动圣地—神瀑、冰湖的唯一通道,是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玷污的。同时,因雨崩村坐落于缅茨姆峰之下,村民认为时时都受到神山的保佑,他们非常珍视这种赐福,不敢对神山圣水有丝毫亵渎。雨崩村民对神山、圣湖的虔诚护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周围森林、湖泊起到了重要保护作用。对村民而言,这种源自宗教的敬畏甚至比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还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在访谈中,一位村民说道:“神山是不能破坏的,现在除了烧火的柴可以砍一点以外,只能砍伐那些被去年龙卷风吹倒的大树了。对神山不敬,神山会不高兴的,去年雪崩死的游客就是因为对神瀑不敬啊!”可见,雨崩的藏族对于其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极为认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使得那些慕梅里雪山、缅茨姆峰等自然景观之名而来的游客对于和谐、静美的雨崩村倍加青睐。
(二)雨崩村旅游业发展状况
自从1989-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念青卡瓦格博峰时,在雨崩村附近搭建大本营作为登山基地之后,它便渐渐被外人所知,之后少量徒步者、背包客等探险型旅游者开始进入雨崩村。2003年德钦县主办的梅里雪山文化年活动,一下子缩短了雨崩村和外来游客之问的距离,雪山和原始森林深处的雨崩村突然活跃了起来,“在村干部的积极带领下,走旅游路、吃旅游饭的梦想变为现实”(洛桑嘉称,2006)。由于雨崩村没有对游客进行过统计,所以无法得到进入雨崩村游客的确切统计数据,但据当地梅里雪山管理局人员介绍,进入雨崩村的游客主要是以散客、自驾车游客为主,约占进入梅里雪山景区的1/4,2005、2006和2007年进入雨崩游客的数量大约为11,300人、14,313人和14,228人。
而目前雨崩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物还是以自然景观为主,雪山、神瀑、圣湖,以及长期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神秘感和所享有的“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等盛名,吸引了一小部分探险旅游者和先锋游客。而对这些颇有游历经验的老“驴友”③来说,尽管雨崩当地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也有一定的观赏性,但脱离不了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相比绝美的自然风光,其吸引力并不是那么突出,因此,反映到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形式来讲,基本就以为游客提供进山观光和探险的后勤服务为主。
游客的到来,使雨崩村民纷纷参与旅游业,并获得了一定的旅游收益。具体来说,雨崩村社区(含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有三种方式:一、租马和牵马。牵着自家马匹搭载游客;二、为游客提供向导服务。基本都是游客随机的选择当地(包括雨崩社区、西当社区、尼农社区和斯农社区)较有经验,并且汉话较好的村民做向导,游览线路主要包括参观神瀑、大本营、冰湖和神湖等景点,或进入藏族家中进行家访;三、食宿接待。一些条件较好的村民也通过开客栈为游客提供食宿来得到一些旅游收入,截至2008年4月,村中共有14家挂牌经营的客栈。
(三)旅游对雨崩族群认同的影响
由于旅游开发较晚,加之可进入性极差(需从昆明到香格里拉,再从德钦到西当,然后走一条极难的山路到雨崩,某些季节还会因天气原因封山),因此,尽管雨崩的名声已通过旅游者的口耳相传及驴友的网络游记传开,但真正进入雨崩的游客人数依然极少,2007年不足1.5万人,相对于其他同等品质的成熟旅游景区动辄几十万的游客接待量,其游客数可谓少之又少。雨崩的旅游开发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者的进入并没有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冲击,旅游作用于社区的强度是比较低的。
但主客之间的接触深度却是很深入的。进入雨崩的游客以散客为主,他们属于先锋旅游者,不追求食宿设施的高档化,而关注于心灵的体验,对于当地的文化和自然持尊重态度。游客吃住在居民家里,关系亲密、自然,许多人离开后还与主人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来看,雨崩社区景观的类型以自然景观为主,游客基本以探险和观赏自然美景为目的,村民为旅游者提供的服务也多以后勤保障为主,不涉及自身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售卖,其宗教祭祀活动和传统文化习俗依旧保持原貌,没有受到旅游商业化的侵袭,相对于旅游发展前变化不大。因而在旅游低强度、高接触作用下,雨崩社区保持了其原有的族群认同。
当然,随着外来者的进入和与他们的不断交往,雨崩村民还是发现了自身与游客的种种差异。以神山、神湖、神树信仰为例,当地居民普遍笃信神山、神湖,而游客们则不以为意,这就与村民的信仰造成了冲突。而2007年5月4日造成2名游客死亡、多名游客受伤的雪崩事件更让村民们坚信,是由于游客在神瀑下脱衣服洗澡这种对神山不尊敬的行为才引来神瀑的惩罚。这些与个别外来游客的价值冲突使得村民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自身族群的独特性,并在这一反向作用力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对自我族群的认同。
二、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强化了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
高强度、浅接触下的旅游作用是指:游客的数量较多、类型为追求观光旅游的大众型团队游客、主客之间的互动较少并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浅层次上的旅游目的地影响。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社区属于这种旅游作用类型。
(一)广为团队游客选择的西双版纳傣族园
傣族园景区位于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27公里的勐罕镇政府所在地。主景区由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五个保存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是西双版纳州集中展示傣族宗教、历史、文化、习俗、建筑及服饰饮食等的特色风景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傣族园公司将五个自然村寨的全部生活区和部分生产区划归景区,景区是以社区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景区和社区叠合在一起,是一体化的。这五个村寨在行政上由勐罕镇下属的曼听村委会管辖,2007年共有村民314户,1,487人。其中,傣族1,476人,占99.26%,汉族11人,占0.74%。主要以农业和橡胶业为主,共有水田3,049亩,人均2.05亩;旱地810亩,人均0.54亩;橡胶1,479亩,人均0.99亩。社区生活是景区主要的构景要素,傣族的宗教、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干栏式建筑特征是景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寨社区的生产、生活也成了旅游活动和展示的一部分。傣族园的游客构成中主要以团队为主,散客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二)傣族园旅游开发历程分析
1998年,广东东莞信益实业总公司投资开发傣族园,后来因运作过程中出现资金短缺,1999年3月,橄榄坝农场投资1,000万元,控股60%参与开发傣族园。2000年8月广东信益实业总公司退出股份,由橄榄坝农场和昆明宜良南洋建筑公司合股建设和经营、管理景区,昆明宜良南洋建筑公司是用建设过程中投入但无法收回的工程款加盟傣族园的。目前,傣族园为股份制企业,股东为国有橄榄坝农场和昆明宜良南洋建筑公司。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傣族园1999年8月1日正式营业,2001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2002年通过ISO质量、环境体系认证。自开业至2007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8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7,022万元。
傣族的宗教、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干栏式建筑特征是景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寨社区的生产、生活也成了旅游活动和展示的一部分。景区所包含的五个村寨都具有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典型特征,是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迷人的热带风光的最佳组合,并且每个寨名后面都有特别的含义,“曼”在傣语中是寨子的意思,曼将是篾圈寨,曼春满是花园寨,曼乍是厨师寨,曼听是宫廷花园寨。寨子里的村民与景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傣族园公司所推出的旅游活动和产品,主要依托于村寨固有的民俗文化和社区活动场所(如佛寺等),并在村民的广泛参与下开展。
(三)旅游对傣族园族群认同的影响
与雨崩社区居民自发开展旅游相比,受商业公司控制的傣族园社区的旅游开发明显要成熟得多,整个社区实际上形同于一个大的景区,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又会成为旅游表演的主体,村民的生活实际上整体成为被游客消费的产品,出于利益的驱动,为满足游客对于傣族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的好奇心和强烈的窥视欲,傣族园开发商调整了部分傣族传统习俗。如泼水节本来是傣历新年时的庆祝活动,但为了让所有游客都能感受到泼水节的狂欢氛围,泼水节成了每天都上演的活动,毋庸置疑,泼水节中本来蕴含的文化意味就会大打折扣,成为一种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其他类似的文化展示活动也是如此,要让本地居民对这些被当作商品售卖的文化习俗产生认同虽然并不可能,但由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可以交换、可以卖钱,社区居民对这样的一种“展演”形式还是非常认同的。“对于在旅游社区或村寨旅游点的文化,首要的工作是清晰区分出整体文化中用来展示给人的部分。认为展示给人的文化部分即便有一定的表层性,它依然在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上有重要价值”(麻国庆,2000)。傣族园景区的傣族老人,通过织锦、傣首饰加工、贝叶经刻制、制陶、榨糖等工艺过程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从事民俗活动展示的民间艺人的年龄偏大,都在50岁左右,最大的已经接近70岁,因为年轻人对于传统的民族手工艺掌握得不多。但除了加工出的产品归自己外,公司每月还发给他们100-200元的工资。民间工艺以往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今得到市场、外来者的认可,他们从民间传统中直接受益(孙九霞,2005)。这有助于唤醒傣族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意识凸显。
当然,由于与潮水般不断涌来又退去的团队游客的长期接触,傣族居民还是能够敏锐的感知到自身与游客之间在族群身份上的差别。同时,也由于傣族园景区确实是这里的居民真实生活的场所,因而居民对于本社区、本族群的认同日益强化。如笔者在2003年10月观察到的傣族园曼乍村一场“赕佛”④仪式中,曼乍村的居民和附近佛寺的小和尚笃定而坦然地进行敬献供品和诵经祝福的活动,全然不顾园内游客们好奇的目光,这充分表达出他们对于傣民族最深层文化元素的深刻认同。由于团队游客往往只在这个展示人文景观的社区里逗留1-2个小时,主客之间的接触只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他们退去后村寨变迅速复归宁静。这种族群空间的留存,使傣族文化尽可能少受商业旅游侵袭,也为傣族族群认同保留最本质的文化内核。
三、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主题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
高强度、异接触下的旅游作用是指:游客的数量较多、类型为追求观光旅游的大众型团队游客、主客之间的互动是异化的、错位的、扮演型的旅游目的地影响。异接触主要体现为游客接触的并非是真正的主人,即使接触的主人是本族群的扮演者,其上演的文化也是经过再造和加工后的文化符号;而主人和客人本身并不刻意寻求文化的真实性,此场域下的双方对族群文化的认知也容易发生异化。深圳民俗村的民族文化的主题化展演属于这种旅游作用类型。
(一)造就主题公园神话的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
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深圳湾畔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简称民俗村),于1991年10月1日正式开业,是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与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投资建造的。这是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内含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均按1∶1的比例建成。17年来,民俗村与锦绣中华两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26亿元,创利10亿元。深圳民俗村、锦绣中华迅速收回投资并开业近20年来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堪称中国主题公园开发的“神话”。
民俗村中各民族民居荟萃,有黎族的船形屋、佤族的干栏式草楼、白族雕刻精美的“三房一照壁”、汉族的“四合院”、傣族的竹楼、布依族的石房、摩梭人的木楞房、哈尼族的“蘑菇房”、傣族的竹楼、哈萨克族的毡房、土家族的水上街市、蒙古族的蒙古包、藏族的喇嘛寺、彝族的“土掌房”等。
游客在民族村寨里,除了可以了解各民族的建筑风格外,还可以欣赏和参与各民族的歌舞表演、民族工艺品制作,可以品尝民族风味食品,观赏民族艺术大游行、民族歌舞晚会等。民俗村内有十多个手工作坊,有二十多项民间手工艺和民间小吃制作表演,如维吾尔族手绣、苗族蜡染、傣族竹筒饭等。村内每月都要举行一次如火把节、泼水节一类的大型民间节庆活动。每当夜幕降临,不仅可以观赏民族歌舞艺术大游行,还可以观赏《阿诗玛的故乡》、《神奇的阿佤山》、马战实景《一代天骄》、大型民族音乐舞蹈《东方霓裳》、大型广场艺术晚会《新中华百艺盛会》等系列节目,甚至可以亲身体验科尔沁滑草场、飞瀑溜索等民俗风情。民俗村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
(二)民俗村中民族演员的认同分化
与雨崩村和傣族园不同,民俗村中已经无所谓传统文化被旅游影响或者破坏的问题,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族群,当然也就没有社区原有的传统文化,这里有的只是被商业化所包装的从若干民俗中所截取的符号化的文化元素,居住在这里的也都是签订了商业合同的职业或半职业演员,因此,讨论这些所谓“社区居民”的认同问题,就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对被商业化了的本民族的文化习俗的认同问题和对自身本底族群身份的认同问题。
据笔者在民俗村中对演员们的访谈来看,各民族演员普遍都对这种将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商业化的包装甚至篡改的运作方式相当不以为然,认为那本来就不是本民族的文化。而对于需要扮演其他民族或者由其他民族来扮演自己民族的表演活动,虽然很不喜欢,但却无可奈何。一位傣族的员工就向笔者诉苦:“我曾多次向领导反映希望能够展示原汁原味的傣族文化,不喜欢穿其他民族的衣服,但丝毫不起作用。”比假扮其他民族演员更夸张的是,在所谓的“壮寨”中,里面的民族展示厅已经被改造为风味餐厅,餐厅中的服务员都是身着壮装服装的汉族,而餐厅的老板则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其间无一人是真正的壮族。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民俗村中,演员们对于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他们将自身的族群身份与所扮演的角色截然区分开来,不管展示的到底是本民族的“假”民俗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对附着于其上的文化形式毫无认同之感。这样的一种身份既导致了认同的错位和迷失,也导致了主客之间的接触成为一种异化的、虚假的互动,尽管游客量很大、旅游作用强度大,但由于无论是游客还是演员都明白这是一个人造的景区,主客之间除了共同合影之外其他的交往则极少发生。
但对于故乡的认知无论是新演员还是老演员都无法淡漠。许多初次走出深山、离开本民族聚居区的演员,他们在民俗村中的生活,无疑有助于迅速确立起自身的族群认同,尽管他们表演的内容与真实文化相去甚远,但通过与游客、与民俗村中其他族群演员的大量而又频繁的交往,他们还是很容易能够发现本族群“故乡”文化的特别之处,从而建构起之前在本民族社区中未曾感受或并不明显的自身族群身份。一位在民俗村中工作多年的傣族老员工就表示,通过在深圳、在民俗村的生活,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于傣族的那份深厚感情,希望以后还能够为发展傣族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说明这些远离故土的主题社区的族群成员的认同发生了分化。对异地主题公园中的这种民俗文化展示而言,要么因他们无法改变主题展演的内容而不在乎在异地上演着何种民俗,要么出于族群出身的本能而不认同所上演的民俗;但对于故乡的认同则日益深化,对他乡的文化可以不问出处,但对于故乡的传统和自己的族群身份则日益强化。
四、结论与讨论
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人们的广泛交往,而大量的跨文化、跨族群交往也导致了文化和认同的变迁。本文探讨了雨崩村、傣族园、民俗村三个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目的地社区,认为在这三个类型不同的社区中,旅游对社区的族群认同有不同影响。
雨崩村作为一个旅游发展刚刚起步的社区,旅游者的进入并没有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大范围的冲击,社区居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旅游的影响还较少,旅游作用于社区的强度是比较低的。藏族居民通过与少量外来者的接触,开始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族群身份,初步建立了族群认同。但主客之间的接触深度是很深的。进入雨崩的游客以散客为主,他们关注于心灵的体验,对于当地的文化和自然持尊重态度。游客吃住在居民家里,关系亲密、自然,许多人离开后还与主人保持着联系。雨崩社区景观的类型以自然景观为主,游客基本以探险和观赏自然美景为主,村民为旅游者提供的服务也多以后勤保障为主,不涉及自身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展示,其宗教祭祀活动和传统文化习俗依旧保有原貌,没有受到旅游商业化的侵袭,与旅游发展前变化不大。因而在旅游低强度、高接触作用下,雨崩社区保持了其原有的族群认同。
傣族园作为一个旅游介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程度的社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社区都已成为旅游景区(即“景区化”的社区),村民的生活受到旅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村民的生活实际上整体成为被游客消费的产品,社区中的部分传统文化也以游客的喜好来做调整和变化,社区居民由于与外来者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对自身的族群认同也有了明确的认识。要让本地居民对这些被当作商品售卖的文化习俗产生认同虽然并不可能,但由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可以交换、可以卖钱,社区居民对这样的一种“展演”形式还是非常认同的。由于团队游客往往只在这个展示人文景观的社区里逗留很短时间,主客之问的接触只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他们退去后村寨变迅速复归宁静,这种族群空间的留存正是未受商业旅游侵袭的最本质的文化内核。
民俗村则属于第三种类型,即主题公园化的社区。在这一类型中,旅游的介入已达到了极致,各类可供游客消费的文化符号已经被从日常生活中剥离了出来,在这些社区中,所谓的“居民”基本属于被商业雇用的演员,他们对自身所演出的“民俗”和附着于其上的所谓的“文化”明显缺少认同。这些远离故土的主题社区的族群成员的认同发生了分化。对异地的这种民俗文化展示而言,要么因他们无法改变主题展演的内容而不在乎在异地上演着何种民俗,要么出于族群出身的本能而不认同所上演的民俗;但对于故乡的认同则日益深化,对他乡的文化可以不问出处,但对于故乡的传统和自己的族群身份则日益强化。
综上所述,目的地的族群认同与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类型、主客之间的接触强度和深度密切相关,三个旅游社区的族群认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他们的认同也有着不同的未来发展趋势。雨崩村民所接触的主要是散客,他们的绝对数量不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观赏目标、以尊重民俗为旅游价值观,因而虽然接触深入但并未对藏族的族群认同产生太大影响。但是这种良好的主客互动和“自我”与“他者”兼顾的认同观的维持有赖于可持续的旅游发展。目前,政府、社区和一些外来企业都对雨崩的旅游发展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大多数利益相关者都主张开通公路,既可以方便居民生活,又可以带来大量游客。当大量游客尤其是大量观光型团队游客涌入的时候,33户人家的小小村落的形态和利益格局将大为变迁,居民的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将面临舞台化和商品化,这对于该小型封闭社区族群认同的冲击将难以估量。傣族园社区虽然因为与游客接触程度浅而没有遗落自己的认同,但目前也面临着旅游以外的冲击。傣族社区的经济条件较好,橡胶收入依然占有很大比重,旅游业并不是唯一有利可图的产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其他行业不需要固守传统就可以致富,靠旅游以外行业致富的村民追求现代化建筑和生活条件的行为也因之而无所顾忌,由此导致社区内部的族群认同产生了差异。而民俗村中的族群认同由于文化表演的符号化而产生了分化和淡化。作为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主题公园,虽然开发者努力营造一种真实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气氛,但实际上那些从“故乡”到“异乡”的所谓传统文化的展示基本上是按照取悦游客、迎合游客的标准来截取的。表演什么、展示什么、不表演什么、不展示什么,都要看其能否最大限度地带来商业上的收益。至于该文化元素的本真性或真实性(Authenticity)就已经不是经营者需要考虑的范畴了。这就使得民俗村展示的民俗并不是事实存在的民俗,而是游客希望看到或者说经营者希望游客看到的民俗,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商业化娱乐活动,与原本真实的、传统的民俗相关联的仅仅是借用了其名称和外在形式,其内在的社会、文化意义则相去甚远。民俗村的未来只取决于游客的游赏需求、企业的市场经营,与族群文化展示者的心理认同关系不大,而民族演员的族群认同也将长时期处于这种断裂的分化状态。
注释:
①作者自2002年起曾经8次到傣族园社区调研,2006年5月和2008年4月两次进入雨崩社区调研,2005年6月和2008年8月两次到深圳民俗村调研。
②名义上是有34户人家,但由于下村一户人家虽然分家,但还一起居住,劳动,村民一般认为只有33户人家,本文沿用33户人家。
③“驴友”对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称呼。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来源于“旅”友和“绿”友的谐音,最初由新浪旅游论坛专出。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去过或者很少去过的美丽风景区。
④“赕”指古代东方、南方少数民族以财赎罪;“赕佛”傣语称以物献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