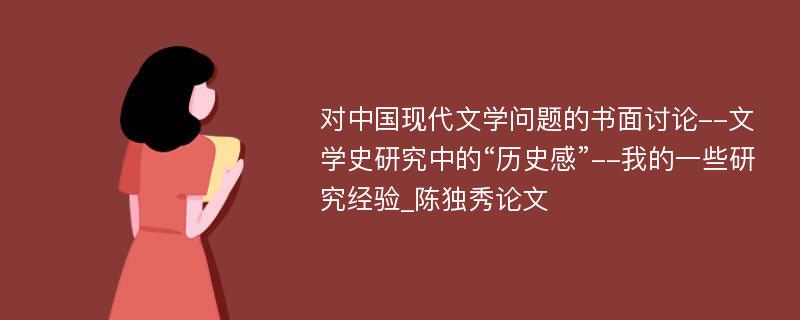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感”——我的一点研究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没有专门做过文献整理工作,这项工作是需要功夫和毅力的,而且需要必备的条件,我不具备,也不行。考虑到会题有讨论“史料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二者关系的含义,结合我的研究,有一些话可说,就说一说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感”的重要性。
我在研究中是比较重视史料的,有对史料的敏感。我认为,文学史研究以史料(经过鉴别真伪的史料,亦可称“史实”)为基础,但文学史又不是史料的堆砌,不是鲁迅批评的“文学史资料长编”,要洞彻史料背后的人的生命现象,即具有“史识”[1](P102-103)。那么,文学史研究怎样才能从史料升华为史识,我认为二者之间缺之不可的中间环节是“史感”。什么是“史感”,“史感”是在文学史史料的触摸中产生的生命感,这种感觉应该以历史感为基础,同时含有现实感,甚至还会有未来感,史料正是因为在研究者的这种多重感觉中获得了生命。显然,我在这里谈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发掘,我谈的主要是如何使我们已经占有的史料转化为我们研究中有生命力的成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史料的发掘。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感是怎样形成的?答案可以在现实感怎样形成中找到。我们对当下文学的感受,显然不仅仅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人生感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则那些作品不会感动你。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经极强烈地触动了我,这是和我的文革经历、和当时整个社会对我的影响直接相关的。但是,当我要研究这篇作品时,就不能局限于我自己的特殊感受,还要找到那个时代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感受,以形成我的“整体感受”,但这个“整体感受”是在我的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丰富了我的感受。历史感的形成也是这样,我读文学史,首先就是去切实地感受那些大量的文学史料,要有感觉,这个感觉的形成就不能仅仅依赖于我在现实人生中的生命体验,要在这个基础上进入那个时代,进入那个社会历史氛围中,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这样才可能对自己所关注的对象在“感同身受”中产生自己特有的生命感。对史料在“感同身受”中的生命感,是我们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形成的根基(注:我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看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敦煌再发现》,片中临摹和复制壁画的娄婕谈自己的创作体验时说,自己在临摹和复制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历史的生命感,这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文学史研究中触摸史料的感觉也应该是这样。)。正是在对史料的这种“感同身受”的生命感中,实现了我们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融会与互补,史料内化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精神主体的有机成分,从而升华出史识。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对此,我认为,就我们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绝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史料。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论争是非常频繁的,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就文学谈文学,而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冲突有密切关系的,并且这种论争直接影响了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革命文学论争”尽管暴露出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但这场论争发生后,大多数从五四走过来的作家的创作转向或倾向于左翼文学。对此1934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从“人”的觉醒到“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前进”中的必然要求,而且,“阶级意识”的觉醒较之“人性解放”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更加贴近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是他们在特定历史境遇和生存境遇中的生命体验的文学表现;进一步说,中国现代作家是在“人”的觉醒的基础上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的,他们的“阶级意识”在本质上要求的仍然是“人”的问题,人的基本生存(人性)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2](P20)显然,鲁迅的这一史识,建立在他在这一过程的身临其境,他对新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向的“整体感受”之上。我们对这一史识的认识,同样需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感同身受”所必须的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整体感受”上。只有这样,我们面对的史料才可能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才可能从不切合我们的实际感受的既有描述中走出来,在我们的研究中获得生命力。
在这方面,鲁迅曾经提出他认识历史注重“野史和杂记”,因为它不摆史官的架子,容易从中感受和认识那个社会,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3]。这值得我们注意。就我自己而言,1978年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就有写文章的欲望,但阅读史料找不到自己真切的感觉,无从着手。1980年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的指导老师邹恬先生借给我看一本曹聚仁写的《文坛五十年》,这是一部“野史”,读这本书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史料视野,使我对文学革命为什么发展为革命文学有了一点自己真切的感受。曹聚仁并非左翼作家,但他在《文坛五十年》中谈到这么一件我们的文学史较少顾及的史实,“1924年春间,郑振铎翻译的《灰色马》(俄国路卜洵Bopshin)出版了,这部虚无主义的小说,到了现在,已为社会人士所淡忘,在当时却是文坛一件大事”,“《灰色马》的出版是热闹的。前面有瞿秋白、沈雁冰(茅盾)的序文,后面有俞平伯的跋文”。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他引出郑振铎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所说的话,“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我觉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怀疑、不安而且蔑视一切”。曹聚仁由此提出,“佐治式的青年,也正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写照,也可以说是所有那一时代青年的写照,虚无思想,实际上,乃是五四运动以后,最流行的思想”[4](P248)——这正是曹聚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感受”。这有助于我真切地感受到鲁迅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5](P159),感受到那个像瘟疫一样漫延着的苦闷的时代病中人的生命表现;苦闷、虚无和怀疑,也正是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我们伴随着解放感的特有的心境。这使我自然想到五四后为什么会出现《沉沦》热,想到黎锦明在19世纪30年代初所说:“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6]由此出发去读1924年前后的文学作品,使我对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所述五四退潮后苦闷期文学以及前面提到的《〈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的史识,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真切的“史感”。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整体感受”,目的在于使我们进入具体的文学史语境中,触摸史料形成的语境感,可以使我们对那些已知的史料有更多的发现和感受,这种发现和感受的核心内涵就是人的生命。我在研究中深深感到,在文学史研究中被忽略或者由于特定背景下的理论概括的需要而被舍弃的“边角余料”,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复原历史,获得更接近历史的语境感,或者说,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描述中的语境感的缺失,可能正是因为把这些史料作为“边角余料”舍弃了。
比如,我在重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注意到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的一段用括号括起来而似乎不很醒目的话:“此时,我应声明:现代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7](P123)我认为,这段似乎与文学无关的话,恰恰有助于我们在五四语境中认识《我之节烈观》这篇能够深化我们对《呐喊》、《彷徨》理解的文章。这段话所以用括号括起来,因为这类“好人”并不属于文章主要针对的“节烈救世说”的鼓吹者;但所以如此郑重地提出,又是因为这种“好人”的思想是与文章主要针对的对象有一致之处,他们也是作者写文章时感受到并明确指向的预设读者,或者说文章主要是写给他们看的,也只有他们有可能看。这无疑增强了我对鲁迅是在什么语境中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感受,使我去追寻在新文化倡导过程中鲁迅这么说有什么具体的针对。当我接触到仍然与文学似乎无关的北京大学1918年1月19日成立的进德会(社团),我从发起人蔡元培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读出了五四极力破除的“酒色误国”的思想,这与“节烈救世说”的内在一致性——在我们的现实文化环境中这类“道德救世”(诸如当下提倡青少年“读经”)的声音还少吗,而有助于我们形成新文化倡导的语境感。当我进一步去清理进德会在北大的位置和影响时,发现进德会为校长蔡元培主持,北大校评议会成员皆为该会领导成员,截至1918年5月24日,入会者已有468人,其中职员91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人数居北大各社团之首;如果考虑到这是北大各社团中惟一的与“校政”直接相联系的组织,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也加入了该会,并且列名为该会的评议员、纠察员,是可以感受到进德会发起宣言提出用以“绳己”、“谢人”、“止谤”的八条“道德戒律”对他们的身心束缚和压迫。1918年1月23日,到北大不久的周作人申请入会,为乙种会员,但他每天回到“S会馆”都要面对正在做“官”又不得不守着一个“无爱的婚姻”的大哥(鲁迅)。对此,我们是可以感受到来自进德会的压力的,认识到周作人为什么首先以《贞操论》发难,认识到他为什么在《〈贞操论〉译记》[8]中把话说得那么悲观——这种感受和认识又是与我们自己的现实人生体验相通的。那么,蔡元培1917年能够聘请陈独秀、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进入北大,他甚至同意陈独秀把《新青年》也带进北大,他为什么还要成立进德会?这显然与蔡元培的观念直接相关,但同时我们也能够从中深刻感受到蔡元培以及引进《新青年》的北大面对的来自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感受到新文化倡导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种境遇中形成的,感受到五四思想文化变革的困境。
我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我们才可能对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中的这段话乃至这篇文章的针对性有更加真切的感受和认识。有这种感受与没有这种感受是迥然不同的,这种感受使我们对以前看过的一系列史料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触。比如,1918年1月15日复刊的《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即陈独秀的《人生真义》和陶孟和的《新青年之新道德》。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出“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且他在文章最后用特大号字说,“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其后的一篇题为《新青年之新道德》的文章援引前文中为陈独秀批驳的孟子的“修身”然后可以“齐家治国”之说,指责“今人”“不思克己修身”却“臧否社会”,“惟社会之是责,他人之是谤,则其诋讦社会,又何异于诋讦一己?”任何具体话语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的,尤其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感觉和认识中似成对立的话语,在《新青年》上都是作为新文化倡导提出的,这不能不改变我们对固有的对五四新文化倡导的单纯性质的认识。而且,蔡元培在反驳林琴南以“覆孔孟、铲伦常”之“罪名”攻击北大时,推出的就是进德会的“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9]。只能在这样一种整体语境形成的“整体感受”中,我们才能认识到五四思想文化变革的艰难程度,认识到《人生真义》的具体针对和假想读者对于作者不是玄远的,而是切近的,就存在于他能够感同身受的语境中,含有陈独秀的这种境遇中切实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挣脱束缚和压迫状态中的生命表现。我认为,我们只有从这样一种语境感出发,才可能更深刻地感受和认识到,正是因为《新青年》的存在,正是因为北京大学的改造使一批新文化倡导者集中于《新青年》,《新青年》才可能在1918年瞬间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空前绝后的变革力度。《新青年》自4卷5号开始连续刊发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周作人译介的《贞操论》和他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等,这些文章和作品异中见同地集中于伦理道德观的变革,而且言辞是如此激烈,与此同时,在“语体变革”上出现的更为激烈的变革主张:新文化倡导者只能在他们深切感受到切实的文化压迫中才能激发出他们生命体验蕴涵的精神资源,触及到中国文化最深层次的症结,触及到至今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问题,而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新青年》自创办以来最富有力度的一场变革。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真正触摸到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整个社会的对立中产生的,这种产生与整个社会的对立程度在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历史上均未曾发生过,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对立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根基,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性质、特征和命运。
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之初就具有的这种性质、特征和命运,又决定了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的迅速退潮。对此的认识仍然需要进入具体语境中,正是期刊保存了我们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思潮影响下更多的被作为“边角余料”舍弃的史料,能为我们提供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语境;作为新文化倡导的核心期刊《新青年》,似乎更能印证那段历史的原形,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复原被我们不断改写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从中感受、触摸和认识到新文化倡导运动迅速退潮过程中的一些不应被忽略的问题。比如,我注意到《新青年》6卷4号(1919年4月15日)与其他各期的不同,即破例在最后加了个“附录”,发的是陈独秀的《我们应该怎样?》——陈独秀的文章在《新青年》上从未这样发表过。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谈着“有自觉智力的人”的“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和“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这两种“危险的人生观”。所说“道德的意识,被和一般动物同样的贪残、利己心……逼迫而去”,此即“发见了自己堕落以至灭亡的原因”;又说“四面黑暗将我们团团围住,不用说这都是我们本性上黑暗方面,和一般动物同样的贪残利己心造成的恶果。有这些恶果,才造成我们现在这样难堪的烦闷生活”;并说“由个人的努力,奋斗,利用人性上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自然以我们努力的强弱为标准”——如果我们真正进入《新青年》自创办以来开创的话语空间和提出的变革话语中,就能看到这种声音在陈独秀已发表的文章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所说肯定相爱互助及道德意识对人的与动物相联系的自然本性的抑制与改造作用,明显与我们前面例举的一年前他也是谈人生观的《人生真义》中的话语的意向迥异。——这使我自然要思考这篇文章是否含有陈独秀当时难以明言的某些生命现象,那种灰暗的调子是不是与他自己当时特有的心境有关,是不是与同时发生的“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事相关。1919年3月1日,北大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定于同年暑假后实施;3月26日,曾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的汤尔和(北京医专校长)打上门来,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促蔡下决心辞去陈独秀[10](P181-182);蔡元培于4月8日召集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不再设各科学长,推选马寅初担任教务长,协助校长组织各系教授会主持校务[11],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已徒有虚名,他在北大已经无事可干(注:据现有史料,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并未开课,他担任文科学长,主要精力在办《新青年》。胡适说他不再担任文科学长后,曾给他安排了课程,但他并没有上这门课就离开了北大。)。此事发生后的《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6号(1919年11月1日)两期上,竟没有刊载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这在《新青年》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这时的文章(只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显然,正是期刊和期刊上的文章为我们暗示出这样一个文学史必须给予重视的事实。而且,我们读期刊形成的这样一种语境感,不仅使我们对那些已知的史料产生了新的发现和感受,同时也能够增强我们追寻和发掘那些被遗弃在“废纸堆”中的史料的感觉和动力。我最初就是在《新青年》(在这方面,只有期刊能够给我们以提示)上陈独秀的文章的发表方式中感受和认识到需要找到“陈独秀离开北大”这一史实的有说服力的材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迫切要求中找到了当事人之一胡适1935年12月23日写给汤尔和的一封信,这封信提供了那个指控陈独秀嫖娼,违背进德会戒律,应去职离开北大的“三月廿六夜之会”的事实[12](P675-676)。考虑到此信写于胡适与陈独秀早已分道扬镳、行同路人的1935年末,且又是写给事件的肇事者汤尔和的,应该说是真实的。当然,这并非是孤证,我由此而在高平叔先生撰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提供的大量史料中得到确证。
我所以将“陈独秀离开北大”作为五四新文化倡导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史实,写进《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中,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件有悖于进德会道德戒律的事情的发生竟然导致这样一个严重后果,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倡导中心形成的脆弱性,缺乏足以对抗整个社会压迫的内在思想凝聚力。更主要的是,陈独秀的离去对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使这个期刊保持着自身思想变革要求的锋芒,《新青年》进入北大后虽然不再是“陈独秀先生主撰”,但他的变革精神仍然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支撑,这种变革精神是《新青年》吸引了大批新文化倡导者加盟的根本原因,是新文化倡导者加盟强化了《新青年》的变革力度的根本原因,是《新青年》1918年后所以能在社会上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注:鲁迅多次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加盟《新青年》时的陈独秀,说陈独秀“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怀刘半农君》中对比在《新青年》编辑会上的陈独秀和胡适,掩抑不住自己对陈独秀的钦佩(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么,“陈独秀离开北大”,他的变革精神在《新青年》开拓的话语空间中的弱化,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群体中的凝聚力的弱化,这是新文化倡导者迅速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史料入手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从“整体感受”出发触摸史料形成的历史语境感,在语境感中形成对史料的新的发现、感受和认识,从而洞彻史料背后的人的生命现象——显然,文学史在这种“史感”中的再审视,是可以不断改写以至重写的。
标签:陈独秀论文; 新青年论文; 鲁迅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我之节烈观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蔡元培论文; 新文化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