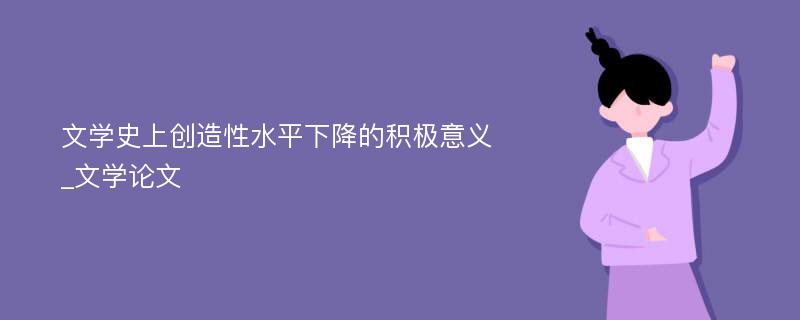
文学史中创作水准退化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水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进程的描述。在一部长时段的文学史中,不管撰史者是站在何种立场,以何种价值观点来评述文学史进程,总会面临着文学发展中的水平起伏状况。即在某一时段中,可能是文学走向成熟、走向繁荣,而在另一时段中,则是看到文学在走向衰落、走向萎顿。面对这一情形,文学史家对于上升段的文学进程是持肯定性评价,反之则持否定性评价,这一点看似天经地义。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述录就会面对着一些价值上的低谷、空白乃至负数的情况,当我们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来看时,这些未被积极评价的时段就与历史线索的整体有脱节之感,仿佛只是为了照应文学史的年序不应空置才将它提及,并且还是作为一个应予克服的消极面来看待。可是如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的话,那么在许多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学价值观可能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我们有权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评价文学,可我们也有义务将文学史的较为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传达给后世,以便未来的人也可以作出他们的较为合理的评判。那么,当我们将认识基点作了这一调整之后,就应在文学史的艺术水准退化时段的积极意义上作一探求。以下则从几个层面来论析。
一
文学史中艺术水准退化是频频出现的。每当文学史著述中指认一个时代某门艺术取得了如何辉煌的成就,那么也就面临着一个“以后如何”的问题。当我们说唐诗的辉煌时,那么宋诗呢?元诗以及明诗、清诗呢?不言而喻,它们在整体上没有达到唐诗的艺术高度,是一种退化。同理,在欧洲文学系统中,古希腊戏剧达到了很高成就,虽然在更晚近的时代也可以列出莎士比亚剧作等作为文学史上后继有人的佐证,但对于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人们认定了其艺术水准不及古希腊时代。
文学史中的艺术水准退化是普遍的,那么它是否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呢?提出这一问题,并不只是要为退化的经常性找到更多的实例,而是如果它是一个规律,那么它存在的合理性就更能得到辩解。
对于艺术的退化现象,在文论家、美学家的论著中很少见到直接作此表述的,但从它们对艺术进化这一相反命题的普遍怀疑和否定上,我们可以见到该种认识的间接佐证。美国批评家克里格指出,“当我们讨论各种人文的、科学的或近似科学的学科以挖掘反映在其中的进步观时,显然,艺术必须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挑选出来,确实需要作为例外来处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论及艺术与进步的关系时,习惯上都将艺术视为同其它学科迥然不同的东西。……反对把进步观运用于艺术作品。”(注:克里格:《艺术与进步观》,见《最新西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如将克里格的否定艺术发展的观点结合到马克思文艺观来认识,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个相近见解,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在著作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也同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把艺术的发展比作植物的不同季节。他用了开花的季节,繁盛时期(Bliitezeiten)这样一词。”(注: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82页。)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来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几个社会阶段,人类未来的社会是共产主义,在这各个社会阶段中,人类文化是与生物进化的规律同构的。但在文艺问题上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将艺术与社会的进化作出比附,他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艺评价较高,对同时代的作品倒并没有特别推崇。马克思在论及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还特别指出:“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在于,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马克思“范本”一说很明确地表达出早先创作的作品,在后来的阶段来看也并未被新作超越的意思,并且新作得从对早期范本的学习与借鉴中触及到文学创作的真谛。既然文学创作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那么后来阶段又没有超越前代成就,由此也就可以说在文学史上退化的规律性特征了。它即使不能拿出一条文艺发展的规律,至少也可以在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不同的意义上来引申出一条文艺发展的规律。
对于科学,对于社会发展,人们可以持进化论或与之相近的观点,认为后来的理论、形态、现实等要胜过以往,可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人们的观念则显得不同,这是何种原因呢?
首先,这在于科学认识、社会实践都面临着实用性的目的,以一种过去的眼光来处理现实的实际问题时,往往会有不切合实际的状况,这就要求人们改进以往的认识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认识事物,而进化论的思想则有助于促动这些领域的知识的进展,可以加强文化累积和发展的动力,而在文学艺术中则不会有这一强大的现实压力。文学艺术中的现实并不直接转化为人们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次,人的文化要求有所发展和创新,也要求有所累积和保存。在人的一般文化领域中,由于现实本身的压力,使得发展创新的要求占有了更为突出的地位,而过去的传统就只好在一种专门史中作出记载,当传统入“史”时,也就是说它已是一种没有多大现实影响力的对象了。而文学艺术记录了过去人们的理想、幻想、生活态度,其中也还包括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核心部分,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部作品的具体生活形态的描写可以被超越,可是民族心理、民族的无意识的内涵是虽经百代而可历久不衰的。当那些古代作品的现实描写方面对于后代的影响力已淡化之时,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则更显示出其深刻性的一面,它可能比当代创作更能触及到读者心灵的深层,由此,人们对文艺自然有较多的怀旧情愫。
再次,文艺表达是以形象来表达思想,以情感态度来看待现实的,因此文艺作品在释义上具有较大的解说空间,这从中国的“红学”研究,英国的“莎剧”研究中可以见出。经过许多代人的阐释评论,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益增多了。文学阐释的空间并不依赖于作者及作者所处时代的界定,它可以是在阐释中体现出当代人的文学体验和社会情绪。因此,过去时代的科学知识可能过时,而在那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随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这正如阿诺德·豪塞尔所说,“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实的,即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塞万提斯,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乔托或拉斐尔,都不会同意我们对他们的作品的解释。我们对过去文化成就所得到的一种‘理解’,仅仅是把某种要点从它的起源中分裂出来,并放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范围内而得来的……”(注: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由于文艺作品可以被赋予新意,使作品在得到新的阐释的过程中不至于过时,同时旧作也联系到当时时代的文化,可以满足人在文化怀旧中的情感需求。由于这些重要缘由,持反对或否定艺术进化的观点有助于维持既有的文学秩序,它才在文化上得到强力支持。
二
当我们明了进化观点并不能简单地移用到文学史中时,我们就可以用其它几种理论观点来看待文学史的进程了。一种是绝对化的静止的观点,认为文学史上的作品都只是对它所处的时代负责,而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就只有特征上的差异而无水平上的高低。另一种是也承认文学史进程上的演进,但认为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各自的审美维度,互相构成了一种反拨与对话的态势与结构,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美学尺度来评价其价值,因而也就难以用进化或退化作尺度来衡量了。还有一种观点作为一种折衷,它认为文学既对它所处的时代负责,也对超越其具体时代背景的文学读者负责,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在问世时的价值与它在后来实际的价值之间有着区别,有时甚至是颠倒的,那么从某一角度来看的文学的某种进步,恰恰是以另一角度来看的退步作为代价的。反之亦然。
笔者认为,关于文学进步和退步的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作出阐明和基本理解,但在对具体文学发展阶段的阐说上缺乏操作性意义,真正在说到某一阶段的文学时,我们得涉及到它对前代文学的承传,对后代文学的启发、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价值比较,否则对此段时期的文学史现象就少了一些根本性的说明。基于此种考虑,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承认在文学史进程中退化阶段的存在,同时对于这一退化也有必要在指陈其不足时,看到它的积极的意义。它包括以下几种类别:
①“下山路”——文学发展的必经之途
如果承认文学史中有着起伏跌宕的态势,文学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那么,就应看到它有走向辉煌的一面,同时它也就有走向低谷的时候。对文学走向低谷作静态的审视,当然它的价值有抵不上走向峰顶那么多值得颂赞的东西,可是既然有高低起伏作为文学发展的走势图,那么走向低谷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为下一步的走向峰顶成了铺垫,它的正面价值在于“走向”上,即不能因为它的水平线不高而否定掉它是为未来的成就进行了必要酝酿的功用。肖驰先生在评价中国诗歌史上晚唐咏史诗是作为盛唐咏史诗的退化时,并未回避晚唐诗风不及盛唐的一面,然而他冷静地指出:“盛唐的确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顶峰。……诗要继续前进,就要越过顶峰,即便是踏上下山路。”(注: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笔者深为赞同肖驰先生这一论断。如果我们将诗歌史的发展再作一个延伸,即由唐诗的繁荣再看到宋词的繁荣,那么唐诗中晚唐的衰变是诗情弱化而诗思骤增,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缺乏形象思维的变化,这从单一的句式整一的诗来说确实是一个阅读中缺乏美感的原因,可是词体是句式参差的后格律诗,它继承了格律诗对于字数、韵脚、平仄、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它又一反唐代格律诗以五言或七言一贯全篇的整一感,句式多以长短兼杂,并且常见词体有几百种之多,可以根据所写内容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用。在一些著名词作中,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也是一些咏史的作品,要说它们的议论色彩是不亚于晚唐咏史诗的,我们可以看到晚唐咏史诗比之于盛唐同类诗作,有缺乏情感韵味的不足,可那是对于句式整一、念来顺畅的诗作而言,在词作的长短兼杂的句式中则有不同,它的念诵由于每句长短不同,要有贴近人们日常口头话语表达节奏的特点,在这时念诵的不顺畅感可加强对它的体验,就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陌生化”效果所起的作用那样。在词的文体中,人们对它的念诵语气蹇迫,其形象的画面感也显得支离破碎,如果以写诗中的写景抒情来衡量,它有不及一般诗体的短处,但它的画面感零散、抒情性受限,也就使得它的议论、明理的特长可以更好地发挥,而这正是词体优于诗体的方面。在由唐诗到宋词的演变中,我们再来看晚唐的以议论入诗的状况,就可见出它虽有从盛唐成就的顶峰上退步的问题,可它也有为宋代词作成就的高峰进行必要铺垫的独特贡献* 由这一全局性的鸟瞰,我们也就可以为“下山路”的水准退化作一些正面意义上的评估。
② 反“化石化”——文学自我更新的机制
化石是过去时代的生物遗体的石质变化。化石保存了过去生物的遗体,使它不至于随时间流逝而腐烂,同时它也歪曲了过去生物的实貌,它是将生物的有机物存在形式转化为一种无机的石质存在,在此转化过程中,是动物的骨头、植物的躯干等部分较多地保留其形状,而动物皮毛、树木的树叶、花蕊、表皮则大多难以留存。当化石在表明自己是过去生物机体的遗存时,它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实质已与该生物体当时的存在状况大相径庭,也许在这里还应提到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化石存在的恒久性恰恰是与生物有机体存在时的短暂、过程性相抵牾的。
将化石化用于文学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认识框架,其理由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总是创作者身处其地,因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与特定的事件、情境、人物关系等相交遇,产生了创作灵感,从而经过某种努力之后创作出了该作品,其作品表达的意思又可能引起读者感同身受的共鸣感或是某种启迪,于是作品得以流传。在这一情形中,作品的存在与作者、读者的有关状况是相互关联的,可以从中剖析出若干复杂的关系,这正同有机体体现的复杂性相似。而当作品经长期流传而被人公认为是传世之作,写进了文学史教科书之后,人们再来审视它的眼光就可能只是将它的作品本文视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所体现的特征就被简单地视为文学成功的一种尺度,这时的作品就已有了化石化的性质,因为它已没有了一种有机联系的网络,也超越了具体时地条件的规定。这一化石化的文学本文,还有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创作的圭臬,使后人的创作难以体现新意。在终极的意义上讲,它使得人们文化的、审美的眼光始终固着在一个维度上,这本身同审美活动中人的自由、开放的精神状态也不吻合。
应该说,在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的态度上,无视前人成就去搞所谓的创新是不可取的,但反过来强调前人成就,并总以前代成就的特征来要求现时的新创也有不可取之处。在此问题上正好是体现了一对在传统与当下中的两难境遇。反化石化的文学取向可以说正是代表了其中的一种为了纠偏而采取的举措。当代美学家莱马里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被创造的东西是无所谓的,只要创造在进行就可以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艺术作品,我们已有了足够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是饱和的和过分饱和的,问题在于要有艺术家,要有想象和自由的具体表现。”“过去人们曾假设没有美便没有艺术,今天人们则认为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艺术即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注:转引自塔塔克维奇《六概念史》,1980年英文版,第八章第五节。)将这一表述结合到当代艺术中的一些情形来看就更好理解,如美国画家劳申伯格有一幅画叫《床》,这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绘画之作,它是由一幅真正的床单,上面再缀上枕套,再涂洒上一些油彩而成。这一作品在60年代的威尼斯艺术展上获大奖。单纯从绘画的美学特征上来看,它基本上与画笔的动作无关,也很难说它有什么特别的美感韵味,关键只是在于它是将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接触一天中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但却多只从实用性考虑而较少从审美上把握的床给予了足够的艺术审视,这一审视又是由真正的床单和枕套作为其对象。它构成了观看者在被要求脱离日常生活审用眼光的同时,又必然保持着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某种张力,这一张力正好是该画作所体现的一种创造性的眼光所致。作为大展获奖之作,它不是在艺术和美的维度受到特别关注,而是在创造性上受到了专家首肯。
③ 网络互动关系——文学的多向选择与发展之道
当我们在言说文学的进化与退化、繁荣与萧条之时,这固然是对文学的创作数量、影响力、美学成就等的综合评价,但从根本上来说,它都是只关注文学自身的情形,尤其是侧重于美学价值方面,而文学的生存之道并不只以美学价值作为追求目标,作家在创作时可以是考虑到表达自己的情志,可以是想到以创作作品作为谋取营生的途径,也可以是因作品内涵刚好吻合了大众情趣而走红一时,等等,这些并不都与作品美学价值呈正向关系,也即它的表达与作品艺术性并不必然相关,但却是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当文学因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发展进程中有所体现时,也许在文学的审美价值上是有所损失的,但这却是文学发展中从事创作和阅读的人的一种自觉选择。
法国文论家埃斯卡尔皮曾对文学生产的经济学内涵作过一番探究。他以版权法的推行为例分析了美国文学的状况。美国作为一个欧洲移民的社会,尤其是由欧洲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它的文化本来就带有母国文化的若干重要特征,当年青的美国在文学上蹒跚起步时,欧洲的尤其是英国的文学理所当然地会带来很大影响。正当此时,由于美国未与英国签署版权法的国际公约,英国作家的创作可以不经翻译就直接在美国传播,并且出版商可以不付给作家稿酬,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为盗版开了绿灯。这一情形给美国作家带来了很大压力。它迫使“美国作家把注意力转向杂志,尤其是转向最适宜于杂志的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注: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在18、19世纪时,正是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它也是作家创作的代表作应涉足之处,因此可以说美国作家在当时被迫在中短篇小说中着力是不得已之举。至少在当时的视角来看,这一创作趋势并非文学进化之举,但它是为美国文学开辟自己的天地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文学史也就应对该种举措作出正面评价。
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为配合五四运动推崇民主与科学的任务而运作的,当年九叶派诗人之一的郑敏教授回顾这一文学潮流时说:“它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在文化上却因拒绝古典文学传统,使白话与古典文学相对抗,而自我饥饿、自我贫乏。”五四一代的诗人,“他们当需要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时就用旧体,每当写白话诗时,力求明白易懂而放弃诗的艺术。”(注: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这就是说,五四诗歌的价值追求已降格为实用文体写作,它的作用在于传情达意,只要将所传达的意思写出来并让人明了也就达到目的,至于作品的审美价值就已相对忽略。郑敏先生作为当年新诗运动的参与者,她对新诗运动的评说就不同于旁观者的认识,多少带有自我批判的性质。这一自省其实在当年的新诗人中就已有人在作了,如穆木天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注:《穆木天致郭沫若》,见《创造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10年之后,鲁迅先生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总结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注:《鲁迅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载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可以说,这些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批评都是中肯的,对于中国这一号称“诗国”的文化国度来说,五四新诗的成就比起古代列祖列宗的光彩难免逊色许多。然而问题在于,除了五四之后新诗运动是当时政治上、文化上进行新创所必须的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应予提及,即在文学中有一个审美的共同因素,它的集中表现是诗歌美学,即只有在诗的开创上有所突破,才能全面带动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上的新创,那么,当我们将目光放到不局限于诗歌创作的领域之后,就可以见出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并不次于晚清小说的成就,五四一代的散文超越了古典散文着力于文人个人情志表达的方面,而五四以后的话剧剧本的写作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语文学中未曾有过,这些进展体现了新的文学审美追求,如果没有新诗运动对于传统的冲击,那么在其它文体中的进展都是难以想象的事,由此综合起来认识,我们对于五四之后诗歌创作的并不杰出也就可以持一份宽容与理解的态度了。它相当于一个开路先锋,也许它并未开启出一条成功之路,但它至少是指出了不成功之路的所在,让后人少走一些弯路。
三
从文学史进程中创作水准存在着退化,并且退化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的认识出发,我们在上文指陈了文学发展进程中退化现象的若干积极意义。本文标题指明了是要讲“文学史”中退化的问题,它同单纯言说文学发展进程还有区别。可以这样来理解,文学发展进程是贯串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它是一个曾经发生并且也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文学史则是对该进程的一种述录,它只是昨天出现的事实,而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实就得留待今后的人来作出认识,它只是文学史的潜在可能性或可能性,同现已存在的述录还有一段距离。
在事实的层面上,至少人们是希图文学向着更好的状况发展,文学退化是人们在感到遗憾之中或许无奈的选择,它的积极意义是在充分体现出消极意义之后的一种展示,或许可说是人们从辩证的观点出发来看到的不利中的有利因素。在对事实作出述录的层面上,情形就有所不同。文学史在述录文学发展的进程时,对于撰史者所认定的文学进化、文学繁荣的若干方面应有所记载,而对于他所认定为文学退化、文学发展歧路的若干方面也应予以记载,从而更衬托出文学成就的可贵,也有利于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因素。在文学史述录的层面上,如果从否定文学退化现象的合理性的前提出发,撰史者可能以此为由对退化只是作出判断而不作具体引述与分析,这在我们触及到中国文学史中的齐梁宫廷文学、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文学时已有前例,因它们分别是对先秦两汉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倒退。那么,作为一种反拨的扭转,这里给出两条理由来对退化现象述录的必要性作出说明。
首先是在文学史家的研究上,有必要对即使是退化的状况作出认真的较详细的述录。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是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来对待史实,他只起到一种收集史料的作用。可是史料是庞杂的,有时也是相互冲实与矛盾的,他很难做到纯客观地选取史料。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值得提倡的工作方式,是从问题的提出和尝试解答入手来搜集和编排资料,他指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法律学家兼哲学家的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一句值得记忆的话里提出,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当他写这句话时,他所要否认的是,科学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应当是毕恭毕敬的态度等待着她发言并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她所决定赐给她的那种东西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历史学方法的真确理论,尽管培根并不知道这一点。”(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自然现象,它是如何来对待这一对象的呢?就以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水往低处流”来说,在古代人那里,曾有老子的水“趋下”的说法,古希腊的亚理斯多德曾以物体的“恋家”来解说此事。到牛顿力学指出了万有引力的规律后,我们有了地心引力的新的理论框架来对“水往低处流”加以解说。对同一现象在不同理论中有不同解释的状况,使我们有必要慎重对待现象的评价,尤其是对负面现象的评价不宜简单否定了事。也应对之作出详备述录以备他日之用。
其次,对于后代读者来说,它在研读、浏览过去时代文学遗产时,那些作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应是他学习、了解的对象。同时,作为文学经典的另一面的、被文学史评为负面意义的作品也有必要作出一些介绍,因为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在这不同价值意义的文学作品的竞争与碰撞之中演进的,如果不将实际进程中的矛盾关系加以展示,那么,那些即使有价值的文学史料也不过是文学史家推崇的,但对读者心灵的震荡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材料。须知,文学史家只是站在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点来看待文学史实的,这一实际上是十分偏狭的视角完全有可能将真正有价值的,或者是说换一视角来看体现出别一意义的东西撇开。马克·布洛赫曾说明过历史撰述中“有意”记录之外还有“无意”记录的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可能是同样重要的,“许多历史事件只是发展到高潮时才为人注意,无论目击者是在事先还是事后为惊人的事件所吸引,他们都不可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今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那些情况上。”(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这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的负面现象上,如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期在明清时代,但生活在明清时代的人还持看重诗文、轻视小说的立场,如仅就诗、文而言,就确实难以明确断言它高出汉、唐等朝代,从当时的观点而言就会对文学发展描述持悲观的立场,而在今天来看当时的小说史就显得薄弱。当时的小说评论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都体现了很高的艺术领悟能力,但在当时也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所谓退化有一个观照视点的问题,它有赖于人从何种视角来看。后代的人有权利在接受前代评价观点的同时,也了解到前代作出评价时的依据是什么,参照系如何,这都得有对退化现象的较全面的记录才能较好地收到此种效果。
文学史中有创作水准退化的问题,然而水准是在一定评价体系中作出的,我们不能要求拿出一个在各时代、各种美学观念的人都公认的评价体系,那么,在评价体系具有主观性的状况下,对于它在负面评价中的情形作出一些要求,就显得是必须的,而且也可以办到。
文学史是对前代文学状况的述录,也是对后代的人了解前代文学及前代人的文学观作出的交代,确立对后代的人负责的态度,像维护生态环境那样维护前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