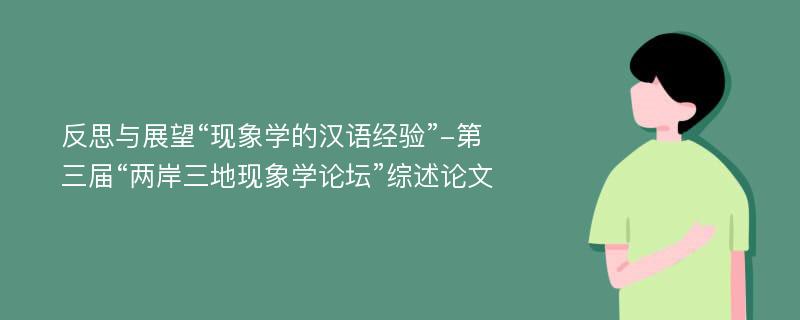
反思与展望“现象学的汉语经验”
——第三届“两岸三地现象学论坛”综述
罗皓雪 董梦璠
由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筹)主办的第三届“两岸三地现象学论坛”于2019年3月30—31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现象学的汉语经验”。来自中山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两岸三地著名高校的20余位学者从文本翻译、概念审查、中西比较等不同视角围绕“汉语现象学”进行了活跃而深刻的发言与探讨。
Fig.4 shows the fitting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Scenario 1.The following was observed:
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孙周兴教授做了题为《汉语哲学的时与势——再论汉语关联性思维及其效应》的报告,孙教授认为汉语哲学的劣势在于没有形成“强推论”的思维方法、“纯形式”的观念世界和“高抽象”的形式科学体系,主要表现为心性上的无超越性和法理上的弱规则性;但同时,汉语哲学的弱势从另一角度来看又是一种优势,汉语的“弱规则性”使得汉语具有极强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和包容能力,且同时汉语的“强关联性”这一特征正是顺应了当代技术的发展趋势,在技术时代,人与物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物联”世界,这正与汉语的“强关联性”相合,因此当下是汉语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倪梁康教授对孙周兴教授的报告评论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和孙教授的“我们处于最哲学的时代”都表达了对哲学的发散性思维的重视。同时他指出,在孙教授的文章中过多地强调观念的构成与变化,即强调“化”,但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性”,但事实上“性”作为在“化”中不可分割的稳定的结构的存在,总是或隐或显地支配着我们。就像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陷入历史主义与发生主义,历史就是观念的构成与积淀,构成是“化”的过程,而积淀则是“性”,“性”与“化”不可分割。
中山大学的方向红教授做了题为《Dasein的翻译及其汉语经验》的报告。方教授主要针对汉语海德格尔研究以“此在”翻译“Dasein”进行了质疑。首先“Da”在德语中既含有“这里”,又含有“那里”的意思,而“我”的停留之地更多是“那里”而不是“这里”,因此“Da”译作“此”就略显瑕疵。同时方教授又指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其实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都无法表达“Da”的原初性,“Da”先于地点副词和人称代词的区分,它是我原始的“生存论空间性”,其根本的两个特征是可能性和展开性。接着,方教授从对“存”的篆文字形入手分析,认为最适合翻译“Da”的是“存”,相应地,“Dasein”就是“存在”。这一译法不仅在翻译《存在与时间》时不会造成任何困难或歧义,同时将这一译法尝试扩展到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中也是并不违和的。但最后方教授指出,“Sein”长期占领着“存在”这一译此,使得“Sein”与“Dasein”的含义会造成混淆,因此这一新译法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
来自高雄中山大学的游淙祺教授在评论中表达了对方向红教授质疑主流翻译的欣赏,并指出我们对翻译应有的几种态度:不违背外文词的原义,同其他概念不存在冲突,中外文语词相匹配。但游教授也提出疑问:对于已经成为非常主流且使用广泛的翻译词来说,这样的反思与质疑是否会造成新的困扰?
所谓PAT算法就是相位自动跟踪(phase auto-track)技术,简单来讲就是控制两个简谐信号的相位差(Δφ),如图4所示.
与受到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过滤制约的正史记载相比,民间口承叙事作为底层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它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贴近最为本能的民众诉求,这使它常常显现出非同寻常的爆发力和想象力,使其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展现出极为必要的底层性与多元性。只有将历史“本文”与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文本”并置,于二者的关联中寻找互补、印证、叠合、传承的要素,才能真正建构起完整而全面的满族区域文化历史。
来自高雄中山大学的杨婉仪教授做了题为《庄子思想中的超越、身体性与伦理:从形变观点谈起》的发言。她首先阐明了三种不同的超越形态:如游于四海之外的神人凝守于自身而不落入世界的形上超越;顺应时与自然而自由地幻化自身,以穿行于天地而弥补天地之裂的气化主体;落于生存现实,在自身生命的转化中所实现的超越。然后分析了虚化自我与物以及世界的关系、化气为形的人与身体性的关系。并最终指出《逍遥游》中道体(大瓠和樗)之主体性即是其身体性、超越即是现实的这一意蕴,而其自身的形变在生发中使万物得以形变的气之转化,最后促成道之为伦理、伦理之为道这一最终的转变。
提高后台服务水平和捐助人举报的效率。平台可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公众号设立举报窗口,对于捐助人的举报及时吸收并统计反馈,对于举报较多的项目,可让专人小组调查该项目真实性,公布项目信息,如举报属实停止项目一切活动,如数返还善款。
作为论坛的压轴环节,倪梁康、游淙祺、庞学铨、王庆节、孙周兴五位学者代表围绕“汉语现象学”这一话题进行了一场富有反思性和展望性的精彩对谈。
此外,南京大学的王恒、马迎辉,同济大学的张振华、高松,苏州大学的李红霞,香港中文大学的邓文韬,中山大学的杨小刚,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韦海波,浙江大学的郭婵丽、杨妍璐和王蒙蒙等学者也奉献了精彩的报告和发言。
为提高充电连续性和可靠性,本文所研究的基于波束成形的一对一无线充电流程如图2所示。增加了扫描、充电完成判断2个环节,并包含NS次扫描,以及扫描到接收端后允许的k次充电子过程。其中,NS≤NSmax,NSmax=2π/θ为波束扫描一周所需次数,θ为单波束角度;充电子过程包含4个环节:连接→读写数据→充电→充电完成判断,k≤K。本文中,令K=3[11]。
来自新竹清华大学的吴俊业教授做了题为《儒家伦理学的心性论与规范性问题——现象学诠释学转化之初步构想》的报告,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学的现象学化和诠释学化这两种方式来克服伦理学层面的心理主义。对此,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庆节教授评论认可吴教授从批判心理主义入手分析儒家心性论的现象学思路,但他也指出或许放弃实践哲学的线路转而走超自然方向的超越论路径才能避免道德心理现象对普遍问题的无能为力。倪梁康教授在评论中指出,伦理学的心性论与规范性之二元紧张是不可避免 的。
高雄中山大学的游淙祺教授同样强调了文化特质对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虽然人们都希望用不同的语言去传达相同的思想,但是思想在经由语言转达的过程中却往往容易发生转变,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性造成的。相比世界上占主流的拼音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汉语是一门图像性很强的语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而如何去开发这种经验,将是今天学者共同的使命和任务。他回想起早在2004年他的导师瓦登菲尔斯(Waldenfels)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曾在私下与他主动聊起这个话题,瓦登菲尔斯注意到了中文世界语言的特别之处,他表示很期待汉语文化圈能在开发汉语经验方面做出一些贡献。游教授指出这与瓦登菲尔斯的思想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他把现象学比作一个“大家庭”,每个“家庭成员”之间都有着或松散或紧密的家族关系,而且这个家族圈子的范围会无限扩展下去。从这一角度而言,现象学应该是持续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了东方的中国,自然会从这个由胡塞尔所开创的运动中延伸出新的内容。游教授强调这是瓦登菲尔斯作为西方人所持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理解为现象学跟其他所有领域的思想一样,它经过本土文化的吸收消化之后,自然会产生新的表达、孕育出新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将会是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现象 学。
首先,主持人倪梁康教授对“现象学的汉语经验”作了题解,类比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现象学如今也面临着相似的文化融合的问题——如何用汉语表达现象学的经验?“汉语经验”一词本身蕴含着一股张力:一方面,无论何种语言都企求表达一种源本的经验,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谈论同一经验时,又会引发不同的对经验内涵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每种语言都有各自殊异的经验,或每一经验有其固定的基本内涵,而是说从不同语言切入的现象学会呈现出新的内容。倪教授认为,除了德国现象学、法国现象学、日本现象学等,“汉语现象学”也正在加入现象学运动的阵营。但至于“汉语现象学”的具体内涵,还需要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加以廓清。
浙江大学的庞学铨教授则认为汉语现象学的一个内在要求就在于吸取和挖掘现象学理论中重要的思维方法,以推进自身的发展。他认为,除了孙周兴教授提出的“关联性”思维之外,“当下性”思维是现象学另一个代表性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在现象学中存在一个从形成到逐渐深化、系统化的过程。胡塞尔首先在阐述现象学基本问题上体现出“当下性”的思维特征,比如在本质直观中,意向性在意向活动中进行立意,就是一个排除了其他思维方式的直接性思维环节,此外,在“小观念”第五讲中,胡塞尔用“当下的正在体验的体验”来表述时间与声音的关系,也凸显了“当下”“体验”的思维特点。但胡塞尔的“当下性”仍局限在意识的范围之内,海德格尔则将其拓展到了生存论层面,此在(Dasein)在可能性中筹划生存和展现自身也是当下性的过程,而之后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则与当下性思维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更是将“当下性”直接作为其哲学构架中核心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核心思想之一。施密茨著作《哲学体系》第五卷的标题就叫做《当下》,其中讨论了主体在当下的形式各异的表现。
同济大学的梁家荣教授在题为《谈意向性吗?说哪个意义?》的报告中指出,“意向性”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实际上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存在着极具影响力的内涵差异,通过对布伦塔诺、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齐硕姆等哲学家对“意向性”的不同意义用法的辨析,梁教授对“意向性”这一概念的不同含义进行了系统考察。以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意向”概念为例:在布伦塔诺那里,“意向性”这个词其实从未被使用过,目前学界笼统的“意向性”概念其实发端于胡塞尔,布伦塔诺所用的只是其形容词和副词形式“意向的(地)”(intentional)。不同于胡塞尔将“意向性”标识为心理现象的特性这一朝向义的,布伦塔诺的意向概念一方面是实存义的,特指对象之实存模态,即“对象之意向的内实存”;另一方面其意向概念也适用于作为心理行为之对象的物理现象。同时胡塞尔使用“意向性”概念带有模糊性和歧义性(一方面用于心理行为,一方面又用于心理行为之对象),而布伦塔诺的“意向的”更多只是用于心理行为之对象本身。
游淙祺教授做了题为《文化物与物:胡塞尔的观点》的报告,游教授从胡塞尔晚期的生活世界理论入手,回溯地总括性阐述了胡塞尔对于“物”的分析,从胡塞尔现象学最基础的感知分析中作为意向相关项的感知之物、超越性的空间物、作为物的身体到文化物等层层递进,不断展现出胡塞尔对于“物”之讨论的多层次、多视角的丰富内涵,并通过对物与文化物之客观性的肯定标准的不同层次揭示出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差异论述(文化物之普遍性不同于物之普遍性的确认,是受制于具体文化群体的)以及延伸出来的欧洲中心论:只要通过欧洲理性文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物的普遍性经验才可能被揭示,因此是否具有认识普遍性之物的能力,便是区分欧洲文化与非欧洲文化的标准,而这也是欧洲文化优越性之所在。在游教授看来这一问题值得非欧洲文化圈加以重视与检讨。
庞教授认为这一思维方式对整个哲学思维转向可能有着直接性的意义:其一,它超越了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后者的根源在于心理主义、还原主义和内摄主义,它们造成了意识和时间之间的二分法,而当下性思维则把思维的存在重新统一起来,使其作为情境或晕圈而存在;其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认识人本身的新视角,使我们从对象性、符号化的认识中脱离出来,对人当下的情境、状态有了更深入的揭示,从而恢复具体、鲜活的主体性,亦即施密茨所说的“真正的主体性”;其三,它有助于我们揭示源初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它不再以主观意识或客观对象来理解“现在”,而是将其看作介于二者之间的、思维与意识模糊混合在一起的影像和情境,从而使我们回到源初的生活经验。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庆节教授则首先追溯了“汉语哲学”这一表述的历史,早在2001年,学界便已经有人提出了“要让哲学说中国话”的讨论,后来衍生为“汉语哲学”,今天时代哲学的“时”与“势”就在于如何推动“汉语哲学”的发展,这其中也包含了“汉语现象学”。现象学的经验不同于经验主义的认知经验,它是作为生命体验过程的经验,是一个历史的生成的过程。因此,现象学被看作一场运动、一条道路,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正如冯友兰提出中国佛学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佛学在中国”到“中国佛学”,王教授认为现象学也正在逐步由“现象学在中国”向“中国现象学”转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学界仍然面临着语言转换的问题:如今人们读的著作、写的论文都带有翻译的味道,这说明人们还停留在用翻译语言来做中国哲学的阶段,那么如何“让哲学说中国话”,怎样用自己的日常语言、用汉语的语言经验来表达和思考哲学问题,就成了当今学者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此外,更重要的转换在于心态,通常人们都把“中国哲学”理解为“在中国的哲学”(philosophy in China),即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或中国地区内的哲学,但我们更应该将其看作是“从中国来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China),因为哲学应该是面向未来,应该关注汉语的语言和历史经验能够为现象学运动作出什么样的特殊贡献。因此在翻译问题上,并不是说汉语只有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才能取得合法性,中国学者们应该摆脱学生心态,树立起汉语哲学自身的合法性。
同济大学的孙周兴教授指出,在“汉语现象学”之前,最早使用“汉语”修饰的学科事实上要追溯到“汉语神学”,而“汉语神学”或“汉语哲学”等命题的提出都与前些年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相关,在这一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哲学或神学这种超越性思维方式与汉语这一非超越性语言之间的内在冲突,因此关注汉语经验是有益的做法。但对于“汉语现象学”而言,现象学应该着眼于何处?孙教授表示仍在思考中,他认为长期以来中西哲学都是在缅怀过去、虚构一个美好的古代,他称其为“乐园模式”——人类失去了乐园,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恢复乐园。当今的人文科学仍然在这个思路内讨论问题,而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它也许需要被重新评估。
孙教授认为马克思应该被看作第一个技术哲学家和现象学家,因为马克思对他所在时代的、由刚刚启动的技术工业所决定的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并揭示出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如何被构造起来的,后来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考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在推进。尼采虽然在早期哲学中虚构了美好的悲剧时代的文化,但是他在后期哲学中更加关注瞬间和当下,并从中推出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线性时间观的一种新的时间理解,孙教授称之为“圆性时间”。他认为尼采所谓的“末人”,其实是指最后的自然人类,也就是生活在线性时间文明中的、缅怀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但在线性时间中,每个人都是“等死的人”,也就没有实现真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尼采认为这必须被推翻。而今天的技术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造时间和空间理解的可能性,“超人”正是这个时代意义上的人。而在技术文明中超人的使命在于重新回到大地、重新获得自然性,人文学科的意义在此凸显出来。因此,孙教授认为面对今天已经被技术撕裂得支离破碎的人类基本经验,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思考应该如何重建人类基本经验,以及哲学究竟应该缅怀过去还是朝向未来。
作者简介: 罗皓雪,浙江大学2018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董梦璠,浙江大学2017级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肖志珂)
标签:南京大学论文; 两岸三地论文; 文本翻译论文; 哲学系论文; 浙江大学论文; 中西比较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