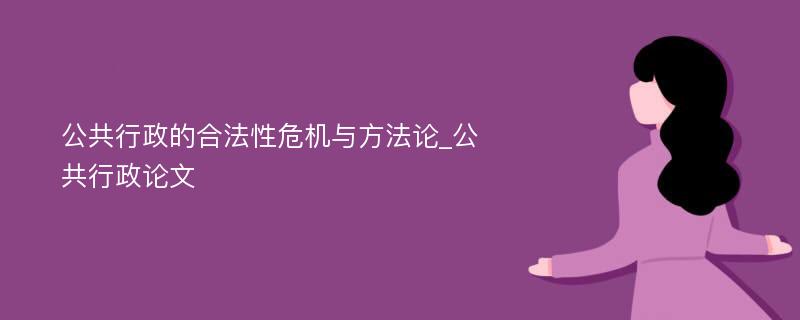
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行政学论文,合法性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1—0102—05
公共行政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以来,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就一直受到质疑。一方面,公共行政与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大量借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常常被认为是某一学科之次级领域(subfield),或是一门谋求“学科”(discipline)地位的“应用”“科目”(subject),而其自身尚不能独立地反映或指导公共行政实践。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所涉及的问题关乎国计民生,以至于其它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往往会对其某些议题感兴趣而“入侵”其某个研究领域,最令公共行政学界感到尴尬的是,公共行政学自身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似乎难以企及“入侵者”的研究深度。因而,公共行政学如何确立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并处理好同邻近学科的关系,如何化解学界、公共行政部门乃至普通公众对于公共行政学科价值的否定立场,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征程。
一
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就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研究,以至于对危机本身的探讨一度成为一种时髦。关注公共行政学前途与命运的人们很难不反思这样一些问题:公共行政学怎么啦?其合法性危机的“病灶”何在?该何去何从?从他们见仁见智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梳理出这样两种基本答案:其一可以概括为缺乏公认的核心议题;其二可以概括为缺乏恰当的方法论奠基。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回答。所谓缺乏统一的核心议题,是说公共行政学科的研究过于分散,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纽南德指出,大量公共事务和行政的研究都无视过去的经验和研究,这导致今天该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新的研究往往在当代问题中跳来跳去,建立在早期研究基础上的持久的后续研究仍不多见。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早期的许多研究已经被透支,而是早期的研究工作甚至包括今天的研究往往被新的研究所忽略(Newland,1994)。因此,尽管尝试为公共行政学科界定核心问题的努力一直持续存在,但没有任何一种努为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选票”,总是难逃遭受无数批评与指责的命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把握到了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然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累积性知识基础。这一现象被沃尔多形象地称为“盲人摸象”问题(Waldo,1961)。戈林姆别斯基也就此悲观地认为,一个企求就某一议题达成共识的学科是不成熟的,因为目前在公共行政领域没有任何一种观点能够有效地将公共行政的研究统一起来;这种想法或许是不现实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公共行政可能是一个专业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能够发展出自己的连贯和统一途径的学科。沃尔多(Waldo,1955)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公共行政学正面临着无法就议题达成共识的“认同危机”,如果其一直不能就此达成共识,更将会沦为一个从属的科目(subject)。
但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悲观。首先,对危机的关注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的一种反思性的理论自觉,而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其不竭的自我反思。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的不断转化可被看作是该学科自由开放研究精神的一种表现,也可看作是该学科勇于探寻真理的一种试错与创造。套用周雪光教授对社会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所进行的评论:它为在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等待我们去开发[1](第14页)。我们认为,这同样也适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学的优势恰恰在于以其兼容并蓄之特质,彰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繁荣。如果严格地为其界定议题,可能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束缚,阻碍对真正有益的研究问题的探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学术界尚未就公共行政的统一议题取得广泛共识,但如果我们撇开具体的研究问题和领域,就会发现,公共行政领域的确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理念,它指引着大多数的公共行政研究。“我认为,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恰当方向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有时并不非常明显。”[2](第172页)登哈特认为,将公共行政的相互独立的理论连接在一起的,是试图在民主责任感的框架下建立一种以对人类行为的实证主义理解为基础的理性行政理论[2](第173页)。怀特和亚当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在公共行政的所有这些表面争执不休的论辩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叙事:即技术理性的宏大叙事(White & Adams,1986),它指导着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几乎“不学而通”的理念。
二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将公共行政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定位于其缺乏公认的统一议题的观点,并不是一个经得起深思熟虑的结论。我们认为,上述第二个根源恰恰是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们所应共同关注并认真思考的,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滞后制约或限制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削弱了公共行政学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作用和功效。
研究方法的滞后是同对研究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不能给公共行政学以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奠基,我们就很难评价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要想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对某一个研究领域的垄断,而在于有自己的理解主题领域的独特方法。同样借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它只是观察社会的一种方法(Berger,1963)。对于社会中的值得研究的各种主题,各个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理解视角进行研究。那么,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否能表现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呢?公共行政能否形成自己合理的观察和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方法?
考察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许多行政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都隐含了自己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或先期预设,即以自然科学的标准——研究的有效性、可测性、因果性等来判断研究成果的可接受性。这种标准之所以盛行并为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地运用,起源于科学和技术在物质世界中取得的巨大成功(White & Adams,1994)。随着自然科学成功地控制自然界,并将人类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技术理性——科学分析的思路和技术进步取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也几乎成为科学研究方法的代名词。它倡导用法则化概述对事实进行解释、预测和控制,认为只有依循解释性模式的研究才是理性的,被视为是知识合法积累的主要甚至惟一手段。
而就其价值倾向而言,“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途径”来指导公共行政学的实证主义量化研究方法必然导致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定位于技术价值或效率价值,因而,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目的偏重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而缺乏对于目的理性的思考;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产出。沃尔多就此概括说:“旧公共行政学的特征是相信行政实践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关键在于执行中的工作效率。”[3](第23页)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公共行政不仅是公民社会公共目的的执行,更是公民社会公共目的的创造,如果在方法上把公共行政简约为技术化或量化,那么,公共生活的根本价值是否也在于效率至上?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究竟何在?随着20世纪中叶公共行政价值中立“神话”的“破灭”,这些质疑不断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公共行政学合法性危机。因而,就其实质而言,所谓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乃是根源于实证主义量化方法论指引下的淡忘公共行政根本价值的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肯和古巴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观察,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主要源于以行政理论的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及其背后的实证论范式(positivist paradigm)。(Lincoln & Guba,1985)台湾行政学者江明修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事实上,以往由于较缺乏方法论的反省,使得一些公共行政学者有意无间地着迷于通则性理论的追求,自居于‘应用’学科的地位,鲜少进行属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再加上大幅度地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造成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出现了‘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危机,更导致公共行政学的‘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江明修,1997)
三
作为一门学科体系之世界观的方法论的成熟度是衡量该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一门学科的具体知识是“鱼”,那么,研究方法就是“渔”。因此,理论与学术的突破与创新,理应奠基于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公共行政学要走出合法性危机,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事实上,公共行政学合法性危机所凸显的方法论危机早就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对传统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批评深刻的反思与批评。一些学者依托哲学和历史对实证主义的量化方法论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批判(Adams,1992; White,1986a),他们质疑主流社会科学的标准,认为,实证主义者们过于强调解释性研究的探索逻辑,而把不同于这种探索逻辑的研究模式视为非理性甚或是反理性的。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证明了科学的理论与逻辑既是诠释性和批判性的,又是演绎性和归纳性的。一个较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应是包含了实证、诠释、批判等三种方法,因为只有保持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经验的了解才会较为清楚(Bernstein,1976)。基于演绎和归纳逻辑的科学分析思路只是研究的一种模式,对于公共行政这样的应用性专业领域而言,它至少是不自足的。因为如果行政管理者面临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量化的科学来研究的话,那么,就没有管理者存在的必要了。贝利(Bailey,1992)则警告说,如果照搬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准,公共行政将面临着丧失公共行政的主旨及强化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隔阂的风险。如果固守妨碍该领域理论发展的主流社会科学标准,公共行政将继续被放逐到大学的次等地位,而他们的研究也将继续被诋毁为“实践取向的”。因此,公共行政必须接受实践取向,而不是为此心怀歉疚。哈默尔更激进地指出,实践者对知识的认识比科学研究者要更为深刻,他们完全能够界定现实、判断哪种知识对他们有用,并形成与他们的世界相关的有效性标准。他认为,公共行政学者的任务,首先是确定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只有关注这些管理者以及他们的知识,才是一个复兴的或新的学科惟一可能的基础(Humme1,1991)。
相比较批判而言,奠定新的方法论基础显得更为艰难。许多学者不畏艰辛,就创新公共行政学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极为宝贵的探索,尝试寻找适合公共行政这样的应用性专业领域的替代性研究方法。早在1971年,柯肯哈特(Larry Kirkhart,1991)就尝试将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公共行政研究。1979年,丹哈特(Robert Denhardt)夫妇首次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拜雷认为,公共行政需要根据实践导向来重新界定该领域,而正是通过案例——经过审慎发展和严谨分析的案例,学者和实践者们才能并肩发展该领域的知识。案例研究是探讨大量公共行政的研究问题的适当方法,它很好地体现了公共行政作为应用性职业领域的特点(Bailey,1992)。施密特认为,公共行政的现实比我们所能想象地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处理能力,使得我们的科学才智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应当尊重看待世界的其它方式以及其它类型的知识,谦恭耐心地参与到现实中去,通过倾听和互动来得到更多的知识,而不是摆着一副支配控制的面孔。他通过对1975年美国提顿河土坝工程失败的分析,提出仅仅依赖科学的知识来控制自然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Schmidt,1993)。哈默尔则认为经理们解释其世界的方法——“讲故事”是产生和积累知识的一种有效方法。故事首先将听众纳入故事讲诉者的世界,使得听众帮助来界定故事情境或问题,并使他们为解决问题做出奉献。故事允许听众暂时将故事讲述的不同甚至是奇怪的经历纳入到自己的世界而拓宽听众自身的世界,或拓宽他们对现实的界定(Hummel,1991)。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整合不同的研究途径,尤其是量的研究方法与质的研究方法,认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上和具体技术上的,它们共有的隐含逻辑是相同的(King,Keohane & Verba,1996)。在公共行政学中尝试进行这种整合性努力的要数丹勒克。他认为,从本质上而言,正如声波理论和微粒子理论都是不完整的,除非将之结合起来,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社会解释也必须加以整合。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定量和定性研究。他提出了一种高阶的系统方法,认为这种新的范式将可以发展出新一代的实践工具和策略,实现公共行政促进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理念,它使公共行政“社会性更强,但科学性不减分毫”(Daneke,1990)。
当然,公共行政学并不是想拒绝主流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而是主张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和知识发展途径能够持续适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所需要的广阔研究范围(White & Adams,1994)。对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的界定标准也许并不需要局限于主流社会科学的传统标准,但无论如何,公共行政要证明其作为大学院系里合法的学科,就必须形成自己关于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的标准,并以此来指导和训练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正如怀特所言,“任何形式的研究都需要方法与标准,也需要实践推理来说明我们的方法与标准的正当性。”(White,1986a)在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程序和方法的情况下,公共行政学者要靠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学者之间的理论对话来寻找并检验这些替代性研究方法的标准和方法,并以此来指引研究者们的工作。通过实际讨论来界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的一个优势在于,它认识到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动态本质(White,1986b)。也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没有独立且通用的标准可用于衡量研究结果的可接受性,这也是为什么说上帝把所有简单的问题都留给了物理学而把复杂问题都留给了管理学。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恰当性问题必须由参与研究的各方通过合乎逻辑的论证来共同解决。在寻求研究方法的标准和规则时,我们并不是在寻求教条,而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思维方式”。诚如怀特所言,这种对话是科学理性的精髓所在,所有自称对我们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研究努力都必须首先具有这种科学理性(White,1986b)。
我国传统的公共行政教育中往往未能给予研究方法以足够的重视。不掌握研究方法而仅仅只是尝试译介国外的最新学术成果,我们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无法超越。当然,关于公共行政的恰当研究方法的这场争论远没有走向终结,只要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学者们仍然希望为知识的增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参与到这场论辩中来,不断地就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的合理方法和标准进行讨论、争辩、审议和论证,并用之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在这一探讨过程中,中国学者的声音至少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子叙事,它们能促成其它学者理解它们当前视角的可能局限性,通过将中国学者自己的视角贡献给这一探讨过程,可以让所有参与探讨的各方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属其中的更大的叙事。我们希望在国外的讨论如火如荼时,能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及时加入到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中来,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国学者的贡献,促进公共行政学科的繁荣。
收稿日期:2005—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