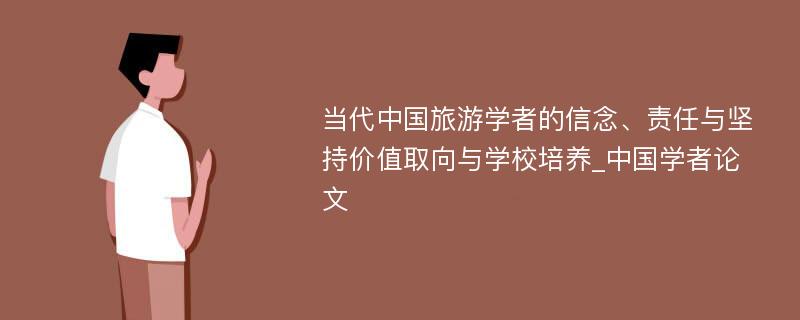
信仰、责任与坚守①——当代中国旅游学人的价值取向与学派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学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10)-02-0001-06
身处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日益扩容的国民旅游市场以及繁荣发展的旅游学术研究,当代旅游学人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50年、100年以后,后人如何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如何去面对历史的拷问?从求学到成长为一个学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下来,国家和社会已经给予我们很多。在接受功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为什么社会给予我们这么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回报社会?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当代旅游学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或信仰来做学术研究?
1 旅游学术研究必须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共同载体是大学。大学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人明白道理,所以我们要“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格物”,就是指探求世界的真理;“致知”,就是要知道“为什么”。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最终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培育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高校做科研不能等同于专门的科研机构:在研究机构里,可以投入百分之百的力量做学术研究;对于大学而言,人才培养则是第一位的。回顾国外大学的起源,从德国洪堡大学开始就一直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到美国教育发达时期,开始强调科学研究、强调人才对社会的价值;现在又重视文化引领。但是有一天,我们把肩负的这些纷繁复杂的责任去掉以后,会发现,最后剩下的纯粹的使命指向就是我们的学生。
每当面对学生的时候,我都深感责任重大。曾经有学生提问,怎样才能进入集团并受到重用。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认为,上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他们面临着发展更为成熟的旅游产业和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因此发展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更少。当时,我的回答是,第一,年轻人不要浮躁,要能够扎进基层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第二,只有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作贡献的时候,社会才需要我们;第三,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不同。20年前我不知道自己会做旅游研究、会成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带头人和政府智库的领导者。但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心态:我要为我脚下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为生我养我的父老兄弟做点什么。可能每一代人的理想不尽相同,但是社会的发展能够给他以回报的肯定就是那些愿意为社会付出的人。后来,这个学生很受触动和启发。我们不要期待做一场演讲、发布一个命令就能把人才大规模地培养出来;能够影响一个人,一个学生,作为教师的责任基点就有了。
怎么去培养人才?有很多经验和模式。当代旅游学人心中始终要有这么一个信念:我们所做的任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面对那么多双渴望成长、期望成才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装着这样一个理想:要培养我们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希望。为我们的家人也好、父老乡亲也好,只要他们把子女送进大学,我们就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学教学设计以及一些学术性会议的组织,越来越偏离教育和学术的本质,商业色彩和利益导向愈加明显。这一代旅游学者应有的情怀,就是一定要基于人才培养去做学术研究。这样就解决了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学术研究要把科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理论知识传递给学生,当知识尚未固化的时候,不要忙着去编教材,那样会误导学生。如果有机会回到体制内做一所公立大学的校长,我很愿意分管教学工作。因为离开教学与教育这一根本目标,大学就可能变成一家研究机构、一个规划公司。旅游学科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学者就去研究这些问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最需要什么,就去研究什么。这样,旅游学术研究就可能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2 旅游学人要与旅游产业发展共进退
回顾中国旅游学术研究30年发展历程,初期学术研究与产业贴得很紧密,以服务和引领本土旅游产业发展为主线。但现在的旅游研究范式以学习西方为主,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西方的旅游发展模式。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发展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学习国际经验是分不开的。然而,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产业实践问题。现在旅游学者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在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在国际会议上获得几个奖项,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于是,在形式越来越精美、发表文章层次越来越高的同时,旅游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却迷失了。
本土的旅游学者,对希尔顿、喜来登等国际饭店集团、对JTB、TUI等国际旅行服务商耳熟能详——创立时间、发展历程、管理模式等。可是我们的学者、教员和学生,对中国本土的首旅、锦江、如家、七天等旅游集团了解多少?很多人对身边的问题、自认为的小问题不屑于去解决,可是往往这些小问题对于以中小旅游企业形态为主体的大量旅行社、酒店而言就是大问题。我通常会在每年假期给研究生布置调研任务,主要是为培养他们的产业意识和学术意识。有一个学生没有完成实地调研任务,原因是她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没有高星级酒店。是谁给我们权利只能去研究高星级饭店?全国的星级饭店也只有1.6万家,但是我们还有30万家社会住宿机构和130万家“农家乐”设施。对旅行社的研究也一样,不能只是把目光放在排名靠前的几家大社或“百强社”,而应该关注2.1万家旅行社的整体发展。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服务于绅士和淑女的住宿机构才可以称为酒店。其实,我们的出身是差不多的,大体上都来自于草根阶层,当父母把我们送到窗明几净的教室的时候,是谁给我们权利忘记他们、不与他们共进退?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天职。
从早期研究国有饭店到现在更多地做政策研究,事实上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国际学者,因为我研究的兴趣点可能和国际主流如低碳旅游、特殊人群的旅游权利、旅游解说系统等热点领域不完全一致。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民,以及还处于大众观光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消费市场,他们对旅游的诉求和旅游需求更亟须我们去研究。我们国家的大众旅游市场是一个以大基础、稳增长、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市场,人均年旅游消费也就是500元多一些。正如温总理说中国的任何事情乘以13亿都是个大数字,除以13亿都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数字。2009年我们国民的出游率达到1.4,而我们国家的13亿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体验过旅游,很多人还没坐过飞机,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
在旅游业正式进入国家战略体系以后,我们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且不断变化的消费形式与相对滞后的产业运行模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快速成长且高度市场化的产业运行格局跟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我国旅游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主要矛盾去研究一些看上去似乎很学术、很国际化的东西,我们作为当代的旅游学者就辜负了父老乡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脚下这片土地的存在。经常跟我的同事、学生在一起聊的时候,我说你们要经常想一想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感叹,“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没有这种情怀,做学术研究是坚持不下来的。做教育也好,做研究也罢,短期内可以靠方法、靠工具、靠技巧,但是放长历史的眼光,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则是理想,是信仰。不能因为现在社会整体很浮躁,就不坚持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就是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跟一个更大的群体、更大的空间结合起来。说实在话,只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很快就会得到满足;但在为一个更大的事业去服务的时候,人就会有永远不竭的动力。就像电视剧《潜伏》里面余则成对晚秋说的,“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有时候看得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么——包括爱。”在这个层面上来谈我们的旅游学术研究就很容易明白,如果不能和产业发展共进退我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
旅游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服务于产业,就无法引领产业的发展。美国有个叫约翰·杜威的哲学家,他在《历史上的英雄》里开篇就说,“谁拯救了我们,谁就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父老兄弟不需要我们去拯救,我们也拯救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他们共进退,与他们在一起,到现场去体味他们的喜怒哀乐。要深入研究旅游业态和旅游经济发展,还应该到老百姓花10块钱住一晚的酒店去看一看,跟他们聊一聊,最好去亲自体验一下。曾经到重庆做课题调研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感受了半天当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在一些地方,10块钱、20块钱即可住一晚的酒店叫“高级豪华酒店”。这些事情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现实。并不是宏大叙述才称为研究,扎扎实实从身边做起也是研究,而且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我推荐我的学生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要解决青年学子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做学术研究,也成不了大家!
3 旅游学人要有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如果说30年前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汲取世界经验的基础上,那么现在到了中国为世界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东方智慧的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中国和日韩在东北亚区域旅游合作问题,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旅游发展问题以及海峡两岸旅游合作问题,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旅游业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输入,更是一个与世界互动的过程。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中国古代没有“国”的概念,都是“天下”。正如电影《2012》里面所预言的那样,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中国的旅游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个词:大国旅游。以“大国旅游”的概念来定位中国旅游发展特征,就要以大国旅游的心胸把中国旅游业纳入到世界旅游发展格局和合作框架下。事实上,我认为“大国旅游”比“旅游大国”更加贴切地描述了我国的旅情。只要我们能把人才培养时时刻刻记在心中,只要我们能把产业发展要求、父老兄弟的需要记在心中,又有放眼世界的胸怀,我们的科学研究才会有方向,才会有价值基础。倡导并身体力行这一方向和价值基础是我们这一代旅游学人的历史责任。
但是,仅有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学者“戏子”心态很严重,总希望灯光、舞台、音响都准备好,最后我们去表演。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更多地要自己去创造条件,自己去搭建舞台。我们要有这股韧劲。经常听人说,我们去做调研,企业老总都不理我们。接触大集团企业老总才是调研企业?拿着介绍信去访谈、发问卷才可以做研究吗?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没有条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而且学术研究的范围不仅仅是研究国家战略,如果能把小到一个村子的旅游经济带动发展起来,学术研究就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当走入历史深处的时候,哪怕留下的只是个背影或是只言片语的记忆,只要历史能够记住我们曾经为这个时代做过什么,对于我们这代旅游学者来讲就足够了。
4 自觉肩负责任,用能力去守护信仰
为什么做旅游学术研究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要与旅游产业发展共进退。那么怎样才能肩负起这个责任呢?
第一,要学习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要有跟同行交流的话语体系。科研的方法不一定是定量分析,历史传承下来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定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定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小学的数学水平都差不多可以读懂,这都是伟大的经典。但是我们不排斥定量分析,读硕士、博士时期都要学习并熟练掌握这些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因为时代在变化,在与别人对话之前,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做过。要做事情,就要有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学者来讲,研究方法和逻辑体系非常重要。就如一篇博士论文读下来,基础的理论体系有了,“马步”扎得很稳,那就迈出了第一步。就像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的激励、保健因素一样,这是一个保健因素,没有它别人就不满意,有了它别人也不会满意。所以必须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过程可能很枯燥。我在研究生时期学经济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要求我用不同的方法证明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一个曲线画下来很简单,但怎么用逻辑的方法证明、用几何的方法证明、用高等数学的方法证明、用案例的方法证明,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老师还说,边际成本的递增和边际利润的递减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要求我证明。我花了很多工夫,终于弄明白了。把这些都搞懂了,一个理论知识就吃透了。这些东西弄懂以后,受益终生。拥有这些知识的积累,跟他人对话的基础就有了,也就有底气了。
第二,要寻找一个好的选题。什么是好的选题?不是奥运来了就去研究奥运旅游;世博会来了去研究世博旅游。当然,这些也需要人去研究,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前面的东西,做一些引领性的研究。在酒店研究领域,我做旅游集团研究、饭店集团研究到后来国有饭店转型重组,做完我就不做了,因为那时已经变成很热的话题,再往下做就像波斯顿公司一样给别人做咨询,那是商业的事情,不是学者的责任。怎样找到好的选题呢?可以靠学术直觉,还可以多跟业界接触,多跟老百姓接触,有时候风起于青萍之末,多跟他们接触,一番谈话以后,看他们最困惑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此外,做研究还要善于观察,到地方去调研,一定要看当地电视台的新闻,看当地的日报,要知道当地老百姓、政府在想什么。还要看百货大楼,知道老百姓在买什么;去一下精品店,看年轻人玩什么;还要去看看菜市场,闻一闻人间烟火气,才能了解一个城市。看看挎着篮子跟商贩为一毛钱讨价还价的老大妈在想什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发现问题的方式,就可以找到撞击思想的东西,他们最焦虑的事情就是学者最急迫要研究的选题。不要只到国际上去找热点,要去现实的土壤中发现主题,这样业界才会跟着学者的脚步。首先要有理论和学术研究做支撑,有厚重感,还要有原始创新的东西,才能跟政府、跟业界对话。一定要跟现实的土壤多接触,脚踩到这块土壤中去,这样才能找到选题。正如温总理说的,“既要做仰望星空的人,也要做脚踏实地的人。”选题不是我们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给我们的。
第三,除了工具、选题以外,我们要会使用好的表达方式。我在研究院要求研究人员读《共产党宣言》,这是学科建设的需要。通过读《共产党宣言》,让大家体会什么叫理性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统一。有的学者,打开电脑可以滔滔不绝,离开电脑、离开稿子就不会讲话了,这怎么行。那只是一个工具。我们要学会一种好的表达方式,在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让他人认可,只有认可了才能一起前行。古人写文章,讲究义理、考据、辞章。就学术研究而言,就是工具、选题和文采,实际就是用什么去做、做什么、怎么表达这三个问题。文采从哪里来?我想首先就是要多读书。现在年轻人读书太少,语言用得很好,但没有内容。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脑袋里要装一些东西。读《古文观止》、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那种文采和感觉才可称作有内容。唐诗不读1000首,但3、5百首是需要的。书读多了,才知道“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什么感觉。对于读书,我们不仅要读中国的经典文献,还要读国外的名篇,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I Have a Dream》、奥巴马的演讲《Change》。现在的年轻人除了一起喝喝酒、泡泡吧之外,还会做什么?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多时间来读书,必须让自己变得厚重起来,做一个真正对别人有用的人。
第四,做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我们任何时候都以平常心去坚守。写一篇论文、做一次演讲很容易,但每天在那里写、在那里讲,是不容易坚持的。做科学研究与很多事情一样,做一次、两次可以,但要长期做下去,就需要不断跟自己对话。人都会有动摇、空虚、迷茫、做不下去的时候,坚守就是要不断告诉自己咬着牙做下去。保持一天的热情很简单,长期的热情则必须靠理性来守护,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撑。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的土地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父老乡亲需要我们的奉献、才情和努力。
但是,怎么坚守?又回到了我前面讲的几个方面,为人才培养做研究,为产业发展做研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积累做研究,要从学者的层面上升到教育家层面。中国旅游界需要大师级的学者,但是更需要教育家。没有这个,就做不了研究。研究还需要团队,需要相应的物质平台。我在现任职的研究机构投入了数百万元建设基础数据库,因为数据是学术研究的基石。但是即便这样,有时自己对着满屏的文字、数据与图表,会有一种荒芜感:这些有什么用呢?这能经世济民吗?有时候心里很惶恐,不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坚持。还是要多读一些历史、哲学甚至是宗教方面的书籍,我们没有宗教传统,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传统,读文史哲方面的书,才能够仰望星空,才不会计较蝇头小利,才会做一个淡定从容的人。还要交一批好的朋友,有时候一个人的品行看他交什么朋友就行。假以时日,那些默默无闻、真正为人民大众做事的人总会崭露头角的。我相信,付出总会有回报;我也相信,这个社会大体是公平的,不要轻易抱怨社会。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寂寞、可能会不舒服;如果我们努力付出了,当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群,我们的父老乡亲,包括我们自己在大地上自由地行走的时候、旅游活动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更高的时候、让人类文明更加进步的时候,我们会会心地微笑的。这就是我们长期坚守的东西。
只要我们坚持与旅游产业共进退,为人民大众旅游福祉提升而努力的学术理想,自觉肩负历史责任——包括责任心与责任力——100年以后,回顾这代旅游学人,我们至少可以对历史说,我们尽力了!
注释:
①本文据2009年11月28日作者在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