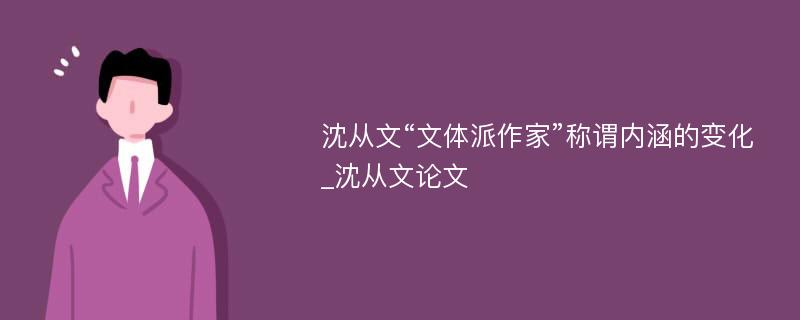
沈从文“文体作家”称谓的内涵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文体论文,内涵论文,作家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行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中,以“文体作家”这一称谓来归纳和概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特征是较为普遍的叙事策略。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道:“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①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直言:“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他的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也不拘常格。”②朱金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曰:“沈从文的创作除了淳朴的风俗民情和美丽的山光水色引人入胜外,他还以丰富多彩的体式和迷人的文字赢得了‘文体作家’、‘语言文字的魔术师’的美称。”③不言而喻,“文体作家”之称倒是简明扼要地勾画了沈从文小说手法万端、风格多变的特点,读者理解起来也并不繁难,被用作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话语自在情理之中。不过,“文体作家”一语既然被加上引号,就说明它是有一定来历的,需要加以适当解释才对。令人不解的是,各家文学史教材指认沈从文为“文体作家”时,几乎都没有对这一称谓的原始出处和基本含义进行必要的注释与阐说,这或许因为著述者觉得此称呼无甚异议,对之另行作注实在大可不必。但在我看来,考虑到沈从文最初被称为“文体作家”时的历史复杂性以及这一称谓自诞生至今的近70年来已实现了由贬而褒的意义演化等情形,为了还原历史,促进读者对沈从文现象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准确的把握,对“文体作家”一语加以一定的说明和解释还是很有必要的。
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正式场合将“文体作家”四个字组合在一起用以阐述沈从文小说创作特性的,应该是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一文中,苏雪林如此指出:“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诞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无意义。《月下小景》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④上引两段话都提及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呼,但价值判断上一贬一褒,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不过细读原文我们才发现,贬的部分确实是在谈论“文体作家”的“文体”问题,褒的部分已经不是谈文体,而是在论述沈从文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了。这两段话告诉我们,沈从文被公认为“文体作家”事实上并非自苏雪林始,“有人”“号为”等语的强调,说明市面上对沈氏“文体”的论谈已非一日。而从苏雪林的表达中可以揣摩到,以“文体作家”来称冠沈从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并不是出于褒奖之意。
苏雪林在文中所说的“有人”,理所当然地包括了韩侍桁。因为在苏雪林《沈从文论》发表之前,这位来自“左联”的文艺批评家早已著文表达过对沈从文小说“文体”形式上的不满。在题为《一个空虚的作者》的文章中,韩侍桁开门见山指出:“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对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⑤“轻飘的文体”,这是韩侍桁对沈从文小说形式特征所作出的基本判断。那么这里所说的“文体”究竟意指什么呢?韩侍桁解释道:“所谓文体,简单地说,便是叙述的方法。某一种事实被构想出来后,随之就要想到怎样去叙述它,这是自然的进展。因此,无论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因为他自己的性格与其所选择的材料的特异,全是各自有他自己的一种文体。”⑥“文体”既然是一种叙述的方法,那么评价一个作家的文体优劣,也就离不开对这个作家的文学语言的析解与品评了。韩侍桁接着论述道:“若顺序地读了这位作者前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为适合着人们的颂辞,大量地写作,尽力地向着外表上发展,时时苦心地构想出那自己以为那颇有深刻意味而又机警的词句。”⑦这些论述直指沈从文小说在文字和词句上的某种不足,可见韩侍桁对沈氏小说的明显不满。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足呢?在韩侍桁看来,导致沈从文小说文字和词句上不足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轻飘的文体”形式:“作者为创造自己独有的风格,是需要对于表现的能力有着多时的修炼,——这是颇费作者的苦心的。因此,有取巧的作者们,不肯经过苦心的修炼,时常取一种最易于模仿而是轻飘的文体,那虽便于叙述,而是有害于力的表现。现今我们所论着的这位作者,便是这样的。”⑧在阐述了沈从文小说取材范围狭小、文本意义单薄而只是不断变化叙述花样之后,韩侍桁最后下结论说:“关于这位作者,我想我们无需多说了,因为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⑨
韩侍桁和苏雪林的文章都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应该算是最早的两篇谈论沈从文小说“文体”问题的文章了。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已博得了“文体作家”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显示着论者对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并不高妙的一种评价,不言而喻是带着几分讥嘲和贬斥意味的。此种情形,一方面表征着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当时的文学主潮并不完全合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文学作品从诞生之期起就是有着争议性的。30年代批评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上的贬义性界说,直接影响到了50年代文学史家的学术结论,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指出,沈从文“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像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⑩王瑶的这段评价,虽然没有在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谓上作过多纠缠,但论述的无疑仍是沈从文小说文体上的问题。在评价沈从文作品“空虚浮泛”这一点上,王瑶与韩侍桁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文学史重写”浪潮里,沈从文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的重写不仅包括对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的重新确认,还包括对“文体作家”这一称谓的内在蕴涵的重新书写。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之前,从正面来肯定和阐发沈氏“文体作家”称号的学者并不多,即便是在给予沈从文高度评价、并对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夏志清那里,对沈从文文体上的表现也是颇有微词的。夏志清指出:“这些小说(指沈从文1924-1928年间的小说——引者注),大体说,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感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11)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评价,牵涉的对象只是作家起步之期所创作的那些小说,也就是说比韩侍桁所评说的范围还要狭窄,同时也没有韩侍桁的那种“载道”论偏见,因此还是较为客观和公允的,不过他的观点显然又与30年代人们对沈从文的评价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体作家”的贬义性意味。从30年代开始直到1980年代初,大陆学界对沈从文称为“文体作家”的界说并没有多大改观,而且学者之间的立论也颇有悬殊,虽然有人认可“沈从文的作品文体繁多,不拘常例。他善于组织情节,特别是结尾,常常出现一个突然的转折。”(12)但更多人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责怪沈从文“很多作品都停留在讲故事上,没有塑造出典型人物。”(13)难怪当凌宇在80年代早期着手研究沈从文时,会得出结论说:沈从文在30年代获得的“文体作家”雅号,其实只是一个“褒贬合一”的称呼(14)。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不仅受到了夏志清、李欧梵、司马长风、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的影响,还受到了当事人对过去历史重述的牵制,从这个角度上说,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对老师的追忆和阐释,自然也影响到了文学史家对沈从文“文体作家”历史意义的重新评定。在接受李辉的一次采访时,论及沈从文对佛经的改写,汪曾祺介绍说:“那是他的拟作,受《十日谈》的影响。当时他主要给张兆和先生的弟弟编故事,就拿此作内容,属于试验。但从文体角度来看,他把佛经翻译注进了现代语言,应该说有所创新。这些小说,语言半文半白,表现出他的语言观,我看还是值得重视的试验文体。”(15)当李辉继而追问有关沈从文文体试验的细节时,汪曾祺很自然地将沈氏的文学创作移接到西南联大时期,他说:“偶尔有这种情况。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曾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创作一部分作品。另外,他有时还有意识地模仿一些名著,我想他是在揣摩各种体验。他的《月下小景》中有些民歌,我不大相信是苗民歌,完全像《圣经》里的雅歌,像《鲁拜集》中的作品。”(16)很显然,汪曾祺所说的“文体试验”之“文体”,与韩侍桁、苏雪林所称呼的“文体作家”之“文体”,并非同一概念。同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的言说,汪曾祺也不再专注于30年代,而是将时间有意识地拓宽,将人们的视线挪移到对沈从文40年代文学创作的关注上。这种叙事策略,早在沈从文逝世之期,汪曾祺为老师所写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篇怀念文章中已有所体现。在该文中,汪曾祺评论沈从文“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40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17)这里不仅是在谈论沈从文40年代的“文体”试验,而且还将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概述为“沈从文体”来加以赞许。汪曾祺的上述评价,对文学史重新阐释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独特身份无疑起到了重大影响和规划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汪曾祺对沈从文文体试验的充分肯定,某种程度上正是为此后文学史家赋予“文体作家”以褒奖之意提供的强大理论支持。
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可以说是从正面塑造着沈从文“文体作家”的历史形象的。程光炜、吴晓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称“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他对文本形式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叙事层面寄寓着审美化冲动。”(18)罗振亚、李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虽然指出了“文体作家”这一称呼的历史原意,但又从褒义的层面力挺他的“文体家”身份:“沈从文早年获得‘文体作家’的戏称,包含着时人对这位‘乡下人’的贬义。实际上他灵活穿梭于各种文体,并且创造性地进行了文体间的融合,可以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家’。”(19)而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一著中,吴福辉较为机智地传递了“文体作家”称谓早已发生了从贬到褒的历史性转折这一时代信息,他阐述道:“沈从文历来被称为‘文体家’。在一个时期内,这个称呼甚至带有贬义,现在我们可以正面对待它。”(20)吴福辉所说的“正面对待”,其实就是对沈从文的文体自觉给以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因此他接着指出:“在小说体式上,他排除了废名式的晦涩和自赏,使得现代的诗体乡土小说生气勃勃,有浓厚的文化积淀、指向。这种小说重视了感觉和情绪,或者说总是将直觉印入物象、人象,注意叙述主体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营造气氛和人事描述的统一,使得叙述灵动而富生气。它并不十分在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刻意安排,而把‘造境’作为叙事作品最高的目标。”(21)从这段话不难得知,吴福辉是将沈从文奉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创作的典范来进行文学史建构的。1990年代以降,文学史家态度一致地将“文体作家”作为褒义之词,来称赏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写文学史”以来以审美性作为文学评价最高标准的美学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从30年代韩侍桁、苏雪林等人以“文体”为关键词来评述沈从文小说,到今天许多文学史教材仍然沿用“文体家”、“文体作家”的称呼来概述沈从文的小说艺术,虽然使用的关键词没有变换,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文体”这个语词在不同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那里,其含义并不完全一致。概括起来,在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描述中,“文体”一语至少有下述四种含义:第一,指“叙述的方法”,这是评价沈从文小说时“文体”一词被赋予的最初的语意,在韩侍桁、苏雪林那里表现得很突出。对“文体”的这种理解,显然是立于传统叙事学的基点上,将小说看作是讲故事的艺术,因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22),所以韩侍桁指责沈从文不会“讲故事”,说他小说中重要的事件“全被作者儿戏叙述的笔调所毁坏了”(23),以此来否定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水准。第二,指文体上的各种尝试和试验,这是汪曾祺的理解,也符合沈从文“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24)的创作理念。这种理解强调了沈从文许多小说的非定型状况和在写法上大胆探索与不断创新的精神。在汪曾祺看来,正是因为沈从文在小说艺术道路上的大胆试验、不断求索,才成就了他富有个性的“充满泥土气息”和“文白杂糅”特点的“沈从文”体。(25)第三,指沈从文所创造的诗化小说体式,吴福辉、杨联芬等即持这样的观点。在这种“文体”理解下,沈从文的小说被认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朴讷、平淡和抒情”(26),有着“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27)。第四,指沈从文的跨文体写作而生成的独特“文体”形态。罗振亚、李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即曰:“他灵活穿梭于各种文体,并且创造性地进行了文体间的融合……沈从文的小说营造了诗的意境,糅合了散文的笔法,从而达到纯美的艺术境界。他的散文则汲取了小说、游记等创作方式,成为另一项创造。”(28)在这种理解下,“文体家”的“文体”就不再专指沈从文的小说体裁了。
综上可知,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谓,其内涵的变迁大致经历了30年代的贬义时期、“重写文学史”之前的褒贬合一和“重写文学史”以后的褒义时期等三个阶段,而“文体作家”中“文体”的含义是多重的、游移的,在不同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沈从文”所在的第十三章为吴福辉撰写。
②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第2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朱金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0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第3卷第3期(1934年9月)。
⑤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1日)。
⑥同上。
⑦同上。
⑧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
⑨同上。
⑩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37页,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11)夏志清:《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文学的前途》,第94~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2)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第5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13)十四院校编写组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0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第3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5)李辉:《汪曾祺听沈从文上课》,《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
(16)同上。
(17)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第1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程光炜、吴晓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罗振亚、李锡龙主编《现代中国文学》,第20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2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1)同上。
(22)[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第20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23)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
(24)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25)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晚翠文谈新编》,第208页。
(26)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第18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83页。
(28)罗振亚、李锡龙主编《现代中国文学》,第205页。
标签:沈从文论文; 汪曾祺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体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边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