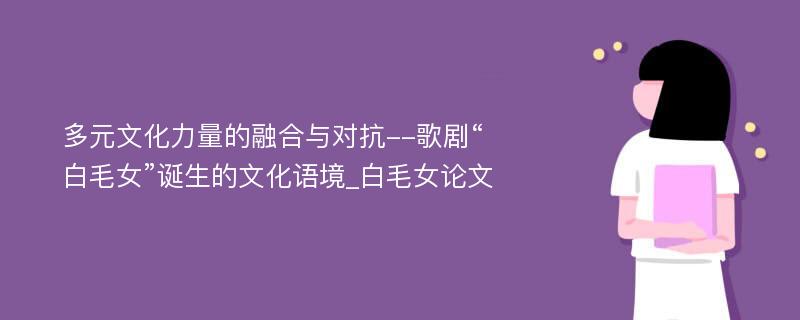
多重文化力量的融合与交锋——歌剧《白毛女》诞生的文化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毛女论文,文化论文,语境论文,歌剧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6-0060-06
《白毛女》被誉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是革命歌剧的经典之作。然而,为什么这个叙事偏偏被写入“歌剧”形式当中,而不是当时已经相对成熟的话剧或者其他剧种,“民族新歌剧”的艺术冒险如何成为必然?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回到《白毛女》诞生的文化语境当中,尤其是追溯到秧歌运动那里。正是新秧歌为“民族新歌剧”提供了土壤和营养——“《白毛女》是在秧歌基础上,创造新型歌剧的一个最初尝试”[1](P860)。
由于戏剧叙事在唤起民众情感认同方面的特殊作用,“秧歌剧”成为阐释新社会合法性的得力工具;而“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恰恰提供了一个最符合时代需要、最契合意识形态话语意志的叙事由头。于是,以“歌舞剧”的形式讲述“白毛女”的革命叙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更重要的是,延安渴望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获取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因此,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创新冲动,试图构建新的文化秩序。1943-1944年间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就是重构文化秩序的初步尝试。改造后的秧歌剧沟通了民间形式与革命叙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成为新文化实践的重镇。然而,秧歌剧不是终点,在创新欲望的驱使下,“民族新歌剧”呼之欲出。于是,“白毛仙姑”传说被改编为“民族新歌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一、民间文化:延安新文化秩序的基点
相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延安确立新的文化形态的自觉是比较晚的,直到1940年才有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2](P662)。这开台锣鼓就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①。这篇演讲不仅确认了延安文化的身份——现代文化转型之继承者与领导者,而且通过鉴别、选择,指明了延安新文化所要断裂和延续的各种文化资源。报告表明,延安试图重新构建文化秩序,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愿景。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普及”和“提高”的现实需求出发,特别将民间文化纳入到新文化的视野中。这是继20年代左翼文人的“大众化”讨论后,民间文化第一次被有效地整合、利用。由此,延安新文化秩序渐趋明朗,即这是一个以民间文化为基点,融合其他“合法”文化资源,向着革命而现代的方向聚拢的等级序列。
为什么延安给予民间文化特殊的重视?为什么首先选择民间秧歌与革命结盟?这与延安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密不可分。1935年10月,长征队伍到达陕北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文化贫瘠的黄土地。这里地处偏远,资源贫乏,盗匪猖獗,社会环境极其恶劣。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处于地方武装冲突中。辛亥革命以后,又成为军阀混战之地:哥老会、皖系军阀和直隶军阀相继控制了陕西。红军到来以前,陕北是井岳秀的基地。“他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小军阀不断从效忠这一军阀转到那一军阀,这是支撑整个这一结构的重要活动方式”[3](P338)。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这里的影响极其有限:边远一些的地方,四五百人中难找到一个识字的,而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整个县内也只有一两个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上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诉求,将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对于新文化的筹划者来说,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以取得民众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最终,他们在陕北农村发现了土生土长、粗野豪放的民间文化,发现了民间秧歌在组织农民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初的民间秧歌,有歌、有舞、有剧,也有歌舞剧三位一体的“小戏”。从表演形态上看,一般是男女对扭,男扮女装,嬉笑怒骂,无所拘束。从美学风格上说,极具喜剧情调,红火热闹。从社会价值上说,秧歌表达了民众对人生和世界的愿望,“含有令人神往而又有危险性的思想、愿望、性冲动、道德怀疑和造反空想,以及诸如此类的颠覆、或者威胁乡村社区的意念等”[4](P2-3)。
30年代末舒湮参观延安时,亲眼目睹了上元节时候民众对秧歌的期盼和渴望:
那天晚上,延安大街上两旁店铺都在廊檐下扎彩张灯,过了酉刻,索性连门也掩上,在门口列着几排长凳,留作观灯的坐席。我们从城外回到旅店,正想走出去吃饭,招呼店伙替我们锁门,谁知他们也都去看热闹了。饭馆灶上封着火,满街全是看灯的人。我们既无处找饭馆果腹,只好也跟随众人后面,忽南忽北,恭候花灯行列的过市。[5](P27)
一时间,花灯、杂耍、丝竹管弦、高跷、舞狮等等,齐向街头涌来。“几个壮汉所扮的乡下婆娘的扭捏模样,脸上打满厚厚的白粉,学着三寸小脚的莲步”,满口调情的俚词,引得人“笑得合不拢嘴”。那高跷尤其引人注目,“跷棒约有七八尺长,踩跷的孩子走路快的时候,连我们两条腿也追不及”[5](P27)。那一夜,无论是秧歌演员还是观众,个个都沉浸在活跃而狂纵的欢乐中。“三百多天积压的苦闷,都在一个晚上发泄尽”[5](P28)。秧歌伴随着陕北农人度过每一个岁末与春始,成为乡民灰色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调剂。那是一种外来者所不能体悟的狂欢性体验,“是它容许农民参与一种戏剧式的游戏”[4](P2)。秧歌不仅折射出民众千百年来被压抑的渴望,也呈现出他们朴实的艺术情趣。
正因为如此,当延安试图构建新文化秩序时,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秧歌)就被突显出来,成为延安新文化秩序的重要基础和生长点之一。而且,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提倡和推动下,学习、利用民间文化甚至成为一种政治表态。否则,就被指责为“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6](P587)。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民间秧歌的兴趣和借用不只是延安单方面的意愿,知识分子“五四”时期就曾经关注过这种民间艺术形式。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他们发现秧歌在民间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力:
农民无论男女老幼,最嗜好的娱乐是秧歌。他们对于秧歌的兴趣比现在城市内摩登青年对于电影或跳舞的兴趣还要浓厚得多。他们不但要在新年、节日及各庙会时去看秧歌,并且在田间工作时,行路时,歇息时,不发声音则已,一发声音就是大唱秧歌。[7](P2)
知识分子敏锐地认识到:所谓“除文盲作新民”的现代改造不得不重视民间文化的力量,或者说只有借用这种力量才能够顺利实现“移风易俗”。于是,他们设想“将已有的秧歌加以改良,保存它的优点,再进一步编写新的秧歌,输入新的理想,来渐渐替代旧的秧歌”[7](P3)。这是民间文化第一次面临现代化挑战。事实上,这一次的秧歌改造仅仅限定在理论设想和初步调查研究的兴趣上,带有浓厚的学术研究色彩,不要说造成大规模的运动,就是具体的改良措施也没有实践的现实条件。但是,这些尝试至少表明了以下三点:一是发现了民间文化内部种种“好”与“不好”,认识到改良民间文化的重大意义;二是以“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意识重新审视民间文化,为民间文化的现代化开启了一种思路;三是将旧秧歌的改造看作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尝试对民间文化进行功利主义的利用。可以说,知识分子早期的努力为延安“秧歌运动”提供了文化和历史的准备。
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争最直接地改变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乡村文化、民间文化取代都市文化、精英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随着知识分子由都市向乡村的迁徙,文化中心由东部向西南的撤退,“到民间去”就不止于口号宣传,而已然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了。“从前的基本观众是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小市民,而今天的基本观众,却是广大乡村中广大的士兵、农民”[8](P29)。在这种情势下,秧歌又一次走入知识分子的视野。不过,与“五四”时期不同,此时知识分子最迫切的愿望是如何改造秧歌,使其“成为抗战的一种宣传工具”[9]。于是,昔日对秧歌的理论兴趣和改造宏愿,终于在战争的催发下化为了实践的力量。
总之,无论是延安有意识的资源重组,还是知识分子自发的文化转向,都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意义,并且都没有停留于民间秧歌的原始形态:皆主张以现代意识改造它,使其实现现代转变②。在创新冲动的驱使下,甚至希望以民间秧歌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秧歌舞,必须改造,必须发展,进而制造新的民族形式的歌舞剧”[10]。否则,“‘秧歌舞’将停留在低级的地步,永不会达到高级的,真正成为一种革命武器的阶段”[10]。换言之,民间文化必须实现现代性转化,才能够与革命关联起来,才能够成为新文化秩序所倚重的基础。延安全力推动的“秧歌运动”,即是加速此种转换的重要文化实践之一。当民间秧歌被现代化、革命化和政治化以后,它终于从民间的、边缘的位置移居到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中,进入历史的视野。
二、秧歌剧改造:民间语法与革命语法的融合
自秧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纳入到延安新文化秩序中以后,“延安文艺界几乎是集中一切来干秧歌了”[11](P109)。其中改造最成功、创作最多、最受重视的还是秧歌剧。“每个延安人都很自负的谈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们谈到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剧就不配谈边区文艺似的”[11](P103)。新秧歌将民间语法与革命语法融合在一起,最终发展为成熟的大型秧歌剧。但是,秧歌剧的繁盛恰恰暴露出延安更急切的创新冲动——它已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创造一种“民族新歌剧”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可以说,秧歌剧叙事功能的发掘和现代化改造,直接诱导了《白毛女》的艺术选择。
(一)戏剧叙事的影响力
为什么“这次各项宣传工作中(即1943年的秧歌运动——笔者注),最好的要算秧歌剧”[12]?这是由于延安充分认识到“戏剧”在民众中巨大影响力的缘故。民众喜欢看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习惯于歌舞剧的表演形式。由于“歌舞剧,在我们中国是一个传统”[13](P88)。延安民众“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地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伸长了头颈等待着。他们渴望着观看”[14]。因此,延安毫不掩饰对戏剧叙事的强烈兴趣,周扬就明确表示:“我是主张秧歌有故事的。故事可以是实事,也可以是虚构”[15] 的。
另一方面,戏剧在满足观众欣赏期待的同时,也满足了意识形态话语诉求内在化的目的。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接受过程不同,看戏时“集合在一个集体中的所有的人,他们的情绪和思想都是一致的,并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他们的个人意识消失了”[16](P10)。所以,戏剧可以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17](P292)。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戏剧”是将革命话语植入民众情感结构的最有效的叙事载体,得到了最充分的信任。
就宣传的观点说,延安对于戏剧的需要比其它文艺更为迫切;就普及的观点说,戏剧是直接和群众感官相通的娱乐,也比其它文艺容易深入民间。[11](P121)
由于秧歌在民间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延安在各种戏剧中,以秧歌剧干得最为出色。1944年,赵超构参观延安时,看到当地大小书店的“文艺书籍中,印得最多,或者销得最好的,是秧歌”[11](P121)。因此,当“白毛仙姑”的传说流入延安时,赋予其“歌舞剧”的形式就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二)秧歌剧的现代化
秧歌小戏一般通过两三个人的对话与唱和来表现剧情。“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叙述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11](P109)。对延安来说,如何借用秧歌剧的民间趣味和叙事结构表现革命话语,如何将意识形态叙事写入秧歌剧,如何处理民间形式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新文化实践的成败。一言以蔽之,秧歌剧改造实际上是民间秧歌革命而现代化的过程。
延安一方面借用秧歌剧的叙事结构,以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置换了民间秧歌中世俗的、充满色情意味的内容,从而唤起民众对新政治、新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将现代戏剧(主要指话剧)手法、现代音乐元素融入其中,使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最终推动秧歌进入主流文化。
对于前者而言,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新秧歌剧”的首创之作——《兄妹开荒》。这个小型秧歌剧不但借用了民间“小场子”一男一女的形式,而且完整地保留了民间秧歌逗趣、活泼的喜剧色彩:“调皮的哥哥,天真的妹妹,也极富乡村的情调”[11](P108)。与此同时,又以兄妹两个生产积极分子之间的误会代替了旧秧歌的男女调情,近乎完美地把民间趣味与政治话语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是百看不厌”[11](P108)。鲁艺戏音系主任张庚曾经坦率地道破民间秧歌革命化的改造策略:
《兄妹开荒》,首先是学了民间秧歌一男一女的形式,而这一男一女必须闹些纠葛,有些逗趣的事情。但是,这中间有几点是和旧秧歌基本不同的。旧秧歌是写旧社会、旧人物,这是写新社会、新人物;旧秧歌是色情气氛很重的,这里却是不能有的;旧秧歌是单纯娱乐的,这里必须有教育意义。也有几个共同点:两者都是要求活泼愉快的气氛;都要求短小单纯,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于是,为了去掉色情成分,就把容易产生色情因素的夫妻关系,变成了绝不能引起色情感觉的兄妹关系。再就是,如果要引起纠葛,最好是二人中一个进步一个落后的对比。但是,为了要表现新社会新人物,如果在这短短的一个戏里仅有的两个人物中间就有一个是落后的,那岂不是很难说明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真实情况了吗?但如果两个都是正面人物,纠纷又如何引起呢?结果就想起了故意开玩笑的办法,这样反衬出两个人的积极性来。[13](P66)
从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话语怎样通过巧妙地更改民间秧歌中的人物关系、置换戏剧冲突等策略,过滤掉原有的色情成分与不合规范的因素;又怎样不动声色地把政治话语镶嵌到民间秧歌的结构中,在满足民众审美期待的同时,培植起民众对新生活的认同与渴望。
随着秧歌改造的深入,旧秧歌剧的主题完全被政治话语所取代,秧歌剧成为规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的载体。延安组建新社会过程中的所有断面,都曾经被改编为秧歌剧。以1944年春节期间的秧歌演出为例,56个秧歌剧中,描写生产劳动(包括变工、二流子转变、部队生产、工厂生产等)的有26篇;刻画军民关系(包括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的有17篇;自卫防奸的10篇;敌后斗争的2篇;减租减息的1篇[15]。在轻松欢快的文化消遣中,“观众对于新的社会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已完全和自己的思想、情感、伦理观念相一致了”[18](P421)。所谓“中国戏剧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将这种戏剧当作一种生活理论的导引”[19](P66),并非虚妄之语。
如果说,秧歌剧内容的“革命化”体现了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交锋,秧歌剧形式的“现代化”则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一次融合。民间秧歌剧有歌有舞,红火热闹,活泼轻松,但往往“拖拖拉拉,不干净,不集中”[13](P64),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叙事效果。而从事秧歌改造的知识分子却大多是话剧出身,他们赋予话剧以“进步”意义:认为话剧“是最现代的进步的戏剧形式”,“从它开始出现的一天起,一直就是站在进步的、反帝反封建立场上的,它已经锻炼成为一个暴露与反映现实的利器了”[8](P38)。所以,当知识分子寻找民间文艺现代化的途径时,竭力主张“必须有话剧的相互扶助来完成这任务”[8](P38)。因为“若不互相配合着,……是不能进一步达到一个新形式创造的阶段的”[8](P34)。作为延安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阐释者,周扬曾明确肯定:没有“五四”新文艺形式的加盟,“新秧歌的创造是不可能想象的”[15]。尽管《讲话》以后,延安话剧创作过于沉寂,但这“不是放弃而是分解”[11](P127):
他们把话剧的化妆手法加入各种旧形式的戏剧中去。像秧歌,就可以说是已经话剧化。在编剧和演剧的技术上,他们也不断利用话剧的经验来提高旧的。既然话剧的优点可以移到旧剧中去,自然没有专重话剧的必要了。[11](P127)
实际上,“到秧歌和话剧结合之后,能够更丰富地来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这就展开了它广阔的前途”[20](P66-67):由最初的小型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逐渐向情节更曲折、视角更广阔的大中型秧歌剧发展,出现了《牛永贵受伤》、《赵富贵自新》等多幕多场剧。1944年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完成,标志着秧歌剧现代化改造臻于成熟——它不仅可以刻画延安新社会的横断面,而且随着叙事手段的丰富和增强,已经能够组织革命历史的叙事了。
三、结语:《白毛女》恰逢其时
“秧歌运动”从1943年发起,中经1944年的高潮,至1945年进入尾声,至少从宣传力度上可以这么认为③。其因由当然与新秧歌剧已经获得民众的认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创新”冲动催促着延安文化实践不可有片刻停留。秧歌剧无论在叙事、音乐,还是表演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延安对于新的歌舞剧的渴望。“秧歌是向这方向的一个努力,但也还只是一个方面的,而且是初步的努力”[15],所以一旦秧歌剧实现了革命化和现代化转化,延安就迫不及待地呼唤“民族新歌剧”的历史性出场:
从秧歌剧,一定能产生出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来的,在千百篇秧歌剧创作之中,总会有好多篇能够得到永久的流传,而在大型民族新歌剧新话剧的建立上它又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重要的推动力量。[15]
“白毛仙姑”的传说恰恰在这个时候传入延安。传奇中蕴藏的叙事意义被敏锐地捕捉到,“人”与“鬼”之间的神奇变换为论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于是,叙事和形式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这里相遇了。一方面是如何对民间传说进行革命化编码,发掘叙事的革命意义,一方面是如何把它组织进想象中的“民族新歌剧”中,实现新文化秩序的构想。对后者而言,这不啻为一种艺术冒险。因为“民族新歌剧”的面目究竟为何,没有人知道。某种意义上,《白毛女》生产场域中发生的各种矛盾、纠葛和曲折,亦来源于形式创新的困惑。在那里,革命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仍旧处于博弈和调整中。延安新文化秩序并非一蹴而就。
[收稿日期]2007-10-20
注释:
① 1940年2月20日,该文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
② 比如,演员上,突破了性别的禁忌,使女性走向了广场;内容上,植入抗日、反汉奸等时代主题,输入新的叙事元素;音乐上,在民间小调中加入了抗战歌曲:“它不仅是几个‘观念的’不相连续的歌子的凑合了,而且也有了简单的故事的联结”;舞步上,也不仅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扭一扭’,而且也有了简单的场面的穿插了”。(林采:《从“秧歌舞”谈旧形式》,《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29日,第4版)
③ 《解放日报》对秧歌运动的报道,1943和1944这两年的宣传力度最大,密度也最大;到1945年时,就只有零星的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