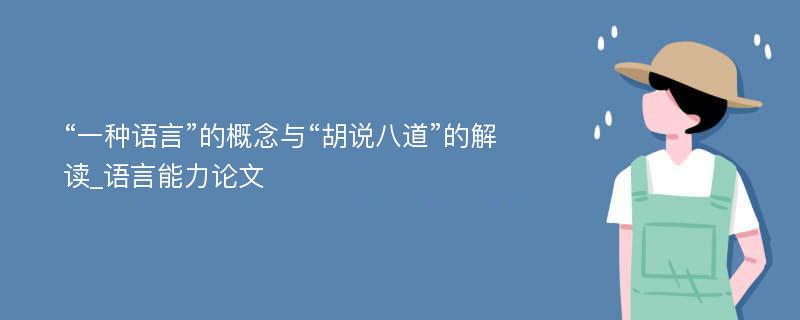
“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门论文,观念论文,语言论文,乱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52-08
一、“一门语言”的观念
平常,人们很自然地说:“方先生‘懂几门语言’(或者‘知道几门语言’‘掌握几门语言’)。”这一说法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绝大多数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接受。不管他们是基于乔姆斯基所说的E-语言观念还是I-语言观念①,“一门语言”通常都被认定为是一个合法概念,“掌握一门语言”这个说法也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以达米特和乔姆斯基为例。在他们看来,设若有两个人在成功交流,则两个对话者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都掌握了一门语言,都知道如何使用这门语言。进而,为解释说话者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会认为,他们大脑专司语言的机能(language faculty)处于同样知道语言知识的成熟状态,装备了同样的内部装置。达米特则会认为,他们对同一个意义理论具有隐知识,更具体地说,他们都知道满足组合性要求的意义理论的公理以及相应的语力理论。[1]
质疑“一门语言”的观念对当代语言哲学家而言不是新鲜事。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经验现象,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划定一门语言的范围以及如何对语言进行个体化。在批评E-语言观念的时候,乔姆斯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一语言观念无法提供区分性标准以区分不同的语言。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汉语中某些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于欧洲一些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2]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提供了一些不利于“一门语言”这一观念的理由。首先,在用游戏来类比语言活动之后,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特征就抵制赋予语言某种本质的理论态度,抵制试图将语言从其用法中抽象出来做理想化、简单化思考的理论倾向。“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3]既然语言或者说各种语言的殊例(token)不过是日常生活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套工具或技法,它们受制于特定的实践活动,那么,抽象地谈论“一门语言”的“类型(type)”就没有意义。其次,“一门语言”必然要预设一种“完整性”的观念。“就他已从主张语言的本质在于模拟事实,转到主张它乃是由不同技法构成的混杂物而言,语言的完整性这一观念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结构或功能,可作为界定完整性观念的参照物。”[4]
出于不一样的考虑,在论文《墓志铭的巧妙错乱》②里,戴维森通过对实际交流的一些特殊案例进行考察,指出:“不存在被称为一门语言的东西,也不存在像很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认定的‘一门语言’。因此,也就没有要学习、掌握或者生而具足的叫‘语言’的那种东西。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个观念,即语言使用者获得有一个被清晰定义了的共享结构。”[5]
不管是这一论断的效果,还是戴维森获得这一结论的方式,都曾让许多语言哲学家感到诧异。达米特、哈金、巴昂、兰贝格等哲学家分别根据自己的理解讨论过戴维森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取得太多一致意见。下面,笔者希望通过对照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立场和他想要攻击的约定论语言观,依据文本分析铺陈戴维森的基本思路,然后以一种合理的方式重构其论证。约定论的语言能力刻画方案不能解释人们对“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这是戴维森的论证所依赖的基本洞察。我们基于这一判断作出的解读,比起其他若干解读有显然的优点——既不需要引入有争议的论题,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戴维森由“乱语”现象的经验观察所获得的哲学洞见。
二、刻画语言能力的原则
通常认为,格莱斯(Grice,P)的论文《意义》(1957)标志着意义研究的一个新纲领的出现,即在探究一个陈述的意义时,从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转向说话者的心智状态和心理内容。按照格莱斯的想法,后者才是语句意义的最终来源。格莱斯首先区分了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6]③他认为,非自然意义才具有语义性质,这也是语言哲学研究关涉的内容。在之后的论文里,非自然意义又被区分为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说话者意义(speaker meaning)。语言意义指的是词句的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也被称为标准意义或约定意义;后者指说话者使用这些词句时所蕴含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词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义都能保持一致。不过,在诸如反讽、隐喻等语言现象里,二者会出现明显的分离。
对格莱斯的区分抱有同情,但不满意于“字面意义”这个概念,戴维森为他的诠释理论引入了“第一意义(first meaning)”的概念。所谓第一意义,指“在诠释的过程中应最先考虑的意义”。准确地说,“第一意义”指“某特定言说者在某特定场合陈述的语句或语词的意义,如果该‘场合’,以及‘说者’和‘听者’都处于‘标准’或者‘常规’的情况下,则第一意义便可以通过查询基于实际用法的字典(如Webster’s Third)而获知”。[7]反之,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或者说当说话者意义和字面意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识别第一意义的最好办法则是通过说话者的意图。
基于这一概念,戴维森概括了三条基本原则,按他的判断,正是这三条原则支撑着为众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语言观念以及对语言能力所作的刻画。它们分别是:(1)第一意义是系统性的。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说话者或诠释者能够根据一个陈述的组成部分的语义性质以及该陈述的结构对该陈述作出诠释。这要成为可能,诸陈述的意义之间就必须具有一种系统的关系。(2)第一意义是共享的。说话者和诠释者要能成功并且经常性地进行交流,他们就必须共享一个类似于(1)所描述的诠释方法。(3)第一意义受通过学习获得的约定或规则的控制。说话者和诠释者的系统性知识和能力是在需要进行诠释的场合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的,并且本质上是一种约定。[8]
针对这三条原则,戴维森提示了一般性的疑虑。比如,“通常,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句中能担当不止一个的语义功能,因此,诠释者对出现该语词的语句的诠释就不能由诠释者的语言能力所包含的规则唯一地确定。尽管陈述所出现的语境的其他特征能够帮助诠释者给出唯一正确的诠释,但要具体地阐述出相应的规则来减轻这种模糊如果说不是不可能,至少也非常困难。”[9]又比如,“并不存在一条将语言场合中的意义与在该场合中出现的语句序列联系起来的严格规则。”[10]这些疑虑与上述一般性的解释语言能力的理论企图相关联,按照一些有影响的观点,获得语言能力不过是掌握了一套句法规则(或者一个意义理论)。
特别值得讨论的是,上述原则是否充分地描述了语言能力?戴维森的回答是否定的。考虑他的两个例子:对于语句“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孩子”与“他们生了孩子并且结了婚”而言,诠释者一般能意识到两个句子的区别;在语句中分别使用“并且”和“但是”可能产生的不同蕴含,诠释者同样也可能清楚。在戴维森眼里,于后者,“没有什么不与语言知识为伍的常识能让诠释者认识到它”,[11]但对于前者而言,诠释者能做的这些事情并不属于基本的语言能力,也许至少包括对社会习俗的了解——比如,生了孩子再结婚的行为不太合乎中国的传统习俗或在法律上不恰当。
格莱斯曾致力于探究支撑我们推测语句蕴含意义的能力的一些基本原则。要进行成功交流,说话者似乎最好知道这样一些原则,然而,对语言能力的描述是否应该包括关于这些原则的知识,这一点尚没有一致意见。一方面,这些原则表达了我们希望诠释者应该具有的一些技巧,没有这些技巧,交流就会极大地受阻;另一方面,这些原则是一个聪明人能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东西,没有这些原则,并不影响人们的生计。[12]
应该说,这几条原则面临的解释性困难不是戴维森讨论的重点。通过对实际的语言交流进行考察,他认为有一类重要的语言交流现象不能为上述原则所容纳,因此,需要放弃基于这三条原则之上的“语言”观念以及对语言能力的描述,特别是需要放弃原则(3)。
三、“乱语”的诠释
戴维森关心的这一类语言现象包括口误、双关、反讽、语词错用、仿词等。仅仅示区别于语言的常规用法(也许这么说很可疑),我依照戴维森的用法,从成语“胡言乱语”中切出后两个字,毫不带贬义地将它们统称为“乱语(malapropism)”。④它们之所以引起戴维森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事实:“听话者能毫无困难地按照说话者所意图的方式去理解。”[13]
确实,当我们听到一个口误、一个无意带有语法错误的句子、一个有意的诙谐说法、一个新出现的习语或者某种语境下改变了语词意义的非常规用法,我们都能正确地理解说话者意欲传达的意思。比如说,当一个小媳妇亲昵地说出“恨死你了”时,她的爱人会觉得如喝了蜜一般甜;一个相声演员说出“人人死而平等”的台词时,理解了的观众立即报以会心的微笑。这类现象,在戴维森看来,“给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带来了威胁”。[14]
在出现乱语的诠释场景中,诠释者是如何理解这些表达式的第一意义呢?问题是,诠释者对这类语言现象的理解绝对不是基于预先装备了的知识,或者根据某种事先的“约定”或者“规则”。换言之,这一类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并不是由通过约定建立的联系得到规定。如果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所遵循的原则与这些现象不相容,那么,这些描述语言能力的原则就要得到修正。
根据原则(1),诠释者必须在掌握了有限数量语词的基础上,学会不同词汇项的组合方式。因此,面对任何一个新的语句,诠释者能根据它所包含的语词和语词之间的组合方式来确定该语句的意义。简言之,语言的系统性和组合性要求我们给语言能力一个递归性的解释。⑤在诠释理论的框架下,说诠释者掌握了一个“诠释理论”就是为诠释者的语言能力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当然,考虑到这个事实,即“没有人拥有用于诠释任何自然语言的说话者的一个完全满意的理论的显知识”,[15]戴维森不认为一个描述诠释者语言能力的理论必须成为诠释者的命题知识;同时,他也否认这样一个理论必须是关于说话者心智运作的理论。换言之,一个理论模型不必要成为心理实在。
要求语言交流的双方共享一些东西,原则(2)的这个方面为戴维森所同意。不过,他坚持认为,对成功交流而言,需要为诠释者和说话者共享的是,他们对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的理解,原则上并不要求他们共享一门语言。
原则(1)和原则(2)与戴维森的乱语案例并无逻辑上的不相容,虽然他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提出异议。然而,倘若结合原则(3),真正的困难便出现了。
关于语言的意义,达米特帮助我们看到这样两幅由语言哲学家给出的图景。图景(1)里,语词具有不依赖于说话者的意义;图景(2)里,是说话者将意义赋予语词,意义总同说话者的内部心智操作相关。[16]自然,这两幅图景都在某些地方过于粗糙,不过,大多数语言哲学家仍在这两个图景的基础上工作。
就图景(1)来说,语言的社会约定特征被认为是最本质的。约定论的语言观可以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发现它的源头,在当代哲学家中,从刘易斯到达米特、米丽肯等人的著作,这都是最鲜明的主题。符号和它所指称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并不由语词或指称物的某种内在性质决定,相反,它们的联系具有任意性的特征,在这个较弱的意义上,大多数哲学家都会同意约定论的观点。不过,倘若认为约定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语言的意义、句法都是出于约定,则会遭遇反约定论者的抵抗。
欣赏图景(2)的哲学家大抵沿袭自格莱斯以来的传统,诸如说话者的意图、欲望等命题态度,心理表征、心智运算等东西(它们被刘易斯讥讽为“心智的隐密操作”)被认为是意义的最终来源。这些哲学家偶或称自己为“新格莱斯主义”或者“反约定主义者”。他们否认通过约定能够给出潜在无穷多的语句的意义,[17]甚至质疑约定对于语言意义是否必要。
显然,原则(3)是那些坚信图景(1)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持有的信念,而戴维森和达米特分别站在不同的画板前。后者认为,“语词自身具有独立于说话者的意义”;[18]戴维森则认为,语句意义同说话者的意图和信念密不可分。“没有约定的交流”是戴维森在《交流与约定》(1984)里就已经论证过的主题。《墓志铭》当然可以看做是这个主题的一个拓展,它同样沿袭了彻底诠释模式以及由彻底诠释引出的反约定主义的语言观。
戴维森给出的对诠释过程的简化描述是这样的:“在语言加工的任何时刻,诠释者都有一个理论。……我假定,诠释者的理论会根据他所能获得的证据进行调整,这些证据包括:说话者的性格、衣着、性别、社会地位,以及任何其他通过观察说话者的行为(语言行为及其他)能够获得的信息。听到说话者的话之后,诠释者会调整他的理论,关于名称的新假设,对那些熟知的谓词的新解释都会帮助诠释者在新证据的基础上对语句的旧有诠释作出修正。”[19]
在简化的交流模式里,要紧的是,“我们用以诠释一个语句的理论总是与特定场合相链接。”[20]正因此,从诠释主义(建立一个关于诠释者的理论模型)的立场出发,戴维森将诠释者在诠释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称之为“即时理论”,以区别于“先在理论”。⑥可以从说话者和诠释者两个不同角度理解这个区分。对诠释者来说,先在理论是他在准备对说话者的一个语句作出诠释之前已经具备的东西,而即时理论就是他在诠释过程中实际如何做的;说话者的先在理论,就是他相信诠释者的先在理论会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即时理论就是他在意图上究竟希望诠释者如何做。[21]⑦
接受这一区分,同时接受上述原则(1)和原则(2)的话,戴维森论证的结果是必须放弃原则(3)。理由在于,在说话者和诠释者没有共享先在理论的情况下,交流仍可以顺利进行,“对成功交流而言,要求被共享的仅是即时理论。”[22]而一个即时理论既“不对应于诠释者的语言能力”,也“并不是任何人(也许一个哲学家除外)愿意称之为一门自然语言的一个理论”。“说‘掌握’这样的一门语言是无用的,因为知道一个即时理论只是知道如何诠释特定场合下的特定话语。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一个语言(如果愿意如此称呼的话)是学来的,或者受制于约定。”[23]
即时理论当然不是我们往常称为“语言”或者“语言能力”的东西,那么,先在理论又如何呢?戴维森争论道:“一般说来,先在理论既不为说话者和诠释者所共享,它也不是我们通常愿意称之为一门语言的东西。”[24]首先,先在理论和日常语言观念的区别因这个事实而显得清晰,即针对不同的说话者,诠释者会持有不同的先在理论,尽管这里的不同还不像即时理论一般,但它同样依赖于诠释者对说话者的了解程度。其次,在多数情况下,先在理论也不必然需要为交流双方所共享,换句话说,共享一个先在理论不是成功交流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可以把这一点视为戴维森的彻底诠释模型的直接结论,对于田野语言学家而言,他的成功诠释并不要求他共享和说话者一样的先在理论,他需要戴维森意义上的宽容原则和对说话者的“持真(holding-true)”态度的确认。因此,从实际交流(尤其是乱语现象)的考察看来,“就交流得以成功而言,诠释者和说话者共享的东西不是预先学会的,因此,也不是他们事先已知的受制于规则或约定的一门语言。相反,诠释者和说话者知道的东西并不(必然)被共享,因此,就不能是一门受共享的规则和约定控制的语言。”[25]
简言之,说话者和诠释者在交流过程中用于语言理解的一般性理论,戴维森称之为“先在理论”。他从正面论证了这一点:在日常的交流场合里,诠释者总是需要依靠特定场合的某些特征以及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揣度,不断将“先在理论”调整为一个“即时理论”,以适应于特定交流场合的方式进行有效地诠释。
综上述,戴维森的主要论证,可以重构如下:
(a)说话者对乱语的成功诠释表明,共享的约定知识(规则)对于成功诠释而言并不充分。
(b)彻底诠释模型表明,共享的约定知识(规则)对于成功诠释而言并不必要。
(c)成功交流所需要的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都不是“一门语言”。
(d)需要放弃原则(3),并且,放弃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受制于约定(或者规则)的知识系统的“一门语言”概念。
四、两种另选解读
《墓志铭的绝妙错乱》究竟主旨何在?哲学家们的判断各不一样。照哈金的观点,它直接否认的是“一门语言”这个概念以及相联系的“掌握一门语言”“语言L的真理概念”等说法。[26]依据另一些学者给出的理解,没有一门语言的主张相当于说,“一门语言”这个概念对于语义学以及交流理论而言没有什么理论地位。一旦我们在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戴维森式的交流理论,“意义”“指称”“一门语言”这些概念就都是可以踢掉的梯子了。[27]此外,也有学者把戴维森的观点理解成“他对诠释的解释导向关于能够给理解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的怀疑论”。[28]
相应地,对于戴维森提供的论证,不同的眼光也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据我所知,当代哲学文献至少还提供了两种解读:一种是巴昂式的解读;另一种是达米特式的解读。按照巴昂的判断,戴维森论证的根基是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论题。达米特的解读则依赖于对语言哲学核心任务的判断。对这两种解读,我们都可以找到拒斥的理由。
在一个评论里,巴昂等人将戴维森的论证重构如下:
(1)判断一门语言的同一性的唯一标准是看是否能将一个唯一的真理理论运用于其上。
(2)在诠释某个体的话语时,总可能存在多个成功的真理理论,并且,没有据以判断哪个真理理论为正确的事实。(诠释的不确定性)
因此,
(3)对于给定说话者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这个问题,总可能有多个回答,并且,没有据以判断说话者说的是什么语言的事实。
但是,
(4)如果存在叫“一门语言”的东西,那么就有据之可以判断说话者说的是什么语言的事实。
所以,
(5)没有叫一门语言的东西。[29]
经过巴昂重构的论证颇难令人信服,最明显的理由是前提(2)还需要辩护。一方面,戴维森确实承认诠释的不确定性——即已有证据总允许诠释者将多种可能的语言归属给说话者;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对于有效诠释而言不会“十分严重”,外部证据和对说话者持真态度的确认可以帮助诠释者作出成功的诠释。后者至少让人警醒——不宜轻易地从前提(2)推出(3)来,毕竟,否认语言事实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反实在论的语言态度,我们确实不知道有任何理由表明戴维森会是一个反实在论者。
显然,巴昂的重构依赖于诠释的“不确定性”。按我的意见,戴维森对“乱语”现象的分析以及以之建立的一般诠释模式不需要依赖于诠释的不确定性论题。更进一步讲,我还特别想强调,《墓志铭的绝妙错乱》和戴维森早期诉诸“塔斯基式的真理概念”的语言研究之间有些距离。
当戴维森讲“(乱语现象)威胁着对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包括我本人需要负责的那些描述)”(着重号是笔者所加),[30]我以为,戴维森想的就是自己早期所构想的诠释模型:当A和B在用汉语(或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时,A和B共享一个关于汉语(或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论(诠释主义的进路不要求这样的真理理论成为A和B的命题知识),该理论为汉语(或被诠释的语言)的每一个语句给出T等式(根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信条,这也就是给出意义)。对根据“乱语”现象建立的诠释模式而言,真正关键的是“即时理论”,而不是“共享”的某种理论结构,后者恰恰是《墓志铭的绝妙错乱》要攻击的东西。对于“即时理论”的建立,外部证据和“宽容原则”仍然起作用,但“诠释的不确定性”却不是论证所必须要的东西。
值得补充的是,巴昂等人重构的论证是基于兰贝格(1989)的理解所作的发挥。对这一点,我们赞成皮晁斯基(Pietroski,M.,1994)的判断——戴维森确实很无辜。[31]
在达米特看来:“戴维森的论证是这样的。为了解释乱语、异常以及不熟悉的用法等等他感兴趣的语言现象,我们需要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或者,照我的说法,称为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这些装备也能充分解释一般性的语言交流。但是,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都不能被描述为关于一门语言的一个理论。因此,语言哲学就根本不需要一门语言这个概念,它要的只是语言。”[32]
但是,这一解读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在这种理解下,完全看不到戴维森对约定论者的攻击,换句话说,约定论者刻画语言能力的原则(3)在论证中完全不起作用。如前述,按我们的理解,这是戴维森的主要攻击目标。其次,达米特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戴维森的论点。这一扭曲的源泉在于戴维森和达米特之间一个广为人知的争论,即意义理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达米特声称自己致力于“意义理论研究(the meaning theory)”,戴维森则乐意谈论“一个意义理论(a meaning theory)”。根据达米特的意见,语言哲学关心意义理论(不是翻译手册,翻译手册已经预设了对一门语言的掌握,诉诸表达式的意义相同也无助于说明什么是意义),一个意义理论应该通过阐明语言的任意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来揭示什么是意义。正是基于对语言哲学任务的这一独特理解,才使得他将戴维森的论证结论解读为——旨在表明语言哲学并不需要“一门语言”这个观念。如果以戴维森的方式来理解意义理论(以T语句给出一个对象语言的所有表达式的意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不可想象。尽管人们已经指出,戴维森的论点同他的其他一些哲学命题不融贯,由此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效果。⑧但是,在《墓志铭的绝妙错乱》里,戴维森本人只承认(或者说只意识到)乱语现象为语言能力的标准描述方案(包括他自己的方案)带来威胁,这一说法显然不意味着他诠释主义的意义理论研究进路有什么改变。
五、结语
讨论乱语现象,戴维森的目标当然不仅仅止于建立一个乱语的诠释模型。毋宁说,通过讨论这些异常的现象,他想要获得关于语言理解的一般性见解。一个诠释性的意义理论无助于说明意义(假定达米特对戴维森的这个批评是对的),同样的道理,既然一个诠释理论需要预设诠释者对语言的掌握和使用,因此也就无法说明诠释者的语言能力。尽管这样,如果将戴维森的论证理解为是对约定论者关于语言能力的描述原则的攻击,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个最基本的教益——如果认为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尤其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语言”。
倘若我们的判断不错,看起来,较之巴昂和达米特的解读,我们的解读就有些显然的优点。它既不需要引入有争议的前提,也不需要强加给戴维森以额外的理论追求。以“如果……那么……”这样的句式作为戴维森论证的结论,似乎弱化了它的冲击力,但这种弱化只是心理上的。约定论语言观与乱语诠释的经验描述之间的相悖,确实要求语言哲学家更好地理解意图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并且要求一种更稳健的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
注释:
①此论文中的“观念”一词大体对应于英文的“notion”或“conception”,不宜理解为洛克或休谟式的“idea”。
②原论文标题为“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与“A Nice arrangement of epithets(修饰词的巧妙安排)”发音近似,但听话者可以在语境中给出这些语音符号的意义诠释。作者以之作为日常交际中口误、用词错误、谐音双关等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出现这些情况时,原则上,不必然会对听说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③格莱斯注意到,“意义”可应用于不同的现象。如“这串足迹意味着熊进了山洞”,二者之间具有类似因果关系的情况,格莱斯称为“自然意义”;再如,“手上的戒指意味着她结婚了”,格莱斯称之为非自然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同说话者的交流意图、意向性相关。用格莱斯的话说,自然意义是事实性的,非自然意义则不然。
④用达米特的术语,则可以分别称之为语言的“标准(standard)”用法和“例外(exceptions)”。
⑤关于“递归”的理解有些分歧。按照达米特的建议,戴维森的“递归”意指“以归纳的方式阐明(specified inductively)”。(cf.Dummett, M.,1986,P.459)
⑥于《信念与意义的基础》,戴维森的最初表达为“a socially applicable theory”,当说话者把这个一般性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说话者言语时,需要把一般性理论精致化,其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为“即时理论”的东西。虑及他的这个想法,可见,达米特将它们分别称为“长期理论”和“短期理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⑦对于这个区分,存在理解上的争议。照哈金的理解,先在理论是对话双方在说话之前具有的一个理论,在对话过程中,它不断演变为即时理论;而在达米特看来,戴维森的真正意思是,先在理论和即时理论都会在对话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笔者倾向于接受达米特的理解。(cf.Dummett,1986,p.459)
⑧针对戴维森的一个常见批评是:既然他的主要哲学目标之一在于,用一个关于真理概念的递归理论作为基础来为自然语言提供意义理论。如果像他所说,“并不存在‘一门语言’”,那么,这一哲学目标就是无的放矢。并且,他对约定T的借用也变得不合法,因为,塔斯基正是要用约定T来刻画对象语言L的真理概念,而对“一门语言”概念的拒斥使得谈论“语言L”变得自相矛盾。总之,戴维森在《墓志铭》里提出的论点会严重损毁他自己的大部分哲学工作(cf.Hacking, I.,1986; Bar-On,D.,& Risjord,M.,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