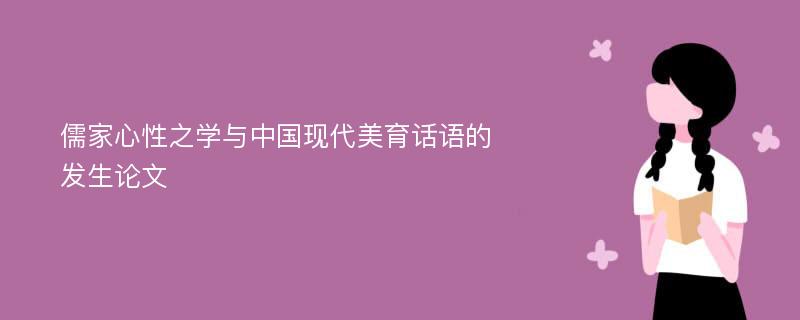
儒家心性之学与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 *
冯学勤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是西方美学引进的结果,这一西学脉络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现代美育先贤引进西方美学的动机、接受西方美学的路径、阐释西方美学的方式,皆受到儒家心性之学的决定性影响。换言之,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是儒家心性之学选择西方美学的结果,从而构成另一条至关重要的本土谱系脉络。研究者极易因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介入,而忽略中国现代美育与本国学术传统斩不断的历史连续性。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等人对于西方美学的接受动机及本土化阐释等问题,将使这条内在的学术谱系变得更加清晰,从而凸显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本土文化特色。
关键词: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儒家心性之学;学术谱系
1948年1月,朱光潜在为天津《益世报》所写的《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中称:“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惟其有普遍性,它是弥漫一时的风气,唯其有连续性,它是一线相承的传统。”[1]336而在发表于1961年7月《文艺报》上的《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中,朱光潜又称:“要考虑到文化历史持续性与对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问题,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一些西方美学中的优秀传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批判地继承我们自己的丰富悠久的传统,因为历史持续性的原则只能使我们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2]317据此,我们不禁要追问,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其“一线相承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其“历史持续性的原则”又体现在何处?
一、儒家心性之学:引进西方美学的本土文化根系
中国本无“美学”,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国人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舶来(途经日本这个“西方文化中转站”)的现代学科。在西方,“美学”学科的诞生,以18世纪哲学家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为标志,美学遂与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研究意志的伦理学并列分呈。换句话说,美学学科在西方的建立,是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分化的结果。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首先是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美学相接触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中国第一代美学家蔡元培、王国维提供了十分鲜明的例证。蔡元培称:“哲学者不过为心性之学……心性者,其体虽无形实,而或动于内,或发于外,有智力、有志意、有情感”[3]355,“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也”[3]357。王国维称:“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4]1,又以宋明理学为例称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4]2。无疑,心性之学成为对接西方美学及美育思想的根基。需要指出的是,“心性之学”与“理学”,指称虽可同一,却存在些许差别:“理学”的狭义专指宋明儒学中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对;若采其广义,也可专指宋明儒学,但会引起儒学内部“道统”之争,同时仍局限在“宋明”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于是,以孔孟-陆王为儒学正统、以程朱理学为“别子为宗”的牟宗三,提出以“心性之学”而非“理学”来涵盖宋明儒学,他称:“我们也可用‘心性之学’一名。这又由于程朱一系讲‘性即理’,著重‘性’;陆王一系讲‘心即理’,著重心,‘心性之学’恰好代表了这两系。”[5]6
评价是合作学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每次小组活动后,教师要及时进行总结评价,一方面通过小组汇报的形式使学生对知识形成统一的认识,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对各个学习小组的活动情况进行评价,如哪一组最团结协作,哪一组最有创新精神等,对小组成员也要进行适当合理的评价,比如谁在合作学习中最积极,谁能用正确的方式向其他学生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等,让学生尝到合作学习的甜头,享受学习的快乐。我们还可以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营造精神家园,让小组之间的竞争看得见。小组之间合作好便给他们贴上一颗星星,每个月评比一次,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该类研究主要是日本移民美国和拉美地区的相关研究。日本移民美国的研究集中在政策演变过程研究、史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在时间序列上学者主要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美国的日裔移民问题以及这一时期美中日三国的国际关系;日本移民拉美地区的研究则关注日本移民对拉美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研究,日本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融合研究等。
事实上,“心性之学”的称谓,宋以后儒学典籍中出现极多。如陈柏《苏山选集》载:“唯伊周既颓,孔孟复逝,经纶之业废,心性之学冺。”[6]实将心性之学追源于孔孟。当然,孔子少言心、性,孟子对心性之学的阐发更多,章潢《图书编》载:“千古发明心性之学,至孟子七篇尽之矣。论本源,则道性善是也。论工夫,则求放心是也。合而言之,则尽其心者,知其性是也。”[7]孟子立性善说之本源,又言心性存养之工夫,为后人开先河,故“至孟子七篇尽之矣”实将孟子视作心性之学的主要源头;再如周宗建《论语商》“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8],则强调内圣外王、知与行的贯通性;冯从吾《少墟集》称心性之学本源于孔孟,孔孟之后为异端(佛家)窃据其名长达千余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学,始恢复吾儒之旧,良足为千古一快。”[9]该论持“道统-异端”观念,大致勾勒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历史脉络,即导源在孔孟,汉唐五代为佛家心性论所遮蔽,自宋儒之后辟佛而出,于宋明时期成为显学。
及宋而理学之儒辈出,讲学授徒,几遍中国。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动机论,而演绎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为规范,得社会之信用。其后,政府又专以经义贡士,而尤注意于朱注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于是稍稍聪颖之士,皆自幼寝馈于是。达而在上,则益增其说于法令之中;穷而在下,则长书院,设私塾,掌学校教育之权。或为文士,编述小说剧本,行社会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苟有从师读书者,则无不以四书为读本。而其间一知半解互相传述之语,虽不识字者,亦皆耳熟而详之。虽间有苛细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议既成,则非至顽悍者,不敢显与之悖,或阴违之而阳从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绳人,盖自是始确立为普及之宗教焉。斯则宋明理学之功也。[3]545
可见,“心性之学”虽以宋明儒学为主体,却不同于“理学”那样局限在对特定历史时期儒家学术的阶段性指称,而具有一种强烈的学术史贯穿性,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牟宗三称:“中国文化……一方客观地开而为礼乐型教化系统,一方主观地开而为心性之学,综起来名曰内圣外王,成为道德政治的文化系统,而以仁为最高原则,为笼罩者,放亦曰仁的系统。”[10]210“心性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一道构成“仁的系统”的两大支柱。蒙培元称:“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他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始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11]1蔡方鹿称:“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理学之所以又被称为心性之学,是因为心性论在宋明理学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充分体现了新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特征。”[12]1
蔡元培这段话,充分揭示了儒家“心性之学”何以能变成意涵更加广泛的“心性文化传统”。其一,宋明儒学通过“遍及全国”的“讲学授徒”大规模传播儒学,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克苦躬行”儒家教义,遂成为士民表率、获得社会信用;其二,得到宋、明、清三代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教体制的支撑,心性之学方能上下灌注。正是由于学术与权力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教义,才能向社会最底层渗透,进而演变成至今绵延不绝的心性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发生,首先不能忽视儒家心性之学乃至本土心性文化传统的历史绵延性——这种绵延性一脉相承,它经宋、明、清士人直至现代美学家乃至现当代学人。这将决定“仁的系统”在遭遇“智的系统”时,首先在中国现代美学家那里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主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讨论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文化起点。
在这方面,三人既具有共性,又各现差异。所谓共性,是指他们作为同代人,皆受清末汉、宋两大儒学之学统的共同滋养。所谓“汉学”,又称乾嘉汉学或朴学,是指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鼎盛、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汉儒为先河的考据训诂之学;所谓宋学,即指宋明儒学,构成儒家哲学——心性之学的主要内容。这两大学统在清代的关系比较复杂。单纯从学术史角度看,汉学的兴起,是对宋学的反动。反动的原因在于,清代汉学家认为宋明儒学有“倚虚不征诸实”的毛病,他们认为,宋明儒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主要是一种“阐发义理”的哲学解释,带有较强的随意性,且掺杂佛道等“异端”思想,对儒家思想的纯粹和正统构成危害。因此,“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义。”[16]259真正能代表清代整体学术特色的,正是乾嘉汉学。然而,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开始走向衰退,直至道、咸年间始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种情势下,一些士人认为,若仍埋头于故纸堆中、汲汲于经籍考证的“小学”,不问世事,放其用心,无以挽救日渐危亡的国运。于是,以嘉、道年间为起始,宋学阵营的士人开始攻击汉学,汉学阵营的士人开始自我反思,因此,具有强烈社会实践指向的宋学得以复兴,遂开清代儒学汉、宋调和的局面。当然,一些激进者更是指责汉学使士人心力陷溺小学考据之中,无以应对时事,而加以吐弃。因此在“调和”的大势下,仍存在激烈的争辩。正如冯友兰所说,“从18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16]259
8月30日,中国恩菲承担设计的云锡文山锌铟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万t锌、60 t铟冶炼技改项目(以下简称“云锡文山锌铟冶炼技改项目”)投产仪式在云南文山举行。中国恩菲董事长陆志方、副总经理刘诚应邀出席仪式。陆志方与项目相关领导共同按下投产启动按扭,项目开始正式投料投产。
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中国思想儒家以外,未尝没有旁的学派。如战国的老墨,六朝、唐的道佛,近代的耶回……我们批评一个学派,一面要看他的继续性,一面要看他的普遍性。自孔子以来,直至于今,继续不断的,还是儒家势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还是儒家信仰最深。所以我们可以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15]4956-4957
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与儒家心性之学以及清末儒学传统的共性,决定了他们最终皆成为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奠基者;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在接受西方美学时路径的差异性,其自身美育话语产生时内涵的差异性。
还令陈颐磊惊奇的是,才隔一天,他的属下就把孔家庙布置成了一个华丽的灵堂。大门眉槛上盘着黑纱,黑纱中间结了一个巨大的花球,进得门,甬道两侧密密排着花圈,顺着甬道,远远看见大成殿上挂着一个墨汁未干巨大“奠”字。
心性之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是什么?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四人曾合发《中国文化与世界》(1958)宣言,称:“然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明有一贯之共同认识。共认此道德实践之行与觉悟之知,二者系相依互进;共认一切对外在世界之道德实践行为,唯依于吾人之欲自尽此内在之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己的要求;共认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13]78据此,可对“心性之学”的特点概括如下:其一,具有泛道德化的整体性特点,树立卓绝超凡的道德主体,融认知、审美主体于其中。其二,具有人性本善的人文主义特点,强调心性动机的纯粹性,认为动机纯粹是道德实践的合法性基础和正义性前提。其三,为了修治纯粹动机,树立格除私利物欲、存心养性的工夫论,具有极强的内向性特点。其四,强调内心修治与社会治理、知与行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高度的实践性特点。其五,以天地合德、天人相参为最高境界,以圣贤为最高的人格目标,具有强烈的内在超越性特点。
中国偌大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如有文化,我们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
二、“移花接木”:儒家心性之学与中国现代 美育话语的发生
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被学界公认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源三大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奠基人。需要指出的是,他们首先是上承清末儒学传统的最后一代“士人”。这是由他们在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所受的系统的儒学教育决定的,他们皆能接续清代儒学的学术谱牒,进而脉承儒家绵延两千多年的心性文化传统。由于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对心性之学最基本内容的掌握,就已达到较高的程度:王国维15岁中秀才,梁启超16岁中举人,蔡元培走得更远,25岁中了进士。这就奠定了儒家心性之学在其一生知识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当然,科举考试代表的是封建官学,内容较为狭窄,思想受到约束,既不能充分反映他们丰富的传统知识储备,也无法呈现清代儒学的基本面貌。而与科举-官学相对的是他们的“私学”,亦即不受功名束缚、根据各自兴趣自由寻求得来的学问,更能体现他们与清末儒学传统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心性之学”不仅代表中国哲学的特点,更是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在该宣言中,当代新儒家明确提出“心性之学”为“中华文化之神髓所在”[13]81,“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14]81。蒙培元亦指出,心性论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14]36在他们那里,“心性之学”不只是代表特定时期的儒学,也不只是代表儒学,甚至不止于代表中国哲学和中国学术,更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特征。关于这点,梁启超在《儒家哲学》(1927)中称:
在这种复杂背景下,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三人与清末特定学统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梁启超在学术谱牒上远较蔡元培、王国维显赫,他是清末汉、宋两派大师的“再传弟子”。汉学方面,经学海堂陈梅坪而接清代汉学大儒陈澧;宋学方面,经长兴学堂康有为而接清代宋学大儒朱次琦。[15]4274然而,年轻的梁启超远不像他两个主张“汉宋调和”、为学“汉宋兼采”的师祖那般平和,曾一度将他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历时五年、较为系统的乾嘉汉学训练,以“无用旧学”之名加以攻击,转而接受康有为指导他的“为学方针”,即宋明心性之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成为他“全部思想的主要骨干”[17]21。与梁启超在学问路径上的差异最为明显,王国维可谓“始于汉学,终于汉学。他的家学中有金石考据的传统,在中秀才后不久便无意于科举,而‘专力于考据之学’”[18]6,这就是“始”;而所谓“终”,则指他在辛亥革命后,弃西洋哲学、美学及文学研究而去,终身从事经史考据之学。蔡元培与王国维、梁启超相比,在清末汉、宋两大学统的关系上持论最为中正,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大破大立”而流于善变,也不像王国维那样心怀故旧而趋保守,在其知识结构中,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也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显得比较均衡。
梁启超充分强调了儒家哲学的文化代表性,以及儒家文化信仰的大众普及程度。不仅如此,他还坚称儒家内圣-心性之学是“绝对不含时代性的”[15]4957,即超时代的,表达了对这种传统的坚定信念。而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1912)中称:
王国维受乾嘉汉学影响最深,并不像梁启超那样高度推崇儒家心性之学,也未曾像蔡元培那样系统整理过儒家心性之学。他对西方哲学乃至美学的引进动机,更出自于建立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学术体系,而非首先由“外向之思”——社会、政治、道德等动机直接引起的。对他而言,“美术”(美学及艺术)独立首先是与“哲学”独立捆绑在一起:“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4]3在王国维看来,美学(包括美的艺术)与哲学一样,以“真理”明“志”,清晰表达了其美学引进是出于建立纯粹学问的动机。他这种判断显然是在接触西方“智的系统”后,产生的本土主流思想中少有的“求真之志”。而与宋明理学相比,乾嘉汉学更接近“纯粹的学问”,多怀有“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之志。章太炎称乾嘉学术为“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慎密矣”[19]370,胡适则称赞:“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朴学,确有科学精神。”[20]285晚年立论持平的梁启超,亦称许清代学者“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赞赏乾嘉汉学诸大师“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15]3086王国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独立论和美育自律论的首倡者,就此而言并非偶然——正是乾嘉汉学精神与西方爱智传统相契合的结果。然而,要向国人说明“为学问而学问”的意义,讲清楚美育的价值,就必须回到“仁的系统”,借心性之学在内心修养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传统逻辑,来阐明这些活动的实际功能。王国维的“无用之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乎?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4]95在他看来,“无用之用”之所以胜于“有用之用”,正在于“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4]17亦即通过美育可达到对“私利物欲”的自然消除,实现修身治国的延伸效果,深深契合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精神。
蔡元培比王国维所受心性之学影响要深,在他那里最清晰地表现出儒家心性之学对接西方美学的思想轨迹。蔡元培在成为中国第一代美学家之前,首先是家乡心性之学传统的自豪者[3]58-59、科举考试制度的成功者——他后来通过殿试进入翰林院,走上封建时代读书人最引以为荣的一条仕途进路。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他开始放眼于西学;戊戌变法之前,他受谭嗣同、严复的影响开始研究哲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冷眼旁观”的结论是:戊戌派太急于夺权,同时缺乏“变法”的国民基础,而他自己则从北京回到家乡绍兴,开始投身教育,从事“培养基础”的事业。1900年,蔡元培在《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中称:“夫家国之盛衰,以人事为消长,人事之文野,以心术为进退,心术之粹驳,以外物之印象为隐括。”[3]288这段话明确透露出他后来重视美学和美育的原因: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在人心中,而人心是否纯粹,则归根结底在如何对待外物,“隐括”即矫正邪曲的工具。这一表述正是由儒家心性之学最基本、最凝练的教义演变而来,这一教义即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八条目”。在儒家看来,最终指向的是“平天下”,即国家的繁盛;中间环节是“正心”,即修治纯粹的动机;发生的起点是“格物”,即对待外物的态度。一如王国维,蔡元培所认识到的:美育正能起到道德修治难以企及的去除私利物欲(格物)、矫正人心、涵养心性的作用。因此,蔡元培从德国回国后屡次说:“涵养德性,莫若提倡美育。”[21]678不仅如此,他还将康德的趣味判断第一契机阐释为“超脱”,就是指超脱私利物欲;对其余三个契机,即“普遍”“有则”“必然”及美学范畴“崇高”的阐释,也完全建基于儒家心性之学。[22]340最后,他的“美育代宗教”说,更是秉持了本土心性之学强烈的内在超越精神。
与王国维、蔡元培相比,梁启超更加表现出一个儒家心性之学的“信徒”特色,而他的美学思想也最具独特性。他并不像王国维、蔡元培那样,具有西方美学的学习经历,其美育思想也谈不上受西方美学多大影响。然而,他却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影响广泛的“趣味主义”和“趣味教育”。学界在讨论梁启超“趣味主义”来源时,往往以为其来自西方美学,然而,它真的是从康德那“趣味判断”(鉴赏判断)中来吗?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是因其清末学术谱系,从儒家心性之学发展而来。尽管康德的“趣味判断”因汉译而与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有着范畴上的对应性,然而,在梁启超的全部文献中并无二者相关影响的证据。他在20世纪初年对康德哲学的介绍,依靠的是编译的日文文献,杂以对心学佛学的阐释,何止“不能信达”[15]1055,更是“剽窃灭裂”[4]21,且并未涉及康德美学。[15]1054-1065相反,他从19世纪90年代初师从康有为到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趣味主义”,却有着一条极为清晰、源自儒家心性之学的发生发展脉络。他“趣味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来自这一谱系,而其理论神髓——“无所为而为”,更是源自宋明心性之学的老命题。没有西学谱系的梁启超,与王国维、蔡元培相比走的是一条速度缓慢的“单轨”;也正是这条“单轨”,最为鲜明的呈现出儒家心性之学在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生成过程中的本土学术脉络。
大数据中心数据库至下而上进行划分为物理层、逻辑层以及逻辑字库层。逻辑字库包含了基础类、参考系、专业类以及管理类等数据;逻辑层主要用来描述国土资源数据的专题图件,细分包括防灾管理数据、地政管理数据以及矿政管理数据;物理层主要用来描述另外两层的关键要素,数据逻辑设计如图3所示:
在共性方面,王、梁、蔡三人皆受儒家心性之学的滋养,皆秉持“动机纯粹”是一切改良、革命、改革等民族复兴事业得以成功的前提性认识,皆怀有内圣(心性修养)与外王(社会实践)之间的贯通性思维,因此,皆强调审美活动具有正人心术、存养德性、健全人性的功能,同时视美育和艺术教育为改造国民性、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这种来自本土学术和文化传统的共性,一直到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那里,仍表现得十分清晰。1932年,虽身处异国但仍心怀国难的朱光潜,在其著名的《谈美》中开篇即称自己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抱有旧时代的信仰”;这种信仰使其“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而要“洗刷人心”,就必须“要从‘怡情养性’做起”,“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23]5-6朱光潜“旧时代的信仰”,正与其前辈一样,是对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的信仰。尽管朱光潜对西方美学和美育思想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也远远超过其前辈,然而他选择、接受乃至改造西方美学的思想文化基础,仍在儒家的心性之学。他在晚年提出并反复强调的“移花接木”[2]533说,更是明证。所谓“移花接木”,正是移西方美学乃至西方思想之花,来接儒家心性之学的木。此外,一个鲜明例证是,受梁启超对“无所为而为”阐发的影响,康德趣味判断的“第一契机”——“无功利的静观”,被朱光潜译成“无所为而为的观赏”,从而为这个决定中国现代美学及美育话语诞生的第一西学命题,注入了来自儒家心性之学的本土文化基因。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说,正代表了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最清晰的发生原则,即“儒家心性之学选择西方美学的结果”。
三、“淬沥固有”与“采补本无”:相反 相成的“建体立极”之路
中国现代美学家为何要“移西方美学的花,接心性之学的木”呢?为什么儒家心性之学要通过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去“选择”西方美学?首先当然是因为“没有”,即美学在中国是“本无之学”。蒙培元指出,儒家心性之学的特点在于“‘道德主体’或‘德性主体’的挺立”,而“缺点在于知性主体的萎缩”,要改变这个缺点,“就要自觉地实行自我分化”,即分化为“道德主体、审美主体、知性主体、政治主体、社会主体等等,而又不失其道德之体”。[24]16我们在中国现代美学家身上,看到的正是一条“分化”道路,即从对道德主体的必要性出发,最终为“美”建体立极,同时又“不失其道德之体”。在这方面,蔡元培和梁启超恰恰构成一个“相反相成”的绝佳案例。所谓“相反”,是指蔡元培走了一条“采补本无之学而新之”的道路,梁启超走的则是“淬沥固有之学而新之”的道路。所谓“相成”,一方面是指“采补本无”使“淬沥固有”的结果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淬沥固有”则使“采补本无”的本土渊源得以更加鲜明的呈现。
先看蔡元培。蔡元培最先接触到西方哲学乃及西方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此时的西方美学尚未成为他关注的重点,相反,为其所重的是与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关系更紧密的伦理学。1902年,他编写了《中等伦理学》。在本书中,他通过日本文献,得知西方伦理学有两派。一是“直觉说”,二是“经验说”。其内容曰:“直觉说便于提醒责备,而恐无以引名教乐地之兴味;经验说便于诱导指示,而恐无以障放利自营之趋势。”[3]168这里所谓的“直觉说”和“经验说”,就是他在十年后成书的《中国伦理学史》中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动机论”和“功利论”。所谓“直觉说”或“动机论”,是指道德行为或“善”,是从人的良知或纯粹的道德动机出发,即基于人的天性也即先天的人性;而所谓“经验说”或“功利论”,则指道德行为或“善”,是从经验(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因功利关系而形成的契约出发的,是属于后天的。然而,他认为这两个极端都有问题。功利论的问题是“无以障放利自营之趋势”,动机论的问题是“无以引名教乐地之兴味”。所谓“无以引名教乐地之兴味”,是指单纯的道德修治缺乏兴味,因此易流于陈腐的教条——这句话他是有所指的,即指向宋明心性之学强调对道德动机的修治而缺乏“兴味”,缺乏兴味自然易流于陈腐教条。为何缺乏兴味?正是因为在宋明心性之学未能“建体立极”的审美被“消融”在道德主体之中,其“必要性”得不到彰显,从而使心性修治更依赖于以“天理之公”克制“人欲之私”的陈腐教条,最终流于不近人情的“存天理、灭人欲”!
需要指出的是,这绝不仅仅停留在一个道德修治“有没有趣”的问题上。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宋明心性之学进行反思时称,无论程朱陆王,皆是“极端动机论”,“势不免自杀其竞争生存之力”。[22]74这句话直指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国弱民穷、工商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语境中,若要大力发展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国家实力,迅速发展工商业,就必须提倡“实利教育”,这点恰恰要大力刺激人的利益诉求、充分肯定人的功利动机才能实现。因此,宋明心性之学格除利欲(尽管只是私利物欲)、追求道德动机纯粹性的基本教义与此相悖,并日益流于陈腐教条。然而,能单纯鼓吹功利主义吗?能将道德原则仅仅安置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之上吗?当道德主体仅仅因社会契约关系而形成时,道德主体就已经被削平了,道德行为内在、自主的驱动力也就丧失了,而在法律远不健全、契约精神本就稀薄的中国国情下,又何以能“障放利自营之趋势”?更何况,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已经认识到,正是服膺“动机论”的宋明儒们克苦躬行、带头表率,才使得一家之学普及人人而成就了本土文化传统,难道要抛弃卓绝超凡的道德主体,进而抛弃中华文化传统的“神髓”吗?这个矛盾才是蔡元培选择西方美学的根本原因。他的解决方案是,应将彰显审美价值和意义、自然消除“私利物欲”的西方近现代美学,与要求动机纯粹的儒家伦理学实现对接。引进西方美学的意义,首先是就这样的功效而言的:通过彰显“名教乐地之兴味”,补救宋明儒学的极端动机论所生之流弊,进而达到“障放利自营之趋势”。正是出自培养道德基础、保留动机纯粹性这一基本诉求,深受儒家心性文化传统影响的蔡元培才选择了西方美学和美育。“选择”之后,原本“消融”在道德主体中的“美”和美育,就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契机,上抵“人性之健全”的更高价值;反之,中国心性文化传统的神髓——“道德之体”,也流溢在其美育话语之中。
最近,一颗重达1404.49克拉(约0.5斤)的蓝宝石被斯里兰卡宝石鉴定机构认定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的蓝宝石。这颗宝石估计最少1亿美元,约6.6亿人民币。它目前的拥有者并不想透露当初花了多少钱买下它。它已被取名为“亚当之星”,因为斯里兰卡人认为《圣经》里的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后在斯里兰卡生活过。
与蔡元培相比,并没有“选择”西方美学的梁启超,彰显的是一条“淬沥固有之学而新之”的独特路线。儒家心性之学并没有为“美”建体立极,因其有“以美辅德”之功效而有“必要”。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产生,正是这种“必要性”最为充分的体现。何以如此?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最初萌芽,要追溯到19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师从康有为之时。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留下一个问题,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真正发端。康有为称:“学者既能慎独,则清虚中平,德性渐融,但苦强制力索之功,无优游泮泱之趣。夫行道当用勉强,而入德宜阶自然。”[25]343-344这句话是康有为在“慎独”和“主静出倪”这两个条目间设置的过渡句。“慎独”是心性之学工夫论的一种,代表的是“省察克治”,强调的是“狠斗私心一闪念”,具有“强制力索”和“勉强”等情感色彩,此即蔡元培所谓“无以引名教乐地之兴味”;而“主静出倪”是另一种,它代表的是“存心养性”的方法,内含“悠游泮泱之趣”。在康有为看来,道德修治不能仅依赖“省察克治”的消极方法,而要依靠更加自然、主动的“存养”法。“主静出倪”的意思是,通过静坐养心,格除私利物欲,养出道德端倪。然而,康有为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主静出倪”内含“悠游泮泱之趣”。如果在静坐养心过程中仅仅收束意念,停止思考,以此隔绝私利物欲的意念,那么乐趣何来?
台风肆虐,险情不断,各地告急,多方受困,往往让一些不实信息有了“市场”,甚至谣言四起。如果准确正面的信息不能占领信息传播的高地,负面影响将不可估量,也将影响整个抗台救灾和社会的稳定。温州市对防台信息发布工作高度重视,防御工作各个阶段都主动向媒体发布台风动态、汛情信息和工作部署情况。10月8日,市政府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温州防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并就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几个话题答复各大媒体。在整个防台抢险救灾过程中,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多次上媒体、进直播间、到一线发布准确的信息,将不实信息和不良舆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了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的有序有力开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这个问题被梁启超紧紧抓住。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将静坐养心法分为“敛其心”与“纵其心”两个步骤。所谓“敛其心”,是从功利考量、私利物欲中要“收其放心”,这一步本无乐趣可言,甚至还存在强制性。真正的乐趣产生于第二步——“纵其心”。他所谓的“纵其心”又分两个方法:一个叫“遍观天地之大”,即通过融审美静观与道德直观于一体,扩大心胸境界,与天地参;另一个方法叫“虚构万死一生之境”,即通过虚构的情境,来砥砺意志。[15]107“纵其心”这两个借重审美的方法,正是对儒家心性之学的工夫论——静坐养心法的创造性发挥。梁启超后来在《德育鉴》(1905)中,干脆继承儒家心性存养“主敬”“主静”二法,增添了一个本不存在的“主观”法,并称“主观”是从“主静”中开出,也就是将“敛其心”视作“纵其心”的第一步。他的美学思想正是沿此思路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梁启超为什么会高度重视审美方法,为什么它没有被“消融”?这与蔡元培可谓同中有异。所谓“同”,是指梁启超、蔡元培皆认定,审美对于纯粹心性修治的必要性,皆受儒家心性之学影响;所谓“异”,是指梁启超因未接触过西方美学,因此他对审美的高度重视,是出自一种极为强烈、十分直接、全为自发的必要性认识,而非如王国维、蔡元培那样直接受西学启迪。这种认识就是,审美是“新民”——国民性改造的有力武器;而“新民”的第一要义正在于“新民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然而,该篇同样是从他的“纵其心”法中开出,即源自儒家心性之学。何以会如此?因为“小说”正是通过“虚构情境”,以获得趣味的最有效手段!正因为对审美必要性的持续重视,梁启超于20世纪20年代即提出“趣味主义”,最终为“趣味”建体立极。但研究者应该注意,他讲的“趣味”,并不是康德注重知性区分的“趣味判断”(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亦即并不是一个纯粹美学概念,而是融道德与审美于一体、内含“责任心”(发自省察克治)和“兴味”(发自存心养性)、以“纵其心”为发生机制、以“遍观”与“虚构”为基本源泉、以标志动机纯粹性的“无所为而为”为思想神髓的“趣味”。因此,他为美“建体立极”,并不像王国维、蔡元培那样,有着一条来自西方知识论的维度,而是对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持续淬沥的结果。
无论是“采补本无”,还是“淬沥固有”,其出发点皆是儒家心性之学,最终皆高度重视美育。一方面,儒家心性之学为中国现代美学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他们胸怀拯救民族于危难、实现国家复兴的强烈目的。对他们来说,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从矫正人心、改造国民性入手,而美育正是实现人心净化、人性向善的有力手段,这正是来自本土“仁的系统”的“历史持续性的原则”,亦即由内心修治转向社会实践。另一方面,由西方“智的系统”所开出的美学,可以弥补本土文化传统的思想盲点,使儒家心性之学具有高度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的道德主体实现自我分化,这种自我分化是保证人的不同能力、活动得以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的健全。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在改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生成中国现代美育话语。这种改造最典型的案例,充分反映在对康德鉴赏判断第一契机的本土化阐释上。面对这个从认识论传统出发、侧重区分性意涵的“第一契机”,王国维将之阐释为“无用之用”,蔡元培将之阐释为“超脱”,朱光潜将之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无论是哪种阐释,康德的第一契机都已被注入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本土基因,即将一个来自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区分性命题,改造为养成纯粹动机、摆脱私利物欲的美育功能论,从而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品格;另一方面,中国心性文化传统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本被消融的审美因素也被激活。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先秦礼乐思想和孔子的审美精神,在梁启超这样的美学家那里受到了不约而同的重视。就此而言,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美学”的建立,从而构成了整个中国美学研究的思想和学术原点。
四、结语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作为儒家心性之学选择西方美学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要借上溯我们的学术原点、重返我们的文化之根,来树立我们的学术自主性,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在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等中国现代美学家那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从未丧失过。且不论像梁启超这样与儒家心性之学具有直接谱系关联的第一代美学家,甚至到朱光潜仍然坚称:“在以往几千年中我们却也有一种中心信仰,而对它也怀有一种虔敬。”[26]493这种中心信仰是什么?“中国中心思想无疑地是儒家,而儒家的渊源在《论语》《孟子》和‘五经’。”[1]118就此而言,他们希望借审美来“正人心”,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决不可将之视为“迂远”,更不只是一个“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儒家心性之学的开山者孟子,也曾被人目之为“迂远”:“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集注》)之所以“迂远”,是因为这种指责来自其对立面——没有什么比黄金白刃、法力诈术更能带来短期效果了。然而,“黄金白刃、法力诈术”这些东西坏人心术,侵蚀一个健康社会、强盛民族所必不可少的信念基础。从根本上说,中国现代美学是建立在对本土心性文化传统的坚定信念上,其中则内含着悠久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而非仅是去除情感内核、切断信念关联的一个“思路”或一种“逻辑”。因此,在儒家心性之学所依赖的封建皇权体制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这种信念仍将绵延不绝,中国现代美育正是其强壮产儿。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下)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5]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陈柏.苏山选集[M].明万历刻本,卷七.
[7]章潢.图书编[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五.
[8]周宗建.论语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
[9]冯从吾.少墟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语录.
[10]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11]蒙培元.中国心性论[M].台北:学生书局,1990.
[12]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9.
[13]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4]蒙培元.心灵与境界——访蒙培元研究员[J].哲学动态,1995,(3).
[1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1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贺麟.当代中国哲学[M].南京:胜利出版社,1945.
[18]王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 (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0]胡适.胡适文存(第1卷) [M].长沙:黄山书社,1996.
[2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4]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Discourse
FENG Xue-qin
(Art Education Departmen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As the result about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esthetics, Chinesemodern aesthetic-education discourse has its owndomestic resourse, whichis ConfucianPhilosophy of Mind. The acceptingmode, introduction path and explanation content of western aesthetics are all influenced by Confucianphilosophy of mind. In another word, the later is decisive fact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ormer. But for the strong influenceof the former,weare so easy to lose sight about this factor. Accordingly, the study about modern Chineseaestheticians such as Wang Guo-wei, Liang Qi-chao and Cai Yuan-pei would show the native genealogyof Chinesemodern aesthetic.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Education Discours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Mind; Genealogy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中图分类号: J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104( 2019) 01-0048-07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6ZDA110)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冯学勤( 1979-),男,汉,浙江海盐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美育理论,动画艺术理论。
(责任编辑:楚小庆)
标签:中国现代美育话语论文; 儒家心性之学论文; 学术谱系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