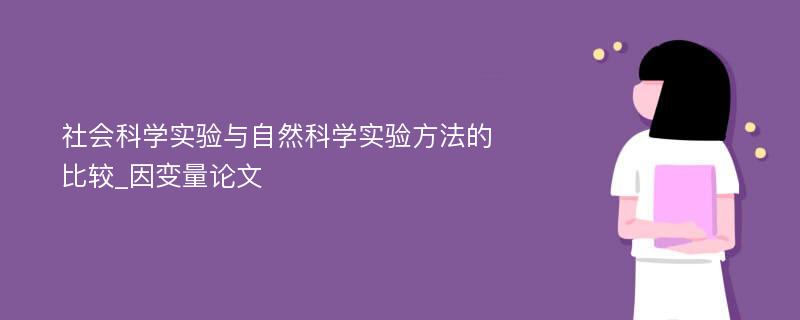
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科学实验论文,自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验是科学的基石,没有实验就没有真正的科学。在自然现象的研究领域中,实验作为一种经验认识方法,是自然科学最直接、最重要的认识基础,自然科学的每一项理论的发现或检验无不借助于科学实验。在社会研究领域,尽管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复杂性,实验方法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研究人文与社会现象的主要手段,但是,科学实验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却是社会研究的精髓,它集中体现在社会调查研究、社会实验等经验研究方法之中。
实验在科学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历来是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关注点。关于实验的要素、结构、程序、设计原则、实验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实验与理论之间关系等研究,都是实验方法论或实验哲学的主要成果。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实验或社会实验相对独立的研究上,而对于这两种实验方法,以及其背后的原则和研究逻辑等方法论问题的对比研究则比较少。本文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自然科学实验和社会实验作对比分析,探讨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深层衔接点和无法通约之处,以加深对社会实验及其方法论的理解。
一
所谓社会实验,就是在一定的人工设计条件下,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人为地改变某些社会因素或控制某些社会条件,来考察某些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研究的四种基本方式,即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社会实验中,社会实验是一种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
一、本质上讲,社会实验是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移植和引入,与自然科学实验有着一脉相承的方法论前提。
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论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后期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提出的实验法。他认为,只有通过感觉验证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而感觉的验证不仅是感官的自然感觉,更重要的是用仪器进行的科学实验,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真理的真正道路。[1]到16世纪,弗兰西斯·培根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观察和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发现一切现象的原因和规律,并制定出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马克思称他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近代自然科学正是依靠着观察和实验,以及科学家的逻辑思维和想像力,才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科学。
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和启发,一些社会哲学家和思想家开始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领域,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法则来建造社会科学大厦,出现了“社会物理学”、“政治算数”、“社会生物学”等新的社会学说。[2]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命题,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研究社会现象和研究自然现象一样,也应该采取观察、实验和比较等实证方法。继孔德之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论,他把社会现象的客观性与整体性联系起来,认为社会现象在整体上是客观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等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不以社会活动的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稳定性和规律性,因此,对社会现象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解释。
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实证精神的引入是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开端,各门社会科学正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下逐步从思辨的社会哲学中独立出来。社会实验体现了这种实证精神,是自然科学的实验传统在社会研究中的传承和发展,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可以说,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实验与社会实验的方法论衔接点。
二、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看,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基本要素、结构、内容和研究逻辑是一致的。
首先,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活动,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都是由实验主体、实验条件和实验客体三个基本要素组合的“刺激—反应”过程。一般地讲,实验主体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条件,在排除无关的干扰因素情况下,对实验客体实施刺激作用,并观察和记录实验客体的反应,从而确定或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在这种认识结构中,两种实验都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通常是受实验主体控制的变量,因变量是由自变量决定的变量,如在自然科学的气体实验中,温度被作为自变量,体积或压强被作为因变量;在检验工作环境与生产效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社会实验中,工厂的照明条件是自变量,工人的生产效率是因变量。研究人员正是通过操纵和控制自变量的变化,来观察和记录因变量的变化,从而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二是事前测验与事后测验。事前测验就是在实施自变量刺激之前对因变量所作的测验,改变自变量之后对因变量的测验则是事后测验。三是比较,包括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是对研究客体在时间纵向上的考察,即把事后测验结果与事前测验结果对比,从而确定因变量受自变量改变这一刺激所产生的变化。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科学实验,特别是社会实验一般还进行横向的比较,即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中引入自变量的刺激,而对照组则保持原来的环境条件,并分别测验因变量的状态,然后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测验结果进行对比,以求得由自变量刺激所导致的净效应。对照组的设置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一般来说,对照组设置越多,实验结果的精确性也就越高。
最后,在实验的研究逻辑上,社会实验同样遵循自然科学“理论先行”的方法论原则。经验与理论或者实验与理论哪个在先,不仅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更是一个科学发展的历史命题。近代科学属于经验科学的阶段,其研究逻辑主要是实验—理论—实验的模式。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都恰当地概括和总结了经验科学的研究逻辑,强调观察和实验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明确指出实验决定理论,即实验在先,理论在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由经验阶段进入理论阶段,其研究逻辑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理论成为实验的先导,即理论—实验—理论。批判理性主义、历史学派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理论的支配地位。如波普尔坚持理论先于观察,认为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为什么观察、观察什么和如何观察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同时观察中还必须有理解,而理解也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3]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主张观察不是中性的,而是渗透着理论,不同理论的渗透可能导致不同的实验结果。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夏佩尔和劳丹等人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概念,强调背景理论对于科学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
应该说,实验和理论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复杂的关系,片面强调实验或理论都是错误的。强调“理论先行”的原则,并不违背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原则,也不是贬低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在科学认识的本原上,科学理论来自观察和实验,实验在先,理论在后。但是,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特别是在科学发展到理论阶段之后,科学经验的获得就必须在已有理论的引导下进行,即“理论在先,实验在后”,以避免盲目性。事实上,那些“在先”指导着实验的理论,并非是凭空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基础之上,被前面的实验检验过的理论。与自然科学实验相比,社会实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社会和人,对社会现象的经验认识更是浸染了概念、理论框架,负载着社会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个人情感和阶级利益等等社会因素,因此,在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中,也一样要强调“理论先行”的方法论原则。按照“理论先行”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实验的研究逻辑是:以问题为起点,根据已有的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再制定观察指标、实验变量,并通过实验观察,检验研究假设或概括出新的命题。
二
尽管社会实验以自然科学实验为模板,引入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研究逻辑,但它毕竟有着与自然科学实验不同的实验客体——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不仅具有可以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进行观察、测量的客观性,而且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差异。社会实验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实验有以下不可通约之处:
一、在实验的主、客体关系上,自然科学实验是人与自然物的单向作用关系,而社会实验则是人与人双向交流的社会互动。当社会实验的对象处于实验环境或得知自己在被观察和研究时,其行为和态度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客观性,即发生所谓的“霍桑效应”。[4]
“霍桑效应”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G.E.Mayo)主持的著名的社会实验——霍桑实验中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西部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同进行了一项旨在研究工人的生产效率是否与工作环境相关的社会实验。在实验中,根据“照明”等工作环境与“效率”相关的假设,把装配电器的工人分成两个小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工作。“对照组”的照明条件保持不变,而改变“实验组”的照明条件。实验结果表明,不仅增加照明度的“实验组”生产量提高了,而且没有增加照明度的“对照组”生产量也提高了。然而,在随后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实验组”的生产效率随着环境的任何改变而都有所提高,甚至那些明显不利于生产的环境变化也能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经过认真的分析,梅奥、迪克逊、罗特利斯伯格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得到一个结论:导致实验组生产效率提高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是实验活动本身,是研究人员的出现使得实验组的工人感到自己是特殊的,他们开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协作,不敢怠慢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些心理因素,而不是研究人员所控制的环境条件,引起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实验人员先入为主的预期心理,也会导致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现象,而不是真实的现象,从而使实验结果发生偏差,这种现象被称为“期望效应”。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Rosenthal)在一所中学对18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预测他们未来成就的心理测试,并告诉老师们,哪些学生获得了高分。实际上,这些学生是他随机挑选出来的,但老师们被引导而相信这些孩子是高分获得者。一年之后,进行智商测试,结果发现那些被随机贴上“高分”标签的学生确实比其他学生有更显著的进步。这表明老师的期望和学生本人接受的心理暗示共同影响了实验结果。
在另一项名为“迷宫学习”(Maze-learning)的实验中,罗森塔尔告诉他的学生要注意聪明老鼠与愚钝老鼠的行为差别。虽然聪明老鼠和愚钝老鼠的标签是他随意贴的,但学生的实验记录却表明“聪明老鼠”比“愚钝老鼠”表现更好。显然,标签所承载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实验观察,进而影响了实验结果。[5]
自然科学实验和社会实验都存在实验人员预期心理的影响,但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实验中的“期望效应”更容易控制和排除。这是因为:第一,自然科学实验的对象是客观的自然物,可以进行重复性实验检验;第二,检验和评价的标准是相对客观和单一的;第三,现代自然科学已经从经验科学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阶段,它以相对完备的背景理论作指导,遵循着严密的演绎—归纳逻辑和假设检验程序;社会研究则不同,研究对象兼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而且还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和评价标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和预期心理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明显,因此,社会实验中的“期望效应”不能被忽视。
三、社会实验受社会环境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与限制。为了克服社会实验中的“霍桑效应”和“期望效应”,很多社会实验设计为“单盲实验”或“双盲实验”,即不让实验对象觉察到自己正在参与一项实验,或者同时让实验人员不了解实验的真实目的或不知道哪些是实验的真正对象,但这样却可能引发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朗(Stanley Milgram)主持的“服从与响应度”实验。
米尔格朗设计了这样一人实验:把自愿参加实验的人,两人为一组,由抽签决定一个作“教师”,另一个作“学生”,告诉他们,实验的目的是要了解,体罚对学习效果有什么影响。在实验中,“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腕上通上电极,“教师”被要求在“学生”答错问题时,按“电击”开关惩罚“学生”。随着“学生”答错次数增加,电击强度逐渐提高。“学生”开始尖叫着哀求停止实验,但实验主持人要求“教师”继续提问和惩罚。到此时,扮演“教师”的40人中,没有人停止实验,当电压加大到令“学生”大声嘶叫和跺脚踢墙,“教师”开始紧张不安起来,有的害怕,有的气愤。但主持人仍然要求“教师”继续实验。此时,有5名“教师”拒绝了继续实验。其余“教师”询问主持人,如果电击对学生身体造成了伤害,由谁来承担责任?当被告知责任全部由研究人员承担时,他们都按照实验要求,继续加大电压,直到实验的最高电压。
事实上,这是一个“单盲实验”,电击是假的,“学生”是实验人员装扮的,“教师”才是这个实验的真正研究对象,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尽管他们以为伤害了,实验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他们对命令的服从程度。[6]
这个实验引发了许多伦理道德问题,比如,隐瞒实验的真实目的是不是欺骗行为?研究人员有权让参与实验的人的精神如此紧张吗?在实验中,哪些做法是允许的,而哪些是该禁止的?为了科学研究而让研究对象付出代价是合理的吗?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无生命的自然物,可以在实验室创造出完全封闭的人工环境,并在严格的受控条件下产生数据,来发现或检验科学理论,因而较少涉及道德、伦理、法律等问题。而社会实验的对象是人,实验室无法创造出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封闭环境,实验刺激必须以不伤害个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为限度。例如,研究拥挤程度与侵犯行为之间关系,则需要把很多人禁闭在一个狭小环境中,但这样的禁闭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把无辜的实验对象置于危险中也是不道德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还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社会后果,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说:“对纽约市断水供应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人们会不会狂暴起来或者变得无情呢?他们是否会试图组织一次革命来反对市政府?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会建议进行这样一个实验,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人民不允许社会科学家拿他们的必需品来开玩笑。”[7]
四、社会实验的结果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而无法正确地反映现实过程。在实验过程中,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导致实验结果失真。另外,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对象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实验结果。
由于上述种种局限,社会实验远不具有自然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和应用程度。从总体水平上来看,社会实验还只是社会研究中的次要的、辅助性的方法。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对《美国社会学评论》1936-1978年发表的489篇研究报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做过统计。[8]他发现,在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社会实验等四种社会研究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是统计调查,而且采用的比重增加较快,在1936-1949年间,统计调查所占比重为48%,1950-1964年间为70%,而在1965-1978年间,该比例达到80%。在相同时期,使用实地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所占比重分别为51%、27%、17%,而社会实验仅占1%、3%、3%。
收稿日期:2001-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