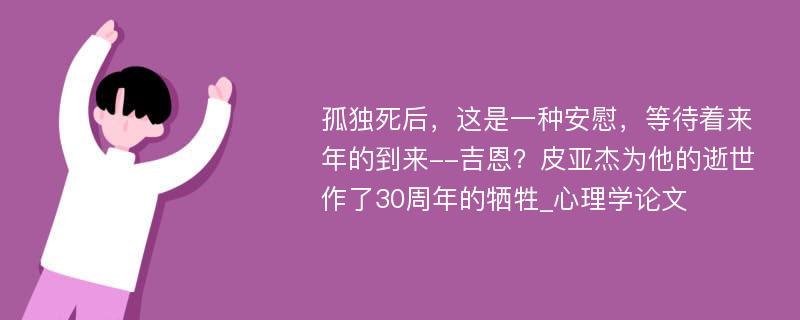
寂寞身后事,蓄势待来年——让#183;皮亚杰(J.Piaget)逝世30周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年论文,周年论文,寂寞论文,身后事论文,皮亚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二位心理学家之一”的皮亚杰[1],在其转身离我等而去的30年后,对今天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们来说,似乎已是一位稍显陌生的名字了。笔者在约十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曾不无遗憾地说过“皮亚杰及其学派似乎已度过了其辉煌岁月。皮亚杰正在走向历史。”[2]
俗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笔者想起了在皮亚杰逝世20周年时,在日内瓦曾与时任日内瓦大学皮亚杰文献档案馆(Archive of Jean Piaget)馆长的雅克·弗内歇(J.Vonèche)教授的交谈,那时他就宽慰笔者说,请放心,用不了多少时日,人们会再次地重新热议皮亚杰,他对此深具信心。[3]时至今日,弗内歇教授的预言似尚待兑现。
笔者以为,对皮亚杰的推崇不是一个私人偏好的问题,它必须源自对皮亚杰遗产的尊重和珍惜。恰恰在这一点上,皮亚杰遭世人淡忘,实乃事出有因,其要害在于: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皮亚杰。
诚然,皮亚杰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位具有特定立场和特色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本人更喜欢人们称其为发生认识论者。人们往往忘记心理学只是他“从事哲学认识论思考的方法论插曲”,尽管这一插曲几成他一生事业的主旋律。因此,提及皮亚杰,便不能离开他所呕心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发生认识论。
发生认识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的学科。甚至按照一位当代研究教育神经科学的著名学者小泉英明(H.Koizumi)的标准,发生认识论够得上是一门“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4]什么是发生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它研究康德所列之先验范畴的个体发生。皮亚杰的悲哀之一是:他常常因此而被某些人冠以先验论者的帽子(这在国内尤甚)。实际上,“发生认识论”的名称本身就已显示它与先验论分道扬镳了!“先验”与“发生”根本就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发生认识论正是为了克服康德先验论而创立的!
可用以下简单的五句话概括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性质:
发生认识论借助发展心理学的实验、访谈等手段考查儿童认知的发生发展过程,其中又以康德先验范畴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线索;
皮亚杰引入了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把范畴归结为一组动作或运算所形成的结构,继而又将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发展成为建构主义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严格说来是一种结构—建构主义;
对动作或运算形成的不同水平的认知结构,皮亚杰从抽象代数中选择适合的模型对之加以形式化:早期使用的是半群、群、格等数学概念,晚年则运用态射(morphisms)、范畴(categories)等更抽象的代数概念重新刻画这些认知结构;
皮亚杰又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描述认知结构的内部运转特征。他早年使用的逻辑工具主要是类逻辑、关系逻辑以及注重外延的命题逻辑(如16个二元命题运算所组成的组合系统);晚年则偏向运用注重内涵的意义逻辑——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不同于一般信息加工认知发展心理学的最重要特点正在于此。因此,皮亚杰的儿童认知研究是基于逻辑分析而不是信息加工的过程分析,两者是不同的研究范式;
从认知结构源自动作、运算这一基本立场出场,势必又会涉及结构产生与发展的功能方面。于是皮亚杰又从生物学(主要是理论生物学)中汲取大量概念来回答结构如何发展以及如何逐步使主、客体达于适应(所谓“同化于己,顺化于物”之和谐平衡状态)等问题。此即所谓发生认识论的生物学类比方法论。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既是发生认识论之整体不可或缺的构成成分,同时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
可以说,在范畴研究的核心目标下,结构主义方法、逻辑和数学工具、理论生理学类比,甚至儿童心理学本身都只是发生认识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完整地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必须掌握以上的相关知识。不能使我们对发生认识论的了解只限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上。四个阶段只与逻辑分析有关,它们是儿童内在逻辑水平的外显反映。
我们今日重提皮亚杰,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推进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其未来前景,笔者持有乐观的信念。根据在于: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皮亚杰为发生认识论设定的目标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皮亚杰终其一生,其实并没有完全恪守“范畴研究”的主线。他就像一名海边拾贝的儿童,常被前方漂亮的贝壳吸引而研究起其他相关的问题,忘记了回到范畴研究的归家之路。[5]或许我们不应过多责备皮亚杰,因为这些“漂亮的贝壳”都与上述发生认识论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方法论有关,属于“必须扫清的外围之战”。皮亚杰晚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才有《可能性与必然性》,《理解因果性》等著作的相继问世。然天不假年,皮亚杰并未实现最初设定的范畴研究的总目标。今天,我们应该回归发生认识论的主题,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包括神经科学),逐一厘清这些基本逻辑—数学范畴的发生发展图谱。这是发展心理学家的本份工作。
其次,我们已看到皮亚杰将被后世学者再次瞩目的曙光。
在此不能不提到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依笔者浅见,这一趋势就是抛弃“认知即计算”的强认知主义基本假设(所谓“信息加工的新皮亚杰学派”则不幸企图作这样的尝试,我认为它们某种意义上已不属于皮亚杰理论的范畴:“新”有余而“皮”不足是它们的共同特征。[6])而回归大脑,从大脑本身的活动寻找对心理(包括认知)活动规律的合理说明(当然要注意避免对“生理如何影响或作用于心理”做还原论的因果解释),此即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兴起的具身化(embodiment)潮流。[7]皮亚杰未及看到这一潮流现今呈现的壮观景象,因为与皮亚杰同时代的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对之一直不以为然)还未发展到认知神经科学的水平。若皮亚杰享年更久,以其一贯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特质(他晚年不是以新的逻辑和新的数学工具把经典皮亚杰理论推向“皮亚杰的新理论”的阶段嘛),或许,他现在正忙碌着fMRI、ERP等实验以印证他的那些关于不同年龄认知结构运转水平的假设呢!因为,别忘了皮亚杰曾接受过生物学的基本训练。皮亚杰的注意目光从未离开过生物学,只不过皮亚杰时代的生物学知识不能向他提供脑的微观机制的解释,而只能向他提供对认知功能与生物体发育功能进行方法论类比的工具而已!不过,从功能类比的角度而言,似乎给皮亚杰戴上另一顶“生物学化”的帽子也不尽合适。倒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当代研究更应要防止这顶帽子落在自己的头上!
如果仅仅说:当年的皮亚杰与今日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不约而同都超越心理学本身而将视野转向生物学(大脑),两者具有共同的旨趣,这显然只触及表象。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尽管皮亚杰受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所限,未能在心理的脑机制上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但他许多重要的思想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知识(逻辑—数学范畴)的起源问题。
第一代认知科学(传统认知心理学)实际由于其所坚持的“离身心智观”而回避了这一问题。[8]起源问题不仅是哲学认识论要严肃面对,同时也是心理学以及脑科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能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至少它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在皮亚杰理论中最具创造性的概念: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动作及其协调。协调会产生逻辑—数学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反省抽象(可以是无意识的)则产生逻辑—数学概念。而后者本质上可归结为一组由动作(运算)所组成的认知结构。认知结构又成为主体同化所有广义物理经验(本义的经验)的工具,由此而形成形形色色关于世界的各种广义物理知识。可见动作及其协调这种“发生于身体、结果实于心理层面”的过程是何其重要!它只能发生于人的身体,协调与反省也只是人的身体(包括脑)才具有的属性。(电脑则无能为力,因为它只能按人为它先设的程序工作,不会产生新的程序——某些软件似乎有此功能(如一些电脑病毒),但就其已预定某种发展结果的意义上来说,它既不为“新”,更不可与“协调”同日而语。)
二是关于动力系统的思想。
动力系统的思想目前已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获得重视。笔者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所涉之变量,其在本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者为多,因而并不适合以传统的变差分析方法处理之。[8]那些非独立的、互为因果(不是单向的线性因果)的变量之间的对偶关系(coupling),实际构成了一种动力系统。心理学研究中的动力系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最宏观的动力系统就是第二代认知科学所描述的脑(身体)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或人们所熟知的遗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关系。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有关脑(神经系统)的可塑性研究,就不能绕开这一问题。脑的内、外环境影响到遗传的基因表达,后者又会影响到对下一步环境作用的效果,进而影响到随后的基因表达。这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介入因素都不是单方向地谁决定谁,尤其不是基因本身独立地决定发展之路。上述思想在理论生物学中早有先驱,即有关生物体发育的衍生论(epigenesis)的观点。
以往人们谈及发生认识论的生物学烙印时,更多谈起的是适应、调节、平衡、同化、顺化等概念,多少有些忽视皮亚杰更重视的衍生构造的思想。时至今日,国内有权威学者在谈到皮亚杰时,还把他与维果斯基对立起来,说他是一名忽视社会、文化因素的遗传决定论者,这实在是大误会。不错,皮亚杰某种程度上强调发展顺序的不可变更以及不可能像布鲁纳(J.Bruner)所主张的:发展可以无限的加速,即所谓“通过一种智慧上诚实的方式,教会任何年龄的儿童任何内容”,条件是“只要你方法得当”。[9]这又何错之有?而且,皮亚杰并非眼中只有主体自身之动作的协调,他同样也重视人际之间的互动,后者势必也会以某种方式植入于动作协调以及后期“内化了的动作,即运算”的协调大系统之中。我们不应忘记皮亚杰在论述儿童如何从自我中心解脱出来时(所谓“离中化”过程)一贯重视儿童之间的互教和相互影响,有所谓同伴互教(peer teaching)一说。[9]顺便提及,皮亚杰与乔姆斯基曾就所谓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的先天性有过一番争论,皮亚杰认为完全可以摒弃它的先天假设而从儿童的动作协调中寻找答案。这是皮亚杰一贯持有非遗传立场的又一佐证。
说明皮亚杰既重视生物学因素对儿童认知成长的影响,同时又反对遗传决定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皮亚杰为了对认知成长(知识获得)提供更充分的有关环境与遗传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证据,他进行了动物(蜗牛)的实验,甚至为此而使用了一个新词,即表型复型(phynocopy)概念。他认为“认知的内源性的重构过程类同于机体发育的表型复制过程”。所谓表型复制,指的是“外源表型被同型态的内源基因型取代”。[10]基因型在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表型改变被固定了,同时又影响到基因型的改变,这就是所谓“被内源基因型取代”的含义。我们也可另换一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不同意“基因型本身改变”这种表述的话),即基因型并不是予成地决定未来的表型,而是原有的基因型在后天环境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是不会被轻易逆转的(除非再经历新的长时间的环境作用)。实际上,抛弃“予成决定”内涵的“基因型”更确切的说法就是“后成基因型”。“后成基因型”的概念与当前脑科学研究中“可塑性”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凡适用于动力系统理论描述的各种类型的不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在基本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难怪有学者在论及第二代认知科学这一思潮的先驱者时,会提到皮亚杰,这绝非偶然。我们期待:皮亚杰最重视的衍生论思想会在走向大脑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中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想到,要论对认知发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远远走在米勒(Miller,G.A.)等人提出的“认知科学”概念之前。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在皮亚杰的主持下曾邀请过许多心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控制论学者、教育家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皮亚杰的逝世,该中心终致“绚烂归于平静”。而后者提出的“认知科学六角形”(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各挡一面)却为今人认同。两者为何遭遇不同,其间深刻原因何在?惜乎没有人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笔者揣度两者命运重大区别的可能原因就在于其生物学(神经科学)介入的程度不同。皮亚杰仅停留在理论生物学的宏观层面,而现代认知科学则借助许多无创研究手段,深入到了脑活动的微观层次。然而这决非皮亚杰之错,乃时代之局限使然也!(不过,当前的“认知科学”又多少有点“认知神经科学”化了,这是否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呢?因为,显然在构成认知科学六角形的学科群中,有些学科的研究者特别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发出的声音太过微弱了。长久以往,这可能会制约认知科学的未来发展。当然,这是另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当另议。)
尽管皮亚杰作古多年,但我认为不应让发生认识论研究走向历史。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似乎我们现在仍不时与皮亚杰进行着对话。笔者2008年与林崇德教授、董奇教授合作,邀请国内发展心理学的同行,把最新版《儿童心理学手册》(W.Damon和R.M.Lerner总主编,2006)翻译出版。我们发现,它其中几乎每一章(特别是前三册)都会出现皮亚杰的名字,可见皮亚杰世纪伟人的地位并非浪得虚名。今借《心理科学》一角,爰作此短文,一为纪念先哲,二是期待有更多的后来者沿此路探索前行。
标签:心理学论文; 神经科学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皮亚杰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认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