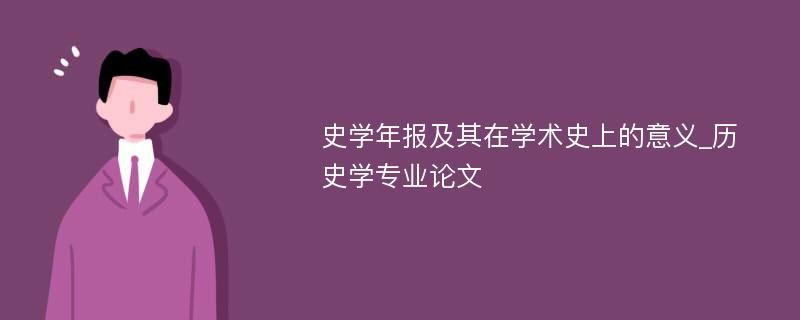
《史学年报》及其学术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年报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5—0099—05
无论是学会这种现代学术组织形式还是期刊这种现代学术发表媒介,都是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学会这种学术团体,桑兵与胡逢详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1]。而对于20年代开始兴起的史学期刊,过往研究虽已有部分涉及,但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的数量而言,仍然很不充分[2]。 本文以《史学年报》这样一个个案为中心,力图把其置放在民国史学这一总体背景之下,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史学期刊与现代中国史学的互动关系。
一、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与《史学年报》
民国时期,史界学人多次尝试以学会组织的形式,联络同仁,分工合作,推进史学研究。至20年代,史学专业学会开始在各地高校出现。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于1920年宣告成立;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学生成立了史地研究会;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于1922年;1927年5月,清华大学史学会成立。不过,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高校学会大多人事变动频繁,加之受到各种纷争的困扰以及经费问题,学术活动不能保持持续性。而后起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内部的运转也一直处于比较规范与活跃的状态。
该会最初成立于1927年,“是时因人数不多,团结涣散,”成立不到一年,无形消灭。第二年秋天,因“校中学会组织风起云涌,同仁等为联络师友感情计,为研讨学术计,为辅助史系发展计,佥以为史学会有重新组织再张旗鼓之必要,于是积极进行,赖师友之热忱,不一周即告成立,师友会员计二十余人,济济一堂。……会友以本会为研究学术团体,且规模又非宏大,主简单组织,期能收实效而止,”[3] 可见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组织。同年发刊《史学年报》,持之以恒,在当时的史学界声望颇高[4]。
在燕大历史学会中,一大批年轻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接受了早期的学术训练,从这里脱颖而出,仅以担任过职员者论,就有翁独健、齐思和、赵丰田、冯家晟、朱士嘉、邓嗣禹、王育伊、周一良、张维华、蒙思明、王钟翰、侯仁之、王伊同、谭其骧等[5]。推而广之,现代中国的史学学会及其所办刊物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外另一条培养史学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学会的活动中,编辑期刊和出版物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与专业层次的最明显的标志,又是向学术界传递自身学术主张,交流学术心得的重要媒介。《史学年报》的编辑主要由燕大历史学会的会员同学负责,这样一份刊物的成功,在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既靠历史学会办刊人员的学识、毅力、积极性,又有制度上、程序上的约束。
在编辑过程中,《史学年报》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会员既有学生,也有老师;既有校内,也有校外),实行匿名审稿制。他们提出:“大抵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史学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历史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故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子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6] 这也在《史学年报》每期后面的“本期启事”中得到呼应,“本期为排版之便利计,对稿件之次第,皆以收到之先后为准,不以己见评定甲已,区分先后,对文字评定之全权一以付之读者。”表明了一种以平等眼光看待学术的态度。
这种编辑方式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历载经营,规模初具,故其销数亦与年俱增。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Tuang Pao)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6]。《年报》出版后的影响程度也可从其绝版重印中得到验证[7]。略观其总共12期全部文章,观点虽时有可商,但绝少敷衍之作,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严密的论证与充分的材料占有基础之上的。其中的很多文章以今日眼光来看仍不过时,一些成果在今日也无法超越。
《史学年报》前后持续11年,共出12期,在30年代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能够不中断,首先在于学会会员的坚持不懈。在第二期中,会员们就相互鼓励,“天下之事,不患其发端之微,而患其故我依然,永无进境,或甚而日趋于衰颓;吾等即毫无成绩,仅有此种精神,前途亦未可限量”[8]。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意气风发的话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史学年报》作为一种学会期刊,是当时这类期刊中年限最长者,虽不能跟与其同时的《燕京学报》、《史语所集刊》等相提并论,但此种精神对于民国时期史学期刊的编撰,十分重要。燕大历史学会所办的另一份刊物《史学消息》在年报创刊10年后如此评价道:“輐近学术刊物如林,多如雨后春笋,即关于史学范围著,亦不乏其俦;要皆不数期后,即告停刊,而或能维持不坠,亦令人每况愈下之感。欲求其宗旨纯正,内容一贯者,百不一进。际此学术界时难年荒之秋,能得此佼佼之史学年报,不其尤为可贵欤。”[6]
《史学年报》创刊10年后,作为第一任主编的齐思和异常感慨地总结道:“余为本刊自创刊以来,为时不过一纪,出版仅至十期,以视欧西各著名之史学杂志,直婴儿之于彭祖耳。蓨途迢迢,前程方远。今既举行庆祝,宁非过早?惟十年来海内鼎沸,四郊多垒,举国无一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此非常时期,本刊犹能维持至今,未尝间断,且内容逐渐充实,销路日有增益。反视国内其他同类刊物,或发刊数期而中途夭折,或昙花一现而寂焉无闻。及至今日,惟本刊硕果仅存,巍为灵光,实非始顾所及,则同人亦不得不私自庆幸矣。”[9] 此语可谓道出《史学年报》能够持续出版的艰辛,更可见其之于民国史学界的特殊价值。一份仅出12期的刊物竟然横跨了10年,其学术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期刊本身,动荡的社会中,一份由学生主办的学术刊物如此坚守,展现出民国学人延续自身学术传统的巨大努力。
二、《史学年报》的学术网络
燕大历史学会除编辑《史学年报》外,还编辑了《史学消息》和《大公报·史地周刊》。三种杂志各有宗旨,侧重点各异,风格也是各不相同,但互相援引,互通声气,已初步形成一个学术网络。
《史学消息》是燕大历史学会另一种重要学术刊物,1936年10月开始出版,每月一期。其目的“在与国内外史学界沟通消息,提倡历史研究兴趣,介绍史学研究成绩,联络会员感情,供本系同学练习编辑之用(编辑及经理事务,概由本系同学分配担任)。”内容“大体侧重国外方面,盖国内方面,已有若干种刊物介绍之矣。……关于西洋汉学之论文,将自西洋负有盛名的学术杂志中,摘取关于汉学的精心著作,逐期体要披露。”[10]
《史地周刊》是燕大历史学会与天津《大公报》合作的产物,每期以《大公报》副刊的形式发行,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内容侧重于中国史地方面,1934年9月开始发行,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停刊,《史地周刊》亦不复存在。一共发行125期。
《史地周刊》是燕大史学会力图回应社会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如果以历史的普及与提高区分燕大历史学会的工作,那么《史学年报》做的是提高的工作,而《史地周刊》则是普及的工作。《史学年报》的成功更多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其影响范围只限于学界,而面对国难日重的整个社会,它的反应是无力的。于是,燕大史学会逐渐将自己的视野跨越了单纯的学术界而投之于广阔的社会,在《史地周刊》第1期即交代了办刊宗旨:“科学的正确与通俗的趣味相结合, 在这一周刊上作尝试……,引起国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供给他们以新国民应有的史地知识。我们盼望本刊的一大部分能够成为中小学史地教师和学生的读物。对于教师供给他们补充教材,对于学生供给他们以课外的消遣。”[11](p108—110)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讲,学术期刊这种形式提供了一个学界同仁互相交流的平台,《史学年报》宗旨就是“集本系师生一得之愚,以就正于海内外同好者也。”[8] 如同刘龙心所言“机关刊物已经成为20世纪学人发表研究心得,交换学术资讯的主要场域。”[12](P370) 而在学术期刊出现之后,现代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也产生根本变异,人们多是在广泛披览报纸杂志之后,就进入一个与并世学者发生紧密互动的交流空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受人影响、与人论辩的过程中,一面形成、修正自己的观点,一面补充、驳正他人的说法[13]。
三、《史学年报》的学术史意义
王晴佳引用了Peter Novick对美国史学专业化形成过程的描述,“学科专业化的标志有如下几种:学术机构的出现(学会、专业刊物),培养专业技能的标准化训练,进行资格考核并发放文凭和合格证书,专业人员地位的提升和专业的自主性。”[14](P621) 这些标准同样可以适用于民国史学界。 以《史学年报》为代表的一批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中国史学制度化、专业化时代来临的标志之一。
专业史学期刊的成批出现表明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化建设有了新的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
《史学年报》的编辑者是一群青年学生,它的出现表明学生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来,阐述他们的研究理念,并向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发刊词》中,燕大历史学会的同学们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史学的看法,“吾国史学,渊源最早,而以其进步迟缓之故,乃至今日反落欧西诸国之后。呜呼!宝蕴于山,过而不顾,货弃于地,俯拾无人,此则同人所为深慨而不敢自弃者也。”[15] 期刊这种形式既是他们展示自我的最重要舞台,又是他们得以形成比较固定的学术组织,与外界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
史学期刊兴起之后,历史知识有了新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也有了稳定的园地。与过去时代相比,个人的研究成果得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正由个人长期积累的著述方式转向相对频繁快捷的“期刊”文字的发表。民国史学少有死后才得以闻名的学术大家,以齐思和、冯家晟、朱士嘉、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侯仁之、谭其骧等人为例,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是凭借文章的发表之功[16]。
史学期刊兴起之后,以往个人的单独研究方式渐渐消失,大量学人开始涌入高校或专门研究机构。《史学年报·发刊辞》体现了这种趋势,“近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几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非敢谓倡导风气,盖亦聊供抛砖引玉之资云尔。”1949年,齐思和在总结民国史学发展时说:“现代的史学和现代的科学一样,已经走到集体工作的阶段上,没有和以前像司马迁、刘知几等震耀一时的明星了。各专门范围之内皆有主要的领导者……”[17]
期刊作为一种学术传播媒介,其传播活动已经是一种社会行为。史学期刊得以维系,需要固定的编辑人员,更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投稿群体。因此,专业史学期刊兴起之后,以其为阵营的学术群体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史学年报》一共12期中,所刊学术文章共计约149篇(发刊词,十年回顾,学会一年回顾,及十年职员录等四篇文字不计)。作为一个学会会刊,《史学年报》所刊文章主要来源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内部,此比例可达三分之二。由此可以观察一个成功的史学期刊之于一个学术团体凝聚力的功效。
但凝聚力的加强相应又导致《史学年报》的开放程度很差。至于是外人投稿太少因而出现在《年报》中的文章也少,还是投稿虽多但不能发表,此文尚无法做出判断。但如果把这种现象扩展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期刊,结论也大概不错。其时,多数期刊都为同仁自办刊物,所刊文章绝大多数来自本身内部成员,即使一期之中看到多篇文章出自一人之手也并不为怪,这与民国时期大多史学期刊的民间性质相关。
以《史学年报》为代表的一批专门史学期刊的创办,也反映了现代学术分类所导致的史学学科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从《史地学报》、《国学季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到《史学年报》、《史学杂志》,表明史学的独立化、专科化的趋势至少从外在形式上得到了验证,史学与地理学、语言学逐步划清界限并开始从国学中脱离出来。《史学年报》在其《发刊词》中就特别注明其“尤侧重于国史之研究”。专业史学期刊是史学独立化进程中的制度性凭借。史学发表有了自己独立的阵地。但当时一些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国学季刊》等,刊布的论文中仍以史学为最主要部分[18],既展示出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生态,表明了史学在传统学术中的分量,又仍然提示着我们史学独立化进程中那复杂的面相。
史学专业期刊的出现也是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科学主义支配下,晚近以来中西学术都有由笼统论述转向专题研究的趋势,研究对象益趋专门与精深,史家在入手处较少将过去历史视为一个必须加以全体把握的整体。史学期刊反映了中国史学从通到专的这种研究趋势的转折之处或衔接之处。《史学年报》在创刊之初就阐明其“内容则学理与工作并重,……非学理无以指导研究工作,非有专门研究,则学理无所附丽。”[15]
与此相应的是,对照《史学年报》共12期的总目录可以发现,《年报》非常强调文章方法与观念上的一致性,大多都是针对一个特定问题,以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考证性的论文,非常强调证据的充分与足够的参考资料。这种问题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与传统学者所一再强调的贵通人不贵专家的观念相当不同。这无疑标明了它的学术宗旨。而30年代已经渐渐兴起的唯物史观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根本不能在此发出他们的声音,以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史大论战为例,《史学年报》中几乎没有任何体现,这既暗含了以《年报》为阵营的这样一个学术群体的学术取向,又反映了民国史学研究中派系壁垒的森严。
考查《史学年报》上的全部文字,可以发现《年报》揭示了20世纪前半期史学研究客观化、标准化的趋势。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会,史学期刊三位一体,由于期刊的学术性质,如果要在上面发表研究论文,必须将个人的色彩减到最少,进行最为客观的研究。历史研究的“诗性之美”在学术论文这种规范化的学术表达形式下得到最大限度的削弱。同时,一篇文章通过刊物的发表,作者的观点能够在学术圈内被更多的人接触,并引起公开讨论与评价,对于文章本身也是不断修订,不断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是出版学术撰著,皆可视为是现代学术型塑客观价值的重要活动。”[12]
史学研究的客观化、标准化方向渐渐确立之后,学术期刊只面向学术社群,在期刊上撰写的论文,也自然而然不再注意一般读者,不考虑对群众的影响,也不考虑它对社会的立即价值[19[(P113)。已经注意到此种现象的燕大史学会与《大公报》合作,创办了通俗性的《史地周刊》,以《大公报》副刊的形式出版,力图最大限度的发挥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但一个基本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自从以《史学年报》为代表的一大批专业史学期刊兴起之后,学术与社会的疏离倾向愈加明显了。
余论
史学期刊虽然改变了民国史学的研究形态,但期刊自身的发行缺乏制度性的保证,民国政府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期刊的发行机构大多为各个大学的历史学会,且学会本身常常处于人员变动之中,《史学年报》这种以民间之力,可以坚持超过10年的专业史学期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一个稳定的、有人力与财力保证的出版机构对期刊的稳定运行相当重要,动荡的社会中,学术的制度化建设,异常艰难而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2006—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