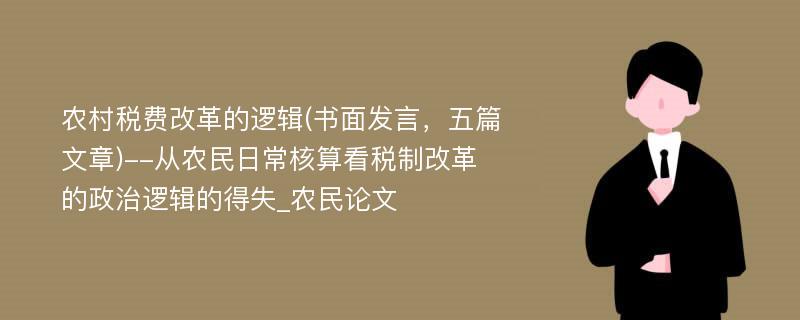
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笔谈,五篇)——从农民日常算计看税改政治逻辑的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笔谈论文,得失论文,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日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税费改革的启动及其所引发的政治、社会效应至少有三套逻辑在运行:政治逻辑、治理逻辑以及市场逻辑。税费改革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三套逻辑的综合平衡运行。本文将从农民的日常“算计”来谈市场逻辑对税改的影响及政治逻辑的得失。
从什么时候起农民开始“算计”着过活?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农民自己自足,多个人无非多双筷子,生活过得紧巴巴,但也有条理,用不着整天算计。集体时代,人们也少算计,因为都是工分和配给制,也没多少东西能够自由买卖。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才开始过着“算计”的日子。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市场化、社会化,农民开始“算计”生活。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算计还不那么厉害,因为分田单干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粮食连年丰收、价格上涨,农民手中有一定数量的钱。进入90年代,农民的景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更为彻底、愈发变幻莫测,农民尚未掌握在其中生存游戏的法则就在市场上翻了不小的跟头:粮食价格回落,农民生活、生产必需品价格上涨得厉害,手中的钱怎么也逃不脱市场的吞噬。农民开始意识到手中“现钱”的重要性,在市场中没有现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惜钱不惜粮”的说法,农民可以从庄稼地里收获足够多的粮食,却无法将其变成足够多的现钱。
因为需要应对市场风云,农民对手中的现钱看得特别紧,用得也特别谨慎,轻易不花现金。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业税费还是分两季度收,夏季收农业税,一般是以粮食的形式缴纳,秋季收“三提五统”,以现金的形式收。农民“惜钱不惜粮”,因此农业税这一头他通过挖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交上了,一般不会拖欠。但轮到秋季交“三提五统”的时候,农民就得好好地“算计”一把,把这年的下半年和下年上半年的所有“出入”都得细致算过。算什么?算需要市场解决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人情的一切,算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算疾病天灾之类的不测,等等。算计来、算计去,手中的现金总是不够开销,因此最紧迫的秋季“提统”也就只能先拖下。农民屋子摆放成堆化肥、农药、种子等,却拿不出一分钱来交税费。所以,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伴随着国家市场化的深入,乡镇在收取“三提五统”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钉子户”、“贫困户”,还有平常户,不分原由一概不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民负担问题开始突显,中央连续下达数个文件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尽管遇到了收取困难和农民负担的压力(来自中央),乡镇税费还得收上来,“税费改革”的思想也就应运而生。1995至1997年的试点改革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但都是针对“三提五统”,基本上都是将秋季收的并到夏季收,以收粮食为主。只要粮,不要钱,减轻了农民对钱(也就是对市场)的心理负担,粮食也就很容易拿出来了。因此这些改革在实行的头一两年内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夏季统一收税费也较为容易,从而也减轻了乡镇的负担。
但是这种并税式的改革并没有逃脱“积累莫返之害”,一两年之后各地又在夏季征收时不断地加码,变本加厉,企图通过将加码的摊派、提统捆绑在农业税上合法征收。一位乡镇干部如是说:“并税改革的确好,过去那些统筹、摊派什么的,农民要就是不交,你还真没办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农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税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于是改革从减轻农民负担入手,以增加农民负担告终。而且从市场的因素考虑,90年代中期特别是98年之后,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甚嚣尘上,市场对农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尤为厉害,而且此时的农产品价格较90年代初下跌得更加厉害,基本上卖不出价钱。也就是说,在农民最需要应对市场、需要“钱”的时候,国家向农民要得最多,农民手中也就最没有钱,从而在市场—农民—国家三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矛盾。其中,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国家的矛盾,而压力则来自市场——因为如果农民有足够的钱来应对市场,向国家交纳的税费也就算不了什么。比较集体时代就很清楚,那时没有市场的压力,即便农民大部分都被国家统购统销走了,也不会在农民的“算计”下发生后来的“三农问题”。
农民此时的“算计”是“做农民划不划得来”:农民负担最严重的中部和中原农村,上缴国家和乡村两级的税费在最高的年份达田亩数的一半收入,即一亩地收获600斤小麦,就得上缴近300斤,这还不算上其他的摊派、集资以及义务工等,如果去掉在农资上的花销(即市场压力),一整年就等于白忙活了,有的年成还要贴上老本。因此这个时候的农民常说“简直没法活了”,不是因为国家把粮食都给挖走了,没饭吃而活不了,而是因为国家要去太多,农民更没法应对市场压力了,是在市场中“没法活了”。所以在粗略“算计”之后,农民得出的结论是“做农民划不来”,原因是“乡镇干部太贪”,于是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能够逃离土地的地区,农民纷纷抛荒到沿海城市打工;而不能轻易逃离的地区,农民对乡镇干部乃至国家的积怨日深。到世纪之交,农民负担问题已经造成了整个农村的“治理性危机”,干群关系恶化演变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挑战。
市场的压力造成了农民负担的压力,但国家却不能去扭转市场的正常轨迹,只能从国家本身入手,采取果断措施进行税费改革,紧接着不到两年时间国家又快刀斩乱麻全面取消农业税,而且国家还增加了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直补”。
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这在农民的“算计”中非常清楚:如果一家5亩土地,按正常的一亩地缴纳约150斤小麦,每斤小麦5角,则这一块免交合起来就有375元,加上粮食直补每亩地40元计算,有200元。这样,比较改革之前,农民要从国家手中直接得到575元的好处,就此一点农民对国家自然会感恩戴德。在农民的“算计”下,国家或者中央对农民是越来越好,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度也加深,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得以缓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巩固。因此,从税改和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算计”来看,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运转得还蛮好,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然而农民的“算计”并没有因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而作罢,算计还在继续。因此,农民不断地“算计”,税费改革的政治效应要想持续就要不断地满足农民的算计,也就得不断的“投入”。于是,国家就不能止步于取消农业税,还得不断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那么惠农的合作医疗、义务教育、最低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出台了,建自来水、建沼气、乡村道路等基础建设的专项资金力度加大,而粮食直补、种子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综合补贴等也紧随而来,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税改政治逻辑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是农民“算计”的结果:农民得到了实惠,国家得到了名声。
但是国家对农民政治投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市场的消解速率。农资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国家税改的启动相伴而生,农民的算计也将二者拴在一起。农民普遍抱怨税费改革后农业生产资料全面上涨,上涨幅度达20%~40%,例如常用的复合肥往年价格是80元左右一袋(50公斤),现在上涨到了125元,上涨幅度高达50%以上;二胺以前是110元一袋(50公斤),现在要卖到135元,上涨30%,其他农资如农药、种子、农机、地膜、柴油等都有相当幅度的上涨,且趋势是还要往高处涨。农民从国家粮食直补中得到的现金现在几乎全部贴到了市场涨价上,刚从国家得到点好处转眼又被市场给掏空了。农民越发不能把持住市场的行情,越发对市场价格的上涨感到情绪不定,终日惶惶,整天算计:今天怕这上涨,明天怕那上涨。
不满情绪总要有发泄的渠道。在南方农村,由于传统上就对国家不信任,物价一上涨就直接把整个责任推到了国家身上,税改政治逻辑的效应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在传统上对中央政权较为信任的北方地区,面对农资价格的上涨首先指责的是市场。但是市场作为发泄对象是虚无缥缈的,而国家则是具体可以接触到的,久之农民的情绪必将从市场转向国家。更何况只要农民将税费改革与农资价格上涨联系在一起“算计”,税改政治逻辑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就要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后,农民已经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维持生计的小农形象,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但是面对市场,农民依然是脆弱的。农民依然要“算计”着过活,要把手中的现金紧紧地拽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民负担、乡镇机构膨胀、乡村治理危机等问题都与农民应对市场的弱势地位有关系,税费改革其中也包含着市场的逻辑,即农民“算计”的逻辑。而且从整个税改的社会效应来看,税费改革主要强调政治逻辑,忽略它的治理逻辑和市场逻辑,将农民完全暴露在市场里面。因此税改后农民日常的“算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农民一有闲空就算计着,家庭里算,公共场合算,调查者面前算得更仔细。税改后对市场逻辑的忽视,已经开始影响其政治逻辑的效应。
裁撤乡镇机构,对乡村缺乏应有的治理眼光,而将乡镇相关的职能和服务都推向市场,则忽视了农民面对市场的弱势地位,是对税改市场逻辑的无知。税改的市场逻辑与治理逻辑密切相连,看不到或者有意忽略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就会盲目迷信市场,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就会导致“用钱买服务”的简单逻辑甚嚣尘上,成为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思路,最终就会使税费改革的治理逻辑长期被掩盖和遮蔽。而不注重它的治理逻辑,则会很自然地把乡镇应该做而且在税改后能够做得更好的对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指导和服务工作抛向市场。这样一来,税费改革就只会凸显它的政治逻辑,只讲究它在国家政治方面的积极效应。
但是政治逻辑只能解决一时的、剧烈的政治危机,长治久安还得倚靠治理逻辑的良性运转,还得倚靠对市场逻辑眷顾,要挽救农民市场的弱势地位就得依赖于乡村治理的实施。税费改革的治理逻辑和市场逻辑是其政治逻辑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个基础政治逻辑很难运转得长久——因为追加的政治投资在短期内能够满足人们的心愿从而为政权获得合法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政治逻辑带来的积极效应终会被农民在市场中越发弱势的地位给稀释,在农民应对市场压力的“算计”中一点点地消散。
因而国家的政策制定需要有综合和广泛的视野,其中重要的是趁着政治逻辑的效应尚未彻底消失,通过财政转移和政治压力使基层政府运转起来,实现税改后的治理逻辑转变,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