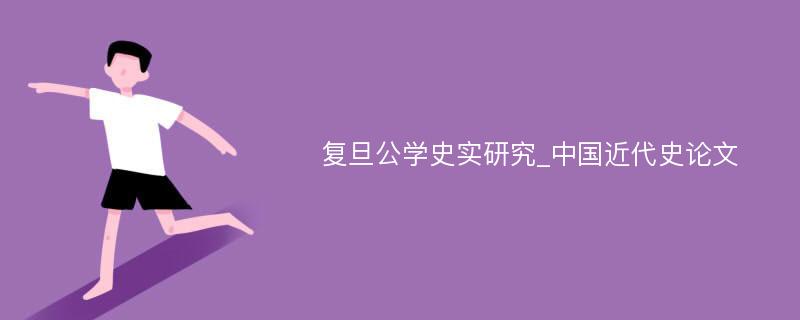
复旦公学创校史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论文,校史论文,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创办的问题,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既有的复旦大学校史记载与有关回忆太过简单,甚或有不少错误和失实之处。如对复旦创校过程中的复杂性描绘不够,过多强调了马相伯的角色,①却忽略了当时两江总督周馥和部分绅商,对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与维持所起的巨大作用;再者,对于复旦所获官方拨款的来源、时间及数目,都存在问题。而且1905年新成立的复旦公学,也并非一私立学校,而是一所官绅商学各界协力打造的“公立”学堂,这也是当时创校者及社会舆论对复旦的定位。②后来在接受官方常年拨款后,复旦公学实质上逐渐官立化,但表面上仍然保有“公立”名份。③
以下笔者根据这些年新挖掘的第一手复旦公学校史资料,重新探讨校史,更详细地再现复旦创校时的曲折情况,意在使我们改变对复旦校史的某些简单化与错误性的认识,去书写更为准确的复旦校史。
一、复旦肇建
1905年3月,因内部发生权力倾轧并升级,1902年才成立的震旦公学解散,马相伯带领学生从老震旦脱离,准备另立新学校。④此事引起上海报界关注,陈景韩在《时报》上专门发表评论说:建立新震旦学校,“此为学界公益之事,国家前途之望”,“凡有子弟者,无一不宜协助,凡有人心者,无一不宜协助,财者助以财,能者助以能,力者助以力”,鼓励各界宜合力建成新震旦学院。⑤
震旦退学重建之事也引起两江总督周馥的注意。周馥为此专门发电报给驻上海的苏松太道袁树勋,询问有关情况,“震旦生退学,闻因教习不允添课,马欲另建一校,确否?如该生等,果系可早,或拨官款,暂赁校舍,俾免逃散”,并要袁查明后回复。袁树勋也迅速回电,将震旦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周馥:“震旦生退学事,饬员查复。该学堂设已两年,课程中西并重,教习系教士充当,所授格致、化炼各科,均用英法两国文字。学生程度颇高,主张爱国宗旨,不肯入教。近因法文教习南君忽议裁去英文,专以法文教授,意欲以教务侵入。学英文者既无所适从,习法文者亦惧教会侵入,颇不满意。后马因此辞退,遂亦退学。现该教习允复英文,惟不许马进院干预学务。诸生以学堂由马创,非马势难久持,乃散各处,意图重建改良等语。”电文最后说:“查震旦生能知爱国,恪守宗教,实为难得,自应遵谕设法维持,晤商马君,如何定办,再禀。”⑥
或许是受到时论、周馥及上海道对震旦退学事件态度的影响,或许是自发的组织,当时在上海的绅商如张謇、王丹揆、曾少卿等,也纷纷关注该事件,计划成立新震旦,以解决学生无处求学的问题。⑦他们于二十日(1905年3月25日)在一品香聚会,决定推选马相伯为新校校长,并讨论筹措资金办法,商借吴淞陆军公所为校舍,且立即电请两江总督周馥等人,希望得到批准,而周馥等也立即回电,答应会就借用事同军方进行讨论。稍后不久,军方即答应将驻军一律牵走,公所暂借与学生。⑧只是鉴于“行台为外海各营会议之区,不便久假,而学堂则因屋宇住舍嫌少,本系暂为之计”,军方同马相伯、张謇、王丹揆等商定,只借一年,学校须要赶快购地兴建校舍。⑨这时,刚担任新震旦董事的张謇,已经替新震旦募得万元,“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⑩随后,新震旦之创办进展迅速,上海道及各绅商亦表示愿意出钱资助(11),并打算在四十亩吴淞公地上为之建设新校舍;江督周馥且派手下陈季同前来上海,筹划有关事宜;主事者亦一度有将之改名为“乐群公学”之议。(12)
目睹此官绅合作情形,陈景韩在《时报》上又赞扬道,“此次新震旦之成立,官与绅俱有力焉,不争意见,不生疑忌,上下一心,更近日新事业中所寡有者。苟能事事如此,中国前途未必无望!”(13)但也有时人在旧震旦解散之初,震旦师生及绅商向江督请求援手之时,即发表评论对此行为不以为然,“诸君独立之精神,与向学之苦衷,当无人不佩服者矣。然余谓有百余英锐青年之团体,有何事不可为,况区区觅一校舍?(有百余学生,有热心教师,无形之学校已成。)而必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进而,该评论还以之前南洋公学退学师生另立爱国学社为例子,表明办学“未尝藉官力为之引援”,也可以成功,现在新震旦接受官方资助,与震旦师生退学之志“未合”,“必自予官场以干涉之路”。(14)
之后,候补道曾铸(即曾少卿)、施则敬等人禀请周馥,请求为新震旦拨款,而周馥根据袁树勋的回复,也认为“该书院办理数年,颇著成效,自应力与维持”,批复江藩司会同上海道、学务处,迅速为新震旦之建设筹措经费。(15)但上海道库并无款可拨,后又禀请周馥,让南京、苏州两藩司、学务处迅速合拨一万两白银,给新震旦作经费。(16)新的震旦本已改名为复旦,但原址重建的新震旦突然呈给周馥一份震旦学堂章程,致使周馥产生疑惑,在复旦公学开学之际,专门发电向沪道询问新震旦与复旦的关系。(17)
事实上,马相伯带领学生脱离震旦之时,曾一度宣布,“震旦学院”经“全体签名解散,旧时院名同日消灭”。(18)但仍有部分震旦教习出面维持学校,不点名批评马相伯带学生出走之行为,号召学生返校继续求学。(19)但效果似乎不佳。故此,天主教会主动同代表新震旦的张謇、曾少卿等人沟通、商议,建议新震旦学校仍由徐汇天主教会办理,并草拟九条合同表示诚意,但未得到张、曾同意,久决不下。最终,由副主教丁出马,“再四熟商”,张謇也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答应帮助原震旦公学复校。丁主教询问张謇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新复旦不再开办,张謇则回答说会继续创办复旦公学,而此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于是现教会继续袭用原震旦校名,新震旦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复旦公学。(20)
确定两校分办后,复旦校方随即发布告白,宣布作为酬谢,原震旦校舍赠予教会;其余一切文具、书籍、标本等物品也早已带走,“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与教会“毫无杯葛”;且震旦公学名字已经不再使用,在原址新建之学校是否沿用旧名,与原震旦公学丝毫无关,“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殆毫无关”。(21)
同时,天主教会也运动张謇、曾少卿成为新震旦的校董后,且与校董“公订校章,申明不涉宗教,西人专司教授,管理则归华人。”(22)随即,新震旦公学立即刊登广告表示,学校已经新请“教育之人”为本院“名誉赞助”,学校会继续以震旦名义开学。(23)稍后,又发布了震旦学院招考广告。(24)作为回应,复旦方面也立即登报,表明震旦名义已经被人袭用,之后与己无关,所有海内外函件,不要再寄往这个震旦公学,而改寄复旦新址。(25)
依靠官绅学商合力,复旦公学顺利创设,所谓“其时得上海官绅学商界之捐款赞助,始克成立”。(26)立校伊始,马相伯便请包括严复、张謇、曾少卿(铸)、袁希涛(观澜)、熊季廉在内的二十八位社会名流担任复旦公学校董,以便让他们为学校募集资金,提高学校声望,并能参与到复旦校务的管理。而在5月从欧洲回到上海后,严复也积极参与了复旦公学的创办。(27)
新复旦本预计8月31日(八月初二)开学,但因“教员寝室尚未修整”,“学生亦未到齐”,故改到9月4日(八月初六)开学;另外由于屋舍不够,还拟再租住附近房屋。(28)然而9月初的一场雨灾,让“复旦学院寄宿所坍墙一堵”。(29)直到1905年9月10日,一度又因月初风灾、雨灾延迟的复旦校舍、宿舍修复工作,终于告竣。(30)校方遂决定于14日下午两点正式开学,(31)并在开学当日刊登广告进行确认和宣传:“本公学于本日下午二点钟行开校式,敦请名流演说,并蒙校董萨鼎铭假军乐全部,务请学界同人暨热心教育诸君子惠然贲临,藉增光宠。谨此代东诸希公鉴。”(32)为了庆祝复旦此次开校、开学,为观礼之人提供便利,淞沪铁路方还为此进行了调整,特意在客运火车来回经过复旦时,均停车五分钟。(33)
综合当时亲历现场的《南方报》、《时报》记者对复旦开学典礼的报道可知(34):复旦此次“开校典礼”在下午二时举行,先由萨鼎铭部军乐队奏“开校军乐”,接着校长马相伯发表了演说,马相伯以泰西来沪的马戏团作比喻,说马戏团中的表演动物虎豹狮象犹可教育,人难道不如虎豹狮象?借此例子,马相伯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随后,作为校董及“名誉教员”的严复也发表了演说,大意为“中国员幅日狭、民族日凋,不畏外强之侵凌,须忧吾人之不振,所望全校学生,须勉力勤学,万不可有告假偷闲之举,庶几日异月新,为将来之国用云云。”最后,复旦公学“英文正教员”、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李登辉亦用英文发表了演说,“谓中国之衰弱,皆由教育之不兴,欲为中国前途造幸福,则必以广推教育为主,所愿在学诸生,各励尔志,是则鄙人之所厚望云云。”演说完毕后,复奏军乐,“到四时,始由校员袁观澜摇铃散会。”参加此次开学仪式的复旦学生约有一百六十人,加来宾及学校职员共约三百人。
为感谢周馥的大力支持,复旦校方在开学成功后即致电周馥,表示感谢:“两江制台钧鉴:复旦十六日已开校,仰赖成全,敬电谢,全校公叩。”周馥也回电表示期望:“复旦公学开学伊始,愿教员实心训导,诸生锐意潜修。谨为全校贺,并为学界贺。馥。”(35)
由上可以看出,在时人的认知与定位中,刚刚创建的复旦公学并非是一所私立学校,而是众人合力创办的“公立”之校。其中,张謇、曾少卿等一部分绅商,为新复旦的建成出力不少。1905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张謇还邀请刚从广西来到上海的郑孝胥参观复旦,伴随参观的还有陈宝琛、王季樵、赵凤昌等人,他们并拜会了马相伯。(36)郑孝胥大概对这次参观感觉不错,一周后还“令佛德往考入复旦学校”。(37)另外,代表官方的江督周馥的支持和资助,对于新复旦的肇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种官方的介入,也为以后复旦受到官方的干涉,并逐渐官办化埋下了伏笔,正为前引《大陆》杂志上的评论所言中。
二、开学风波
脱离震旦、另立新校,马相伯自然是此行动的主要领导者,然而这背后,一批爱校学生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甚至是带头作用,其中就包括深受马相伯器重的震旦旧生叶仲裕(景莱)(1879-1909)。马相伯脱离震旦,他和沈步洲带领学生坚决支持,还在报上发表声明号召同学追随马相伯,并希望学生与之联系有关事宜。(38)复旦之成立和得以继续维持,叶仲裕和于右任(即刘学裕)出力不少。(39)
复旦正式开学一学期后,鉴于校舍与经费紧张,时为庶务长的校董袁观澜(希涛)遂在《南方报》、《时报》、《中外日报》等上海报纸上刊出《复旦公学广告》:
本公学于夏间禀借吴淞提辕先行开校,屋少不足容来学之众,地复潮湿,校外借寄书社七处,益形散漫,于卫生、管理二者多所妨碍。现拟就炮台湾拔定地亩,赶筑校舍,一俟落成,即当改定章程,召集生徒来校就学。其提辕借设之校,明年暂不开课,特此广告。(40)
假若照广告所言,复旦暂停招生,这对于刚创办的新学校来说,不啻是自掘坟墓,不仅不孚外来学子之期望,亦大伤害从震旦以来一直追随的学生,还会影响复旦初创之际在舆论界留下的爱国向学形象,辜负社会各界的支持。更何况该广告所言事出突然,不符合官绅商学各界创立复旦之目的,更导致追随学生无书可读的局面出现。
因之,在《中外日报》上刊出的该广告立即遭到复旦住校学生的关注,他们第二日即登出《复旦住校学生公启》质询:
本日贵报告白,有《复旦公学广告》一则,云本公学明年停止开学云云。同人阅之,深为诧异,比即走询各校董,亦皆同深感疑惑,莫名其故。俟查探明确,再行奉阅。此事关系本校者甚大,同人不能默然,先此布陈,乞登入贵报为幸。(41)
这些留校学生在叶仲裕(叶此时大概为复旦学长,角色或类似后来的学生会主席)带领下,马上质询校董,以图挽回。他们分别以叶仲裕与复旦留校学生名义在《时报》、《南方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登出广告,谴责袁氏这种擅作主张之行为,并希望想要负笈复旦的学子不受其迷惑和误导。其中以叶名义所发的《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启事言:
报登公学明年不开课云云,其中另有枝节。校董不会议,校长不在沪,学生毫不与闻,而谓可独断停学,景莱不才,窃未明公理何在?现竭力禀商各校董,妥筹一切。愿我远近同学,毋遽惶惑。叶景莱敬白。(42)
以复旦留校学生名义所发启事分别为《袁观澜先生鉴》、《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其中《袁观澜先生鉴》曰:
昨报告白,复旦明年听课云云,殊深骇异。走询校董,皆不知为谁主持。往谒少卿(即曾少卿,时为复旦校董,引者注)先生,则云稿由先生拟就送登。学生等劳燕分飞,甫有生趣,忽又丁此意外波折,先生素号热心教育、深明事理之人,而忍出此?除商各校董作正当之交涉外,并请莅临开示一切。同深叩祷。复旦留校学生公启。(43)
《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则公布了同学们质问袁观澜的结果:
昨请观澜先生莅临开示一切,来函因病未能到,故对付办法未便即决,当随后续布。留校同学公启。(44)
袁观澜也立即登出广告《袁观澜告复旦同学》,回应复旦留校学生的质疑,表示暂时停课的决定不是他一人做出,乃是来自于学校董事会,由他执行而已。他不满学校董事会在学生压力下居然前后不一、立场反复,有诿过于人的嫌疑,并表示之后不再过问复旦校事:
前登复旦明年赶筑新校、暂不开课之广告,系仆闻诸校董。仆深恐年假已过,迟不发布,有妨诸同学求学之计,故特拟就广告,询诸校董,由仆分登各报。今阅诸同学广告,云校董均言未知,则前广告似仆误登。至究竟如何办法,请还问诸校董,仆已辞明年校务,不敢预闻,特此更正。(45)
之所以发生此停课事件,据这些留校学生分析,是因为校董袁观澜和曾少卿存在矛盾,而校长马相伯在年底恰恰奉江督周馥之命东渡日本,(46)遂有因两校董私人意见不合而致登停课广告之事。为了挽回大局,他们还分别致电两江学务处总办沈凤楼、校董张謇、驻日公使杨枢,请求援手,两江学务处随即回电表示支持。《中外日报》、《时报》上同时刊载的《复旦公学致各处电文》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记录。(47)其中复旦学生致两江学务处的电文为:
两江学务处沈凤楼先生钧鉴:复旦蒙通人提倡,甫见萌茁。今校长不在沪,校董不会议,竟以私人意见,登报明年停学,深骇闻听,乞鼎力维持。复旦留校学生公叩。
致张謇的为:
通州张季直先生钧鉴:少卿先生与袁先生龃龉,登报明年停学,校董不会议,校长不在沪,竟贸然出此,学生等断不忍坐待瓦解,有负诸先生提倡初心,敬乞竭力维持,详情请季廉先生函达。复旦留校学生公叩。
致马相伯的为:
东京清国杨钦使转马相伯先生:校事有奇变,众情愤激,乞公毕速归。学生公叩。
两江学务处的复电为:
复旦留校学生来电悉,复旦设立,甚费经营,湘伯先生赴东,不久即归,断无停学之理,已禀督宪,竭力维持。望诸君努力勤学,以光学界。桐。
可能是受到学生、官方及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复旦校董会的立场出现改变。旋即,《中外日报》、《南方报》、《时报》等出现了以复旦公学名义发出的醒目大字黑体启事,表明复旦在积极筹建新校舍,并会正常开学:
本公学明年照常开学,并即行筹划建筑新校,敬此布告。复旦公学启。(48)
该广告旁边还附有《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启事,表明同校董及袁观澜的沟通获得效果,误会已经消除,各方会通力合作,停课问题得到解决,得以如此之原因,大家要牢记不忘:
明年停课问题,已由各校董主持撤销告白。昨仲辉、仲裕、叔和共谒观澜先生。先生躬自厚责,并多勖勉语。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系铃解铃,深感大德。前事已了,诸同学函电,不一一驰复。停课告白出诸意外,蒙沈凤楼、熊季廉诸先生函电筹挽回。曾少卿先生有一面开学,一面筹建筑,此校不成,将笑中国人不能办事之论。李登辉诸先生有倘因经费不敷,则教员愿减薪水,必竭力共争,不使学生失所之论。热心毅力,至可歌泣。我同学宜永志勿谖,力求进步。谨布告以慰远系。留沪留校学生公启。(49)
除登广告声明之外,复旦留校学生亦致电两江学务处总办沈凤楼,向其表示感谢,《中外日报》亦在“紧要新闻”栏刊载了这则《复旦公学学生致南京学务处电》:
南京学务处沈凤楼先生钧鉴:明年停课事,已由各校董和平商了,学生等同处惊风骇浪之中,纵遇极不平,不敢不委屈含忍,已电禀马师静待开学,仰蒙维持,敬电谢,并乞转禀帅座。复旦留校学生公叩。(50)
春节刚过,两江学务处即回电,表示官方的努力已有结果,原来复旦借住的校舍暂时不必搬迁,大家静等开学可也:
复旦留校生,现复旦新校未成,提镇行辕,暂缓迁让,已由督院电商杨军门,允再暂借,明正仍开校,望诸生勉力向学。桐。艳。印院代印。(51)
但此事还有余音,春节过后,复旦公学居然没有及时开学,一些同学遂发出函电质问复旦管理层究竟。于是复旦留校者不得不再发通告《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安抚大家情绪:
校务已公请熊季廉先生竭力主持,校长临行改定章程,亦已付印。诸同学来函,迫于公愤,自不免过激。在校同人,仍以暂时隐忍为宗旨,静待开学为义务。一切应行公告、学校函件,俟公决再刊布,不欲一时多腾口说,使得以嚣凌,藉口畏葸云云。非惟不甘,劳亦不能,愿勿过虑开学日期及预算表等,校中当即登报,请各少安,以续东装。敬布告,即希公鉴。留校同人公白。(52)
随后,复旦校方即刊出“复旦公学公告”,宣布延期开学时间及收费方案:
本公学展期于二十六日(指农历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即1906年2月19日,引者注)开学。凡旧生务于二十二以前到齐(迟到不留位置,有特别事故者须先函报)。本公学以屋舍不敷,一时势难增扩,设有徐(余)额,届时介绍选补,不再招考,远道已报名诸君,请勿跋涉。凡寄宿生,无论校内校外,概收洋一百二十元,通学生七十元(另一律缴校友会费两元,随学费分缴),细章已发刊并白。复旦公学启。(53)
开学一事尘埃落定,可两位校董曾少卿、袁观澜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却激化了。曾少卿在《南方报》上刊布声明,指责袁观澜渎职,有侵蚀复旦公款嫌疑:
奉书不一答,岂有所见怪耶?复旦开课不过三月,校费用至二万余金。捐款者欲知用法,所以三次奉函,请将帐籍交下,以便应人查阅,乃延不送来,且又不见一复。仅于年杪接学生叶景莱函,云已函达袁先生来淞取送,且有吴淞木行欠款三百余元,袁先生未清付,已出账,催索甚急等语。该校财政乃执事专责,钱由执事手支,账应执事手交,此乃天下通例。若以校务已辞,经手之账即可不顾,恐无如此办法,尊意云何?尚希明教。曾少卿言。(54)
袁观澜马上刊出答复,反击曾少卿的指责:
阅广告,知曾三次赐函,仆均未接到。复旦总核清册一本,已早交上,其余簿籍,均存淞校,叶君之函,亦未达,固不知公之促交也。一切出账之款,去年无不付清者,至所用二万零五百余元之款目,不但当报告助款诸君,并当以决算之数,请学界公览。(55)
看到袁观澜的回应和诿过于人,被牵连其中的叶景莱也立即登报声明,解释其中原委,表示事情起于信件未达的误会,个别事实的确如此,而非自己在其中的挑拨,暗中亦将矛头指向袁观澜:
十五日曾少卿先生告白催袁观澜先生交送帐籍中叶景莱函述云云,谨将详情声布如下:
廿五,景莱得少卿先生赐函(廿三付邮),嘱将校中帐籍送往。当即至淞检取,惟册籍纷如。会计张君又以总核册系前会计陈君经手,不详悉其中头绪,势不能冒昧径送,以致别生意见。故于廿六函达观澜先生取送云云。三十饬人投送。
木行欠款云云,则登报停学后,宝大木行曾屡至校催问,皆由阍人支吾答复。廿九晨十钟,该行汪沛云突至会计处询索。当时不得已,会计员即以十三已出账回复,呶呶而去。上少卿先生函曾附及,并言见观澜先生请提及,以时值年关,恐再催索也。
十五下午,至淞,询阍人冷桂,知少卿先生寄观澜先生三信均未由淞校转。
十六见观澜先生,云宝大款已于廿九午后清付,已商该行登报以祛人惑,并云曾信均未收到。景莱当即请观澜先生详询少卿先生寄信处所。观澜先生并言即将收支各款刊布云。景莱谨启。(56)
当事方之一吴淞宝大木行也一并登报声明:
昨阅《南方报》登曾少卿先生询袁观澜先生之告白,内有年杪接学生叶君函,云吴淞木行欠款三百余元,袁先生未曾付等语。查复旦修理所用敝行木料各价,概由袁先生付楚,并无欠款。特此声明。(57)
曾袁之争以此结束,袁观澜就此淡出复旦管理层,其掌管复旦财政的职位——“庶务长”一职,稍后由叶景莱取而代之。(58)
历经曲折后复旦终于正式开学,然而毕竟是借地上课,为长远发展计,复旦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建筑新校舍。鉴于此,复旦管理方就派代表到南京向江督周馥游说,《中外日报》以《复旦公学总代表来宁》为标题,报道了此事:
上海现办之复旦公学,公推马湘伯先生为校长,已有学生二百余人。其经费先由教员、学生倡捐,集有万金左右。唯建筑校舍,推广规制,需款浩繁。顷特举刘君郁之为总代表,来宁谒见江督,面禀办法,商请匡助,以维盛举。(59)
可能这次游说并没有取得好的结果,校舍问题一直困扰着复旦,直到辛亥革命后。
在这次的复旦开学风波中,以熊季廉、叶仲裕为代表的主张维持复旦正常运作的力量,依靠各方面的帮助,最后胜出,且推举熊季廉单独主持复旦校务。但实际上,熊季廉对于复旦的事务参与不多,因为他“于正月初四日(1906年1月28日)设席于九华楼,邀请同人集议校务。是晚,未及赴席,而腹痛大作,不图一病不起,竟于三月廿九日(1906年4月22日)晏然长逝矣”。(60)
三、“公立”与“官立”之争
爱徒熊季廉去世后,严复曾致信熊季廉之弟季贞,解释熊季廉为复旦事所累情形,其中对复旦校事评论道:“又复旦公学去年为索观澜侵蚀公款至数千金,反以此为学生罪,天下不平无过此者。季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维持复旦为己任。”(61)在该信里,严复还对复旦的内部矛盾和人事变动做了评述,认为复旦校董张謇、曾少卿等沪学会人士过多干涉复旦校务,原监督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携行李离堂矣”。眼下复旦公学大局岌岌可危,复旦学生在学长的“勉自榰柱下”,“幸团体尚坚,未即分散”,他们迫切希望能“得贤为之校董”。严复还向熊季贞通报了7月19日晚在愚园开会商量维持复旦的事情,表示会上大家都很思念熊季廉。
据郑孝胥日记的记载,7月19日晚,严复与郑孝胥、张元济往愚园赴陈三立(伯严)之约,商讨维持复旦公学的事情;会议参加者还包括复旦学生代表、庶务长叶仲裕(景莱)等人。(62)根据严复的描述,经过与会诸人的努力,特别是依赖与熊季廉关系密切、感情深厚的陈三立的奔走,大家集体化解了复旦“危业”,“为筹维持之术,既资以款,复为之解纷,使龃龉者无,遂至(止)于冲突。”严复还乐观相信,从此以后,复旦公学“当不至离散也”。(63)
大概正是在陈三立、严复等人的集体努力下,复旦大学获得了一宗实物捐助及三笔金钱资助,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据当时的一则《复旦公学广告》所言:
本公学蒙庞青城先生捐助物理、化学仪器十四箱,已照数祗领,敬此鸣谢。本公学因上学期经费稍有不敷,蒙陈伯严先生借垫洋一千元,顷又收到两淮赵渭卿都转筹拨库银二千两;江宁朱菊尊方伯筹拨库银三千两。除分别禀复外,谨登报鸣谢。(64)
复旦这里得到的款项,应该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周馥通过“扬州运使”划拨给复旦的,如郑孝胥的记载,“银二千两,乃南洋协助复旦公学之款。马相伯已不理复旦事”。此款是托郑孝胥转交的。(65)至于上引广告中所言的“库银三千两”,或系来自周馥的后续赞助。
在当时往往人去政息的情况下,周馥给复旦的拨款,继任江督就不一定会继续划拨。而此时周馥已经离任,新的两江总督由端方(1861-1911)接任(1906年9月初到任,1909年初调任直隶总督)。(66)端方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主张改革,“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67)
有此东风,在马相伯不堪重负而辞职后,(68)复旦公学干事员叶仲裕(叶景莱)、张桂辛等人希望端方能延续周馥的政策,继续给复旦拨款,在丙午冬(大概在1906年12月~1907年1月间),他们正式向端方提出申请,请求让与复旦有深厚关系的严复担任监督,官方并能为复旦拨款、添聘教习。(69)
而据严复自谓,端方对严复非常赏识与尊重,屡屡接见,还让其子拜其为师,甚至谦称自己也想拜严复为师。(70)故由严复继任复旦公学监督,端方乐见其成。12月6日上午,严复在南京首次拜会了端方,他与端方商谈了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条件——“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71)端方答应了严复的条件,向清廷上奏折,请批准每月拨给此时有175名学生的复旦公学银1400两(约二千元银元),“作正开销”。(72)端方还在1907年3月底致电严复,表示“复旦公学禀悉,经费每月由财政局筹拨洋两千元,即来宁具领。督院庚印”。(73)稍后,端方还派夏敬观和桂埴于三月初三日(1907年4月15日)前往复旦,调查有关情况。两人在该日上午视察校内外情况后,复入课堂旁听教员上课,午后三时,学校开欢迎大会迎接两人,两人相继登台演讲,“勉励周至”,晚上去计划中的复旦新校舍选地炮台湾视察,第二日两人又到学校,“详询一切,并嘱将经费收支表及学生名册、课程表等详细开呈”,以便“转禀立案”,向江督端方交差。(74)
由严复接任监督,得到了江督端方的任命与经费援助,也实现了复旦公学师生的预期要求。之后十四个月,复旦公学进入严复时代,这是一个复旦公学努力官办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有比较充足的经费挹注时期。(75)
可以说,自复旦公学肇建,就一直依赖官方的支持。到了1907年后,更是需要官方常年拨款,才能维持运行,监督亦需要官方任免,才获承认。故此,时任复旦监督的严复说:“丙午以前,复旦公学虽赖众擎之举,尚为私立之校。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已成官立之校。今昔性质皦然不同。”(76)
但一些学生对“官立”说法并不买账,他们公开批评严复:“反以官办二字之徽号宠锡我校,我校何幸得此?但不知我校之受官款津贴者,其体制为何如耳?”(77)这些学生反对“官立”的说法,并不能改变此时复旦的官办身份。事实上,倘若没有官方的这些津贴与拨款,“公立”复旦公学早就难以为继,甚或根本无法成立。学生们很可能只是把反对“官立”,作为反对严复继续担任监督,进而批评严复“溺职”的口实而已。(78)不过,显然,他们对于“公立”的坚持还是取得一定效果,从稍后于宣统元年(1909)公布的《复旦公学章程》中,即可看出官方对学生坚持的迁就——因为此时的复旦名义上并非“官立”学校,仍为“公立”:“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高等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由此研究泰西专门学术,底于有成,应定为公立高等学校,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79)可惜,这种“公立”只剩一种名义而已,“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已道尽这种“公立”的实质!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复旦公学在创办伊始,即已受到两江总督周馥及上海当局的极大关注与经费、校舍支持,后来更是经由江督端方的常年经费拨款才得以维系,校务也经常受到端方的干涉,一度学校监督都要由其委派。故此,这时的复旦公学虽然有着“公立”名义,可其实际地位同“官立”学堂几无差异,只是这种准“官立”的办学情况,对于当时复旦的生存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不能因其受到官方的介入,就轻易否定官方因素介入在当时的新式教育中所起到的一些积极作用。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复旦公学实际是马相伯、张謇等人集体发起创建的一所“公立”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其程度大致类似于今日的高中或中专,(80)而非“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81)这是我们在认识和书写复旦大学校史乃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时,必须要给予澄清的。
本文蒙匿名审查人指点斧正,特此致谢!
①参看张若谷编:《马相伯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第66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15页;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3月号,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②复旦大学档案馆所存清末文件中,现存可以看到的对复旦公学的全称到1910年还是——“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复旦公学一览表》,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4,第1页)。
③据江苏学务处的启事所言,当时上海学堂的办学性质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参看《江苏学务总会广告》,《南方报》1906年4月9日。1985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志》中也明确说复旦“是一所公立的高等学堂”,该书又根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列举了“官立”、“公立”、“私立”的标准:“由官府设立的名为官立,由地方绅富捐集款项、或集自公款的名为公立,由一人出资的名为私立。复旦完全符合公立规定。”参看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8页;又见《复旦大学百年志》,第19页。
④关于这些学生脱离震旦的原因及马相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马相伯事后曾有回忆,而当时不同媒体亦有相关报道,可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1935年10月31日),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1页;《震旦学院解散记》,《中外日报》1905年3月10日;《论江督令上海道扶助震旦学院之善》,《中外日报》1905年3月17日;冷:《宜合力助成震旦新学院说》,《时报》1905年3月11日;《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忠告震旦学生》,《大陆》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纪事”,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3~14页,唯《复旦大学百年志》所列《大陆》出版日期有误,应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905年3月20日);《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复旦大学集捐公启》小册子,目录号ZH0101-1,案卷号0001。
⑤冷:《宜合力助成震旦新学院说》,《时报》1905年3月11日。
⑥《江督与上海道往来电文(为震旦院生退学事)》,《中外日报》1905年3月20日。据马相伯后来回忆说,周馥因为是淮军出身,马相伯也同淮系和李鸿章有关系,故此周馥愿意支持马相伯。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1935年10月31日),转见《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1页。
⑦正在欧洲漫游的严复,“本有在沪组织一学校之意”,蒋维乔目睹震旦事件后,马上提醒张元济注意严复的这个志向,张也觉得“乘学生未散”的机会,的确是个不错的办学机遇,就“驰函”给尚在法国的严复,述说此事,希望严复能抓住时机,回来开办一学校,“以使震旦学生无所失”。参看蒋维乔:《鹪居日记》,转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⑧参看:《震旦学院之最近情形》,《时报》1905年3月31日;《杨军门札以行台假复旦学院》,《时报》1905年4月2日。
⑨《震旦学堂不日开课》,《中外日报》1905年4月11日。
⑩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张謇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二月二十四日(1905年3月29日)日记,第548页。
(11)像商人曾少卿即曾自谓为复旦募捐万金,“今年则提倡复旦万金。”《曾少卿致商学界书》,《申报》1905年8月9日。
(12)据当时报道,复旦选定在吴淞炮台湾皇宫大校场地建设新校舍,该地“本已筑成宽阔马路多条,南通淞镇,北通宝城,东至外滩马路,西即永清大马路”,已有复旦学生多名曾在此勘探,以备将来兴工,“将来此学堂造成,屋宇宽敞,操场广阔,可比诸南洋公学”。(《复旦学校改期开学》,《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胡适当年曾参观过规划中的炮台湾复旦新校址,亦认为“地址甚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胡适:《澄衷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3)冷:《震旦新学院之大局定》,《时报》1905年4月14日。
(14)吼:《忠告震旦学生》,《大陆》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纪事”,第2页。
(15)《江督批查复建设震旦新院拟请筹助经费禀》,《时报》1905年6月10日。
(16)《督批筹拨震旦新院学费》,《时报》1905年7月30日。
(17)《江督电询震旦、复旦两学堂之原因》,《申报》1905年9月5日。
(18)《震旦学院解散》,《时报》1905年3月10日。
(19)《震旦同学公鉴》,《时报》1905年3月27日。
(20)《详纪复旦、震旦交涉情形》,《时报》1905年7月22日。
(21)《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时报》1905年6月29日、《中外日报》1905年6月29日。
(22)《震旦学院第二次解散始末》,《神州日报》1907年10月9日。
(23)《徐家汇震旦学院》,《中外日报》1905年6月29日。
(24)《震旦学院招考》,《中外日报》1905年7月23日。
(25)《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7月22日;此广告亦见《中外日报》1905年7月23日。这些广告在报纸上都是多日重复刊登的,下同。
(26)《复旦公学宣统二年下学期一览表》,第2页。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4。此档案是马相伯于宣统二年正月重回复旦任监督时所编写,表明马相伯也应该认可这样的提法。引者注。
(27)参看拙文《严复与复旦公学》,《历史研究》2009年4月号。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目前又对该文进行了大规模修订。
(28)《复旦改期开学》,《申报》1905年9月2日。
(29)霜:《吴淞水灾记略》,《南方报》1905年9月6日。
(30)参看《复旦公学特别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复旦公学开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学务汇录·复旦公学改期开学》,《中外日报》1905年9月3日。
(31)《复旦公学开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0日。
(32)《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4日。
(33)《淞沪铁路启》,《中外日报》1905年9月14日。
(34)《记复旦公学开校典礼》,《南方报》1905年9月15日;《复旦公学开学记》,《时报》1905年9月15日。
(35)两电均见《中外日报》1905年9月18日。
(3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册,第1018页。参看《张謇日记》,第560页。不过张謇该日日记没有记载去复旦参观事,只记了几人一起去视察了“渔业会所”。
(37)《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19页。
(38)《同学诸君公鉴》,《时报》1905年3月12日。
(39)参看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转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第16~17页;参看《马相伯年谱》,第215页;又可参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正月至八月)》,台北:“国史馆”,1987年,第687页;赵聚钰:《于右任谈复旦创办》,收入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0)《南方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
(41)《中外日报》1906年1月14日版。
(42)(43)《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5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5日等期。
(44)《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时报》1906年1月16日;《中外日报》1906年1月16日。
(45)《时报》1906年1月17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1月17日等期。
(46)据《中外日报》后来的报道,马相伯“去岁(农历,引者注)奉玉帅委,赴日本调停留学生退学事,今岁三月间始回沪。”《复旦校长上兴学条陈》,《中外日报》1906年5月23日。此次取缔规则事件发生在1905年12月中旬,所谓“自日本行取缔规则后,留学生大起风潮。”(《咨送留学生人数表格》,《中外日报》1906年6月19日。)在陈天华跳海死后,被建构为因“取缔规则”而死,事件迅速升级,“一时人心大震动。”(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28~529页。)复旦公学学生也很关注此次事件,曾在报上刊登广告和致电南京,主张集思广益,团结对外,寻求解决之法。参看《敬告主持学界诸君子》,《时报》1905年12月17日;《规正同盟停学事》,《时报》1905年12月27日。马相伯等是1905年年底受周馥委派,于1906年年初赴日,意图在“安抚三江留学生,劝令照常上课,勿附和罢学归国之议”。参看《江督派员赴日安抚学生》,《中外日报》1905年12月31日;《纪苏绅莅宁劝谕学生事》,《时报》1906年1月5日。马相伯大概四五月之交回国(农历三月)后,随即去上海会见江督,讲述在日本情形,并以复旦校长身份给江督周馥上条陈。《复旦校长上兴学条陈》,《中外日报》1906年5月23日。有关此次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斗争及马相伯的一些活动情况,可参看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77~407页。
(47)《中外日报》1906年1月17日;《时报》1906年1月17日。
(48)《中外日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南方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
(49)《中外日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时报》1906年1月19日等期。
(50)《中外日报》1906年1月20日。此电《时报》1906年1月19日亦有刊登,唯报道标题误作震旦学生——《震旦学生再电江苏学务处》。
(51)《两江学务处致复旦公学电,为复旦仍旧开校事》,《中外日报》1906年1月28日;《南京学务处致复旦公学电》,《时报》1906年1月28日。
(52)《时报》1906年2月1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2月1日等期。
(53)《时报》1906年2月4日等期;《中外日报》1906年2月4日等期。
(54)《袁观澜先生鉴》,《南方报》1906年2月9日等期。
(55)《袁观澜敬答曾少卿先生》,《南方报》1906年2月10日等期。
(56)《声明》,《南方报》1906年2月11日等期。
(57)《吴淞宝大木行声明》,《南方报》1906年2月11日。
(58)大概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叶仲裕接任袁希涛(观澜)担任复旦公学庶务长。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目录号ZH0102-1,案卷号0010,第8页。必须说明的是,这份档案所收教职员名单并不完整,且各教职员任职时间也不尽准确。如第16页说张汝楫是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入校,即误。张1905年10月即为复旦教员了。参看《请究火车美兵驱逐华人电》,《申报》1905年10月4日。
(59)《中外日报》1906年3月5日。
(60)《追悼会员》,《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第38页。
(61)《与熊季贞书》(1906年7月20日),收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62)《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49页。
(63)《与熊季贞书》(1906年8月5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278页。标点略有更动。
(64)《中外日报》1906年8月20日等期。
(65)参看《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50页。郑孝胥是在1906年7月23日日记中记载此事的。
(66)参看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册,第1501~1503页。
(67)吴庆坻:《端总督传》,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9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页。
(68)根据马相伯自谓,他在1905年底即不实际参与复旦事,实际辞职时间或在1906年年末:“复旦公学去秋开校至年终,仆于银钱言定不问不用,所有修屋置器及教员俸等九千余两,均由曾少卿先生津贴,理当代为鸣谢,今年校事一切均未过问。马良启。”“马相伯通信处”广告,《时报》1906年11月18日。马相伯任内,应该还存在教员欠薪问题,据《申报》后来的报道,曾有在复旦任教的西洋女教习控告监督马相伯欠其薪水三千金。参看《教员追索束脩》,《申报》1907年4月14日。
(69)根据《叶景莱启事》所言:“自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年经费后……”参看《叶景莱启事》,《申报》1908年2月10日。
(70)《与甥女何纫兰书》(八)(1906年12月6日),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32页。
(71)《与甥女何纫兰书》(八),《严复集》,第3册,第832页。
(72)参看端方:《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江宁学务杂志》第5期(丁来年七月十五日[1907年8月23日])、《四川教育官报》丁未第9册(1907年10月)(第4页)、《北洋官报》丁未第1453册(第3~4页);该折又见《端忠敏公奏稿》,第1007~1009页。马相伯年谱编者认为此拨款来自马相伯的努力,为误,此拨款主要是来自时任复旦监督严复的努力。
(73)《江督端致复旦公学电》,《中外日报》1907年3月26日。
(74)《江督派员考察复旦公学》,《申报》1907年4月18日。
(75)参看拙文《严复与复旦公学》,《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6)《严复启事》,《时报》1908年2月12日;《中外日报》1908年2月12日。1909年初送去立案的《复旦公学章程》起首也言:“本公学由各省官绅倡捐,并蒙两江督宪奏准,辅助常年经费,檄拨吴淞官地……”《咨送复旦公学厘定章程请核转详准予咨部立案由》(宣统元年),第1页,上海:复旦大学档案馆藏,ZH0101-3。
(77)《神州日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时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中外日报》1908年2月17日等期。
(78)后来中国公学亦曾面对相似的情形。1908年11月17日,中国新公学诸人来找郑孝胥,“言公立之中国公学不应改为官立事。”郑孝胥立即从官方立场驳斥之:“如学生能自筹费,不借捐款、官款则可;今‘公立’二字久已卖却,复何言乎?”见《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66页。
(79)《咨送复旦公学厘定章程,请查核转详准予咨部立案由》,ZH0101-3,第1页。
(80)如复旦公学1905年8月的招生广告所言:“本校学程现定预科四年(一为实业专门之预备,一为政法专门之预备,期可直接大学),专科二年。”参看《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8月18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81)参看田正平、陈桃兰:《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创建考辨》,《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