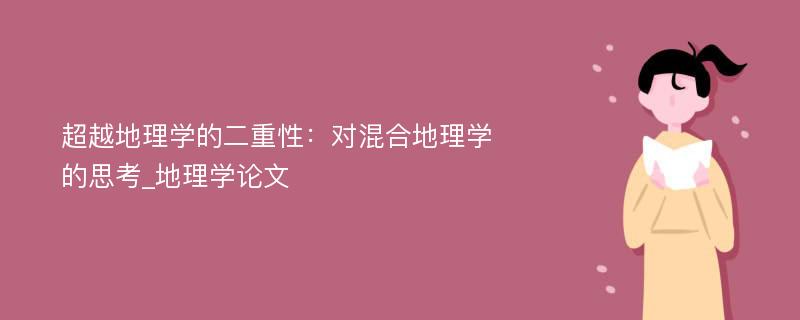
超越地理学二元性:混合地理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0/dlkxjz.2013.09.001
修订日期:2013-08.
1 引言
20世纪的地理学在诸多思潮的争鸣中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各种理论视角在不同时期相继涌现、此消彼长,但其过程往往伴随着尖刻的批判,特别是有关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往往会蜕化成顽固的对立话语(Martin,1989)。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学家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不同的学科传统或领域,而这些学科传统或领域通常被视为互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冲突的。
在此背景下,20世纪的地理学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并对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一次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裂,起源于地理学中的“自然”与“社会”的本体论分离(FitzSimmons,1989;Hanson,1999;Massey,1999,2001);另一次是“社会—文化”地理学(social-cultural geographies)与“空间—分析”地理学(spatial-analytical geographies)的分裂①,发生在人们尝试建立一种脱离实体的地理分析模式的过程之中,试图将空间模式和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相分离(Sack,1974;Soja,1980;Gregory,1981;Sayer,1985;Rose,1993;Brown,1995)。
这次分裂以及后续的来自各种批判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质疑,使得“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愈发被理解或表述为地理学不相容的两个领域(Gould,1994,1999),人文地理学家分化为社会理论家和后现代学者,以及空间分析学者、定量研究者和地理信息科学学者两大分支。尽管批判社会理论和计量方法已经被当代地理学广泛接受,但在“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传统之间建立联系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困难。虽然不少学者关注地理学内部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之间的分裂,并且开始思考一些其他的选择,或者强调计量方法在批判理论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如Pratt,1989;Lawson,1995;McLafferty,1995;Barnes et al,2001;Plummer et al,2001;Sheppard,2001;Kwan,2002c;Schuurman,2002),但是,这一分裂似乎已经难以弥合,甚至在多次极端的争论中得以强化,从而导致了两类地理学家之间的冷漠相向。
作者认为,地理学家有必要正视这一分裂,因为它可能对新世纪的地理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寻求沟通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的可能性,首先探讨地理学中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之间分裂的原因,然后探索“混合性”的理念在缓解学科极化趋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思考如何运用“混合性”来协调不同地理学家和地理学的立场,并简要总结混合地理学已有的实践;文章最后将对以“混合性”为基础的、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进行展望。
2 混合地理学的背景
2.1 地理学“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的二元性
在20世纪,为了把地理学表述为统一的学科并提高其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地理学家曾多次尝试为本学科提出一个一应俱全的视域(vision)(如Schaefer,1953)②,其中的重大事件包括宣布前一阶段的地理工作“毫无价值”,宣称将创造一些更好的、更有挑战性的事物,以及声称只有唯一正确的地理学研究方式等(Hannah et al,2001;Wyly,2004)。新视域提出之后,往往发生认识论上的理性化,这意味着有关认识论的论证在新观点中并不是必要的、关键的部分;但它们却在新视域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分裂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Barnes,2000)。
在地理学新视域的形成中,往往会发生一个“纯化”的过程,即与之不兼容的观点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杂质而从地理学研究实践中被剔除(Latour,1993;Sibley,1995)③。“纯化”的过程意味着地理学为了满足提高学科地位的迫切需要而失去了观点的多样性(Johnston,2000a)。这是地理学新旧观点对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一系列关键人物和事物④构成的强大行动者网络有力地推进了地理学新门类、新领域的出现(Barnes,2001,2002)。在这一背景下,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与边界很可能在新期刊的创立、各协会中新研究小组的成立等制度性过程中被僵化,从而加剧了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理学家被划归为“立场对立”、“非此即彼”的不同领域(Massey,2001)。
在地理学家努力宣扬某种理论视角的过程中,相对更加包容和温和的观点被忽视了(Kwan,2002b)。虽然这些声音有助于协调冲突观点并渲染和睦气氛,但观点之间的差异和边界却在一些因素(如不同领域之间极端化的争论)的影响下被顽固地强化(Wyly,2004)。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学科逐步走向“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之间的二元分立。
2.2 学科统一性的谬误
从数十年的对立与争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用一个单一的学科视域建立地理学的统一性、提高学科地位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纯化”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而地理学的研究实践远比人们认识的更为多元(Gober,2000;Hubbard et al,2002;Blunt,2003;Johnston,2003)。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对地理学发展过程和演进路径的认识可能有所偏颇。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理学学科的演进历程。当前我们对学科发展的认识很可能是受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影响⑤(Kuhn,1962)。库恩将学科的发展理解为观点的更迭,认为一个观点战胜另一个观点是学科发展的常态,主张新旧观点之间泾渭分明,提倡单一学科视域的主导性(如Chorley et al,1967)。或许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对我们学科的影响是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强调观点的演替以及对不相容的旧观点的排斥,这些认识使得新观点的提倡者倾向于与旧观点的持有者划定界限、互不相容;而与此同时,地理学鲜明的多样性特征难以在他的理念中体现。
由此可见,库恩的科学革命观似乎并不适用于地理学这类有多种观点和方法论同时存在的学科。与之相比,将地理学观点与研究实践的变化历程描述为“传统观点与新观点融合、交叠、共生,从而创造出更为复杂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似乎更为妥当(Heffernan,2003)。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综合,在发展过程中,学科本身及其各领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如Gregory,1994;Fischer et al,1997;Moss,2002;Poon,2003;Oberhauser et al,2004;Warf,2004)。相比于追求学科的单一性而言,保持观点的多样性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开放与沟通,似乎是提高地理学学科地位更为可行的策略,因为这些不同的领域对于学术界不同部门以及不同的资助机会而言有各自的吸引力,并且可以在跨学科活动中相互促进⑥。
2.3 超越认识论决定论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认为,保持地理学多元观点共存、增进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的沟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在两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有效方式。事实上,在不久之前,科学方法一直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手段而不是压抑进步的工具,而近期对科学的批判也“并非认为科学研究毫不重要”(Hannah et al,2001)。另外,Haraway(1991)的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也强调了现代技术科学在妇女解放中的作用(Kwan,2002a,2002b)。上述事实意味着,当前的空间—分析地理学的科学技术特征并不会排除其与社会—文化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尽管两者之间的一些基本差异将会限制其相互结合的程度(Sheppard,1995)。
为了寻找沟通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的方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地理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许多历史回顾表明(如Morrill,1993),计量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但往往被忽略的方面是定量方法被提出并被实践后的认识论论证。Barnes(2000)认为,大卫·哈维等地理学家转向实证主义的过程(Harvey,1969),实际上反映了计量方法事后的理性化。通过仔细的历史考察可知,空间—分析地理学的认识论论证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地理学实践,而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方法没有必然的联系⑦。与此相似,GIS在成为科学地理学新的基础方法之前早已存在(Openshaw,1991),而GIS的使用并没有要求任何预先的认识论论证。可见,技术本身并不会将使用者限定在某种认识论当中(Goodchild,1995;Wright et al,1997;Kwan,2002a,2002b)。
因此,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Bennett,1985),我们不能仅仅从地理学家使用的方法中推断出地理学家的认识论和立场。定量和GIS的空间分析可以用于非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同时定性方法也可以用于实证主义的研究之中(McDowell,1992;Suchan et al,2000;Sheppard,2001)。显然,有了这一认识后,社会—文化和空间—分析之间的选择就是个伪命题(Wyly,2004)。也许我们陷入了将方法论与认识论混为一谈的陷阱之中(Lawson,1995),而几十年的争论和二元对立的观念留下的集体记忆束缚了我们沟通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的想象力。另外,我们还有必要认识到认识论理性化的事后性并不意味着这些论证不重要。相反,作为一种对研究实践的基础理论的系统思考,它们可以为新词汇以及理性化的其他选择的形成提供借鉴,从而帮助沟通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
3 混合地理学的概念与实践
前述了对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产生原因的思考。作者认为,保持地理学观点的多样性、促进不同领域的沟通是提高地理学学科地位的更好的策略。地理学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在不同领域中都可以发挥作用。下面将考察“混合性(hybridity)”的理念以及在超越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中所具备的潜质。
混合性在文化研究中表现为对个人属性(如性别、种族和国籍)固定和刚性分类的反对(如Bhabha,1990;Young,1995;Mahtani,2002)。它也被用于超越那些将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经济与文化设定为相互独立、不可渗透的两部分的二元构建(如Latour,1993,1999;Haraway,1997;Murdoch,1997;Whatmore,2002;Wolch,2002;Forsyth,2003;Warf,2004;Barnes,2005)⑧。混合体(hybrids)在不同部门之间“穿梭”、将它们沟通,“超越并取代二元性的边界,并由此产生在本体论上的新事物”,进而“导致某种二元性对立的消弭”(Rose,2000)。在混合化(hybridization)的过程中,被视为不可兼容的、相互冲突的元素能得到有效的整合。
在本文中,混合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是指超越二元对立的边界,促进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相互沟通的地理学研究实践(可以称之为地理学的“跨境工程”)⑨。混合地理学通过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在不同领域中的混合使用,实现对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隔阂的超越并形成更有洞察力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混合地理学的实践要求地理学家思考以下问题:定量方法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应用到基于批判社会理论的研究中,或者如何考虑居民的生活经历?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如何在定量分析中被强调?定量方法如何考虑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质性材料如何与量化数据相结合?目前,已有许多地理学家围绕上述部分问题开展了混合地理学的某种形式的实践。
第一类也是最常见的混合地理学实践,是使用定量或GIS方法来强调批判地理学的研究议题(Kwan et al,2009a,2009b)。例如McLafferty等(1997)运用1980年和1990年的调查数据,量化分析了纽约都市区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女性、种族差异变化在通勤时间上的表现,以此强调批判地理学所关注的性别、种族议题;Wyly(1998)使用1990年美国所有大都市区的数据,应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地方化通勤和职业性别隔离的关系,试图定量探讨女性就业中的空间制约效应。近期,复杂理论、基于代理人的理论、地理计算以及地理可视化得到发展,使得面向城市/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定量研究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如Bergmann et al,2009;Hamilton,2009;Strauss,2009)。
第二类形式的混合地理学试图将地理空间技术(GIS与GPS)与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生活经历的定性理解相结合。这一类混合地理学建立在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GIS可处理的信息类型不断扩展的技术基础上。例如,电子照片、视频、音频等非量化素材可以链接或加载进GIS中;质性研究中常用的手书、手绘地图和其他通过深度访谈及民族志方法采集的草图也可以通过某种形式载入GIS中。可以说,这是通过GIS等地理空间技术与质性材料的结合而形成的混合研究方法,试图探索在知识、权力和社会与政治变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多重现实与故事(如Parks,2001;Pavlovskaya,2002;Cieri,2003;Jiang,2003;Nightingale,2003;Bell et al,2004;Kwan,2007,2008;Kwan et al,2008,2011)。
第三类混合地理学试图整合批判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方法。例如,近年来作者一直在进行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和基于GIS的地理计算与可视化方法的交叉研究,包括开发相关GIS方法再现个体在日常生活的活动—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如Kwan,2002a;Kwan et al,2003,2004)。作者在GIS和批判社会理论中“穿梭”,并且它们在作者的研究中相得益彰,使得基于GIS的女性理论以及批判GIS的实践成为可能。
除上述混合地理学实践之外,混合性还可以置于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之间的其他位置,以减少它们的二元性特征。混合性流动的特质可以在两种地理学传统之间创造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另外,发展新词汇和隐喻(如“批判GIS”或“批判空间分析”;Schuurman,1999;Barnes,2005)将有助于促进两者之间的联动,并允许地理学家同时成为“社会理论者”和“空间分析者”,从而改变过去对地理学家的二元分类方式。
4 结语: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
综上,本文提出有关地理学“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一些未来思考⑩。所谓“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是指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不再相互冲突、二元对立,地理学的发展将不再被不必要的隔阂或模式化印象(如“后现代主义者”、“定量主义者”或“GIS者”)所羁绊。
作为一门学科,地理学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保持观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同时,提升其在学术界与社会中的地位。用单一的视域取代不同的观点以提升地理学学科地位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使地理学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学科的同时,不抹杀学科中的差异性。我们需要接受不同观点,允许它们同时进入有建设性的对话中(Cloke et al,1991)。我们应该更多地聚焦在理解它们的差异、探索它们如何沟通以及相互促进上。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克服想象的和现实的隔阂也许是未来地理学最重要的任务。
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是理解混合性的重要例子。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题是开展跨越文化、空间和社会位置的研究(11),这加强了我们对于超越社会与地理边界、协调不同的对象与差异的理解能力(如Valentine,2002)。通过跨国身份与混合文化等主题的研究,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了对“跨越各种隔阂”的各种复杂话题的有效洞察方式(Staeheli et al,2002),这与地理学的未来尤为相关。
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地理学的演进动态。上文提到,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并不适用于地理学这类视角与方法高度多元化的学科。相反,基于主题网络的演进模式也许能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框架。主题网络跨越了不同的领域,能灵活地重组以应对外部变化(如社会变化或资助机会),并兼听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声音。可见,这种基于主题网络的演进模式或许有利于改善学科极化的趋势。
不同领域之间辩论的态度会继续对未来地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地理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促进团结。在促进学科沟通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世界性宽容(cosmopolitan tolerance)”(Cosgrove,2003)与“求同存异(differentiated solidarity)”(Young,2000)的理念:前者由丹尼斯·科斯格罗夫在对文艺复兴的宇宙学的思考中加以定义,而后者由伊利斯·杨提出,作为一种解决居住分异问题的理想方式。两种概念都强调适应差异的需求,保证个体自由,允许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同时通过更大背景下的宽容和相互尊重来维持群体的集体性。如果像这样的想法能够在地理学研究中付诸实践,那么地理学的未来将会有新的面貌。
最后,我们有必要培育一种超越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定性与定量、批判性与技术性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二元性的混合体(或第三类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诚如是,地理学的未来将不再“非此即彼”,而将“协同共进”(Barnes et al,2001)。
致谢:本文是在作者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总结而成,部分内容是基于Kwan(2004)的修订、更新与整理,对帮助整理中文内容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陈梓烽、塔娜同学表示感谢。
①本文中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是指强调场所、人的经历、社会生活的质性理解的批判性和诠释性视角;“空间—分析地理学”是指采用定量和GIS方法分析空间模式与过程的视角。这一分类方式没有考虑地理学科“内部”的分歧(比如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考Kobayashi等(1989)。
②例如,Schaefer(1953)曾阐述“空间关系是地理学唯一重要的议题”。
③例如,Gould(1979)将地理学“计量革命”比作“奥革阿斯时期(Augean Period)”,比喻对20世纪早期的传统区域地理学的纯化、清理过程。
④例如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Harvey,1969)。
⑤需要强调的是,对地理学产生影响的是地理学家对库恩研究的理解和运用,而不是库恩的研究本身。请参考Mair(1986)关于库恩的研究如何在地理学中被误读或误用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科学变化的主观性与劝说性,以及作为“行为准则”而非哲学与理论的规范表述的库恩范式的理论。
⑥参考Driver(2001)和Marino(2002)关于地理学人文传统的地位提升的论述。
⑦空间—分析传统的地理学家对于科学以及定量方法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上有不同的观点(Taaffe,1993)。例如,《地理分析》(Geographical Analysis)期刊的四位前任编辑——迈克尔·古德柴尔德(Goodchild,1995,1999)、埃米里奥·卡塞蒂(Casetti,1999)、威廉·克拉克(Clark,1999)和雷吉纳德·戈里奇(Golledge,1999)——的观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卡塞蒂(Casetti,1999)的论述特别有趣:“我们需要记住:那些反对科学及其主张、角色、有效性与影响的声音会引出一些话题和主题,这些话题和主题需要被强调,以重新定义科学、改善科学。”
⑧参考Rose(1995)和Mitchell(1997)对于这一概念的批判性的评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文地理学内部的根本差异或不兼容性可能难以完全消弭,因此“混合化”在人文地理学中作用有限。另外,除了混合性以外,还有其他可能有效的策略,例如,珍妮弗·沃尔什(Wolch,2003)的“极端性开放(radical openness)”的概念既没有提出“大综合”的目标,也没有倡导单一视角的主宰或方法的演替。
⑨混合性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隋殿志(Sui,2004)曾讨论的“第三文化”的概念相似。他认为,“第三文化”是指“艺术和科学中的创新理念的协同与相互影响”。读者也可以参考Gilbert(1995)和Woodward(2001)关于跨越科学与艺术边界的论述。
⑩作者注意到那些为地理学建立视域的相关话题(例如Sayer,1999;Gregson,2003)。作者在这里仅表达一些个人的思考,并非尝试为地理学建立另一个“一应俱全的视域”。
(11)可参考Nast(1994)、Gilbert(1994)、Nagar(2002)、Mountz(2002)、Pratt(2002)、Raju(2002)、Silvey(2002)、Staeheli等(2002),以及Valentine(2002)。
标签:地理学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文化地理学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地理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认识论论文; 社会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