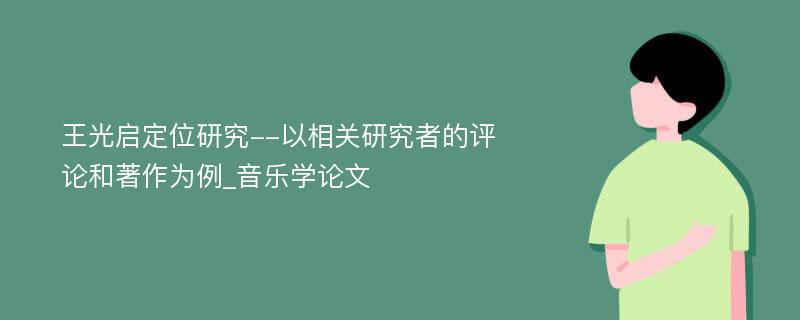
对王光祈定位的研究——以相关研究者的言论及著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为例论文,研究者论文,言论论文,王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0)04-0072-06
王光祈的研究,如果从1959年开始算起,已历经半个多世纪(51年),其间的研究成果已呈汗牛充栋、叠床架屋之势,但对王光祈“定位”——定性研究的专论,却极为鲜见。本文试图集吕骥等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后来者言论于一炉,反映历史中的一段“真实”。其中跌宕起伏的变化,映衬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前行脚印”。
一、延安定调
对“王光祈研究”而言,吕骥在《新音乐运动》[1]的“引论”中,首先将王光祈归为“新音乐运动”的一员。其次,在对“新音乐性质”的归纳中,认为他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介绍了许多西洋(的)东西”[1](第1页),并把他称作:“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在音乐的观点上,有比萧友梅更为进步的意义,即王光祈不是全盘西化论者,而是吸取西洋的血液,复兴中国之礼乐,并主张人应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在思想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倾向”[1](第11页)。吕骥在这一时期对王光祈的定位突显了三个关键词:“狭隘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改良主义”。以上三词,第一个涉及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方针、路线中的古今关系,但由于王光祈是在参照了西方文化之后的立论,故已不仅单纯为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要在借鉴西方音乐文化前提下的发展,但对其定义的基调是“封建复古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后两个则是一种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对非党人士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定性。
吕骥当时所处的时期与地点,是中共未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处于“第二次合作”(1937-1945)并共赴国难——即抗日战争时期中的解放区。故此,他的“王光祈定位”,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意识色彩①。对比这三个关键词,“改良主义”是温和与中性的,“民族主义”对“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而言,是狭隘的。所以这种定位在当时有其历史、阶级及政党的鲜明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利于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第977页)[3]之方针,并具有排他性。
二、新中国之初
因吕骥1949年后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②,其特殊的身份对于新中国初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写(尤其是对于王光祈的定调)来说,不可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在1959年为国庆10周年而组织策划的向新中国献礼丛书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写作提纲》[4]中,虽然使用了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史小组的集体名义,但仍然明显流露出吕骥影响的痕迹,如该书之第四章第三节:“国乐的搜集与整理。王光祈等在民族音乐方面的工作”中,在“对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的介绍”的第一句话,即有“王光祈的改良主义思想”[4](第29页)之语,并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定位为:“企图通过国乐来‘恢复民族特性’以唤起中华民族的复兴。”[4](第29-30页)这段文字明显受到吕氏观念的影响,对之持有较明确的否定态度。但同时对以国乐甚至礼乐复兴中华民族的特性及唤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作了“正确”与“错误”的两面分析。即认为王氏主张发扬国乐,要“利用西洋科学方法”,及国乐“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思想是正确的。但“秦腔二黄小曲时调……只是一些浅陋冶荡之音”,中国“简直可以说没有国乐”等观点,则是错误的。并冠之以“民族虚无主义”[4](第29-30页)的大帽子。
该文较之前吕氏观点略有进步的,是对王光祈“狭隘民族主义”的定位有了改进,对王光祈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其国乐理论方面如中国乐制、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戏曲、中国记谱法等研究及其研究的特色,中西音乐的相互比较对照等方式方法,则给予了首肯。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年,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拔白旗”等政治运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意识的逐步深化,在这一较为敏感的时期内,对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阵营”的王光祈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进步,就是对其“正、反”两个方面做了具体区分。另外还在组织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的浩大工程③中,注意搜集了王光祈的各方面资料,由此产生了由冯文慈主编的“王光祈有关资料”[5](第237-337页)之资料大全。其中包括冯文慈编写的“王光祈年表及全部著、译目录”、“王光祈旅德西文著作十八篇存目”、王光祈非音乐类论文数篇,及王光祈逝世后,他生前友人在《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中文章的选录,这些均使我们得以领略相对完整的王光祈“原貌”。这是后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王光祈的基础材料。也可说是在吕骥所领导下的中国音协,为“王光祈研究”办的一件大好事。
但当时对王光祈定位上所存在着的偏狭态度(如:狭隘民族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音乐家等),对以后王光祈的研究,不可谓没有影响。
三、发展中的史学观
(一)20世纪60-80年代
这一时期的相关学术论著及教材里,也包含有受到上述吕氏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初稿)》(1961)[6]及《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63,俗称“小白本”)[7]一书为例,在对王光祈的“和谐音乐观”、“儒家音乐观”进行批判之时,该书认为“这正反映了王光祈早年受封建文化熏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及其反对政治斗争的改良主义思想”(按: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6](第98页)。可以说,这是对吕氏“狭隘民族主义”的实质即“封建复古主义”及“改良主义”等于“反阶级斗争”论点的进一步明确。而对王光祈音乐美学、特别是王氏音乐本体论的评判,一方面评价较低;另一方面也带有将其斥之为“改良主义”的影子:
他(指王光祈—引者)的论著中对音乐的本质与社会作用的解释,也错误地一再强调要发扬音乐的“谐和精神”、以及复兴所谓礼乐结合的“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实现救中国之利器……由此可知,在他的音乐思想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思想影响,并且它们与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观点结成一体了。[7](第39-40页)
如影随形的“改良主义”,成了对王光祈评价的关键词。这明显是“阶级斗争论”及其衍生物——以阶级斗争之锋芒尖锐与否来衡量一切的音乐史学观所导致的,所谓“谐和精神”及“封建文化”不足以成为“救中国之利器”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是“当然之论”。这已然成了该时代使然的“集体无意识”。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小组的论著中,也再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相同话语:
王光祈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进步的与倒退的、民主的与封建的、科学的与唯心的倾向,全部都是他本人充满了矛盾的政治思想的反映。王光祈的政治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这一范畴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封建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都兼而备之。[8](第21页)
其加之于王光祈头上种类繁多的帽子,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光祈的“吕氏定义”之“小资产阶级”代表,也升格为“资产阶级”,这是“左”的思想在当时音乐史学界中的突出反映。并且,对不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音乐家、理论家的批判势头已悄然形成。但同时必须指出,当时这类论著中,立论最为扎实、史料最为充分的,是冯文慈、王东路、崔其焜等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第二编[9]。虽然其中也有对王光祈“改良主义”的评论,如对于王光祈“社会改良要循序以进,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循序之奋斗”以及组织“工读互助团”等“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等观点,被认为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实质上还是逃脱不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老路。此外,王光祈走学术之路而不问政治,声称不属于任何党派,不赞成内战,希望一致对外。这些虽属爱国的思想,由于没有阶级倾向,同时也由于其对红军的报道中,包含了将红军的武装斗争描写为“蹂躏数省,民不聊生”的字句,而被认为“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不通之路[10](第96-97页)。以上虽是依各种旧报文章对王光祈的言论进行的摘抄,并较真实地反映了王氏的历史言论原貌,但在当时无疑是冒(政治风)险的行为。由此当事人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真正有人站出来为此申辩,则在25年之后[11](第33页)。而对王氏“反动”的批评,也显露出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必然——即“时代”(50年代)语境(context)中,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实话实说”历史唯物主义之侧的真实历史动向。
与此同时,该书也比较客观地认为:王光祈是以“比较音乐学的角度”并“创用‘调子音阶组织’的分类标准来研究中外各种乐制”的第一人。他的“音乐物理学和西洋乐器法”等著作的出现,在当时均为中国人运用西方新学术观点、方法的最早著述。在乐律研究方面,王光祈“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比前人阐述得更为精确”。在研究音乐史的方法论上,“最早提出要注意研究‘环境背景以及无名英雄’(按:即非主流音乐家)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以及实际的音乐作品,而不要脱离实际仅注意几个大作家,或老在音乐材料之中找生活,以及脱离实际作品,只偏重于纯理论的律和调的研究”等,是“可贵的意见”,并说:“即使在其著作中有较大的缺憾……(但)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在音乐理论上的贡献,他全部著述终归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甚为可贵的遗产。”[10](第100-101页)
笔者认为,以上归纳,突显了王光祈研究方向的三层意蕴:⒈以比较音乐的角度研究中外音乐;2.注重音乐文化环境与音乐的关联,不再就音乐而论音乐——自律论,而更注重音乐以外的多种因素,故是明显的他律论,同时也不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3.注重非主流音乐家的研究。王光祈的研究预示了以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一些重大趋势,即在文化中研究音乐(study music in culture),把音乐作为文化研究(study music as culture)。把研究视野,拓展到西方专业音乐以外的无文字传统民族的音乐、非主流社会的音乐、甚至下层普通民众的音乐之中去。而王光祈研究项目各类的本身,大都属于历史音乐学研究,故他的研究,也是日后获得极大发展的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的雏形与先声。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4年6月,因中国音协主席吕骥的支持与倡议④[12],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王光祈研究学术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联合主办)上,吕骥认为:
王光祈逝世已经四十八年了,然而音乐界对他的工作,还没有全面清理过,过去倒是有些对他不公平的评价,因此更加使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次集中地研究,全面介绍他的工作,对他作出公平的符合实际的评价。这不只是对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我们过去的理论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能否作出恰当的总结,这也不只是对过去的工作的认识问题,也是检验我们今天的理论工作是否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强调的、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前发展的问题。[13](第8页)
而吕老所说对王光祈的历史功绩、贡献还没有进行的“全面清理”及加之于他身上的“不公平评价”,当时便集中体现在1981年交稿,1984年才得以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4]——这本基本延续《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63)主要精神的教材中,其长期对王光祈“和谐说”、“儒家音乐观”——即封建主义文化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及王光祈的“改良主义”等于“阶级调和论”的基调原封未动:
在他(王光祈—引者)的音乐思想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思想影响,并且它们与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观点结成一体了。[14](第56页)
理论形势及研究观念上的突变,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权威教科书”中对王光祈评价的“依旧如常”形成的巨大反差,居然与“全面清理”王光祈历史功绩的伟大学术研讨会,发生在同一年,令我们不得不对舆论的先行,与实际“清理”工作的滞后,表示由衷之感叹!就在这次会议上,赵宋光认为:“在前些年,二、三十年来吧(按:如以“三十年”计算,应自1954年以来),在王光祈评价中有两个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复古主义。我想,今天对这两顶帽子是应该清理的时候了。”[15]这是广大音乐研究者的心声,也是我们对踽踽独行、筚路蓝缕、开启中国音乐学研究之“山林”的伟大先辈王光祈的历史责任。之后1992年及2002年,两度召开的纪念王光祈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都)、110周年(暨首届光祈音乐节,成都、温江)学术活动中,以黄翔鹏在第一次会议(1992年9月11日)中,对加之于王光祈定位中“封建复古主义”(按:此涉古今关系)、“狭隘民族主义”(按:此涉中西关系)的清理,来得最为彻底。他说:
王光祈一生的作为无疑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业绩:这又和我们今天讲改革开放,讲文化工作、学术工作现代化建设有甚么直接干预呢?王光祈的那个时代不是早已过去了吗?他对古代文化的态度是有点传统包袱过重了吧?好像还有点儒家的味道。他的那一点“西学”不也早就落后了吗?一句话,我们能把这类“潜台词”在这个庄严的纪念会上抖出来吗?[16](第347页)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王光祈知道:新的文化建设需要传统的基地,王光祈知道整理传统遗产,创造新的东西,需要西学的帮助。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人士中,他是少有的、未以静止或割裂眼光看待‘古今关系’;未以形而上学标准衡量‘中西关系’的杰出人物”[16](第349页)。黄翔鹏之语,道出了自五四以来,王光祈破旧立新的密码:即他的创新是要在中国传统的基础及借鉴西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并不以牺牲传统或“以西代中”为代价。学习西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用来整理自己的遗产,要用来创造自己的新国乐,决不肯当个黄皮肤的洋乐家便完事”[16]。这与封建复古、不偏不倚、和平中正的儒家门墙,及赶时髦式的“以新替旧”、花样翻新甚至“以西代中”,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
对王光祈研究资历最深者吕骥,虽已驾鹤西去,但在他生前(1986年3月)题书的“王光祈的全部音乐理论著作,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17](彩页9)表明,早年加之于王光祈的“狭隘民族主义”等不实之词,已被王光祈身上“爱国主义”的万丈光焰遮蔽。
而使我们真正眼前一亮的,是跨越新世纪的第二年,出版量最大,影响最广,使用院校最多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本的第二次修订版中,对王光祈的评价方面,所做的最全面的改动。
首先,它转变了以前版本中简单地将王光祈视为资产阶级音乐家的定位,认识到王光祈对中国近代“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如:“完全以音乐学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只有王光祈一人。他以自己毕生的努力为中国近代音乐学学科的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努力。”[18](第104页)
其次,对王氏改良主义音乐观、受封建文化以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思想影响等认识,也有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认为王光祈主张的音乐“不完全等同于封建时代的‘雅乐’,也不是当时有些人鼓吹的‘复兴乐教’”[18](第107页),而是“一种能‘唤起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的、……(并)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18](第107页)。
第三,明确指出了王光祈开创性地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考察世界东西方音乐之异同,对后来亚洲各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起到了深远推动作用,并分类地重点介绍了他的著作。如:“关于东方音乐的研究和中西音乐比较的研究,是王光祈将西方创立不久的‘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用以考察世界东西方音乐之异同的开创性研究。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对后来亚洲各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曾起着影响深远的推动作用。”[18](第108-109页)
这可说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王光祈研究而言,“权威教科书”在观念上的一次彻底转变,从而也基本使王光祈的“定位”首次与历史原貌吻合。由于政治标准的变动,及对历史进程中某些指导思想的纠偏,历史研究的结论才使人逐渐信服。而产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2009年10月13日下午四川成都温江区鱼凫国都酒店召开的“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成都温江区政府、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上,年届八十的汪毓和教授的发言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
历史研究,必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探讨,而……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对中国解放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应尽可能符合历史实际。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将他们一律按革命者去要求,常常犯求全责备、不实际的偏向,特别对处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无论工人阶级以及各种劳动者,……受各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因而还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进行艰苦的启发教育,何况对一般政治上处于中间阶层及中上层知识分子,应该说,当时能够坚持正义、爱国的立场,就很不容易了。⑤
这种宽和的态度,如果在50余年前出现,对王光祈的定位,就不会出现“左”的偏差。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正因为对一切阶级,以“革命者”去要求,那么以此眼光看来,王光祈的“改良主义”而非“武装斗争”的音乐学术之路,肯定就是一条“不通之路”了。但对王光祈这样的一介文人而言,此高标准的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符合他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定位标准的改变,也必然带来定位的极大改变。其改变之一,即对王光祈那一代赖以依傍的文化根基、五四以来饱受批判的儒家文化观有了新的认识:“他(指王光祈—引者)原有家学古学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与西方文化的一引者加)契合点,特别他发现中国儒学中的‘和’的思想,与现代音乐学中的和谐的理论,有相应之处。”⑤以前所谓“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14](第56页),现在变成了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契合点”及“相应之处”,从而成为与王光祈“一直信奉的,通过合理的社会改革的政治追求之间的密切联系”及他“热情投入音乐学的志向……有力的理论支持”[14](第56页)。其中儒家及其学说的“封建、复古”定性的改变,及王光祈的改良主义道路,在新世纪里都变得合理起来,这是时代使然的进步,并鲜明地体现在作者“与时俱进”的发言中。
对王光祈阶级属性、角色、性质的定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本文仅开了个头,并注重提供一般研究者所难以查找的、未出版的材料。这些类似于档案的材料(只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中找到),已尘封多日了,而从事这一工作的前辈或驾鹤西归、或年届耄耋,及时展现这些材料中的内容,取的是“正视历史”的态度,也便于后人如实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局限所在。
其次,王光祈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其魅力在于,王光祈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及视角,绝无从众、媚俗之态。这是他得以在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西方人文学科中,找到自己正确音乐学方向的先决条件。面对如此艰辛、冷门的音乐学,并以卖文方式艰难维持,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勇气及内省力呀!这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而在他身后如此起伏跌宕的不同时代的评价,也表明了他的多样性的内质。这是吸引一代代学人对“王光祈研究”痴迷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提出“王学”(——王光祈学),也是不无道理的。当然王光祈也不是完人,甚至在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正如冯文慈教授——这位资深的王光祈研究者所言:“由于他(指王光祈——引者)具有音乐艺术是人类生活的表现,并和经济、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其他姐妹文艺密切相关这样一种朴素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又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学、史前学、哲学、物理学、文化艺术史等等学科的知识,这样就有助于他克服缺乏唯物史观的弱点,在中国音乐史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卓越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具有深刻启示力量的论著遗产。”[19](第80-81页)这是我们所看重王光祈的最本质及最实在的东西。谨以此文祭奠光祈先生的在天之灵。
注释:
①因吕认为萧在音乐教育上不考虑中国的社会条件,全盘地抄袭西洋的音乐教育(按:重点号为引者所加);音乐创作,内容充满着要求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问》(等艺术歌曲)对旧社会的怀疑是种爱国思想,但缺乏战斗的意识,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见参考文献[1],第10-11页。
②194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并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后任该院副院长。1953、1960、1979年度,三次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③指1958年冬至1960年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发动组织全国各地各高校近20名科研人员、教授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及参考资料的工程。
④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主席杨超称:“在筹备(王光祈研究学术研讨会—引者加)过程中,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和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见参考文献[12]。
⑤李岩(现场采录),10月13日下午四川成都温江区政府、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主办“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实况录音,四川成都温江区鱼凫国都酒店,2009年。
标签:音乐学论文;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定位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