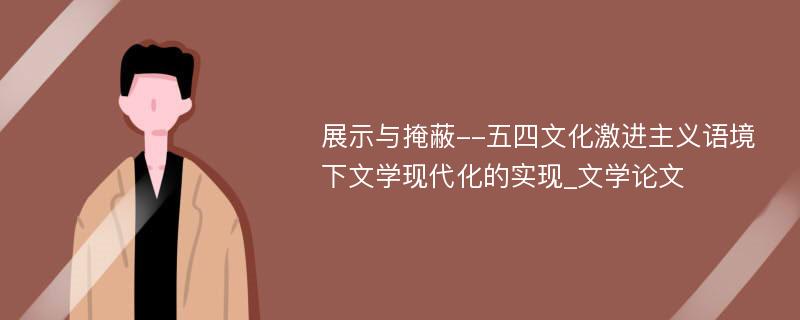
彰显与遮蔽——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下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3-0150-07
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学格局和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势必导致一种偏颇,因此,把文学放置在广泛的文化结构中或者说以宏观的文化视角透视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含量,揭示文学的深层文化底蕴会使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这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绝非如“加数”与“和数”的关系那样简单。有的学者把文学置于文化建设中进行考察,认定他们彼此之间是一种“互建”的关系:文学活动的发展与繁荣肯定对整体的文化建设有利,而整体的文化建设,作为人的一种创造历史的活动蓬勃发展了,也必然会推动文学活动的发展与繁荣[1]。也有的学者从否定主义美学出发,认为文学应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2]。他们对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种种界定都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又不可能涵括二者复杂关系的全部,而文化与文学间的应然关系与二者之间的突然状态往往又是两码事。更何况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类型的文化与当时的文学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中呈现为彼此间相互作用的场性效应。分析这种具体的意义场之间的交相作用才能真切地把握文学与文化的生动关系。
肇端于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积蓄至五四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东西文化之间的冲撞构成了一个巨大而丰盈的文化张力场并作用于文学。在这个文化张力场中,由《新青年》和它唤醒的第一批新青年所创办的《新潮》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思想启蒙为主旨构成了此文化张力场的主导价值倾向,一方面为转型中新文学现代性的生长提供了契机与动力,另一方面又对其现代性的实现造成某种程度的遮蔽。
一
革命——作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最鲜明的现代表征,既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进行艰难转型的重要动能和必然选择,也为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正义性依据。时至近代,积淀着中国古老元典精神的“革命”精神,经由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中国社会、文化新生的激切心态的表征。邹容的《革命军》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现代“革命”的范本:“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3](P650)中国“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传统革命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已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命令,也成为中国危机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化情绪,所以当这种革命性思维应用于文学从而推拥出“文学革命”时,就显得顺理成章。尽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伦理道德革命相提并论,但在中国的历史行程中,文学革命并不属于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方案相并列的一级概念,而是作为中国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点环节——文化启蒙的派生物出现的,而文化启蒙必然升浮起文学革命之舟几乎成了中国近百年来明显可见的一个历史规律。虽然梁启超的带有改良色彩的“三界革命”不同于陈独秀具有政治暴力倾向的“文学革命”,胡适具有建设性、承续性的革命与钱玄同破坏性的主张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现代化方案的构思却是一致的,即实现思想、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并以文学作为这一改造工程的有力武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种激进的文化语境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转型。但由进化论母体中演化出来的“革命”话语是以直线向前的时间认知作为前提的,图新弃旧是它的重要特征,所以当革命成为文学转型的正义性依据时,也同时依照历史进化的思路在新旧之间做出了价值上的优劣判断和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把时间意义上的“新”等同于追求中的“现代性”,传统则被认定为旧的与现代性绝不相容的对立面遭到否弃,这样,就曲解了文化及文学现代转型的实质性内涵。现代性理应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努力,也是一种多维度的动态结构生成,文化激进主义所主张的“新”固然可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持对立观点的一派,因其是在现代性的开放视野中对传统所做的重新确认也应成为“现代性”的归属对象,而且,作为历史结构中把“新”等同于现代性思路的互补、制衡力量,理应纳入现代性的范围之内。同样,对于属于精神范畴的文学而言,传统既可以凭借其独特的个性存在于线性时间之外,与现代文学共享同一个空间,同时作为绵延至今的历史积淀必定会参与文学现代品性的塑造。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把审美与历史的现代性做了一种同一性理解,既显示出满怀历史激情的文化启蒙主义者以文学话题呈现出的政治意欲,又使文学现代性的生长一开始就显示出片面性。
作为激进派,《新青年》和《新潮》同人在文化运动中最为热烈、峻急同时也最为人以片面相诟病的是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所做的趋于一端的价值选择,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新青年》老将陈独秀早就断言: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兼程以进,犹数望尘,甚勿以抑扬过当为虑”[4]。这种激进主张对于要急于摆脱几千年旧债的中国历史而言具有重要的策略性意义,而对于文学的转型而言则未见得合适。但被纳入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五四初期文学在寻求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恰是采取了与历史价值相认同的策略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坚决否弃的态度而以“欧化”作为实现现代性的必由路径。胡适就认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不可不取例。”[5]把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他的学生——《新潮》的主将傅斯年和罗家伦。他们把东西方文学进行了系统但带有鲜明价值倾向的比较:“西洋文学是切于人生的,中国文学是见人生而避的;西洋文学是为唤起人类同情的,中国文学是为个人私自说法的;西洋文学是求真相的,中国文学是说假话的;西洋文学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国文学是贵族的,矫揉的;西洋文学是要发展个性的,中国文学是要同古人一个鼻孔眼出气的,所以中国文学都很有在博物院里的价值。就文学的体用特质而论,我们中国文学还惭愧得多呢!”[6]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借物,历史上的好小说不过《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有文学价值,其余都要不得。两两对照,西洋的文学对于人生是何等浓馥,何等活泼,何等真实,我们的文学是何等干燥,何等死闷,何等虚伪,比较的结果,于是创造新文学的材料和路径哪能不会决定呢[7]?他们的决定就是“欧化”,“我们径自把它取来,效法他,受它的感化,便自然而然地达到‘人化’的境界,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把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8]我们今天几乎无法从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了解“欧化”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迄今所见到的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的为数不多的初期新文学作品,都经过了编者精心的筛选,绝少反面的典型,因此我们也就感受不到欧化给文学带来的窘境。这种情形只有从当时人的言论中才可略知一二。反对新文学的人自然会把欧化作为攻击的口实,即使坚决主张欧化的新文学倡导者,谈到欧化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针对当时有些读者对于文学欧化的抱怨,沈雁冰曾有过这样的答复:“我们应当先问欧化的文法是否较本国旧有的文法好些,如果确是好些,便当尽量去传播,不能因为一般人暂时的不懂而弃却,所以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体,我是赞成的,不过也主张要不离一般人能懂的程度太远。因为这是过渡时代不得已的办法。”[9]或者从这些语言表述的缝隙中已经透露出话语背后的历史真相:“欧化”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看不懂的窘境。自然,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文学创辟期的“欧化”是难免的,但这仅仅是文学现代转型的路径之一,并非惟一最佳路径。而且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审美范式和由此形成的审美意象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成是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处的,除非异想天开地把整个文化连根拔掉,否则我们将永远立身于从古代绵延至今的文化之中,无法真正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而传统的存在和他所具有的源泉性力量终究会被正视。所以后来闻一多曾大声疾呼,“现在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披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10]诗人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不可割裂和它所蕴涵的巨大艺术潜能,以及由于对传统的漠视而造成的诗美的偏颇。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正是在成功地吸纳了传统的基础上对文学的现代品格做了与欧化不同的定位。大量的文学事实证明,正是能在转型的进程中找到现代与传统恰切的接榫点之后,才能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或许能启发我们:历史的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与距离,尤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文学与历史应该存在着一定的逆差。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现代性的实现,都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访的问题,尽管在某种情势下会出现偏向于一端的发展,但历史最终总会启动其纠偏机制,做出补偿性的调整。
二
如果说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语境推动下的文学现代性的初步实现,“革命”性思维为其提供了动力,“欧化”为其提供了路径,那么“启蒙”则使20世纪文学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脱离了传统的文学价值观,真正体现出现代性精神内涵。“启蒙”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话语成为文学现代性生长的主要资源。曾有学者认为,“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人的精神——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立本质,是它的核心和精髓。”[11](P70)对此,我也深以为然,正是在启蒙的焦点——“人”的问题上,新文化与新文学找到了最深层的精神关联并达成了默契。对当时和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的文学”恰是彰显了与传统文学殊异的精神气质,而处于转型期的新文学确是主动迎合了这种规约,努力实践着《人的文学》所做的两方面的规定的——(一)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考察当时的文坛,当时大多数的翻译作品可归为第一类,多表达的是一种向上的人生观和超越现实的渴求。最为典型的便是易卜生戏剧对个性主义的张扬以及托尔斯泰作品中对爱与和平的向往与颂唱。而当时“寂寞的文坛”为数不多的创作则基本是目光向下的,表现了中国当时病态社会的病态人生,如汪敬熙的《雪夜》、欧阳予倩的《断手》、杨振声的《渔家》、《一个兵的家》等等所描写的是社会的窳败给下层人们造成的贫病交加。另一类则是写传统礼教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上的痼疾,如杨振声的《贞女》、俞平伯的《狗和褒章》、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等。而鲁迅此时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风波》、《故乡》、《明天》等更是深透地揭示了国民的病态人生。由这些作品可见出,此时期的新文学是全身心地把文化启蒙的主题当做自己的创作主题的。两杂志中所涉及的诸如社会、文化问题多以文学的方式得到了展现,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些文学作品与其所处的两大刊物所构成的文化语境做一种互文性的理解。
无可否认,文学由于对启蒙思想的涵载获得了现代素质,但也因此对自身的现代性产生了某种遮蔽。对整个20世纪文学影响深巨的“人的文学”,作为文化启蒙命题,对于文学而言无疑构成了一种理论预设,既是一种价值导向,也是一种价值限定,它有效地把文学导入历史变革轨道的同时又使文学植根于一隅,虽然这一隅有着广阔而深厚的土壤。新文化运动者曾对文学做了这样的规定:“文学是发达人生的惟一手段,既这样说,我们所取的不特不及与人生无涉的文学,并且不及仅仅表现人生的文学,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学。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排斥的文学。”[12]“人的文学”,包括稍后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几乎成了文学现代性的法定指归,启蒙话语以外的艺术表述日益失去了合法性,这也是后来“问题小说”一度独踞文坛的一个重要根源,一些准艺术因为在历史价值层面上所显示的进步意义而被时代所认可,文学却因与历史中心行为的价值认同而斫伤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从数量上看最能显示新文学实绩的应该说是诗歌。诗歌可以说是最具个人性的情感艺术,也是最讲究形式意味的文学样式。而五四白话诗由于附着于文化启蒙而使自身缺少一种诗性之美。语言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役,其胜利成果最迅速地体现在诗歌上,五四白话诗以文言诗作为反叛对象,打破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规则,虽然彰显了启蒙意义上的白话,但却忘却了自身为诗的特性。所以俞平伯也感到用现今白话文做诗的痛苦,因为白话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成了缺乏艺术培养的俗语了,久已丧失了制作文学的资格,认为中国现今的白话,并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13]。在内容上,白话诗所表达的也是社会化的启蒙意识,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与胡适同题的《人力车夫》、俞平伯的《“他们又来了”》等在对“非人生活”的描述上与小说显示出思路上的一致性。这虽然是诗人们对于现实的一种主动承诺:“现今社会的生活,是非常黑暗悲惨的……我们做诗,把他赤裸裸地描写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五四初期的白话诗由于对启蒙思想的主动承载,以不加提炼的白话为工具,往往显得直白琐碎,缺少诗所具有的含蓄蕴藉之美和形式上的意味,从而显露出诗性与诗思的偏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平心讲来,主义一方面,比较前人总有进无退,在艺术方面,幼稚是无可讳言的。”[13]因此有学者认为“五四白话诗取得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胜利,而在审美价值上却丢分过多。”[14]这也为后来“格律派”和“象征派”在诗美上对其纠偏埋下了伏笔。
诗尚且如此,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又怎样呢?发表与《新青年》和《新潮》上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和谐地融入两杂志所构成的激进的文化氛围,是因为他们和杂志中其他评议性散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二者有着一致的精神气质,有着对于旧礼教、旧社会、旧家庭相同的热烈而激愤的情绪,有着对相同问题的相似的表述。如《一个贞烈的女孩子》既可以看做是一部小说,又可以看做是与《吃人与礼教》、《万恶之源》同类的揭露性的散文,因此《回眸新青年》丛书中,编者把它编入“语言文学卷”的散文一类似乎也还说得过去,更不用说诸如《谁使为之?》《是爱情还是痛苦?》《这也是一个人!》此类的小说更是《女子问题》、《贞操问题》、《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类社会性论文的另一种版本。《新年》和《新潮》的“问题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更何况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人文启蒙主义者,文学不过是他们参与社会人生现实问题讨论的另一种方式。小说中的人物不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象征符码,缺乏人物应有的性格特征和艺术感染力,给人更多的是“问题”的警觉与不平。对于启蒙思想的全神关注导致了对审美的忽略,思想大于艺术成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硬伤。这也为文学的反抗意识提供了生长的可能,其逐渐强化的艺术的律性反过来必然要反抗启蒙理性所带来的压抑,寻求现代性深度存在方式。其实就在当时一些人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敬熙在《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学革命的呼声,既已打破了旧日的桎梏,又正值中国各种人的生活都感痛苦的时候,应该产生一些好的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文学革命给小说家新加上了镣铐,这些新的镣铐包括“人道主义”、“人的文学”、“写实主义”等等,种种执著蒙蔽了许多作者的眼睛,磨钝了许多作者的感情,不知不觉将弄狭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视阈,因为要保全诸如“人生艺术派”一类的招牌,而把小说写得如劝善书一般。稍后的一些文学家提出的似乎偏向另一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是出于对工具性制约的一种反拨,以回归文学本身的纠偏式的努力所做出的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指向——审美现代性的诉求。
三
文学作为一个有着独特规律的价值系统,并不总是一定表现为与历史、社会同一性的关系,它还要保持自身与历史、社会的一种张力,也就是维持文学艺术的自律意义——对于文化批判中认识偏颇的矫正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和质疑。文学的现代性最初虽然是依靠历史现代性的负载得以实现的,但艺术自主性原则反过来也会对历史现代性质疑,凸显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并以此作为历史现代性的制衡,这就是文学的独立价值。文学的独立性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文学的独立性在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被关注,但在启蒙运动的高涨期,这种独立性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在文学革命初倡期,确切地说是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的“通信”中与胡适谈及:“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做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谈。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看似一种本体论的表述,其实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思考。陈独秀此时此地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并不是从文学自律意义上所提出的要求,而是与文化启蒙的主旨相附和的。启蒙要求知识分子摆脱传统专制政治的“弄臣”身份是与要求文学脱离粉饰太平“文以载道”的附属品地位相表里的。陈独秀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必须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言’”。无疑,文化启蒙从“人”解放的角度冲击了中国自古以来正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把文学从经史的附属品地位解放出来,使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又是以对文化启蒙的附着为前提的,并未形成自律意义上的独立叙事,而是被放置到历史叙事之中,文学刚刚获得的独立性又在工具性的规约中丧失了。其实,在文学革命伊始,这种关系就被设定了。以历史变革为鹄的的文化启蒙主义者是通过对文学的工具性定位使文学有效地参与了历史与文化的重建活动,倡导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认为,政治界历经革命而黑暗未减,乃是根源于国人精神界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黑幕层张,因此,政治革新的首要前提是必须革新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可见,“文学革命”的政治性、文化性内涵远远大于文学自身的成分。正如蔡元培在总结新文化运动时所讲的,“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15](P484)文学的工具化和审美的功利性是对文学的性质截然不同的要求。功利性并不是妨碍文学独立性确立的根本性原因。因为功利性属于文学的内在属性,只不过功利的范畴不同,不同作家对于功利与审美之间的倾斜度不同而已,但仍旧属于文学自身的问题。自然,当文学急进地追求某种功利(尤其是政治的功利)时,内属的功利性就会成为外在的工具化存在,而工具化则要求文学呈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主要是作为手段依附于目的,启蒙文化对文学的要求就是如此。这样,文学的首要指向就在于历史而不是审美。新文学就在这种寻找又失落的悖论中追求着自身的独立性,寻求着它的现代性。当启蒙主义者把审美与历史做同一性的要求时,既为启蒙也为文学设置了内在的否定性,使二者都未能完满地实现自身,启蒙没有通过文学达到救国的远大目标,文学也无法依赖启蒙实现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因此突破困境,超越旧有束缚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将航天器送入太空的火箭推进器一样,当二者必然分离时,推进器已经能够把自身的能量转化为航天器所需的运行速度。启蒙对于文学也是如此,尽管文学五四初期是被启蒙文化负载着进入转型的轨道的,却因此获得了独立运行的能量。启蒙落潮后,文学与文化客观上产生的疏离使彷徨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产生的对于历史的逆向性叩问和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体悟使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
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和《新潮》为主的文化激进主义阵营的大力倡导下,20世纪中国新文学以其对启蒙精神的自觉遵循,以新的形与质显示了文学与历史要求的深度契合,从而彰显了自身的现代性。但不必讳言,由此给文学造成的某些现代性的缺失也是相伴而生的,由于文学对于历史的顺向呼应使文学的自律性难以张扬,并显示出文学自身建设的贫弱。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新潮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