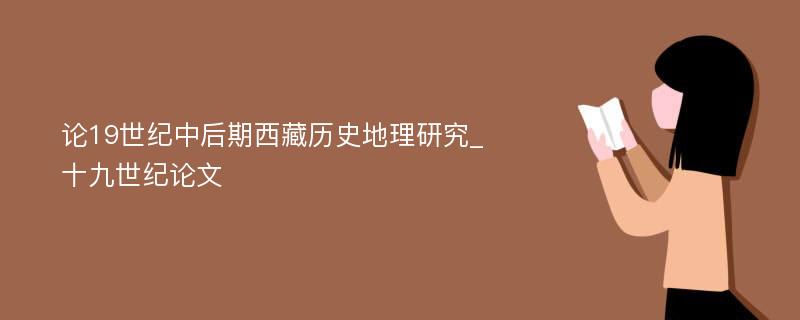
试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藏史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试论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至19世纪末期,随着英、俄等列强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和西藏边疆形势的日益危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于西藏史地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并且逐步地将西藏史地研究推向深入。这一时期的西藏史地研究大致可分为19世纪四、五十年代、60年代初至1888年英国侵藏战争前和1888年至1900年三个阶段。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魏源的《圣武记》(卷五)和姚莹的《康輶纪行》最具代表性;60年代至80年代末,黄沛翘的《西藏图考》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王锡祺等提出的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对当时的反侵略特别是抗英斗争则起到了积极作用;1888年至19世纪末,王锡祺所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和袁昶刊刻的《卫藏通志》,代表了西藏史地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既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和保卫神圣领土、坚决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力图把学术研究与筹边抗敌、维护祖国统一结合起来的经世致用的学风。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也成为它们尤其是英、俄侵略的重要目标。全国人民支持西藏地方军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也加入到这一斗争中去,他们把学术研究与筹边抗敌结合起来,在19世纪中后期形成西藏史地研究的持续热潮,为巩固边防、抗击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西藏史地研究大致可分为19世纪四、五十年代、60代初至1888年英国侵藏战争前和1888年至1900年三个阶段。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三个阶段的西藏史地研究状况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的青藏高原,自古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藏族同胞的祖先,唐宋时期史书称为“吐蕃”,是由古代的羌族西迁青藏高原后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而形成的。[1] 当吐蕃还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时代时,就同汉族有了联系;7世纪以后, 吐蕃政权就同唐、宋等内地汉族政权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则在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西藏始终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一部分。
但是,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沙俄扩张势力就把侵略魔瓜伸向西藏。 18 世纪末, 英属东印度公司曾先后派出博格尔(George Bogle)和忒涅(Samuel Turner)到日喀则, 要求与西藏建立通商关系。这一要求被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但他们却乘机搜集了有关西藏的大量情报,为进一步侵略作准备。[2]此后, 英国侵略者采取新的政策,即逐步控制了中国西藏周边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布鲁克巴(今不丹)和克什米尔等国,并以此为基地入侵西藏。1840年以后,英国更乘鸦片战争之余威,向中国西部西南部大肆扩张。40年代,英国多次要求勘定克什米尔与中国西藏的边界,并单方划定了非法的边界线,侵占了原属中国的拉达克地区(中国历届政府对此均未承认);50年代,又挑唆廓尔喀发动侵藏战争,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了廓方提出的不平等条件。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样,沙俄对中国西藏也早有侵略野心,1721年彼得一世即命令已占据了中亚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的俄国侵略军加固已有堡垒,并“与中国的赛里木城(今青海西宁),达巴城(今西宁西郊多坝)及达赖喇嘛住地亦应有商务往来”,而“此等商务往来的目的”在于派间谍搜集情报,尤其是“查明能否到达该地,并加以占领”。这就暴露了沙俄力图向中国西藏地区扩张的野心。此后直至19世纪50年代末,俄国多次派遣间谍以传教、朝佛、考察为掩护搜集西藏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活动作准备。[3]
面对英、俄侵略势力向西藏的积极扩张活动,西藏人民从印度、廓尔喀等周边国家的遭遇中受到教育,提高了警惕,坚决抵制。与此同时,深受经世致用学风影响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关头,极为关注边疆事务,留心边疆史地,并对西藏史地的研究相当重视。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姚莹等人积极从事于西藏史地的研究工作,并产生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魏源的《圣武记》(卷五)和姚莹的《康輶纪行》最具代表性。[4]
《圣武记》是魏源在鸦片战争后为劝谏清朝统治者励精图治、强国御侮而编写的。该书第五卷是有关西藏史地的三篇:《国朝抚绥西藏记》(分上、下两篇)、《西藏后记》和《乾隆征廓尔喀记》,1846年刻本还在各篇后附录了《康輶纪行》的有关段落。《国朝抚绥西藏记》侧重于叙述道光以前西藏的政治、军事等的历史变迁,并总结性地指出:“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5], 提醒统治者对西藏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西藏后记》则主要介绍西藏的地理、宗教,与《国朝抚绥西藏记》各有侧重,并构成姊妹篇,全面地介绍了西藏的史地状况。《乾隆征廓尔喀记》追述了乾隆朝驱逐廓尔喀侵藏军队的史实,宣扬清王朝的赫赫“武功”。
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反对“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6]的单纯考据,主张经世致用。 《圣武记》中有关西藏史地的三篇都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同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国朝抚绥西藏记》建议统治者重视西藏问题,《西藏后记》主张“募腾越战士勇万人,渡怒江而西南”,直捣孟加拉,[7]摧毁英国的鸦片产地; 《乾隆征廓尔喀记》则设想利用法、美、俄等国与英国的矛盾,牵制英国,使之不敢远犯中国,以收“以夷攻夷之效”[8]。 这些设想虽有些天朝上邦以夷制夷的虚骄心态,虽有对西方列强共同侵华的一面认识不清的偏失,但其忧国筹边之心和学术联系实际的学风,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成为近世西藏史地研究的主流与趋势,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影响。
《康輶纪行》成书于1844至1846年间。当时作者因鸦片战争期间在台湾抗击英国侵略军遭到反动势力迫害,被贬官回川。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外夷桀骜”步步入侵,使他“窃深忧愤”,[9] 并留心于边疆史地,积极探求强国御敌之道。此书就是他在奉命到川西抚谕乍雅和察木多两地宗教势力之争期间,广泛搜集西藏史地资料,关注中外形势的基础上撰写的。《康輶纪行》以“乍雅使事始末”为纲,对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及风俗民情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该书还对英、俄等国情况作了介绍,不仅揭露它们尤其是英国的侵藏野心,而且更相信英国“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之方略乎?”[10]从而表现出了必胜的民族自信心。另外,本书作者尤其关注当时的中外大势,注意到英俄在争夺中亚方面的矛盾,和魏源一样,主张利用俄、法等国与英国的矛盾牵制与打击英国。[1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姚莹不仅注意对西藏史地文字资料的搜集,而且对于地图的绘制也极为重视。他在《康輶纪行》一书中绘制了《乍雅图》、《西藏外各国图》各一幅,并分别作图说加以说明。《乍雅图》以粗线条的形式勾勒了乍雅地区的山川走向,对道里程站和区域划分也作了标注;《西藏外各国图》则大致表示了中国西藏周边国家、部族的地理位置,二者虽均失于简易,但对于了解西南边疆形势、筹划边防提供了一定帮助。加之二图均有图说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更有利于人们加深对乍雅状况和西藏周边地区史地的认识,在当时形势下对筹边御敌、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西方列强尤其是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虎视眈眈的形势下,魏源、姚莹等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自觉地展开了西藏史地研究工作,他们把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国防、筹边联系起来,把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注入到经世致用的学术之中,实现了爱国主义与经世致用的统一,开近世西藏史地研究之新风。他们在方法上,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即文字的介绍与地图的绘制双管齐下,既帮助人们加深对西藏及周边地区史地的认识,又使筹边卫国获得较为直观的资料——地图,从而为当时的筹藏事务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也对后来的西藏史地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姚、魏等所做的工作并不太多,西藏史地研究的成果在当时也微而不著,但是,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文图并举的研究方法却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边疆危机也随之加深。至19世纪80年代末,台湾、东北、新疆处处告急,大片领土被割占。此间,英、俄双方在中国西部地区也加紧了争夺,西藏是它们侵略的重点之一。《天津条约》签订后,英、俄、美尤其是英国就多次要求到西藏游历、传教,由于西藏人民的反对而被清政府拒绝。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以断交、开战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该约附有专条,允许英人入藏游历,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由驻藏大臣“派员妥为照料”[12]。这就为英人入藏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但这一规定因遭到西藏各界人民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在多次失败后,1886年英国以清政府承认其对缅甸的控制权为交换条件放弃了游历、传教的要求。英国此间还在大吉岭等地设立市场,企图以经济手段打开西藏大门,因西藏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一阴谋也宣告破产。在种种手段均告失败后,英国决定以野蛮的军事手段达到侵略目的,于1888年发动侵藏战争。而这一时期,沙俄虽对西藏有极大的领土野心,但因无力与英国抗衡,便采取了派遣间谍打入西藏上层,培植亲俄势力的办法。为此,它派出了大批间谍人员以学经和朝圣为名潜赴西藏,德尔智就其中之一,他们的活动加剧了一部分西藏上层分子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因此,60年代至80年代末,西藏边疆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对于严峻的西藏形势,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与姚莹、魏源相比,他们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西藏史地的研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筹边建议,积极地为抗敌卫国献计献策。这一时期,黄沛翘的《西藏图考》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王锡祺等提出的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对当时的反侵略特别是抗英斗争则起到了积极作用。[13]
黄沛翘于同光年间多年参与西南边务,“留心时务”,在英国“经营印度汲汲若不终日”[14],阴谋以其为基地侵略西藏的紧急形势下,认识到西藏过去只是“滇蜀之藩篱,今则西南攘印缅,西北御俄罗斯,正北又为新疆之后障,坤维大局,斯其咽喉,未雨之谋,履霜之戒,岂可忽耶”[15]。他还认为,筹划边防不仅要有文字材料,而且更要熟悉山川险要和舆地原委,要重视地图的作用。因此,他从1885年秋即“汇群书而互证,集众说以从同”[16],广泛搜集西藏史地资料,并请人绘制西藏地图数幅,与《西招图略》、《康輶纪行》中的一些地图一起,汇集成书,于次年夏出版了《西藏图考》。
黄沛翘之所以对绘制西藏地图工作极为重视,是与当时的状况密切相关的。自18世纪末期起,英俄等国派遣间谍入藏绘制了大量的地图。而中国当时明显落后,清朝内府藏有《西藏全图》,但束之高阁,“外间未见临本”;松筠著《西招图略》中有西藏地图数幅,“最明确,而方向倒置”(采用上南下北定位方法,与传统方法相反);而盛绳祖、马揭1792年(乾隆57年)编成《卫藏图识》,所绘地图至光绪时代已“模糊不可辨识”[17]。在英国陈兵于西藏边境,随时阴谋入侵的紧迫形势下,绘制清晰、准确的西藏地图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当务之急。黄沛翘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请人采取计里开方的绘图方法,绘制了《西藏全图》和《西藏沿边图》各一幅。《西藏全图》“每方二百里,界限用单线,度数用斜线,河道用双线,地名用单圈,程站用密点”[18],以上北下南方法确定方位,较为清晰地展示了西藏山川险要、道里程站的状况。虽不能与今天的地图相比,但对东西数千里的塘站远近、道路迂直、山水纵横均作了较为准确的描绘,这对于了解全藏地理形势和筹边抗敌无疑有很大帮助。《西藏沿边图》“每方计四百里”,“略于中而详于外”[19],大致反映了中国西藏周边的政治地理形势。它与姚莹所绘《西藏外各国图》相比,更为清晰、准确,为当时人们提供了认识外部世界的较好资料。该书还收入了《西招图略》中有关西藏的12幅地图和姚莹所绘《乍丫地图》(即《乍雅图》),帮助人们了解西藏各部分的地理状况。以上各图,既有总体描绘,又有分区说明,既有西藏地图,又收入周边地区的地图,且各图均附有说明性的文字,这大大便利了人们了解西藏地理状况,对当时筹边抗英斗争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也为今天研究我国地图发展史和清末西藏地理提供了资料。
《西藏图考》不仅收入了大量地图,而且分卷介绍西藏源流、山川险要、道里程站等史地知识,并以《艺文考》两卷收录清代(光绪前)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对人们深入了解西藏提供了很大便利。该书中有些材料至今仍有重大价值,如卷六《地利类》所述拉达克地区的历史沿革,充分说明该地区本为中国领土,是被克什米尔封建主和英国殖民者强占而归于今天的克什米尔的,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拉达克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和谎言。
黄沛翘希望书中所收《西藏全图》“匪惟考古者所必需,抑亦筹边者所宜亟讲也已”[20]。不仅如此,事实上《西藏图考》的图、文都是出于“未雨之谋”的忧患意识和固边抗敌的目的而完成的,均非仅仅出于单纯的考据目的以满足考古者所需,可见黄氏进行西藏史地研究继承了姚莹、魏源的经世致用与爱国主义的宗旨与精神,并且在研究深度上有所加强,时人称,“海国有图,寰瀛有志,而况卫藏……犹我宇下……异日驰域外之观,扬钩深致远之威……必将以是书为权舆矣”[21]。此处把《西藏图考》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相提并论,或有过誉之嫌,但把该书与巩固边防、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并抗击外敌“深致远之威”联系起来,且视此书的编写是这种御敌固边活动的起始点,这表明黄沛翘为筹边卫国所作的努力与此书在此方面的价值已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得到了人们承认。而此书刊行后不到两年,英国就发动了侵藏战争,它在抗敌斗争中无疑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西藏史地研究的另一大成果,就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形势危急的关头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多方面的筹边抗敌和建设西藏的建议。首先,他们在广泛搜集史地资料、深入研究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军事、外交和行政方面的筹边建议。“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先事预防,诚有不可稍缓者矣”[22],这在英国发动1888年侵藏战争前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呼声。但如何“先事预防”呢?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一,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以迎击来犯之敌。黄沛翘在所编撰《西藏图考》卷二中重录了松筠所作《西招图略·审隘》一文,并写成《续审隘篇》,详论西藏山川要隘、程站道里,并指出面对英国侵吞南亚诸山国西藏已危在旦夕的现状,“藏南沿边一带数千里地”,当为未雨绸缪之计,“详审要隘”、“多设关卡”,[23]以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保卫神圣领土。此文所论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即以正义之师抵抗侵略者,维护国家统一。其二,外交方面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英、俄。他们普遍重视姚莹、魏源曾提出的“以夷制夷”主张,此间正从事于西藏史地研究的王锡祺把魏源《乾隆征廓尔喀记》全文收入他后来出版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就表明当时人们仍希望这一策略在抗敌斗争中发挥作用。其三,行政方面,在西藏改设行省加强军政管理。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筹藏建议。《西藏改省会论》和《西藏建行省议》比较有代表性地阐明了这一主张。前者总结了清代西藏“羁縻勿绝叛服无常”的历史,提醒统治者在边疆危机的状况下更要重视西藏问题;并驳斥了“西藏之地大半不毛……不若东取朝鲜犹为事半功倍”的错误认识,主张固边御敌、维护祖国统一。作者进而指出,台湾新疆“仿十八行省例添巡抚司道以下诸员……经营草创示久安长治规模”,而西藏“与滇蜀临近,逼近五印度,有不得仍恃驻防者”,不如“改为行省徐策富强”,“既可杜旁伺之心,复不至前功尽弃”,可收先发制人之效。[24]与此文相比,《西藏建行省议》对于西藏改设行省问题则作了更深入、具体的探讨。作者认为,西藏原来“设戴唪治兵,设碟巴治民,设堪布治喇嘛,虽受制于达赖而总其成于两驻藏大臣”的政教合一体制,“形势格紧,井井有条”,为改设行省提供了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前藏、中藏、后藏、拉里可分驻提镇司道”,里塘、巴塘等原设粮台可建府,江卡、乍雅等处可建州县”,而督抚驻于拉萨。[25]可见当时所设想的西藏建省方案是具体完备的,具有可行性。在19世纪初期龚自珍写成《西域置行省议》,主张西北地区设立行省防御沙俄入侵,后此议成为筹边抗俄的措施之一。而这一时期爱国知识分子在藏事危急的关头提出的西藏建省主张,虽未能实施,但其爱国筹边之良苦用心以及该主张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当与龚自珍的西北设省建议一样给予充分肯定。
如果说上述筹边建议多为抗击外敌的应急之策,那么当时有识之士对于开发建设西藏的认识则更有深远意义。《西藏改省会论》的作者虽主张西藏设省,但又认为这不过是“浅近之谋耳。”他认为,只有在改建行省后,开发西藏,建设西藏“徐策富强”,才能更好地巩固边防、维护统一。作者首先对于西藏开发建设表现了坚定的信念,他相信西藏完全可以从“大半不毛”的荒凉状态走向繁荣。他极述改设行省后,台湾、新疆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新疆伊犁在改省后由冰天雪地“一望皆戈壁”而“复有小杭州之比”,使人们相信西藏也会像台湾、新疆那样获得巨大发展,出现发达繁荣的景象。再者,作者相信人的作用,虽然他在文中谈及“天运有变迁”、“地灵有感化”,但他更相信“劳心者君子劳力者小人上下勤劬,硗瘠可期于饶沃”。[26]这一认识固然有“劳心”、“劳力”的剥削阶级观念,但他相信人力在开发西藏中的作用,相信人的努力会使西藏发生巨变的思想还是应当肯定的。此文充满信心地展望西藏的美好未来,主张从长远考虑开发建设西藏,在当时不仅激励了全国军民为保卫西藏、维护国家统一而斗争,而且澄清模糊认识,使人们对西藏的美好前景加深了认识,对于抗击侵略、保卫神圣领土和建设西藏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今天的西藏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如上所述,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藏受到来自英、俄等列强的更为严重的侵略,西南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在这种形势下,黄沛翘等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姚莹、魏源等研究西藏史地的优良学风和方法,同时又加以发扬,取得了比姚、魏更大的成就。在研究深度上,这一时期有了更大进展,不仅重视对西藏史地状况的介绍,而且注重对已有资料的汇编出版,《西藏图考》中就收入了清代光绪前的有关西藏史地资料,便于当时人们更广泛地获取筹边材料;而姚、魏仅是撰文介绍西藏史地状况,未作已有资料的汇编刊刻工作。同时,他们不仅比姚、魏更重视地图的绘制工作,而且注意在搜集旧图的同时绘制更为准确、清晰的新图,以备筹边之用。另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在研究已有资料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更为务实的筹边建议和未来规划。如果说姚、魏的“以夷制夷”设想是中国战败之后的“病急乱求药”,其爱国之心、筹边之意值得肯定,但其设想却难以实行;而黄沛翘、王锡祺等人在这一时期则从军事、外交、行政多方面献计献策,其设想多属可行之议,如军事设防、设立行省等确实更具有可行性,而且还从长远考虑注意到开发建设西藏使之“徐图富强”才可固边守土长治久安,这些不仅对于当时有积极影响,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此,19世纪60年代初至1888年英国发动侵藏战争前的西藏史地研究在深度上超过了前一阶段,研究成果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参考价值。
三
1888年英国发动了侵藏战争,西藏军民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奋起抵抗,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压制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加之西藏地方军队武器装备多方面处于劣势,英国侵略军得以攻占纳汤、亚东等地,为以后向清政府敲诈勒索提供了有利条件。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清政府,在此形势下,于1888年底不顾爱国军民反对派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议和。英国借助于军事侵略的暂时优势,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1891年《中英藏印条约》和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攫取了“保护督理”哲孟雄、亚东开市、领事裁判等特权,而且侵占中国西藏南部的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也为其工业品输入西藏大开方便之门,破坏了西藏与内地的传统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俄国为了同英国产中国西藏,出加紧了活动。德尔智等间谍利用1888年侵藏战争后西藏上层人士中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挑拨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煽动达赖和西藏上层集团投靠俄国。在德尔智等人鼓惑下,西藏上层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强,后来竟派德洋智作为使节访俄表示同沙俄“亲善”。对于德尔智和沙俄的阴谋,西藏爱国军民坚决抵制,清政府也有所觉察,至访俄事发则向沙俄政府抗议。英、俄的侵略活动日益加紧,西藏边疆的危机在19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也随之大大加深,祖国神圣领土西藏面临着被分割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许我爱国知识分子为筹藏抗敌努力,更加重视西藏史地研究。这一时期,王锡祺所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集清代西藏史地的主要论著于一书,袁昶刊刻了《卫藏通志》,代表了西藏史地研究的主要成果。
《卫藏通志》为曾任驻藏大臣的清代名臣松筠所撰,[27]但此书初无刊本,且流传甚少,1895年由清会典馆纂修袁昶刊刻发行。袁昶在《刻卫藏通志后叙》中指出,当时西藏已处于极为危急的形势之下:“雅鲁藏布江下游,则割入英缅,三藏之南边,绒辖、江孜、定日、帕克里与英主黎(即指英国)接壤”,而亚东被迫开关,哲孟雄又已被英国控制。[28]在此种形势下,刊刻此书目的显然在于为巩固边防、抗击英国有可能再闪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史地参考资料。而《卫藏通志》详述喜庆以前西藏的政治(镇抚、抚恤等)、经济(贸易、钱法等)、宗教(喇嘛、寺庙等)、地理(山川、疆域、程站等)、历史(纪略等)和军事(兵制)等状况,资料丰富,且松筠任驻藏大臣多年,又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吏,得以了解西藏方面的档案材料,因而本书资料可靠性强。因此,本书可视为清代嘉庆以前西藏的小型百科全书。《卫藏通志》刊行于1888年英国侵藏战争之后,与当时已广泛流传的《西招图略》、《西藏志》、《西藏图考》等书一样,为筹边抗敌、抵御英、俄以后进行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大量资料,而本书又以其详备、可靠的优势起到了他书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研究西藏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则以其集清代众多西藏史地论著于一书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该丛钞编辑者王锡祺是一位忧国忧民而又具有开放精神的地理学家。他“抱用世之志所自期”,曾受维新思想影响拟上万言书条陈政见,后赴日本学习整军经武之道,[29]为富国强兵抵御上敌效力。他愤怒斥责反侵略战争中奕山等无能官吏“割东陲三数千里于前……弃南疆三数千里于后,自撤藩篱,开门揖盗”的丧权辱国行径,感叹“无汉张汤、唐郭子仪、宋岳飞、元贴木儿、明于谦其人敦纾”的积贫积积弱现状。但面对“异族扣关,觊觎百状”的紧迫形势,没有仅仅停留于“抚膺扼腕长太息”的悲愤和感慨,而是以自己的努力为固边守土、反抗侵略搜集资料、献计献策。他从1877年起即“从事舆地洋务时政”,“集丛书、丛钞千数百种”,[30]于1895年前后陆续刊刻,即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书包括正编、补编、再补编三部分,每一部分12帙,共收入清代国内外的地理学作品和游记、杂感等与地理学有关的作品1430篇,是清代地理学的一部重要选集,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地理学丛书之一。编辑、刊刻此书不仅花费了王锡祺近20年的精力,而且耗费巨资,以致此书刊行后他却负债累累贫困潦倒客死他乡。[31]他之所以投入巨大的精力、财力编辑出版此丛钞,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生敌忾之心”,希望“薄海同仇,定深义愤”,[32]并让国人“洞然于国势敌情,战败利钝”[33],为抗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而斗争。其学术救国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该丛钞所收入作品涉及地理学总论、各大洲地理状况、中国各省区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既详于本国,又放眼世界;1430 多篇作品的600多位作者,不仅有国内的学者、旅行者等,而且有外国作者40多人,分属东西洋各国。这体现了王氏中外兼容、东西并重的开放精神,而史地本身联系密切,这又开近代史地研究之一代新风,反映了史地研究的巨大进步。就西藏史地而言,作者虽视丛钞为舆地丛钞,但收入的32篇作品其实是史地一体密不可分,因而正编第三帙中收入的作品实为清代西藏史地资料的汇编。就作品内容而言,不仅有总体介绍西藏历史沿革、山川道里、政治宗教制度等概况的《卫藏识略》、《乌斯藏考》、《前后藏考》、《抚绥西藏记》(即魏源《国朝抚绥西藏记》)和《藏炉总记》、《西藏后记》等篇目,又有介绍西藏局部地区状况的《康輶纪行》(仅取原书“乍雅使事始未”纲目)、《前藏三十一城考》、《墨竹工卡记》、《得庆记》等作品,而且收入了介绍西藏周边临近国家、地区史地状况的《锡金考略》、《廓尔喀不丹合考》和《征廓尔喀记》(即魏源《乾隆征廓尔喀记》)三篇,因此作品涉及到西藏史地的方方面面,信息涵盖范围大而全,可为筹边抗敌和西藏史地研究提供多方面的材料。就作品撰写年代看,既有清开国至鸦片战争前姚鼐、松筠、杜昌丁、盛绳祖等人的作品,又有近人魏源、姚莹和编者当代人黄沛翘等人的论著,因而容纳了清初至19世纪末250多年间西藏史地重要作品, 为当时人们了解西藏和筹边御侮提供了几乎一个朝代的尽可能多的一手资料。就作品的作者而言,既有驻藏大臣松筠和久居藏地的官员盛绳祖、王我师、徐瀛等人,又有治学严谨的学者姚鼐、魏源、姚莹等,还有一些曾亲身入藏的作者,如杜昌丁、林俊、王世睿等,因而所收入作品大多是详实可靠的。当然,该丛钞收入的这30余篇西藏史地作品未附地图,且保留了原文中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歧视性的称呼,如“番”、“夷”等,都是本丛钞西藏史地部分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此30余篇作品是从清代众多的西藏史地论著中精选出来的,无论是从作品的资料性、可靠性,还是从涵盖信息的广泛性来看,都起到了补已刊行的专著如《西招图略》等书之缺的作用,对于当时人们了解西藏和总结经验教训、巩固边防、抗击侵略、维护统一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也为今天研究西藏史地保存了重要材料。可以说,此书以其集清代西藏史地之大成的特殊贡献,不仅功在当代,而且泽及后世。
总之,1888年抗英斗争的失败和英、俄对西藏侵略的加紧,使祖国神圣领土面临被帝国主义分割的危险。为支援西藏爱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王锡祺、袁昶等人积极从事于西藏史地资料的搜集、刊行工作,使多年未见刊本却又有重要资料价值的《卫藏通志》得以刊行于世,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集清代几乎一朝的西藏史地重要作品于一册,保存了丰富的西藏史地资料,不仅为当时的反侵略斗争提供了参考材料,而且推动了西藏史地研究的继续发展,也为今天的西藏史地研究、今天的西藏建设保存了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的成绩全面丰富,做了集一代大成的工作,与前两个时期相比,不足之处在于未在绘制地图方面有所建设树。笔者认为,这一不足与此间清政府下令各省赶绘地图有关,由于各省(含西藏地方)在1895年前后纷纷把绘制的地图呈报中央,并刊刻发行,所以西藏史地研究者便未在这方面着手。因此这一不足当视为客观状况使然,而非研究者的缺失,他们在西藏史地资料方面的成就仍应作为主流加以肯定。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以后至19世纪末期,随着英、俄等列强对西藏侵略的加紧和西藏边疆形势的日益危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于西藏史地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并且逐步地将西藏史地研究推向深入。从魏源、姚莹等人对西藏史地的一般性介绍、西藏地图的粗线条勾勒及筹边建议的简单设想,到黄沛翘、王锡祺等人对于西藏史地资料的广泛搜集、西藏地图的专注绘制和一系列具体务实的筹边建议的提出及开发建设的远期构想,再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和《卫藏通志》刊刻于世提供的丰富、广泛的西藏史地资料,西藏史地研究工作逐步发展,形成了持续高涨的热潮。而综观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又无不贯穿着对祖国的热爱和保卫神圣领土、坚决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精神,无不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力图把学术研究与筹边抗敌、维护祖国统一结合起来的经世致用学风,正是这种爱国主义与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动了这一时期西藏史地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对以后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时期的西藏史地研究成果是相当突出的,既有对西藏史地方面已有资料的搜集、汇编和刊刻,又有对西藏史地的多方面介绍和西藏地图的精心绘制,而且还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筹边建议和远期构想,从而不仅为当时的反侵略斗争提供了资料和可资参考的方案,而且为今天的西藏研究、西藏建设保存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这一时期的西藏史地研究不仅承前启后使西藏史地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也为当时人们了解西藏和筹边抗敌提供了资料,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今天获得了研究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宝贵文献资料。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像对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一样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注释:
[1]《中国古代史纲》(下)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参见《英国侵略西藏的早期活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 年第6期。
[3]参见《沙俄侵藏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4]《番僧源流考》为道光年间所撰,以论述西藏宗教史为主, 故未列入本文所论范围。
[5][7][8]《圣武记》第219、230、23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魏源集》第35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9][10][11]《康輶纪行》,《自叙》,卷十二,卷三。
[12]《中外旧约章》,第一册,第350页。
[13]19世纪60—80年代末清朝有关官员关于西藏的奏报也含有西藏史地的内容,因系官方奏牍性质,非自觉性的研究,故未列入本文所论范围。
[14][15][16][17][18][19][20][21][23]《西藏图考》,见《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合刊本,第35、49、38、47、49、52、49、37、79—8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25]《西藏建行省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
[24][26]《西藏改省会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三帙。
[27]《卫藏通志》作者向无定论,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松筠,今从此说。参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第567—57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 第158 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31]参见《清末地理学家王锡祺》,《科学史集刊》,第10辑,地质出版社1982年版。
[30][32]《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序文。
[33]《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