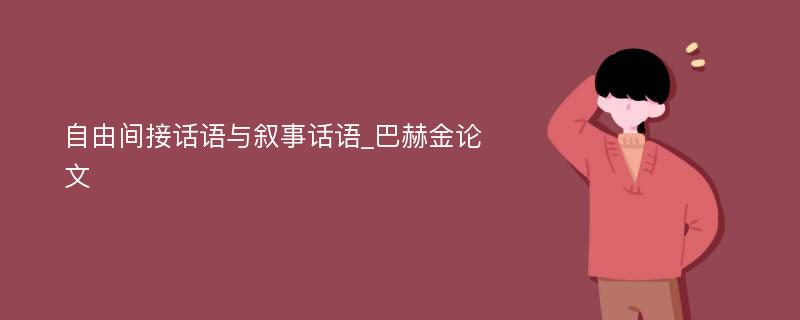
自由间接话语与叙事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声音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5-0036-06
一、自由间接话语
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简称FID)来自语法术语“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西方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界对自由间接话语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2年出版的Bally的著作《现代法语中的自由间接文体》(Le Style Indirect Libre Francais Moderne)可视为第一部系统研究自由间接话语的文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自由间接话语的论著层出不穷。60年代末及70年代的论著主要偏重于语言学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Jones(1968)[1],Bronzwaer(1970)[2],Fillmore(1974)[3],McKay(1978)[4]等。从以Genett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兴起以来,叙事学和文体学对自由间接话语与叙事声音之间关系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呈愈演愈烈之势,影响较大的研究包括Pascal(1977)[5],Genette(1980)[6],Leech和Short(1981)[7],Banfield(1982)[8],Toolan(1989)[9],Erlich(1990)[10],Fludernik(1993)[11],Fergerson(2000)[12],以及Short et al(2001)[13]等。
什么是自由间接话语?Toolan[9](第119、122页)在探讨小说角色话语再现时划分了12种语言类型:
1)纯叙事(Pure Narrative,或PN)
2)直接言语(Direct Speech,或DS)
3)间接言语(Indirect Speech,或IS)
4)直接思维(Direct Thought,或DT)
5)间接思维(Indirect Thought,或IT)
6)自由直接言语(Free Direct Speech,或FDS)
7)自由间接言语(Free Indirect Speech,或FIS)
8)自由直接思维(Free Direct Thought,或FDT)
9)自由间接思维(Free Indirect Thought,或FIT)
10)直接内心独白(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或DIM)
11)言语行为叙事转述(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或NRSA)
12)思维行为叙事转述(Narrative Report of Thought Acts,或NRTA)
其中1)可定义为叙事者直接叙事,与人物话语关系不大,即使是用以再现人物的言语和思维,也是经过叙事者的语言和逻辑加工,带有明显的叙事者色彩。当然关于这一定性的可靠性下文还要做进一步的探讨。10)实际上就是我们熟悉的意识流,虽与FDT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通常缺乏语法与逻辑的驾驭。11)和12)分别是叙事者对人物言语和思维的转述,Toolan明确指出是延用Leech和Short的术语。这两种叙事模式与PN的分界线是非常模糊的,但因不是本文的主要议题,在此不做过多评述。如果将言语和思维统称为“话语”(discourse)的话,那么,余下的8类可归纳为4种角色话语类型[9](第130页):
1)直接话语(Direct Discourse,或DD)
2)间接话语(Indirect Discourse,或ID)
3)自由直接话语(Free Direct Discourse,或FDD)
4)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或FID)
Toolan总结了6种区分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的特征:
1)DD使用人物时态;ID使用叙事时态。
2)DD使用人物代词;ID使用叙事者代词。
3)DD有明显的行文标记,如引号,另起行等;ID则没有。
4)DD框架句(framing clause)与被转述句(reported clause)之间是并列关系,二者在ID中则为从属关系。
5)DD使用人物指示语(deixis);ID使用叙事人指示语。
6)DD使用人物语言色彩;ID使用叙事人语言色彩。
那么,FID既非DD,也非ID;在以上6种特征中1)、2)和3)趋向ID,而4)、5)和6)趋向DD。Toolart指出,自由间接话语并非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的简单混合。仅从语言层次上看,FID已经不再依赖于框架句。在叙事的解读过程中,与FID相对照的不是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而是纯叙事;不区别FID与PN将导致对叙事者与人物叙事声音的混淆。
二、自由间接话语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声音
虽然在文学批评中对叙事声音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但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创立以前这些探讨都是零散和感性化的,主要体现在对单部作品叙事技巧的评论中。Genette对小说叙事声音的探讨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声音研究的开端,之后叙事声音便演变成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关键术语。其实,Genette的“叙事声音”一词是对西文语法中“语态”(英语的voice,法语的voix)的借用和延伸。在Genette的模式中,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放在“时间”、“方式”和“声音”三个标题下来讨论,这三个术语正好与西文中“时态”、“语气”和“语态”相一致。与其他结构主义批评家试图以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规律来阐释文学作品,找出与语言语法相类似的“普遍文学语法”一样,Genette的这种分类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烙印。
Pascal最早有意识地将自由间接话语与叙事声音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5]Pascal分析了在FID所表达的多种叙事者与人物的关联,但总的结论是FID所传送的是叙事者和人物的双重声音。一方面,FID再现了人物的话语,其语言表征和色彩的人物化色彩,至少在传统叙事小说中,是可以明确辨认的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从整个叙事框架看,还是叙事者在叙事,只是出于某种目的,或强调,或加强可信度,或讽刺模仿,才去刻意接近人物话语的。这种话语在真实生活,特别是口语中是较为罕见的,因此Banfield将其称为“说不出的句子”。[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来自语法概念,“叙事声音”是建立在现实“听觉”基础上的一种假说,换而言之,它借用了现实中“说—听”交际模式的比喻。小说毕竟不是录音带,小说叙事是由书面语言符号所建构的文本。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几个叙事段落的分析,来说明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功能,并阐述笔者对双重声音的再思考。为了尽量完好地反映原文的FID句子结构,本文中的文学作品段落都是由笔者翻译的。
(1)夏泼德赶紧告诉他,克劳夫将军健壮、健谈又不失英俊;见过些世面,倒也有限,所以他的思想行为都很绅士——不可能就条款方面进行难为人——只是想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而且尽快搬进来——知道要我所得到的方便付出代价——知道能满足他的要求置满家具的房子得要多少房租——沃尔特爵士多要也根本不会吃惊——早就打听过这所房子——有这么个代理人很高兴,可也不真在乎——偶尔也掏枪,可从没杀过人——非常绅士。[14](第51页)
(2)所以,在科瓦寥夫就要让司机直接开到警察局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已经表现的这般无耻的那个骗子、无赖会很容易利用这耽误的时间趁机溜出城去,这样的话他所花在找鼻子上的努力都白费了,甚至还有可能再花上个把月。真该死。[15](第52页)
(3)没关系:她并不幸福,也从来没有幸福过。为什么生活这么令人沮丧?为什么她所依仗的一切在转眼之间就化为尘埃?又为什么,假如某个地方果真有这么一个强壮英俊的人——一个勇敢的男人,感情高尚品位高雅,有一颗诗人的心和天使的外表,一个铜弦竖琴般能奏出悲壮的婚颂乐章进入天堂的男人——为什么她就不能有幸遇上他呢?[16](第322页)
这三段都是带有典型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段落。(1)除了“夏泼德赶紧告诉他”这部分为框架句外,整段全部由FID(FIS)构成。这组连续的自由间接话语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夏泼德如何极力说服沃尔特爵士把房子租给他所找的人。每一个分号和破折号前是一个理由,都可以改写成一个句子成分完整的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这段自由间接话语最明显的艺术效果是加快话语节奏。引语中主语都被省略、与框架句中的“赶紧告诉他”相呼应,人物的迫切心情表露的一览无遗。FID的人物语言色彩在这里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如“很绅士”、“非常绅士”等。由此,人物声音的再现在这段FID中是明白无误的。仅从语言证据上看,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叙事人的声音存在,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段FID之中的逻辑联系便不难发现,夏泼德的这些“理由”根本没有什么相互间的逻辑联系,纯粹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有的与租房毫无关系,甚至会起反作用,如“有这么个代理人很高兴”和“偶尔也掏枪”等。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叙事者与夏泼德这一人物是保持了相当距离的。
在(2)这段叙事中,开始的时间分句“在科瓦寥夫就要让司机直接开到警察局的时候”属于PN,“他突然想到”是框架句,其后的便可看成FID(FIT)。与(1)不同的是,这里的FID与框架句联系相对密切,没有(1)中句与句间的并列关系,也没有明确的符号标识,因此,除了最后的“真该死”外从句法结构看更像ID。但从Toolan所列举的特色(5)和(6)看,应该判定为FID。“这样的话”是明显的人物指示语,而“那个骗子、无赖”等都带有明显的人物语言色彩。“真该死”更是没有框架句依托的FID,因其祈使句的句法特征,倒更像引导外的DD,科瓦寥夫这个人物也从一个“被叙述者”变为直接面对读者的叙事人。在这一段叙事中,如果我们划一条由叙事者声音到人物声音的轴线,那么叙事声音大体上是由叙事者到人物角色方向移动的。从一个态度中立的讲故事的人,到人物语言色彩在类似ID的FID中的出现,再到更为接近DD的FID。这一段叙事话语中双重叙事声音比(1)更为明显。因为其人物言语和思维的荒唐,在转述人物思维的FIT中传达出明显的来自叙事人的取笑声。
段落(3)则彻底摆脱了框架句,完全由FID(FIT)构成。在这段心理叙事中女主人公的“浪漫乐章”显然是主旋律。但在“诗人的心”、“天使的外形”和“铜弦竖琴”这样典型的仿佛又让读者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在说“你真是太浪漫太幼稚了,真是在做白日梦,唉……”,在类似的情况下,另一些作家如费尔丁和萨克雷完全有可能用作者插入来处理,而福楼拜所用的是FID。
三、对自由间接话语和双重声音的再思考
以上三段叙事段落全部摘自19世纪传统叙事小说。对FID的界定总体上是有其语言学依据的,然而,对叙事者与人物双重声音的分析却更多的依赖于语言学以外的因素。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关键术语,叙事声音在FID中的再现却很难找到“科学”的证据。本文对双重声音的分析,特别是叙事者声音的分析,主要是从语义方面而不是从语言形式方面入手的。这种方法在分析叙事声音中是带有普遍意义的,Genette本人对Proust作品多重声音的探讨也依赖语义和逻辑分析。但是,Toolan所强调的FID与PN之分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以上三个例子中,人物话语的色彩明确无误,人物叙事声音也更容易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Toolan的6项标准并不能完全科学地区分开FID和其他叙事话语形式。一是因为并非所有的FID都带有人称代词、指示语等语言特征,导致这些判断标准中的最为客观的条目的失效,而第6条标准与前5条实际上不属于同一范畴。前5条是客观的语言学标准,而第6条却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认知标准。我们不能假定每个叙事者、每个人物都有自己专利式的语言色彩,而且读者都能对此达成共识。例如,在某一叙事文本中出现“他爱她”这么一个句子,那么用Toolan的6项标准根本无从判断它是PN还是转述DD“我爱她”的FID。如果非要作出这种判断那么只能依赖语境。
本文探讨的另一关键术语“叙事声音”的可信度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热乃本人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已明确表示,它只不过是一个从语法中借用的比喻,不能赖以建立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但其后对“叙事声音”的争论恐怕是叙事学领域内最为激烈和持久的。1991年冬季号Diacritic期刊同时登载Banfield[17]和Ducrot[18]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以Chomsky句法学为理论依托的带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语言学色彩的叙事理论与语用学叙事理论的正面交锋。Banfield曾运用Chomsky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对文学叙事中的自由间接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FID与DD实际是共有一个深层结构,进而否定了一个句子双重声音的说法。[8]当然,Banfield也论及“多重声音”(polyvocality),但这与Pascal等人讲的“双重声音”或“多重声音”是有质的区别的。Banfield所说的多重声音是纵向的,也就是说,需要在不同的句子中再现,而不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句子,Durot站在语用学的理论角度批驳了Banfield的观点,强调文学话语的语用功能,指出Chomsky的句法学不适用于分析文学话语。而Banfield的文章又是对Ducrot的反批评。
本文无意全面总结和评价这场争论,只是想借此说明,叙事声音已经作为一个相当定型化了的术语被广为使用。但是随着20世纪叙事小说的发展,对叙事声音的判定越来越困难,随之而来的叙事理论界对此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种讨论在詹姆斯小说叙事特色分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具有相当的代表性。Aczel在分析詹姆斯后期小说叙事特征时,几乎是全面否定了Genette等传统叙事学家的理论。Aczel的结论是,在詹姆斯后期小说中作者话语对角色话语的侵入是一个重要特色,作者声音对角色声音常常起着支配的作用;对FID的判定主要依赖于语境;而对双重声音的理解,巴赫金的对话性小说话语和双重音理论更为有效。[19]
巴赫金所定义的双重音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双重声音则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有些叙事学著作(如Bal1997)[20]也试图将巴赫金的理论融合到叙事学中,但Genette等原创结构主义叙事学里的“叙事声音”与巴赫金的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巴赫金所讲的双重音实际上是作者对角色的语言操纵。他(Bakhtin 1984:199)将双重音话语定义为“朝着另一个人的话语方向移动的话语”,是“作者通过在本身已有并保持着其语意意图的话语中插入新的语意意图来利用别人的话语达到自己的目的”[21](第199页)。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已超出本文的主要议题,但仅是巴赫金将作者纳入讨论视野这一点,就是结构主义叙事学难以容忍的。但是,因为正如前文所提到的,Aczel突出强调了詹姆斯后期小说叙事人对角色声音的支配,Aczel引用巴赫金的理论倒是非常自然和恰当的。而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技术性术语的“叙事声音”归根结底还要还原到“谁说”这一个基本点上。如果说在前文所分析的几个19世纪小说的叙事例子中,叙事声音还大体上可辨的话,那么在Aczel所列举的詹姆斯《大使》中的“It wouldn't do at all,he saw,that anything should come up for him in Chad's hand but what specifically was to come;the greatest divergence from which would be precisely the element of any lubrication of their intercourse by levity”[19](第31页)这样的叙事中,叙事者语言色彩和角色语言出现在一个句子框架中,如果非要分辨叙事声音的话,那么我们听到的不再是两个可辨的叙事者的角色的双重声音而只能是这两种声音的混合。而这种分析已经不能回答“谁说”这个问题了。
以上的分析已经足以说明,有较为充分的语言特征的自由间接语言在小说叙事中并不总能仅靠其语言特征就可以分辨。语境在分辨自由间接话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叙事声音辨别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认知;通过分析叙事话语结构本身来寻找叙事双重声音至多只是一种幻觉。
四、结语
自由间接话语是小说叙事中再现人物话语的重要手段,也是相当于其他再现话语形式而言最为复杂的一种。自由间接话语在不同的叙述文本中有不同的功效,但在传统叙述小说中大体是可以分辨得出它所传送的叙事者与人物的双重声音,不论叙事者的声音是对人物话语声音的强调、模仿还是嘲讽。
然而,叙事声音毕竟是建立在说—听这一交际流程比喻之上的一种假说。Genette在将其纳入结构主义叙事学时主要是用以与叙事角度建立在视觉比喻上这一传统叙事理论概念相对照的。在20世纪复杂的叙事文本面前,不仅是叙事声音变得模糊化,而且自由间接话语也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明显的语言学标记和表征。
巴赫金的“多重声音”(polyhony)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声音是不同的概念。不论如何比较,巴赫金所强调的小说话语乃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构成,多重声音所体现的是多重社会与文化建构。[22](第44页)随着文化研究在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日益得势,巴赫金的理论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重新走上前台。但是,巴赫金的理论却不能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叙事声音的参数。
本文所分析的作品仍然属于较为传统的叙事文本,如果从文学流派来讲可以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后现代实验体小说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带来的冲击以及解构主义思维模式对结构主义的全面肢解并未纳入本文的视野。通过观察传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声音分析模式在新的小说叙事文本面前的窘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叙事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已成为必然。只有将性别、阶级、种族、社会与文化这些人的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以对具体叙事文本的解读建构作为出发点,彻底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模式,这一新兴学科才能重现新的生机,才能如Rimmon-Kenan所说的那样,使叙事学成为一种“永恒变化、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23](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