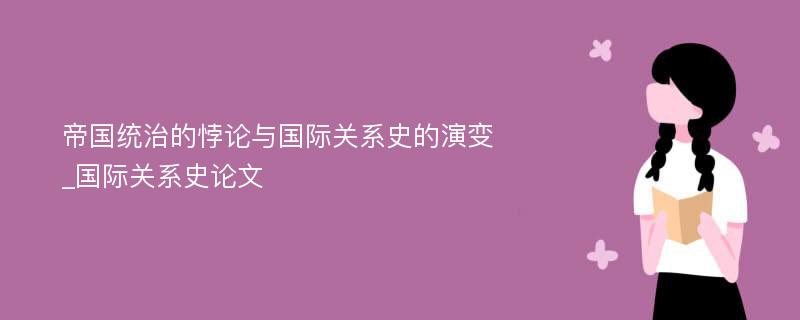
帝国统治的悖论与国际关系史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悖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之后,国际关系史经历了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存亡,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之间的攻伐战争使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到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规则也是以殖民帝国的形式传播到全球。帝国既是一种政治单位,也是一种国际体系。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农业帝国、游牧帝国和殖民帝国等不同帝国形式,三种帝国的兴衰源于其内在的悖论,农业帝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中上演着统一与分裂的剧目;游牧帝国则需要调和定居与移动之间的难题,殖民帝国受困于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矛盾。农业帝国和游牧帝国对峙与并存了几千年,终结于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则被其宣扬的主权、民族主义等因素撕裂,帝国的时代也就落下了帷幕,但是帝国的遗产依然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 农业帝国是人类组织形式的一种跃升,通用语、文字、宗教、货币、驿站系统的出现为农业帝国铺设了权力的基础结构。农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灌溉农业的出现为农业帝国奠定了经济基石。“因为不断增大对土地的利用,所以整个趋向是朝着更大的社会和地域的固定性。农业的成就与束缚是分不开的”。①对土地不同的依赖性使农业与游牧成为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农业是一种延迟回报而非即时回报,需要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周期性的耕作。世界闻名的农业帝国分布于河谷地带,灌溉农业意味着对水利设施的依赖,对个体也是一种束缚。因此,“农业帝国的中心都位于人口稠密、农业产品丰富的区域,并且常常有主要的交通运输线——通常是适于航运的江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黄河)——构成了帝国的主干”。②可以说,农业帝国将自己“囚禁”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中,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网络在分裂之后,若没有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系的吸引,则这片广大疆域的次级体系势必再度凝聚为一个个整合的体系”。③ 农业帝国要有效治理广袤的土地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实现领土范围内权力的集中化、制度化。帝国有两种手段实现对广大地域的控制:郡县制和封建制。前者是纵向一体的官僚制度,后者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古代世界中,军事活动能力的半径大约为90公里,即便是纵向一体的郡县制度也很难实现对帝国的严密控制,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地方长官久居一地便可以割据称霸,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巡视四方或者安排亲密之人监督地方长官。依靠官僚制度实现对帝国的统治,是帝国统治者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面对的是一个破碎化的社会权力结构,帝国境内存在多元小共同体,或者通过血缘或者通过地缘连为一体,这种共同体的格局对帝国中央政府权力的渗透是一种障碍。这种社会结构不但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而且还可以与帝国政府博弈,国家权力占据上层的地位,社会权力则占据基层地位,国家权力无法完全渗透到社会基层,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社会基层精英的支持。 在帝国统一的外表之下是多个分权的集团,帝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各种权力下放到地方,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交给地方统治者,而只保留军事指挥权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已经盛行,庄园主成为介于帝国最高权力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中介,这种情境必然会增加庄园主在帝国权力网络中的地位,“当保持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治制度的负担超过了社会经济、精神资源可承受范围时,封建主义就出现了”,④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封建秩序转型深刻地体现了帝国分权与集权的悖论。 农业帝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中演绎着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剧目,而游牧帝国则无法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积聚权威,游牧的生产方式需要在不同的牧场中转移。“流动性和财富积累是截然对立的”,⑤这种内在的悖论使游牧帝国能够掀起征服的风暴,但是很难建立自己的文明,关于游牧帝国的记载多半源于周边的农业帝国。 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欧亚大陆、东非、阿拉伯半岛等地,游牧部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依侍马匹或者骆驼作为骑乘工具,游移于草原与沙漠之中。与农耕生产不同,游牧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不看重,他们需要的是牧场的使用权。“对游牧民而言,时间与空间是相关联的部分:他们与在一个特别的时段使用一块牧场有关,或者对诸如水井投资的财产权的保护密切相关;独有的土地所有权很少有其内在价值”。⑥游牧生产面临着脆弱的生态环境,财富的积累主要体现在牛羊等牲畜,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使财富的积累很难持续下去。依靠财富很难积累自己的权威。生产的移动性使支配与强制关系难以确立,若遇到压迫性的首领,可以举家迁徙,重新开辟牧场。因此,“游牧民族本来是高度民主、奉行平等主义的,直到一些战争首领建立了国家”。⑦ 游牧民分散灵活的生产方式与战争连为一体——马匹或者骆驼提升了游牧帝国军队的机动性。劫掠与征服使游牧民对定居的农业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比如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劫掠作为一种文化的融合机制(integral mechanism),借助外部的冲突减少血缘社会内部的冲突”。⑧当游牧帝国迅速向周边地区推进,飙起劫掠风暴时,他们依然将占领地区视为一种战利品,而不会“让帝国的统治完成从剥削性的方式向投资性的或者说传播文明的方式过渡”。⑨一个以在空间移动中维系生存的民族,其本性并不适应建立一个空间固定的帝国约束自己的行动自由,游牧帝国在空间移动的本性及其劫掠的生存策略使之具有剥削偏好,他们可以在瞬间破坏一个世界,但是却不愿意重建一个新的世界。 游牧部落的首领可以依靠暴力征服广阔的领土,但是很难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比如作为权力象征的首都。走向定居意味着对游牧生产方式的否定,但仅靠游牧生产的财富不足以建立帝国。“一位游牧首领或许会凭借军事才能统一草原,但要保持草原帝国的完成,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中原能够提供。匈奴的内战表明,当游牧民族被迫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生存时,他们的大规模政治结构就会瓦解”。⑩ 游牧帝国中生产分散、移动的要求与帝国在空间固定的逻辑的矛盾最终使游牧帝国面临生死抉择:要么向定居帝国转换,但这要以牺牲游牧生产分散、自主抉择的灵活性为代价;要么帝国在完成劫掠后土崩瓦解,消失于无形。 游牧帝国和农业帝国在冷兵器时代对峙了两千多年,最终都被囊括于殖民帝国体系之下。殖民帝国可以远溯至腓尼基或者雅典,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贸易体系,是近代帝国的先驱。而真正的殖民帝国时代则源于西方近代的殖民运动,商业殖民帝国时代,只是在沿海建立了一系列的商站网络,19世纪中期以后,凭借蒸汽机、铁路、机枪、奎宁等现代工业力量,全球性殖民帝国出现了。 殖民帝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又控制着广大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被认为是民族国家,而它却是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核心区域;现代美国的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关岛却被按照帝国的原则进行统治”。(11)民族国家基于平等的公民权而建立起来,但殖民帝国的海外统治者们要面对着“落后民族”和“低等种类”。(12)殖民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强大意味着对民族性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否定。 殖民帝国还面临着内在的悖论: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冲突。对于殖民帝国的起源有很多理论模式,但对利润的追求是主要的驱动力量。殖民帝国也是军事—金融复合体,持剑经商的理念一度流行。格劳修斯就认为,“私人贸易公司像传统欧洲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发起战争”。(13)殖民地为宗主国提供了一种避免利润率下降的选择,就像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的功能,“时空修复不过是一种隐喻,以此来形容通过空间的扩张和时间的延缓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14)通过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将过剩资本投入到交通通讯、教育、科研等自然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部分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的利润下降或者过度积累的危机。 殖民地并不能永久性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随着商业殖民主义向工业殖民主义的转变,对殖民地的介入和控制更加深入,涸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开发,导致殖民地社会失序、经济崩溃,为了继续在殖民地维持统治,宗主国不得不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殖民帝国向殖民地派驻军队、警察,对殖民地进行直接领土控制。军事征服与资本扩张齐头并进,“无独有偶,军事活动高度制度化之际,正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巅峰到来的时间。在殖民地的重要城市中,高效专业的机构为训练职业军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殖民者耗费相对少的资源而达到利益最大化”。(15)领土的逻辑要求宗主国将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于殖民地,但改造殖民地社会结构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领土控制的逻辑与资本逐利的逻辑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殖民帝国的崩溃也就难以避免了。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除了殖民地的反抗之外,殖民帝国内部危机也是重要的原因,更注重资本逻辑的大英帝国采取了主动撤出的策略,而偏重领土控制的法国则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殖民帝国最终被主权国家体系所取代,但帝国的逻辑却并未消失,主权国家承担了领土控制的责任,而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自由化,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宣称:“如今帝国的存在是既有事实,就如同在英国统治并塑造着现代世界的300年间一样。”(16)帝国,并未远去。 ①[英]迈克尔·曼著,刘北城、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9页。 ②[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③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④[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著,华佳等译:《现代国家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⑤[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等译:《石器时代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页。 ⑥[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⑦[英]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从苏美尔到罗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⑧Louis E.Sweet,"Camel Raiding of North Arabian Bedouin:A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7,No 5(1965),p.1148. ⑨[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阎振江、孟翰译:《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⑩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13页。 (11)Andreas Wimmer and Brian Min,"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1,No.6(2006),p.871. (12)[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3页。 (13)[美]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4)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15. (15)Joseph R.Strayer,"Empires-Some Reflections on Roman and Modern Imperi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66(1),p.102. (16)[英]尼尔·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