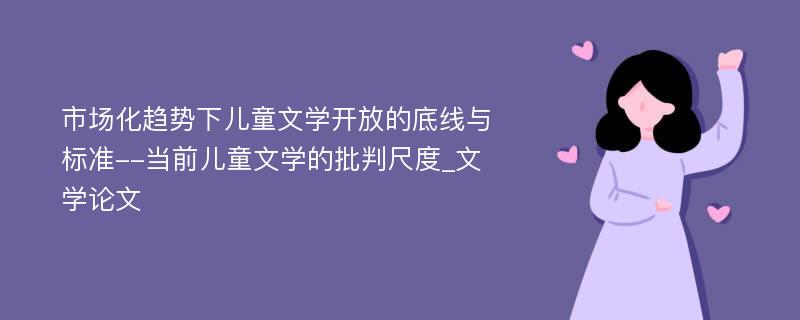
市场化潮流中儿童文学开放的底线与碑石——论当下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文学论文,碑石论文,尺度论文,底线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市场化潮流中,谈论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显然不合时宜。客观地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市场化冲击的时候,儿童文学似乎应该对市场化时代怀有感恩之心。至少,与被边缘化的成人文学相比较,儿童文学在市场中的读者群、发行量一直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甚至有一种增长的势头①。尤其,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原创力的增强,儿童图书文化市场已经改变了国外引进出版物一统天下的格局,由此拉动了对本土童书的内需。然而,儿童文学界固然可以相信销量就是硬道理的市场化逻辑,但是否可以据此漠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或困境?如何理解儿童文学在市场化潮流中的开放性?如何理解儿童文学开放性中的文学性、经典性?基于这些问题,我试图对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作一思考,并由此牵连出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特征。
儿童文学批评亦是“重读的艺术”
九十年代初期,当代文学研究者黄子平借助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文学批评即重读的艺术”②。儿童文学批评既然属于文学批评的一种,以“重读的艺术”作为其批评尺度同样有效。如何理解“重读的艺术”?罗兰·巴特在《S/Z》一书中指出:“所谓重读,是一桩与我们社会中商业和意识习惯截然相反的事情。后者使我们一旦把故事读完(或曰‘咽下’),便把它扔到一边去,以便我们继续去寻另一个故事,购买另一本书。”③ 罗兰·巴特针对的不仅是商业文化本身,而且是商业文化纵容下的读者的阅读陈规。在罗兰·巴特看来,不遵从“重读的艺术”的阅读即是一种“即弃式”的阅读。“即弃式”阅读培养的只是读者的消费习惯。对此,黄子平的解读非常透辟:“即弃式的阅读其实读到的总是‘我们自己’,从一个文本中理解到的仅仅是我们以前已理解的东西,一个定式,一个已研读过的固定文本。也就是说,不同故事的消费等于同一个故事的重复。”④
儿童文学批评当然差异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即儿童文学批评应该考虑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如何理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我们不妨参考朱自强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的论述:“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如历史上教训主义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⑤ 不过,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立关系,正如朱自强的论述中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儿童与成人的可贵品质叠合在一起才构成丰富的人性。而且,正是因为儿童处于一个人一生中打底子的时期,儿童文学批评才承担着超出一般文学批评之外的要义。进一步说,儿童文学批评就是要以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有益于儿童成长的精神生态环境作为批评尺度。如曹文轩所说:“文学能给孩子什么?文学应给孩子什么?在拥挤嘈杂的现代生活节奏中,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净化孩子的心灵,培养出健康的精神世界?道义感、情调和悲悯情怀,是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关键元素。”⑥ 从这个意义出发,儿童文学批评应该自觉意识到儿童文学对儿童创造力的“挑战”、对儿童“再阅读”的可能性的提供,对儿童从同一个故事中产生无穷无尽的故事的想象力的开发、对儿童“自我”的小小胚胎的培育。而这一切都只有经过“重读”才能实现。
不必讳言,将儿童文学批评理解为“重读的艺术”,其实隐含着这样的话语:儿童文学批评不是以一种貌似儿童为本位的立场来取悦于儿童,而是以一种理性的儿童为本位的尺度来理解读者。依据理性的尺度,我以为: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划分为“可重读的”和“不可重读的”。“可重读的”作品培育的是模范儿童读者,“不可重读的”作品培养的是经验儿童读者;“可重读的”作品具有经典文学的品质,“不可重读的”作品具有快餐文化的特质。尽管在市场化潮流中,快餐文化是大众文化的一种,但从儿童这一未来国民群体的培养来说,快餐文化的即时性、消费性无法给儿童的成长带来深远的养分。同样,尽管儿童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更多地来自自发的兴趣,但随着儿童的成长,“一到他能自行考虑如何才能获得他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一到他能了解一些重大的关系,从而能判断哪些东西对他是合适或不合适的时候,他就有区别工作和游戏的能力了,他会把后者当作前者的消遣了”⑦。到这个时候,“可重读的”作品就可以让他获得真正有用的东西。而在儿童读者与“可重读的”作品相遇之前,“模范读者”的角色则由儿童文学批评者来承担。
如何理解“模范作者”?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符号学理论。艾柯认为:“一个故事的模范读者不是经验读者。经验读者就是你、我,或者任何在读着小说的人。经验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去阅读,没有条例能规定他们怎么读,因为他们通常都拿文本作容器来贮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而阅读中又经常会因势利导地产生脱离文本的内容。”⑧ 艾柯对“经验读者”的界定显然来自对“模范读者”的参照,即他假定有“一种理想状态的读者,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如果按照读者的立场,艾柯所命名的“经验读者”的阅读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但如果从文本和作者的立场,“经验读者”就是在用一种“不对”的方式在解读文本和作者,因为“经验读者”是跟着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文本的情节、作者的意图在阅读。儿童文学批评承担着“模范读者”的要义:儿童文学批评完全可能用批评者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文本和作者,但不能只顾寻找自己的经验,因为儿童文学批评是为所有的儿童文学所确立的理性尺度。即儿童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连接儿童、文本和作者的肌腱。所以,儿童文学批评的价值在于坚持“重读的艺术”尺度。“重读的艺术”为儿童读者推举的不是消费品,而是艺术品。
文学性:儿童文学开放的底线
市场化潮流中,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依然以文学性作为谈论问题的起点。道理并不难理解:儿童文学是否能够经久地作用于儿童心灵取决于文学性要素的实现。正是儿童文学作品多重的文本寓意、独特的人物形象、机智鲜活且带有文化底蕴的语言、神奇的想象力、奇巧的故事情节和惊人的细节等具体要素,才调动了儿童的阅读、影响了儿童的心智,由此规定了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
市场化时代虽然为儿童文学的传播与生产提供了开放性的文化空间,但无法逾越文本作为意义存在的底线。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固然可以在图书市场上以鲜亮的装帧、出版方的宣传、书评人的书评、作者的签名、作者与读者的面对面交流等等方式推动图书的发行,可真正打动、吸引、提升读者心灵的原因在于其文本世界的多重寓意。一般说来,儿童文学的文本意义不似成人文学那样追求深刻的主题,单纯的主题更适宜于儿童透明的目光。但单纯不是单薄,更不是肤浅。正如透明的光线中隐含着千变万化的色彩一样,儿童的阅读期待并不能满足于一次性消费的确定性意义的单面作品。巴西当代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发表于1988年的一部畅销书,至2000年仅在国内就印了一百五十八个版次之多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心灵抚摸,而是一种关于远方、梦想、选择、心灵、倾听、勇气、执著、智慧、幸福等多重形而上意义的追问,正如作者所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象征性的作品。”⑨ 寓意丰富的当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不乏其例。曹文轩的长篇小说《根鸟》、《大王书》和秦文君的长篇小说《天棠街三号》皆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无限解读的文本世界。《根鸟》和《大王书》讲述的是东方少年逐梦的故事。梦想作为少年成长中的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大书,寄予了丰富的寓意。小说汇聚了梦想、寻找、苦难、勇气、犹疑、欲望、幻灭、天启等多重要义。小说没有嫁接在西方文化的链条中,而是着力复现在东方古典美学的根基上。在多重要义的交织下任情节展开,纠缠、厮杀,读者一路读来收获了神奇、新奇、惊奇等诸种震撼之感。《天棠街三号》以“天堂”这一寄寓着多重形而上意义的中心意象作为小说结构,承担着整个文本的象征功能。围绕这个中心意象,等待、温暖、亲情、友谊、伤痛、宿命等等少年在成长阶段的普遍性体验,乃至人的普遍性欲求都在文本世界中被叙写。如果说上述关涉成长小说更多地呈现出意义的复杂性一面,那么童话等文体则为低龄儿童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意义“单纯”的阅读空间。但如果以为低龄儿童读物只是表现单一性的意义,无疑是一个误会。安徒生童话之所以与孩子产生精神联系,儿童文学研究者李红叶认为源自三个层面的意义:“同情意绪”、“欢乐意绪”、“成长意绪”⑩。诗人金波的近作《乌丢丢的奇遇》是一段关于生命和爱的祈祷,内涵丰富。总之,以儿童文学批评的尺度看来,让多重意义并存的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够充分实现儿童文学的本质要义。
儿童文学仅仅依靠丰富的寓意还难以赢得自身的审美魅力,饱满、鲜活、独特的儿童人物形象是儿童文学的依傍之地。市场化潮流可能改变儿童的阅读方式,却无法漠视儿童人物形象这一底线。儿童文学由于儿童这一特定阅读对象对于形象的敏感和需求,将形象塑造作为儿童文学的第一要义并不为过。姑且不说叙事类儿童文学的故事情节的设计最终是为了塑造儿童人物形象,就是非叙事性文体,譬如儿童诗,也通常着力于形象的意象并伴随着隐约的叙事之链。很难设想:米兰·昆德拉式的深刻、思辨的语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段的意识流动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儿童的天性就是喜欢按照游戏的思维方式与故事中的各种形象打交道。尽管儿童不具备成人的知识结构所赋予的理性分析力,但他们与生俱来的简单明了的直觉判断力则可以辨析出作品形象的魅力值。依据儿童成长期的心理,一味善与恶的形象并不能博得他们的青睐。尽管儿童的善良天性常常同情于那些弱势人物,但真正让他们推崇和着迷的则是那些具有英雄色彩的强力人物。譬如:彼得·潘、长袜子皮皮、机器猫、小木偶、爱丽丝、哈利·波特等等。与此同时,魔法师式的形象对于儿童而言也具有一种挡不住的神秘感和诱惑力。可以说,儿童阅读中最过瘾的事情就是与王子或仙女同行,或者与魔法师过招。当下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由此沿着写实与幻想两条路径获得了儿童的欢迎。在写实的道路上,以往宏大叙事话语中的“英雄”、“好孩子”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经历了苦难与挫折的邻家兄弟姐妹、“顽童”、“另类”、“快乐天使”,如桑桑、细米、青铜、葵花、贾梅、贾里、马小跳;在幻想的道路上,西方童话中的儿童形象被注入了东方文化精神,如乌丢丢、根鸟、芒等。然而,不得不承认,如此具有生命感的儿童形象在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其中原因,以儿童文学批评的理性尺度看来,一个症结在于作者与儿童形象的关系缺少理性的认知。一个具有生命感的儿童形象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家一定听命于儿童的阅读兴趣。事实上,儿童文学作家书写的儿童形象并不是儿童本身,而是作家自己的儿童经验和体验。基于此点,金波直言不讳地阐释他自己的“童年的诗学”:“我能为儿童写作,这是最自然的事情。我不必变成孩子,再去写孩子,我写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鲜活的童年体验。”(11) 事实也是如此:饱满、鲜活、独特的儿童形象理应是儿童文学作家以理解与倾听的态度对儿童的想象。此中真义,鲁迅早已阐明:“觉醒的人”与“新人”之间的关系,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12)。由此,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形象的关系即是进入文本之后的疏离,儿童文学作家有责任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将儿童从消费阅读引导到审美阅读中来。
儿童文学的寓意和形象归根结底依靠其艺术形式。儿童文学对艺术形式的要求与成人文学不同。儿童的趣味、习惯与方式,不能以成人的标准来简单地加以要求。前不久,泰州市三所小学随机发放二百多份《儿童阅读习惯问卷调查表》。调查显示:在“最喜欢的书”一题中,不少学生填下五花八门的漫画书名,少数学生填的竟然是《谋杀村》、《鬼吹灯》、《地狱船》等惊悚恐怖题材的书籍(13)。尽管这个调查结果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尚属疑问,但悬疑这种高强度的故事情节确实能够吸引儿童。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儿童文学也可以称为“故事文学”。问题也正在这里。我认同艾柯的观点:“故事和情节并非一种语言的功能,而是一种通常可以完全被翻成另一种符号系统里的结构。”(14) 市场化潮流中,人们可以轻易地将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重新改写,或改编成动漫和漫画书,乃至影视剧,可作为经典文本的艺术形式却遭到某种程度的损害。正因如此,在市场化潮流中,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的特殊性是不应以牺牲其文学性的底线为代价的。无论故事情节多么奇巧,富有文化底蕴的语言,神奇的想象力,精湛的细节描写都是衡量儿童文学质地的评价标准。这样,从另一个意义来说,儿童文学就是一种文本世界,而非故事。更明确地说:“儿童文学存在的依据——文学性。”(15)
经典意识:儿童文学开放的碑石
儿童文学研究家樊发稼曾经提出:“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16),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可谓当下儿童文学批评不可缺失的标尺。然而,在当下市场化潮流中,对于缺少宗教情怀的中国作家,儿童文学的经典意识自觉受到很大冲击,可以说日渐稀薄。可是,倘若儿童文学批评确实从理性的尺度出发,就会发现:经典意识的自觉是儿童文学开放性系统的确证。因为儿童文学的开放性意味着儿童文学不应仅仅关注当下儿童,更应着力于未来的儿童。一个不关注未来的儿童的儿童文学是封闭的系统。那么,儿童文学如何实现经典意识的自觉?唯一可能正确的方式即是不再局限于当下儿童的固有对象,超越儿童文学自身的有限空间,进而努力使儿童文学处于开放性系统之中。只有这样的觉醒存在于当下儿童文学作家心目之中,儿童文学作品才可能达到最大的开放程度,并由此接近并抵达经典的尺度。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论证的依据:2006年1月,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纪长城”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第一辑(二十五册),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系囊括了从五四至今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作,从叶圣陶、冰心、陈伯吹、张天翼到严文井、金近、郭风、任溶溶,从任氏兄弟、孙幼军、金波到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以至年轻作家汤素兰、彭学军,他们光彩熠熠的名作尽收其中。同时还展示了香港、台湾儿童文学名家的创作成果。而从文体、样式来看,除儿童剧、影视文学外,小说、童话、诗歌、散文、科学文艺、寓言,应有尽有,相当齐全(17)。尤其,这套书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具有经典意识的评价尺度,即这套书的作品整体上符合“重读的艺术”:读者在对这套书的阅读、品味和感悟中,通过对儿童情感和存在样式的体验和把握,往往能够提升、丰富自己的生存智慧,并从文本世界的细节处体味到恒久的审美价值,正如这套书的总序所说:“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18)
当然,对于当下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具有自觉的经典意识是一回事,是否接近并抵达经典的品格则是另外一回事。当下究竟有多少儿童文学作家有耐心接受时间的检测,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市场化潮流中的儿童文学虽然相遇了开放性的机缘,却又放逐了经典的碑石。可是,经典的尺度并没有因为市场化潮流而有所改变。无论文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至少呈现出如下品质:其一,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与作家的人格密切相连。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在时间中可能被重评,但难以被遗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这些作品灌注着作者的人格力量。其二,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超越儿童与成人的边界。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经具有了经典的开放性,也便对一切读者敞开了文本空间。同样道理,正如职业儿童文学作家也会兼顾成人文学创作一样,以成人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未尝不可以创作出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的《社戏》《朝花夕拾》、废名的《桥》、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漫游记》、汪曾祺的《受戒》可以说书写了另一种脉络的经典“成长小说”。其三,经典化的儿童作品往往具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底蕴,并呈现出文学史的文脉。大凡具有经典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即便是以时尚的现代文化作为主打文化的作品,也仍然是文化史和文学史链条上的写作。其四,经典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具有人类的视阈,并善于汲取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的滋养。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儿童叙事作品,既是参照,也是养分。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克莱齐奥的小说长篇小说《金鱼》和《乌拉尼亚》、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海底隧道》,借助儿童视角,将时代的风云、残酷的现实、生活的无奈、生命的无常、无常中的悲欢全部放置在人性的透视中。还有罗琳的系列小说《哈利·波特》,它的轰动效应一定有耐人寻味的道理。
在市场化潮流中,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相逢了开放性的机缘,同时也陷入了封闭性的危机。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声音固然微弱,但理性的尺度依然不可放弃。那就是应该坚持这样的儿童文学批评观: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被看作商品,故事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读者的看点,语言可以时尚化、娱乐化,但文学创作的底线不能逾越,对经典的敬畏意识不该消解。
注释:
① 王佳欣:《出版社大多涉足少儿出版,福兮祸兮?》,“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调查数据显示,全国579家出版社曾经涉足少儿图书出版的出版社已达519家,也有业界人士坦言,如今没有涉足少儿图书出版的出版社是越来越少了。”人民网2009年3月23日,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9004965.html。
②④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176、1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罗兰·巴特:《S/Z》,77页,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16—17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
⑥ 曹文轩:《文学应给孩子什么》,见《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⑦ [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尔》,1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10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⑨ [巴西]保罗·科埃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丁文林译,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⑩ 参见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11) 金波:《珍惜童年的记忆》,转引自徐鲁的《儿童文学的花灯与盛宴》,见《广州日报》2008年8月15日。
(12) 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 孙飞、徐霖、王亦清:《调查显示:儿童读物不敌教辅书》,见《泰州晚报》2009年4月3日。
(14)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39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 这是曹文轩于2006年4月在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新浪亲子中心网络支持的“中国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趋势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
(16) 樊发稼:《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见2006年4月樊发稼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新浪亲子中心网络支持的“中国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趋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17) 束沛德:《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的价值》,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27日。
(18)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高端编选委员会:《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总序》,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