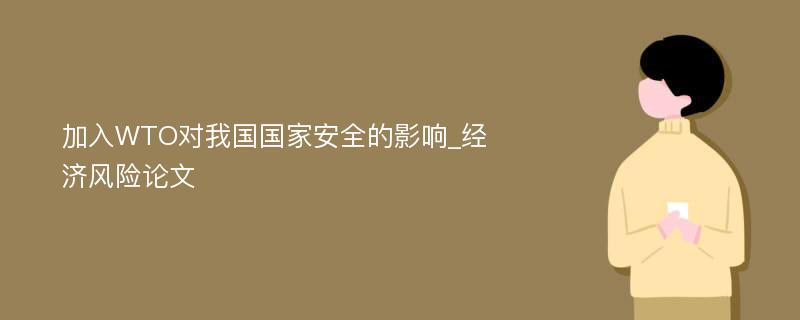
“入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交锋和艰苦的谈判之后,终于在北京签署了两国间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漫漫13年之后,终于在“叩关”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尽管中国还需要完成与其他世贸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谈判,但由于美国在世贸组织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及其所处的特殊地位,中美两国间关于中国“入世”谈判的成功,则意味着中国在“入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排除,中国在2000年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已成定局。
世贸组织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不仅是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而且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和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战后以来,作为世贸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通过它所主持下的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等多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资金、劳务和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流动和合理化配置,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这些谈判所达成的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各国间经济交往的纽带。在经济竞争日益取代传统的政治与军事角逐而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焦点的今天,拥有135 个成员国的世贸组织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代名词和维护当今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支柱。不加入世贸组织这个“经济联合国”,就无法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合法经济权益,无法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红利,就意味着被国际社会孤立和遗弃。
但世贸组织毕竟是一个以西方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在它主持下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特色。加入世贸组织,并接受它的各种规则的约束,至少部分地意味着对西方经济理念及其游戏规则的接受和认可。由于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西方主导下的世贸组织及其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而在70年代我国重返联合国时,并未主动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进入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大工程的启动,我们逐渐在主观上改变了对这一机构的认识,并于1986年提出了“复关”的申请。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日益认识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这个全球性经济组织声望的提高及运作的正常进行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将中国纳入这一组织后对其维护和谋取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与世贸组织之间的差距;因而,中国艰难的“入世”之路终于走到了瓜熟蒂落的阶段。
但中国的“入世”,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与差别彻底消除。在全球范围内同化和根除共产主义,是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是它们的长期战略目标。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实质,仍然是要利用和通过对华“接触”,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改造”中国。就中国“入世”本身而言,西方国家先是惧怕中国“入世”后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并扩大影响,因而一直不断设置障碍,但在这一政策濒临破产的今天,西方国家转而改变策略,寄希望于通过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多边经济体系,利用中国不得不向全世界开放的机会,借世贸体系之力,实现演变中国这一战略目标。克林顿总统在评价中美之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这一事件时,再次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美方的这一战略意图(注:新华社华盛顿11月15日电:《克林顿发表谈话,欢迎中美就世贸问题达成协议》。)。
就中美两国而言,除了上述固有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外,还有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冲突,那就是近年来美国顽固地将中国认定为它所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并必欲除之而后快。根据西方的霸权稳定理论,一个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必将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霸权国家体系,并以维护这个体系的稳定为己任,同时为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但相对于这个霸权体系的稳定及维护这个体系稳定的霸权国家而言,惟一的威胁就是这个霸权体系的挑战者。因此,霸权国家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及霸权体系的根本方式,就是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霸权挑战者(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178~184页。)。在战后40多年中,美国一直将苏联界定为它所主导下的霸权挑战者。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战略家们经过仔细的考察之后,发现在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中,惟有中国有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了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美两国间这种特殊关系形态的存在,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以遏制和削弱中国为主的本质内容。因此,尽管中国的“入世”会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但中国与美国以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并不会完全消除;与此相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斗争的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中国“入世”后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因此,如何尽快提高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艺术和水平,以适应“入世”后新的安全形势的需要,将是我国今后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课题。
“入世”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为直接的冲击来自于经济领域。首先是金融安全。这是因为,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是市场配置关系的主要形式,金融体系安全、高效、稳健地运行,对经济的全面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由于金融业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波,从而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自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金融问题, 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东南亚、东亚各国的经济实力,这场危机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损失超过了2000亿美元,经济发展普遍倒退了10年左右(注:曹建明:《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中经网。);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还导致了有关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政府更迭。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有关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程度相当。在当今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金融领域的斗争更是揉合了许多与金融业务本身无关的政治性因素。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战略时,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是“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是“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是“掌握国际资本市场”(注: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二版,第75~76页。)。 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竞争中的基本战略。无独有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不光彩行为的默许和纵容,更使一些有识之士将这场危机看作是一场以经济形式发动的、针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阴谋(注:利可求:《冲击亚洲货币大阴谋》,香港中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3月第二版,第5页。)。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必须指出,在我国金融业中也隐藏着较大的风险隐患。例如: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一些地方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乱搞集资的问题比较严重;证券、期货市场和股份制改革、运行不够规范;不合要求、不规范运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多,效率低下;外债风险日益显露;金融犯罪特别是金融诈骗犯罪日益突出等等。我国当前金融业本身存在的这些风险隐患,是长期以来逐步积累下来的,原因比较复杂,相关因素也很多,既有过去旧的经济体制弊端问题,有内部管理问题,有经济行为不规范问题,也有金融立法滞后,执法不严问题,等等。这也正是我国在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入世”后我国金融安全的风险除了我国金融领域本身所固有的内部风险外,还将面临由于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而带来的国际风险。尽管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后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确定了五年的过渡期,但由于中国金融行业整体的脆弱性、中国金融运作体制与世贸组织所主导下的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的长期存在,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是中国“入世”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产业安全是我国“入世”后经济安全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产业安全就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各种国家安全因素,并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安全状况(注:赵英、胥和平、邢国仁:《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第50~51页。)。对产业安全的分析,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以何种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提供支撑和依托;二是如何在面对外来冲击与挑战的情况下,确保国家产业体系的安全。长期以来,由于受两大阵营对峙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建立起一整套相对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产业体系,它是我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基础。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的不利影响,这一产业体系在与世贸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行业条块分割、整体效率低下、竞争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等种种弊端。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当我国的传统产业体系不得不与世界产业体系全面接轨时,就会暴露出许多的缺陷与漏洞,从而产生巨大的不安全风险。在与国际企业的全面竞争中,我们的有些企业可能会彻底倒下,有些可能会被外资并购和整合;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更加广泛,在国家安全领域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随着人员交流的增多,可能会带来艾滋病、毒品以及消极文化等负面影响的上升,而农产品市场开放之后有可能引发农业环境安全问题,随着开放的扩大,还有可能对一些封闭地区,特别是一些敏感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等等。
对“入世”后我国国家安全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首先要加强和深化对世贸体系及其风险的研究,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要建立起以学界、军界、外交、安全和经贸界为核心的、官产学为一体的、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参加的国家安全与风险研究机构,要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以及在它的主持下各成员国间达成的各种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进行深入而细致的了解和研究;同时,要比照我国与一些世贸成员国间已经达成的双边协议,认真评估“入世”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以及对各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并就机会利用与风险防范提出比较详尽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其次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体系的科学认识,加大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尽快建立起完整的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相衔接的、适应现代社会诉求和全球化趋势需要的新的国家制度体系,从根本上奠定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和化解安全风险的体制基础。再次是要加快企业改革的步伐,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能力。这一方面我们要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为着眼点,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推动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效能;另一方面,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精心培育和完善现代企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推动各个行业之间、国内和国际企业之间公平竞争、互利合作的良性发展。最后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要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既要加快法律空白地带的立法建设,也要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大幅度的适应性修改,提高立法的及时性和科学性;要深化体制改革,坚持严格执法和科学执法,真正树立起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
关于国家综合安全问题,在我国早已进行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讨论,但由于我国相对封闭于世界体系之外的特殊环境,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式的“务虚”阶段。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期的逐渐临近,我们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具体感受和极端的紧迫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军事安全,而变成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因素在内的综合安全;国家安全的国内和国际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间的分野日渐模糊。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我们在安全观念、组织结构和运作体制上都作出相应的重大转变,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