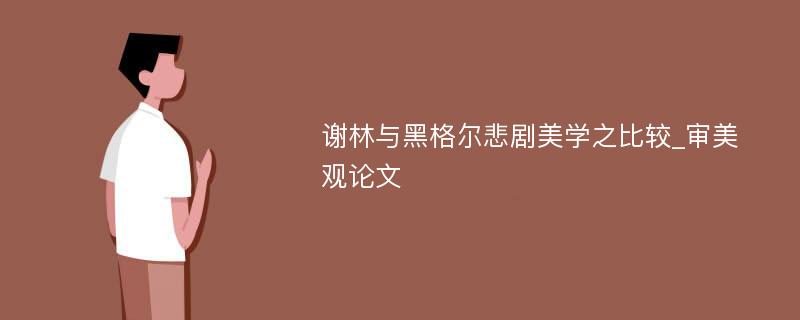
谢林与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观之论文,悲剧论文,谢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德国古典美学上,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上承康德,下启黑格尔,有着和席勒同样的桥梁作用。在对康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黑格尔的启示和影响方面,谢林和席勒在各自沉思的理路上有很大的不同:谢林的“同一哲学”朝“客观”迈出了一大步,这直接催生了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席勒则把美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思考解决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调和问题,这促成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基本思想的诞生。正是在这个不断扬弃和完善的基础上,成就了黑格尔这一德国古典美学的高峰。我们试图通过对谢林与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的比较,说明各自的不同影响,从而指出谢林在德国古典美学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现代悲剧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一、比较的可能性
谢林和黑格尔是同时代的人物,这使得我们的比较有了时间上的可能。既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思想是一定时势下的产物,那么,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谢林和黑格尔的理论观点是否相同呢?在德国古典哲学上,谢林由早期的自然哲学发展到后期的神话哲学,他自始至终坚持的是从绝对同一之物出发来构建他的“同一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则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其核心和灵魂是“绝对精神”。谢林的“同一”是指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种同一是万物的始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指世界的本原在于精神,精神是第一性的。同时,黑格尔吸取了谢林“同一哲学”的辩证思维,把其“绝对精神”界定为一个包含矛盾的理念运动过程,而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仅是精神性的,也是实践性的。这样,黑格尔扬弃了谢林“同一”的抽象性和无差别性,指出主客体的同一应是有差别的同一,从而赋予其哲学体系更多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这正是黑格尔超越谢林之所在。可以说,谢林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上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起点。诚如黑格尔所说,“到了谢林,哲学才达到它的绝对观点”。[1]78
在美学领域,谢林的《艺术哲学》和黑格尔的《美学》都把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谢林赋予了艺术崇高的任务和地位:“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这个证书总是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即行动和创造中的无意识事物及其与有意识事物的原始同一性。正因为如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2]276对此,黑格尔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艺术虽然早已在人类最高旨趣中显出它的特殊性质和价值,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艺术的真正概念和科学地位才被发现出来,人们才开始了解艺术的真正的更高的任务,尽管从某一方面来看,这种了解还是不很正确的。”[1]78黑格尔的任务就在于不断修正谢林的不正确之处。他否定谢林把艺术作为宇宙中最高的、绝对的存在。黑格尔认为,艺术中的主客观同一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绝对同一;艺术的感性直观并不能充分认识绝对精神;艺术只是绝对精神认识自己三种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的最低一级,艺术“用感性形式来表现真理,还不是真正适合心灵的表现方式”。[1]133只有高于艺术的哲学用逻辑概念的思维才能达到绝对精神的认识顶点。黑格尔正是在批判谢林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最完备的美学体系。可以说,谢林美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上也是黑格尔美学的直接起点。
由此可见,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早期的谢林远远地走在了黑格尔的前面。对此,鲍桑葵从两人的气质和性格方面做出了解释。①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美学史,吸取的是同样的美学滋养,但在诸多方面黑格尔却受益于谢林。我们很难说黑格尔得力于谢林的地方有多少,但“黑格尔的《美学》中的论点很少没有受到谢林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些见解和理论的启发,不管这种启发是用多么奇特或反面的方式提供的”。[3]286我们之所以“取黑格尔而舍谢林,这也一部分是因为谢林的思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的缘故”。[3]300正是因为两人的生活时代和理论观念有诸多的一致性,所以才有了可比性和比较的对等性,这样的比较研究也才有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就从悲剧审美观入手来探讨两人的一致性和相异性,看看黑格尔是怎样继承和发展谢林的美学思想,从而做出对艺术的正确了解的。
二、比较的内容
谢林的悲剧审美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该书主要是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对悲剧的本质进行界定的,“悲剧的实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与客观者的必然之实际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并不是此方或彼方被战胜,而是两方既成为战胜者,又成为被战胜者——即完全的不可区分”。[4]371由此可见,谢林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和客观的必然性之间的斗争冲突。而他所认为的必然性却是一种内在的神秘的不可知性,或称为命运、天意。“全部悲剧艺术都是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这种干预为基础的”。[2]245这就是谢林悲剧起源的“干预说”。可见,在悲剧起源上,谢林沿袭了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说——“一切皆为命运注定”。但是,在接受命运惩罚之时,人的绝对自由也同时得到了应有的荣誉从而被承认,自由“使自身上升至普遍性,并从而居于罪愆的后果之上,并与必然性相结合”。[4]374所以谢林说:“如此完满者,既摆脱福运又不受制于厄难者,处于两者皆空的心境中者,怎么能称之为不幸的呢?”[4]375这正是谢林“同一哲学”的核心在悲剧审美观中的反映。在谢林那里,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2]244“自由和必然,同时既是被战胜者又是战胜者,呈现于其最高的不可区分性中”。[4]368自由与必然的平衡,才是悲剧这一美学范畴的审美意义所在,“该无辜的获罪者甘愿领受惩罚,则成为悲剧中崇高的契机,——唯有借助于此,自由可转化为与必然之最高的同一”。[4]376这就是谢林的悲剧效果说,“悲剧可以借助不仅同命运,乃至同生命完全和解的情感来结束”。[4]375谢林的“和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但他赋予了悲剧更高的意义:通过自由和必然的斗争,人的绝对自由得到了承认,从而获得了“崇高心境”。
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美学》三卷本中,主要是从现实的矛盾冲突出发论述悲剧理论的,认为悲剧所要表现的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与和解。“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5]286这就是说,从各自的立场看,冲突双方的理想都是合理的,都具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可以付诸行动。但就世界的普遍情况看,冲突双方的理想又都是片面的,不符合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这就造成了成全一方势必牺牲另一方的两难之境,悲剧的根源正在于此。悲剧冲突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但是遭受痛苦或毁灭的仅仅是他个人,而不是他所代表的理想,所以“永恒正义”获得了胜利,“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5]287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虽是一种痛苦或灾难,给人以恐惧、怜悯和同情,但“永恒正义”的胜利则给人带来愉快和振奋,“因此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调解的感觉”。[5]289黑格尔援引了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来图解他的悲剧理论。苏格拉底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他作为雅典精神生活新理想的代表,则是功不可没的。安提戈涅顾全了亲属之爱而破坏了王法,但遭到毁灭的只是企图实现这些片面理想的人物,而王法和亲属之爱依然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谢林和黑格尔在悲剧审美观上的不同。第一,在悲剧的根源上,谢林的悲剧“干预说”虽然继承了古希腊的“命运说”,使得必然性带有神秘的色彩,但自由和必然的斗争中又包含了矛盾辩证法。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说”是对谢林学说的改造,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辩证法色彩。冲突双方是两种实体性的伦理力量(如亲属之爱、国家意志、宗教生活),由此造成的两难境地就是悲剧的起源。第二,在悲剧的结局上,两人都主张“和解说”,但“和解”的内容是不同的。谢林的“和解”是斗争双方既是战胜者又是战败者,完全地不可区分,但人的绝对自由得到了承认并显现。黑格尔的“和解”是一方遭受痛苦或毁灭,而“永恒正义”获得了胜利。前者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后者突出了人的社会性。第三,在悲剧的效果上,两人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但谢林认为,悲剧让人获得了“崇高心境”;而在黑格尔那里,悲剧是不在崇高范围之内的,因为崇高属于象征型艺术类型,而悲剧作为一种诗歌形式,既是古典型艺术又是浪漫型艺术的最伟大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悲剧效果上,黑格尔削弱了悲剧的力量。在谢林那里,悲剧具有更深刻的哲学意味和美学启迪,能给人以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和灵魂震撼,是真正的“崇高的诗”。虽然黑格尔在许多地方指出了谢林艺术哲学的“不正确”之处,但在这一点上,谢林远胜于黑格尔。
在悲剧审美观上,谢林一方面接受了古希腊的“命运”说,另一方面他也赞成亚里士多德反对希腊戏剧所常用的“机械降神”的观点。因为“仅仅外在性质的灾厄,并不能引起真正的悲剧矛盾”,[4]371只有像“命运之不可违抗、劫数之不可避免或诸神之报复”这样的灾厄,才是“一切灾厄中最登峰造极者:并无确凿之罪,由于阴差阳错而成为获罪者”。[4]372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重申过,并且以“永恒正义”来代替古希腊的“命运”,“永恒正义凭它的绝对威力,对那些各执一端的目的和情欲的片面理由采取了断然的处置,因为它不容许按照概念原是统一的那些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真正的实在界中得到实现而且能站住脚”。[5]289诚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指出的:“正义的观念无论从一般意义上还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起来,都是和命运的观念正相反的;因为正义观念把悲剧结局的责任归结到人身上,而命运观念则认为不应由人来承担责任,正义观念坚持认为悲剧灾难是可以解释的,而命运观念则承认神秘和不可解的东西的存在。”[6]从这个意义上讲,谢林和亚里士多德既相同(反对“机械降神”的错误观点)又不相同(谢林承认“命运”,而亚里士多德则绝口不提“命运”);谢林和黑格尔也是既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两者都强调自由和必然的斗争(矛盾性),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最终和解是以“永恒正义”的胜利收场,谢林则暗含了古希腊“命运”干预的色彩。当然,恰恰是因为如此,谢林在强调悲剧必须有灾难(灾厄)这点上比黑格尔要突出,从而使得悲剧具有了崇高的色彩。
那么,两人在悲剧审美观上的不同,对后世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呢?
三、比较的意义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悲剧审美观是对谢林悲剧审美观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汲取谢林美学理论的辩证精神,彻底完成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表现在悲剧审美观上,形成了他著名的悲剧“冲突说”。在现实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求和理性责任之间的冲突。由于社会力量的强大,个体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发展需要个体做出牺牲的必然性和个体欲求虽然合理,但又不得不毁灭的必然性,从而造成了悲剧结局。这正是后来恩格斯所表述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因此,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直接来源。谢林“隐蔽的必然性”经过黑格尔的改造具有了更丰富的辩证法色彩和现实的伦理意义。
有趣的是,谢林美学思想中被黑格尔认为是“不很正确的”、应当摒弃的东西,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谢林的悲剧审美观沿袭了古希腊悲剧审美观的传统,有着命运论或先验论色彩,同时他又高扬了悲剧主体的崇高和自由,从而对后来的耶拿浪漫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黑格尔对浪漫主义是比较反感的,他更倾向于古典主义。虽然他也承认浪漫主义是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却是艺术开始解体的阶段,是精神溢出了物质,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艺术发展的理想阶段。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艺术最终要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哲学(理性)高于艺术(感性);而在谢林那里,情况正好相反。
在谢林看来,悲剧的一切情节都源于必然性的命运,“悲剧中绝不可能有偶然事件的地位”。[4]376这也是实现自由所必要的一个前提,“人虽然在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在其行动的最后结局方面却取决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凌驾于人之上,甚至于操纵着人的自由表演”。[2]245而艺术是具有绝对客观性的那个顶端,“如果从艺术中去掉这种客观性,艺术就会不再是艺术,而变成了哲学;如果赋予哲学以这种客观性,哲学就会不再是哲学,而变成了艺术。——哲学虽然可以企及最崇高的事物,但仿佛仅仅是引导一少部分人达到这一点;艺术则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到达这一境地,即认识最崇高的事情”。[2]278这是谢林艺术哲学的核心思想。只有艺术才能把哲学家只会主观表现的东西弄成客观的,但这“必须期待哲学就象在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与所有那些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一起,在它们完成以后,犹如百川归海,又流回它们曾经由之发源的诗的大海洋里”。[2]277由此可见,谢林的艺术哲学实质上是诗化哲学。一切都应该复归于诗,包括科学、哲学,而复归的中间环节就是神话。在谢林那里,神话已不仅仅是一种人类原初的艺术形式,而是关系到人的生存本身的问题,所以新神话的出现“唯有寄望于世界的未来命运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2]277谢林的艺术哲学最终走向了神话,走向了对人生存本身问题的关注。这正是现当代美学所思考的核心问题——美学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联,如何通过审美达到人生存的自由?谢林给出的答案是新神话的出现。这种新神话应该是通过审美活动达到的审美心境,物我同一,互为主体,从而实现生存的自由和超越。
谢林和黑格尔的悲剧审美观产生在同一时期,虽然在理论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又存在着许多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集中表现为谢林悲剧审美观的神性色彩和黑格尔悲剧审美观的人性光辉,因而对后世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他们的悲剧审美观对于今天的悲剧艺术又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今天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悲剧?是命运注定的无法摆脱的厄运还是现实中两种伦理力量的实体性冲突?是崇高的绝对自由的显现还是“永恒正义”的最终胜利?遗憾的是,在今天的艺术舞台上,无论何种悲剧,艺术的力量都削弱了。虽然我们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现实社会中,各种伦理实体间的冲突比比皆是,但上演的悲剧艺术,却没有了震撼与感动,谈何“净化”?谈何“崇高”?因而,我们至少可以从谢林那里得到这样的启示: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应该关注人的生存,思考人的本质,尤其是具有崇高意味的悲剧艺术,更要探讨人自身。这样,即使缺少了命运的安排,没有了神性的光环,它依然让人感动,使人震撼,因为它关系到人的最本真的存在,能给人带来“崇高心境”,进而思考生的本质。从这一点上来说,谢林的悲剧审美观对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悲剧艺术理论创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更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收稿日期:2006-09-20
注释:
①相关内容请见鲍桑葵《美学史》,第30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