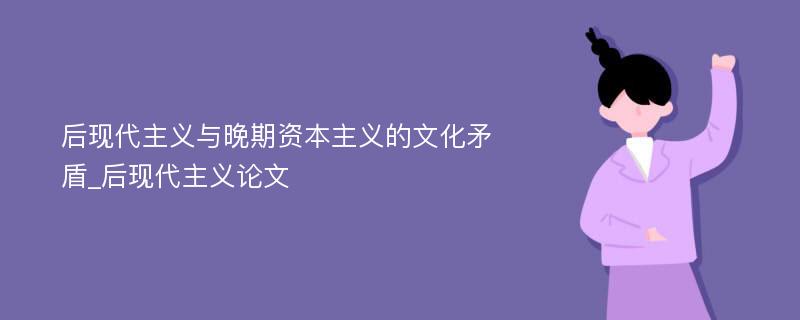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晚期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矛盾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种以全面检讨西方文明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悄然而生,并在欧美思想界引起一场“后现代主义论战”,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彻底反传统、反理智,甚至反文化的精神品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以反思古希腊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为基础。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在批判实证主义、批判工具理性的时候,仍然试图建立新的理性原则,把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但是在许多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的核心仍然是对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整体的、终结的看法,追问人类生存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他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批判这种形而上学,反对重新确立任何理性原则,把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逻各斯中心主义”确信,存在着客观的、终结的、不需要任何媒介的“现实”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人能运用语言对每件事物的本质作真实的说明,并由此而获得客观的知识。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真理应当是人类活动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占有决定的地位。对此,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哲学力图从语言入手破除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文字的目的不是要通过自身去看文字背后的事实,文字背后没有真理,也不显示真理。在文字中并不存在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符号不能在字面上代表其意指的东西,产生出“在场”的东西,相反,一种关于某物的符号必须意味着某种东西的“不在场”。符号总是为其它符号所限定,符号的意义只能在语境关系的区别中决定,因而它永远不能最终确定。由此,德里达否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主张的通过对语言的理解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可能性,否定了借助语言建构客观知识体系的可能性。
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清理也得到了罗蒂的响应。罗蒂从语言的隐喻特征入手,否定任何绝对价值和绝对标准的存在。罗蒂承认,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的。语言在使用中会使意义发生扩张和转移。语言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对事物的重新描述。这种重新描述会对原先的理论框架起破坏性的作用。他认为,人对语言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具有绝对特权的词汇。人是通过偶然的“语言游戏”来参与文化活动的。文化的进步就是以自由地选择语言工具为基础的“隐喻重描”。他反对以实在论为基础的真理观,反对构建以利益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他说:“在这里,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1〕
后现代主义者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对语言的确定性和意义可靠性的怀疑、对真理和价值的否定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通过解构,一切秩序和结构均被消解。一直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真理、价值、实体、本质、精神、善等都被置于动荡和怀疑之中,代之而起的是“失落”、“倒错”、“分延”。没有任何绝对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绝对的权威。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人们在寻求权威的合法性时,权威本身却已经彻底崩溃。一切均可以,“什么都行”,但一切均无意义。罗蒂说:“我们最好的真理标准是,真理是由自由研究获得的意见。在这种自由研究中,任何东西,无论是终结的政治和宗教目的还是任何其它东西,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得到苏格拉底式的责问。”〔1〕 无怪乎罗蒂把后哲学文化称作“讥讽的自由主义”。既然文字不表达事实,没有真理和价值,那么由文化史所表示的历史演进过程亦已消失,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只不过是形象和幻影。表示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等只不过是一堆杂乱的符号堆积。文化已经与历史和未来发生断裂,剩下的只是一串纯粹的符号,孤立的现在。时间已经被转换成永远驻足的空间,转换成杂乱的符号堆积。它与事实无关,它的意义可以由人们随意解释,但没有终结意义。这一堆失去历史维度的符号给人们的只是一些现时的阅读体验,零碎的意象堆积。在这一虚无主义的阴影之下,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只寻求当下的体验和即时的享乐。
既然无价值、无真理、无至善可言,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可以说,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赖以立身的根基。在存在主义那里,现代人虽然是孤独、苦恼、焦虚、畏惧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却是在思考着和追求着人的价值目标和生存意义;而如今,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们放弃了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人们不再孤独,焦虑人的一切精神维度均已崩溃,维系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已经折断,人无聊地活着。人所留下的只有本能的躯体和无意义的劳作。人甘于沉沦和堕落。自杀和歇斯底里的本能发泄也因此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所确立的“人”已经死去。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上述特征在哲学上表现为,反对“镜式哲学”,反再现论,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具有绝对权威意义的语言表述(“元话语”),否定真理和价值的存在,强调无中心、无价值、无真理。在文学上,它表现为反对重现和再现论,否定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提倡本能的宣泄和自我瓦解,艺术趋向于多元开放的、玩世不恭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形式。在美学上,它表现为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消失,否定理解作品的可能性,否定作品深层意义的存在,强调阅读的精神体验。在未来的态度上,它把希望建立在重建新宗教和日常世界上。
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秩序、对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主义管理方法的控诉。它以“反文化”的方式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文化上的价值世界的丧失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价值。它以对自己内在心灵的痛苦的分析来抨击这个令人痛苦的现实。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呼唤新的价值体系。
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根源
后现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相互矛盾的结果。
首先,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主体的丧失和人的价值的失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使理性归于消失、真理失去标准、价值丧失主体、知识失尊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本来,知识就是力量,追求真理、实现知识的价值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但是理性的工具化却使知识分子怀疑真理和理性,他们不再为真理而战,不再愿意为问题而争论。他们对“本文”世界和“话语”世界的解释和说明都不过是一种解构的游戏。那种把一切都确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为统一的科学目标而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
其次,文化的扩张、文化工业的兴起,使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文化丧失了传统的地位,这也造成文化的危机。以往,聆听美妙的古典音乐,欣赏绘画大师的杰作是陶冶人的情操、逃避物欲世界侵染的有效途径。如今以高技术为手段的大工业可以把古典艺术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摹本可以代替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文化工业与商品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工业已经开始把古典艺术作为商品在柜台上出售,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品之一。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艺术与生活、商品与文化的界限消失了。文化应当遵循的是商品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它失去了传统的价值意蕴,失去了传统的地位。
再次,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职业上的分工所决定的权力交往和为了物质需求而进行的金钱交往,充满友谊和情感的语言交往日益困难。在权力和金钱的交往中,人的语言是按照职业和金钱交往的要求而说出的。在这里,程式化的语言(套语)到处盛行。传统的、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语言失去了功能和价值。为此,生活中的人们痛切地感到程式化的语言不适用于表达人的情感,阻碍了人们之间的日常交往。人们感到,自己说出来的话不是自己情感的自然流露,恰恰相反,它们都是谎言。在这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里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在这里,不是人在说话,不是人把自己的情感自然地流露出来,相反,适合于金钱和权力交往的格式化语言却控制了人,是语言强制人说话,是“语言在说我”。无怪乎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从语言入手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倡导重建人们“日常世界”。
最后,自我意识的丧失导致价值标准的失落。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以赚钱为目的。个人主义和对自我的崇拜是这一时代文化的特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是行为的绝对标准,自己的利益追求是行动的轴心。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个人都丧失了自我中心,每个人都按照职业和角色的要求行事,他人的行为标准就是自己的行为标准。在这里,按照他人的行为方式行事才能与他人共处,甚至其它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标准是什么。人的行为失去了标准,丧失了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自我沉沦于他人之中。人怀疑自我、否定自我。许多后现代主义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竭力描写同性恋、性无能、恋父情结甚至自杀的冲动等。这只不过是对自我怀疑的张扬,并以对人生信念的彻底的绝望来反叛这个导致自我意识丧失的时代。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禁欲主义宗教约束力逐步丧失,代之而起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贝尔指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力是被锁合在一起的,“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1〕但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使这两种冲力之间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在社会生活中,精打细算、禁欲苦行、克己敬业的精神与追逐名誉、地位的个人主义精神发生冲突;在工业和生产组织中,生产组织的日益制度化和规范化与积极要求发挥主体作用相冲突;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与个人的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相冲突。这种冲突的直接后果是,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力越来越受到威胁,“猖獗的个人主义”急剧膨胀。自由贸易、自由流动、自由交换成为人们生活的理想,通过攫取财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他们活动的目标。从此,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股冲力反目为仇,相互害怕、提防、乃至敌视。科学理性和世俗精神对宗教信仰的贬斥和批判,使早期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力丧失殆尽。从此,个人处在严重的自我分裂之中。
这些都引起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严重冲突。本来。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攫取财富、克尽职守得到新教伦理的合法性论证。但是,随着这种宗教冲力的消失,它的合法性也将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应当从社会文化中得到说明。更具体地说,“社会行为的核准权已经从宗教那里移交到现代主义文化手中。”〔1〕但是现 代文化却拒绝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任何合法性论证。它公开敌视理性主义的经济行为。这就造成了现行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核心。
三、解决文化危机的构想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文化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提出了种种设想。其中以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和贝尔等人提出的观点最富有代表性。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需要重建“日常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社会行为的主体具有诸如规范、规则、价值观、心照不宣的理解等诸如此类的知识以及人际沟通所必须的适当的社会背景。在日常世界中,人们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作为彼此相互理解的手段,进行自由的交往,以便在行动上达成一致。在交往行动中,“行动者为了商议共同对情景的界定,他们才同时涉及到客观的、社会的、主观的世界中的各项内容”〔2〕。这就是说,通过交往行动, 日常世界中的三个组成部分文化、社会和人格能够达到理解、协调行动和社会化,它有利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人格的形成。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社会分化的趋势日益严重,要维持日常世界的再生产就必须依赖于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交往。但是,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科学技术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权力和金钱等“非语言的驾驭机制”贯穿于社会系统之中,它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中交往的手段。市场、法律体系、福利政策甚至家庭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权力和金钱等非语言的媒介手段来有效地运行,它们成为社会整合的手段。于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往受到侵犯和干预,文化再生产出现困难。换句话说,经济和政治的运行手段干预和统治“日常世界”,并因此出现“日常世界”再生产的危机。人们之间无法共同理解、共享文化。为此,哈贝马斯主张重建日常世界,通过交往行动把社会整合起来。具体地说,在政治方面,重建“公众圈”,通过语言的讨论来对社会问题达成共识,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社会政策,而不靠权威来制定政策,靠金钱(富裕的生活)来赢得公众的政治支持。在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方面,通过日常世界的沟通来实现文化的共享和相互理解。
当代法国的哲学家利奥塔德对哈贝马斯重建生活世界的构想提出质疑。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企图通过语言的交往来达到普遍的共识,并借此整合社会、消除社会危机。在利奥塔德看来,这一思想仍然没有超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路。从表面上来看,人们似乎是通过平等的交往来形成共识,但它实质上仍然是强求一致,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控制。因为这种妥协的自由仅仅表明人们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在哈贝马斯那里,人类交往的目的只不过是形成另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知识形式。利奥塔德认为,交往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共识,而只企求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去不断发现谬误,或者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去进行证伪。他说,“共识只是属于讨论问题时的某种特殊情况,共识不是科学讨论的终结目的,正相反,讨论的目的不是追求共识,而是追求谬误推理。”〔1〕在利奥塔德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再追求至善至 美,不再追求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知识,恰恰相反,它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人类知识,乐于承认各种知识的局部合法性。他认为,不加批判地接受知识助长了驯服和奴役。
以“新保守主义”著称的贝尔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规范化、理性化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对晚期资本主义中否定真理、否定价值等“反文化”的偏激表示无限的忧虑。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所丧失了的“宗教冲力”显出殷殷缅怀之情,期望探寻一条解决人们精神危机和价值失落的有效途径,这就是重建新宗教。
贝尔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程。在前工业社会,人处理的是自然世界,在工业社会,人对付的是技术的世界,而在后工业社会,人面对的是社会的世界。后工业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后工业社会,人越来越远离自然,越来越少地与机器和物器打交道。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贝尔指出,“如果自然世界由命运和机遇控制,技术世界由理性和熵支配,那么社会世界只能具有在‘恐惧和战栗’中生活的特点。”〔2〕宗教是用天堂和地狱的形象、 惩罚和救赎的形象来使人恐惧和战栗。他认为,宗教所具有的威慑力量与它的超功利的特征密切相关。它是一种与终极价值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道德秩序的根据。如果宗教衰微的话,那么依靠宗教力量来维系人与人之间共同情感和情操的纽带就绷断了,社会就有涣散的危险。理性主义的扩张引导人们追求知识的绝对性,世俗化过程的张扬引导人们追求新奇和享乐。这两者都导致对神圣王国的亵渎。神圣王国权威的消失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没有什么文化信条能够“守住邪恶的大门”。本来。宗教衰微之后,文化应该承担起解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意义的重任。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化不但不象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邪恶,反而开始接受邪恶,探索邪恶,从中取乐,还把它(正确地)看作是某种创造性的源泉。”〔3〕
基于上述情况,贝尔倡导建立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是一种文化崇拜,它包括对人类生存的规范和秩序的认知追求,对超自然的神圣东西的感情渴望以及建立与别人之间情感联系的基本需求。在这个新宗教体系中,个人应当认识到团体道德给他规定的义务,如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养育和照料,他对社会团体所欠下的教育债务等。贝尔的新宗教构想显示出他对西方文明发展的深刻反省的精神和重建人类精神世界的良好愿望。
但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和贝尔等人都把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矛盾寄托在改变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如前所述,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矛盾是社会经济行为以及其它社会行为无法在文化上得到合理的说明,因此,解决这一文化矛盾不仅要重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且还要改变人们不适当的社会行为。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解决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方案未必可行,但他们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研究和处理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矛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1〕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2〕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3〕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
〔4〕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5〕转引自《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81页。
〔6〕转引自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7〕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5页。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9页。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