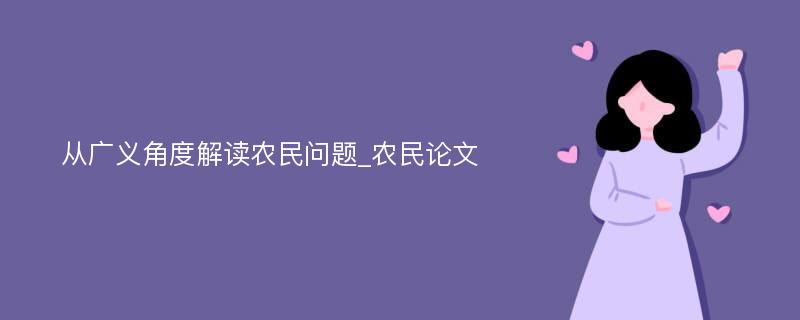
用大视野审读农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视野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这样说过:“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话意蕴无穷。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当前“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瓶颈”制约,仅从经济方面找原因和想对策是很不够的,还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多层面分析,用大视野全方位审读农民问题。
一、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必须改变
解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逐步有所改善,但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祖上是农民户,就有可能世世代代延袭下去。因为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而为了防止各级城镇、市的人海之患,于是,一堵堵户口高墙矗立起来了。尤其是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这条界线,鸿沟之深、反差之大,世人无不知晓。现行的这种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国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主要根源。
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农业生产地位的重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说,社会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农业生产,却由被人看作最不重要的社会成员去完成。这种二律背反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须知,一个职业阶层的主体成员受歧视,这个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由于农民在不公平的环境下缺乏种田的内在动力,经常要靠外部输血打气,才能维持生产或换来短暂的繁荣。凭借这种没有健全的动力机制的农业基础,怎么能维持农业的稳定增长呢?
决策者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是与非农业人口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多年来,我们就是在这种衰退→重视→恢复→再衰退的怪圈中循环往复。这说明,如果农业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农民以外的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偏好,那么农业的周期性萎缩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提高
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多少世代以来,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耕作经营。全国解放后,我们虽然搞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并没有真正找到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较好形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重建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经营组织,大多数农民仍旧局限在小块土地上,自家耕种自家田,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传统的村社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低下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只能以个人对群体的方式进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压抑感和自卑感。
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阶层,在这些方面总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的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比如,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不买就会带来更大损失;农产品收购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不卖则要承担各种风险和压力。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即使价格严重不合理,损害了自己利益,他们也无力改变现状。现在城里人享受各种补贴,国家财政不堪负担,在经济上也是极不合理的,但哪一级政府也没有勇气取消它。因为市民阶层已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如果得罪了他们,就会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而农民就不同了,他们的怨气再大,牢骚再多,也是以极端分散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形不成直接威胁社会秩序的集团性力量。
中国的农民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用语中便可窥见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负担”、“多给农民些好处”、“让农民得到实惠”、“一定要兑现承包合同和奖售政策”等等。从这些用语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总闸门开关操纵在别人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如果不给,关了闸门,或者把闸门开小,你也无可奈何。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地位竟如此之低下,怎么能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农业!
三、农民的参政渠道必须畅通
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我们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差。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农民参政既有其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政策方面的因素。
首先,农村的信息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从客观条件来讲,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素质差,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从主观条件来讲,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镇(乡)政府及村民组织,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新闻、影视、文学等形式的信息载体,面对着广阔的农村空间,其触觉只能伸到其中极小的部分。农民的保守观念、宗法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在受到屈辱和侵害之后,不敢见官,缺乏披露事实其相的手段,迫不得已时也只会采取旧式“告状”方式。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高层领导机构在作决策时,就缺乏可靠的依据。
其次,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起步较晚,民主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还要大。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比如,选村干部、选人民代表,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非常淡薄,对乡、村发展规划的决策,村民也很少有机会发表意见,往往由少数人说了算。对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农民就更觉得远离自己了。县、乡、村干部的选拔和任命,虽然推行了差额选举制,但由于信息传递和参与渠道不够通畅,人们对选举程序还不够熟悉,因而选民的意志事实上还难以充分表达。因此,干部的使用实际上主要通过垂直任命方式决定。这样,干部的行为方式取向倾斜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选民的利益无法取得政治保障。
第三,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投入某些物质性硬件,是很不够的。唯其如此,只能起到输血打气的作用,暂时减轻困难的症状,使加剧的矛盾有所缓解,而不能釜底抽薪,使农业走上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这是因为,农业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它的存在状态如何,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取决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其它社会因素。有鉴于此,我认为农业的出路不仅在于强化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而且要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其它社会地位问题。目前,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取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得以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中打了胜仗,最后夺取了政权。这一经验,不仅对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实践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凡是农业兴旺的时期,都是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人格受到尊重、政治参与渠道比较畅通的时期。凡是农业衰落的时期,都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人格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受到冷落的时期。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农业的兴衰,而农业的兴衰又直接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很有必要形成新的全民共识。
第二,政府应始终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去领导农业。我国农产品的消费,可分为两大集团,一是农民集团,二是市民集团。农民集团满足消费的程度,一般被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与政府关系不大,政府也不承担多少实质责任。而市民集团对农产品的消费,一旦供不应求,匮乏加剧,便喊声四起,叫苦连天,政府马上要承担巨大压力。往往只有在这时,农业和农民问题才重新被重视起来。一旦市场供应情况好转,农业和农民问题似乎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目前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的政策选择,其直接驱动力仍然源于城市利益偏好。因为城里人被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掉所困扰,这时才又一次打起了农民和农村的主意。这样,发展农业的动力不是来源于农业内部,而是源于农业外部,时而被政府所重视,时而被政府所忽视,农业就跳不出兴衰反复的周期率。政府只有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去指导农业,农业的发展才能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上,农民才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为全社会提供丰富的农产品。
第三,政府对农业的宏观指导,要建立预警系统和事先调控体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导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反抗。比如,缩减播种面积,实行粗放管理,拒绝完成订购任务,与基层政府和官员采取不合作态度等。这种不满情绪来势缓慢、温和,在短时间内形不成轩然大波。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当风起于青萍之末,严重的后果已经初露端倪时,往往不易觉察。但一旦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才着手纠正时,已经不好收拾,从而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政府对农业问题,应未雨绸缪,变事后纠正为事先调节,当某些不好征兆一出现就能引起警觉,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四,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建立农会,作为农民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团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接受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它的基本职能是: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情况,及时向各级党和国家政府的决策部门输送意见和要求;代表农民参加政府决策工作,对于有关农业的重大决策,农会要参与意见征集、方案论证、提出有关草案或修正案的工作,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当农民的利益受损害时,农会可以代表农民向有关部门交涉,为农民申张正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五,改革农村产业组织,提高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现代农民的品质素养、精神风貌的培育,离不开现代产业组织这个根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必然催化新型农业组织的发育和生长。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的情况,应在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农业产业化经济组织,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使供产销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样的经济组织,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容易发挥优势,抗风险的能力较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因此具有发展前途。农村的供销社、信用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组织,应以服务于农业为己任,指导生产,疏导流通,推广技术,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锻造一代新型农民的可靠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