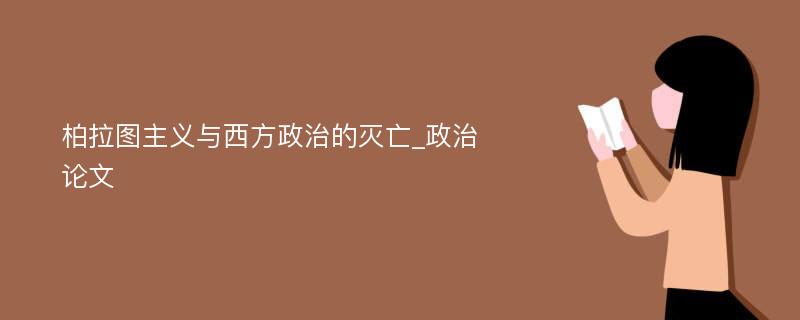
Arche:柏拉图主义与西方政治的湮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Arch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12.18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11-0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一、柏拉图主义:作为开端与统治的Arche① “当公元前375年,柏拉图写下《理想国》的时候,希腊城邦已是风烛残年,而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时,希腊已经在喀罗尼亚与马其顿的腓力对阵时惨遭败北,也就是说此时独立的希腊城邦虽已产生了理论著作,但却即将不复存在。”[1]37面对陪审团,苏格拉底在申辩的结尾说道:“但我对他们提个请求。我的儿子们长大后,诸位,如果他们在你们看来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了关心德行,你们要惩罚他们,像我烦扰你们一样烦扰他们;如果他们实际不是什么而以为是,你们就要谴责他们;就像我谴责你们一样,告诉他们没有关心应该关心的,自以为是他们按品行所不是的,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和我的儿子从你们得到就是正义的。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2]142 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对哲学家的命运感到恐惧和不安,他认为:“所有的恶果之根源在于,在民主城邦中进行的辩解始终还处于意见的层面上。”[3]14城邦的事业与哲人追求真理的决心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苏格拉底被陪审团处死,因为在雅典的军国体制中,战争是第一位的,苏格拉底被控诉亵渎保佑战争胜利的神灵,用思考和沉思消磨青年战士的斗志。在雅典城邦的公共领域中,苏格拉底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只牛虻,在德菲尔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指引下,引领雅典公民追求真理和自由,呼唤知与美。积极的生活体现在苏格拉底的事业里,苏格拉底完美而又成功地践行了一个追求自由和灵魂不朽之人的一生。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在希腊时代,人作为言说的政治存在,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政治的动物”。交谈与言说在这一语境中作为逻各斯(Logos)的动词,逻各斯之意为:在语言中将现象汇聚和展示于世界。在希腊文化罗马化的过程中,这一交谈、说话、谈论的含意被拉丁化为“理性”,而在原初表示涌现、创生的“弗西斯”(phusis)也被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所代替②。海德格尔认为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过程并不是随意和无害的,而是对希腊哲学源始本质的割裂和疏离的最初阶段。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同样源始的观念,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即源于这些词语的翻译,而非转渡,转渡作为翻译的形式之一在最大程度上是关照和考虑源始词语的根基的[4]170。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与不同的人交谈、论辩,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在多样化的私人空间中,我们有各自的想法和世界,并且沉沦其中;而在城邦中,如克劳斯·黑尔德所说的:“人必须超越出他们各自特殊世界的兴趣状态和本己,并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相互遭遇,而后才能在做出辩论的过程中通过承担责任来认真对待生活。根据这个结论,在雅典的城邦中——并非与哲学同时代——就偶然地形成了第一个民主制度,从而也形成了最源初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就其希腊的原创性来看,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开辟一个具有自身负责理由的共有世界。所以在这个民主中,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变换不定的、超越出特殊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是开放的论证,希腊人将它称之为‘议事’。在由修昔底德流传下来的关于战死者的名言中,伯利克里强调:雅典的民主制并不认为,让逻各斯——即在相互言谈中被感知到的理由——先行与对行动的决定是有害的;事情恰恰相反。”[3]14就是在这一由言谈开辟的世界中,人们发现了共同的世界,并在世界之中存在。通过在这一世界中不断超越、论辩和议事,此在的人“绽开”着,并被定义为政治的动物。 与哲人们后来倡导的沉思生活相比,语言的在场与行动的直接性使世界在不同的意义维度中显现出来,此在的人通过言说将自身呈现于世界中,他与存在者通达并且超越了存在者。由此,意见(doksa)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显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汉娜·阿伦特的考察中,“意见”一词涵盖显现和呈现的动态含义,“它是指每个人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德性,而德性来自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意见是公民重要的政治品质”[5]88。在意见得以言说的过程中,人通过分有神的德性而进一步展现自身是“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展现出不同的德性,而正是在这纷繁杂乱而又看似无序随意的言说中,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汇、融通,所有相同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真理自然呈现为“无蔽”。而这一无蔽的状态下,面对人类的公共事务,政治世界呈现为意见的涌动和斗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符合观中以正确性为标志的真理观。伽达默尔说:“我们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不是说在语言背后还有其他实践方式,诸如劳动、统治。在语言的呈现中,呈现的不是背后的物质力量,不是说在语言的背后存在可能性,而是说可能性只在语言中存在,我们只能理解语言的世界。”③ 一件伟大的事情既不在于其动机,也不在于其成就,而在其本身的显现过程。古老的希腊人将生命的必然性领域视为低于公共事务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中,由于受到生命必然性的驱使,家长制和奴隶制仍然存在,因此,生命的必然性和人类生活中的暴力被认为是前政治状态;而政治领域是独立自主的雅典公民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探讨之地。德谟克利特说道:“政治的技艺在于教人们如何去展示伟大和荣耀的东西,只要城邦在此,激励着人们不要惧怕非同寻常之事,如果城邦衰落了,一切就都不复存在。”④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位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他们交谈、商议,追求不朽和荣誉。而私生活是幕后的,隐藏不显的,依靠奴隶制去维持生活的繁复和循环,用家长制的权威规定着家庭的秩序。而这些因素在希腊人的公共领域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它们属于必然性的私人领域,而真正的自由超越这必然的一切。克劳德·黑尔德评价道:“家是生命保存得以发生的共同体,而且具有双重形态:它既是需要的满足,即满足个体继续生活必须得到的日常需求,又通过养育小孩而保障了人类这一种类的继续存活。希腊人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以开放性和封闭性为基本差异,一边是居所,家庭共同体,藉着其公共性格,城邦区别于具有隐蔽性的居所。如此一来就可以说,政治世界的自身开启的意义在于:它是对立于家的隐蔽状态而实现的。”[3]281古希腊人几乎毫无私人性或私人生活的概念,每一个在公共领域言说的公民都深知此在的人作为必有一死者,要残酷地顺应自然的必然性,他们追求不朽,建立勇气和荣耀的纪念碑,分享众神的德性,其私人生活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必然性,财产作为手段成为进入政治世界的必要条件。而当私人生活在近代获得不可侵犯的“隐私性”之前,私生活呈现出被必然性所统治的特征,如奴隶制、家长制甚至暴力。必然性的需要使这些支配性的行为成为必需,但这一切却是每一个得以言说的必有一死者在城邦里能够追求不朽的保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是必需的,而不朽才是目的。离开私人的家,这一被遮蔽的领域以及被必然性限制和锁闭的领域,展现自己是“谁”,而非是“什么”,成为人之为人、政治之为政治的基础。 苏格拉底对自由的先行献祭,固然使柏拉图在政治理念的构建中开始怀疑这种苏格拉底所倡导的行动着的、交流着的积极生活的形式,但此种倡导行动的脆弱性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政治学的构建。因此,缔造一个有序、稳固的共同体成为柏拉图的目标。 在这一“缔造”的过程中,哲学家试图“统治”城邦,而不是以一种行动的态度去追求自由和正义,这些价值蜕变为与“理念”契合的“至善”。汉娜·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关键词‘理念’即来源于制作领域的日常经验,因为制作的过程显然也分为两部分,首先,制作观看有待生产之物的形象或形状,然后动手制作。在制造、生产活动中,真正的起点、动力和统治者是最终的那个要达成的目的。目的在制造过程之前已经被看到了,这个被先行看到的目的就是‘Arche’。”[5]110~111Arche在希腊语中有开始与统治双重含义,其起源、开端的含义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而之后有关统治之含义,则要追溯至希罗多德和品达,Arche在他们关于历史和诗的表达与描述中获得了统治、领导、支配等含义。但若究其本质,Arche所展示的是事物的存在、产生以及被解释和说明的起点。 无须赘言,西方的政治传统从柏拉图开始,但他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将有关Arche的哲思视为不断涌现在思考和对话中的光,如同真理乍现爆裂的闪电,在不断的行动的呼应下闪现和存在。而在柏拉图看来,这一切脆弱而又危险,城邦的论辩水平仅仅局限于意见,混乱而又局促,以致哲学家的生命处处受到威胁。他要以“理念”这一新的Arche来衡量和控制人类的事务⑤。 如若再将时间向前追溯,便可以发现早在柏拉图之前,面对意见与真理的对峙,也即在政治与哲学的争论中,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就已经出现了取消意见、构建真理并确保真理牢牢统治的倾向。巴门尼德斥责把存在看作状态或属性,认为存在与非存在交替流变的这类观念是意见,并把由此将世界归结为某种本原或始基(archee)的思路批评为意见之路。巴门尼德自认他的使命就是在哲学上彻底终止意见之路,并开创一条新的思路:追问纯粹存在的真理之路,即不再对世界进行自然主义的研究,而是把世界万物通通看作是纯粹的现象,追问存在和存在自身,也就是追问纯粹思维、纯粹形式。一句话,追问万变之自身。柏拉图正是继承了巴门尼德的追问思路,力图以纯粹形式的理念(eidos或idea)去解释与把握万变之自身,更准确地讲,是规定变动不居的世界万象,解决现象的缘起也就是现象如何可能的问题,用希腊哲学术语表达乃是:diasoizein ta phainomena(拯救现象)[6]57。这是哲学史上的事件,柏拉图在城邦危机的时刻力图用“理念论”的形式将现象从各种相对主义的沼泽以及变幻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之流中拯救出来。历史充满了偶然,一种由“看”主导的“理念论”本身是为了拯救现象而诞生,而其自身却成了对象,理念变成了“是者”,而非巴门尼德探求一生的“是”。在柏拉图主义或“理念论”的话语中,聚集现象之涌现的逻各斯将其展开的Physis蜕变为nature。 在著名的“洞穴比喻”中,柏拉图表达了自己对苏格拉底悲剧的看法:一个真正观看到理念的哲学家是不愿意再返回洞穴参与公共事务的,他以沉思的生活获取更高的旨趣,洞察世间的一切。但作为此在的人,哲学家又不得不在城邦里生活,不得不参与政治生活。在这里,Arche流动着,呈现出不断在幻灭中重生的状态,而这一现象被柏拉图明确地从人类制造活动中所观察和感受到的经验来解释和规范,直到亚里士多德将Arche变成对第一因的追寻。至此,哲学变成形而上学,政治成为人造的,而不是被探索和开拓的。 在“理念”之光照射一切“善”的光影与黑暗洞穴折射的光影中,哲学家以“善”的标准统摄万物,为存在订立规范和边界,“至善的真理”和“洞穴中的意见”便对立了起来。在永恒的“理念”下,哲学家也将技艺人有关制作的技巧和意念带入了我们的政治传统中,“制作”内在固有的稳定性及持续性由此进入了人类的政治领域。一个永恒的“理念”得以呈现,而其他事物只是“摹本”,它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理念”。 柏拉图将哲学变成了形而上学,即在生成和变化的现象之外,还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混乱、世俗甚至虚假,而理念世界才是真实和值得追求的。在柏拉图看来,重要的不是言说和行动的一体化,而是通过理念建立和规范一整套道德世界。至于将“理念论”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阿伦特评价道:“将绝对标准引入到那本无此种超然在上标准的、诸事相对的人类事务领域,其结果是哲学家统治政治,就像哲学家用灵魂统治身体一样,造成了绝对的权力统治。”[5]38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稳定的、永恒的真理被“理念”所拥有的“可视性”所引导时,真理便由无蔽转向了被陈述和觉知所包裹的正确性之中了。在这里,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⑥,这也是真理本质的改变,真理不再作为无蔽被理解,而是符合了天空中的“理念”。从无蔽到正确性、符合性的转变深刻又明确体现在柏拉图开创的政治传统中,柏拉图将“技艺人”的“制作”以“造形”的方式成功改变了以行动、交谈为主导的政治领域,政治被稳定性所驾驭,哲人通过“理念”为行动与言说奠定了框架,哲学家高尚的沉思和苏格拉底式的牛虻被一分为二。我们看到,在由超感性的“理念”所统摄的生活世界中,“真理”不再是逐渐递进式地探寻和去蔽,它成为现成的东西,即作为认识的终极结果,所有一切都必须符合“理念”投射出的标准和刻度。另外,这种追问真理本质的方式即符合论,并没有追问真理的符合如何可能,即使符合成为真理的本质,这种符合也需要真理的在场与敞开;而人作为真理的探寻者,显然忘却了比“让真理无蔽”更加源始的“真理的遮蔽”,以至于在柏拉图主义的开端,生活世界的事务已经陷入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贫瘠和乏味里,主体表象谋划出至高的存在“理念”定夺着万物及其意义。阿伦特说:“表象或现象的优位性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事实,不论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无法逃避它,他们必须从其实验室或书房,回到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他们抽离自这个日常生活之世界,才能够从事各方面的科学与研究,但无论他们有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哲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无法改变他们生活与日常世界的表象或现象性格。”[5]52 另一方面,由追求理念所引发的理念化方式也恰恰是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保罗·利科写道:“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出现了——无限使命的人属——一些彼此独立的个人构造了哲学的观念……这一突变贯穿于从生命意愿到惊叹、从意见到科学之中……普遍之物被追求,纯粹的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的使命中形成,这种哲学探讨的共同体通过文化和教育跃出自身的框架之外逐渐改变了文化的意义。”[8]39在这一意义上,柏拉图主义伴随着“理念论”被创造而诞生,作为希腊性的哲学,也由起初惊讶于“是者”的涌现而转向证明“是者”如何,哲学成了证明体系,变成了形而上学,而理念就是作为始基及统治的初始——Arche。 二、柏拉图主义与技术科学 政治作为追求自由和不朽的伟大开端被理念所终结。海德格尔在1925年开设了以亚里士多德《智者篇》为主题的研讨课,阿伦特深受其影响。海德格尔认为技艺(techne)是非真的真理形式,因为它不是以自身为目的去思考自身,它的目的蕴含在被制造的物品中;而明智(phronesis)是以自身为目的,思考自身。技艺是生产性的活动,它需要在过程中不断完善;明智是展现性的活动,无需过程,其本身就是完美的。明智体现了人可以支配开端,但技艺不能恰当地支配开端[9]62。技艺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在技艺人的心中以理念为始,制成品为终;而对象化活动的过程则充满支配与统治,在手段目的的思维下,过程虽然必需,但结果才是重心。 一种“技艺人”的思维模式最终以某个“至善”的理念形式主导了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它以一种“制作”的经验,稳定和控制着由先前变动不居、难以预测的行动和言说主导的城邦,也以一个永恒的理念统摄着生活世界中瞬息万变的意见。真理不再是流动、显现的无蔽,而是观念引导和确立下的“善”。沉思代替了行动的优先。 在技艺人的世界里,我们看到后世出现的绩效主义(功利主义)概念,技艺人渴望创造一个恒久世界以延缓和抵御自然必然性的残酷,这本身毫无问题;而如若将技艺人的思维以理念论的形式植入以行动和言说为主导的政治世界中时,它就取消了行动和言说的人们所具有的力量,以至于在政治理论的发展史上,技艺人的思维完全侵占公共领域。这种对原初政治世界的颠覆在后世发展出一种以“快乐计算法”为特点的政治哲学范式,这种影响亦体现在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改革的革命性创见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再次看到,新教徒完全可以生存于自我的信念和信仰构筑的世界里,而非那个公共领域主导的世界,生活在世界中的是“人”而非“人们”。在技艺人的世界里,产品的制造同样不需要他人的在场和言说的回应。在技艺人的“产品”之中,甚至出现了国家——一个依靠契约而达成的主权,而不是源自自然的秩序和规律。 柏拉图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在历史上也衍生出了近代的技术科学。柏拉图主义不仅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衰败,而且蕴含着现代技术科学的起源,其中数学因素(ta methemata)⑦不仅是柏拉图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更是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样式,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之天命”。 以存在论的视角,技术本身是比科学更加源始的东西,故此处技术科学的称谓是相对于惯常的科学技术而言的。18世纪现代科学的兴起也正是依托于技术的“去蔽”。为了更切近地理解技术,海德格尔将techne译为知识(wissen),作动词解,而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将techne解释为一种借助努斯(理智)的德性。技术是一种与真实的理性逻各斯相联系的产出性行为,即关于如何制造某物的知识。技术并不意味着制作,而是去蔽意义上的知道,即技术的本性并不属人,而是本源性的真理——去除遮蔽,让物如其所是地显现。古希腊意义中,“技术”的本意在于让某物显现[10]109。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规定为“集置”:它是一种去蔽的特殊方式,是人与存在者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一种强迫的、促逼的去蔽,而在这一强制的、促逼的范围内,人不再与事物或对象发生联系,而是将处于功利主义视野中的一切视为可自由使用的持存物。在这一思路下,techne也显示出一种强制的造形的本质,通过对存在者强制提出功能主义的属性化和造形要求,将其摆置到客体化、对象化的位置上,对其强制地去蔽,最后推演至整个世界。技术本质的“座架”(Gestell)将整个世界(自然)置于量化与计算理性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中,强制地进行去蔽意义上的显现与宰制,而非自然涌现或是基于理论的“观审”⑧。“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已经明确地从人类制造活动的经验中获取线索来解释开端,即对第一因的追寻,而前苏格拉底时代对于开端的不断追寻和言说现在则变成了对原因、终极因的追寻,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开端被解释成为目的因,即运动变化的最终目的,在制造和生产活动中真正的起点。动力和统治者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制造活动之前就被先行看到了,这个被先行看到的目的即为eidos,在整个制造活动中始终制约、统治、主宰着全部的变易过程,而生产或变易过程也即是向着这个目的的运动……因此,形而上学同时又是目的论:一种源于制造和生产经验的形而上学——目的论。在其中一切都是可操纵、可支配的、似乎事先已经安排好,注定好了。”[8]9 数学因素是一种先行于“是者”的物性筹划,数字作为数学因素中最具特性的要素,并不是从我们对物的把握中形成的,数字更倾向于一种先验的、在物之前就已出现的思维活动。丹皮尔认为,最早把数的抽象概念提高到突出地位的也许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实用数学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发现使数学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使人们相信数是实在世界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就是存在之构成的原则。可以说,就是存在(是)由之构成的物质。”[11]31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世界全然是数的,这一主张是在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上提出的。赫拉克利特将哲学描述为“爱智慧”,在他看来,“数”与“爱智慧”即是等同的,对“数”的探求也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方式。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秩序”具有Logos的规定:“这一世界被各种尺度点燃和熄灭,就世界中的每一文化都被‘度量’所言,它是被Logos所控制的。”[12]884Logos在这一度量和准绳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数学因素”。 数学在诸科学中最稳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最为纯粹。数不依靠概念,具有直观性,并且不包藏任何利益。数学较之其他学科更接近理性(Laraison),因而不同意见在数学上的差异很小。很明显,在数学标准上,良知和理性没有差异[13]67。数学因素不依靠任何概念框架,也不源于任何情感,因此可以在意见的巨流中提供确切稳定的知识之基础与导向,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和标准。数作为物性筹划的方式,是一种保证确知的直观形式,是知识而非意见。数学因素首先揭示出持存的现实物,开启一种视域,从而在量级层面对现成物进行规定。在这一新的视域中,现实物被摆置于一个物性筹划的新领域,被先行的数学因素牢固地把握为知识,并在这一领域中显示自身。 海德格尔认为,所谓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测量科学的规定都属于对科学本质流俗的解读,皆未道出现代科学的实质,因为科学的本质在于“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筹划凸显为一种对物的数学筹划,因此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称,“作为一个学科的数学仅仅是数学因素即数学的东西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从“数学”一词在古希腊使用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太多的、现今人们习以为常的数字的痕迹,它可以指持续性的物(自行涌现和人工产出的),也可以指人们能对其加以作用的物以及有“某种”意义的物,总体而言则是“就其是可学的东西而言的物”[12]856。而这种“可学”从表面来看只是在使用之前对物性的获取,实际上体现的是“取得认识”或“占有某物”的要求,是一种先验的认识,关于事物数量的数字并非来自对事物本身的分析,而是来自人们对数字已经具有的直观形式。在此,便可以注意到数学因素是指对物的一种认识态度,一种摆置原则。海德格尔说:“数学因素是那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因此,数学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基本前提。”[12]856因此,数学因素起先是作为一种人与物在前科学、前反思的层面相遇的方式,作为一种物敞开的维度,并在此维度中作为一种为物规定了标准的直观方式,让我们经验物、占有物。 在此分析路径中,可以觉察出一种倾向或是发展的轨迹:数学因素作为近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与先前其作为物之为物的把握方式的断裂或许就发生于“理念”之后,数学因素完全脱离物自身,疏离生活世界与前理论的世界而跃升于理念的超感性区域中,具有了一种本体论色彩。数学通过背身于前理论的生活世界,在理念的世界中获取了摆置物的方式,而此种摆置与作为去蔽方式的技术结合,更是为后来的研究科学做好了准备。整个自然便在这种由数学因素主导的理念化的物性筹划中被设定为存在者,存在的属性被这一数学因素抽取完毕并转化为存在者,完全被摆置于由技术科学解构和分析的研究平台。 数学因素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扮演了重要地位,柏拉图主义的根基“理念论”就是数学因素的哲学表达。据传在柏拉图学园的门匾上刻有“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在柏拉图看来,不懂数学是无法超越可感世界而进入可知世界的。数学是超越可感世界进入可知世界的最有力工具,是真正哲学训练的必备工具[14]48。“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通常的希腊数学,然后是希腊的自然科学,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诸片段、诸开端……古代人就已经在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指导下将经验的数、量,经验的空间图形,即点、面、体都理念化了……而后来的哥白尼最突出的特征是把天文学事实置于一个比较简单和比较和谐的数学秩序中,因而起绝对作用的是被理念化的几何学思想,经验化的自然感知和自然秩序被数学的、理念化的模型替代了。”[14]18 胡塞尔认为,“对于理念形态来说,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绝对的同一性规定它,将它当作绝对同一的、可以在方法上一义规定的诸性质的基体来认识”[15]128。科学真正处理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些“绝对同一的可以在方法上一义规定的诸性质的基体”——理念。至此,生活世界(洞穴)被下降为不值得期待的、混乱的、世俗的世界;而理念的世界虽然遥不可及,但却高尚而又真实,这才是应当追求和定义的目标。理念不可被直观。在柏拉图所划分的两个世界中,可感觉和感受的世界是被我们的肉体触碰和明视的;而至上的真理则是我们无法直观的,不管是在智力和心灵上都超越了人类感知和理解的能力,需要“灵魂之眼”的洞察,所以这一极限的理念概念只能在数学上加以描述和规定。伽利略感叹数学是上帝的语言,他声称:“哲学是写在那本永远在我们眼前的伟大书本里的——我指的是宇宙——但是,我们如果不先学会书里所用的语言,掌握书里的符号,就不能了解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别的几何图像。没有它们的帮助,是连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没有它们,人就在一个迷宫里劳而无获地游荡着。”[14]135~136 宇宙不再是等级制的有限宇宙,而是开放的、无限的。整个理念论衍射下的极限话语通过将生活世界的经验进行理念化的运作而产生出科学的话语,不再是观审、推理和归纳,而是假说、演绎的体系化。这一进程后来通过了牛顿物理学工作的验证,数学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为自然科学提供最基本概念的理论框架。胡塞尔说道:“在这种数学的实践中,我们达到在经验的实践中达不到的东西,即精确性……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变成了数学流行。”[15]33~34但吊诡的是,理念作为创生的哲学概念被极限规定,并且是超越人类经验的纯粹思维活动的创造物,人们愈是要在思维或形态上对理念加以描述和分析,愈是要远离和背弃洞穴里活生生的一切,生活世界既然不再值得被信任,理念的世界就具有数学语言精确的描述范围内不可置疑的现实性。保罗·利科说:“真正的现实性是数学的方式,因为这一要求——以数学为方式观察自然——便是‘自明的’。”[7]40 因此,自然科学目光中的自然不再是我们借以安身立命、在世界之中被感性直观方式所给予的自然,不再是那个我们联系为一体,相互构筑世界的、跃动着的,让我们呼吸、驻足、死亡的自然世界。自然在理念的统摄下,成为数学化的自然。胡塞尔称之为“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了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7]41。在这一前科学、前理论化的自然中,世界作为我们栖息其中的家园,作为一个循环不息、圆满自足的整体出现在现象里,它在人类所有思想、论证、理论、逻辑、话语出现之前就已经和我们密不可分了,就像我们的呼吸。而在科学中,客观主义则意味着科学在生活世界基础之上构造的理念被视为真正的客观实在,并以此理念为依据和本源对生活世界的构成及其合理性进行判断和裁决。科学对自生的根基思之甚少,以至茫然无知,在这一现实性的客观主义层面上以理念对生活世界进行持续的理念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异化,而在原初发生的则是世界的异化。“一旦思想变成工具性的量化知识,一旦世界成为抽象化的逻辑公式,由于人类主体居于‘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世界就决定性地成为图像。”[16]25 胡塞尔认为将一种不可直观和把握的“理念”进行“理念化”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这种理念实践也就创造和催生出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理念”。而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理念实践,它本身是无限跨越的,但仍以生活世界的先在为基础,就其本质而言,它要求对生活世界中一切感性的经验和体验进行理念式的无限化。如胡塞尔所说:“关于一种合理的无限的存在整体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存在整体的合理的科学的理念的这种构想,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物。无限的世界,在这里由理念的东西构成的世界,被构想为这样一种世界,它的对象不能够单个的、不完整的,好像是偶然被我们所认识,而是要通过一种合理的、系统的统一的方法才能达到。这种方法在其无穷的进展中最终能够把握每一个对象的全部自在存在。”[15]32在胡塞尔的理论中,这一非历史性的“直观世界”被称为“生活世界”,它与我们科学化的自然、理性化的逻辑以及理念的统摄产生了巨大的对立,但以理念论为基础的科学世界“是一种理论的基层结构,它原则上不可能被知觉,不可能在其自身中被经验,而生活世界的主体性正是在一切方面都以具有实际可经验性为特征,生活世界是一原初明证性领域”[15]32。 三、西方政治的湮没 随着理念论的确立,政治生活被理念的超越性所统治,而在理念愈发绝对化的过程中,这一绝对化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在其语言即数学语言之上建立起一整套超验的形而上学神话。它以我们逃离自身存在的生活世界为前提,将现实性即所谓的科学性牢牢地固定在那个无限的理念上。而当这一切理念的理念化运作相应地出现在政治领域中时,它的颠覆也将是绝对性的。阿多诺说:“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计算世界的公式。柏拉图在其后期著作中将理念和数字等同起来,这具有神话的味道,数字成为启蒙运动的准则。”[17]207知行合一的苏格拉底式的实践和德性传统顷刻间被理念论的永恒和不朽打破了。确定的知识驱逐了意见,这一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在超越生活世界古老的道德与宗教习俗之后,忘却了对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人类而言的政治的存在,它应该是,也必然是道德和传统的。政治的思想不再是思想着(as)政治本身的思想,它变成了“对”(for)政治的思想。 支配性的政治世界来临了,霍布斯以“逃离恐惧”为代价,制造出一个非人格的利维坦。而在霍布斯生活的时代,一部分哲学家正在以近代的方式发动着对知识论的怀疑论攻击,即人类无法在本质上认识事物,除了借助科学手段。如梅森和伽桑迪阐发了一种经验性的、实用主义的近代科学观点,这是一种没有形而上学、无须证明的科学,他们试图以实用主义的方式缓和怀疑论所造成的危机。他们的朋友,包括格劳修斯与霍布斯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而后来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则以另一种方式将其发展为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时在怀疑论的普遍攻击下,一些重要的神学家、政治哲学家、法学家都放弃了对完全确定的知识的需求,转而满足于能够进行修正和证实的有用性的知识与假说[14]151。 在利维坦的统治下,统治者垄断着权力与暴力。合法性是以契约的形式达成,并以统治和服从作为一切政治合法性需求的正当依据,它在“利维坦”的庇护下,放弃了积极的自由而更多地追求和导向消极的自由。这也是近代兴起的资产阶级形象,他们精于计算个人得失,以理性主义的价值准则衡量一切,追求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实现,不再是社群的而更多是原子式的个人。在他们看来,安全、秩序才是重要的,而非荣耀和不朽。在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伦理规范中,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最终与利维坦达成契约。奥克肖特说道:“霍布斯是近代世界第一个坦率重视流行的个体性经验的伦理学家,他将人理解为受避免毁灭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与所选择的追求之冲动所支配的有机体。”[18]90由此人便理应获得自我保护的权利,而正是这种以权利为导向的话语成就了现代自由主义,而达成自我保存的最终目的也就自然超越了对追求自由的渴望。至此,自私的合法化已在现代政治学的版图中被刻画好了,它甚至不再需要任何义务与责任。列奥·施特劳斯分析道:“如果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那么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是一项义务,而是一项权利。所有义务都源于自我保护这一根本的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因此,不存在什么绝对或无条件的义务;只有当履行义务而不至于危及我们的自我保护时,那些义务才是有约束力的。唯有自我保护的权利才是绝对的。按照自然,世间只存在一条不折不扣的权利而不存在不折不扣的义务。确切地说,构成人的自然义务与自然法并非一项法律,既然基本的绝对道德事实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那么公民社会的职能和界限就必须以人的自然权利而非自然义务来决定。”[19]18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塞罗所谓的“共和国”——“民众之事”,它是由依照法典及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要求而联系、构建起来的群体。这一结合的目的完全不是为逃离死亡的威胁或是自我保存的需要,而是出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即公共领域内言说着的本质所规定和赋予的是其所是。 自由允诺一切,但偏偏不是幸福。历史充满了嘲讽,当追求自由的人民逾越主权范围的底线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主权使暴力这一必然性的概念成为正当,而个人可以随时被消灭,到了最后,归属于支配性的暴力依然存在,变成了自由的敌人。而政治被认为是可以运用一系列普遍化和形式化的法律及制度规范的框架而解决的问题,权力在其中被权利所限制。政治这一议题根本上与追求自由的行动相互冲突,它外在于自由的世界,以至于政治所涉及的领域越广泛,自由就越岌岌可危;反之,自由就会不受阻碍。古希腊人早已意识到,支配他人者必定没有自由,因为支配性的概念仅仅存在于被必然性支配的私人生活中。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希腊城邦的保卫者都已做出承诺,假如战败,自己将完全从公共生活中隐退,这些保卫者既不希望自己成为支配者,也不希望自己成为被支配者[20]159。在霍布斯看来,为了换取和平与幸福的权利,在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无常时就必须拥有利维坦——被制造的国家机器,即支配是必需的,甚至本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因此,现代人惯常认为,自由的程度越大,政治的因素越小;自由被剥夺,完全是政治出现了问题。从霍布斯为现代性打下基础开始,自由就已成为外在于利维坦的问题,与政治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张力。主权以及后来的民族等概念都是从抽象的形式化概念出发的,涂抹着活生生的个人,也决定了西方的政治。 阿伦特甚至认为,柏拉图是人类历史上将知行分离贯彻至政治传统中的第一人。她认为:“对于柏拉图而言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他在《法律篇》结束时清楚无误表明的,唯有archein才有资格统治,archein在柏拉图的思想传统中,这种原初的、在语言学上规定了‘统治’与‘开端’的一致,造成了所有开端都被理解为统治的合法化后果……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行理论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有无法化解的权力意志所做的辩护。”[5]175柏拉图主义将统治与服从的二元对立原则拓展到以言说和显现为代表的政治领域后,支配代替了行动,自由的概念发生了改变。“理念论”首先将关于技艺人的制造思维(目的-手段)引入政治学,以统治为目的,以服从为结论。此时,政治学成为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分支,即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而后“理念论”又将关于制造的理念贯彻于对自然的态度上,政治学成为本身可以被分析和谋划的一项制造物。 技术与数学的合力将政治学数字化,使其适应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并延伸出后来的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等诸多研究方法。可以说,政治学已被完全地数字化,成为可以被控制的变量与一种科学研究。米歇尔·福柯不无讥讽地认为,现代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不同于古代,它完全来源于数字,不再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危不受侵害为基础,而关注控制和平衡统计学中的数字——死亡率;现代权力,也以一种知识化、技术化的权力面貌出现;而现代的知识学说,从政治统治的层面来看,也是一种由技术理性所主导的权力形式,它暗含着权力宰制的功能设定,所以现代的知识属性体现为一种在本质上分析人和规范人的真理话语体系,成为一整套严密的、符合整个社会运转及保证主权存续的“训育式的真理话语与知识体系”。“一方面,权力在逼迫我们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需要这种真理,我们也必须生产真理,如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生产财富,为了权力生产财富,我们必须生产真理。”[17]107既然主体性是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建构起来的,那么这一建构也必然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被不断地重塑,甚至生产和取消。 柏拉图主义行进至笛卡尔的时代时,通过“我思”而完成了主体性的奠基,人类由此跃出“世界之中”而站立于“世界面前”。自人被视为自然的立法者之后,启蒙运动裹挟着乐观主义的理性精神和进步原则,技术科学的力量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理性则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当主体背身于他得以驻足的生活世界时,主体也就沦为客体了。本真的人脱离了世界,成为虚无主义荒漠中的浮萍,进而在18世纪实证主义兴起的大潮中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经济学上的人、生物学上的人、人类学上的人或社会学中的人。在科学范式主导的专业分工背景下,作为真理话语体系下的人被重新塑造和规训,权力也在现代呈现出从王权到生命权力的过渡⑨。人成为被奴役的君主、被监视的监督者。主体以征服自然的名义将一切存在者表象纳入技术科学的研究轨道中,而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沦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执行这些任务的便是所谓“人之科学”或“人文科学”。 现代是人的时代,也是人之科学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与人文科学的各项专业化知识门类紧密结合。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与真理话语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伴随着新知识的生产与真理话语的更迭,以适应权力进一步对主体的训育和治理。因此,现代统治逻辑的权力机制与技术科学的“座架”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点⑩。座架促逼着将一切尚未显现的“是者”强行纳入到解蔽的过程中,而整个现代统治赖以维系的权力机制也将人作为对象化的存在者纳入治理的序列中。权力机制的构成和散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严格地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畴相吻合,这也就意味着权力机制本身与真理的形式是共为一体的。因此,现代的政治学就是关于主体的真理话语和知识体系。福柯认为:“关键不在于使真理摆脱任何权力制度的束缚,这不过是空想。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力,而关键在于使真理摆脱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支配形式。而在目前,真理就是在这些形式内行使职能的……总之,政治问题不是谬误、幻想、被异化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就是真理本身。”[17]109 在古代,人们通过确立坚实的知识论及其严密的论证体系去把握和联系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在现代,知识论陷入了混乱和失序的状态,它已被技术科学的极限话语与工具理性的暴政重新编排和控制,科学在实践层面已经完全主宰了人文学科领域。在人类成功地将自然计算为图像,并用理性加以分割和谋算的时候,主体自身也被摆置于技术的座架中而被强行地层层剥离、拔出根基,去不断适应技术座架的要求和权力所生产的真理话语的规范。海德格尔认为:“牧人们不可见地居住着,居住在荒漠化了的大地的荒地之外。荒漠化了的大地只可能对保障人类统治地位有用,而人类的作用限于作出这样一种估计:某物对生命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作为求意志的意志,这种生命预先要求一切知识都以这种有所保障的计算和评价来活动。”[21]101当人的存在特征即言说被遮蔽在现代政治体系的实践中,则意味着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和流放了。随着政治本身被技术科学拆构和宰制,原本已被遮蔽的公共领域变得更加晦暗不明。一种统治的形式逻辑随着言说的停止与技术科学的渗入,使政治赤裸裸地被塑造和形构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主权之争以及民族国家经济体系中商业逻辑的副产品。而这一统治的底线也是由技术科学的产物“原子弹”所蕴含的摧毁地球的巨大能量所挟制和悬隔的。如同瓦尔特·本雅明所预言的那样,时代的境况凸显为一种“大灾难”征兆,而这一巨大的灾难并不是注定的,而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偶然的时刻,并将一切摧毁。 四、结语 柏拉图主义通过创造理念和借助理念化,对现实和意见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在人类的精神体系内引入了无限的概念,成就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也衍生出现代的技术科学。而理念论被应用于古老的公共领域之中,不但颠覆了我们政治存在的特点(它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颠倒),同时这种背离生活世界的去自然化也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并依据理念世界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使人本身不再是居住于大地之上“存在”的牧人,而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种共振的“技术原子”。因为整个星球及其存在者已被摆置于技术研究的座架之上,而现代政治治理术的一整套统治逻辑和治理形式也与技术科学的本质呈现出逐渐契合的状态。 希腊时代的自然目的论——万物如其所是的存在状态被“理念论”打破了,自然和世界在理念的引领下被赋予了超越论的特征。对本源的探寻从未停滞,在基督教兴起后,这一去自然化的、探寻本源的过程在全能、全在、无所不能的造物主面前继续推演着。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一种想要摆脱历史和时间从而把握永恒的倾向。而这一切去自然化的状态,即背离生活世界的悖论,直到尼采痛苦地将柏拉图主义颠倒之后,随着剧烈的批判才展现出这一去自然化进程的效果,即Arche作为开端与统治的双重性原则在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历史中与世界的倒错关系及其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注释: ①“Arche”作为一个严格的术语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在希腊语中有“开端”与“统治”的双重含义。参见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3页。 ②“自然界”——当我们这样说话时,现象早已衰败和褪色了,形而上学将整个世界标示为对象,并将其在主体的意志中表象化。 ③转引自孙磊《行动、伦理与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的交往政治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④同上,第161页。 ⑤“理念”诚然是柏拉图哲学的主要概念,来自人造事物领域内的活动经验,其诞生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认识所要制造之物的意象模式或“理念”,然后确立和整合各种手段并开始执行。柏拉图在他的《会饮》和其他与政治哲学并无严肃关系的著作中把“理念”描述为“光芒闪烁”之意象,因此是美的变化形态;唯有在《理想国》一书中,“理念”才转变为行为的准据与规则,而成为“善”之观念(古希腊之意义的“善”)的变形或衍生,此时它意指“有用”或“适用”。参见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译文略有改动。 ⑥在希腊文paideia(教育)的解释中,海德格尔回溯至柏拉图,并认为对paideia的正确解释应为“造形”。在《理想国》的段落中,柏拉图说道:“接下来,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以下情形……”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paideia的释义变为:“接下来让我们根据(下面描述的情况)来获得‘造形’以及无造形状态(的本质)的一个样子,后者(其实是共属一体)关系到我们人存在的根基。”参见朱刚《开端与未来——从现象学到解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页。 ⑦Mathesis意指学,ta mathemata意指可学的东西,即就其是可学的东西而言的物,参见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57页。 ⑧“理论”源于希腊语动词“观审”(theorein),对应的名词为“知识、理论、观审”(theoria)。这一“观审”的概念在希腊意味着对无蔽的在场者之持续的“看”,观审的生活方式属于希腊人此在的一部分,它区别于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活动有目的导向和功利主义色彩。因此,“理论”源始意为对无蔽状态即真理的一种“看”的护持。罗马人将theorein译为cnotemplari,将theoria译为cnotemplatio,指将某物分离而围住,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无蔽者持续的观看之护持已被丢弃了。cnotemplatio的德文翻译为Betrachtung(观察),这一词根也即Trachten,为拉丁语tractare,意为对某位的提取、制作、加工,为了获取和占有某物而去tractare。从观审的理论到对物的属性的获取这一词义改变,可窥见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实验科学的递进过程。详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9~50页。 ⑨福柯认为,生命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训育,训育臣民。不是统治者的诞生,而是臣民的制造。这就使生命权力呈现出明显的技术特征,是一种知识权力,它是一种管理、提高、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积极的权力,其原则为:既增加受奴役者的力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及效率。参见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⑩主客体关系在“座架”上获得了它纯粹的“关系特征”,亦即订造特征,其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吞并了。这并不是说主客体的关系消失了,相反,它现在达到了它的极端。根据集置而预先被规定的统治地位,它成为一个有待订造的持存物。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6页。标签:政治论文; 柏拉图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数学论文; 数学文化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