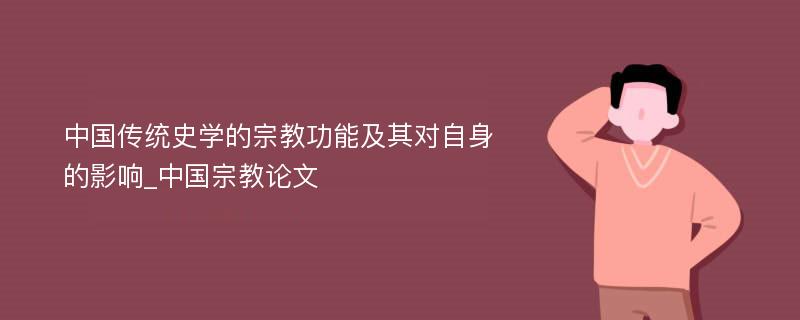
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及其对自身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其对论文,职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经世济国之学,——“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①。而到了当代,史学似乎逐渐被边缘化,除了“戏说”、“趣说”之类还为社会所关注外,似乎得了自闭症,只在自己的圈子之内发生影响,而且随着研究者题目的逐渐细琐,能够影响的圈子还在缩小,乃至某些研究成果关注者仅以十数人计。于是史学家多抱怨社会冷漠史学,以为这是社会追逐实利、轻视文化所致。前段时间在网络上读到余世存先生的文章《今天怎样读历史?》②,其中表述了“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的观点,尽管笔者并不怎么同意他的说法,但颇受启发。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反思史学自身,有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特性。
一、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后期,史学地位很高。主流学者或认为“史”与作为统治思想基础的“经”同等重要,互为表里,“经”述理论原则,“史”表实际事例。元郝经曰:“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③明杨慎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要其归宿,言以史之相表里也。”④或认为“经”即“史”,直接包含于“史”之内。明王世贞说:“史学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⑤明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⑥明李贽说:“经、史一物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⑦到清章学诚,则将“六经皆史”⑧一句置于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全书之首。依此,史学必然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学术,包含了理论原则和实际事例两个方面,从而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为什么中国古代学者如此重视史学,认为史学在社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史学执行着一定的宗教职能。
宗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在宗教学领域也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从功能上说,无非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就社会方面而言,它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如德国思想家西美尔所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诸多关系形式,它们承担着各种不同的内容,其中似乎就有那么一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宗教形式”,它“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做是自身内的东西”⑨。也就是说,宗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将个人按照一定的秩序联结起来,从而将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各种社会势力、集团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联结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各种要素使之一体化。宗教通过其观念、教规、礼仪、组织等等形式,将某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进而演变为个人内在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取向,从而使个人的行为和精神都严格遵循确定的社会关系,并维护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与此相对应,就个人方面而言,由于为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作出了贡献,这种社会关系相应给予参加宗教的个人以一定的稳定生活,包括各种援助系统,在这种现实援助的基础上,同时又给个人以精神的稳定和安宁,借助于超人间的神的力量,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
就社会整体的层面观察,宗教仍然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规则、一种秩序,以强制和非强制的方式,要求人们遵循这种社会规则,从而保证确定社会关系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有许多种,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法律、条例、军队、监狱等等,主要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一类则如道德、舆论等等,主要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来维护秩序。宗教似乎介于二者之间,例如部分教规包含有强制性的内容,但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是借助“神”的威慑力,以道德、舆论等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导向和约束教徒的行为,使之心存敬畏而遵守秩序。正是由于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因此,不管宗教的形式有何种变化,不管“神”以什么形态出现,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宗教,不能不完成由宗教所实现的那些功能。
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迥异,中国比较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⑩,虽然有道教之类本土自生宗教,也有佛教等域外传来宗教,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们一般处于非主导地位。在世界很多地区由宗教来实现的那些社会职能,在中国也必须得到实现,这种职能就部分地落到了史学身上,特别是其中非强制性的道德、舆论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不等于宗教,但它以道德审判和舆论导向的角色积极干预社会生活,调整和维护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心存敬畏而遵守一定的秩序,发挥着很强的现实作用。典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让人们敬畏“神”,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敬畏记载下来的历史,以此为标准净化自己的灵魂,遵守一定的秩序,从而都完成了一定的宗教职能。
史学宗教职能的实现,取决于史学自身和社会两个方面。一方面,史学明确认为自己有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的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也认可这种导向和审判。
自孔子开始,史学就明确担当起了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的责任。《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将扬善惩恶作为史学的基本任务,而这种修史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从而将史学及史学家置于极高的地位。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史学的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功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在解释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时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得很清楚:与其立空言设褒贬,“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司马迁还引董仲舒评论《春秋》之言曰“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1)。史学除了明确自己惩恶扬善的责任外,还对自身的道德审判效果予以高度评价:“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史学可以对现实政治发生强大的作用。这种传统一直持续了下来,如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2),“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13)。王阳明说:“史以明善恶”,“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以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14)。
与此相对应,社会也普遍认可史学的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争取“青史留名”、“流芳百世”,而绝不能“遗臭万年”、“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当说是社会的共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绝唱,也可谓是这种道德价值观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一些社会精英人士,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不公的待遇、甚至被推向绝路,而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准则时,往往会选择牺牲自己,寄希望于历史,以求在历史的肯定中得到永生。不仅如此,帝王也经常使用这种道德价值观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当臣下的言行符合其利益时,往往给予“宣付史馆”、“诏史官树碑颂德”等褒奖。
不仅在上层,社会下层也被这种道德价值观深深地浸染着。杨家将血染疆场、岳飞精忠报国,秦桧卖国求荣、魏忠贤奸佞误国,这一类有着明显道德审判内容的历史叙事通过戏曲等形式广布民间,指导着一般民众的道德价值判断取向,也成为他们判断眼前事物价值的道德准绳。黄永玉先生有一幅画,画面是故乡凤凰县陈家祠堂里的戏台,上有匾额,书“观古鉴今”四个大字,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这种戏台在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足见以历史记载作为道德价值判断依据的观念已经深深渗入到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心灵之中。
人之著史,扬善抑恶。人之读史,趋善除恶。历史具有了强烈的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功能,部分完成了本该由宗教完成的社会职能,这样,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史学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史学又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主流史学道德价值观的性质
在典型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类道德审判和舆论导向的功能由宗教来执行,宗教教义是其基础,而最终的判定者在形式上是上帝之类的神。一般来说,在这里,道德价值判断归之于宗教,历史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而只好落到实处,注重于现实历史过程的记载,注重于历史与现实存在的人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给予历史以一定的解释。他们往往着力于历史的解释和重构,从而对历史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性和人性。与此相适应,历史学家并不试图对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发生太大的作用,不想把宗教的职能揽到自己身上。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由神最终确定的道德价值判断,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历史的身上,从而使历史学家似乎部分地取代了神。这种现象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历史在社会的道德价值判断领域真可以发挥很大的实际作用,真可以“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可以使“乱臣贼子惧”。这种错觉给予了历史学家过重的责任,同时也给予了过多的荣誉,使历史学家飘飘然,以为自己可以提出某种独立于社会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某种独立的史观,并在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将这一点予以强化,反过来似乎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假象面前存在两个问题:1.历史学家、特别是主流历史学家能否在本质上提出自己独立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某种独立的史观?2.史学家所提出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对社会、特别是社会上层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先看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社会是复杂的,作为社会成员的历史学家可能甚至必然提出多元的、互异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及史观,未必就能一致,班、马的差异就是显著例证。但不管史学家个体的思想有多大差异,究其根源,仍在于具体史学家的具体社会存在,也就是他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由这种位置所必然确定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影响。个体可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思想发展,但无论如何奇特,他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包括思想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史学家所提出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和史观都无法获取充分的独立性,或者说,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主流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特征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史学主流的道德价值判定和史观必然与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利益取向相一致,与他们的道德价值判定相一致。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强势集团、特别是统治者决定了主流史学的道德价值判断,而主流史学的道德价值判断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主导性力量的社会地位。
从不同时段来看,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利益取向是有差别的。就短时段而言,例如一个王朝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皇帝、或同一皇帝的不同时期,其利益取向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就影响着主流史学家的道德价值判定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任何时代,由于适应环境是作为个体的史学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大多数史学家总是不断改变自己的道德价值判定,以适应社会主导力量的利益取向,生产出种种为现实服务的史学著作来。而就长时段而言,例如涉及一个王朝、或若干个王朝以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主导力量的利益取向就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他们要求统治者能舍弃一些眼前利益,限制贪欲,以维护自己集团整体的长远利益。与这种利益取向相适应,史学整体则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道德价值判定和史观。统治者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必然发生冲突,在史学领域,适合于这两种不同利益取向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也处于矛盾之中。由于后者表现出了更强的稳定性,而且往往与现存的统治者利益相冲突,以至于好像这些东西是史学自身独立于社会而产生出来的。但不管它们如何矛盾,最终都符合社会主导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因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至于反映非主导利益集团或者说非统治集团利益价值取向的史学,虽然不能说不存在,但总是非常微弱,无法动摇主流史学的地位。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主导性力量的长远利益取向选择了儒家的思想、当然也包含其道德价值判断体系,因此,史学整体、长远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必然也以儒家思想作为基础。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成为史学道德价值判断的灵魂。
余世存先生认为,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历史就是人心、人性”,“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惩恶扬善,净化人心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史家传统来维系的”,并从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价值审判作用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这种肯定更多出于良好的愿望,选取了传统史学中符合自己要求的那部分内容,其前提是历史记载符合真实过程、符合良知,但已有的历史记载未必符合真实,更未必符合良知。这种肯定态度会引导人们过分信任已有的历史记载,因而无疑是有害的。首先,在任何时代,人心是多样的,符合人心的历史也是多样的,有符合下层老百姓人心的历史,也有符合上层统治者人心的历史,但占统治地位的只能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历史,这种历史在根本上属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其次,尽管是下层老百姓的人心,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跟随上层统治者的导向,杨家将血染疆场、岳飞精忠报国之类意识就是很好的表现。社会弱势群体的自我意识本来就十分艰难,而统治者总是阻止其自我意识。最后,即使历史记载对现有统治者眼前利益持强烈否定态度,虽然就长时段来看,表现出了更大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其道德价值判断只是符合统治者长远利益,而并不是出于被统治者利益,这种历史最终仍然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历史。肯定历史的这种道德价值审判作用,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只是表明我们还缺乏好的道德价值审判体系,无力对某些现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只好求助于传统。某些时候,实际上是采用了所谓“抽象继承”,即在传统历史道德价值审判体系的名义、名词之下,表达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再看第二个问题。史学家所提出的道德价值判定体系对社会、特别是社会上层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由于统治者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史学的道德价值判断也必然出现矛盾,因此,就会出现本着儒家精神、符合统治者长远利益的史学派别,对统治者的短视行为进行的道德价值否定,那么,这种否定或限制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尽管史学家高度估计了其作用,以为可使“乱臣贼子惧”,但从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其作用其实十分有限。统治者一般并不害怕历史,尽管过去的历史记载由于其道德价值判断导向而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一定的限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他们是历史的主导力量,正在按他们的意志现实地制造着历史,他们由此永远都着眼于现在,着眼于现实的利益,历史的道德谴责是身后之事,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史书的纂修,从而使史书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撰写。
前一点几乎不用说,历史上的统治者哪一个在涉及他们利益的行动和决策时会认真考虑历史将如何记载,他们很清楚,历史记载中“成者王侯败为寇”,首先是要成功。当他们考虑到历史时,往往是按照需要,或“作秀”让历史记载下来,或设法让历史不要记载某些事,甚至直接表示出对历史道德价值审判的蔑视。东晋大司马桓温就有一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15)他们只在乎现实的权与利,而并不在乎历史如何记载他们。
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从根本上控制了史书的纂修与研究,其手段主要有四:
1.垄断修史权,定正史为官修,禁私修。
班固继承了父亲班彪的修史事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只是经过其弟班超“诣阙上书”,“具言固所著述意”,为明帝赏识,“除兰台令史”这一“秩百石”小官,方得以撰史。可见,至少从东汉开始,私修国史是违法而要被刑罚的,只有被任为史官,方能合法撰史。而合法撰史,则必须歌功颂德,“思仰汉德”、“述叙汉德”。正是为表现颂扬汉德,班固攻击司马迁“私作本纪”,将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16),“是非颇缪于圣人”(17)。此后,正史修纂垄断于统治者之手,自唐设史馆之后愈演愈厉,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定制,“近于现代之正史,悉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偶有纂述,辄以肇祸,后遂相戒而不为”(18)。
2.以暴力令修史者俯首帖耳。
史家多津津乐道南史、董狐之秉笔直书,殊不知史家亦人,生存总是第一位的,统治者使用危及其生存的暴力,总会使修史者俯首帖耳。金毓黻先生论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风日杀”,认为其远因是北魏太武帝时令崔浩修国史,崔“无隐所恶”,遂导致“坐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时并为之废史官”,导致韩愈等后人“相戒不轻作史”;近因则是隋文帝“下诏曰,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此后屡屡有因撰史而获罪者,直至清代,“每因修史受祸”(19)。刘知几说得很清楚:“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0)
3.控制修史指导思想乃至直接操纵修史。
修史权既垄断于统治者,修史指导思想也为其所控制。有时,统治者也会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修史指导思想,如李渊就说,“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21)。但更多时候是通过监修官直接控制修史思想。刘知几说史馆修史“所载削,皆与俗浮沉”(22),宰相之类监修官或曰“必须直词”,或曰“宜多隐恶”,操纵修史。甚至尚在草拟之中,“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从而使修史完全处于统治者操控之下(23)。对于这种歌功颂德的史书,皇帝有时还觉得不够,直接指令再加颂扬内容。唐许敬宗等奉诏撰唐初国史,高宗李治嫌其“多非实录”,要求增加皇帝德政记载,诸如李世民之德政:“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鞮鍪生虮虱”,又如某次检阅军队,因“忽然云雾昼昏,部伍错乱”,李世民“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以免责罚过多,等等(24)。
4.垄断修史资料。
此亦惯例,金毓黻先生即言“史由官修”,“则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唐宋以降,“时君贤相,锐意求书,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在秘府之掌,即入显宦之家”,故如万斯同“有志独修明史,而不能不主于时相之家,以博观其藏籍”(25)。
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统治者牢牢地控制了史学的主流,当然也就控制了史学的道德价值判断,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即使是史学以“直笔”引以为自豪的南史、董狐也莫能例外,皮锡瑞云:“刘氏以为董狐南史,各怀直笔”,“无乃乌有之谈。不知南董非崔赵之臣,故可直书”,——南史、董狐并非崔杼、赵盾臣下,故有直书之举。又直接质问刘知几:“刘氏在唐,曾为史官,试问其于唐代之事,能直书无隐否?”(26)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史学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判断约束统治者,岂非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由此可见,传统史学就主流而言,其所具有的宗教职能,实际上是以符合统治者利益的道德价值观,通过史籍对社会进行道德审判和舆论导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们的精神和行为。而且,即使是这种符合统治者长远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对于统治者的约束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符合统治者长远利益的史学道德价值观不会对统治者的短视行为不予抨击,也不意味着不存在与主流史学不同的坚持其他道德价值观的非主流史学,当然更不意味着非主流史学的道德价值观不需要展现自己的风采。其实,史学的光彩更多时候是由非主流方面表现出来的。
三、宗教职能对传统史学的影响
既然史学承担着这样的宗教职能,起着社会的道德审判与舆论导向的巨大作用,那么反过来这种职能必然对史学自身产生重大影响。
宗教劝导人们出世,但宗教本身却入世极深,直接干预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史学虽然叙述的是过去的事,但它的宗教职能也使它成为一种入世的学问,与社会生活发生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这,正是史学得以成为具有“经世济国”作用的显学的基础。
史学的这种入世,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地、理性地干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依据史学所获得的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所坚持的道德价值判断,指导和制约人们的精神追求及现实行为,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由此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
刘知几明确指出史学的职责:“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7)“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28)史学家俨然就是社会道德审判官。他还将史学成果分为三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清浦起龙将此三等分称为“秉直者”、“勒巨册者”、“徒多闻者”,发挥道德审判功能的“秉直者”是上等,而“勒巨册者”和“徒多闻者”为中下等(29),此外史学作品只能属于等外,可见刘知几非常重视并高度评价史学的道德审判功能。
章学诚也认为,“史志之书”须“传述忠孝节义”,“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30),坚决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史学,强调真正的史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蜕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31)。将学术贴近于现实指为必须,将不知当代而好古之文视为琐碎和猜谜。他说自己的著作“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32)。他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而为此,就必须厚今薄古,“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33)。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如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4)又如现代史学家陈垣曾述及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研究,“九一八”后,讲《日知录》“注意事功”,“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以振之”,此时作品“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35)。
但另一方面,史学的入世也表现为消极地、顺应地服从现有社会秩序和规则,为现实统治者和统治思想服务,这往往是史学的主流。孔子“《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笔则笔,削则削”(36),已成为中国历史撰述的一种传统。即使认为史书撰著必须“直笔”的刘知几也认为这种“隐讳”是合理的,“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37)。“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讳之可也。”(38)
消极入世的传统则给史学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历史记述远离历史真实。刘知几说,史家或畏统治者权势而不敢直书,“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欲求实录,不亦难乎”(39)。或追求名利而不愿直书,“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40)。或为个人私利,借修史报个人恩怨。“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41)。这种类型的入世使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他认为这在史学中是“罪之甚者”(42)。刘知几自己也有切身体会:当其奉诏撰史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所载削,皆与俗浮沉”,“凿枘相违,龃龉难入”,“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因此方有《史通》之作(43)。
史学的入世一方面使史学谋求积极、理性地干预社会生活,试图改变现实,一方面又由于种种原因,消极地顺应环境,为统治者服务,二者必然形成尖锐矛盾,史学工作者也由此形成两个基本的群体。由于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学术都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因此,史学的入世更多的是顺应环境,而只是在少数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奋斗之下,其积极的一面才能表现出来并发挥一定的作用,与此相应,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是消极的入世者,但史学的希望并不在多数,而往往是在非主流的少数人那里。除此之外,当社会环境不允许积极入世时,有可能产生一种中间形态,即出世的形态,——一方面不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姿态,另一方面也不明确表示顺应环境,而是将史学与现实隔绝开来,进入似乎是纯学术的境地。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时期,乾嘉之学就是一个例证。然而,即使是这种出世也脱离不了社会现实,它作为粉饰太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为统治者所允许,并借此背景得以繁盛;当它甚至连这种粉饰作用都实现不了的时候,也就只能走向衰落。
由宗教职能而来的入世,使中国传统史学还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既然是入世,就要以一定的思想、立场、价值观干预现实生活,这就导致史学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并不完全建筑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之上。既然是入世,就要表明自己所说的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人力所无法抗拒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它特别强调历史的因果性、规律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主体能动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既然是入世,就要说明它所叙述的一切事件、过程都是真的,因而它所得到的有关因果律的结论也是真,这就导致它坚信——或至少表现出坚信——自己所其描述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不顾历史的基础只是少量残留下来的且带有相当假冒伪劣内容的史料,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眼光看待这些史料,并通过这些史料试图与过去“对话”③。限于篇幅,笔者将这些内容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宗教职能及由此而来的强烈的入世精神,一方面使史学与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了较大的距离,不是把历史看作纯客观的对象进行研究,如同植物学对待植物或动物学对待动物,因而不能得出纯客观或比较客观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它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与现实的思想、生活联系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史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将历史学从象牙之塔中引导出来,成为一门切切实实的俗世学问。正是由于这种学科特点,刘知几列“秉直者”为史学之上等,而将“勒巨册者”、“徒多闻者”列为中下等,更遑论等外之作,章学诚将“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之史学称为“鞶蜕之文”、“射覆之学”,不过是琐碎与猜谜而已。
现代史学来源于传统史学,其缺点与优点是我们先天的遗传因子,无法摆脱。史学远离现实生活,现实社会当然也会远离史学,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史学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回到现实。当然,如何回到现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特别是“文革”影射史学的恶劣作用仍历历在目,而新时代的史学又失去了发挥宗教职能的条件。当然,史学可以将自己变成一种与史学家个人兴趣相关的纯学术,但这样它就必须甘于寂寞,不向社会伸手,从而甘处“隐学”的地位。
出世必然没落,消极入世又违背正直史学家的良心,积极入世才是史学真正的前途。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能扬长避短,通过发挥史学正确的入世精神而治疗其自闭症,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呢?
注释:
①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外篇·史官建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http://www.jianwangzhan.com/cgi-bin/index.dll? pagel? webid=jianwangzhan&userid=147978& columnno=0&articleid=6062.(访问日期:2007年1月1日)
③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经史相表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⑤王世贞:《纲鉴会纂·序》,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本,1899年。
⑥王守仁:《阳明传习录》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⑦李贽:《焚书》卷五《读史·经史相表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⑧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一·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⑨[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⑩关于儒教是否宗教,学术界并无定论,鉴于其与世界各大典型宗教仍有较大差别,为避免过多解释和界定,本文暂将其置于宗教之外。
(11)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2)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1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14)王守仁:《阳明传习录》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6)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
(17)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2738页。
(1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8页。
(19)金毓敲:《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8页。
(20)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2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2)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2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十《忤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1页。
(2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2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
(26)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3页。
(27)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28)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29)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辨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30)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第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21页。
(31)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第五·史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1页。
(3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上尹楚珍阁学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3)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70页。
(3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5)转引自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5页。
(36)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37)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38)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四《惑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5页。
(39)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9页。
(40)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4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42)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2页。
(4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44)[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