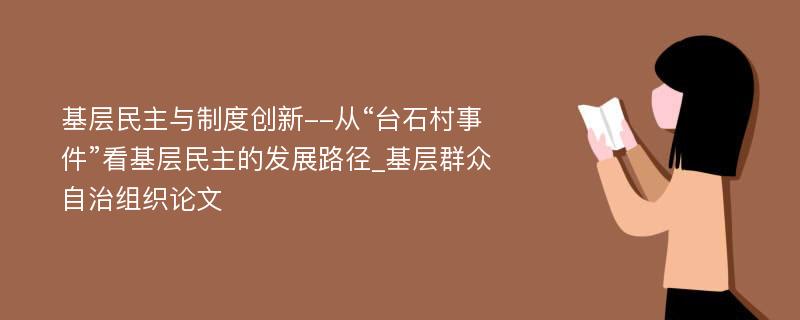
基层民主与体制创新——从“太石村事件”看基层民主发展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民主论文,路径论文,体制创新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载体。随着利益主体的日渐多元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在推进基层民主的过程中,“两委”经常遇到一些异常情况,其中,“太石村事件”最具典型意义。我们以此为例,探讨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
一、“太石村事件”
2005年5月初,番禺区太石村村民梁树生当选为该村第七小组组长。选前曾承诺给每位村民分1万元和1块宅基地。当选后,他要求村委会分配集体征地款和“辛苦补偿费”,遭到村委会主任陈进生拒绝。7月底,梁树生等人以“贿选”、“非法倒卖土地”和“卖地款去向不明”等为由,组织村民罢免陈进生的村委会主任职务。8月3日开始,约100名村民为了“保护账簿”强行占据村委办公楼;8月16日,150名村民围堵警车和执法人员长达2个多小时;9月5日,冯伟南等人向番禺区民政局提交892个签名,其中584个签名有效,依法启动了罢免程序。9月12日,番禺区公安干警和综合执法队员对被村民占据40天的村委办公楼进行清场;9月12—16日,番禺区政府对该村的财务进行审计,基本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个人损害集体、牟取私利”;9月29日,由于有396名村民撤销罢免要求,因未达到法定人数,罢免动议自行失效。
在此期间,境内外媒体和互联网争相报道该事件,普遍支持罢免行动。《人民日报》题为《有感于村民依法“罢”村官》的评论文章认为:“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该文章还引用学者的话说:“太石罢免村官具有代表性,将是农村村民自治的一个典范。”
“太石村事件”耐人寻味的不仅是地方政府的“无助”,而且是信息的极度混乱: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是“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地方政府为何要“力挺”被村民“依法”罢免的村委会主任?一件普通罢免案为何引起境内外媒体和互联网的广泛关注?
“太石村事件”最重要的意义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在城乡基层选举中,姑且不说贿选,也不说黑恶势力或宗族势力的介入,仅仅是一些不负责的承诺就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第二,当选者为了“兑现”承诺,可能罔顾国家法律和集体利益;第三,当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有人可能采取非法的或貌似“合法”的手段制造事端,甚至酿成群体事件;第四,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判断是非不一定能够得到群众认同,反而容易将群众与基层干部的矛盾演变成为与政府的对立;第五,在“仇官”心理的作用下,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听信一面之词,在境内外媒体、互联网,以及各种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政府容易陷入“有理说不清”的被动状况;第六,“民主”与“利益”纠缠在一起,普通问题被政治化,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二、“两委”的困局
由于“两委”普遍承担城乡基层大量行政管理工作,如果放任群众自行选举和罢免“两委”成员,势必会影响我党的执政基础。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局”。
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定身份承担城乡基层的行政管理责任,“两委”的角色容易发生混淆和冲突。
首先,“两委”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为了加强城乡基层管理和改善公共服务,许多政府部门把工作延伸到基层,将大量行政性工作交由“两委”承担。在人、财、物高度依附政府的情况下,“两委”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搁置群众自治的职能,久而久之,行政化倾向严重,偏离设立“两委”的初衷。
其次,群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以自荐或联名推荐的方式参加“两委”选举甚至罢免“两委”成员等情况越来越多,加上选举逐步走上程序化和规范化轨道,基层政府“驾驭”选举的难度越来越大。
再次,人员变动频繁不利于提高管理水平。“两委”成员普遍兼任专职工作人员,一届三年,期满后将根据选举结果重新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造成城乡基层工作队伍的不稳定,势必影响管理水平的提高。
可以说,“两委”的“困局”源于其行政管理职能与群众自治职能的混淆和冲突。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序推进城乡基层民主,需要进行体制创新。
三、创新基层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此,各地从分离行政管理职能与群众自治职能入手,进而推进两个职能的衔接和互动。
2008年9月,北京颁布《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要求设置社区服务站,“代理代办政府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办理本社区内各种公共服务事项,把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实现政府职能重心下移,逐步实现与社区居委会职能分开。”
无独有偶,2005年2月,深圳颁发《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在全市设立社区工作站。与北京的社区服务站相比,虽然名称有别,但其性质、职能,及其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基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也实行类似的体制:“洞(社区)居民中心”是一级行政单位,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负责福利、文化、就业、生活和体育等便民利民服务。与其相匹配的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负责收集和表达民意。这一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由政府设立的机构承担行政管理,可以强化基层管理;由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专责群众自治事务,可以加快推进基层民主的进程。
以深圳为例,经过五年实践,社区工作站与居委会的关系形成三种基本模式:一是分离式——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组织,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二是交叉式——两个组织的成员交叉任职,各有侧重地承担相应的工作;三是重合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尽管新的社区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其作用已显而易见,即使居委会仅仅加挂社区工作站的牌子,就足以形成解决“民主困局”的机制:一旦当选的居委会成员不适合从事基层行政管理工作,或遇到类似“太石村事件”等异常情况,只需要任命适合的人担任社区工作站站长,就可以在不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确保社区的管理水平。
在设立社区工作站之前,深圳已剥离了居委会的经济职能。2002年,深圳颁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城市化社区居委会与集体股份公司脱钩及党组织分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居委会与集体股份公司脱钩:一是机构脱钩,各自独立运作;二是职能脱钩,居委会负责居民自治,集体股份公司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产;三是工作人员脱钩,不安排居委会成员与集体股份公司工作人员交叉任职,但后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居委会选举。
在同时剥离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之后,居委会真正成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体制保障:一是有效地防止为了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参选的现象发生;二是吸引了一批真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人士参加居委会选举;三是居委会可以更专注于收集和反映民意,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居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体制创新加快了基层民主的进程,深圳的居委会直选率呈跨越式提升:2002年为1.7%,2004年跃升到47%,2008年提高至92.82%。迄今为止,这一体制基本上是在城市社区实行,这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使然。实际上,对于管理难度特别大,尤其是陷入“民主困局”的农村社区,也不妨采用这一体制,总比像“太石村事件”那样劳师动众地“救火”强。
四、几点思考
城乡基层民主关乎社会主义的存亡,在推进这样一项基础性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群众参与是基层民主的重点。推进城乡基层民主发展,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活生生的民主实践,培养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民主技巧和民主习惯,让民主自下而上地逐步拓展,这是我国民主建设的基本路径。
(二)保持稳定是基层民主的前提。既要拓宽民主的渠道,更要规范民主的行为,发展城乡基层民主,必须以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前提,必须是在可控的情况下有序地加以推进。
(三)“去行政化”是基层民主的关键。在区分行政管理职能与群众自治职能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构建两个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体制创新,实现“两委”“去行政化”,是推进基层民主的关键环节。
(四)“去经济化”是基层民主的需要。在区分经济发展职能与群众自治职能的基础上,剥离“两委”的经济职能,有助于避免经济利益因素对基层民主的负面影响,这是基层民主健康发展的需要。
(五)社会组织是基层民主的载体。基层民主的主旨是有组织的群众自治。社会组织的民间性使之能够比较好地体现群众的主体地位,成为表达民意和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的有效方式,是群众有序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理想载体。
(六)体制创新是基层民主的保障。我国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既不能为了民主而罔顾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不能因噎废食不推进民主。从城乡基层做起,通过体制创新,可以为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标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 基层民主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