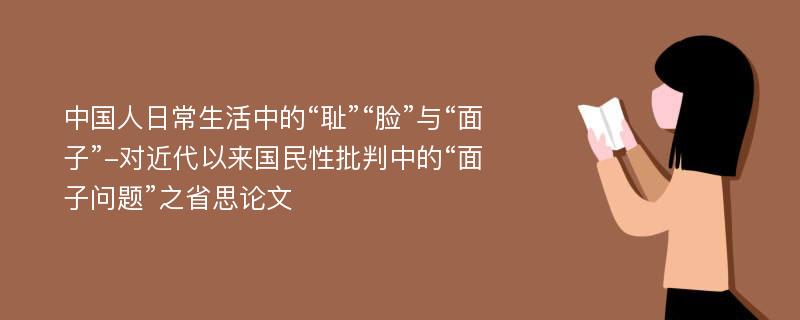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耻”“脸”与“面子”
——对近代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面子问题”之省思
李富强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通过对近代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面子问题”之省思,可知批判者们没有真正辨析“耻”“脸”与“面子”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异。儒家的“耻”观念是“脸”与“面子”的真正内核,“脸”是面对自我的道德性的耻,它是以耻为标识的人格尊严的“形象”。而“面子”则是面对他者的社会性的耻,它是作为人格尊严之形象的“脸”在他者心里留下的特定心理地位。“面子”与“礼”的形式主义有密切关联,“礼”本来是要为社会群体提供一套普遍的行为规范,但事实上却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面子”的形式化是对人格尊严的弃绝和道德价值的颠覆。儒家文化中的耻感取向在培养道德人格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育崇德知耻的国民性格。
[关键词] 国民性批判;耻;脸;面子
作为一种民族性难题或缺陷的“面子问题”真正进入中国学者、文学家的视野,始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鲁迅、林语堂等人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有很强的“面子意识”,这种落后的、鄙薄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围绕着“面子”展开的问难成为国民性批判的焦点。“耻”“脸”与“面子”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观念,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耻”多出现于经书典籍之中,是儒家的“八德”之一,“脸”与“面子”则是较为通俗流行的日常用语,“不要脸”“丢脸”“要面子”等俗语是我们现在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脸”与“面子”是社会学家研究的经典议题,胡先缙、黄光国、翟学伟等社会学家对中国人的脸面观都做过深入研究① 参见黄光国,胡先缙主编:《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用西方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去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社会性特征,未能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视域对“脸”与“面子”背后的儒家“耻”观念做哲学分析。前辈学人金耀基肯定了“面子”与儒家传统中“耻”观念有内在关联,探讨了“面子”背后的儒家文化逻辑,他论述的重点在于辨析Shame Culture与Guilt Culture的异同以及对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分析。他在结论中肯定了社会性的“面子工夫”也可以成为推动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但忽视了“面子”的形式化所导致的虚伪与去道德化等更为严重的消极后果。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认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汉语中脸面概念和表述之无可争议的思想背景和基础”② 成中英:《脸面观念及其儒学根源》,欧阳晓明,翟学伟译,见翟学伟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他从“礼”“德”“名”“实”等儒家哲学的传统观念探究了脸面观的儒学根源,将“脸”与“面子”的关系,比喻为“实”与“名”的关系,从一个固有的“实”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名”,“面子”是社会规范之“礼”的延伸,“脸”与“面子”是儒家体系中“德”观念的社会对应物。笔者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耻”观念是“脸”与“面子”的真正内核,“脸”是面对自我的道德性的耻,内观自省的耻。“面子”则是面对他者的社会性的耻,外务整饬的耻,用荀子的话说,“丢脸”是“义辱”,“丢面子”是“势辱”。“脸”与“面子”的分离是“面子工夫”成为社会交往技术的前提,“面子”的形式化是对人格尊严的弃绝和道德价值的颠覆。面对羞耻感不断衰减的现代社会,重塑积极健康的民族性格,应该重视儒家传统中的“耻”观念,培养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崇德知耻意识。
一、国民性批判中的“面子问题”
“讲面子”“要面子”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其中的褒贬色彩在具体情境中有所差异,但将“面子”当作国民性批判的靶子则始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所谓国民性意指一个民族在自身文化传统塑造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将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言述焦点或研究风尚可以说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清末民初的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向的转型时代,与西方先进文明的接触,使得很多有识之士在自卑心理的刺激下,转向对旧传统旧文化的猛烈批判,而其中的国民性批判尤为突出。国民性是一种稳定的民族性格,具有地方性、区域性的特征,长期生活于本区域和文化传统之下的人对自身的国民性缺乏明确的认知,有一种当局者迷的意思。一旦接触到异质文明及浸润在异质文明下成长的外来人士,在相互比较中,本土的国民性格就会凸显出来。最早对近代中国国民性中的面子问题进行描述的是一位叫史密斯的西方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之久,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他在1894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人性格的书《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又译为《支那人气质》《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的特征》等,这本书应该是研究中国国民性最早的著作。史密斯在该书第一章就提到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说:“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参照戏剧化的样式,中国人就会很有面子。当他们全心入戏时,如果你不理他们,轻视他们,或者喝倒彩,他们就会觉得‘丢面子’。‘面子’犹如一把钥匙,一旦人们正确理解了它所包含的意义,就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的性格之锁。”① 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鹤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史密斯认为,“面子”是理解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窗口,它在中国人的日常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他提醒读者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族群,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演戏本能,所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参照戏剧化的方式进行的,一旦破坏了戏剧化的方式,就会造成“丢面子”的后果。面子问题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表现在它能左右社会正义是否真的得到了实现,中国人喜欢用“面子”的比例去分配社会正义,尤其在诉讼裁决中,由于要顾全各个方面的“面子”,使得很多诉讼裁决变成了不分胜负的拉锯游戏,到最后便会不了了之。
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性格的分析,影响了鲁迅、林语堂、潘光旦等人对中国人民族性格或国民性的看法。鲁迅可以说是对中国国民性批判最严厉的文人,而他用来批判国民性的靶子就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早在1923年,鲁迅就在日文著作中批判了中国人重“面子”的陋习,他发现中国人身上有一种日本人无法理解的民族性格,这就是所谓“面子”,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仅次于生命。“爱面子”是中国人的普遍特征,他在《“面子”和“门钱”》一文中说:“这并不仅仅限于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们,就是西崽、车夫和目不识丁的一帮子人们,一论到‘面子’,就会用几近于迷信的强大力量加以维护。”② 鲁迅:《“面子”和“门钱”》,见《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到史密斯的著作,他很认同书中关于“面子”的看法,他说:“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③ 鲁迅:《马上支日记》,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鲁迅进而痛斥一些国粹家、道德家,说这些人提倡的保存国故、振兴道德、维持公理、整顿学风的口号全是演戏的假把戏。鲁迅又在《说“面子”》一文中谈到:“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④ 鲁迅:《说“面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在鲁迅看来,“面子”和“脸”有本质区别,机械性的“要面子”和不顾人格尊严的“不要脸”容易混淆,“今之君子”顾全“面子”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不要脸”行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将“面子”“命运”和“恩典”视为统治中国的三大女神,“面子”抽象而不可捉摸,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的地方,中国人的社会交往都以它为依据。而且“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①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迟迟不能实现民主法治,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面子意识阻碍了这些进步观念的落地生根。潘光旦同样认为中国人是富有戏剧本能的一个民族,中国人遇到事情时,常将自己视为一出折子戏里的角色,然后去演完这个角色。这一类日常生活中喜欢扮演的行为就是“要面子”的问题,假若不会扮演或扮演时受到阻挠就会觉得“没有面子”或“丢脸”②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短暂访问过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谈到过近代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③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在罗素看来,“面子”是中国人的伦理准则,“要面子”是相互尊重的需要,他将“面子”视为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加以褒扬。因为罗素在中国访问的时间有限,他对中国国民性中面子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浅薄的,没有深刻认识到“面子”的形式化所具有的虚伪性和非道德倾向。王造时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僵化的礼教之恪守是国人“爱面子”的主要成因,未能对礼教做出损益的变革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使得原本富有精神内涵的礼教只剩空壳,变成了虚伪的繁文缛节,虚伪的表面是“面子”,“因为中国人最虚伪,所以最讲面子,不讲实际。”④ 王造时:《国民心理》,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庄泽宣对王造时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与发挥,他也认为所谓礼教都是文饰的东西,顾全“面子”的思想支配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顾全“面子”,难免沦为虚伪的矫饰,成为假道学的鬼把戏。而且更容易引起人的猜疑心理,造成中国人缺乏合作与团结的精神,面对艰难的时局,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⑤ 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第226页。 。
其实,面子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它是中国人经常议论的重要问题,任何在中国有社会生活体验的人,都会意识到中国人对“面子”的敏感性。不了解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以及背后的面子工夫,也很难对中国人的心理性格与社会行为有真切的认知。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学者和文学家对面子问题的批判,透显了国民性格中有缺陷的一面,即中国人的虚伪、假道学、不切实际,他们认为落后的、鄙薄的“面子”观念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此同时,这些批判者较少去探究国人在社会互动中重视“面子”的传统文化根源,忽视了中国人也有“要脸”和“知耻”的性格特征,没有真正辨析“耻”“脸”与“面子”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异。
二、“脸”与“面子”:道德性的耻与社会性的耻
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对中国人的“面子”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说:“自我由以同他人、社会相拘着的东西,不过是被给予社会关系中的某种地位。这个地位就是‘面子’。因此,中国人的社会精神作用是作为社会关系中自我的地位、‘面子’出现的。对于中国人,社会价值是‘面子’,其社会归于‘面子’方向。”④ 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的精神结构》,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第209-210页。 “面子”的实质就是社会关系中自我的地位、身份或声望。但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在“面子”之外,对“脸”的格外重视。费正清就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他在论述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时,认为中国人所谓个人尊严的问题,都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的。“丢面子”来自个体行为的失检与不当,使别人瞧不起自己。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谓“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⑤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人的价值或每个人固有的道德品质通常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脸”,它是具有内在约束力的,是道德性的耻,而非费正清所谓的需要从外界获得的“面子”。
“脸”与“面子”可谓是“耻”的两个向度,两者植根于“耻”,有重叠的时候,令一个人“丢脸”的事情也常常使其“丢面子”,反之亦然。但区分两者的本质不同更为重要,尤其是“面子”对“脸”的背离,会导致道德价值的颠覆,以至于出现“要面子”而“不要脸”的非道德化取向,这也是近代以来鲁迅等人对国民性中存在的面子问题持严厉批判态度的根本原因。“面子”的形式化是对人格尊严的弃绝和道德价值的颠覆,其中的发生机制就在于对“礼”的形式化恪守。梁漱溟在总结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指出一条是“爱讲礼貌”,他说:“此一面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礼”是古代中国社会伦理规范的总称,原始儒家主张礼乐教化,“克己复礼”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际和谐。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礼”的形式化、精细化与复杂化使其越来越成为束缚人性的僵化教条,究其原因在于“礼”失去了它懒以生存的实质内容,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作为实质性内容的“仁”为依托,“礼”就变成了充斥在人际交往中的繁文缛节、虚情客套的假把戏。这些假把戏就是工夫论层面的面子工夫,一旦这种面子工夫成为社会交往技术,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严复谴责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的病态当中。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德治和礼治的社会,而非法治与刑治的社会,德治是抽象的形式,礼治是具体的内容,通过复杂精细的礼制、礼仪、礼节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治主义的社会是由崇德知耻的个体构成的和谐社会,“耻”在儒家伦理规范中具有核心地位。正如孟子所言:“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孟子•公孙丑上》)羞耻感是人对自我之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道德谴责,以之为耻则必然要行仁、为仁。金耀基肯定地认为:“儒家的道德规范——礼——之体现,可以说都有赖于‘耻’感的发挥。”③ 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见《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制礼”的目的本来是要为社会群体提供一套普遍的行为规范,以仪式化的程序保障行为符合人性对伦理道德的内在诉求,但事实上却造成了形式主义,中国人重“面子”与“礼”的形式主义有密切关联。故而,没有道德羞耻感的“爱讲礼貌”只剩下“礼”的空壳,便会导致流于形式的、虚假的“爱面子”。
综上所述,“脸”与“面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儒家的“耻”观念是“脸”与“面子”的真正内核。一个“不要脸”或“不要面子”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羞耻感的人,“要脸”“要面子”是一个人处于知耻状态的表征。“脸”是面对自我的道德性的耻、内观自省的耻,它是以耻为标识的人格尊严的“形象”,“丢脸”意味着个体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不足,因自身的道德瑕疵而丧失人格尊严和社会的尊敬。“面子”则是面对他者的社会性的耻、外务整饬的耻,亦可以说是在社会互动的人际关系中,作为人格尊严之形象的“脸”在他者心里留下的特定印象,“丢面子”则意味着他者对个体的评价背离了其原本所期许的和自身地位、身份及声誉相匹配的价值承诺。用荀子的话说,“丢脸”是“义辱”,“丢面子”是“势辱”④ 荀子曰:“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荀子•正论》)荀子将耻辱区分为“义辱”与“势辱”,以“义辱”为标识的耻辱产生于对完善的内在道德人格的侵害,这种耻辱可以通过修身得到清除。“势辱”则是外在的、社会性的不可抗力加之于个人的伤害,没有办法通过个人修养得到清除。 。“脸”与“面子”的分离是面子工夫成为社会交往技术的前提,“面子”的形式化是对人格尊严的弃绝和道德价值的颠覆。作为国民性的“面子问题”需要批判,但也应该看到“面子”背后的“耻”观念,特别是由儒家文化所塑造的“耻感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就国民性格的改造而言,儒家“耻感文化”是极为有益的传统资源。
“我想创造出在拳台上和拳手对打的感觉,使我的这张照片就像某个电影里的截图那样,我想要表现一种戏剧的冲突感。”
中外学者都对“脸”与“面子”下过定义,由于两者本身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所以关于它们的定义总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翟学伟注意到“脸”与“面子”本身具有的丰富内涵和错综复杂的价值判断、文化情境以及社会关系,是导致人们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界定的主要原因。笔者试图引入另一个与“脸”和“面子”具有内在关联的概念——“耻”——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脸”与“面子”的内涵,“脸”与“面子”都是较为现代化的日常用语,最早只具有自然的身体属性,其附加的道德性与社会性意涵起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与它们具有内在关联的“耻”观念则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在高文典册中频繁出现。儒家的“耻”观念兼具道德性与社会性意涵,可以首先通过对“耻”的分析来引出我们关于“脸”与“面子”的探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一个人“不要脸”或“丢脸”,其实这是一个严厉的道德谴责用词,等于说这个人是个“无耻”或道德败坏的人,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即没有人格尊严的人。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说一个人“爱面子”或“不体面”,“面子”总是意指某种表层的、可用来整饬的、去做给别人看的形式化的东西,目的是维护与我们的身份相符合的某种个体形象。胡先缙是第一个将“脸”与“面子”严格区分开来的学者,她在《中国人的面子观》中认为,所谓“面子”在中国人生活的语境中主要意指一种声誉、声望或名誉,它是借由个人的成功以及社会赞誉而获得并累积起来的社会形象,这一社会形象离不开外在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所谓“脸”则是社会团体对个体道德完满者或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者所表达的一种由内而发的尊敬,因为这种人在任何艰难的处境下,都不会做出违背个人良知的事情,恪守内心的道德律,保持道德上的无瑕疵。所以,胡先缙强调与“面子”相比,“脸”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能力”③ 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光国,胡先缙主编《: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脸”更多地指向我们如何“是”一个人,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真诚地面对自我,并在社会性的人际关系里保持自我人格尊严的完整性。“面子”则指向我们如何“做”一个人,确切地说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来确保我们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完美呈现,它暗示了这样一条规则,即在社会互动中的他者对我们的评价远比我们对自身的评价更为重要,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究的“面子”与“门面”。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过1”和“过2”主要是附着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结束和完成”和“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过”表“经过”“通过”义时与动词组合是“过”语法化的关键。以下是一些“动词+过”的情况,如:
据《说文解字•心部》记载:“恥,辱也,从心,耳声。”又据《六书总要》记载:“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恥”字左边是“耳”,右边是“心”。“耳”代表官能上的生理感受,不具有反思能力,这是动物也具备的官能。“心”则代表道德内省、反思等理性能力,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正在于人有能思的“心”。犯了过错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行为失当就会有面部上赤红的生理反应。从字源上即可看出,“耻”由“耳”入“心”,是一种人类所独具的道德意识,标识着心灵的某种品格状态。羞耻感产生的精神机制在于人因寻求人格尊严而在自我意识中产生的价值冲突,它产生的前提就在于较高价值与较低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舍勒说:“在人的精神个体的意义和要求与人的身体需求之间,人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属于羞感产生的基本条件。”①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和羞感》,罗悌伦,林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羞耻感揭示了处于动物性与神圣性之间的人,应该如何有尊严地生存这一存在性焦虑,并且这一存在性焦虑的核心是道德上的善与恶,所以说羞耻感是人类“道德的第一根基”② 张任之《:舍勒的羞感现象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25页。 。舍勒的关于羞耻的现象学分析,有其自身的基督教神学背景,但他关于羞耻的看法,具有跨越中西文化鸿沟的普遍人性根据。“耻”的本质是人因确保其人格尊严而在自我意识中产生的一种价值冲突,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性感受,这种自我保护意识显然与人的自我完整性或道德完善性有内在关联,任何有损于个体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可能触发羞耻感。故而,羞耻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感受,这是一种道德性的耻,它是先天而又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也可以说是内生的。还有一种社会性的耻,它是社会习俗塑造的结果,它是后天的,也可以说是外塑的。据人类学家观察,长期赤裸上身生活在原始部落的黑种女人,不穿衣服的时候,她们并不会觉得羞耻。但当人类学家让她们穿上衣服时,她们反而感到羞耻,因为这违反了部落的日常生活习惯,会对她们的身份、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这种社会性的耻在个体道德层面基本上是中性的,虽然与侵害人格尊严之道德性的耻有所关涉,但又有本质区别,它是社会教化的产物,有很强的身份属性,一旦违背约定的共同体价值就可能遭受社会舆论制裁,使个人在内心里产生一种丧失社会尊重的羞耻感。道德性的耻与社会性的耻,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脸”与“面子”,就其内涵而言,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运用文化模式理论率先提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说,将日本文化归类为耻感文化,西方文化归类为罪感文化。在她看来,羞耻感在产生遵循伦理准则的道德行为的动力方面是较弱的,羞耻感仅仅是一种他律的道德意识,不应该纳入道德体系。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这种化约论式归类,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赞同的同时,亦受到很多批评。如日本汉学家森三树三郎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与日本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中的耻感意识更强,耻感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中国。第二,耻感意识是内在的道德意识,不是外在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评价的产物。第三,耻感意识有调节社会秩序的伦理作用,这是其作为社会意识的价值,罪感意识则是基于信仰的宗教意识,实现灵魂救赎是其重要内容① 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王顺洪编译《,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2期,第118-123页。 。台湾社会学家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展开论述,社会、个人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他通过对儒家经典“四书”中耻观念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社会是“耻感社会”;中国人的人格是“耻感取向人格”;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或者至少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耻感”占据优势的文化② 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见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14页。 。虽然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都有耻感取向,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以关系为本位是耻感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社会互动更加容易受到具体情境下“面子意识”的左右,而日本人的社会互动则偏向于以“义理”为导向的社会规则。所以,鲁迅留日期间得出的一个社会经验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爱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讲究按规则办事。“耻”是儒家“八德”之一,耻观念在儒家伦理学中有特殊的位置。就“耻”这一具体德目而言,它的基本内涵是不断丰富与完善的,通过对儒家思想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儒家学派有关羞耻之心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从孔子“行己有耻”(《论语•子路》)的道德自律意识,到孟子“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的人性论建构,再到周敦颐“必有耻,则可教”③ 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 的社会教化观,明代吕坤“五刑不如一耻”④ 吕坤《:呻吟语》,见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38页。 的惩戒教育观,一直到康有为“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⑤ 康有为《:孟子微》,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的社会风尚建设。可见,从先秦原始儒家到清末的改良派儒家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与社会功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耻感意识,培养个体知耻的道德人格是这种耻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时代下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主要包括项目实施的标准化设计、相关构配件的科学生产、现代物流企业的运输配送、装备式施工等等,共同构建成了全产业链。基于此,为了有效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应当对整个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并且将创新能力逐渐渗透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中,有效搭建起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在项目实施的前期,建筑企业可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的论证,根据国家及相似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起相应的技术标准,同时采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对整个产业链的结构进行整合优化,逐渐实现节点之间的有效连接和建筑的抗震能力等等。
三、重塑“知耻”的国民性格
综上所述,诺舒子宫内膜去除系统可有效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其手术疗效与宫腔镜子宫内膜电切术相当,但手术更为微创,对患者卵巢功能无影响,值得临床推广。
儒家传统认为羞耻感或羞耻心是人的类本质规定性,它是先天的道德本能,人生而具有的羞耻心是道德意识的重要来源,保持个体的羞耻心或羞耻感,在培养道德人格时具有重要意义。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它是人的良知、良能将要呈现出来时的萌芽状态或初始状态,“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它是人天生的道德本能,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孟子、陆九渊、王阳明代表儒家的心学传统,王氏门人有个小故事,即讲为何是羞耻心点出了良知是人的道德本能。故事大概是说,王氏门人夜间捉住一个盗贼,他对盗贼大讲良知之学,此盗贼不以为然。因为天气过热,于是王氏门人让盗贼脱掉裤子,盗贼面露羞涩,认为这样不太雅观,羞耻感油然而生,王氏门人告诉盗贼这个羞耻感就是他有良知的证明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羞恶之心”作为人的本心、良知、良能,是一种主动的道德情感,只要“扩而充之”,就可以提示个体主动地去完善自我的道德人格。
羞耻心或羞耻感作为一种先天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标识着人是有良知的道德存在,这不仅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其普遍性在现代哲学或现代思想语境中得到了相应的呼应。如前文提到的现象学家舍勒曾提出“羞与羞感的现象学”,将人类独有的羞耻现象纳入现象学伦理学情感分析的领域⑦ 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或价值伦理学是对康德伦理学中情感与理性二分模式的一种突破,在康德伦理学中道德主体是先天的实践理性,这一立法原则缺乏将道德法则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动力,而作为道德动机的情感则属于经验的领域,因为缺乏先验自由而不能自作主宰,如此一来,道德责任的问题便落空了。舍勒将道德情感提到道德主体的层面,提出情感先天性的价值伦理学,这与儒家伦理学有相似之处,就道德主体而言,儒家伦理学中“本心”“良知”不仅是一个理性主体,而且也是呈现为情感性的“四端之情”。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9页;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38页。 。他通过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现,羞耻感是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标识着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位置。在羞耻感起源的问题上,舍勒明确反对将羞耻感的本质视为社会化、习俗化结果的后天说,它不是一种仅凭后天教化而养成的习惯,我们感到羞耻的内容以及羞耻的表达仪式可以经由后天的教化而形成,但羞耻感本身则处在人类本性的明暗交接处,是人类经验结构中的本质要素。舍勒将羞耻感区分为身体羞感和灵魂羞感,前者源于指向生命价值的生命感受与指向感性价值的本能冲动这两种价值意识的冲突,后者源于指向精神价值的精神感受与指向生命价值的生命感受这两种价值意识的冲突。以性羞感为核心的身体羞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其先天性尤其在女性的性羞涩这一自然本能中得到体现。通过道德谱系学的考察,他进而认为性道德是一切道德的自然根基,性道德是对引起羞耻感的对象和内容的概念化,它是人类良知和善恶知识起源的最重要源泉。布罗涅借鉴了舍勒的看法,明确指出羞耻或廉耻的第一特性是其作为人类道德的自然性① 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李玉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这种羞耻感类似于孟子的良知,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判断能力,倪梁康将其视之为“道德潜能”② 倪梁康认为孟子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人类道德意识来源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前者是一种先天的道德实能,后者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潜能,它们是在排除了一切社会化、习俗化的道德替代品之后仍然植根于人类自然道德本性中的残余物,因而构成一切道德学说的基础。参见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作为一种潜在的道德本能,其存在形式是先天的,但需要有意识地去开发它,这也是后天的伦理教育或道德说教之所以具有有效性和必要性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现代宗教哲学的奠基人索洛维约夫将羞耻、怜悯和虔敬三种基本情感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永恒根基,这些最基本的道德情感或原始自然道德把人对低于自身、等于自身以及高于自身的生物应该具有的道德关系囊括无遗了。索洛维约夫进而认为:“最高的道德学说只能是上述人类道德原始材料全面而正确的发展。”③ 索洛维约夫《:道德的原始材料》,董友译,见王岳川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就其中的羞耻感而言,人羞耻于物质本性对自己的奴役,承认自身的内在独立性和崇高身价,因此,人要占有物质本性而不是被物质本性所占有。羞耻感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性感受,它所捍卫的不是主体的物质生活,而是他的崇高人格,或者说是在证明其人格尊严尚保存在由羞耻感所标识的道德本性中。如果说良心的原始根基是羞耻,那么在没有羞耻感的动物身上寻找类似于人类生活中比较复杂的羞耻现象则是徒劳的。安斯康姆批评西方现代道德哲学的失败在于它缺乏一种必要的道德心理学,如果我们在道德心理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以及道德上对“应当”“规则”的道德意识概念就可以抛弃了,因为这些都是道德心理观念的残留之物或派生之物。道德心理学主要研究与人的道德动机相关的某些心理活动,或者说,在道德语境中分析与追踪人的心灵状态。所有与人类的“心”相关的、并且具有伦理道德意蕴的、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起到导向作用的心理与情感因素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西方学者的道德心理学研究主要围绕意愿与自由、意志自由与必然性而展开,中国学者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对象也是基于一些基本的核心观念,如仁、义、忠、恕、耻、信,等等。羞耻感作为一种先天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尊严具有内在联系,它先于一切经验而植根于人性之内。罗尔斯在谈到如何定义羞耻时说:“现在我们可以把羞耻规定为当某人经受了对于他的自尊的一种伤害或对于他的自尊的一次打击时所产生的那种情感。”④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羞耻感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自身的人格尊严——这种特殊的善或德性——的贬低而产生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
胡宏关于“心体情用”和“心兼体用”的内容,与王阳明的“心兼体用”在理论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相同。然而,胡宏心性论中的“心”必须与“性”连接起来且需要以“性”为基本才能够形成本心。由此可见,“心”和“性”并不为一,而且体用关系和尚未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关系时“性”和“心”之间存在主要关系。站在思想发展历史的角度看,从“性体心用”到“心性为一”的转变是完全科学合理的。
总而言之,我们从儒家传统和现代思想语境这两个维度探究羞耻感的本质,可知羞耻感是道德性的,是先天的,良知是人的道德本能,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羞耻是一种重要的德性,它是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观念之一。羞耻感本身是一种具有转回自我意识的“良知提醒装置”,它关涉着人的整个存在,在羞耻体验中,个体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他者以及公共价值对我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对他者和公共价值意味着什么。应当承认羞耻感是值得提倡的积极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它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认为现代道德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急剧加速,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羞耻感的薄弱与衰退往往意味着人的道德力量的衰减,这是人的类型的退化,退化到与禽兽无异时,人便不复成其为人,所以舍勒强调:“在近代史上,羞感的明显衰减绝不像人们肤浅断言的那样,是更高级和上升的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种族退化的一种确凿的心灵标志。”⑤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257页。 由于现代社会中个体主义自我价值的过度膨胀,羞耻感的衰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羞耻感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减削弱了个体自身从道德上对其自身价值应做的反省,重建崭新的社会伦理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面对羞耻感不断衰减的现代社会,矫治与解决中国人过分重视“面子”的民族性难题,重塑积极健康的国民性格,应该重视儒家传统中的“耻”观念,因为儒家文化中的耻感取向在培养个体道德人格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有助于塑造崇德知耻的国民性格。
“Shame”,“Face”and“Mianzi”i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nese:A Reflection of the“Mianzi Problem”in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it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LI Fu-qia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A reflection of the“mianzi problem”in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it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reveals that the critics do not really distinguish the inner relationship and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shame”,“face”and“mianzi”.The Confucian concept of“shame”is the real core of“face”and“mianzi”.“Face”is the moral shame of facing the self,which is the“image”of the human dignity with shame as a symbol.However,“mianzi”is the social shame of facing the other,which is the specific psychological status left in the other’s heart by“face”as the image of human dignity.“Mianzi”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lism of“ritual”.“Ritual”i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provide a common set of behavioral norms for social groups,but inclined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formalism whereas the formalization of“mianzi”is the rejec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subversion of moral values.The orientation for the sense of shame in Confucian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moral personality,which helps to cultivat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respect for morality and awareness of shame.
Key words: criticism of nationality;shame;face;mianzi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1004-1710(2019)05-0173-08
[收稿日期] 2019-04-04
[作者简介] 李富强(1987-),男,河南周口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责任编辑:张文光]
标签:国民性批判论文; 耻论文; 脸论文; 面子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