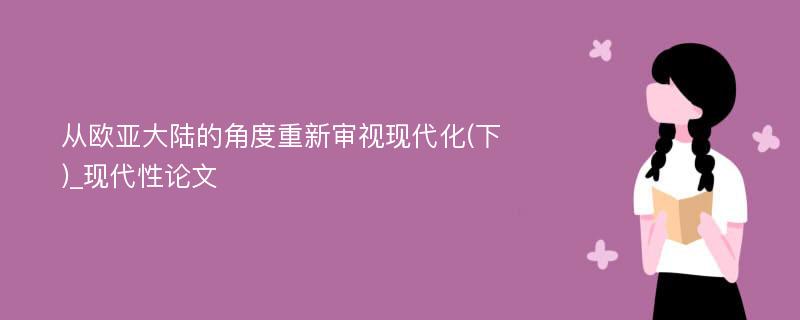
以欧亚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性(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大陆视角中的明朝
中国在何时开始了现代性?对于这个问题的流行回答一直是19世纪同现代性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相遇,这一相遇亦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抵抗、文化转型和革命的起点。在各种流行的讨论范式中,以及在中美学术界,这都是一种想当然的历史分期。如果我们把从欧美现代性模式中提炼现代化标准的那种实体性现代性定义视为当然,那么就可能像某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臭名昭著地(然而愚蠢地)宣称的那样①,甚至做出下述主张:中国绝不是现代的,即便在今天,它也没有成功地通过现代性考试。
无须否定欧美在发明现代性——在过去2个世纪里,这创造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过程的历史作用,然而同样清楚的是,无论怎样设计这种现代性的实体性定义,它都不足以承担测量我们习惯上称为现代世界中的变迁的尺度。特别是在解释18世纪晚期以来欧美现代性在全球的统治和霸权所压制的那些别样的历史轨迹时,它抹杀的东西比它解释得还要多。如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性讨论就需要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的重构以及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在其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意义的位置:中国在资本主义出现中的位置,中国在欧亚(以及最终全球)中的位置,后者不可还原成资本主义现代性出现的空间语境。与上述讨论的某些学者相反(不是指像加文·孟席斯那样学者,他们的还原论只不过歪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使它们变得肤浅),并没有人否定下列这一点:欧洲人在与资本主义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的产生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这种全球化本身只是由于地方性的帝国经济的存在才得以可能,作为当代全球性要素的“世界经济”诱使欧洲的扩张,使全球化力量活跃起来,那些力量在我们时代的起点上便存在着。这便是最近的学者放弃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论的结论。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推动其他地区社会转型的方式,诸如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时期日本、中国明朝(1368-1644年)、莫卧儿王朝(1526-1858年)、奥特曼帝国(1300-1923年)、萨非帝国(1501-1723年),以及其他一系列地方社会转型,这都是一些高度地方化的城市聚集带,它们横跨欧亚、亚洲和美洲,改变着既存的并创造新的政治体系。那些变化可能是与“早期现代”欧洲同时产生的社会形态的结果,而不是它们自己历史轨迹造成的②。如果欧洲人在这些发展方面拥有优势,那么正是粗心大意的欧洲人注定通过它们在这些社会之是的中介活动而实现这些发展③。不过,在此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描述这些社会,它们作为同一种创造现代欧洲的力量的产物,而不是表面上与领先于它们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尽管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获得了胜利,它们也没有被迫进入同那种胜利联系在一起的非线性历史轨迹?在我看来,不承认它们的现代性,便是陷入同一种错误,在现代化话语中,因为它们是“落后的”,或换句话来说,不同的,那种错误便否认不同社会的同时代性。“早期现代”是一种可能性,不过,它受欧洲现代性目的论之困。充满了其他可能性的欧亚现代性可以提供最令人满意的其他选择。在我看来,它对改变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是有意义的,那种改变使我们更好地处理反常的论据而不忽视它们以保护我们的概念化!从这一视角看来,它对谈论欧亚现代性也是有意义的,那种现代性肯定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不过后者当前可能正在向分享了许多欧亚现代性特点的全球现代性让步,只是采取了那种形式,它们是由欧美霸权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来重组的。
最令人满意的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实际上是在这些时空特点中进行的:源自多种横跨欧亚的世界体系的单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18世纪以来,最终在欧洲成为中心,从那时起,整个世界被带入这种世界体系之中④。虽然自人类的起源在非洲-欧亚之间便存在相互作用,但我认为,人们没有能够观察到,正是蒙古的入侵创造了我们所知的欧亚,也正是从蒙古的入侵开始,才有可能把中国(多个帝国之一,如莫卧儿、萨非和奥特曼帝国)和欧洲的出现看作是我们所称的现代时期。
然而,横跨欧亚大陆的跨地区相互作用在一个新欧亚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不同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便是这些相互作用在欧洲语境中的产物。看起来情况是这样的:跨越非-欧亚范围以及跨洋的“新”大陆,每一个地方加强了交流活动,每一个地方的独立“企业家”——如地主、商人和劳动者——都不断增加。在亚洲不同的地方,后果因环境而异。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现代性,这很快导致欧洲和美国对世界的统治。
在东亚,同一时期见证了帝国的巩固——如我们所见,“中国”在明清时期的形成。如郑和下西洋表明的那样,明初是开放的,而在这之后则是对边疆的更大控制,以回应沿海和内地同时加强的压力(这或许解释了整个明朝的“战备扩张”)。
然而,世界的“停止”并没有阻止贯穿东亚世界体系的大量的相互作用,包括文化上的交流。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定中亚相互作用在东亚形成过程是重要的,那么明清便对这个地区(蒙古、俄国和中亚其他集团)具有更大的兴趣,而不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的陌生人⑤。不过,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明显地出现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晚明观察到的“资本主义萌芽”之中(如果看不见的话)。把“中国”视为一个发展单位的史学倾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批评者都一回事)以多种方式存在于对这些发展的完整评估中。问题与一种关于明清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国家(以及明朝中期的北京)中心视野混杂在一起,正是在中国的南部和中东部(江南地区),这些关系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最为显著。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们指出,正是伴随着“明朝中期以后的中央控制弱化”,社会经济表现出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贡赋交换使得海上私人贸易像鬼火一样繁荣起来,这导致海上经济和社会组织在传统体系内部萌发⑥。转向对北部蒙古问题的重视可能对这个结果产生了更一步的影响。
明朝和清朝早期的中国也许同东亚以外的外部世界并没有密集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改变经由南海的商业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那种商业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美洲的银子和粮食,这对于它的金融结构和人口动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商业关系也向东南亚(包括菲列宾)的海外移民。从明朝中期起,海外中国人在中国经济(以及东南亚经济)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大陆与海外的联系纽带⑦。欧洲的触角伸到中国沿海,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防卫性闭关,特别是欧洲人的活动从融入东亚空间转向根据欧洲需求来改变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世界体系不再只是欧亚的,而且也包括了美国(通过菲列宾)。然而,明-清控制边疆的努力既阻止了商品流动,又阻碍了向东南亚的移民和中国人口的扩大。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动的转型无疑为欧洲和中国的同时扩张提供了背景,虽然关注下列差异同样重要:两种扩张都是正在浮现中的全球世界体系的产物,只不过其中一种得到了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持,而另一种则是防御性扩张,在任何尺度上,丝毫都不能同由资本主义支持的帝国主义结果相比⑧。
关于明清历史的争论有很大。然而,在下述这点上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明朝建立在蒙古入侵基础上,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标识出新的出发点,从16世纪中期起,中华帝国便呈现出欧亚社会广泛共享的那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⑨。正是在明朝,帝国中心巩固了对已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那些地区的控制(大多数清代的“边远”地区都已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帝国政治体系变成更加稳定,由于检察体系制度,国家和社会空前地一体化了,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和地方精英合作建立了控制社会关系的规则。作为社会权力的基础,血缘关系体系也在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控制中服务于国家利益⑩。
政治转型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齐头并进。仍然在明朝早期占优势地位的庄园经济在明末清初逐步让位于小农经济(11)。全帝国范围的城市网络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都反映了社会商业化程度得到提高,这使某些学者认为“小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12)。实际上,大规模工业已经存在,这些工业的规模足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和陶瓷和丝绸业的出口经济。也有一些垄断商人,例如作为国家垄断私人代理的盐商(13)。不过,最重要的产业仍然是小型的家庭手工业,而“小资本主义”都与国家控制的“贡赋”经济勾结在一起。当明朝政治逐步采纳现金支付税收,从而改变了直到明朝中期都主要采用的瑶役支付方式,贡赋经济日益增加了货币的供给。
国家无疑并不干预“小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通过诸如公所和会馆制度极大地保持了自主性,那些制度的形成和扩散伴随着社会的商业化和商人的流动(14)。已经出现的商人阶级绝不会获得这样大的自主性,成为一个挑战贡赋经济或者要求政治权力的阶级。更恰当地说,这些结构转型造成了商人的乡绅化和乡绅的商人化,它所产生的政治阶级只是一种集政治、商业、文化和资本于一体的新的精英。新的城市文化,以及商人在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之中的友好变革充分表明了其优点(15)。这些新城市文化的文献(在最广泛意义上,包括流行的宗教宣传册和百科全书)从明朝开始随着出版业的商业化而广泛地传播——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海外华人社团以及日本和朝鲜(16)。尽管明朝的学校和图书馆都不是新的,但木版印刷的广泛使用和出版业的商业化却在明朝中期以后导致(无疑也从中获得好处)学校和图书馆的空前扩大(17)。在文化和政治上,明朝都表现为帝国形态,需要把它同那些融入其制度的各种各样要素的谱系区别开来。不只是欧洲中心的历史学,而且中国历史学和流行意识,都一直对明清社会的“现代性”视而不见,它们只是坚守一种把这种形式的特点投射遥远过去的五千年文明的到陈词滥调,忽视了塑造明朝的那种新的历史情境,那种情境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重大的历史遗产,它们只是作为中华帝国历史中相当空前的复杂总体性的组成部分开始形成。
这些发展暂时被明清转换所阻碍,这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责备清朝不能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确实,18世纪晚期,清朝社会显露出主要由人口增长又加上资源压力而引起的长期危机征兆,但是,一旦在康熙年间清朝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654-1722),明代形成的那种社会发展便得到持续(18)。18世纪中期或许很好地代表了帝国历史的政治远地点,当它扩张到北方、东北、东南以及台湾,其边界达到了它今天主张的那些地方(19)。如我在上文主张的,需要把这种扩张动态与由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的革命性帝国动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清朝扩张暗示着,当英国人在18世纪晚期第一次侵略清朝——这预示着接下来在19世纪发生的一切,他们遭遇的是一个绝不会成帝国主义猎物的国家。
此外,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发展,并不因此暗示中国经济不发展,或者停滞了;而只是暗示着它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和乔万尼·阿锐基主张,直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反市场的”大商业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突出特点,它出现于16世纪的欧洲,并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巩固了其全球霸权(20)。中国社会从明朝以来的商业化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一个特点是工业和农业中的小规模生产。用理查德·冯·戈劳恩的话来说,“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勤劳革命’,这种革命并非与用以解释当代日本和欧洲的假设并非不同,首先是人口的扩大,紧接着是劳动的密集化以及乡村非农业生产的增长,这又伴随着地方和地区市场中的水平交换的发展,导致经济的专业化、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及过度的人口增长”(21)。
我认为,这些长期发展为理解18-19世纪的遭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大不列颠与清朝从18世纪以来的对抗并不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商业驱动下与一个封闭的传统的——如马克思著名评论那样,“停滞着,背逆时间”——帝国之间的遭遇,而是已经具有300年历史的关系顶点,它预示着现代性展开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将由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推动,它最终会要求欧洲(以及美国)对全球的霸权。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帝国主义由工业革命而加强了,它能够迫使清朝向世界体系开放。在19世纪末,东亚世界体系已经融入全球世界体系,走完了至少已经进行了400年的历程。
从这一角度看,20世纪的现代化与革命似乎便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具有自身地方特殊性的内部社会差异和冲突,离开明清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点,不可能解释这些社会差异和冲突。同样,民族的建立也是限制和控制这些新的力量以及抵挡帝国主义的努力的结果之一(需要我们记住,民族主义被普遍化为欧洲扩张的政治形式之一,其后果之一)。社会主义将实现资产阶级不可能在依附性发展条件下实现的民族整合目标,这一承诺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合法性。不过,社会主义也被另一种欲望激励着,即探索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避开和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能把社会主义还原为民族主义。如果它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它将提出一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即把世界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
结束语
上述论述似乎只是重新命名了我们已经早以熟悉的东西,即使我们所知的东西已经因为受全球刺激的研究而极大地丰富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由历史复杂性所提出,移开目的论的欧洲中心的历史学——现代性概念是其核心——之遗产投射在它们身上的阴影,那些复杂性大白于天下,但它也受解决概念反常的需要所激励。在我看来,抛弃它们的概念不会克服这种历史学造成的难题,我们必须同时仔细地考查在这一淘汰过程中的得失。通过给它们贴上“早期现代”的标签而把所有的欧亚社会都等同看待这是不够的,它有意无意地把更早与传统(以及其他类似的术语)联系起来。最终,几乎所有这些社会都与“前现代”牢牢地绑在一起,并且欧洲,或欧/美,仍然是现代以及历史的最终参照,过去和未来都是。如我前文主张的那样,重新命名的目标是打破这种联系,并为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思考现代性(以及欧洲)开辟道路。下一步是认识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那将为横跨同样重要的差异而使用一个术语提供合理性证明,术语实际上只是指各种特点的集合,它们把这些社会的现代性与它们先前各种各样的前现代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国例子中,把明同宋区分开来)。我在此采取的重新命名首要地试图把术语从其过去的联系中拯救出来,以便以新的历史计划成为可能。在其从“单一现代性”中脱颖而出之前,这些计划需要通过承认现代性之中差异和共同性来宣布。因此,在其所有不同历史轨迹之起点上得到理解的现代性(尽管由全球力量驱动),被地方性地体验为:欧洲现代、中国现代、印度现代等等,其他选择不是被由资本主义支持的欧洲现代性霸权消灭,就是被它们边缘化。这些早期其他选择的记忆在当前全球现代性条件下将为“别样现代性”提供鼓舞,不过它们今天将建立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22)。
不过,我主张的命名走得太远了,它不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命名。从一种对现代性的实体性理解到关系性理解,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同时要求把那些促成现代性的力量以及由不同力量领域暗示的不同空间性重新概念化。换句话来说,我们也需要克服根据欧洲现代史学的国家或文明单位来思考现代性的那种习惯,把注意力转向跨地区的力量,这些力量改变着这些单位最初形成的那种范围。
在上文中,我几乎没有讨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或不发达,这个话题一直让那些欧洲、北美、日本和中国学者着迷。由于采取了一种由欧/美资本主义宣布的历史目的论,那个问题在理解中国的时候提出了不少东西,但它同时也是理解历史差异的障碍,作为差异,它们远不是某种缺乏或失败。如盖里·哈米尔顿评论的那样,多数学者,从马克思和韦伯开始,试图理解的都不是其他社会而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23)。反讽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问题同样是用来解释失败而不是差异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同样力量领域在多样历史轨迹之中创造的可能性的承认,传达的正是这种最近才被学者们领悟到的差异的重要性。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以及同样不会得到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别样的现代性最终是否熄灭了,就如在黄宗智、尹懋可的著作中多少以不同的方式暗示的那样,它们最终因为自己的负担而坍塌了。不论他们的差异,这两位作者都同意:既存的生产方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只有少数征兆表明它们能够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匮乏背景下满足进一步增长的需求(24)。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仍然使下列问题悬而未决,如果中国未能成功地融入由欧洲现代性塑造的世界,那么接下来它将如何发展。
事后看来,这一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似乎已经在由这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几种发展轨迹中脱颖而出。“中国的别样性”对当代欧洲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因为其物质成就,而且因为它是一种反对宗教和专制统治遗产追求文化和政治现代性的可能模式。在此,关键就不是这些中国形象是否比它的负面形象更容易接受,那些负面形象也是存在的。重要的是,晚至18世纪,那些名字主要地与欧洲现代性价值(在这种情境中,启蒙运动)表达联系在一起的人,如莱布尼茨或伏尔泰,他们不只是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当代社会,而且是在多个方面比欧洲更先进的社会。同一个社会为突然出现的消费社会提供商品,这些商品无论真与假,都将成为其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满足新的异国情调渴望(25)。
只是随着18世纪明显出现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中国历史落入了资本主义元叙事,成为它的地方性叙事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从地区的国家的到地方的范围)。如果这看起来像是贬低中国历史(在那些认为它是“例外论”的人看来),那么值得强调的是,欧洲历史在这种元叙事中亦是一个地方化的版本,是资本全球化的空间形态之一,尽管它在现代性的产生之中扮演着霸权角色。而且,如我在上文解释的那样,上文引述的大部分著作都存在一个难题,克服欧洲中心主义仅仅滑入了中国中心主义,这是一个普遍的知识趋势,伴随着新一轮的“中国风格”的复兴。实际上帝国中国在现代性的政治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它也不是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唯一国家。我在上文做出的与明清发展有关的主张在同时代的其他帝国体系中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在它们随着欧洲中心的殖民现代性而步入衰落或屈从于殖民统治之前(26)。而且,相反地,19世纪武力“打开中国”之前很久,全球互动在帝国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形成中,并且或许稍弱一点,在政治和文化上,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有可能做出下述评论,晚期中华帝国史的最惊人的失败之一是明朝把领土与人口的巨大增长视为好像只是明史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而不是一种变革性的发展。当把这种发展和明朝与其外部世界“不可见的”关系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将强调明朝融入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重要性。
改正现代性不只是试图把其他社会视角带入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这只不过给正在出现的欧洲的中心性增加了一个维度,而维持了对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27)。另一方面,对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适当的强调,将会导致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忽视来自外部的力量塑造“中国”方式,同时抹杀了其他位于东亚与西欧之间的社会扮演的角色(28)。中国或许是这种“中心主义”转移的最恶劣例子,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其他的候补有“印度中心主义”和“伊斯兰中心主义”。把注意力从个别社会转移到它们的大陆(和跨大陆)语境,这强调了跨地区和跨文明力量的重要意义,那些力量推动了在现时代开端遍及欧亚的许多现代性的产生,形成了仍然在今天别样现代性主张中清晰可见的那种历史轨迹。
如果一定要形成一种对现代性的批评性历史理解,那么仅仅从欧洲现代性遗产中恢复它的过去是不够的。反对那种新传统主义也是有必要的,这种新传统主义试图在那些轨迹为自己在欧洲现代性熔炉中的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找一个伪装。不同于早期的别样现代性,当代全球现代性的替代方案不是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其中的另类,欧洲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法去掉的构成性组成部分。
这些倾向更尖锐的替代方案的特点并非微不足道,它们也不只具有学术价值。它们暗示着与单一历史轨迹中不同变量相对的不同历史轨迹之间的差异,欧洲现代性的霸权定义了前者。在现代性源点上的变迁的不同轨迹最终被欧洲现代性在全球的胜利边缘化了,甚至被消灭了,欧洲现代性谴责它们落后与停滞。在当前重新回忆它们不是要回到已经消逝的过去,而是把当代置于一种历史视角之中,那种视角远比欧洲现代史学想象出来的更为丰富和多样性。从这种霸权中把现代性作为概念和历史现象拯救出来,这是以不同方式思考现代性的绝对必要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要克服那些如我们所知的现代的最终危机,那么以不同方式来思考现代性是至关重要。
注释:
①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WW Norton & Co.,1990),p.xxiv.
②有一个讨论强调了Takeshi Hamashita著作的重要性,参阅Satoshi Ikeda,"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vs.The History of East-Southeast Asia",Review xix.1(Winter 1996):49-77这篇文章的观点,如Hamashita在自己著作一般讨论的那样,值得考虑,不过它对下述问题的质疑弱化了自己的论点:已经在东亚和东南亚活跃的欧洲人在这个时期承担着在这个地区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地之间的联系中介。
③布尔斯廷的《发现者》研究了这种知识的“疏忽”的一个方面,在那本书中,作者考察了地方知识在欧洲的世界知识创造过程中的运用。
④在此,我指出Janet Abu-Lughod创造性的著作,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对这种方法的完整发展可以在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市场和资本主义》(施康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三卷中的下述著作中发现。
⑤几个中国历史学家写的最近一本书主张,明朝不断增长的对中亚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方便,它导致中国政府放宽对动态的南方经济的控制。菲列宾人和马尼拉的大型帆船在这些经济交换中具有重要作用。参阅杨国桢等:《明清沿海社会和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导论。关于马尼拉大型帆船对明朝经济影响的保守估计,参阅Timothy Brook,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05-207.
⑥杨国桢等:《明清沿海社会和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⑦杨国桢等:《明清沿海社会和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同时参阅,Ho Ping-ti,The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for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new world" crops.
⑧关于明清的扩张,参阅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05).上述John Darwin的著作的第2章讨论了这一时期帝国体系在欧亚范围的扩张(包括奥特曼、莫卧儿和俄国),同时欧洲则通过商业和军事前哨最初采取一种“群岛”构型进行扩张。
⑨历史学家最近开始承认,尽管蒙古进行了掠夺,它们对俄国的入侵,但蒙古帝国在推动跨大陆交流方面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元朝(1275-1368)也为明朝的巩固准备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蒙古,参阅Morris Rossabi,Voyager from Xanadu:Rabban 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West(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2),这是作者同一主题许多著作的一本。关于元朝的重要意义,参阅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ed),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2003).
⑩关于这些发展,参阅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Alexander Woodside,Lost Modernities:China,Vietnam,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David Faure,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1)Robert B.Marks,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WI: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Chaps.1-2.See also,Sucheta Mazumdar,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Technology,and the World Marke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s.4-5,and the works by Elvin and Huang cited above,fn.13.
(12)在他的许多著作中,G.William Skinner已经分析了明清时期城市化和经济地区的构型,参阅"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s.1-3(1964-1965),pp.13-43,195-228,363-399.同时参阅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参阅Han Dacheng《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and,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and,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像陶希圣那样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取得发展归结为城市没有能够把自己从乡村“解放”出来。参阅德里克:《革命与历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双元经济的共谋或冲突,参阅Hill Gates,China's Motor: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3)Ho Ping-ti,"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130-168.对商业社会的兴起以及重商主义活动的最详尽的分析,参阅Timothy Brooks,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op.cit.同时参阅他的"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XXIV,Part Ⅱ(1981):165-214.关于商人与政治关系,参阅Ho-fung Hung,"Early Modernitie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Mid-Qing China,1740-1839",International Sociology,19.4(December 2004):478-503.
(14)Gary G.Hamilton,"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s in 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1.1(1985):187-211.
(15)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载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212页。同时参阅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关于“非国家”儒生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参阅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日常生活水平的交换,参阅,S.A.M.Adshead,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1400-180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16)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w(ed),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关于这种文学在东亚的影响,参阅Claudine Salmon,Literary Migrations: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17th-20th Centuries(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7).
(17)Timothy Brook,"Edifying Knowledge:The Building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17.1(1996):93-119.
(18)根据最近研究,满族统治的巩固之后便是清朝向贸易的“开放”。参阅Gang Zhao,"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or the Global Integration):Maritime Policies in 1684-1757",ms.
(19)关于这个时期清的扩张,参阅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以及 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op.cit.For Southwest China,see,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有趣的是,当代帝国话语也包括这些新近的融入“中国”的地区,至那时为止,“中国”都用为表示长城以南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Gang Zhao,"Reinventing China: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odern China,32.1(January 2006):3-30.
(20)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Verso,1994).
(21)Richard Von Glahn,"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1500-1800",in Dennis O.Flynn,Arturo Gira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ed),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1470-1800(V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2003),pp.187-205,p.201.关于“勤劳革命”,参阅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4.2(1994):249-271.
(22)有关“国家体系”的最新研究,参阅Ravi A.Palat,"Power Pursuit:Interstate Systems in Asia",经作者同意引用的未出版论文。
(23)Gary Hamilton,"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op.cit.
(24)参阅注释13关于基于与日本对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发展观的不同视角,参阅Kaoru Sugihara,"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Paper presented to the 13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Buenos Aires,26 July 2002.
(25)参阅,Gunther Lottes,"China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1750-1850",in Thomas H.C.Lee,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1),pp.65-98; D.E.Mungello,The Great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1500-1800(Boulder,CO: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5); Adrian Hsia,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8); and Dawn Jacobson,Chinoiserie(London:Phaidon Press,1999).
(26)参阅John F.Richards,The Mughal Empir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especially,chap.9; John F.Richards,"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op.cit.; David Washbrook,"Indi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conomy:Modes of Production,Reproduction and Exchange",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7):87-111; Kate Currie,"The Development of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Mughal India",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4.1(1982):16-24; and,Halil Inalcik,with Donald Quataert,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14(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especially chapter 17.在此顺便一提的是德顺幕府时期的日本,在全部主要的亚洲政治体系中,它作为日本现代化序幕已经引起很多的注意。
(27)在John Darwin的After Tamerlane一书中是相当明显的,这本书可说是“新瓶装陈酒”,但它也在某种意义上是弗兰克、王国斌和彭慕兰有关著作的延伸。
(28)例如,有关伊斯兰的讨论,参阅Darwin的After Tamerlane第二章。
标签:现代性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全球帝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