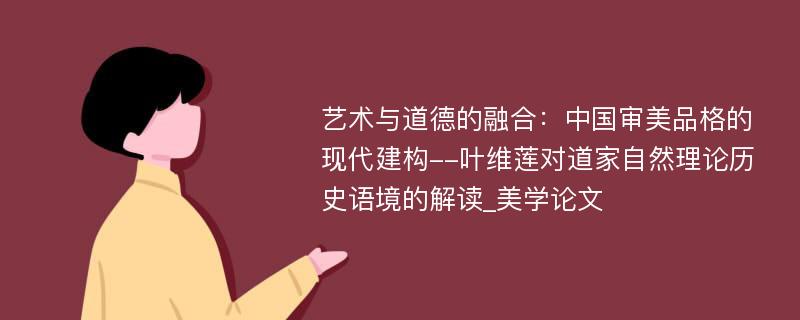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道家论文,品格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美学的自然品格,是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与其他学者相比最为执著的美学理念。之所以用“自然”来定位叶维廉的中国美学理念,在于叶氏并没有认同道家极具玄虚意味的“道”,而向往其物我无碍自由兴现的自然境地。这两者的分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言:“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对于后者,即庄子的自然论,叶维廉曾关注“道家在主客离合上不落名义的独特视野”①,并认为道家“大体上是要以宇宙现象未受理念歪曲的直现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示宇宙现象。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求自然得天趣是也”②。由此,叶维廉对中国美学品格的定位也正在于“自然”。
一、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
叶维廉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认同有三个来源,一是道家的自然论,二是玄学家郭象的崇有论,三是禅宗的异常论。其中,道家的自然论是叶维廉倾力最多的地方。述其概要,共有两端:
一是道家美学观物态度的自然论。叶维廉认为,由于对人和语言的限制性的认识,即人知力无法概括所有的事件同时发生共存的整体,因而对人、知力和语言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感,“这一个对人、宇宙万物和语言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道家影响下中国美学诗学的据点。”道家美学是反概念、反名制、反意识、反语言的,这决定了道家美学所具有的反知识论的基本品质。③叶维廉还用现代词汇“直觉”阐释道家的这一观物态度,认为“以物观物”这个反概念、反名制、反意识、反语言的境界,是一个信赖“最初直觉”的境界,“我们张目一看,我们看到万物,或是万物呈现在我们眼前,透明、具体、真实、自然自足”。④而西方哲学正因为“不能信赖他们接触万物时对万物之为万物的最初直觉,不信赖他们作为一个在未求解状态前的自然反应”,执著于“对所谓真理的追逐”,所以偏离了事物的本真。
二是道家美学由此所呈现的现象世界。叶维廉认为,中国诗人“倾向于将多层透视下多层联系的物象和它们并发性的兴发以戏剧的方式呈演出来,不将之套入先定的思维系统和结构里”⑤。由此,中国诗歌所呈现的山水是透明、自足、灵动的,这来源于道家美学的观物态度,“道家的美学大体上是要以自然现象未受理念歪曲地涌发呈现的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现自然,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求自然得天趣是也”⑥。中国诗人移入万物而无碍地遨游,对宇宙现象里活泼泼地涌现的山水作凝注,正出于“以物观物”的态度。形诸于诗,正如他在解读王维、柳宗元的诗歌时所言“每一物象展露出其原有的时空的关系,明彻如画”,“清、幽、明、快、静、动、远、近而直逗物象最鲜明的兴现”。⑦中国山水诗明彻如画的意味正来自诗人虚怀纳物的心境。
郭象的崇有论是对庄子自然论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叶维廉认为,“郭象对道家思想中兴的最大贡献,是肯定和澄清了庄子‘道无所不在’,道是‘自本自根’的观念”⑧,“这个肯定使中国的运思和表达心态,完全不为形而上的问题而困惑,所以能物物无碍、事事无碍自由兴现”⑨,郭象对中国美学形而下品格的影响,正如叶维廉说所说,晋宋间山水意识的兴起“最核心的原动力是道家哲学的中兴。在当时,王弼注的老子,郭象注的南华真经,都是清谈的中心题旨,尤其是郭注的庄子,影响最大,其观点直透兰亭诗人,达于谢灵运,及与兰亭诗人过从甚密的僧人支遁。郭象注的南华真经不仅使庄子的现象哲理成为中世纪的思维的经纬,而且经过其通透的诠释,给创作提供了新的起点”⑩。在叶维廉看来,“由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经晋宋的‘山水是道’(孙焯),到宋朝的‘目击道存’(宋人袭用庄子而成的批评术语)乃至理学家邵雍由老子引发出来的‘以物观物’,无一不是中国传统生活、思想、艺术风范的反映”(11)。
禅宗与道家美学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观物方式有着一致之处。叶维廉认为:“禅宗公案中所使用的‘异常’策略——包括特异的逻辑,用攻人未防的字句、故事与特技,以戏谑来突破知限,以越常理而使我们跳离字义,以惑作解——都与庄子有一定的血缘。”(12)“道家,禅宗,除了提供一些消解距离、消解语言中的连接媒介、虚位、换位等手法去逗现无以无状的道之外,都用了语言,而都用了戏剧性的寓言与公案和它特异的逻辑来突破知限,突入一种奇特的知之中。”(13)在叶维廉看来,禅宗常常用高度的诗句答结语,像“春来草自青”这样的回答正是自然之律和自然之道,但见活泼泼的生机。
叶维廉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描述是对中国美学精神价值的肯定。在世界文化的对比中思考中国美学的特殊性,以这种特殊性抵御现代性进程中文化生态趋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叶维廉始终相信中国文化是解除这一危机的一条有效途径。叶维廉认为道家美学代表着中国的美学风范,并以此与西方形成显著差异。(14)
他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眷恋,来自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和批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为透视中国美学的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角,而分析中国美学的观感方式和表达系统,这种寻根探本式的解读,为他重新发现中国美学精神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这说明文化交流不是用一个既定的形态去征服另一个文化形态,这种互比、互照和互识一方面突出了中国美学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为重建新的美感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自然:直觉·现象·经验
《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制器者尚其象”。这里,玄虚的阴阳之义谓之“道”,有形的卦画谓之“器”。可见,器是体现道的,道与器合二为一。《系辞》:“易也者象也。”根据胡适的考证,这里“象”通“相”,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模型而成的。“《易经》的象字是法象之意(法象即是模范)”,“先有一种法象,然后有仿效这法象而成的物类”(15)。
中国哲学道与器不即不离的关系,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柏拉图意义上的纯粹理念在中国哲学中并不适用。器即现象,法象之物象,这都显示了经验层面的含义。而中国哲学最给人以启示者,正在于其道器不分的品质。这也正是叶维廉以直观(直觉)阐释道家美学的根本原因。而以直观阐释道家美学,正是20世纪以来,道家美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核心。
受康德哲学影响,王国维以直观为知识的来源。(16)王国维说:“真正之新知识,必不可不由直观之知识,即经验之知识中得之。”(17)王国维把理性摆在了高于直观的地位,认为理性是知力作用中之最高者,是人区别于动物所独有的知识形式,他说:“夫吾人之知识,分为二种:一直观的知识、一概念的知识也。直观的知识,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直观的知识,人与动物共之;概念之知识,则唯人类所独有。”(18)王国维说:“若直观之知识,乃最确实之知识,而概念者,仅为知识之记忆传达之用,不能由此而得新知识。真正之新知识,必不可不由直观之知识,即经验之知识中得之”(19),王国把“直观”摆在了超越理性的第一位,又从知识论的角度承认理性之于人类的意义。
其次,是作为艺术特质的直观。王国维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在于能够唤起直观。“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而无概念杂乎其间,故叔氏之视美术也,尤重于科学。……如建筑、雕刻、图书、音乐等,皆呈于吾人耳目者。唯诗歌一道,虽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与否。”(20)艺术的价值正在于通过直观唤起人的真切感受,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
对于作为艺术特质的直观与情感的关系,王国维说:“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21)激烈之情感,亦为直观之对象,是因为在艺术中认识的主体不再是个体,而是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主体的自身意识,而对象也不再是个别事物,而是事物的总类。因此,物我能够超然于利害。在王国维看来,直观和情感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一对,知识、情感和意志在天才那儿得到了统一,它们的统一造就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和作品不同的审美特征。
1934年,郭绍虞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谓:“庄子所谓听以气云者,即是直觉。盖庄子之所欲探讨而认识者,即庄子之所谓‘道’。道是宇宙的本体而非宇宙的现象。明宇宙的现象须后天的经验之知,故是常识所能辨别的;明宇宙的本体贵先天的性知,所以是超常识的。”(22)郭氏以先天之知与经验之知作为区分本体与现象的特征;先天之知是绝对和独立的,所以是排斥经验的。很明显,郭氏是以康德的先验之知与经验之知这一对范围阐释道家的。(23)在郭氏看来,神遇的境界正是超越了耳听目视的感觉而达到了与道合一。郭绍虞强调庄子对直觉的重视,但他却以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阐释道家。“听之以气”既然是“直觉”,那么显然是走向了经验;但郭绍虞口风一转,在谈到庄子的“神遇”时说,“这个和他的名学有关,因为他的知识论立言高远,富于神秘的色彩。他所重的知识是性知,是先天之知。这先天之知,是不用经验,不以触受想思知的”(24),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直觉和先天之知,显然是不能对接的。“听之以气”是直觉,但“道”却是先天的性知,郭绍虞却认为两者能够对接;但两者之间如何进行沟通,郭绍虞并未进行学理上的探讨。
前述王国维和郭绍虞所谓“直观”分别有着理性和形而上的内涵。与此不同,叶维廉认为直觉重具体经验,具有反知识论的基本品质。道家美学反概念、反知识的境界,是一个信赖“最初直觉”的境界,“我们张目一看,我们看到万物,或是万物呈现在我们眼前,透明、具体、真实、自然自足”。(25)道家美学从“最直接的经验开始”,所以能够摆脱知识架构的纠缠。而西方哲学正因为“不能信赖他们接触万物时对万物之为万物的最初直觉,不信赖他们作为一个在未求解状态前的自然反应”,执著于“对所谓真理的追逐”,所以偏离了事物的本真。显然,叶维廉有着更为彻底的经验倾向。正如他在评价中国诗时所言:“显然地,中国诗要显露的是具体的经验。何谓具体经验?‘具体经验’就是未受知性的干扰的经验。所谓‘知性’,如上面先后指出的,就是语言中理性化的元素,使具体的事物变为抽象的概念的思维程序”(26)。在《严羽与宋人诗论》一文中,叶维廉更进一步解释说:苏东坡“在创作上,对虚静的强调,所谓心斋,所谓坐忘,都是源出于庄子所要求的去知得真或返朴归真的主张,亦即冯有兰借用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语所发挥的‘纯粹经验’,亦即我另文中提及的具体经验”,“所谓纯粹经验,即无知识的经验,在有纯经验之际,经验者,对于所经验,只觉其是‘如此’,不知其是‘什么’。……庄学所说之无知,乃经过知之阶段,实即知与原始的无知之合是也。此无知经过知之阶段,与原始的无知不同,对于纯粹经验,亦应作此分别。如小儿初生,有经验而无知识,其经验为纯粹经验,此乃原始的纯粹经验也。经过有知识的经验,再得纯粹经验,此再得者,已比原始的纯粹经验高一级。从这个道家的哲学观来看,如要直取具体世界或自然本身,必需去知性的、抽象的思维干扰,虚怀纳物。”(27)“具体经验”、“纯粹经验”正是叶维廉所谓“直观”的内涵。
叶维廉以“直觉”、“现象”和“经验”阐释道家的观物方式和美感经验,并以此作为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异质性,所欲突出的正是道家美学的自然品格。
三、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现代美学进程中,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和刘若愚等美学家的一个共同话题是,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成为了一个参照,中国美学也因这一参照得到了新的阐释,并产生了新的意义。通过对西方形而上理论的思考和批判发现中国美学的现代价值,这是中西思想比较和碰撞的结果。
1928年至1930年间,宗白华写作《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认为中国哲学乃“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在阐释中国美学的形而上品格时所言:器为载道之象,“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也”(28)。宗白华认为,形上学之两大体系为唯理的体系与生命的体系,“中国哲学家对古宗教仪式,礼乐,欲阐发其‘意’,于其中显示其形上(天地)境界。于形下之器,体会其形上之道。于‘文章’显示‘性与天道’。故哲学不欲与宗教艺术(六艺)分道破裂。‘仁者乐道,智者乐道。’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29)。宗白华认为形上之道与形下人生的融合,使得中国美学终结于生命化的宇宙而非理化的宇宙。
1965年,徐复观写作《中国艺术精神》时意识到,“庄子的本意只着眼到人生,而根本无心于艺术。他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乃直接由人格中所流出,吸此一精神之流的大文学家、大绘画家,其作品也是直接由其人格中所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所以,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庄子之所谓道,有时也是就具体地艺术活动中升华上去的”。他对中国思想“是否要借助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感到非常怀疑,对于熊十力等师友建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把孔子的思想,安放在希腊哲学系统的格式中加以解释,使其坐上形而上的高位,这较之续凫胫之短、断鹤胫之长,尤为不合理。因为凡是形而上的东西,就是可以观想而不能实行的。”(30)唐君毅认为对中国思想的形而上学建构只能使我们离古代思想越来越远,甚至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徐复观并未将孔子、庄子纳入康德或者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予以阐释。他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完全按照西方美学方式阐释中国美学的路径,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学术问题的具体情况。
另一位新儒学的代表唐君毅认为中国的艺术批评是哲学的艺术批评。在《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一文中,他说:“艺术精神融摄内心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而使人于外界中看见自己之内心,于物质中透视精神,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而中国主要哲学儒家哲学之内容正在合内外之道,和融精神物质之差别相,于形色中见性天,即形下之器以明形上之道。中国的道家哲学亦以道为无的不在,而不以之为超越,要人于蝼蚁梯稗中见生天地之原理。儒道二家正是最含艺术性的哲学学说。”(31)针对新儒家对道德良知的推崇,当代学者傅伟勋认为“由于当代新儒家为了应付尊重‘知性探求’独立自主性的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强烈挑战,而被迫谋求儒家思想的自我转折与充实(决非所谓‘自我坎陷’)的思维结果,仍不过是张之洞以来带有华夏优越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老论调的一种现代式翻版而已,仍突破不了泛道德主义的知识论框架。”(32)傅伟勋强调要正视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难题,创建出合乎现代化进程的知识论方法。
1965年,刘若愚在写作《中国文学理论》时,认识到了从事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困难,“来自有些中国批评家习惯上使用极为诗意的语言所表现的,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直觉的感性;这种直觉的感性,在本质上无法明确定义”(33)。尽管承认中国文学批评“直觉”的感性,刘若愚却对“形而上理论”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在对中国文论归类时,他将“形而上学理论”(即描述宇宙与作者关系性质的理论)列为首位。认为“这些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可能来自这些理论”。(34)刘若愚对形上理论中作为宇宙原理“道”的起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受道家老子和庄子关于直观自然以及与道合一的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和艺术批评中,完美的直觉的艺术作品那几乎是无须力求,自然而然的,通常称为“神”。(35)刘若愚认为庄子之“‘虚’(emptiness)也表示从心中除去理性的知识这种观念”(36)。刘若愚同意郭绍虞的看法,认为庄子所谓“听之以气”是直觉的认识,但他认为这种直觉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专心致志和自我修养才能获得的,而从有意识地致力于观照自然转到与“道”的直觉合一,这是形而上理论与西方摹仿理论的显著区别。
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和刘若愚在阐释中国艺术精神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道的形而上品格与形而下显现,而以艺术体验为与道合一的通途。(37)道所蕴含的这种体验特质,也吻合了中国美学家对“道”所持有的美育期待。如徐复观就认为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他向往“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38)。“直觉”在康德那里虽有着形而上意义,且这一意义在王国维和郭绍虞的引用中得到延续;但“直觉”的形而上意义却在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和叶维廉等人的美学建构中被过滤了。
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的现代价值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线索。宗白华等人对西方形而上理论的怀疑和否定反倒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国美学的特质——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性为特征。中国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并非是在追问终极,而是在弥纶物我融合道器。物显露着法象,也显露着真实;其间并不存在原本与现象的差别。无论是《周易》、《庄子》,甚至是儒家,“道”可视可触的直觉体验色彩都为它赋予了非常富有艺术意味的特质。以生命精神消解唯理倾向,以艺术精神消解形而上学,以形下之器消解形上之道,以直观消解玄虚,这是上述美学家在谈形而上学时的一个共同倾向。“道”玄虚的一面被淡化和隐匿,经验的一面被彰显和称颂。从比较发现中国美学独特的人文价值和现代意义,这是文化认同矛盾的最终解决。
四、结语
西方形而上学在古希腊柏拉图时代成为了真理确定性的最高典范。依照形而上学的看法,个人生命的极致,就在于突破时间、空间、现象、感觉和经验的限制,进行到真理的永恒世界。难怪柏拉图认为诗人偏执于激情,是误国误民的大敌。哲学与文学的这种僵持关系,也以文学的屈尊而获得暂时的平衡。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追求柏拉图传统的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倾向达到了极致。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开始认为,哲学不再能为科学奠基,哲学的作用应该局限在对科学进行检查和理解,或者对它的前提假设进行批判。源于古希腊终于黑格尔的这场争论似乎已经见出了分晓,形而上学似乎被永远地贬到偏远的冷宫。
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身上承担了如此多的宿敌——与文学,与科学。这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寻找“爱智慧”的意义时无法预料的。在形而上学疲软之际,似乎到了文学应该浮出水面的时候。对经验、感觉和个人独特性的认识,使得人们对文学进行了重新的观照。难怪尼采放弃了任何对“唯一”的思乡病而坚持对世界的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相信唯有诗人才能真正体悟到本真。哲学的困境,正如理查得·罗蒂所言:“在哲学与诗的古老争辩中,如果诗获得胜利——‘自我创造’隐喻最终胜过了‘发现’隐喻,那是因为我们终于俯首相信,这是面对世界时,人类所能期望拥有的唯一力量。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坚持,真理——不仅力量和痛楚——必须在‘那儿’等着被发现。”(39)
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如此诡异。既不能为科学奠基,也无力与文学抗衡,哲学成了这个时代的众矢之的。哲学的负伤,意味着形而上学这样的信念再也经不起推敲。但我们仍旧难以走出传统哲学的阴影,难怪柯拉夫斯基在他那本《形而上学的恐怖》中会说:“今天,没有人在心灵和宇宙中寻找那种不可动摇的确定性之难以理解的圣怀,人们普遍设想,在探索‘我思’中的所有发现——不管是胡塞尔印象非常清晰的洞察力,还是维也纳学派的记录命题——都变成了假的。我们无法返回到前文化的、前语言的、前历史的——就是说前历史的——在认识上的无知。我们仍然在继续运用我们哲学习语来描述它。”(40)这种前文化的、前语言的、前历史的无知,似乎正是道家的精髓。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对于道家自然品格的推崇与对于形而上学的诟病,巧妙地汇合成为一个文化立场。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其背后有一个普遍主义的预设,即西方哲学以形而上学为核心,中国思想则道器不分。
在现代语境中,奢谈形而上学问题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而中国古代经典中可以找到如此多的基因与诸如理性、体系、中心这样的观念相比较和抗衡。这正如西方哲学内部,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对胡塞尔先验论现象学的扬弃,实则因为海德格尔并没有从理性和先验这些抽象的秩序出发来解释“活生生的此在”,从而脱离了胡塞尔理性主义的纠缠。形而上学的困境正来自西方现代哲学的反思与东方哲学的参照。
在现代性焦虑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美学家们以“艺道合一”为中国美学精神的归依,正出于民族认同心理的一种想象。道家美学以非形而上学的自然品格出现,它所充任的正是这种非西方的文化形象。道家美学也是以这样一个异质性的文化角色在西方世界出场的,这也正是它被人视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原因。(41)而新儒家以良知替代知性的理论建构,显然是为了从正面回避中国哲学知性探究上的缺失,通过心界与外界的双重道德化,抬高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最高哲学原理。现代新道家和新儒家们最终殊途同归——以艺术精神和道德良知化解哲学知性。
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和与经验主义的较量一直催生着新的哲学思想;而在东西哲学比较中,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碰撞又提供了有趣的话题。饶有意味的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现代性语境中,这种较量和碰撞竟被悄然化解——即以形而上学一元论替代西方哲学整体,以经验主义一元论替代中国思想整体,将思考对象限定为封闭的体系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正如萧驰所言,西方人对中国从语言到文化、历史观的种种偏见,无一不是出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然在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照下,“中国进入话语最经常是作为本质化西方的反面(countercase)”,此两极图式(polar schemes)的流行总令我们试图重建反命题的历史现象和寻找使此现象不言而喻地存在的共同基础,结果是“问题不仅在削华夏之足以合泰西之履,甚至亦有为彰显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对比而忽视中国传统本身历史脉络的问题。”(42)而以自然品格(经验、现象、直观)化解中国哲学内部、西方哲学内部、中西哲学之间的复杂性,往往将问题趋于单一化。结果就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处境,一方面我们似乎身处非形而上学的传统和优势,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逃脱与形而上学的比对和纠结。
注释:
①叶维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叶维廉文集》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②叶维廉:《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叶维廉文集》壹,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③⑤⑥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贰,第127、133、133页。
④(12)(13)叶维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叶维廉文集》贰,第148、175、177页。
⑦⑧⑨⑩(11)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叶维廉文集》壹,第185、178、179、176、175页。
(14)叶维廉:《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叶维廉文集》壹,第121页。
(1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16)康德拒绝任何既不是在经验中被给予又不是与经验有关的知识。根据康德,所有知识毫无疑问都是从经验开始的,正如他所言,一切思维都与直观相关,都与感性相关,对象与思维的关系由此发生。其中感觉与对象相关之直观,名为经验的直观(empirical intuition)。除去经验直观之表象,先天地存于心中的感知方式,即空间与时间,称为纯粹直观(intuition)。康德既承认了经验直接性,又预设了时空之先验性。
(17)(18)(20)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1、46页。
(18)王国维:《释理》,《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22页。
(21)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44页。
(2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38页。
(23)在康德看来,虽然经验直观是认识的开始,但它得通过先天的直观方式——空间和时间处理经验直观的内容。而这先天的直观是不依赖于经验而独立的。康德在经验和先天、现象和物自体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2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页。
(25)叶维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叶维廉文集》贰,第148页。
(26)叶维廉:《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叶维廉文集》壹,第72页。
(27)叶维廉:《严羽与宋人诗论》,《叶维廉文集》叁,第131页。
(28)(29)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宗白华全集》壹,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11、586页。
(30)徐复观:《向孔子的性格回归》,《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3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47-48页。
(32)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48页。
(33)(34)(36)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8-9、56页。
(35)刘若愚之所以用“形而上学”来描述庄子的大义,是因为“庄子用‘气’和‘神’这两者所表示的是‘精神’,或一个人借以了悟‘道’的那种直觉的、超理性的能力。而当一个人达到这种直觉了悟的境界时,庄子称之为‘神人’,或‘真人’,或‘圣人’……如此,庄子对‘气’的概念是形而上的”。(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58-59页。)
(37)如徐复观就曾言:“西方由康德所建立的美学,及尔后许多的美学家,很少是实际地艺术家。而西方艺术家所开辟的精神境界,就我目前的了解,常和美学家所开辟出的艺术精神,实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则常可以发现在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身上,美学与艺术创作,是合而为一的。”(《中国艺术精神》自序,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页。)
(3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39)[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0页。
(40)[英]柯拉柯夫斯:《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74页。
(41)1974年,罗兰·巴特身临中国,参观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诸地,凡三周。后作《中国怎么回事?》,他以为中国是散发着道家气息的,“中国是单调的,田畴平阔,无中国画常见的峻岭瘦石,望去,小国寡民的自在之境,宛然在目。……中国文化是散文化的,政治芒刺而外,人们无做作,无骚动,无歇斯底里。”([法]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页。)
(42)[新加坡]萧驰:《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对时下中国传统诗学研究四观念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标签:美学论文; 道家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国学论文;
